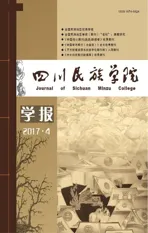汉法翻译中的中国旅游文化不可译性
2017-04-12秦琼芳
秦琼芳
★翻译研究★
汉法翻译中的中国旅游文化不可译性
秦琼芳
卡特福特在讨论可译性限度时,把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这为翻译理论在语言学的角度开拓了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也对极具文化性的旅游翻译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翻译思路。中国是法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大国,法国游客都希望能在中国进行深度的文化旅游。文章从中法文化差异着手,选取法国人感兴趣的几个文化现象来分析旅游法语翻译中的文化不可译性,并尝试研究其补偿方案。
旅游法语;文化信息;不可译性
一、引言
在1965年出版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J.C.卡特福特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不可译性的存在。他认为,从翻译等值来看,如果目的语的语境并不能与源语的语境特征功能相关,翻译就算失败,即产生了不可译性。而从广义上来讲,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语言不可译性是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差异,源语文本中的一些语法或词汇特征,涉及到语音、语义、语形等各方面,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等值成分,即是语言不可译。同时他也指出,源语与目的语的等值对应只是形式上而言,而这种对应本身就比较少见。所以语言的不可译性可以视为“绝对”不可译。而文化不可译性,就是在源语语境特征中的文化现象词汇并不存在于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这就像是在目的语中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这种就叫文化不可译。相比“绝对”的语言不可译性而言,文化不可译显得“相对”化,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翻译策略尽可能地实现翻译中的等值效应。由此可见,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非指可能翻译或不可能翻译的意思,两者是可译性的限度问题,即可译度,翻译到什么程度的问题。[1]63-69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对于翻译实践活动有着方向性的理论指导作用。本文主要着力于对旅游法语中的文化信息翻译的不可译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二、旅游法语翻译中不可译的文化信息
涉外旅游翻译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口译与笔译,即导游陪同口译及外宣材料的翻译。两种工作形式涉及到口语语体与笔语语体,但是不管形式如何,都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众所周知,文化因素在旅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于是乎涉外旅游翻译完全可以称之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汉朝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国文化就开始大放异彩,数千年来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历史和文化。而在当今社会,由于国际间交流的通畅,中国文化的传播更加迅速,影响也更广泛。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中国投资、贸易、定居和旅游。如旅游方面,法国人就认为文化旅游比自然或人文风光旅游更令人感兴趣,因此他们会选择了解中国的儒学、老庄哲学或易学,也会如痴如迷地欣赏京剧等传统艺术表演,甚至会学习中国书法和烹饪中国菜肴。法国游客愿意参与中国居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他们也急切想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趣味、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因此在旅游的途中,涉外导游担负着陪同、讲解和翻译的重任,他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宣传中国的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由此可见旅游翻译的重要性。涉外导游不仅需要有两种语言(汉语—法语)之间相互转换的能力,还必须了解并熟知相关的中国文化。而在旅游法语翻译中,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一些不可译的文化因素是极为常见的。以下便选择了法国游客对中国文化最感兴趣的几个方面来分析旅游法语中不可译的文化现象:
(一)民族节日文化
西方国家的节日极大部分直接源于宗教或受宗教的影响。如法国主要的宗教节日有封斋节Le Mardi Gras、复活节Le Paques、万圣节La Toussaint、圣诞节Le Noёl等,其他一些节日或假日(即法定不工作的日子)也一般来自天主教,体现了“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的民族节日,尤其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多数与宗教无关,而是受到农业生产、天文历法、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等影响,体现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或是“人和事(农事)”的关系。[2]366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当旅途中遇到中国人欢庆节日的场面,法国游客总是十分兴趣盎然,一副想一探究竟的模样。如清明节,俗称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在法国与之相类似的节日就是万圣节,在这一天,法国人会带上鲜花去逝去的亲人与朋友的墓前祈祷。而在中国,清明节的传统习俗有祭扫、祭拜、踏青、放风筝等,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悲伤又高兴的节日,悲伤是在缅怀逝去的亲人,高兴是在春天,万物苏醒,景色迷人。但是由于两国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的差异,便会产生文化的不对等性,这些类型的节日习俗并不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搭配,或者说,在目的语文化中并没有相对等的习俗,所以是“不可译”现象。但是这种“不可译”现象是相对而言的,并非绝对。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它的句法、语义信息集中体现在“意合”之中,以达意为宗旨。在汉语中的“祭扫”、“祭拜”和“踏青”用词简洁,仅仅两个字就包括了许多的动作,如祭扫,就是准备一些祭品如鲜花、水果等到墓前祭奠亡灵,并且还要打扫坟墓,如清洁和拔草等。“祭扫”和“祭拜”等词语中也蕴含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而在实践翻译中,可以把这些存在于特定语境下的文化现象选择近似的翻译等值成分,把该动作描述出来,让游客领会。如:
祭扫:nettoyer la tombe et offrir des aliments, un bouquet de fleurs et quellques objets qui plaisent au défunt de son vivant
祭拜:bruler des papiers et se recueillir et s’incliner devant le défunt
踏青:avoir une sortie au printemps
放风筝:jouer au cerf-volant
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对这种语言之中的文化信息进行了归纳,分别为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声象化符号;民族社会化符号;民族地域化符号及民族物质化符号。由于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广泛共性及渗透性,此五种文化信息符号在双语转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译的”,可以在双语中找到契合对应或平行对应。[3]130-131
(二)社会风俗文化
古语曾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呈现出该民族的心理、志趣、信仰和历史发展。[2]326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有几个特点,其一为积久性,由于历史悠久,任何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莫不是经过了时间的积淀;其二为多元性,多民族多区域形成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涉及到喜恶、禁忌、崇拜等;其三为相融性,在几千年的风俗文化形成过程中,其他民族或多或少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汉民族文化所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影响性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得以长期和睦相处的保证。[2]329-329社会风俗文化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穿衣戴帽、一日三餐、婚俗与葬礼、祖宗祭祀、民间崇拜与禁忌等。如传统婚礼,从周朝开始规定婚嫁就必须行“三书”、“六礼”,“三书”分别为聘书、礼书、迎书;“六礼”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这些属于“文化盲点”现象,即是说,中法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法国游客在特定的语境中无法获得相关的文化信息,他们作为语言的接受者并不能将“言语意义”与“语境信息”联系起来,故而会发生语义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音译+注释”的方法进行翻译补偿,使游客充分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
三书:聘书(pinshu: le livre de fianc ailles)、礼书(lishu:le livre des cadeaux)、迎书(yingshu: le livre utilisé le jour des noces)
六礼:纳采(nacai: demander un mariage)、问名(wenming:demander le nom et la date de naissance de la fille)、纳吉(naji: vérifier un bon mariage)、纳征(nazheng:offrir des cadeaux à la famille de la fille et en retour)、请期(qingqi : choisir un jour propice pour la noce)、亲迎(qinying:l’accueil de la fiancée)
又如,“洞房”、“洞房花烛”等词的翻译,可以说这些是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的民族社会化符号。[3]131在翻译过程中这种文化信息词的内涵容易产生遗漏。关于“洞房”一词的由来有许多的版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词来自祖先们的洞穴式的居住方式。如果把“洞房”译为“la chambre nuptiale”或“la chambre de mariés”,那么就失去了“洞房”的民族社会化符号,只是“新房”的意思,但是如果译为“la grotte-chambre”,法国游客便会不知所云:难道岩洞跟结婚有关系吗?同样的,把“洞房花烛”简单译为“la nuit de noce”,便失去了词语原本的美好意象,对于可译性的限度而言,这是找到了双语语际之间交换的信息通道,但是在目的语中并没有获得对应。
(三)饮食文化
鉴于中国菜是东方菜肴的代表,法国菜是西方菜肴的代表,两者都是世界三大烹饪(另一是土耳其菜,代表伊斯兰菜),又由于“吃”在旅游途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单独列出饮食文化,试图从饮食的文化差异来讨论中译法的不可译性案例。无论是中国菜还是法国菜,都是“美的活动”,区别在于法国菜倾向营养学角度,考虑菜肴的结构和食品的成分,而中国菜侧重于艺术学,讲究色香味形。[2]335在中国的旅游过程中,法国游客发现他们所享用的中国菜与他们在法国所品尝过的大不相同,于是疑惑就开始了,从烹饪手法、调料、食材、食品功用等方面都是他们提问的要点。如对食物名称的法译。中国南方人有食田螺的风俗,广西桂林阳朔还有一道名菜叫田螺酿,那么“田螺”译为法语时一般会译为“escargot(蜗牛)”,而不是“paludine(田螺)”,这又是怎么回事?Paludine在法语中的解释是“淡水中的一种胎生的腹足纲软体动物,其外壳与蜗牛类似”。而其实“蜗牛”和“田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是“paludine(田螺)”这个词对普通法国游客而言相当陌生,一是他们没怎么见过田螺,二是他们也不吃田螺。于是在旅游翻译中介绍“田螺”时,便会使用文化替换词(cultural substitution),实现在一定语境中的语言杂合。也就是说,法国人喜欢吃蜗牛,所以用escargot来替换paludine,这样虽然在语义上有一定的缺失,但是普通的法国游客都会接受这一食物概念,虽然他们知道中国和法国的escargot是不一样的。
无独有偶,对于“木耳”的法译也是如此。字典中对于木耳的翻译有几个,首先,auricularia(“木耳”的拉丁名词)和trémelle(从拉丁名词tremella演变而来)这两个词都是“木耳”的意思,但是在法国民众之中的普及度不高,这也跟法国人没见过“木耳”这一物品有极大的关系;其次,fongus是医学用语,有的词典里标注为“木耳”,其实应该为“蕈状的赘生物”,这让人一听会联想到肿瘤,而“木耳”是可食用的美味的山珍,这样的译法会让人大倒胃口。于是也选用了一个文化替换词:champignon(蘑菇),这样游客就会接受。而其实在法国的中餐馆的菜单上,就是用champignon noir(黑色的蘑菇)来表示“木耳”。这种语言上的杂合应当列为“归化”的一种,在旅游翻译中常会碰到此类译法,如:苏州——东方威尼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在翻译效果立现的旅游翻译中,这种译法是十分可行的,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提高客人的文化接受度。
(四)汉字文化
汉字是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活化石。方形结构的汉字,加上变幻莫测而又不失优美的线条变化,形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自踏上中国之日起,目之所及都能看到汉字,从西安的碑林到桂林的摩崖石刻,法国游客对汉字文化赞叹不已,甚至于有些团队还会在旅游途中专门设置一门“书法课”,让法国游客亲自挥毫泼墨,感受汉字的魅力。
汉字讲究造型美,注意字形的结构平衡,线条流畅,主次分明,虚实相间,刚柔并济。对于涉外导游陪同而言,介绍中国汉字结构及落笔笔划的一撇一捺部分是比较轻松的,而谈到字源时,由于中国汉字的特殊性,又加上译者本身的文化水平所限,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客人在剧场进出时看到“入口”、“出口”等字样,有时便会询问这个“口”是什么意思?当然可以回答“口”便是“嘴巴”,也指出入通过的地方,如“关口”、“港口”等。而从“口”字便可以引申出一个汉字小故事。汉朝时,有一个四方院子,住着郭和徐两户人家。有一天,郭先生拿着斧子要把院子中的一棵树砍掉,徐先生十分纳闷,问为何要砍树?郭先生说:“你看这方方的院子,形状就是‘口’,‘口’里有‘木’,便成了‘困’,多不吉利啊?”徐先生笑道:“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住在这个方院子里,不都是‘口’里的‘人’,成了‘囚’了吗?岂不是更不吉利?”于是郭先生哈哈大笑,再也不砍树了。[4]145-148故事很简短,也很能引起法国游客的兴趣。但是如何用法语把这三个象形字“口”、“困”、“囚”清晰地、形象地讲述出来呢?
汉语有“因形见义”的传统。汉语和法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它们是非同系或同族语言,在非亲属语言之间进行语符转换时,结构上的语言手段(如符号形态,指一些具有视觉表意功能的汉语文字如日、月、水、口、困、囚等)是不存在信息相通的渠道,因而具有明显的可译性限度,甚至是不可译的。[3]108但是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手段实现此类语符的转换。由于汉字方形的信息是三维的,其视分辨率很高,信息很大,所以汉字可以用“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3]111在《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一书中,陈刚把旅游翻译进行了分类。从涉及语言和符号来看,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种情况应属于符际翻译,就是说,可以使用非语言符号如手势、图画、数学符号、音乐符号等来解释语言符号,或者使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5]60那么涉外导游便可以在纸张上写出“口”、“困”、“囚”三个字,使法国游客通过图画形成图像概念,加以辅助讲解,便能体会汉字其中的文化内涵。
结 语
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实践),属于专业翻译。这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5]59涉外导游翻译是民间文化大使,他们面对的是来自海外的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涉外导游翻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就是一场文化交流,不仅仅是法国游客,对其他国家游客来说也是如此。在旅游翻译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文化方面非常广泛,并不仅限于本文所列出的案例。涉外导游翻译应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掌握文化典故,做到文化信息信手拈来,并且还能用地道的外语翻译给游客。在此过程中,对一些文化中的不可译性现象需要加以特别关注,这些是旅游翻译中的棘手之处,同时也是关键所在,是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的突出点。霍米巴巴指出:语言的“异质性”是不可译的核心,超越了主题的透明度,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意义传递不能是完整的。[6]314在承认文化不可译性的同时,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尽可能地构筑一个信息通道,最大限度地使这些文化信息的可译性限度扩大化,实现文化信息传递和交流的目的。
[1]J.C.卡特福特.可译性的限度[J].吴旭东译.福建外语,1985年第11期,p63-69
[2]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4]陈政.字源谈趣(第二集)[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p145-148
[5]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6]Bhabha, Homi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ation[A]. In Homik. Bhabha(Ed.). Notion and Narration[C]. London:Routledge, 1990:314
[责任编辑:陈光军]
On the Chinese Tourism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in Chinese- French Translation
QIN Qiongfang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JC.Catford divided the untranslatability into language untranslatability and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This has opened up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translation method for the cultural tourism translation. China is a tourist destination for French tourists and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carry out the depth of cultural tourism in China.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n this paper, some Chinese tourism cultural aspects interested by French tourist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discuss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in Chinese-French translation. Moreover, the paper tries to study its compensations scheme.
Tourism French; cultural information; untranslatability
H059
A
1674-8824(2017)04-0100-05
秦琼芳,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邮编:541006)
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旅游法语翻译中文化信息处理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KY2015LX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