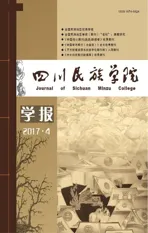《文心雕龙》“纲领”、“毛目”解
2017-04-12魏伯河
魏伯河
★语言文学★
《文心雕龙》“纲领”、“毛目”解
魏伯河
刘勰在《序志篇》里谈及《文心雕龙》的结构,称上篇为“纲领”、下篇为“毛目”。古往今来许多注译者和研究专家迄今尚未得其确解。各家大多按照字面意思进行释读,虽见解或同或异,却均未能完整疏解文意;有的据此推论下篇不及上篇重要,以致明显背离了刘勰的本意和《文心雕龙》全书的实际。其实,刘勰在这里运用了“参互见义”的修辞艺术,所谓“纲领”、“毛目”,不过是各举一边以省文,上篇的“纲领”包括了“毛目”,下篇的“毛目”也包括了“纲领”,并且两者都是“以纲代目”的;解读时必须将其结合起来。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写作动机;纲领与毛目
刘勰(约465-520)在《序志》篇里这样介绍全书的结构: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我们看到,在本篇的这个句群(段落)里,刘勰把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文之枢纽”和上篇、下篇。何谓“枢纽”?枢即门轴,没有门轴,门户就无法开合;纽即把手,没有把手,器物就无法提挈。两者组成一个合成词,代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环节。对“文之枢纽”(今人习称之为“总纲”)在全书的关键地位,研究者历来没有多大异议。但刘勰明确称上篇为“纲领”,下篇为“毛目”,则使不少人感到费解。何谓“纲领”?纲,为渔网上的总绳;领,为裘服的衣领,喻指在事物整体中起骨干、决定作用的成分;何谓“毛目”?毛,指裘皮的毛;目,指渔网的网眼,喻指事物中属于细节、从属的部分。语出晋葛洪《抱朴子·君道》:“操纲领以整毛目,握道数以御众才。”[1]《南齐书·高逸·顾欢传》则说得更清楚:“臣闻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2]从那时开始,“纲举目张”成为流行语。人们都知道,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事情,都必须提纲挈领,即抓住其主要的、起骨干或决定作用的部分。刘勰当然也不例外。但他称上篇为“纲领”,称下篇为“毛目”,从字面上看,似乎上下篇轻重迥异、地位悬殊。而通观《文心雕龙》全书,不难发现,上篇仅仅是文体论,所论述的文体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种类,其中有的属于主流文体,有的则是边缘文体,尽管刘勰对文体论十分重视,但无论对上篇还是全书来说,很难说都属于“纲领”。而下篇涉及创作论、批评论、文学史观、风格论、作家论等,恰恰都是关涉“文心”的重大问题(尤其在我们今天看来),更非全系“毛目”。靠上篇的文体论是根本不可能带起下篇的各项专题论述的。也就是说,文本实际与《序志》此处所说相去甚远。
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扞格难通的现象,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深究的兴趣。历来的研究者对此或熟视无睹,或虽觉有疑义而浅尝辄止,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代表性释读举隅
先来看有关的注释。
因“纲领”系流行语,故注家大多无注,均仅注“毛目”:
清人黄叔琳(672-1756)对“毛目”加注云:“《子华子》:“毛举其目,尚不胜为数也”[3]。意为略举其中数项,不能一一列举。毛,被解为“略,大略”。不难发现,在其语境中,“毛目”没有被作为一个双音词对待。
杨明照(1909-2003)认为:“黄注引伪《子华子》非是。”他列举了四则书例,来解释“毛目”:
按《抱朴子外篇·君道》:“操纲领以整毛目。”《南齐书·顾宪之传》:“举其纲领,略其毛目”。又《高逸·顾欢传》:“纲领既理,毛目自张。”《弘明集》柳憕《答梁武帝敕》:“振领持纲,舒张毛目。”并以纲领与毛目对言。[4]
杨说纠正了黄注对“毛目”的误解,指出了“纲领”与“毛目”对举的特点,是一大进步。可惜的是,他仅到此为止,并未能解决读者所关心的刘勰为何称上篇为“纲领”,而称下篇为“毛目”的问题。而此后的多种注本,大多并未出杨氏之窠臼。
再来看与此相对应的译文。
周振甫(1911-2000)《文心雕龙选译》一书将此译为:
本书上部的以上各篇,纲领是明显了。……本书下部的各篇,细目明显了。[5]
在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里,周先生仍保持了这样的译文。
龙必锟(1932-)所撰《文心雕龙全译》译为:
本书写作上篇各篇文章的纲领就明确了啊。……这样,属于本书下篇以下所有篇章的毛细目录便显目了。[6]
王运熙(1926-2014)、周锋合作的《文心雕龙译注》则译为:
本书上篇写作的纲领已经明确了。……本书下篇写作的各种眉目也就清楚了。[7]
类似的译文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就翻译方法而言,都属于直译。这样的翻译,好像忠实于原文,无可厚非,其实并没有把原文的全部意蕴正确揭示出来。
再来看相关的论述。
周勋初(1924-)先生在《文心雕龙解析》中对“毛目”作了这样的解读:
刘勰把二十五篇以下的文字称为下篇。下篇之中主要包括创作论、批评论、文学史观等部分,刘勰似乎认为其价值不及讨论总纲和讨论文体的上篇部分,但也深入地一一作了讨论,所以称为“毛目显矣”。“毛目”,指细小的项目。[8]
在周先生看来,既然刘勰称下篇为“毛目”,而“毛目”属“细小的项目”,那就是认为“其价值不及讨论总纲和讨论文体的上篇部分”。但这一判断显然不够理直气壮,所以持论谨慎,在句中加上了“似乎”二字。
日本福冈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甲斐胜二在《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问题——<文心雕龙>的基本特征余论》一文中说:
对刘勰来说,文体是非常重要的,难怪以文体分析为中心的上篇便是“纲领”;而排列一些围绕文章的各种内外问题,例如创作心理、文章风格、作家论等的下篇是“毛目”。“纲领”之与“毛目”的关系自不待言。[9]
在这样的翻译和解读中,不难发现,学者们认为刘勰称上篇为“纲领”,就是认为上篇更为重要;称下篇为“毛目”,就是认为下篇相对于上篇比较次要。但这显然不符合全书的实际和刘勰的本意。刘勰明言全书“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他对全书每一篇(包括《序志》)同样都是高度重视、精心结撰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对文体的研究固然高度重视(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甚至是过于重视了),但决不至于把下篇看作并不重要的部分。而且,“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对“文心”的探究固然是贯穿在全书里的,但最直接、最深入的探究却无疑是在下篇里面,可以说,没有了下篇,《文心》就不成其为“文心”了。刘勰怎么会认为这些内容不够重要、与纲领无关呢!
有的学者显然是觉察到了这一矛盾现象,因而在注译中试图加以弥合,可惜并不成功。如郭晋稀(1916—1998)《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虽然注意到了“‘毛目’与上文‘纲领明矣’的‘纲领’二字,遥遥相对”,但他认为:“‘毛’不是‘毛举细故’的‘毛’,而是‘毛毛草草’的‘毛’,‘毛目’是后二十五篇的大目”[10]。在译文中,他把“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译为“下半部二十五篇,大略举其篇目也就很明显了”。[11]这样的解释当然是过于勉强了。“毛毛草草”或作“毛毛糙糙”,意为做事不仔细、不认真、不讲究,属现代流行的口语词汇。古文阐释中,借助于俗语、口语并非全不可行,但必须与可靠的书证相辅而行才有说服力。他所征引的“毛毛草草”的“毛”,本来就与“大”义相距甚远,何况译文中又退回到“大略举其篇目”了呢!
陆侃如(1903-1978)、牟世金(1928—1989)合著《文心雕龙译注》也说:“‘毛目’指概貌,和上文‘纲领’略同。毛,粗略。”[12]
注意到两者的“略同”,自然是符合文本实际的;但把两个对立的概念简单混同起来,却没有从语义分析上给出任何根据,便难以让人心服。在该书译文中,这句被译为“这样,就在本书下篇里边,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种种具体问题都大致讲到了。”“毛目”又成了“种种具体问题”,和注文相比,未免又向“毛目”即细目的传统解释退缩了。后来有人对郭晋稀和陆侃如、牟世金之说加以辨正,认为“由于上下篇的内容有综述和分论的差别,故‘纲领’和‘毛目’不应意有重叠,即其一指纲要,另一则当指细目。”[13]又彻底回到望文生义的原点上去了。论者们大概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上篇并非“综述”,对各种文体何尝不是逐一“分论”的呢!
二、值得重视的“互文”现象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笔者以为,症结在于当今的学者们普遍忽略了中国古籍中大量存在的“互文”现象,才导致了种种释读之扞格难通。
那么,何谓“互文”?
“互文”现象相当复杂,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格。从其总括性称谓来讲,“互文”又称“互辞”、“互体”。而从其具体用法来说,又有“互言”、“互举”、“互相明(互明)”、“互相见(互见)”、“互相成”、“互相足”、“互相备”、“互相挟”等种种分别。它之所以产生并大量应用于古籍的写作,一则由于古代书写条件的限制,作者力求文字简省;二则因为中国语言崇尚词句的对偶,往往非彼此“参互见义”不能达到对偶的要求。在对应的两句中,相同的位置如果表达同样或相近的意思,也需要变换其辞以避免重复。而变换其辞的办法,一是分别使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词语变换而意思不变,释读时彼此可以互训,如“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征圣》)句中,“精”与“微”、“曲隐”与“婉晦”、“无伤”与“不害”都是如此。二是要表达的意思包括两方面,就在对应的分句中采取“各举一边”的办法,使之既符合对偶的要求又避免了重复,理解时彼此应该互补。如“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神思》)句中,“援牍”与“举笔”、“口诵”与“宿构”均应作如是解。因为“援牍”时也将“举笔”,“举笔”时也必“援牍”,纸笔俱备,方能写作;“口诵”与“宿构”好像是两种表现,但“口诵”必须有“宿构”为基础,有“宿构”则“口诵”自不在话下。所以,“援牍”与“举笔”、“口诵”与“宿构”都是就曹植(子建)和王粲(仲宣)两人而言,用以表现其文思之敏捷。而这一类语言现象的形成和普遍运用,归根结底还和我们的古人高度重视事物间相互对应关系的思维特点,尤其是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的普遍观念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据现在能够见到的资料,最早发现并为“互文”命名的学者是东汉的经学家郑玄(127-200)。他在为经传作注时,大量接触到这类现象,发现如不揭示其“互文”特点则难以圆满周备地揭橥经传的文义,因此在他的注解文字中,多次出现了“互文”及其相近的语汇。[14]到了唐代的贾公彦(活动于公元7世纪中叶,生卒年不详),在对郑注进行疏解时,又对“互文”这一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在《仪礼疏》卷第三十九《既夕礼》第十三中说:“凡言互文者,是二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当然,这样的定义并未能涵盖所有各种形式的互文。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再作补充说明,例如他指出所谓“互相足”,与一般的“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文不同,是“一物分为二,文皆语不足。”[15]意即作者把一件东西分到上下两句里去说,而上下句的语意都不完备,在理解时必须把上下句意结合起来才行。历史地看,贾公彦在互文研究上贡献颇大,使人们对“互文”的认识进了一大步。贾氏以后,直到清代的朴学大师们的相关研究,不过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而已。
三、结论
了解了古人表达方式的“互文”特点,回头再看刘勰的表述,就可以豁然贯通了。刘勰在《序志》中概括介绍全书内容,只能提纲挈领,以纲代目,是不可能遍举“毛目”的。用到“毛目”一词,只不过是为了与前文对应语句中的“纲领”一词在形式上形成对偶,在文义上实现互补。我们看到,在刘勰这一句群的表述中,“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与“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恰好处于对应的地位。在这两句里,刘勰既运用了“各举一边以省文”、“一物分为二,文皆语不足”的“互相足”之法,同时还运用了“变文避复”的技巧(“明”、“显”)。在解读时必须把作者省略的文字和意思补充起来,如下所示:
上篇以上,纲领(毛目)明(显)矣;
下篇以下,(纲领)毛目(明)显矣。
其中,“纲领”与“毛目”属“各举一边而省文”,二者“文皆语不足”,必须“互相足”,都是兼就纲领、毛目而言,并非以上篇为“纲领”、以下篇为“毛目”。理解时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即上句所说的“纲领”也涵盖了下篇,下句所说的“毛目”也涵盖了上篇,而且两句都是以纲代目,偏重于“纲领”而言(郭晋稀和陆侃如、牟世金在注译时显然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由于没能认识到其“互文”的修辞手法,所以离正确解读只差了一步)。而“明”、“显”二字则属于互文的另一种最常见类型:变文避复,即:明、显二字同义(现代汉语中已成为同义复词),可以互换、互训,翻译时可用现代汉语的双音词译出。
弄清楚了古籍中互文的特点之后,如果对这两句分别进行语译,译文则应为:“上篇的纲领(和毛目)就很明显了;……下篇的(纲领和)毛目也就很明显了。”而如果会通起来加以讲解时,则应为:“这样,上下两部分的纲领和毛目(也可简称之为‘纲目’)就都很清楚了。”当然最好同时给予提示:这里的“纲领”和“毛目”运用了“互文相足”的修辞技巧。
《文心雕龙》中运用互文(具体还有各种类型)的地方还有很多,造成理解困难和解读争议的也有不少。通过此例,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自可思过半矣。
[1]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p232
[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p929
[3]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p288
[4]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p629
[5]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p12
[6] 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p620
[7]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465-466
[8] 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p811
[9] [日]甲斐胜二.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问题——《文心雕龙》的基本特征余论[A].戚良德主编:《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p580
[10][11] 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p229、230
[12]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p385
[13] 张灯.《文心雕龙·序志》疑义辨析 [J].《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14] 刘斐.中国传统互文研究——兼论中西互文的对话[D].中国知网
[15] 李学勤,等.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p868
[责任编辑:朱茂青]
Explanations on "Gang Ling" and "Mao Mu" inWenXinDiaoLong
WEI Bohe
In the "Xu Zhi Pian" inWenXinDiaoLong, Liu Xie called the part one "Gang Ling", and the part two "Mao Mu". Through the ages, many translators and researchers have not yet got the reasons why Liu Xie called them in this way. Though they have usually been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ich literal denotations, they are still a great muddle for us to know; hence, some inferences are that the part two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part one, which obviously deviates from Liu Xie'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actual content of "Wen Xin Diao Long". In fact, Liu Xie here only utilized the so-called "Gang Ling" or "Mao Mu" to represent each other, "Gang Ling "is subsumed to "Mao Mu" and vice versa. As a result, they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interpret the whole book.
Liu Xie;WenXinDiaoLong; writing motivation; "Gang Ling" and "Mao Mu"
I206
A
1674-8824(2017)04-0087-05
魏伯河,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山东济南,邮编:2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