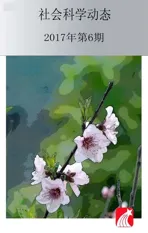史学方法与史学发展:《食货》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
2017-04-10阮兴
阮兴
史学方法与史学发展:《食货》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
阮兴
《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流行一时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刊物。其办刊宗旨与风格当时自成一种学风,既重视史料的收集,又不忽视史学方法。其史学方法的提倡与运用,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对《食货》所提倡与运用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与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趋向与特征。
《食货》;中国经济社会史;史学方法
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①。《食货》创刊后很快引起社会与学界的关注,成为流行一时的刊物。与北平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很快刊出介绍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学术通讯,“这种‘食货’运动是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上的一个新的动向”②。《文化建设》杂志也发表了介绍《食货》的文章,认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食货》“指示着此后应走的途径”③。在销量上,《食货》甚至一时超过了由顾颉刚创办的著名的《禹贡》。据陶希圣称,《食货》开始每期只印行两千份,但《创刊号》发行后一星期,便又被迫又再版一千份,到第1卷第5、6期,印行数已达四千份。④而《禹贡》初期每期印五百份,后来每期才增加到一千五百份⑤。不仅如此,《食货》“在日本方面销售不少”⑥。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讲求方法,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生产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⑦。在史学研究方法上,《食货》所倡导与运用的主要有地方志收读法、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
一、地方志收读法
民国以来,地方志的史学价值已日益引起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利用方志史料研究往昔和当时的社会,这在民国也成为一种风尚了。”⑧民国时期,不少史学名家治史即非常注重方志的利用。如陈垣利用《至顺镇江志》里的史料,考证了元也里可温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利用顾颉刚为其从《江南通志》中查得的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的职官表,考证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使红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⑨。但3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利用方志来进行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陶希圣所说:“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⑩
顾颉刚是《食货》的热心发起人之一,对方志比较重视,其兴趣与研究领域虽非经济社会史,但似乎洞察了当时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这一不足。《食货》创刊后,顾颉刚即致信陶希圣,提议从地方志中里找寻经济史料⑪。这一提议与陶希圣创刊《食货》时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的思路正相一致。陶希圣认为顾颉刚的提议是一个切要的工作,并于《食货》第1卷第2期发出经济社会史研究者共同着手搜读方志的倡议。其实,对于从地方志中搜集经济社会史料,陶希圣早有此意,只是腾不出工夫来做这一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把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历史概况弄清爽,还有不少的书是要看一看的,譬如二十二史”⑫。但陶希圣认为在对社会的历史过程的认识稍有头绪之后,便应下工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社会史料,尽管这是一个要费很多劳力的工作。陶希圣指出方志虽是当地稍有史地知识的文人,或稍有名望的文人的作品,并非全部是原始的材料,因为这些人在作方志时并没事先经过社会调查。但其有两方面的价值:(1)它是研究一地的历史的最方便的书;(2)它保存有人口、食货等方面不少原始的记录,因为这些记载都是从功令、档案里来的。尤其是其中关于地方风俗、财政经济制度的记载比较清楚。为此,陶希圣提出搜读地志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陶希圣认为由此可看出大都会的发达史、从前的大都会的衰落过程以及现代大都会的起源发达经过。在大都市史初步作过后,再选择别种类的方志;“第二个原则是分工的办法”。陶希圣指出分工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的地方志。这是由于容易启发兴趣,也是由于本省人对本省的地方情形知道的多些⑬。
同期,鞠清远也在《食货》撰文对地方志的收读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鞠清远认为,中国的方志书,尤其是县志,大部分是官书。其编纂者的学识与眼光往往不甚高明。并且在章节与格式上,又往往相同。而其中建制、沿革、官制、孝子、节妇等记载往往占去不少,这些材料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往往没有什么用处。但地方志自有其研究上的价值在,因为“有许多经济史料,在他处很不易找到,而在方志书中,可以找到”。但鞠清远认为中国的方志,数量太大,因此,应先确立中心问题,以此进行选读,以节省时间,增加效率。其具体建议是:“(1)先读历史上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以都市为中心。(2)先读在水路交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以交通线为中心。(3)先读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县府方志。——以工业矿区为中心。”鞠清远进而阐述了以这三个中心问题搜读地方志的原因、意义及研究上的便利。鞠清远认为,以都市为中心,可以得到中国经济都市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时也可知在都市的贸易领域里,工商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时以都市为中心,在研究上有三个方面的便利:“(1)由一大经济都市,可连带的研究许多小都市。(2)许多小都市的发展,或者也按照大都市的发展原则,假如不是采取同样的形式,至少可使我们知道或者还有另外的特殊原因。(3)假如能明了大都市在工商业方面,有什么特殊势力,或特殊贡献,我想这样也可使我们明了所谓国民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交通线为中心,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自古至今,似乎都是不平均的。在水陆交通线附近的都市、府县、村镇、驿站,都因地理环境的关系,而特别发达一些。其研究上的便利则是:“(1)可以明了交通路线,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2)可以明了由交通路线之改变,而经济中心如何变迁。(3)这样可以明了在特殊环境的地方,经济发展的实况。(4)这样可以推知,比较不在交通线上的都市的经济的实况”;至于以工业矿区为中心进行研究,鞠清远认为是由于古代关于这类事件的记载太少,希望借此可以得到关于古代矿业组织的记叙,同时借此认识当时工业矿业都市的发展过程。鞠清远认为这三种读法,有许多地方难免相互重复,但可以设法避免。如以交通线为中心来读方志,则可不必读重要都市的方志。最后,鞠清远指出了在读方志时不应忽略的几个方面,如方志中的《杂录》与《金石录》以及关于驿路、水路交通、驿站的设置地点与组织、物产、贡赋、和买、寺院、庙会、市、集会、水利事项、桥梁建设等种种记录。鞠清远认为这些记载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但它们都是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有重要意义的史料。⑭
为倡导地方志的收读,《食货》第1卷第5期刊载了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这是瞿兑之以前读地方志时所作的笔记,载有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经济社会史料⑮。《食货》刊载瞿兑之的文章,不无树立范例之意。瞿兑之是民国时的方志学名家,从二十年代即开始注意从方志里收集史料,历时十余年之久,收获颇丰:“端居读史,见有关制度风俗者,辄随笔记录之。积十余年寒暑,遂充箱箧”⑯。后来,瞿兑之将其所收集的材料整理,编辑成《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嘉惠学林。陶希圣对瞿兑之从地方志中收集史料的工作评价颇高:“在搜集材料的努力中,我佩服瞿兑之先生。他有很大的计画搜集地方志中的材料。他有很多的条目,可以供我们的研究的运用。他于今把宝贵的材料,一集一集的发表出来,可以算是中国社会史界的福音”⑰。
《食货》搜读地方志的倡议很快引起了注意与响应。杜若遗在《文化建设》撰文介绍《食货》时即指出:“(《食货》)第二期中,鞠清远、陶希圣两先生发起评读地方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提议”⑱。一些学者在读了陶、鞠二人的文章后,即向《食货》撰文,就地方志收读方法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吴景超撰文表示同意陶希圣提出的先读大都会的地方志以及分工合作的两个原则,并认为鞠清远提出的地方志的三种读法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颇有参考价值。但吴景超认为,鞠清远提出的三种读法,应当合并起来,否则难以对都市有彻底的了解。因为“工商业是都市繁荣的根据,而交通线是都市与其贸易领域打成一片的工具,我们如想了解一个都市的经济,是决不可忽视这两点的”。因此吴景超提出,如果要分工,还是以都市为根据的好。吴景超表示,自己研究都市的方法是从理论下手,根据理论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其个人收集材料所用的纲目:(1)都市的定义及其与乡村市镇的区别;(2)都市的历史;(3)近代都市发展的统计;(4)近代都市发达的原因;(5)产生都市的区域;(6)都市的位置;(7)都市与内地的关系;(8)都市间的关系;(9)都市的人口; (10)都市的结构等。吴景超表示,这个纲目最适宜于研究近代都市,但对研究古代都市也许不无参考之用。同时吴景超还指出,海关每年出版的中外贸易报告统计册、大都市中的银行、工厂、公司每年所出的报告、市政府及其隶属机关所出的公报及其保存的档案、学术机构关于都市某一方面的调查报告、外国人对于中国都市的各种生活的描写等等,都应作为史料收集起来,以为研究都市的依据,此外,还应进行实地调查⑲。
吴景超是当时新晋的社会学家,1928年留美归国,先在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后于1931至1935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社会学上专攻都市与工业化问题⑳。1929年,其第一部著作《都市社会学》出版,主要是介绍西方都市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引用了一些中国都市发展的的材料。吴景超研究都市的目的,是为解决现代都市的各种问题提供依据,以建设理想的都市:“有铁硬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我们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㉑。吴景超依据欧美都市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的都市史料收读法,别具特色。陶希圣认为吴景超的这篇文章可以“指导我们做近代都市发达史的工作”㉒。
王沉也来信讨论地方志的搜读方法。王沉认为,鞠清远关于地方志的搜读法即以都市、交通和工业三点为中心,虽很扼要,但“最好再加上物产这一部门。这对于古代一般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很有许多帮助的。因为过去的中国工业,究竟有限”。而搜读地方志,应“不仅限于省志,连县志以及小部分的村镇乡志,也应该收罗起来”。王沉并开列出了一个从地方志中收罗材料的单目:(1)都市——各部门的记载;(2)交通;(3)工业; (4)物产;(5)赋税;(6)风俗;(7)人口; (8)货币;(9)地域;(10)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11)贸易;(12)天灾;(13)官制;(14)兵役;(15)城市的迁移;(16)宗教;(17)缙绅与地主的姿态;(18)商业;(19)文化; (20)教育。王沉认为不论大都市或小的城镇都可按这20个部门来收罗材料。㉓
二、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
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也是《食货》倡导与运用的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一种重要方法。作为主编的陶希圣十分重视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1934年10月,陶希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演讲,对其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方法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在演讲中,陶希圣以经验之谈阐述了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认为过去社会经济史与现代社会经济如风俗、习惯等的调查是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过去的经济社会史,“从社会问题入手也是一个常见的办法。问题的类别很多,如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犯罪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每个问题都可搜集许多的材料去做研究的解释”。陶希圣自谓其研究商业的兴趣即是由于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注意所引起的。陶希圣指出:“明了过去社会如何发展,可以明了现代的社会如何发展,反之,看清了现代的社会,也可以推知历史上的社会。如果对于现代社会不了解,即对于历史的认识是死的,反之,如果对于历史不了解,则现代也是死的,必须了解历史,更能洞察现代,才能相互参照,才有意义。……对于现代社会认识越透彻,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愈深刻。时代的变化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正如了解历史,能帮助了解现代的社会一样。所以总起来说,过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现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相互为用的。”㉔陶希圣在《食货》上大力提倡以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1935年3月,陶希圣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到济南部分学校演讲,演讲后游历济南当地的一些地方,对游历之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考察。在游历当地村庄李村时,陶希圣对这一村庄的田亩、人口数、农家经营的副业、佃户对地主的负担、家族制度、寺庙等情况予以特别关注。在考察过程中,陶希圣认为当地的一些社会关系的真实情况,“是多少社会改良家苦做了一辈子,也看不透的”。同时在考察与参观中,陶希圣对学术与实际的生产的联络也产生了兴味,认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都是为了实际的问题存在的。只有逃避实际的玄想家,把人们引上虚无缥缈的路上去”㉕。这次游历,陶希圣认为是颇有收获的,因此在《食货》第2卷第1期上作了《鲁游追记》一文,以记这次游历的经过与感受。后来,陶希圣更是有进行大范围社会调查的计划。1937年下学年秋季起,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教授将满六年,按规定可获休假,陶希圣计划利用这次休假,游览并考察中国西北、中部、西南等地,考察的主题是牙行的崩溃、银行与钱庄的交替,农业金融等问题㉖,可惜这一计划因抗战爆发而没能实现。
《食货》第2卷第2期出版正值暑假开始之际,陶希圣在该期《编辑的话》中发出号召,“希望大家回乡作本乡的经济史调查”。陶希圣的号召得到了响应。籍贯广东的王兴瑞即乘暑假返乡之便,试做这种工作,对其家乡——广东某一村庄的经济社会状况做了调查。王兴瑞对该村庄的“农业经济”、“土地分配”、“村民生活与外汇”、“宗法组织及其崩溃”、“贱民阶级(奴隶阶级)”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撰成《广东一个农村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一文在《食货》上发表。在文中,王兴瑞对社会调查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论述:“现实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不仅在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上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之探讨,其效用亦不亚于书本上的搜索”。王兴瑞借王宜昌之语解释其所以重要的原因:“人体的解剖是猿体解剖的的钥匙。因为在猿体中还未发展的部分,在人体中十分发达起来,而在猿体十分发达了的衰颓了的部分,在人体中还留下了痕迹。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但在解剖学上应该如此。我们应该从最高的最发达的人类社会解剖起去,而渐次达到最原始的社会阶段。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一事物的结束的存在,推求其原因与发展”㉗。
王宜昌的观点明显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㉘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流行开来,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常为人们所征引,社会分析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渐为人知。而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前,情况则并非如此。正如1935年顾颉刚所说:“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㉙
和陶希圣一样,《食货》的一些作者也主张从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入手进行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吴景超在《近代都市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指出,自己研究的方法是先从理论下手,同时认为“研究近代中国都市,还少不了社会调查”㉚。王瑛在《食货》上撰文,提出应把“由果推因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原则与方法。除引上述王宜昌之语外,王瑛又引施复亮之语说:“我认定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近代中国经济史,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生性上去把握问题,不应当从封建经济的没落去把握”,王瑛进而认为:“其实,何独近代经济史,简直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当从现代经济研究起。”㉛刘兴唐也认为,研究历史要从现实社会的分析做起:“因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是进步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其中自然有许多现在已经死亡,而只保留其残余。单单从过去的古籍的究明,我们很难认识出其本质,在这些方面,我们便不能不借助于现实所有的残余。从现实所有的制度,去认识过去。人体的解剖,即猿猴解剖之钥匙。下等动物所含有的向高等动物发展之暗示,那只有把高等动物阐明了之后才有可能。在过去的社会经济之发展,有些固然已经因为不适合于现有经济组织而成为已经死亡了的残余而存在着。而尚有一部分在过去仅只是一种萌芽,到现在则发展成了灿烂的文章。现实的社会,虽然可以把一切过去的经济的形态包括起来,但其中要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必须从现实的经济组织说起。对于现实的所保有的社会残余,和古籍上的历史材料,同样不可以忽视。只有这样,我们方才能认识人类怎样由类人猿,而发展到现实的文明”。㉜实际上,从现实社会分析入手进行研究,是刘兴唐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1935年,刘兴唐在《食货》上发表《唐代之高利贷事业》,这是国内较早研究唐代高利贷的一篇文章。刘兴唐很明显地是分析了当时的现实社会,然后再以此为参照来研究唐代的高利贷。
实际上,《食货》的一些作者之所以从事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本身即与其社会经历与社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3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李文治,其学术写作是从研究唐代农民运动开始的,而这与其早年的社会经历有很大关系。1931年,李文治在河北省容城县教育局当督学,因工作关系与当地农民有较多接触。就在这时,河北各州县地方政权成立官产局,迫令过去租种旗地的农户补交地价。李文治在容城县秘密策动了一场反抗当地“官产局”搜刮民财的农民运动。事发后,李文治离开容县,不久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问题了”㉝。1935年李文治发表《黄巢暴动的社会背景》一文,刊载于《师大月刊》;1936年,又在《食货》上发表《大业民变的经济动力》、《北宋民变的经济动力》两篇文章,从而开始走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学术道路。这正如李文治后来说:“我之所以从事农民运动的研究和写作,是由于我曾经有过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㉞
刘道元早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除了陶希圣的影响与引导外,与他当时从事的社会实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年,时为北京大学预科生的刘道元,受国民革命形势的激励,利用暑假之便,返回家乡山东曹县,成立曹县“党务处”,“发动青年起而行动,以迎接国民革命军之到来”。在负责曹县“党务处”工作时,刘道元和其北大同学王保合一起主持了当地的田赋改革事宜,并将改革的情形,作成一详细的报导,在天津《大公报》专文发表。这一社会实践的经历,使刘道元认识到,田赋是历代中央与地方的主要财政收入,其制度的良窳则关系到当时的经济的盛衰与朝代的兴亡,于是引导其“走上研究中国田赋史的道路了”㉟。
三、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也是《食货》倡导与运用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对于统计方法的运用,陶希圣早年即予倡导,并在具体研究中注重应用这一方法。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陶希圣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须应用的方法,除了演绎方法外,其一是概括的记述法,其次是抽象法,第三便是统计方法:“要对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趋势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我们第三要有统计法。”陶希圣对统计方法的定义、使用时的局限及应注意之处进行了说明:“在一群现象中,发现一定特征以如何次数实现及以如何程度实现之量的研究,叫统计法。不过,中国的数字的记录在历史上非常缺乏,便有也靠不住,即如人口的官厅报告大抵不甚正确,因为满清以前,赋税是按人口抽收,所以匿报是原则的情形。近百年来,统计的记录较多,但正确的还是很少。”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早期的系列著作中,陶希圣都运用了统计的方法。
统计方法在研究历史时,自有其优越处,但如运用不当,则往往不免以偏概全,偏离事实的真相。陶希圣便曾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批评。如刘节即认为陶希圣所运用的上述包括统计法在内的方法便有不当之处:以此“整理史料则可,若用之以排比事实,求一贯之因果,则尚不足。盖历史进化,决非事实之积聚,乃各种事象之交辐发展。求其一鳞一爪,皆属片面理由。何况概括与统计二法,尚不能脱离形式逻辑中求同求异之理,且系考证家所常用之方法。至于抽象法,则所寓之危险更大,一有不慎,必至抹杀证据而后已”㊲。这一批评似乎对陶希圣有所触及,后来陶希圣在论及统计方法时,尽管依然认为统计方法用途很广,但态度则较前谨慎:“统计的功用很广,许多共象可用统计数字来代表,……但是要注意有的现象固然可以用数字来表现,同时更有许多重要的事实不能用数字来表现,那就是社会现象间的具体的关系,单看数字,我们没法了解这种具体的关系,而且不了解这种具体的关系,单看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了解了这具体的关系,即是不但了解了统计表的本身,更要紧是了解了统计所指示的意义了。因此,单靠统计的数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明白数字与数字中间的关系和连锁,才能求得社会现象间的真相。”㊳
陶希圣创办《食货》,积极提倡统计方法的运用。《食货》第2卷第2期刊载了由连士升翻译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判的《经济史的纪律》一文。这篇旨在论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指出了统计方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克拉判认为,统计方法只有在研究较近时期的历史,即有调查及其它官方统计的时代才能够应用。但“十二世纪以后,任何时期的价格史都有丰富的文件,因此要研究价格史,必需懂得现代研究价格的方法和指数的基本原理。最近的时期的研究,需要比较完全的统计设备,因为种种统计材料的丰富,所以能够应用更精密的统计方法。这种工作自然要让归纳法的经济学者来干”。克拉判认为,每个经济史学者都应该具有统计的意识,“就是关于某制度、政策、团体、运动,须时常提出下列的问题:多大呢?多久呢?几次呢?代表是怎样呢?”克拉判指出,尽管这种需要很明显,但是“许多较旧的政治制度的经济史因为忽略这种需要,至用处较少”。例如从前的史学研究者以为“广大的土地产业”(Latifundia)很能代表纪元前一世纪初期的罗马经济生活,其实不然。大陆的学者关于都市的起源的许多理论,提出‘代表是怎样’的问题。德国的学者想把经济的发展的情形列成表,即进行经济史分期的计划,也由于忽略了“代表是怎样的问题”,结果遭致失败。㊴陶希圣认为,克拉判的这篇文章中关于统计方法的论述让人很感兴趣:“克拉判的经济史方法论,最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便是他对于数目字在经济史研究上地位的估价。”㊵该期之后,对于统计方法,陶希圣在《食货》上加以提倡,并在实际研究中积极运用。在《明代王府庄田之一例》一文中,陶希圣运用统计方法,依《晋政辑要》一书,对明代王府庄田的分布区域、纳税地、更名地进行了数字统计,并制成表格。陶希圣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有它的意义在:“表虽然是枯燥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意义来”。如王府庄田是分散在各县的;各县的庄田多少不一定。大约庄田最多的处所,是田地较好的处所等等。不仅如此,在同期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又对这一研究方法特别加以提倡,认为如从清代《赋役全书》里把各省的更名田及田的分配情形给录下来,则明代王府庄田的实在情形可以明了许多,因此希望食货会员有人能做这一工作㊶。
在随后的《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一文中,陶希圣又运用统计方法,以《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对唐天宝时期户口较多的州县,以户口数目为等级标准,进行数字统计,制成不同的表格加以区分,以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陶希圣认为,《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州郡户口,是根据天宝时调查的,在括户运动之下,这些数目最近于当时实在的人口数目。从这些数目中,便可以找出各种的意义来。陶希圣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唐代天宝时期的宋州、睢阳是河淮之间的农业平原的交通中心,户口繁盛,均在十万户之上,从中可以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些地方能抵抗安禄山的军队而保障淮河流域以南的半壁江山㊷。陶希圣的这种研究方法及倡议对《食货》的读者及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锡纶在读了陶希圣在第2卷第2期《编辑的话》后,即“跑到故宫,把现存的《赋役全书》(只三十五册)翻阅一遍”,虽没有找到“更名田”的记录,但却找到不少关于“明代户口的逃亡与田土的荒废”的资料,于是再参合《明史·食货志》及《续文献通考》两书资料,在当时在故宫工作的单士元等人的指导下,按陶希圣的研究方法,对明代丁口的原额和逃亡额、土地的原额和荒废额的数目进行了统计,制作成表格,成《明代户口逃亡与田土荒废举例》一文,发表在《食货》上㊸。
其实不仅陶希圣对统计法加以运用,《食货》其他一些作者在研究中也注重运用统计方法。马非百即非常注意统计方法的运用。如他对两汉时期各地的矿产、物产分布情况、西汉时赐金的金额、西汉郡国户口均进行了数字统计,制作表格,进行分析㊹。陈啸江对统计法更是情有独钟,认为这是建立新史学的科学基础的重要方法之一:“统计的方法,也是巩固新史学的科学的基础一个重要的方法”。陈啸江认为统计学有两个基本原理:“齐一之法则The Law of Statistctical Regluarity”与“大量不变之法则The Law ofLargeNumbery”,它们“都非常合于新史学的本质”。因为“新史学所注意的东西,是社会的‘共相’!而不是社会的‘特相’”。而旧日历史家过于注重“特相”,每硁硁于一人一物,支离破碎,这是因为未曾受统计精神的洗礼。陈啸江认为,尽管中国的旧史里不易找出统计的材料来,但中国史籍浩繁,只要耐心收集,并辅以一定的统计技术,则定能有相当的收获,因此应当努力实行,不可因噎废食㊺。对于统计方法,陈啸江不仅倡之于言,同时也积极实践。在《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陈啸江耗费大量精力,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各种数据,制成许多图表。陈啸江在书中道出这一作法的苦心用意:“用统计方法来研究历史,虽然有人提倡,不然(过)彻底实行起来却很少。固然西汉社会,离今已远,材料未充,在实施统计工作上,有许多困难。但个人凭着笨拙的心情,干着繁重的工作,总算造成许多的图表出来了。这种风气,我以为要使历史早日跻于科学之域,是需提倡的。”㊻陶希圣对陈啸江的这一论著颇为推许,将其收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并在《食货》上进行推介,认为:“这个理论缜密而内容充实的作品,可算得这门学问的大贡献了”㊼。
四、《食货》的研究方法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
《食货》提出搜读地方志的倡议,一方面是着眼于史料的收集,一方面则是着眼于陶希圣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其研究取向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是相当有意义的。1944年,傅衣凌曾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此前长期难有满意的进展的原由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我常想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一个道理,有一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㊽
傅衣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其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启发和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和日本、美国许多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而成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㊾。傅衣凌治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非常重视和善于利用地方志。傅衣凌在后来的学术回顾中曾自述地方志对其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30年代)东渡日本,一面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一面到东洋文库看书,开始懂得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后来我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㊿。30年代,傅衣凌曾向《食货》投寄文章、译稿,其重视地方志除了受梁启超史学思想(51)与日本学界的影响外,与《食货》提倡从地方志中搜读经济社会史史料恐怕不无关系。傅衣凌这一学术见解“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与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52),具有深远的学术洞察力。《食货》提倡地方志的搜读虽与傅衣凌所说的“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有很大差距,但其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也正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需着力进行的研究。
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对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有着重要意义。后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史学家,均比较重视实地的社会调查。如梁方仲即特别重视社会调查,30年代“曾前往陕甘三省从事社会调查,不辞劳苦,深入农村,搜集有关资料,为期凡八阅月”,以调查农村土地关系和农民田赋负担问题(53)。傅衣凌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抗战初期,傅衣凌由沿海城市来到福建永安农村,接触到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认识到,一个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接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种认识对傅衣凌开拓其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54)。
当时的一些社会史研究者,开始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这本是纠正社会史论战空泛学风的正确的途径,但一些研究者由于过于重视史料的收集,而忽视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及社会调查的工作,这种现象已为当时的一些人所察觉。对经济史研究颇为用心的金海如即致信《文化批判》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年来专治中国社会史的一些学者们,目前好多拼命的在那儿做‘翻史书’和‘抄史料’的工作,而考古之风,于焉大炽。”(55)金海如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应当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多从研究社会现实出发:“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我主张是多多着重现实,这不是说忽视过去,而是说除了用叙述的方法作历史的研究外,还应当要用研究的方法作追溯的研究。”《文化批判》编辑王海鸥对金海如这一见解深表赞同,认为“是精确之论”(56)。
统计方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中一项重要方法。“数量统计方法的重要性,一是便于进行比较,可以化繁为简,使复杂的事物明朗化;二是数量统计具有精确的特点,作出论断更有说服力;三是可据以考察事物乃至社会经济发展趋势。”(57)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梁启超是先行者。1903年,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较早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之中(58)。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更是力倡统计方法的运用。梁启超对统计的定义是:“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梁启超认为用统计方法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欲知历史的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了;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它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59)除梁启超外,当时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倡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如丁文江即为其中较热心的一位。1923年,丁文江在《科学》第8卷第1期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以统计方法考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影响较大。不过,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统计方法有所保留。如傅斯年即对丁文江的上文运用的统计方法提出了疑问。傅斯年认为丁文江的文章虽然很有刺激性:这篇文章很刺激我们从那些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曾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但指出丁文江以统计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却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傅斯年认为:“研究历史要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截用起统计方法来,可要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60)以新史学为务的何炳松也认为统计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有限,只能算是一种偏而不全的方法:“统计方法所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非社会演化之真因也。真因维何?即人类内心之动机是也。统计学在史学上所以为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61)
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统计的方法的运用日益成为需要。朱谦之认为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他引用Harold.U.Faulkner的话以说明统计方法的重要性:“统计学一方面使史学家的工作趋易,而他方面则使之益难。这一种新工具,使他能作更确切的推论,但同时却使他的工作,愈益繁重。凡史事之可以应用统计的材料者,则不用统计学的,结论便有缺憾。同时统计学亦使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加广,总之最要紧的是统计学已给经济史及社会史的发展以有用的助力,而使此古老的史学有一新的目的和新的生命了。”朱谦之甚至将能否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研究作为区分是否为经济史社会史家的依据:“统而言之,就现状来说,历史家中只有社会史家经济史家才真正能运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也只有能运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者,才能代表文化史发展之最新时期。”(62)《食货》运用统计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体现也增进了这一史学发展的动向。
总而言之,《食货》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流行一时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刊物,积极倡导与运用地方搜读法、社会分析与社会调查方法及统计法等研究方法进行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既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状况、趋向与特征的反映,也推动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的发展。
注释:
①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1937年7月,《食货半月刊》停刊。1936年12月与1946年6月,陶希圣又分别在天津《益世报》与《中央日报》创办《食货周刊》。1971年4月,陶希圣在台北复刊《食货半月刊》,改为《食货月刊》。本文如无特指,《食货》均指《食货半月刊》。
②⑥长江:《陶希圣与〈食货〉》(三),《北平晨报》1935年1月18日。
③⑱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
④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
⑤《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期合刊,1937年4月。
⑦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版,第344页。
⑧⑨傅振伦著、陈怡整理:《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08页。
⑩⑪⑫⑬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
⑭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
⑮瞿兑之:《读方志琐记》,《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⑯⑰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题语》,见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⑲㉚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⑳周叔俊:《吴景超》,载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3页。
㉑吴景超:《都市社会学》,见《社会学讲座》第1集,台北启明书局1961年版,第81页。
㉒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㉓王沉:《关于地方志》,《食货》第2卷第1期,1935年6月。
㉔㊳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北平晨报》1934年11月14日。
㉕陶希圣:《鲁游追记》,《食货》第2卷第1期,1935年6月。
㉖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5卷第12期,1937年6月。
㉗王兴瑞:《广东一个农村现阶段的经济社会》,《食货》第3卷第2期,1935年12月。
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08页。
㉙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㉛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下,《食货》第2卷第5期,1935年8月。
㉜刘兴唐:《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文化批判》第2卷第2、3期合刊,1935年1月。
㉝㉞《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㉟刘道元:《九十自述》上册,台北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3、47页。
㊱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㊲刘节:《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图书评论》第1卷第12期,1933年。
㊴克拉判著、连士升译:《经济史的纪律》,《食货》第2卷第1期,1935年6月。
㊵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2卷第1期,1935年6月。
㊶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2卷第7期,1935年9月。
㊷陶希圣:《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第2卷第10期,1935年10月。
㊸张锡纶:《明代户口逃亡与田土荒废举例》,《食货》第3卷第2期,1935年12月。
㊹马非百:《秦汉经济史资料》之(二)、(四)、(五),《食货》第2卷第10期、第3卷第2、3期,1935年12月。
㊺陈啸江:《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厦大周刊》第12卷第13期,1932年12月。
㊻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序》,《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
㊼见《食货》第2卷第7期,1935年9月。
㊽㊾㊿(51)(54)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2)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页。
(53)(5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见汤明檖、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6页。
(55)《通讯》,《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
(56)王海欧:《编辑的话》,《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
(58)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
(59)梁启超:《历史统计法》,《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1923年。
(60)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刊上的物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
(61)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商务印书馆1933版。
(62)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1933年5月。
(责任编辑张卫东)
K092
A
(2017)06-0016-09
阮兴,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