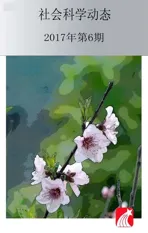词语·观念·思想史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重意
2017-04-10何晓明
何晓明
学术反思
词语·观念·思想史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重意
何晓明
历史文化语义学应包含词语、观念和思想史三重意蕴。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词语,在此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不过,历史文化语义学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尤其注重其蕴涵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在此层面上,社会语言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一般地辨析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考析,厘清人们特定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并确定其在民族思想流变的时、空坐标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更加缜密、精细和圆融的水准。就词语、观念、思想史三重意蕴表达的圆融通达而论,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堪称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典型范本。
历史文化语义学;词语;观念;思想史
大约十年前,冯天瑜先生根据自己长期学术探索的体会、感悟,出于推动思想史、文化史向纵深拓进的考虑,倡导开展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本文拟对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厚重意蕴稍作剖析,敬祈方家指正。
我以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应包含词语、观念和思想史三重意蕴。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词语。在此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要略》引述黄季刚先生的论断:“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①周先生列举了释义的经典方法(声训、形训和义训),又揭示了传统训诂学的若干弊端(如厚古薄今、烦琐寡要、穿凿附会、增字解经、随意破字、拆骈为单,等等),这些都为今天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技术工具和方法指导。
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同于传统训诂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区别是它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更加注重其蕴涵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在此层面上,上个世纪国内兴起的社会语言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论道:“我们的社会语言学将从下面三个出发点去研究语言现象:(1)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3)语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显示。”陈先生强调,社会语言学探索的两个领域,一是探讨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引起语言的变化,二是从语言的变化探究社会的变化。②这一认识无疑是历史文化语义学得以成立的学理依据的一般性表达。
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一般地辨析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考析,厘清人们特定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并确定其在民族思想流变的时、空坐标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更加缜密、精细和圆融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本身的内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④就此而论,如果说社会语言学是传统训诂学与现代社会学联姻的产物,那么历史文化语义学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在观念史、思想史方向上的专业开拓与深化。换言之,历史文化语义学同时具有词语、观念和思想史三重意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⑤所以,“就中国近代新名词的整体结构而言,仅仅将其理解为单纯语言学含义上的词汇,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它们乃由三个层面的内涵构成,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它们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⑥
近代以后,中国的思想话语系统中的某些重要词语之所以会出现歧义纷繁的现象,与这一时期世界文明大冲突、大交融背景下的中西日文化互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⑦中国现代思想话语系统里的最基本词语,如: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民族、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几乎无一不是这种“借贷和交换”的产物。
革命,最早见《周易》的卦义解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改变、除去之意。革除夏桀、商纣之命,意义不仅在杀掉两个人,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机器的颠覆、政治权力的转移、社会秩序的重构。伴随这一过程的,既有胜利、成功、光彩和荣耀,也有混乱、失败、破坏和屈辱。其价值判断,以判断者的立场不同而多歧,甚至根本对立。在近代中国思想话语系统里,革命与外来的revolution对译。据研究,这一作法由日本人首创。公元6世纪,《周易》传入日本。8世纪后,“革命”已融入日语系统。此时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已成天经地义的民族共识,因此,日本学人对于以皇权易姓为标志的中国式革命,并不取认同态度。但是,这一态度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使用“革命”这一词语,来表达对制度重建、社会改良的积极评价。与“汤武革命”不同的日语“革命”,不含暴力夺权、改朝换代的意义。明治维新时代,“革命”其实是“尊王变革”。这与中国稍后发生的戊戌“变法”,意义几乎完全相同。英语revolution源自拉丁文,原指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14世纪到18世纪,revolution的内涵经历了“叛乱”到“变革”的转变,兼有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双重意蕴,词性也由贬义转为中性或褒义。日本学人接触到revolution后,将其翻译为“革命”,既可指英国式的温和变革,也可指法国式的激烈革命。
1890年,王韬著《重订法国志略》,其中有“法国革命”的说法。这是近代中国话语系统受日本影响,以“革命”对应revolution之始。其后的中国学人陆续援用此法,渐成风气。如果仅从古词语表达新观念的意蕴层面看,考察到此似乎已可告一段落。如果要更进一步,辨析立场各异的学人如何理解“革命”的精确含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不同的学理分析和价值判断,则必须进入思想史的领域,从而完成历史文化语义学意义上的研究过程。例如,梁启超基于对“革命”兼有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双重意蕴的理解,一方面热烈鼓吹“诗界革命”、“宗教革命”、“资生革命”、“女权革命”,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彻底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现实“政治革命”。而陈天华则取“革命”涵盖政治、道德诸领域的极端进步意义,大声疾呼“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⑧从此,兴中会的排满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等,均将革命的正面价值发挥到极致,而将一切怀疑革命,阻扰革命,反对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统统归于扫荡之列。如此这般的后果如何评价,至今仍然争议不断,众说纷纭。而求得共识的认识前提,当在为“革命”正名。在此方面,历史文化语义学大有可为。
“人民”一词,在古籍中出现很早。《史记·乐书》即有“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亦作“民人”,《汉书·王莽传》有“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均为臣民的意思,其近义词为氓、百姓、黔首。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惠顿的著作Elementsof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万国公法》,其中用“人民”翻译“citizen”。这一用法悄然改变了其中国古义,实际表达了具有近代政治色彩的法治、民权、公民等观念。从古代的“人民”到近代的“人民”,词语本身丝毫未变,但其表达的观念天地翻覆。这种词语与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也只有在思想史流变的研究框架内,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确定的意义。
Citizen,更准确的中文对译是国民,公民。从观念层面讲,国民或公民意识的养成,与人们对“国家”意义的现代理解和把握直接相关。梁漱溟说:“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⑨1899年,梁启超就论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⑩直到1901年,思想激进如陈独秀者,“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⑪这正是近代不同于“臣民”的“公民”意识的肇端。不仅在野人士有此认识,在朝官员同样如此。1907年,孙宝瑄在日记里记载:“前闻荫亭言:我国今日为治,当区民为三等,最下曰齐民,稍优曰国民,最上曰公民,一切纳赋税及享一切权利,皆截然不同。而国家亦须设三种法律以支配之。其有欲由齐民跻国民、由国民跻公民者,必其程度与夫资格日高,然后许之。如是则谋国者方有措手处。余以为然。”⑫朝野上下“共识”的形成,说明思想史上的启蒙时代已经到来。
我们再看与“人民”、“公民”等词语意义密切关联的“民主”。
民主,是《尚书》、《左传》等先秦文献里即出现的古典词语。“天为时求民主”⑬,“天命文王,使为民主”⑭。“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⑮这里的“民主”,即“民之主”,是君王的意思。数千年后的1870年代,这一词汇被《万国公报》用来介绍美国总统:“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已百年矣。”⑯就最高统治者这一层意义看,这里的“民主”与《尚书》《左传》的用法相近。但从这“主”是否“民”选,“主”权是否“民”授来看,则《万国公法》的用法显然依据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观念,而《尚书》、《左传》的用法则契合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上古政治现实和政治观念。两者的思想史定位和价值定位,距离不可以道理计。
有论者列举了《万国公报》以后媒体上出现的“民主”的四种含义:(1)民之主,指皇帝;(2)民主之,指人民支配和人民统治;(3)与世袭君主制度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国”、“民主党”;(4)外国民选最高国家领袖。⑰并进一步分析了1864年至1915年间不同含义“民主”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发现第2、3种含义的“民主”(对译英文democracy)被广泛运用,以中性介绍为主,但负面评价逐渐增多,尤其是1900年以后更甚。第4种含义的“民主”,在1895年出现了使用的高峰。论者分析这种态势出现的原因是,戊戌时期,主张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士人信奉“西学中源”说,将其比附为三代的大同。“正因为把民主视为古已有之的制度,民主的第四种含义(民选最高统治者)在1895年才出现高峰”⑱。维新运动失败后,专制势力抬头,所以对“民主”的负面评价相应增多。1905年以后,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声势日盛,立宪派的实际政治操作也渐入佳境,“民主”的使用频率再现高涨。尽管其中负面含义的用法依然占据多数,但终究表明思想史上不可抗拒的民主时代,已经来临。
从现实政治生活的样态考察,人民民主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与人民是否拥有思想“自由”直接相关。严复当年曾一语破的,称近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⑲。针对国人对“自由”的误读,他辨正道:“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肆、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⑳近来,有学人详尽考察了中国思想语境中的“自由”语词源流。“自”、“由”二字,甲骨文中即出现。最早出现“自由”一词,当见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后郑玄、应劭也用过此词。这一类“自由”,正如严复所论,“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汉唐间史书多用“自由”,基本沿袭“遵从自我或自我做主”的词义,但已经出现皇帝应该“自由”而权臣不可“自由”的明显价值判断意味。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佛经多用“自由”,指称超越生死、天地和轮回的神通自由。禅宗兴起,融和佛教与老庄学说,慧能《坛经》等数十次使用“自由”,其义不再强调必须脱离世间、修行证悟、隐身遁形,主要指精神上的自由无碍。隋唐以后,全真教日见兴盛,教徒以“自由”描状个人摆脱尘世、得道成仙的逍遥体会。南宋以降,儒、释、道三教融合,“自由”使用更为普遍。但多数学人都对“自由”持拒斥态度。简言之,中国传统思想语境中的“自由”,与国家制度、伦理关系之间,存在难以化解的紧张。这与西方自古以来“自由”与权威、法律、国家互补、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㉑近代以降,“自由”在中国成为老百姓迷茫、启蒙者竭诚呼吁的疑难话题,只有通过词语、观念、思想史层层递进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才能最后揭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答案。
如论词语、观念、思想史三重意蕴的圆融通达,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当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范本。
“封建”一词,本来表示的是古代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样态,即封邦建国。后来“封建”被用来命名从秦朝至晚清的社会经济形态,表达的是史家关于历史演化规律的系统观念。这一观念其实已经与作为名词的“封建”本义距离遥远。进一步考辨这“封建”观念与“封建”名词所指代的历史事实之间说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发现其反映的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关系到学问宗旨、理论建构、价值基准、文本阐释诸方面的重大疏漏与缺憾,因此,对其正本清源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还“封建”名实关联以本来面目,也不仅仅在于为自秦至清的中国历史阶段寻求一个名实相符、意义精准的称谓,而是在于清醒揭示学界数十年来“积非成是”的认识误区,扫除“约定俗成”的懒汉陋习,让实证与思辨圆融结合的灿烂阳光,长久照耀我们的思想世界。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前景广阔,我们满怀希望,乐观其成。
注释:
①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②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③④《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25页。
⑤⑰⑱金观涛等:《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7、257页。
⑥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新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⑦转引自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⑧邹容:《革命军》,《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0页。
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⑩梁启超:《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9页。
⑪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⑫《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6页。
⑬《尚书·周书·多方》。
⑭《尚书·周书·洛诰》。
⑮《左传·文公十七年》。
⑯《选举民主》,《万国公报》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⑲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⑳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㉑胡其柱:《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中的“自由”语词源流考论》,《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卫东)
K03
A
(2017)06-0005-04
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