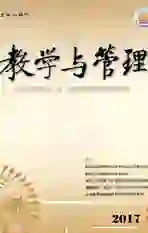部编教材“教读”课型的定位与教学策略
2017-04-10傅登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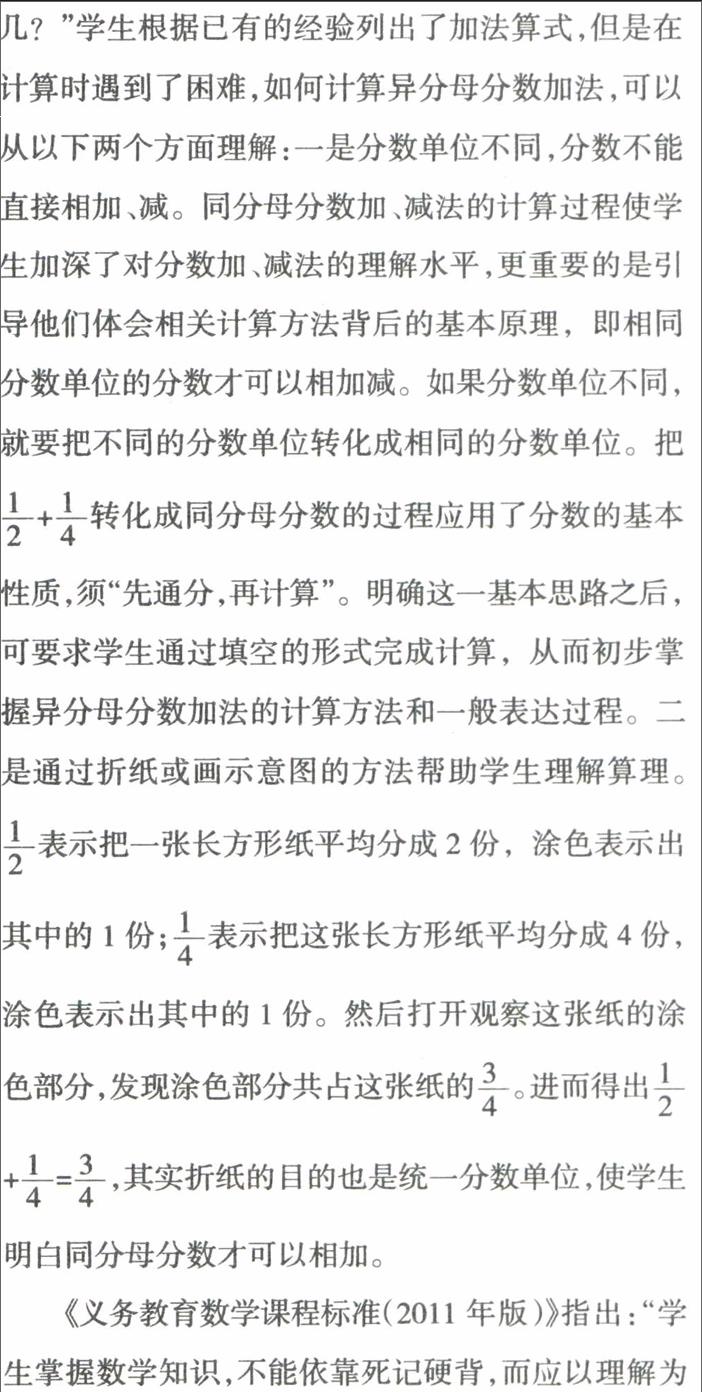

部编语文教材,在课型名称上作了重大修改,把原人教版“精读”改为“教读”,改“略读”为“自读”,增加了“课外阅读”,共同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课型结构。“教读”与“精读”区别有哪些?“教读”课型如何理解、定位?如何发挥“教读”课型在深化课程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如何发挥“教读”在“自读”和“课外阅读”两类课型中的引领作用?“教读”课型该采取怎样的教学策略?等等都是部编教材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读”课型具有鲜明的贯通性
“教读”不是“精读”的翻版,而是课型的重新定位。“教读”顾名思义,是教师教学生阅读或教会学生阅读。“教读”课型不仅要教会学生对言语的理解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学会阅读方法。如针对年级、内容和目标要求学生掌握默读、浏览、快读、跳读、猜读等常用的方法。通过系统、持续推进的教学过程使学生习得整体阅读、厚书读薄、薄书读厚、口诵笔述、分类阅读、比较阅读等方法,也就是说“教读”课型的关键是化“教”为“读”,将教师“教”的主导性转化为学生“学”的主体性。
1.“教读”课型趋于内容明确
“教读”课型所涉及的内容很广,但千万不能再延续“精读”课型的做法,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课文有什么就教什么,既不考虑学情,也不顾及教学目标。“教读”课型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说的:“双线组织单元结构:一条是按照‘内容主题组织单元,但又不像以前教材那样予以明确的单元主题命名;另一条线是将‘语文素养的各种基本‘因素(‘双基、学习策略、学习习惯等)分成若干个‘点,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分布在各单元课文导引或练习题设计中。”“在教材呈现和教学中不要刻意强调体系,防止过度操练。但总得让一线教师使用这套教材时有‘干货可以把握,一课一得——把学段知识能力目标落实到教材单元之中。”也就是说部编教材“教读”课文,不仅有“点”可抓,更有“干货”要落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因“精读”课型所带来的“教什么”的模糊性而导致教师教学的随意性。
2.“教读”课型单元整体贯通
“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不仅在词义上贯通,层层推进,而把阅读过程从主体引向自主,这个不断开放的过程符合学习认知、实践和运用的学习发展规律。由“教读”的认知、得法,到“自读”的尝试、实践,再到“课外阅读”的运用、熟练,三类课型自然衔接、层层推进,这样更有利于整体贯通,整体提升。这样的单元组合思路同样也适用于现行的人教版教材,如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一组“祖国大好河山”单元,安排了《古诗词三首》《桂林山水》《记金华的双龙洞》《七月的天山》四篇课文。《古诗三首》主要通过充满音律的景物描写展开想象,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向往之情;《桂林山水》采用了“总分总”结构分类描写景物;《记金华的双龙洞》采用“移步换景”、曲径通幽的描写方法;《七月的天山》集“移步换景”与“抓住景物特点”描写于一身。如果采取“教读”—“自读”—“课外阅读”单元组合思路,教学中可以采用“激发思维—习得方法—实践运用—课外延伸”的设计思路,深化阅读教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教学需要贯通性,“教读”课型不仅贯通于一个单元,而且还贯通单元之间,甚至贯通整册课文和全套教材。这就有效避免原人教版教材为了凸显“人文”主题而导致的目标不明、序列不清。
二、“教读”课型强调阅读的方法性
有人把小学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概括为理解、运用、思维和初步的审美。把思维纳入核心素养,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把思维发展的隐形目标提升为教学培养的显性目标,这样教学依据更清、目标更明,落实更理直气壮。再说,任何方法都需要思维的支撑,阅读方法也不例外,其实知识是容易和可以遗忘的,而正确的思维和有效的教学方法却能够受用终身。“教读”课型的核心是培养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1.方法的重要性
温儒敏教授就部编教材说,教的内容应侧重方法的授予。教给方法,让其得法后运用,教就有意义,就能够影响学生阅读的发展路径,改变学生阅读的情态。同时,教方法也是让其在“自读”与“课外阅读”时能有“法”可依,得“法”用法是解决问题的需要。“精读”课型只在“文本解读”上下功夫,极为强调“个性化”,不断在挖掘“言外之意”上一比高下,成年化解读和强制性灌输的教学方法的流行,严重忽略了学生得“法”、用“法”学习的切身需要。学生阅读确实需要沉浸于文字间,体悟字里行间的表达密妙,但他们更需要在阅读范本中归纳总结,发现可借鉴、用得上的方法[1]。
2.教“法”的有效性
阅读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的核心是閱读方法。如课程准标中提出“默读”“浏览”的目标要求,而在以往的“精读”课型教学中,多数教师只是提出“默读”“浏览”的要求,但很少有教师教“默读”“浏览”的方法。方法不落实,少习得,效果自然难以显现。如何阅读,可以简单概括为:应该看什么地方和从这些地方应该看出什么来。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五组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回忆录课文,教师应该结合故事内容的解读,教给学生如何写的方法。在与学生共同研读文本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回忆录的作者亲见、亲闻、亲历对于历史题材回忆录写作的重要性。同时,感受作者如何注重记叙中的细节,将每个生活细节串联成故事情节,以情节凸显历史人物的气节[1]。再如,“伯父摸着胡子,笑了笑,说:‘哈哈!还是我的记性好。”一个句子连续用三个动词,就把当时的情境生动地再现出来。首先要让学生发现,然后关注动词之间的逗号,“摸着胡子,笑了笑,说”这三个动作原来是一气呵成的,不可能有逗号。逗号是表示动作的停顿和延缓,这里不可能停一停。为什么要逗号?这就是回忆性文本有两个“我”:一个是当时的“我”,一个是写作时的“我”。作者把他对“我”的反思放在里面。以上两点就是读懂回忆录写法的核心要义,需要依托教学传授。在教学之后,还要鼓励学生用上这样的方法尝试为身边人写一段回忆。“教读”课型要实现得法课内,延伸课外,服务实践[1]。
“教读”课型的方法,包括理解和表达,即言语内容与形式,有时也被称为知识或能力,如阅读知识、写作知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但不管称呼如何变化,其核心还是“方法”,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会用,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教读”课型注重文体的适切性
多年来小学阅读教学“文体”意识比较淡漠,不管哪类文体的课文多数教师都采用统一的教学模式,如背景介绍、整体把握、理清结构、逐段讲解、总结延伸,重点聚焦“富含深意的语句”“文字中的真情实感”。导致阅读教学在低效中徘徊,写作能力也难以提升。
1.文体不同教法不同
写作是文体思维,阅读显然要遵循文体思维。“教读”课型注重了文体的适切性,便于教师拿到一个文本后从文体思维出发考虑“应该看什么地方和从这些地方应该看出什么来”。如故事类(童话、神话、寓言等)重在复述;诗歌(童诗、古诗、现代诗等)重在诵读、背诵、默写;记叙文重在梳理“四要素”;说明文重在表达方式;文言文重在古译今;绘本重在图文结合;非连续性文本重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和运用;整本书重在兴趣、方法;[2]章回小说适合评书播讲等。把阅读装进文体的笼子,统一指向“文体阅读”。同时也要关注同类文体不同文本的阅读方法和重点差异。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七组“动物小说”单元,可以从文本线索探索阅读方法。如《老人与海鸥》作者抓住“老人喂海鸥”“海鸥送海鸥”两个感人的场景,两相对照,使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情节互通,在情感表达上和思想传达上相得益彰。《跑进家来的松鼠》叙述了三件事,而串起三件事的是“我们”一家对松鼠的喜爱之情。《最后一头战象》选择的是战象临死前的表现,课文的线索是回忆与现实的交融,是读者在战象近乎于人的行为中感受到它的悲壮与豪迈。《金色的脚印》则是明线与暗线穿插展开,老狐狸为解救小狐狸所做的种种努力,正太郎对狐狸一家的态度变化,使这个故事变得丰满而感人[3]。
2.阅读方法与文体适切
多年来语文教学对阅读能力的研究,持有的是抽象的阅读能力观。几乎每篇课文、每堂课,语文教师所设计的活动都大致相同,朗读、概括大意、品味语言等等。其逻辑是,阅读教学中用不同课文培养学生几种核心的阅读能力[4]。这是个伪命题。其实阅读方法既取决于阅读取向、目的,又取决于文本体式。也就是针对不同的阅读对象,需要借助已有的阅读经验,灵活地采取与阅读对象相匹配的阅读方法。再说,“教读”课文绝大多数属散文范畴。什么是散文,有人说,除诗歌外、小说、戏剧之外的文章都叫散文。散文研究专家南帆也说“散文无规范”,也就是说散文就是“散”文,一个作家一个样式,一个时代一个样式,一个人一个样式,没有规范。散文最难读的地方,或者说好散文之所以是好散文的地方,就是作者的感受和经验超越了常人。散文的阅读和鉴赏,重点是语言的精准和作者精准的言语表达出的人生经验以及经验的分享[4]。如《生命,生命》通过举例展现作者对生命精神的独到感受和体验。《珍珠鸟》通过动词表达情感,系统的动词表达细腻情感的妙用,以及小珍珠鸟、老珍珠鸟明暗交错的结构安排。只有沉浸于文本语境中细细品味,才能把握文本的要义。阅读教学要在鼓励学生持续的海量阅读中,不断积累、整合和提升阅读的基本方法,并逐步形成个性化阅读素养。
从文体或相同文体不同文本出发探究和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是阅读教学有效性的追求,但由于荒废多年,更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做更多的探索,从“教读”课型中提炼出具体的阅读方法,并在“自读”“课外阅读”课型中逐步走向成熟。
四、“教读”课型展现样态的多样性
本次“教读”课型包容了多种样态,如整本书阅读教学、单元组合教学、主题教学、研究性阅读等。“教”的意味在样态上得以体现,例如,整本书阅读的教读课,既能教给学生整体性、持续性的阅读方法,带来更为真切的阅读感受,又能拓展阅读面,扩大阅读量。同时,阅读整本书的过程中,自然涵盖浏览、快读、猜读、跳读等各种方法,还有助于阅读习惯的养成。这些变化都是原来“精读”课型无法预想的。
1.把现用教材纳入“教读”课系
目前部编教材仅一年级上册在使用,其他年级还在使用原有教材,面对这种状况,教师应尽快与部编教材理念衔接,对所使用的教材进行改造,使“精读”向“教读”转换,“略读”向“自读”转换,增添“课外阅读”。如对上文提到的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七组“动物小说”单元,改造为单元统整教学。《老人与海鸥》《跑进家来的松鼠》《最后一頭战象》《金色的脚印》是四篇不同语言风格、不同地域、不同作者背景的文本。《老人与海鸥》的作者邓启耀是一位人类学教授,他的语言表现在情感性与客观性之中。《跑进家来的松鼠》的作者是俄罗斯的斯科列比茨基,他的语言比较夸张,用艺术手法表现个性。《最后一头战象》的作者动物小说家沈石溪对战象的描写更趋人性化、深刻化。椋鸠十是日本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他所写的《金色的脚印》则故事性更强,简洁、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构成了和谐完美的整体[3]。进行对比阅读,引导学生发现差异,感受多种写作方法,想必学生的收获比单篇“拆开来、揉碎来,细细碾压”式教学大得多了。
2.对典型文本作深入挖掘
“教读”课型的教学,要站在整体的高度、整体推进,克服单篇教学所带来的弊端,但同时也离不开对单篇文本教学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整合,为样态多样性教学提供更宝贵的资源。如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四组“感人的故事”单元,《桥》一文是小学阶段唯一的一篇小小说文本,教师一定要精准把握这一文本的表达要义。如惜墨如金,语言简洁、准确,极具感染力;故事情节曲折、感人;结尾往往出人意料、印象深刻等。又如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生活启示”单元中《落花生》一文是详略得当的文本经典。该文写了种花生、收花生和议花生三项内容,种花生和收花生仅用了短短的81字来介绍,而大量篇幅是写议花生。显然仅仅从内容多少上来判断“详略得当”是不够的,更要从言语表达上去认识。为此,有教师设计了这样几个阅读问题:(1)“播种”的“种”这里该是读zhǒng还是读zhòng(为保持词语“动宾”的一致性该读zhòng)?(2)“买种,播种,翻地,浇水,没有几个月,居然收获了”中“买种”“播种”“翻地”“浇水”之间为什么用逗号而不是分号?(3)这样表达作者有什么意图?(用上逗号说明种花生、收花生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用词语表达是为了简洁。另外用上简洁、明快的词语表达与后面“居然收获”喜悦之情相呼应。)
在认识“教读”课型后,“自读”课型也就很明白了。让学生自己读,教师少干涉。读得自然,即便一知半解也无妨,因为有“教读”课进行专业、集中的补充。“课外阅读”更是明朗化。课堂得法,形成阅读习惯后,鼓励学生课外海量阅读。让阅读成为学生“语文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生的永恒姿态[1]。
参考文献
[1] 何捷.部编本教材“教读”课型的理解定与位[J].中小学教材教学,2016(11).
[2] 傅登顺.习作知识生成的土壤与特性表征[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6(9).
[3] 傅登顺.寻梦十年——特级教师傅登顺语文教改观[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5).
[4] 王荣生.阅读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陈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