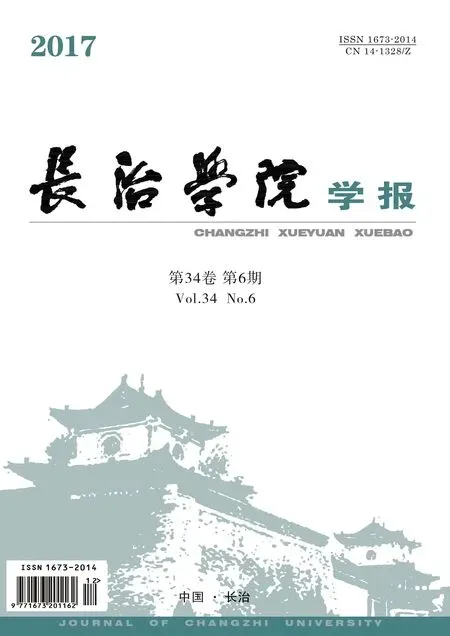《恩惠》:有色人种女性的身份缺失与“后种族主义”迷思
2017-03-29陈新
陈 新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长治 046011)
睽违五年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带来了自己的第九部小说《恩惠》(2008),此书一经出版便迅速引起各界关注,并于2008年年末被《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评选为年度“十大最佳图书”之一。与她以往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呈现了两个崭新的视角:首先,莫里森史无前例地将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在17世纪末的美洲大陆,那时,奴隶贸易尚处于萌芽阶段,奴隶制也尚未与肤色划等号,莫里森在访谈中表示,其目的是“为了将种族和奴隶制度分离开来,看它可能会呈现的样貌”[1];其次,新世界中所有主要的种族类型都被聚集到小说中——黑人、印第安人、混种人、白人,这打破了莫里森在以往作品中探讨种族问题的模式,不仅聚焦黑人,同时也关注了不同种族和不同肤色的其他人种。
小说以一个十六岁黑人少女佛罗伦斯的讲述为线索,首次呈现了一个多元文化团体,将伐尔克的农场描绘成一个主流社会边缘人扎堆的地方,这里有被迫与母亲分离的黑人奴隶少女佛罗伦斯,有部落覆灭的印第安女子莉娜,有混血奴隶莎罗。在白人至上的男权社会中,白人与非白人、男性与女性的二分法导致了一种二元思维,即“一方并不仅仅是与另一方不同, 而是根本与另一方对立”[2]。在这样的对立关系中,便出现了“高”、“低”之分,为了合理化“高级”一方(即白人和男性)的统治,那些“低级”的非白人和女性便被物化为了“他者”,从而失去了自我和主体性。小说中的这些有色人种女性皆是如此,她们在白人至上的男权社会中,同时遭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被物化、无法走出过去的创伤、遭受文化错位、被孤立……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她们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缺失。
一、佛罗伦斯:被困在过去的黑人女孩
因为其母亲的黑人奴隶身份,佛罗伦斯生而为奴,她被剥夺了为“人”的权利,仿佛是一件随便的商品,可以不断被男人任意交换买卖。例如,她的奴隶主和伐尔克达成交易后,她便如同一件货物一般被以“二十枚八先令”的价格卖了;此后,她成为了伐尔克和他妻子的财产,在去寻找铁匠的途中,她的身份和自由全凭女主人丽贝卡的一封信决定,信上说:“她属我所有”[3]。她抵达一个清教徒社区后,发现一个年轻女孩正被当作魔鬼而遭到迫害,而佛罗伦斯的面孔使她成为了女孩的替罪羊,因为她的黑皮肤表明了她的与众不同,同时也表明了她的罪恶:“一个女人开口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黑的人……她是非洲人,是非洲人,而且黑得多,又一个说……魔鬼就在我们当中,这是他的奴仆”[3]。他们将她的肤色与魔鬼联系起来,羞辱性地检查她的身体,以此来确认她“不为人”的资格;她们看她时如同在看待另外一个物种,眼神中没有任何对她人类身份的认同,佛罗伦斯感到:“自己已经不一样了……某种宝贵的东西正在离我而去”[3]。此刻佛罗伦斯的“被种族化”使她的内心产生了巨大转变:此前,她的肤色和她所遭受的奴役之间仅存在偶然联系;此后,她的肤色成为了魔鬼的标志,真正变成了其被奴役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导致她身份缺失的关键因素是家庭的湮灭及舔犊之爱的缺失。父母之爱和家庭教导在一个人主体性建立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好的母女关系可以充当心灵港湾,也可以使孩子明白“自我定义”的重要性,对黑人母亲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她们充当着传递祖先智慧的传统角色,一旦母亲与孩子间的联系被切断,孩子便也失去了与自己种族的联系。小说中,佛罗伦斯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弃女”行为是出于对她的爱和保护,她只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内心深受创伤,后来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的小男孩还在吃奶。带走女孩吧,她说,我女儿,她说。就是我,我”[3]。两个“我”字的连续使用,表现出佛罗伦斯的极度震惊和困惑,这个场景在书中出现多次,前后呼应,表明过去的记忆仍持续地影响着佛罗伦斯现在的想法和行为。从那之后,佛罗伦斯便被“被抛弃”的恐惧笼罩着,她开始变得渴望爱与情感:“她对每一分关爱、每一次的轻拍脑袋和每一个赞许的微笑都深怀感戴”[3]。后来,这种“对母亲的渴望”则转化成了对铁匠的疯狂迷恋,从而进一步导致她失去了自我。总之,佛罗伦斯无法走出过去的创伤,身体和心灵都被禁锢,无法找到自我或进行自我定义,而佛罗伦斯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她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无数黑人都遭受过类似的苦难。
二、莉娜:错位的印第安人
莉娜是一个印第安人,她的部落因天花而几近覆灭,她幸存下来但却永远失去了家园,而因为害怕再次“失去住所”或“孤独地活在世上”[3],莉娜被迫承认“她(自己)是不信教的野蛮人,任凭自己被(欧洲价值观)净化”[3]。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她意识到自己的印第安文化被认为是野蛮且有罪的:“赤身裸体在河里洗澡是一种罪孽;从果实累累的树上采摘樱桃是偷窃行为;用手抓玉米糊吃是种怪癖”[3];她失去了原本的名字:“她们给她起名叫麦瑟琳娜……但素常都缩成小名叫莉娜”[3],象征着她与自己种族之间的联系自此断裂。由此可知,在白人文化的绝对统治下,印第安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语言及其他一切,祖先的文化遗产被掠夺,联系也被切断……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支撑,印第安人被强行灌输了“非白人就低一等”的想法。后来,尽管莉娜努力尝试融入白人文化——她做白人做的事,以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但她最终还是像一件商品一样被卖掉,卖她的广告词这样写到:“吃苦耐劳的女性,已皈依基督教,能做一切家务,可用货物或钱币交换”[3]。
作为一个非白人,莉娜深受白人至上主义侵害,同时作为一位女性,她也无法逃出男权至上的压迫。她曾多次被她的“爱人”虐待:“他那两次生气时用了他的手掌……之后有一天,他先用了拳头,后用了皮鞭……”[3],这些描写清楚地表明当她努力融入这个新社会时,该社会当中的成员再次将她拒之门外。在白人至上的男权社会中,莉娜永远是“异乡人”,她自己的印第安文化和白人社会都无法成为她的归宿,她无家无根,正如她对着那些树说的:“你们和我,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家园……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这里背井离乡”[3]。这样的文化错位也使莉娜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我。
三、莎罗:格格不入的混血儿
生活在船上的混血儿莎罗遇到海难后,就变成一个被原来生活抛弃的孤儿,被锯木工救了之后,她被随意给予一个新名字:“你想怎么叫她都行,我老婆叫她莎罗(Sorrow),因为她是个弃儿”[3],从某种意义上说,莎罗和莉娜一样,都被别人重新命名,没有归宿,颠沛流离。除此之外,莎罗还被当成了一件泄欲工具,一次是在她十一岁时,“发生在隔板后面的,那两兄弟(锯木工的儿子)当时都参与其中”[3],另几次则被认为是“在一堆木头后无声地顺从于一种缓慢进程或是在一条教堂长凳上匆忙了事”[3],莎罗从未感受过爱,她意识到自己只是男人的“玩物”而已。莎罗怀孕后,锯木工和他的妻子并不接受她肚子里的孩子,而是急于摆脱她,将她送给伐尔克,因为她“有点混血”[3]。
此外,莎罗还遭受了来自小社区(伐尔克的农场)里其他成员的敌意和孤立。莉娜认为莎罗“本人就是厄运”[3]、“是天然的诅咒”[3],她应该为伐尔克和丽贝卡孩子的死负责,她也不被允许接近佛罗伦斯:“每当莎罗靠近,莉娜就命令她走开,或是打发她去干急需要干的活”[3],没有人关心她,甚至没有人和她说话。莎罗遇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殖民者的,一个是被殖民者的”[4],而她则被卡在中间,即霍米巴巴提到的“第三空间”。作为一个混血儿,她没有归属感,因此她更加封闭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仅与分裂出来的“另一个自己”交流。莎罗的混血身份和女性身份交织作用,使她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从而无法建立自主性及获得自我实现。
四、托尼·莫里森对“后种族主义”迷思的批判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许多评论家和媒体称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期”(post-racial),即人们的命运不再与他们的肤色有关,种族在当代美国已经不再重要。米尔顿·威克曼进一步指出“后种族主义”包括的四个主题:“多样化”、“对有色人种不戴有色眼镜”、“政治上对有色人种不戴有色眼镜”、“种族歧视的终结”[5]。“多样化”指美国种族景观的多样性,20世纪时,对美国来说,“种族”主要指“黑人”和“白人”,因此,多样化人口超出了历史上“种族”一词所包涵的范畴,而这进一步催生了“传统的黑人与白人间的种族障碍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的信念;“对有色人种不戴有色眼镜”是“后种族主义”的基本核心,它认为在当代美国,能力和自我努力(而非肤色)才是决定一个人向社会上层流动和取得成就的原因,种族与美国人的生活无关,应当被忽略;“政治上对有色人种不戴有色眼镜”认为种族已不再对美国大选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而奥巴马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种族歧视的终结”反映出一个信念,即“美国已经超越其历史上的种族模式”,白人尤其倾向认为种族问题已经是过去式了。
然而奥巴马的成功真得标志着“后种族时期”的到来吗?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种族歧视并没有消退,只是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新种族歧视的一部分”[6]。旧形式的种族歧视被称为“Jim Crow种族歧视”,可概括为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包括:种族间的社会鸿沟、“黑人从生理上就低人一等”的想法、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种族隔离政策的赞同等。而新形式的种族歧视则更微妙,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对少数族群的负面感觉,并反对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种族关系,可以说其实质仍是维护旧的种族秩序,维持白人特权。有研究发现:在收入、财富、房屋、教育、职业以及有色人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仍存在着“种族鸿沟”[6]。
由此可见,“后种族主义”只是一种迷思,即: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只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定义并曲解的概念,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但假设美国已经进入了后种族时期显然很危险,因为它很可能会忽略或掩盖社会中仍旧存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恩惠》出版于奥巴马当选后一周,莫里森在采访中曾用“先种族主义时期”(pre-racial)来描述小说中17世纪末的种族景观,通过与“后种族主义时期”相比,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相似之处:一是种族多样化,二是似乎都不存在“种族主义”——一个在其开始前,一个在其结束后。因此,尽管莫里森将她的时间线设置在过去,但其作品中却充斥着对当代美国的思考。对于“后种族主义时期”这个词,她在采访中也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我有点不喜欢这个词……似乎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些我认为不真实的东西,即我们已经抹去了种族歧视”[7]。显然,莫里森也认为“后种族主义”是一个迷思,不加批判的盲目接受是很危险的。
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也演变为了一种更“现代”的形式,旧形式的性别歧视认为性别不平等是天然的,甚至是可取的;而新形式的性别歧视则是否认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并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反对女性角色的转换。而在这之中,有色人种女性则拥有更低的地位。
五、结论
在普遍盛行的白人至上意识形态下,《恩惠》中的有色人种女性,包括佛罗伦斯、莉娜、莎罗,均成为了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而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她们也同样被认为低人一等。作为有色人种女性,她们被压在等级鲜明的名为“种族”和“性别”的两座大山底下,被当作“财产”,被迫与家人分离,被困在过去,被剥夺名字,被虐待,被错位,被孤立……正如佛罗伦斯的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伤口,即使结了疤,底下也永远生着脓”[3],以上种种所有都导致了她们无法获得自我及建立自主性,也因此都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身份危机。
长久以来,莫里森都在通过她的小说探索如今美国的情况,作为一个作家,她的目的之一便是使读者“更愿意看到事物的另一面”[8]。基于此,在“后种族主义”和新形式性别歧视的语境下,莫里森通过创作《恩惠》这部小说,将有色人种女性这一边缘弱势群体带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启发人们对她们如今的身份问题和“后种族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同时也鼓励她们不断反抗多重压迫,继续与白人至上的男权社会做斗争。
[1]Morrison T.Toni Morrison Discusses A Mercy with Lynn Neary.[EB/OL].2008-10-27[2016-8-22].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5961382
[2]Collins P H. 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M]. 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2:77.
[3]Morrison T.A Mercy[M].New York:Knopf,2008:112,111,115,7,59,47,47,47-48,47,52,104,59,120,119,128,120,53,55,124,163.
[4]Jamili L B, Rad S F. Unhomeliness:Deconstructing Western MasterNarratives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J].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ofEconomics Development &Research,2011,26(2):310.
[5]Vickerman M.The Problem of Post-racialism[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9.
[6]Bonilla-Silva E, Seamster L. The Sweet Enchantment of Color Blindness in Black Face:Explaining the ‘Miracle,’Debating the Politics,and Suggesting A Way for Hope To Be‘For Real’in America.[G]//Go J.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Rethinking Obama.Boston: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1:141,142-143.
[7]Morrison T.Toni Morrison on Human Bondage and a Post-racial Age. [EB/OL].2012-04-18[2016-9-10].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8072491
[8]Lister R.Reading Toni Morrison [M].Santa Barbara:ABC-CLIO,200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