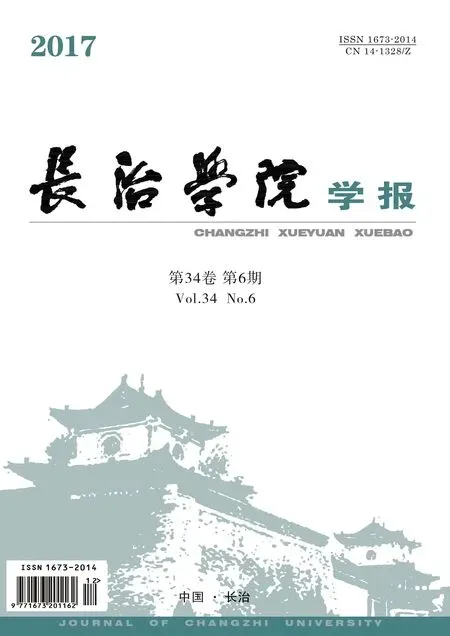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沈从文作品研究
——以“还乡”作品为例
2017-03-29陈影
陈 影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自人类诞生以来,女性与自然就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之母”盖亚的形象,还是老子“尚水、尚下、尚静”的女性自然哲学,都表明女性和自然的紧密结合。不断兴发的妇女解放运动和逐渐开展的生态运动共同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Eco feminism),同时作为女权主义和生态哲学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流派,于1974年被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德奥博尼在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她认为,统治自然和统治妇女有着天然而紧密的联系,社会高速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但几乎没有人从“父权制”社会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她在著作中对此展开论述,以此希望引起社会对妇女在生态改革中角色和地位的注意,同时号召女性觉醒、认识并拯救自己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1]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生态女性主义逐渐呈现多元化视角的解读和运用,但始终立足在两个焦点之上——女性和自然。沈从文作为我国重要的乡土小说家,其作品主要分为湘西和都市题材两类,其中湘西题材的作品立足于我国湘西地域特色,呈现出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文学作品中的还乡作为一种生命追求的象征,是对作者内心深处某种价值观的怀念与追寻。沈从文自身生活环境的骤然转变,使其把故乡作为精神补偿呈现出来。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从人与自然以及男性和女性方面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析和诠释,欲表明他对自然和女性生态问题深刻的忧患和思索,揭示出沈从文作品中蕴含的独特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最后试图架构起“人类/自然”和“男性/女性”等传统二元关系的绿色生态新图景。
一、人与自然——“诗意”地“栖居”
生态女性主义首先对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平衡非常重视,认为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组成部分之间是彼此联系、互相作用的,并且处于自然存在中的人与自然也是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的。希冀通过重新界定“自然”从而架构起新的人与自然的价值体系。使人类能够真正“诗意地栖居”。而海德格尔更是认为,诗意的创造使居住成为一种居住。“诗意”和“栖居”是如此紧密相连。在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人与自然就如同“希腊小庙”般和谐共存,栖居在沈从文“原乡世界”的人们和谐而诗意,具有和谐生态美因素。
这种和谐美首先表现在“天人合一”的诗性境界。我国老庄哲学中就已有“天人合一”的阐述,认为从本质主义来看,人和自然其实是相通的,例如老子就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是沈从文所有生态思想的基石,他认为“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是“绝好的宋人画本”,是“诗,一种纯粹的诗”。[2]379《边城》中因着住处两山多翠色逼人的簧竹,老船夫便给孤雏起名“翠翠”,船夫“哑哑的声音如同竹管声”,酉水高山、桃杏瓦墙的位置“与周围景致极具相同步调。”更进一步而言,尤其是女性形象,与自然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和亲密的相连性,是和大自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罗婷曾认为“女人与自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亲近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连性。”[3]166如翠翠、三三、老七、夭夭等女性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们和自然是同为一体的,是自然另一种生态存在的表现。可以说,沈从文具有女性化的生态意识。因而,在沈从文的“还乡世界”里,大自然的景致往往被赋予柔和的女性美,无论是《丈夫》中“烟雨红桃”同时表现了自然景物和船上的妇人。《三三》中的“金色竹林”同时映衬了竹林晚霞和打竹林走过的三三母女。这些女性似乎与自然联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相处,显示出自然和女性的光辉。在抒写美丽的“大自然的女儿”之外,沈从文更是把带有自然灵性的特质赋予了伟大的母亲。例如《菜园》这篇小说,可谓是沈从文写给母亲、写给自然的赞歌。清浅的故事情节,却洋溢着对土地和目前浓厚的深情韵致,形成了“菜园—土地—母亲”的内在联系方式。菜园不仅使一家人摆脱了生活的窘境,而且还使全城人都能吃上非常新鲜的蔬菜。这里的母亲勤劳朴实、素心清净,待人真诚。儿子在寡母的教育下也生长的知书明理、璞玉浑金、富有一切人性的美好。菜园和母亲正是自然和女性的共同伟大之处。
其次,和谐生态美体现在“爱有生一切”的生命态度上。崇尚生命、敬畏生命是沈从文生态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沈从文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他说:“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4]294沈从文的这种“生命之爱”是超越了个体生命和人类生命的爱,而是一种对一切生命的爱,对一切生命悉心的爱。同时,他曾在《烛虚》中说道:“我过于爱有生一切”。[5]277他的这种爱,是超越了物种,超越了生命的爱。从翠色逼人的簧竹到清致透明的白河,无不使人眼目欢快,从悠然嬉戏的蚱蜢鱼虾到自在歌唱的杜鹃黄莺,无不充满生命的灵动。还有《三三》中“咿咿呀呀唱着意义含胡的歌”的椿木水车,以及《贵生》中浅水里游荡的小虾子“躬着身子远远弹去,好像很快乐。”表现了沈从文对一切生命的挚爱和赞美,对一切生命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悦心,不仅是沈从文“爱有生一切”思想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是他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表现。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格里芬曾认为我们是“观察大自然”的自然。而沈从文正是自然的抒写者,在沈从文看来,自然具有伟大的母性情怀,她既生产着生命,又滋养着生命,而生命只有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契,才能获得“永生”,得到永恒的生命体验。
“天人合一”与“爱有生一切”散布在沈从文“原乡世界”里的每一片土地,人是无处不在的,自然也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从绿植鸟兽中窥见自然之巧与生命之巧的多方魅力,看到自然的完整形式,绽开缤纷的生命之花。
二、男性和女性——他者的“失乐园”
马克思曾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6]119如果说在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人与自然就如同“桃花源”般和谐共存,那么男性和女性则如“失乐园”般压迫与被压迫。在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人类(男性)在征服、统治自然的同时,女性作为自然的存在也难逃和自然同样的命运,女性已成为受虐狂和裸露癖的性别代码,成为被统治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人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和人类对自然的生态统治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都根源于父权制的社会构成等级观念,以及自古而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面对现存社会中生态和两性的双重失衡,沈从文从现实出发,基于人和自然,以生态主义思想和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关照其笔下的“原乡世界”。
在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女性悲剧表现的尤为明显,女性只能听从男性或者命运的安排。《边城》中,虽然沈从文淡化社会因素和男性形象,但是《边城》也并非“桃花源”般存在,其中仍旧弥散着两性生态不和谐的因素。大老看上了翠翠,但却对爷爷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有情人,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好媳妇。”[7]67显然,深受传统社会思想浸染的大老,认为“大自然的女儿”翠翠还不能够成为一个他眼中“合格的媳妇”。最后的结局,大老和爷爷死去,二老离去,翠翠一人独自等待着二老未知的归期。彰显了沈从文对男性霸权社会的忿然以及强烈的生态女性批判意识。在《三三》中,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大自然的女儿”——三三做媳妇,因为“这媳妇的妆奁是一座碾坊。”来乡下养病且已有家室的白脸男子看上并企图占有三三,管事先生也常常“制造机会”。《长河》中保安队长看上了滕长顺的橘子的同时,也看上了他的小女儿夭夭,并制造机会企图占有夭夭,而夭夭也只是巧妙的“反抗”,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可见,在这些小说中,女性作为弱势存在总是和自然、生命一样在男性的窥视和掌控之下,成为男性支配的对象。
如果说,三三、夭夭、翠翠等还只是男性窥视和支配的目标,并没有彻底沦丧为男性的傀儡。那么,在《萧萧》《丈夫》等中,萧萧、老七却完全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萧萧》中萧萧十二岁便做了三岁丈夫的童养媳,整日带着丈夫去玩,祖父说笑让萧萧做女学生却也不过是因为“打哈哈的趣味”以及“那被说的萧萧感觉一种惶恐”于是,“说这话不为无意义了。”被花狗引诱怀了孕,萧萧和花狗商量逃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但花狗却胆怯而退缩,最后一走了之,留下萧萧独自承受非议。伯父和丈夫家决定把萧萧嫁人作“二路亲”,后因生了个“团头大眼”的儿子,才有了“既是儿子,便不嫁别处了”的结局。这里女性地位和人格双重丧失,她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是由男性来决定她是生还是死,是留还是走。《丈夫》结了婚又不急于生养的妇人便被丈夫送到城里“做生意”,“名分不失,利益存在”。送老七来“做生意”的是丈夫,决定让老七回家过日子的也是丈夫。《贵生》中鸭毛伯伯看到金凤在哭,心中却说:“回去一索子吊死了吧,哭什么!”[8]96可知这里女性已经完全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了,自我没有决定权和选择权,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一切的命运都只能听从男性的安排。两性之间是不平等的,两性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不完整的。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在沈从文的城市系列小说如《如蕤》、《薄寒》等中看到了女性的积极主动和对男权的抗拒,城市女子对“成为公式的男子”的厌倦和主动渴求“人间本性的对面”,追寻自我独立的人格,说明男权统治下必然会引起女性对分庭抗礼的不懈追求。
可见,在“人类/自然”和“男性/女性”的二元思维模式下,女性永远是男性窥淫的“他者”,真正的性别生态和谐仍旧很难达到。沈从文正是从两性关系和谐的生态视角出发,通过对二元对立思想下两性不平等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男性话语霸权下的社会进行表现和剖析,同时,通过对女性生存状态、地位和命运的深层表现,试图为女性遭遇的不平等进行呐喊。这样,沈从文对自然生态和两性生态的认识就具有了更深的广度。他的自然观和女性观就不自觉地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同一和契合。
三、“人类(男性)/自然(女性)”——构建绿色生态新图景
若论性别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莫过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形成了一个二元论结构,但这种状况在实践层面和学术发展上导致了种种困境”。[9]236要想突破现有的性别“二元对立”的话语窘境,就必须解构这种对立局势。沈从文“原乡世界”的作品中始终保持着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生态状态,展示出其回归“桃花源”的心迹。因此,要建构沈从文作品中后果的生态和谐世界,重构“人类/自然”以及“男性/女性”的绿色生态新图景,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构建两性绿色生态新图景,一方面是要僭越传统的二元论。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论”的理论立场,造成了性别对立的思维方式,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模式。这种二元论作为理论基础被普遍认同,大多数文学作品仍旧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建构方式,女性角色仍旧作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而没有展示出真正的女性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成为可支配的资源。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翠翠、金凤、老七等的悲剧命运就是由传统二元论的不平等父权制所决定的。《边城》中大老对爷爷说翠翠不适合做媳妇的话,《三三》中白脸男子已有妻室仍旧想要侵占三三,《丈夫》中女性在结婚之后便会被丈夫送到城里“做生意”贴补家用,《长河》中保安队长已窥视夭夭良久并企图占有。因此,建构两性生态和谐,首先就要突破传统的二元论,打破性别对立的固有思维。并且,这种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突破并不是厚此薄彼,而是重点关注具体问题的探究和分析,关注对男性霸权社会产生原因和本质的批评,而不是仅仅建构一个绿色生态乌托邦。
构建两性绿色生态新图景,另一方面是要做到“两性平等”。这里的“两性平等”是建立在两性平等的社会意识形态前提下,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两性之间在权力、机会等的平等。试图在充分尊重两性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霸权的和谐社会。这里的“两性平等”倡导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是在“和”的基础上发挥两性的优势,寻找两性的支撑点,在此之上建构起和谐、平等、优势互补的生态新图景。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中,虽然他努力建构起两性生态关系,但是基于作者主观性以及社会背景,也出现很多不平等的情节。例如作品中女性对婚姻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萧萧》中萧萧在还懵懂的时候便嫁给了小自己九岁的丈夫,被花狗引诱怀孕后面临着沉谭或者发卖的命运悲剧。《边城》中翠翠对大老和二老的求爱没有表现出主动,面对大老和爷爷的去世,二老的离去,有的也只有被动接受这一切,然后默默等待二老的归来,一个无期的等待。此外,在“人类/自然”的二元关系中,也应做到二者平等,和谐共处。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发展观认为社会和谐需要适度而不是肆意发展,人类应该保护生态,呵护自然,并且女性在这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就是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自由是息息相关的。
柏拉图曾在《会饮篇》中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人的一半,合起来才是全体的符码”[10]240表明两性的和谐共处才是形成人全体的符码。同时,伍尔夫认为,“男女之间要先合作,然后创造的艺术才能够完成”。[11]128虽然柏拉图和伍尔夫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具有相对性,但此时她给了我们如何思考两性关系的方向。图海纳就此问题在《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中提出过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两性能否“平等而又互有差异的和谐共处”。两性的和谐生态关系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社会都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女性主义学者王红旗曾认为:“虽然当代女性生存处境的困惑仍是百年、千年,甚至是‘永远在路上’的困惑,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在不懈地努力追寻,毕竟会离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男女两性共存共荣共享时空的理想的‘绿色世界’越来越近”。[12]29这种绿色的两性和谐共处的生态图景终将会实现,人和自然的,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格局也终将会被打破。构建“人类(男性)/自然(女性)”的绿色生态新图景,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目标,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更多的则是意识形态的重组,因此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结语
沈从文的“原乡世界”作品,一方面描写了原生态自然状态下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更描述了“大自然的女儿们”在男性霸权社会下所遭受的苦难和无奈,进而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以及两性生态和谐的重视,因此沈从文的作品可谓说是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已成为学术界一道不可忽视的绿色风景线。作为一个正在发展、成长的理论而言,结合经典文本进行分析,无论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女主义在批评生态和性别语境的同时为也为文学研究和创作注入了绿色的新生命和新活力。
[1]Francoise Faubonne. Ecologie feminisme:Revolutionou mutation[M].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 press,1978.
[2]沈从文.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8]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9]佟新.社会性别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2]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