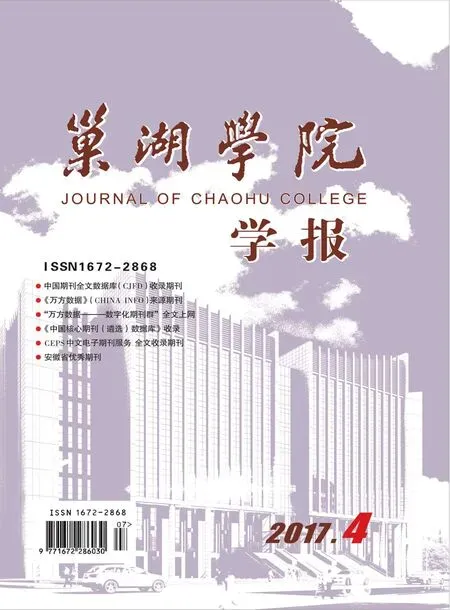评“工画者多善书”
2017-03-29曹司胜
曹司胜
(1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2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评“工画者多善书”
曹司胜1,2
(1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2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形象性与意象性是书画同源或书画同体的精神实质。汉字的书写从实用功能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艺术表达,其书写性特征又与绘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将中国传统文人绘画推上了重视笔墨趣味、不拘于形似超越形似的写意高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工画者多善书”,表达对当时宫廷画家缺乏激情、只求形似、毫无意韵的绘画样式的不满,提倡一种快意书写、将书法用笔的气势与力度融合于绘画之中的艺术风格,通过对吴道子艺术的赞美,赞赏一种书写性重要的文化意趣,也为后世的文人画家提供了从事绘画实践的理论基础,阐明了绘画与书法用笔辩证统一的关系与“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唐代“水墨之变”局面的形成。随着用“笔”与用“墨”技巧的进一步融合,文人画笔墨范式与趣味基本得以确立。
形象性;意象性;书画同源;水墨之变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论画六法》有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1]工画与善书,从一般意义上成为后人论述绘画与书法的相辅相成亲密关系的重要论据。在今人看来,首先书与画使用的材料工具基本相同,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含情运思于纸笔之间,表达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其次,作为对符号化了的汉字的书写,书法在点、划、疏、密之间创造的抽象美,共通于中国画的用笔力度、构图形式的张弛与墨色变化的技巧,因此,对笔墨技巧的共同要求构成了“工画”与“善书”的内在一致性。古往今来,画家的艺术成就往往得益于书法学习中对于笔性墨性的把握,书写性的笔墨趣味将中国传统绘画推上了不拘于形似超越形似的写意高峰,“工画者多善书”也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画诀”与座右铭。此外,赵孟頫的题画诗、郭熙的“画诀”、赵希鹄的《古画辨》乃至明人董其昌、陈继儒等鼓吹绘画的南北宗论,将张彦远的“工画善书论”进一步深化与推衍,使之成为“书画同源”“书画同体”等传统文人绘画的基础理论。
1 书(字)画同源或同体的精神实质:“形象性”与“意象性”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叙画之源流》中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1],认为汉字造型中的“象形”与绘画的“形象性”追求“异名而同体”,引申之则有“书画同源”之意。王维《为画人谢赐表》中有两句话“卦由于画,画始生书”,《宣和画谱》上说:“书画本出一体。盖鱼鸟迹之书皆画也,故自科斗而后,书画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间,尚及见其典刑焉”[2];明代何良俊的“书画同出”、清代邹一桂的“六书始于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乃至近代如董作宾、姜亮夫等学者基本观点都认为书出于画,书画同源同体,基本上成了定论。但也有不同意书画同源说法的学者,比如著名学者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谈书与画的关系问题中认为,追溯绘画的早期形态,如彩陶文化与青铜器的纹饰,都是图案性与抽象性的,而文字一开始是追求模仿物象的,即象形性,然后又说《周礼》将绘画之事,统于冬官,而《春官》外史则专掌书令,反映了古代书画分属不同的系统的遗意[3]。因此认为我国的书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否定书与画同源。
徐复观先生的观点把书画分属于不同系统还是值得商榷和有价值的,但就此认为书画并非同源似乎有些牵强,与其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一贯学术观有某种联系(如在兰亭的真伪问题上)。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用了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来概括了彩陶文化的抽象纹饰,他说:“这个由动物形象而符号化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对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4]但是彩陶文化的图案是否仅仅是图案化与抽象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通过图示我们可以看出,彩陶文化的图案是由物象的形态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当它形成装饰化的系统之前,其对物象的“意”态的把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彩陶图案的象意表达是图案化与抽象化表达的前提与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书(字)的起源都存在象形象意的创造心理机制。
《说文解字序》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由此可见,字与画的同源性在于其形象性。姜亮夫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将文字的起源的学说分为结绳说、八卦说、仓颉造字说,从文字学的角度基本可以论证“绘画是文字的先驱”[5]。同时我们也认为,象形的“初文”在汉字造型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另外更多的是象意表达,如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字方法。因此,我认为形象性和意象性才是书(字)与画的同源的精神实质,这种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象意”从根本上是契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文人画认为“论画与形似,见于儿童邻”,象形只是很基础的一种方式,“象意”才是高级选择。“意”有画中意,亦有画外“意”,中国传统绘画对画里画外 “意”的追求是自觉的,“状难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可谓意味深长。书画同源不仅仅是象形性的,更是象意性的精神性的契合。因此,从工画到善书便转化为善书而工画,书画同源同体在理论上完成了“书画家”的双重身份认证。
2 “水墨之变”:从用“笔”到用“墨”
书法不仅是笔墨技巧训练的直接方式,更易于形成“守其神,专其一”的精神品格。赵壹在《非草书》中就记载了许多文人沉迷于这种笔墨的游戏之中,流连忘返的情形,“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以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息。”[6]书法从实用转向了艺术的表达,打通了与绘画在艺术性格上互通的路径。“工画善书论”强调绘画与书法有着共通的笔墨价值,以书入画,可以对谨严的宫廷绘画的艺术品格与艺术趣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重视书写线条质量力度、有笔有墨的笔墨技巧,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绘画对于笔墨的核心地位的充分肯定。
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张彦远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又说:“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但是“自顾陆以降,画迹鲜存,难悉详之”,能将书法的书写性运用于绘画之上的,“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很显然张彦远是在表达对一种快意书写、将书法用笔的气势与力度融合于绘画之中的艺术风格(即“吴带当风”)的赞赏与复兴主张,成为后世兴起以“笔墨”审美趣味的文人绘画的理论源头。正如王朝闻在《中国美术史》(隋唐卷)中所说:“他们继承了‘描法’而又不局限于描法,他们抓住了‘用笔’这一关键,将中国画语汇的探索与纯化工作潜心尽力地进行了数百年,使‘笔法’得到了系统而完善的发展。”[7]唐人朱景玄著录的《唐代名画录》被认为较为客观公正,具有史的价值与意义。朱景玄在其序言中自称“景玄窃好斯艺,寻其踪迹,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推之至心,不愧拙目。”[1]朱景玄认为陆探微在木屋、人物禽兽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山水草木则只是“粗成而已”,可以想见,当时这种“疏体”绘画强调“用笔”书写性的技巧在表现较为具体的物象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对于较为模糊混沌的自然,仅仅用书写性的“用笔”不免有点捉襟见肘。但是吴道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天才,“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见,张彦远对于吴道子的赞赏并非空穴来风。
《唐朝名画录》与《太平广记》等古代文献都曾记载明皇思念嘉陵江水,命李思训与吴道子同画嘉陵江三百里的故事。这个画史故事耳熟能详,然而作为史料却是有疑问的,如有学者考证李思训的生卒年代与吴道子有很大差距等等。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则史料,却可以有另外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即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唐代山水画风格样貌的一个重要依据。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工严重彩的画风与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快意书写的风格截然不同,李思训父子在山水上发展了青绿精妙谨严、堂皇富丽的画风,李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说李思训“与子昭道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号大李、小李。思训格品高奇山水绝妙”。而吴道子将四川嘉陵江水目识心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能“一日而毕”,笔简意远,后人说吴道子挥笔用线“如莼菜条”,可见用笔较为劲绵有力而自由。前朝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将书法笔画入画,开创了绘画的“疏体”风格,疏密二体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就已经并行不悖了。在绘画上,唐代崇尚雍容华丽的色彩系统,相较于工整严丽、“焕烂而求备”的近代之画,水墨的简淡意境并未被赋予文人的文化涵义,点画披离、弯弧挺刃的“吴家样”后继者乏善可陈。但随着造纸业的进步与发展为书画的通融架通了桥梁,笔与墨的艺术趣味也开始发生融合,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董其昌说“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而认定王维是文人水墨的始作者,但是以王维、项容、郑虔、张璪、王洽等为代表的水墨渲淡一路,似乎与率意书写、点画披离的“吴家样”是一脉相承。水墨系统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并不一定始于唐代,也许正如荆浩《笔法记》所说“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故张璪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旷古绝今,未之有也”;“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象写成,亦动真思”;“项容山人……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这种以墨色渲染为表现技巧风格样式,是唐代绘画的重要成就,被称为唐代的“水墨之变”[1]。因此,荆浩说要采吴道子与项容二子之长,并提出山水画的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将人物画的审美运用到山水画领域,将题材的审美特质最终落实到笔墨技巧上来。
3 工画者必善书:后世文人画的理论依据
无论中西,宫廷画家一般都被认为是匠作之人,社会地位相对卑微,庄子论画中虽然是对那个解衣般礴的“真画者”的赞叹,但同时也反映了宫廷画师地位的低下;东汉王充说:“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唐阎立本位高权贵,对绘画 “性之所好,终不能舍”,但是对于这一艺术才能不但不引以为荣,反而耿耿于怀,并告诫子孙:“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宋时,由于徽宗皇帝的原因,宫廷画家的地位才有所提升,到了明代,宫廷画家被授予各种官职,看似地位受宠有加,但其实与宋代画家的地位已有本质区别,“这些画家,虽授以‘待诏’或‘中书’之职,但绘画活动主要由内府各级太监掌管,通过上传下达为宫廷创作,画家直接面见皇帝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明代诸殿待诏的地位和职务,远不及宋代的 ‘画院’‘待诏’”[7]。 西方的艺术家地位更是如此,柏拉图就对绘画艺术心存芥蒂,认为图画与真理隔着三层;对于艺术,米开朗基罗曾不无悲凉地说“夜间的话”,更像是对艺术家辛勤劳作却受尽屈辱的叹息,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是对艺术家精湛技艺的赞叹,其真实动机则是呼吁要提高艺术家的社会地位。
相比较于宫廷画家,文人画家却因为对于文化资本的占有,地位要远高于前者。在《论画六法》中,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其上下文的语境是“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呜呼!今之人斯艺不至也。”很显然,张彦远是以一种厚古薄今的态度来对当时的画工的匠作之气提出批评,“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绘画需要文人的书写性的审美旨趣,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形象的表现,更需要在画中传达出一种文化的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牛克诚先生认为,水墨画讲究书法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绘画性的。而这可能恰恰是它的话语来源,讲究书法性就要求它向画外面走,讲究中国哲学、中国诗文,或者强调画家本身的人生体验、游历山水,强调画外的东西,画得越不叫画越高级,画得越业余越高级。张彦远的“工画善书论”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为后世文人画的崛起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邵宏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从艺术风格学的角度来看,其大致关系似为:‘六法’中除‘气韵生动’之外的其余五法,为整个中国绘画归纳出技术性指标;元代文人们的‘书画同体’则从理论上拓展了中国绘画的技术外延,而明代的‘南北宗’论却恰好以‘书画同体’为理论依据,从技术上确定了‘文人画’的正统地位。 ”[8]
一般来说,人们在追溯文人画时,总是将源头追溯到王维,然后是苏轼的窠石枯树与米元章的云山。李泽厚先生认为文人画的正式确立应从元四家算起[4]。上文提到的赵孟頫的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言之凿凿将书写的抽象美凌驾于物象的形象美之上,从而使笔墨本身独立的价值突显出来。然而,从艺术语言的形态上来说,宋元绘画的笔墨趣味是建立在唐代水墨之变的基础上的,与唐代的快意书写的重“笔”画风有着诸多联系。与李思训、李昭道的工整严丽的宫廷富贵风格不同,吴道子的“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的书写性似乎就是后来文人绘画笔墨趣味的理论依据与源头,如今这些重“笔”风格的作品已然不存,我们只有通过文献的记载来想像这种风格的形态。近来随着唐代一些墓室壁画的发掘,如唐韩休墓壁画、章怀太子墓壁画、富平朱家道村唐墓山水屏风等,这些“真正的唐代的作品”似乎为研究唐代水墨画提供了实证,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绘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代书风一方面法度森严,但另一方面又有狂放恣意的艺术性格,正如唐人草书的鲜明特质。吴道子师从张旭学书不成,在绘画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因此从情理上来说,他的绘画的用笔技巧应该会与书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因此,这种快意书写、将书法用笔的气势与力度融合于绘画之中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具体在什么层面上却不得而知,也许相对于唐代绘画的“笔彩”体系,“笔墨”可能只是局限于某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之中,诸如道佛壁画、墓室壁画等,如果这种猜想成立的话,那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考古学的材料来进一步证明。
4 结语
综上所述,张彦远的“工画善书论”进一步拉近了绘画与书法的同源关系,形塑了中国绘画中对于“用笔”作用的重视,而书法用笔对绘画的介入又导致了水墨体系的进一步演进,将中国传统绘画推上了重视笔墨趣味,不拘于形似超越形似的写意高峰。阐明了绘画与书法创作辩证统一的关系与“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唐代“水墨之变”局面的形成,随着用“笔”与用“墨”技巧的进一步融合,文人画笔墨范式与趣味基本得以确立。
从工画与善书的历史关系来看,笔墨问题是传统艺术范式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值得思考的是,随着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特别是85新潮美术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画又遭到当头棒喝,吴冠中在香港《明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笔墨等于零》引发了美术界的轩然大波,将笔墨与绘画的价值关系一下子解构了。吴冠中认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随后张仃先生虽作了正面回应,但他提出的却是如何界定中国画的概念问题,即中国画的底线问题。笔墨的变革与继承问题一直伴随着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其实简单的价值判断已然不重要,比讨论笔墨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与观念的斗争,这也许才是中国画创作的动力源泉,随着当代水墨的兴起,笔墨问题已然不断被稀释、消解,工画者不善书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1]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32、27、22、608.
[2]宣和画谱·二: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5:438.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8.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15-32、183.
[5]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七:古文字学[M].昆明: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6.
[6]张彦远:法书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3.
[7]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隋唐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27-28.
[8]邵宏:书画的同源与同法——从赵孟頫题画诗的英译谈起[J].新美术,2005,(1):37.
COMMENT ON PAINTING PEOPLE ARE GOOD AT CALLIGRAPHY
CAO Si-sheng1,2
(1 Chaohu College,Chaohu Anhui 238000)
(2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 100029)
Figurativeness and imagery is the spirit of painting-calligraphy homology.Chinese characters writing liberated from the practical function,and became a kind of artistic expression.The features of writing and painting were integrated and mutually promoted,and eventually pus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painting to the peak of ink taste,beyond form likeness.Zhang Yanyuan said"painting people are good at calligraphy"in the Li-tai ming-hua chi.He expressed a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ourt painters′lack of passion and style.He advocated a pleasure writing,momentum and vigor of calligraphy merged in the painting art style.With appreciation of Wu Daozi′s art,he favored the cultural charm of calligraphy and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painting in the later literati painters.He expounded the relationship of dialectical unity and "legality"foundation,promoted the Tang Dynasty"change of ink and wash".With the skills of"pen"and"ink"further integrated,the literati brush ink paradigm and tastes were fundamentally established.
figurativeness;imagery;painting-calligraphy homology;change of ink and wash
J201
A
1672-2868(2017)04-0055-05
2016-12-19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16BF087)
曹司胜(1978-),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