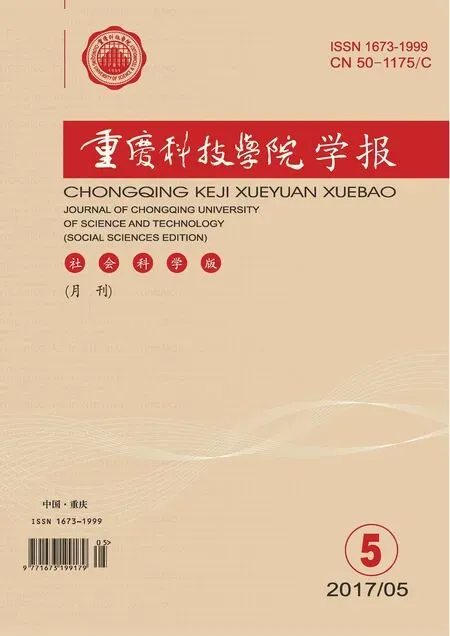论庄子的快乐观
2017-03-22魏微李霞
魏微,李霞
论庄子的快乐观
魏微,李霞
庄子认为世人趋之若鹜的“俗乐”只是浅薄的物欲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而且它反使人“役于物”。庄子推崇的快乐境界为至乐,即与天地万物相感通,与自然和谐共处。要达到此境界,庄子指出的途径是遵循“无为”的方法与准则。庄子的快乐观反映了人类对自性生命的反思,以及对精神乐土的憧憬与追求。
庄子;天乐;道;无为
庄子生活于战国乱世,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世间苦难加剧,人们追逐名利物欲而失去真朴本性。庄子对俗世大众趋附声色利益并以此为乐的现象提出质疑,不愿人们身陷其中,希望寻求摆脱生命的无奈与困苦的道路,追寻心灵的自由,体会真正的快乐。
一、“俗乐”非乐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声音也。”[1]480在庄子看来,天下人引以为乐的是长寿富贵、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而追求声色物欲、富贵名利等浅薄的享乐,实质是人“役于物”,它会造成人背离本性的异化,失性于俗。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1]480尽管庄子所言看似不可知的态度,但正如林希逸所说,“谓世俗所谓乐体现的是不乐,我皆未知如何也”,其实表达了“深鄙之之意”[2]。庄子对“俗乐”深为鄙视,认为“俗乐”不仅受限于自然规律、社会环境、自我情欲,而且毁损形体,进而威胁性命。“俗乐”受自然规律的限制:美食需用口舌品尝,服饰需穿戴在身,颜色图像要用眼睛观赏,声音要用耳朵聆听,一切都要寄于形体;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形体不可能永远康健,倘若失去形体的依托,“俗乐”便不复存在。“俗乐”受社会环境的限制:社会安定时,能够提供享乐所需的物资,个体的时运也随之好转,“俗乐”便更易得;而社会动荡时,物资匮乏,个体之时运随之沉浮,“俗乐”只能灰飞烟灭。“俗乐”受个体的情感、欲望限制更甚:所得大于欲望、是心之所好的,便欢欣鼓舞;所得没有满足欲望、是心之所恶的,则“大忧以惧”[1]480。“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1]480富有之人为聚敛财富而辛劳,却不能完全使用,这与保养形体是背道而驰的。显贵之人时时担心自己的名声好坏,对于养护形体亦是疏忽。长寿者昏昏沉沉,忧患于如何才能不死,这样苦恼更是与保护形体渐行渐远。在庄子的眼中,世人为了能够得到短暂的享乐却弄巧成拙伤害了形体,连自身都养护不了,反而使享乐的形体遭受损毁,最终“丧己于物,失性于俗”[1]438,甚至威胁生命。
庄子描述了人性异化情景下的“俗之所乐”,然后旗帜鲜明地指出:“俗乐”并非真正的快乐,有时反成人生的枷锁,与真正的快乐相悖。
二、“天乐”至乐
庄子冷眼热肠,融心于大道,追求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1]18的境界,他所推崇的快乐自然也不会拘泥于世俗之见。
庄子在《天道》中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67庄子在论述“天乐”前先以“人乐”作引,称人与人相互感通、和谐相处是“人乐”;天地间自然万物相互感通、和谐共处便是“天乐”。钱穆言:“庄周特推扩人生而漫及于宇宙万物,再统括此宇宙万物,认为是浑通一体,而合言之曰天。故就庄子思想言之,人亦在天之中,而同时天亦在人之中。”[3]在庄子的思想中,“人乐”与“天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天乐”是“人乐”的推扩,是理解与共情由人与人之间扩大至人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之间;而“人乐”的实质是“天乐”,包含于“天乐”当中。《秋水》中,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即为“人乐”与“天乐”关系的生动展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1]476“鱼之乐”,因其出游从容,“出游从容,自遂其天乐”[4],从容之态是适从自然的流露,“鱼之乐”显然是天乐,庄子知“鱼之乐”,因庄子与鱼感通,故其也为天乐。惠施则认为:“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是持有“物”“我”的对立观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隔阂之中故步自封。而庄子一语道破惠施“已知吾知之”,将惠施拉回了与其相通的“人乐”之中,认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知“鱼之乐”,再进一步推论他实已承认“鱼之乐”,即知“天乐”。
“天乐”究竟是怎样的境界呢?庄子对此作出了解释:“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蓄天下也。”[1]368虚静推及于天地之间,通达于万物当中,这就是天乐了,是如圣人慈爱体恤之心养育天下。这样的“天乐”之境,“赍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1]367。调和万物却不认为是义,恩泽波及万世却不以为是仁,长于上古却不算老,复天载地雕刻万物的形象却不露技巧。然而,这样的“天乐”之境却是“俗之所大苦也”[1]480。这是因为“天乐”的一部分表现正是“俗乐”受自然规律、社会环境、自我情感与欲望之限制时的状态,然而“天乐”之境却可以顺应客观规律,化苦为乐。以《至乐》中的寓言为例:“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1]486支离叔与滑介叔观天地自然的变化,滑介叔的左肘忽然长出了瘤子,这在享俗乐的人看来是享乐的生命形体受限于自然规律,可谓“大苦”。滑介叔遵循自然的变化,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心中亦无好恶,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看作是与支离叔观化而化及自身。
那么“天乐”的境界怎样才能达到呢?庄子给出了答案:“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1]483通过“无为”的方式可以几近获得至乐。“无为”并非毫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而行动。“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1]483天无为却可以自然清虚,地无为而能够自然宁静,天地无为相和合,繁多的万物得以变化生长。“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1]483。身为天地间智慧的存在,人又“孰能得无为哉”[1]483?“无为则悠然自得,安命无为是取得人生自由的唯一途径”[5]。以“无为”为思想方法与行为准则,“天乐”之境便能自然达到。
“天乐”是庄子推崇的最高境界的快乐,是他认为的真正快乐。若能体会“天乐”之境,便是以精神的自由摆脱世俗的种种枷锁,不待于己,无役于物,从人之异化的状态复归于道,找回本性的素朴,遵从自然,安世顺化。
三、余论
庄子的快乐观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庄子对“俗之所乐”坚定地反对,认为“俗乐”是浅薄的享乐,致使人“役于物”,并非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最高境界的快乐是“天乐”,即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和谐共处的快乐。“天乐”是“人乐”的推扩,需“无为”方能获得。“天乐”之境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体道境界的衍生。人若与道相去甚远,便只能承受“俗乐”及其带来的损毁;若能够虚静无为体道之深远,便能体会人生的至乐,达“天乐”之境,逍遥而游。
关于快乐,儒家也有许多言论。如《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6]49,所言之乐是由学习并实践引发的快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6]49,是由与志同道合的人相聚默契产生的快乐。孟子认为的“君子三乐”是“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6]332。 儒家的快乐观较之庄子,人伦的意味更浓,圣贤之心更甚,但却是将快乐与体道的精神境界挂钩,体道越深,乐之越高。不过,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不是同一个东西。
庄子的快乐观在道家哲学中亦有深远的影响。《淮南子·原道》中说:“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喜怒哀乐的迸发与天道自然相违背,是人的行为不合乎道的表现。它直接来源于庄子“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1]426-427的思想。汉代将庄子之快乐思想具体而微,使其成了统治天下的君王的行为准则之一。
庄子作为清醒的旁观者,不落世俗,“独与天地之精神相往来”[1]939。 庄子的快乐观,一方面表现出对现实中种种制约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以虚静胸襟感怀自然,以“无为”超脱世间福祸苦乐的悠然自得。庄子对快乐的哲学阐释也是对生存环境的审视和自性生命的反思与省悟,是对人与万物自适其性、各得其所的精神乐土的一种追求。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7.
[3]钱穆.庄老通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18.
[4]林云铭.庄子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3.
[5]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7.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编辑:王苑岭)
B223.5
A
1673-1999(2017)05-0003-02
魏微(1993—),女,安徽大学哲学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李霞(1962—),女,博士生导师,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安徽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道家哲学。
2017-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