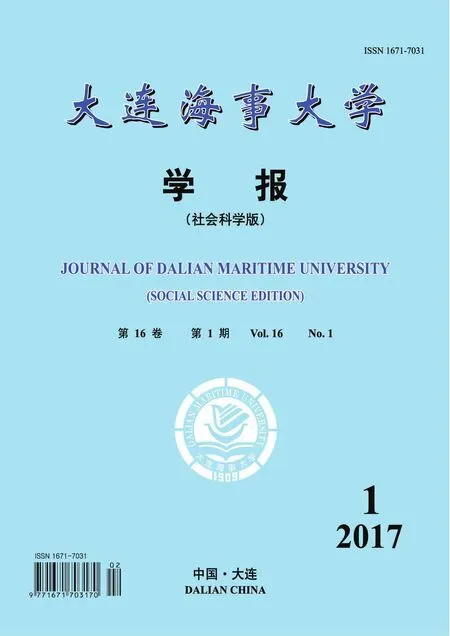汉字造字方式与意象思维
2017-03-13于芝涵
于芝涵
汉字造字方式与意象思维
于芝涵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汉字的造字方式深受思维方式的影响,体现了强烈的“意象”思维。“意象”思维在汉字造字方式中有三种表现形态:“象形”的方式、“会意”的方式和“类意”的方式,分别对应汉字构造中的象形字(连同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同时从接受的角度为意象思维何以在汉字创造中起主导作用给出解释。
汉字;造字方式;意象思维;象形;会意;类意
一、引 言
本文的主旨是从汉字的造字方式中探讨古人的造字思维方式,讨论之前,先交代和本文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汉字造字方式。提到汉字造字方式,免不了要论及“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对“六书”的性质,学界争论颇多,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六书”是造字法*这种观点最早源于汉代班固,其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第一次明确提出“六书”是造字法。;“六书”中的前“四书”是汉字结构分析法*这种观点认为前四书是有关汉字形体结构,后二书是汉字的使用,即通常所说的“四体二用”,因为将六书视为汉字的六种结构类型,在具体分类上有很多困难之处,即便在正例下分出变例或者分出许多小类也于事无补。清人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对“四体二用”有详细论述。这种说法突破了“六书”的系统性,从“体”和“用”两个层面认识汉字。;“六书”是一套教学用语*这种观点李运富在《“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1期)中有详细论述,其认为“六书”具体内容涉及汉字形体来源、理据构造、类聚关系、用字法则等,构成汉字基础知识的教学体系,不是单一理论的类型系统。。笔者认为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既可以视作汉字的结构方式,也可以视作造字方式,而后“二书”(转注、假借)在结构上隶属于前四书,是汉字的使用方式。因此本文所指的汉字造字方式就专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
第二,关于造字和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按照张岱年、成中英的定义,就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的、稳定的、普遍的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事物的审视趋势和公认的观点”[1]。汉字为汉先民所造,作为汉文化的承担者,是汉先民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其造字方式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思维方式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造字过程中,不可能只用一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某种思维方式起主导作用或存在思维偏向的问题。
第三,关于意象思维。这里首先得区分“形象思维”和“意象思维”。“形象思维”是指“以具体形象和表象为支柱的思维”,按普通心理学看来和“表象思维”*表象具有直观性和概括性。所谓直观性,是指反映的事物通常只是事物的大体轮廓和一些主要特征;概括性是指反映同一事物或同一类事物在不同条件下表现的一般特征。从其定义和论述可见,表象可以反映事物的外在表现特征固然使得它可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却只能是处于人类思维方式中比较低级的层次和阶段。具体论述可参见叶奕乾、何存道、梁宁建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有关表象的相关内容。本文中“形象思维”的定义取自本书第276页。大体可以画等号。意象是主观化了的形象,其中融进了人的主观情感和想象,是主体之“意”与客体“象”双向运动的一种心理现象。那么本文所说的“意象思维”就是以物象、感性认识为基础的浸染了主体认识、选择的一种思维方式。通常所说的象形思维(表象思维)可以视作是意象思维的组成部分。意象是人对外界的认识过程从感知到思维的中介,它既立足于物象,又在此基础上融入个体的认识和体验,因此经常会因为某些特定目的的需要对物象作出选择或调整。
二、“象形”的方式——象形和指事
许慎对象形的定义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可见象形就是一种描摹实物形体的造字法。根据象形字形体和字义之间的关系,象形字可以分为三类:全摹象形,例如,甲骨文中的“山”像山峰耸立的样子,“雨”就像雨水降落之形;部分象形,例如,甲骨文中的“牛”只是画出来牛的犄角,“羊”只是画出来羊的犄角;附加象形,例如,甲骨文中的“果”除了画出果实,还画出果树,“眉”除了画出眉毛,还画出来眼睛……尽管从字符形体来看,象形字并未完全遵循一种标准,但是这并不影响意象思维的主导作用:无论上述哪一种象形字,字符和其所要指称事物的形体都具有匹配性,二者存在“象似”关系。
全摹象形是通过字符本身的形体来表达其所指称的事物,人们一看到这个字符的形体,自然而然地就会在脑海里浮现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形象,通过这种形象再现以达到理解字义的目的。部分象形字,是用实物的显著特征来代替一个完整的形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一种经验的现象,其中的每一成分都牵连到其他成分,每一成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为它与其他部分具有关系”[2],即视觉会把不完整的形象按照记忆补充完整。所以人们在理解这个字符时就是以其典型部分还原匹配全体,以“牛”犄角来理解整个“牛”字符。至于说“附加象形”*许多专著所说的“合体象形”,本文用“附加象形”这个名称,是因为“合体象形”的立足点是区别于独体象形的,而本文的侧重点是探讨象形的方式、字形结构和字义的关系。,裘锡圭已经做过说明:“有一些象形字的字形比较复杂,这些字所象的东西很难画出来,或者孤立画出来容易跟其他东西相混,所以为它们造象物字时需要把某种有关的东西一起表示出来,或者另加一个用来明确字义的意符。”[3]
关于指事,许慎将其定义为“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意思为一看就可辨识字形,细察才能体悟字的意思。指事字以象形字为基础,因为无具体的“形”可“象”,所以要通过一定的指示标记附加在象形符号上。例如“本”,以象形字“木”为基础,在其下添加指示性标记,意为“树根”。
从已解读的甲骨文字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来看,无论是反映自然事物的日、月、山、水,或是社会生活的衣、鼎、舟、车,或是反映人自身的人、女、目、手等,都是取象赋形的。但这种造字方式为何能被人们所接受,人们是如何从字的形体上得以感知造字者所要表达的意义的?鲁道夫·阿恩海姆说,“形状不仅仅是由那些当时刺激眼睛的东西决定,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凭空出现,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最新的经验。因此,新的经验的图式,总是与过去所曾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4]。正是因为造字者根据象形这种方式所造出来的字不仅仅反映的是其自己眼中的物象,同时也是受众眼中的物象,普通受众关于此物象的印象与造字者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尽管象形字是一种个体主观性的表达,但是理解的一致性可以召唤受众记忆中关于此物的印象和理解,这样所造出的象形字可以被广泛地认知和理解,这就是象形这种造字法被接受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象形和指事都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但是它们还只是在“客观取象”的程度,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它们还只是相似性符号,仅仅反映事物的外在形象特征。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字符的造字方式是意象思维的初级阶段——形象思维支配下进行的一种文字创制活动。
三、“会意”的方式——会意
许慎对会意的定义为“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可见会意就是把两个或以上意义相关的意符合二而一,意义上加以联系,以显示新义的造字法*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所说的会意方式,包括会意字和会意兼形声字。。和象形与指事不同,会意字所表达的字义通常比较抽象,且无形可象,因而象形这种造字方式无法满足汉字表意功能,只能联合已有的象形或是指示符号,采取“会意”的方式,描摹出一幅图画或创制一种情景,使识字者在感知画面或情景的过程中理解字形所要传达的意义。根据会意字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三类:情景会意、指示会意和联系会意。
情景会意,即通过两个或多个表达要素给识字者提供一幅画面或是能凸显字义的一种情景。如“暮”,其甲骨文形体为“太阳落在草丛中”,使人们在“日落草丛中”的画面和情景中体验“暮”的意义;“武”,其甲骨文中的形体描绘的就是“人荷戈行进”这样的一种画面情景,这只是“武”字所表示字义的一个典型的片段,但是在这个画面中人们却可以通过给出的情景来体会字形所表达的意义。指示会意字明显地继承了指事造字的原理,通过强调词义表达所涉及的特定的部分,以二者的指示关系来表达词义。如“见”甲骨文字形在人形上加上“目”,表示“看见”的意思;“鸣”,其甲骨文形体为“一个鸟旁边一个口”,通过“口和鸟的指示性关系”来表达“鸣叫”的意思。联系会意,这类会意字表达的意义更为抽象,多为形容词和意义抽象的名词,这类会意字既不能通过画面也不能够通过指示来反映所指,但又必须借助象形或象意的手段来表达词义,故而只能用词义来把其构型要素强制联系起来,只有在理解词义的基础上才能体会字符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如“赤”,甲骨文字形从大从火,表示“红色”的意思,词义“赤”是字形“大火”的颜色特征。
如果说情景会意是通过提供一种情景画面,且能为受众所能亲身体验到的“视知觉”*同样的,“视知觉”具有完形功能。来表达字义,那么指示会意和联系会意则是通过一种“意知觉”,通过字符组合后体现的指示性联系来表达字义,或者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其构成要素的联系,它们的意义关系不是通过画面叠加而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两个象形符号的逻辑来推导,在以形表意激发人们认知联想的同时,其内部的引导性逻辑关系已经引导人们进入一个固定的范围,以保证字符的意思可以被理解。
会意字作为一种记录事物的符号,它并不能穷尽事物本身,为了缓解这种言不尽意的矛盾,造字者往往只能采取省略表达形式。所以,无论是情景会意、指示会意还是联系会意,会意字都是造字者为了表达字义所截取的典型代表的组合。从符号的角度而言,会意字其实是一种激唤性符号,等同于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它只起一个刺激引导作用,以字符形体引导接受者意会其传达的意义。根据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认识的发生和构建心理的过程主要有四大步:图式—同化—顺应—平衡[5],也就是说,接受者在接受之前,是有其原有的图式(认知结构)的,当外物契合其图式时,就会被同化作用吸收,但当原有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就会根据外物来进行自我调节,或改变原有的图式或创立新的图式,以适应新的客体,以便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中。
会意字的意符多是与当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皿、车、田、示、木、禾、日、月等字素,它们共同反映了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动具体地展现了我们祖先的历史生活。而且,同一历史时代的人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水平,而共同的生活环境、生产劳作方式、生活习俗等共同的文化氛围,则会使得同时代的人的认知和理解具有“历史相似性”。因此,造字者的观察视野其实是和受众的期待视野大体上是契合的,造字者在字符中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经验与体验,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经验。
情景会意字,字符构成要素本身的易理解和接受性,加之其构成画面的可视和可感性,反映的又大都是同一社会中人们共同的经验和认识,所以这类会意字因为可以直接调动接受者的生活经验或想象而可以被同化在受众的认知图式中。指示会意字通过二者的指示关系来表达词义,受众在理解时,预先了解指示符号的所指关系,才能将其纳入具体的情景中体会字符表达的意义,所以受众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必须在同化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原有的认知背景,使其顺应认知图式。联系会意字表达的意义比较隐晦,所以只能在理解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明确其构字要素之间的关系。尽管每个接受者都会有关于某个词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很有可能和造字者所用的字符构成形态不同,但是一旦接受了这种表达形式,就必须改变原有认知图式,建立新的图式,以适应客体将其强制纳入到自己的认知范围中。但无论哪种类型会意字的理解和接受,都需要人们把过去经验中的背景图式视界和眼前的字体所呈现的关联性视界或是全新视界作出想象的对比,字体之“象”呼唤着相应的“意”的出现,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进行回忆或是重建,搭建起与造字者的意象轮廓相似的意象,通过进一步的领悟体会会意字之所指。
相比于象形和指事的“取象”而言,会意更侧重的是“取意”,会意这种造字方式的本质不在于“立象”或“描摹”,而在于一种“象征”:由象著意、象中寻意。因此,如果说形象和指事是意象思维较低程度的“象形”思维的体现,那么会意就是意象思维的较高阶段“象意”思维的体现。
四、“类意”的方式——形声
许慎对形声的定义为“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可见形声是根据该字所表示的事物选择一个义符(即“名”),再选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作为声符(即“譬”),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新字的造字法。形声字的形符(汉字符号化以后成为义符)通常表示类属或者相关范畴(名词的形符大多表示类属,谓词的形符大多表示相关)。例如,“喙”、“嘴”中的“口”表示字义所归属的范畴,“叫”、“啼”中的“口”表示相关范畴。
相比较前面两种造字方法,形声字中的意象性已大为减弱,它更多的是通过“类意(类象)”的方式,以形符表意的类化来表意。根据“类意”的定义,“整体地或部分地揭示有关对象在‘象’上的某种共同特征,其结果就是类化了的意象”[6],形声这种造字法造字时已经按照字义对字符进行了分类,这种分类以形符(义符)在字符上体现,同类的事物因其共同特征而联系在一起,统归为一类的事物可以抽象出来一个共同属性。如以“木”为义符的形声字:柳、槐、樟、桐、杉、松……都和“木”有关,它们都是“木”的下义位,在概念上都是从属于“木”这个概念,整个以“木”为形符(义符)的字形成了一个“木”系统。另外,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无论是累增字(果—菓),假借字上加注义符(采—彩),初字的同源分化加注义符(解—懈),或普通的一个音符加一个义符所形成的形声字,从中都可以看到古人的类属观念:“果”在甲骨文中是个象形字,画出了果实和藤蔓的形状,后来因为汉字符号化和线条化以后,象形特征不明显,因此又给它增加了一个义符“艹”提示其类属;“采”甲骨文字形是手在木上表示“采摘”义,后借用为色彩义,为了区分加上了义符“彡”提示词义和类属;“解”甲骨文字形是分解牛表示“分解”义,后引申出“松懈”意思,加义符“忄”表示“松懈”是心理的状态和动作,起到标示词义和提示类属的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外来词的汉化”,先借用一个字符来表音,但是在意象思维之强烈表义的压力下,通过加形符的方式来让它表义,以使它符合整个汉字系统的表意性。如“狮子”的“狮”字,它本来是借用“师”这个字符来作为一个记音符号,但后来又通过形声的方式给它加了一个意符,造了一个新字“狮”,把它从字符上归入到“豺”的类属里,以通过“类象”达到认知和理解一类事物的目的。
从文字的形音义关系而言,形声字可以视作纯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的过渡,使文字更加向语言靠近。但是,这种类意的方式明显依然摆脱不了意象思维的影子:因为以形符提示字义,不仅仅是继承汉字以形表意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符合汉民族长期的认知习惯;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象形(指事)和会意这两种造字方式是不成系统的,在造字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突发的、间断的、顿悟的、无序的思维(这也是意象思维的显著特征),因此,这两种造字方式所造的个体字之间没有关联性,它们之间是零散的、可数的关系;形声字与之不同,它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形声是按照意象思维的类比方式来造字的,形符(义符)是联系它们的纽带,同一形符(义符)的文字一般都具有意义的相关性,形声字所表现出来的“意”实质是一种类化和归类。
形声突破了汉字单纯以形表义或以形立意再表义的方式,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造字:它所采用的构件是以前所创造和应用的字符,一部分表义,一部分表音,使字符和语音直接相关,即语言音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字形上得到反映,因此形声这种造字方式可以用有限的构件组合生成尽可能多的字符,而且不用过度增加人脑的记忆负担,因而既符合语言材料利用的经济性,也利于人们接受和掌握。所以,形声这种造字方式一经产生,就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形声字比例不算高,但小篆中的形声字比例高达87%以上。
[1]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07.
[2]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序5.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18.
[4]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腾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8.
[5]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
[6]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93.
2016-10-12 作者简介:于芝涵(1987-),女,博士研究生;E-mail:zhihanbnu2012@163.com
1671-7031(2017)01-0113-04
H1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