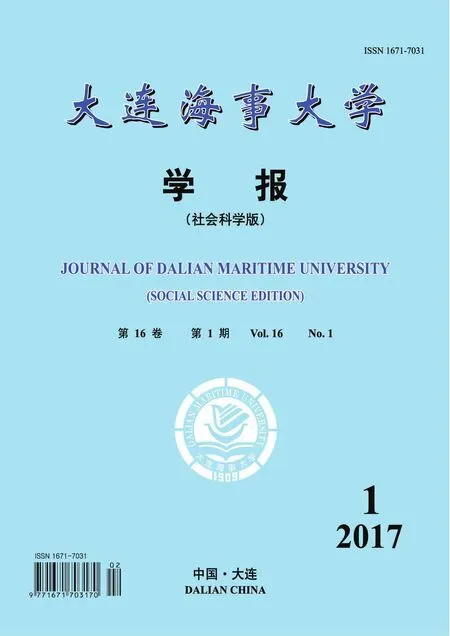开头的功能与结尾的意义
——以阎真的小说为讨论中心
2017-03-13郑国友
郑国友
开头的功能与结尾的意义
——以阎真的小说为讨论中心
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沙 410205)
精彩的开头不仅是吸引读者的手段,同时还承担着文本表达的功能。一个好的开头,往往为整个小说的情节走向、精神布局、思想表达打下了坚实的桩基。而好的小说结尾能从现实的沉浮中超拔出来,生发出“现实之上”的“心灵探寻”和精神意义。阎真在其小说中设置“倒叙型”的开头来对“过去”进行颇富“痛感”的反思和“时空压缩型”的开头来形成小说情节展开的精神背景,并在结尾通过隐喻和象征导向意义思索,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了开阔而厚重的生命境界与凝重而和谐的艺术品质。
阎真;小说;开头;结尾;功能;意义
几乎可以说,任何小说创作都是对时间的裁剪、删减、重组。生活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发生、发展,小说也不可能与生活同步,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处理,必然要按照小说家的叙事逻辑和艺术方式来进行重排。因此,可以说,小说的艺术是一种结构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时间统一性”的破坏和重组。所有的故事都必被作家安排在一个预定的叙事框架中来完成,而在这个框架中,对于经典作家来说,开头和结尾显得尤其重要。正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开头总是很麻烦的”,而“结尾是大多数作者的薄弱之处”。[1]165“麻烦的开头”和“薄弱的结尾”,让作家颇费心力,比如阎真就谈到:“长篇《因为女人》,为了开头一句话我思考了大概四个月,翻看了几十部名著,怎么能够精彩而不落窠臼?这是令人痛苦的。”[2]任何小说写作都是“有限度的”,它必须有一个开头,即从什么地方写起,它也必然有一个结尾,即小说必须在某个地方止笔。既然开头和结尾处成了作家文本营构的重中之重,那么,对开头和结尾的研究便有了必要和意义。一般来说,开头是功能性的,而结尾则表达着意义。在这里,以阎真的小说来作为讨论中心,试图对小说开头的功能和结尾的意义作一探讨。
一、开头的功能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谈到:“小说的第一句(或第一段、第一页)是设置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与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世界之间的一道门槛。因此,小说的开局应当如俗语所说‘把我们拉进门去’。”[3]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快速、信息铺天盖地、休闲和娱乐方式丰富的时代,要把人们从忙碌和热闹的生活之中,拉进小说阅读之门,让他们退守到沉静的“纸上城邦”,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可以说,小说写作也是一种“眼球经济”,而小说的开头,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刺激眼球”的“抓人”功能。为了吸引注意,“故弄玄虚”的悬疑式开头和“先从高潮写起”的倒叙式开头便成了一些作家“屡试不爽”的开头方式。然而,小说艺术也会越用越俗,越用越流于大众化、通俗化。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突破和创新,正如马尔罗所说,“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4]。
真正优秀的作家,利用精彩的开头来吸引读者目光停留往往只是一种手段,而其“特别”的开头往往承担着文本表达的功能。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和《因为女人》同样具有一些通俗小说“倒叙”的开头特征,但与一般小说过于强调开头“精彩”的不同之处在于,阎真的倒叙将“现在”置于小说的开头,而将“过去”当作小说的叙事主体来处理,从而形成了一个与辩证法相似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又不得不“追忆似水年华”的小说“装置”。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说的那样:“这是对回顾过程的模仿,它将过去推向未来,以构成一个回顾性的前景或者未来的先前。”[5]57通过“现在”来对“过去”进行“回忆”,拉开了“现在”与“过去”的距离。虽然小说的主体叙事是“过去”而非“现在”,但在“现在”的开头之中,“过去”的故事已经对“现在”具有深刻意义,而正是这种“故事的开头既身处叙事文本之内,又身处其之外”的文本结构方式,[5]55使小说获得了一种跨越时空的远距离的对过去生活的冷静追思和审视。《曾在天涯》中小说的第一句“多少年来,我总忍不住想象自己将在某一个遥远的晴朗早晨告别这个世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何其相似,它显然将“过去”的故事导向了一种深重的“回忆”和沉重的“追思”之中。而在《因为女人》中,小说依然是从“现在”起头,写青春不再的柳依依被一种依稀熟悉的声音所吸引,进而终于想起了那是自己的初恋夏伟凯的声音,从而激活了“对这个世界,自己实在也不能再幻想什么”的柳依依的情感记忆,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种记忆“像一只狼,在严寒的冬季把深埋的骨头从雪地里扒出来,细细地咀嚼”。而这样痛苦、悔恨的开头方式与鲁迅《伤逝》中的第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又是多么的相似。在伤感的回叙、沉痛的诉说中,情感的底色、人物的命运、文本的主旨、精神的氛围,都在文本的“开头”形成了坚实的桩基,同时也唤起了读者阅读的兴趣。
这种“回忆型”的开头方式可谓是“经典”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百年孤独》和《伤逝》外,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所采用的亦是如此方式,该书开篇第一回第一段第二句便交代:“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在这里,小说与真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虚幻在真实之上,而真实比虚幻还虚幻,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生命回首的沉重和哀叹超越了时空。这种开头方式在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也同样被采用。影片的开头,一群商人打捞泰坦尼克号的遗骸,企图找到宝石“海洋之星”。而影片所要表达的是超越了名利的、比“海洋之星”更宝贵的情感,于是镜头对准了年近九旬的罗丝的双眼,在一个“特写”中,泰坦尼克号上演的“永不沉没”的人类真情故事便开始了。不单《泰坦尼克号》,同样获得奥斯卡奖的《拯救大兵瑞恩》《放牛班的春天》依然采用的是这种“回忆型”叙事镜头。显然,“回忆”成为故事讲述的一种经典方式,通过“回忆”,主体精神对事实的渗入便不可避免,于是,故事也就在这里获得了意义性的表达和价值性的思考。
在“回忆型”叙事中,《曾在天涯》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小说开头开创出的生命境界和反思色彩。该小说的故事主体是叙述高力伟三年多的北美漂泊生活,小说除去开头,也是基本上在陈述高力伟留学生活的艰辛、困窘、无奈、挣扎,以至抛弃绿卡和拒绝爱情而仓皇回国。可以说,除去开头,小说也能够“自圆其说”,也依然能够表达一种为留学生活“存照”的文本价值。然而,“高明”的阎真却在小说的开头安排了一个“引子”,在这个“引子”中,“我”已经回国了,但仍然总是不能自制“心惊肉跳”般地回想起北美“梦魇”般的漂泊生活。在“引子”里,“我”深刻而恐怖地体验到了死亡的真切,“生命的最后挣扎”、“生命的最后感受”、“生命的最后时刻”、“生命的最后微笑”的“想象”让“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意识到生命只是一个暂时存在更能给人一种冷漠的提醒”。除了“折磨得我好苦”的想象,还有让人痛苦的“迷茫的梦境”以及“过去生活的幻象一幕幕在心中浮现”,这同样让“我”“清晰地意识到生命在无尽的时间之流中只是那么迅速的一瞬,它与这个永恒世界的共同存在只是一次偶然的邂逅”。正是在痛苦的“想象”、“回忆”和“迷茫的梦境”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生生死死、如梦如幻之中,“我”“意识到了生命的存在”,终于有了强烈的生命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告诉在未来的什么年代什么地方生活着的什么人”一些生命的事实。通过“引子”的这些交代,阎真无疑是在提升小说的品质和意义,既从生命的高度来表述留学生活。也就是说,阎真在《曾在天涯》中,通过开头“引子”的设置和交代,从生存性的现实,写出了精神性的关怀,从生存的异国漂泊之艰难,写出了精神失根者的精神漂泊之苦痛,从而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存在进行反思的“形而上”色彩。可见,时空的大跨越、“现在”与“过去”的接通、虚与实的交替、存在与反思的缠绕,这种“回首式”的开头,使小说获得了超越和深度。
与《曾在天涯》《因为女人》开头设置的“回顾型”叙事不同的是,《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的开头采用的是一种时空压缩型的开头方式,即在一种简约、浓缩的开头中,对时空背景做压缩处理。《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都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叙事,即小说表达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但阎真瞩目的更在于要表达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实处境。而这种文化和精神是传统的,它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但在今天却遭遇了危机,面临着没落的命运。只不过,在《沧浪之水》中,阎真通过池大为表达的是只能顺应,否则便是消亡。而在《活着之上》中,呈现的则是虽然无法抗拒,但良心还在,知识分子还有可能保持精神的自持。但顺应也好,自持也罢,在这两部小说的开头,阎真都相似地设置了一种宽阔、厚重的精神背景,并将这种精神背景做了时空压缩式的处理。小说中,池大为的精神认同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追溯到屈原,而聂致远的精神根源在小说中则上溯到他的爷爷,上溯到《石头记》。但这种几千几百年的时空都在小说中做了压缩式的处理,即将历史当作一种精神背景,为后文人物行为选择提供参照和根据,同时在文本的层面来构成对时代的文化反思和精神质询的意味。如马克·柯里所说的便是“将现在发生的时间匆匆付与过去然后又将它们重新语境化”[6]。在《沧浪之水》中,除了在扉页引用了屈原《渔父》中的句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外(这个句子显然是该小说之名的出处),在小说“序篇”中,也就是在小说的故事主体——池大为在卫生厅的经历之外,将池大为“付与过去”的“现在”“重新语境化”,而这也正是池大为在步入官场后遭遇精神苦痛和最终“杀死原来的自己”的核心性格文化因素。“序篇”中,池大为的父亲死了,这是一个好人,承受了许多社会不公,但他依然没有低下头颅,坚守着精神的高贵,珍藏着代表着一种精神源流和象征这精神信仰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而“我”在对“父亲”“遗产”的“清理”之中,也同样认同了“父亲”,确认了一种精神皈依:“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除此之外,小说的开头还通过我在大学生活中的社会调查、校园游行、与许小曼的初恋、以婚姻换发展的诱惑等,如一幕幕的镜头,来强化池大为的精神认同和灵魂归附。这显然是在为后文池大为的生存选择之难构筑坚固的精神堤坝。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指出的,“在分裂为产生辩证运动或叙事运动的两个对立面之前”,于开头“建构了一个虚拟的永恒困境”[5]56。“堤坝”筑得越高越实,后文人物的生存便越艰难。因此,《沧浪之水》的开头显然在强化这种“对立面”,提供了一个“虚幻”但强大的精神上的“无物之阵”,从而为后文的“辩证运动”叙述提供了动力和能量。而在《活着之上》中,聂致远与池大为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两部小说在创作路线和主旨表达上几乎是一种“同型异构”。小说讲述的是聂致远的高校生存,但小说却在开头先写“爷爷”的死,先写《石头记》。小说写道:“爸爸把爷爷的头扶起来,将几本厚厚的书塞在他的头下,我看清了是《石头记》”。而十七年后,“我”再次看到了《石头记》,而这时已经“世事如烟”、“沧海桑田”、“昨是今非”了,一切都在朝利益看齐,世俗化潮流浩浩荡荡。“我”在与赵教授的接触中,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让在俗世中沉迷的“我”警醒。这种警醒,便是后文让聂致远保持精神警惕的精神力量。而《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也基本是在小说开头构建的精神与世俗、理想与现实、此岸与彼岸的“两个对立面”上展开。可见,一个好的开头,在短短的篇幅中,整个小说的情节走向、精神布局、思想表达便基本形成了氛围、奠定了基调。短短的开头要承担如此重要的文本功能,这也就怪不得作家们抱怨开头“很麻烦”和“令人痛苦”了。
二、结尾的意义
虽然乔治·艾略特感叹“结尾是大多数作者的薄弱之处”,但对于优秀作家来说,结尾往往是他们显示其写作优势和眼光高远之所在。高明的结尾,我们总会用“水落石出”、“余音绕梁”或“令人回味”等词语来形容,但这种形容只是指明了叙事的效果,还终究没有抵达产生这种效果的艺术上的技巧及其意义上的揭示。假如说,开头是功能性的,那么结尾更具意义上的表达和提升。
本文借助阎真的小说来讨论结尾的意义。结尾往往是故事讲完了之后的一个“作结”。然而,“作结”并不代表彻底“结束”,如果是彻底“结束”,那么其文本的启示意义将大打折扣。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说:“倘若只能得到一种结尾的感觉,那么也就很可能是受到了一种梦幻式终结的蒙骗。”[5]51而弗兰克·克默德也认为:“一个平铺直叙、结尾明显的故事似乎更像是神话,而不是小说或戏剧。”[1]17因此,可以说,好的结尾必然会将读者导向一种意义,归宿于一种情感。在小说的形式上,完全可以认为,一部小说写完了,但从情感上,我们仍然无法拒绝那部小说还在我们的心底起飞,将我们牵引到一个新的心灵世界,给我们以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甚至于“总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即根本无法确定该故事是否确实已经完结”[5]52,而这正是作家和批评家争论不休的所谓“结尾的难题”。在《曾在天涯》的结尾,高力伟的回国是小说的终点,但未必又不是起点。高力伟之所以滋生出强烈的回去的情感,就在于他在异国找不到认同和归宿感,于是回去便成了其最终的价值选择。小说的“尾声”也正是在登上回去的飞机处作结。然而,这样一种作结是在一种新的生命意识处的作结。三年多的异国漂泊并非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的意义便在于这种生活改变或更新了高力伟对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比如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平庸,“我不能再依据古往今来的那些伟人的事迹去设想自己的人生”。因此,高力伟踏上航程,其实也隐喻着另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开启。这种结尾方式其实将读者导向了“不可知”,呈现出开放性。高力伟在异国经历了种种不适之后,其悔恨之意逐渐被其强烈的生命体验和思考所覆盖,以至于我们不再关心其留学生活本身,而更愿意在“文本之上”观察和想象高力伟生存遭遇中的人性之悲、岁月之衰和生命之痛。《沧浪之水》的结尾选择了一个世纪末的日子,在这一天,已经贵为厅长的池大为回到了当年“父亲”下乡和自己的出生之地,在这里,他感慨万千,生命选择几乎完全改写了,他站在父亲的坟前怀着一种背叛,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告慰的心情,渴求父亲也能“理解另外一种真实”。池大为最终在父亲的坟前烧掉了那本象征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从而宣告了一种精神的死亡,但在小说的最后他却又“仰望星空”,这显然表征了深谙官场之道的池大为身心分离的现实无奈。正如有批评家认识到的:“小说的结尾用了北岛诗歌的意蕴,这显然又是一种悖论与荒谬。”[7]因此,可以说,《沧浪之水》正如《曾在天涯》,小说的终点,未必不是其起点。小说的结尾,池大为选择的是一个新的价值平台,而人们对这种选择产生的心灵忧患和焦灼,必然会让人倍感无奈、沉重,从而形成一种悲剧性的,甚至躲不掉的、宿命般的生存紧张。这样一种结尾方式在《因为女人》中同样“奏效”。假如说《沧浪之水》表现的是男人的时代性困境,那么《因为女人》表现的则是女人的时代性陷阱。在小说的结尾,柳依依“说服自己这是宿命,悲剧性是天然的,与生俱来”,“不可能会有奇迹发生”,逃不掉的,从而也想着要趁着琴琴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要把她那种天然的信仰萌芽摧毁”,以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避免女人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小说通过对柳依依“生存困境的展示”,确认了女人的悲剧性宿命。小说的这种结尾方式,已经彻底轰毁了消费时代女性的精神支撑,它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生命悲叹和人性思索。正如有批评家所指出的:“《因为女人》结尾处由欲望、文化等种种不可逃避的存在因素构成的‘黑色的漩涡’,要将所有的人都吸进去。浓重的悲剧意识笼罩着小说世界,意义已经虚无。”[2]既然反抗已经失效,意义已经虚无,那么小说对市场经济、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优先、道德无底线的反思和批判显然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这,却又“溢出了文本”,成为从结尾引申而出的题外之义。
从《沧浪之水》结尾烧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仰望星空”和《因为女人》“黑色的漩涡”可以发现,阎真喜欢在结尾使用一种“隐喻”的方式,从而使文本意义“溢出边界”,在一个开放式和象征式的结尾中,对时代予以追问,对人性予以沉思,对生命予以警醒。在《活着之上》的结尾中,阎真更是将象征发挥到极致。在《活着之上》的结尾,蒙天舒充分利用时间搞关系去了,无所事事的聂致远有心无心地再次来到了门头村,在经历了纷繁世事后,他依然保持着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某种“对话性”,并在“沉闷的风的中心”,感受到那种“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小说的结尾可以说处处是象征,比如门头村、曹雪芹、《红楼梦》的精神象征性,比如聂致远和那位锄草的大娘的对话,比如那“沉闷的风”、那“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都让我们领略到聂致远心灵的无奈和精神的紧张,从而在“文本之外”探寻到阎真在《活着之上》表达的意义叩问和价值追寻。综观阎真的四部小说,可以发现,其小说的结尾都具有开放式的意义表达,从而把“薄弱的结尾”做得厚重、高远,使小说从现实的沉浮中超拔出来,生发出“现实之上”的“心灵探寻”和精神意义。
三、处于“结构之中”的首与尾
上文探讨了小说开头的功能和结尾的意义,但并不是说开头的意义和结尾的功能就可以忽略,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甚至多面。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整体总是大于局部,而且是先于局部的,一部小说的意义都只能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因此开头的功能和结尾的意义也只能在整体中体现。也就是说,小说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格非所言:“小说中的任何部分一俟产生,都毫无例外地被包孕在‘结构之中’。”[8]
如上文所述,阎真的小说结尾在意义传达上是开放的,但从形式上看其小说却又具有封闭性,体现出结构上的完备。在《曾在天涯》和《因为女人》中,从时间点上看,小说的首尾构成了一种闭合关系,即小说主体在叙述过去,但在结尾处却又和开头的现在取得了衔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形式上“弥合”的“自足”的小说整体。而《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在时间上虽然是一种顺延和更替,但两部小说通过意象的首尾重复(如《沧浪之水》中首尾重复出现“上坟”、“仰望星空”、《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活着之上》中首尾重复出现登上西山、曹雪芹和《红楼梦》等),也构成了一种“照应”关系和“完结”体系。甚至可以说,《曾在天涯》起于回国,终于回国;《沧浪之水》起于上坟,终于上坟;《因为女人》起于女人“青春不再”的哀叹,终于女人“青春不再”的哀叹;《活着之上》起于《红楼梦》,终于《红楼梦》。这都是阎真小说在形式上自觉追求的一种叙事“圆满”和“作结”,这样一种结构上的“严密”和“照应”,显然成了阎真小说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与话剧名作《雷雨》的结构方式极为相似。《雷雨》的故事主体是一个“过去完成时”,而其序幕与尾声是一个“现在进行时”,首尾彼此呼应且贯通,以“现在”共同对“过去”构成一种远距离的观照和反思。但细致地来分析,这种封闭型的结构模式在阎真的小说中却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姿。先来看《沧浪之水》。《沧浪之水》的首和尾显然是一种对比性存在,即在小说的开头,精神是坚硬的,而在小说的结尾,精神不得不让位于生存。因此,小说的开始,《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是“父亲”所珍藏的,而在小说的结尾,这本书却也只能在火光中化为尘埃。小说的开始,“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我”上坟时心中怀着的是恨,恨世道的不公,恨人性的丑恶,但在小说的结尾,“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悲枯草覆盖”,“我”心中有一种“怯意”,需要勇气走到“父亲”的坟前。在小说的开始,“仰望星空”是豪迈的,激情满怀的,而在小说的结尾,“仰望星空”的感觉“我无法对它做出一种准确的描述”。通过这种首尾的呼应和对比,阎真赋予《沧浪之水》一种结构性意义,看到了一种精神文化的现实处境,这种富有历史意味的文化“转型”和精神的死亡,便在触目惊心的前后对比中得以生成。《活着之上》同样使用了首尾重复的手法。正如有批评家注意到的,“小说以《红楼梦》开头,也以《红楼梦》结尾,在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文学基调之时,也在展现作家的文学野心”[9]。在这里,《红楼梦》在小说中不仅只是一种前后照应关系,使文本形成一个整体,其意义更在于首尾的呼应关系,即通过聂致远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致敬和朝拜,强化了聂致远在世俗化大潮中的“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的认识,从而也进一步伸张了精神坚守的意义。《曾在天涯》和《因为女人》采用的是一种“倒叙”的结构,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同时也是在开始的地方结束,以“回望”的方式对短时间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予以重新观照,从而在“过去”与“现在”的扭结处进行生命思索和价值表达。只不过这两部小说中《曾在天涯》更侧重于空间跨越的远距离观照,而《因为女人》则更侧重于时间上的青春不再。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首尾对比,还是首尾呼应、前后照应,阎真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时空”观念的引入。如《曾在天涯》的开头:“多少年来,我总忍不住想象在一百年一万年之后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遥望这今天的人们”,而结尾:“隔着这一千多个日子望过去,我已经步入中年,生命的暂时性有限性已经不再朦胧生命的暂时性”;《因为女人》的开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怀有恶意”,结尾:“直到时间的深处。在那里,一切都化为乌有”;《沧浪之水》的开头:“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而在结尾,“我”“仰望星空”,等等。阎真通过在小说的首尾引入“时空”,使人物在浩渺的时空和永恒的宇宙中感受到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从而使人物的思索更具生命内涵和哲理意味。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开头虽然“麻烦”,而结尾也确实是容易陷入“薄弱”,但对于高明的作家来说,越是“麻烦”和“薄弱”的地方,却正是其大展身手之处。阎真在其四部小说中设置“倒叙型”的开头来对“过去”进行颇富“痛感”的反思和“时空压缩型”的开头来形成小说展开的精神背景,并在结尾通过隐喻和象征导向意义思索,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了开阔而厚重的生命境界与凝重而和谐的艺术品质。
[1]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M].刘建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余中华,阎真.“我表现的是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平均数”——阎真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8(4):47-51.
[3]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56.
[4]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6.
[5]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2.
[7]阎真,姜广平.“心灵的博弈无处不在”[J].西湖,2011(2):92-98.
[8]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81.
[9]萧夏林.《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J].文艺争鸣,2015(5):114-121.
2016-06-29 基金项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2015年科研资助项目(XYS15S04) 作者简介:郑国友(1974-),男,讲师;E-mail:zhengguoyou2003@126.com
1671-7031(2017)01-0117-06
I207.4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