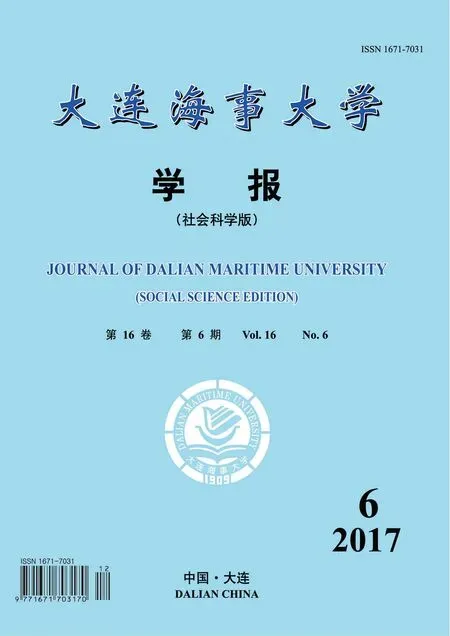《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第5条第1款第1项评析
——兼论中国惯常居所制度之建立
2017-03-13杨育文
杨育文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
第5条第1款第1项评析
——兼论中国惯常居所制度之建立
杨育文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惯常居所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判决项目《2017年2月公约草案》的间接管辖权依据之一,但各国对惯常居所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居住期限、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建议以3个月作为认定惯常居所的必要期限但不具有强制性。在经常居所、经常居住地和经常居所地等措辞相近而含义各异的术语中,中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对应着该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但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与惯常居所存在不少差异,包括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不能指向外国(地区)、在客观要件的认定上过于严格、对其他因素考虑较少等。为更好地实施未来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公约》,司法机关应当引入惯常居所制度,尤其是引入居住期限以外的其他考虑因素,而不是直接适用现有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制度。
判决公约;惯常居所;经常居所;经常居住地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一直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注的问题之一。2017年2月,特别委员会公布了《2017年2月公约草案》(以下简称《公约草案》)。《公约草案》第5条第1款第1项以惯常居所作为审查外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即“间接管辖权”,《公约草案》中称之为“管辖权过滤器”)的依据之一。在国际上,尽管各国普遍接受惯常居所这一术语,但该术语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公约中从未被界定,而不同国家在解释该术语时存在差异,且根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关于公约建议文本背景和主要问题的注解》(以下简称《注解》*Hague Conferenc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COPIL”), Explanatory Note Providing Background on the Proposed Draft Text and Identifying Outstanding Issues, Prel. Doc. No 2, April 2016.),一国对惯常居所的认定对另一国不具有约束力。
在我国,尽管学界已广泛接受“惯常居所”这一术语,但这一术语并未为立法机关所接受,我国不同法律中的措辞分别为经常居所、经常居住地、经常居所地,措辞相近而含义各异。各国对惯常居所间接管辖权中的惯常居所的具体理解如何,这些差异对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有何影响?我国法律中哪一个术语对应着《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其含义是否与惯常居所含义相当?我国批准未来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公约》(以下简称《判决公约》)时又该如何认定惯常居所?本文拟对此展开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各国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惯常居所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涉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无多大影响,故本文不涉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惯常居所。此外,本文仅讨论成年人的惯常居所,而不涉及未成年人的惯常居所。
一、惯常居所间接管辖权规范的比较分析
《公约草案》第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在其成为原审国诉讼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时,被请求承认或执行判决的人在原审国具有惯常居所”作为判决可以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一。该项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被请求承认或执行的人是原审国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此处的当事人显然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与1971年《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以下简称1971年《执行公约》)第10条第1项仅包括被告不同,根据《注解》,此处的当事人包括任何当事人,原告、第三人及参加诉讼的其他当事人,*参见《注解》第18页。其中当然包括被告。《注解》认为这体现了通常接受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参见《注解》第18页。据此,如果原告与被告在同一国家具有惯常居所,原告在该国起诉,被告则对其提起反诉并获得胜诉判决,该判决可在其他成员国得到执行。与2016年4月《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建议草案文本》相比,《公约草案》取消了向该判决义务的承担者请求承认与执行的规定。此一规定似乎是因为义务承担者并非外国判决确定的债务人,超出了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本身”的范围,似乎更适合在国内执行程序中解决。
第二,该方当事人在原审国具有惯常居所。在《注解》中,常设事务局未区分自然人或组织,对惯常居所打了一个比方,即家(“at home”)。*参见《注解》第18页。对于自然人的惯常居所,《公约草案》没有做出界定,这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公约往往把惯常居所的界定交给各缔约国的传统一致。1999年《民商事管辖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解释报告认为,尽管惯常居所不是纯粹事实性的,也存在多种解释,但其在事实意义上更为可靠,倾向于指一个人在某一地方(place)持续很久的出现,其留在该处的意图仅起到附属的和不重要的作用。*HCOPIL,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dopted by the Special Commission and Report by Peter Nygh and Fausto Pocar, Prel. Doc. No 11, August 2000, p. 40.因此,如果把惯常居所的构成要件区分为客观要件(居住的事实)和主观要件(居住意图),那么《公约草案》通常只考虑客观要件,而不考虑主观要件。
第三,该方当事人在原审国取得惯常居所的时间仅限定为其成为原审国诉讼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时。与1971年《执行公约》第10条第1项相比,尽管对被请求承认或执行的人的惯常居所的审查时间从“提起诉讼时”改为“成为诉讼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时”,但是根据《注解》,此一时间实际是指有权起诉一方对该被请求承认或执行的人“提起诉讼程序之时”,*参见《注解》第18页。并无实质差异。成为原审国诉讼程序的一方当事人之后的惯常居所的变更不影响该项的适用,这与管辖恒定原则是一致的。
对于构成要件一和构成要件三,各国已达成共识;对于构成要件二,尽管各国在“惯常居所”的措辞上达成一致意见,但这并不代表各国在“惯常居所”的理解上达成一致意见。本文将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文件和国内法中挑选部分有代表性的立法进行比较。
(一)欧盟:以住所为惯常居所
欧盟法中的惯常居所总体是指,“该自然人确立的作为其永久或惯常利益中心的居所所在的地区(country)”[1]187。尽管欧盟法院已就惯常居所做出了许多判决,并指明了一些因素,包括该自然人的家庭状况、(跨境)移动的原因、居住的期间和连续性、工作的稳定性和该自然人在所有情形下显示出来的意图,但是,上述因素不是用来确定长期或短期的定居意图是否强化了该自然人实际居住在一成员国,而是确定该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其永久或惯常的利益中心。[1]188
但是,在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欧盟并未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尽管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和2007年《卢加诺公约》均已取消了管辖权审查,且两者均为双重公约,但仍可作为参照。2007年《卢加诺公约》的解释报告否定了以惯常居所替代住所的提议,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一些专家认为惯常居所更适合于个人和家庭事项,而不适用于商业性质的事项;其二,惯常居所需要独立的定义,而对此可能很难达成协议。该解释报告同时还否定了把惯常居所并入住所并作为备选的确定管辖权的依据的提议,理由是可能导致多重管辖,尤其是住所和惯常居所位于不同国家时。*EU,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signed in Lugano on 30 October 2007-Explanatory Report by Professor Fausto Pocar, 2009/C 319/01, 23 December 2009, p. 7.
在欧盟法上,住所总体而言意指“一个人与一成员国境内某一较小的地方组织的联系”*EC,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by Professor Dr Peter Schlosser, OJ C 59 (1979), p. 95.。2007年《卢加诺公约》的解释报告认为,至少在自然人作为被告方面,住所作为建立管辖权的主要依据还未遇到特定的困难。*EU,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signed in Lugano on 30 October 2007-Explanatory Report by Professor Fausto Pocar, 2009/C 319/01, 23 December 2009, p. 7.即便如此,住所规范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和2007年《卢加诺公约》均以“住所”作为人的主要的间接管辖依据,并分别在第62条和第59条规定在确定某人是否在一成员国具有住所时,适用该成员国法律。其中,住所的构成要件以客观要件为主,但不排除主观要件。比如,德国《民法典》第7条第1款规定,“经常居住在一个地点的人,在该地点设定其住所”,虽然德国《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通说认为,设定住所必须满足“具有将该地点作为自己生活重心的意思”[2]8,但又无须采取任何形式,因此,需要以客观事实来推定当事人的主观意思。
综上所述,考虑到2007年《卢加诺公约》的解释报告中否定了以“惯常居所”替代“住所”的提议,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同样坚持以住所作为管辖依据,同时考虑到欧盟已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组织(REIO)批准了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这似乎意味着在批准未来的《判决公约》时,欧盟很可能推动其成员国(包括2007年《卢加诺公约》的非欧盟成员国的缔约国)把该公约中的惯常居所解释为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中的“住所”,进而适用当事人主张的其住所所在的成员国国内法进行判断。
(二)英国:以惯常居所(平义)为惯常居所
在欧盟法之外,英国法可以分为普通法和制定法,*本文中的“英国”仅指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包括苏格兰。分述如下:
在普通法上,英国法院认可的间接管辖权依据主要原则之一是“判决债务人在诉讼提起时出现”,包括单纯出现(即标签管辖权)和居所。[1]690在制定法上,1920年《司法行政法》第9条第2款第2项从反面规定了“未通常居住(ordinarily resident)在原审法院辖区内的人”在未满足某些条件时,不予命令予以登记(即拒绝承认与执行)。1933年《外国判决(互惠执行)法》第4条第2款第1项第4目对此稍稍做了修正,“如果判决债务人作为原审法院诉讼中的被告在诉讼提起时,居住在该国”,则英格兰法院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即排除了外国法院的标签管辖权。
英国法用居所(residence)来表达“一个人与某一特定地区的法律联系”。*EC,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by Professor Dr Peter Schlosser, OJ C 59 (1979), p. 95.住所并非适格的管辖依据,在一国具有住所但未在该国居住或出现,并不能给予外国法院管辖权。[1]705其中,惯常居所总体是指“以作为其当下生活的正常秩序(regular order)的一部分的确定的目的(settled purpose)而居住的地区(country)”[1]177。该定义包括了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欧盟法上,为减少英国普通法对住所的严格解释与英国加入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前该公约原缔约国对住所的理解之间的差距,[1]405英国在1982年《民事管辖和判决法》第41条就该公约(包括后来的《卢加诺公约》)中的自然人住所定义如下:自然人在英国有住所是指“该自然人在英国(或其特定部分)居住,且居住的性质和情形表明其与英国(或其特定部分)有实质联系(substantial connection)”。其中,自然人正居住在英国(或其特定部分),且最近三个月或以上时间内已在英国(或其特定部分)居住,就推定满足了“实质联系”的要求。该定义取消对自然人定居意思的要求,与惯常居所较为接近。自然人在缔约国外有住所的定义与在英国(不包括其特定部分)有住所类似,但不适用上述对实质联系的推定。
综上,1982年《民事管辖和判决法》中住所的规定,是英国在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时,应后者要求而修改的,英国脱欧可能会导致该规定被废除。在对自然人的惯常居所管辖权进行审查时,由于英国脱欧的影响,适用何种标准尚不清晰;但很可能会继续遵循先例,即对“惯常居所”做平义解释,即强调“确定的目的”且该目的是“其当下生活正常秩序的一部分”,此一定义严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
(三)美国:以住所为惯常居所
在制定法上,美国涉及对外国法院管辖权审查的法律主要是州法,而非联邦法,并主要以1962年《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案》(以下简称1962UFMJRA)和2005年《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案》(以下简称2005UFCMJRA)为蓝本。以下将以两者为依据进行分析。
1962UFMJRA第5条第1款第4项规定,“诉讼提起时被告在该外国(foreign,可以理解为包括外州)具有住所”,则不得以该外国法院没有对人管辖权为由而拒绝承认。2005UFCMJRA第5条第1款第4项仅在措辞上明确其适用范围为外国(foreign country,不包括外州)。
在立法建议案上,虽然2005年美国法学会(以下简称ALI)《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法案》没有明确规定惯常居所管辖权,但从该法案第6条第1款明确排除“原告的住所、惯常居所或成立地”而没有排除“被告的住所、惯常居所或成立地”,可以推断“被告的住所、惯常居所或成立地”是合格的管辖权。此一推断可以从作为各州立法基础的1962UFMJRA和2005UFCMJRA的上述规定得到印证。
在学理上,《冲突法(第二次)重述》(以下简称《重述》)则准用第92条(有效判决的要件)评注e指出的各条作为审查外国法院管辖权的主要依据。《重述》中与惯常居所相关的主要有住所(第29条)和居所(第30条),似乎排除了自然人的出现(第28条),同时,该两条均规定“但自然人与该州的关系如此微弱以致行使该项管辖权不合理时除外”,分述如下:
第一,住所。《重述》第11条把住所界定为“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家(home)”,而家的标准规定在该重述第12条:其一,住处的物理特征;其二,当事人花在该住处的时间;其三,当事人在该住处做的事;其四,该住处中的人和物;其五,当事人对该住处的态度;其六,当事人离开后返回该住处的意图;其七,与当事人相关的其他住处,及该住处与上述因素有关的情形。*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 of Laws (1988 Revision), §12, comment c.特别是其家人所住的地方;在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何处的证据时,其住所有可能在其工作地,但其工作仅为临时性质时除外。*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 of Laws (1988 Revision), Special Note on Evidence for Establishment of a Domicil of Choice.其中,住所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第二,居所。在考虑是否根据居所行使管辖权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其一,该自然人在该州内所花费的时间,应是相当一大部分的时间。其二,其在该州内居所的性质,应该是固定的住处而非宾馆或旅社。其三,其对该州的思想态度,比如,其是否喜爱地(with affection)把该州看成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去的地方;其到该州来是自愿的,而不是因为经济因素或其他必要性。其四,其在该州内所做的事情,应是重要的。一个自然人在一州的活动越多,其与该州的关系就越密切。*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flict of Laws (1988 Revision), §30, comment a.可见,该重述中的居所比较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但其构成要件中要同时考虑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但是,在“固特异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对自然人而言,行使一般管辖权的典型法院是其住所(地法院),*Goodyear Dunlop Tires Operations, S.A. v. Brown, 131 S. Ct. 2846, 2853 (2011).尽管该案仅针对公司的直接管辖权,该观点可能被视为附带意见,但是,该观点可能会强化1962UFMJRA和2005UFCMJRA中的相应规定,即对于《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美国法院仅把其理解为“住所”,而不包括居所或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有美国学者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此一观点过于僵化,并提出以居所或惯常居所代替住所,[3]美国是否会批准《判决公约》及批准该公约后如何执行还有待观察。
综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般管辖权的理解与1962UFMJRA和2005UFCMJRA的规定基本一致,即对自然人而言,《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仅限其住所,其适用条件较为严格。
(四)瑞士:以住所(惯常居所)为惯常居所
瑞士《国际私法典》第26条第1项除明确规定适用镜像原则外,还规定在瑞士法没有对应规定时,如果“被告在原审国(州)具有住所”,则该外国法院具有间接管辖权。该法典第20条规定:“1.在本法意义上,自然人:(a)在其以定居的意思居留的国家内有住所;(b)在其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国家内有惯常居所,即使该时间在开始时是有限制的;(c)在其业务活动中心所在的国家内有其营业所。2.任何人不得同时拥有一个以上住所。如果一人没有住所,则代之以惯常居所。《瑞士民法典》关于住所和居所的规定不予适用。”[4]此处的“惯常居所”似乎包括居所和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因此,瑞士似乎倾向于把《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理解为其《国际私法典》中的住所并辅以惯常居所,比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内涵要宽一些,其中住所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五)日本:以住所(居所)为惯常居所
日本2011年《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规定,“法院对以一个人为被告的诉讼具有管辖权,如果该人在日本具有住所,或虽没有住所或住所不明时但在日本具有居所,或虽没有居所或居所不明但在诉讼提起前在日本具有住所,但是该人在日本最后一次具有住所后,又在外国具有住所的除外”。日本《民法典》第22条规定,“每人以各自生活的根本场所为其住所”。[5]因此,日本似乎倾向于把《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理解为住所(居所),且仅考虑客观要件。
(六)中国:以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为惯常居所
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其中,住所和经常居住地,均只考虑客观要件,而不考虑主观要件。
2017年《民法总则》第25条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对《民法通则》第15条,即“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做了修正,以“经常居所”取代了“经常居住地”的措辞,与原有的“住所”相对,更符合中文语言习惯。虽然住所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导致经常居所适用范围的缩小,但住所实际上主要针对在中国进行居所登记的自然人,对其他自然人则不适用,因此,住所定义的扩大并不能完全排除经常居所的适用。
我国签订的明确规定了管辖权规则的11个双边条约中,除中国—阿联酋、中国—科威特双边条约增加了“不动产以外的诉讼”的限制条件外,均规定“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则该缔约一方法院具有管辖权。因此,上述条约似乎倾向于把《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理解为“住所或居所”,但“居所”的含义宽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未必能够满足统一私法国际协会(UNIDROIT)与ALI共同制定的《跨国民事诉讼原则》中的“实质联系原则”,因此,此处的居所似乎比较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
2000年《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58条(间接管辖权)第1项以被告在该外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惯常居所”,作为认定外国法院具有间接管辖权的依据。但是,该示范法第三章(法律适用)第61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经常居住地为其惯常居所”,虽然该定义并未出现在第二章(管辖权),但由于此种理解与《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一致,这似乎意味着2000年《国际私法示范法》也倾向于以住所(经常居住地)作为认定外国法院间接管辖权的依据。
综上,对于《公约草案》中“惯常居所”,虽然我国批准未来的《判决公约》时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本文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把“惯常居所”理解为住所(经常居住地)。
二、惯常居所间接管辖权规范的法律问题分析
尽管惯常居所是一个广泛认可的间接管辖权规范,但如前所述,相同的概念下对惯常居所的不同理解,正是该间接管辖权规范最大的问题。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系列公约中从未对自然人的惯常居所进行界定,目的是避免该定义成为技术性规则,但是,不同国家在解释惯常居所时却存在重大的不一致,特别是在1980年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诱拐公约》)下。[1]177尽管惯常居所的认定通常被认为更接近于事实认定,但原审法院对自然人惯常居所的认定对被请求法院不具有约束力;*参见《注解》第19页。此外,与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不同,《公约草案》直接取消了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对被请求法院的拘束力的规定。对于《公约草案》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各缔约国原则上运用本国法进行解释,因此,各缔约国可以依其本国法对原审国的“惯常居所”进行审查。由于各国对自然人惯常居所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意味着惯常居所的事实认定可能处于不确定状态,可能存在法律冲突。此种冲突可能主要表现为,依请求国法律,该自然人在该国有惯常居所,而依被请求国法律,该自然人在被请求国没有惯常居所,从而认定原审国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但不排除其他的间接管辖权依据)。关于我国法院判决在美国承认与执行的“陈诉孙案”就涉及此一问题。被告是持有中国工作签证的美籍华人,其妻子和孩子住在纽约,从原告主张来看,原审法院似乎认为被告住所位于美国,而被请求法院则认定被告住所位于中国,*Chen v. Sun, Civ No. 1:13-cv-00280 (ALC) (KNF), 2016 U.S. Dist. LEXIS 7253, at 3 (S.D.N.Y. January 21, 2016).并最终以不具有诉讼标的管辖权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自然人惯常居所的居住期限的问题
同一法院的判决在多个缔约国申请承认或执行,由于被请求法院分别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而各国关于惯常居所的宽严不同,由此可能导致同一法院在一些国家被认为具有管辖权,而在另一些国家被认为不具有管辖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惯常居所的居住期限问题。美国已有学者提出,在《海牙诱拐公约》下为惯常居所设定时间标准,以增加法律确定性和促进适用的统一性。[6]68笔者进而认为,有必要为惯常居所的居住期限设置一个推荐性的最低标准,在达到此一最低标准后,则鼓励各国根据有利承认的原则,根据本国法律尽可能认定成立惯常居所,但各国具有最终决定权;达不到此一最低标准的,则应当谨慎认定成立惯常居所并充分说理。
从国际范围来看,可能涉及惯常居所的期限主要包括3个月、6个月和1年三种情形:
第一,3个月。欧洲议会及理事会《关于联盟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移和居住的第2004/38/EC号指令》第8条第1款规定,“在不损害第5条第5款的情形下,对于居住期间长于三个月的,东道成员国可以要求联盟公民向相关机构进行登记”,*EU, OJ L 158/77, 30.4.2004, p. 77-123.又如英国在1982年《民事管辖和判决法》第41条(《布鲁塞尔条约》中的住所)的规定,以及瑞士关于设立惯常居所的最短居住时间的通说。*BGE 119 III 54 E. 2d. 转引自文献[7]。
第二,6个月。多数国家规定,即只要在现住地居留满6个月,即可作为常住人口登记。[8]在国际税法上,通常以个人在有关历年中连续或累计停留超过183天(相当于6个月)作为对个人的独立个人劳务和非独立个人劳务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期限。*United Nations Model Double Taxation Conven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1), Art 15, 16.在国际家庭法领域,德国、奥地利均要求连续居住满6个月即取得惯常居所,美国《统一儿童监护管辖和执行法案》(UCCJEA)及此前的《统一儿童监护管辖权法案》均以至少连续六个月的居住作为认定儿童家所在州(home state)的标准。[6]15-16,65-66我国也有类似规定,比如,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只要“居住6个月以上”并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情形之一的,就可申领居住证;又如,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也把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列为“常住人口”。*国发〔2014〕51号。
第三,1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统计司《关于人口动态统计系统的原则和建议》为统计常住人口时建议采用12月的期限,*UN, Statistics Division,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 Vital Statistics System (2014), Statistical Papers, Series M No. 19/Rev.3, p. 28.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中也通常以1年作为认定经常居住地的标准。
此外,英国学者彼得·斯通(Peter Stone)还提出一种方案,即一个成年人如果在一个地区实际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an appreciable period of time),并自愿且稳定地(settled)继续在此无限期或长期(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居住,则其在该地区具有惯常居所。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指至少1个月的时间,长期则指至少3年时间。[9]366该方案与英国判例基本一致,即强调主观意图且其意图中居住期限至少3年,对实际居住的期限则不太强调。适用该规则的情形可能较少,并可能导致惯常居所成为一个新的技术性规则。
应当说,6个月的期限是比较合理的期限,但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各国通常不对惯常居所规定具体的期限,且英美法中认定惯常居所的期限可能很短,因此,笔者建议以3个月作为认定惯常居所的必要期限,而6个月作为认定惯常居所的充分期限。但是,上述期限仅仅是推荐性标准,供各国参考并逐步推动国际统一适用。当然,彼得·斯通的方案与笔者建议并不矛盾,可以作为辅助性规则。
(二)自然人惯常居所的构成要件及证明标准问题
如前所述,在自然人惯常居所的认定中,《公约草案》、日本和中国不考虑或几乎不考虑主观要件,仅考虑客观要件;欧盟则以客观要件为主,但不排除主观要件,且根据被主张的“惯常居所”所在成员国的法律决定;英国、美国和瑞士则通常需要考虑主观要件。此外,一些国家在认定自然人惯常居所时,还考虑惯常居所的丧失问题。
德国《民法典》第7条第3款规定,“以放弃居住的意思取消居住的,住所即被取消”,[2]3此即德国“惯常居所”的终止条件,包括客观要件(取消居住)和主观要件(放弃居住的意思)。
在英格兰法上,在确定惯常居所时,(惯常居所的)取得和丧失是有区别的因素。与惯常居所的取得不同,惯常居所的丧失可以是立即的,正如布兰登勋爵的典型表述,“一个自然人可以在一天内停止在一国惯常居住,如果他或她以不返回该国而在另一国长期居住的确定意图离开”,但是出国较短的期间或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也能导致立即丧失惯常居所。[1]180此处,同样涉及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且以主观要件(确定的意图)为主。彼得·斯通总结英格兰判例后提出的规则是,一个成年人离开一个地区或持续不在该地区,且其目的稳定,即不为了继续无限期或长期居住而返回该地区,则该成年人放弃其现有的位于该地区的惯常居所。其中,长期同样是指至少3年。[9]342,366应当说,该方案为惯常居所的放弃设置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可能导致很难认定惯常居所的放弃,尤其是主张某人已放弃其惯常居所的人并非被主张的人本人时。
我国民事诉讼中也涉及“惯常居所”的放弃问题。“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唐雨东(第一被告人)与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告人)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以下简称“中能公司案”)就是一例。该案中第一被告人曾在原告处工作多年,后离开原告处到第二被告人处工作且第二被告人为其支付购房款,至原告提起诉讼时第一被告人已工作约3个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13号。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如果起诉之前被告就已经离开了经常居住地回到住所地,或者明显不可能再回到经常居住地而到其他地方居住的,那就不应再以该经常居住地确定案件管辖,可以由公民住所地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中,“明显不可能再回到经常居住地而到其他地方居住”,即经常居住地的放弃。与德国和英国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仅采用客观要件。与英国不同,对经常居住地的放弃采用相当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即高度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与德国相当),而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则通常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即足够显示“具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理由更可能是真实的。[10]相对而言,我国的证明标准更高。
综上所述,在惯常居所的认定(包括丧失)中,在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公约草案》并未涉及此一问题,但是,从惯常居所的取得主要采用客观要件来看,惯常居所的丧失也应当主要采用客观要件,证明标准也交由各国国内法解决。
三、中国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与《公约草案》惯常居所的不兼容问题
如前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我国应当把《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界定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但有必要对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与《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的兼容性进行考察。
(一)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惯常居所的对应者
关于经常居所/居住地,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三个司法解释,即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虽然总体一致,但也存在不少的差异,主要差异有措辞、是否必须是生活中心、认定时点和除外事项的差异。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哪一个术语对应着《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一些法院并不能区分《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经常居住地与《法律适用法解释》的经常居所地,如“刘海洋、刘海军、王斌、韩旭、徐福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王斌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立民终字第00040号。“王斌案”主要争点为:被告上诉,认为自己因私出国,不是劳务派遣,并在刚果(布)已工作生活数年,应认定刚果(布)为其经常居所地,并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告知三原告向刚果(布)国家有关法院起诉。最终二审法院未对该上诉理由进行分析,直接驳回被告上诉。
应当说,上述三个司法解释分别适用于实体法、程序法和国际私法(冲突法),性质并不相同,因此,在管辖权领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因为在确定管辖权时,各国通常以原告提起诉讼时这一时点来确定被告的惯常居所,从而确定管辖法院。《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意见》和《民法总则》及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经常居所的规定,仅仅是概括性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管辖权的确定。同理,虽然《法律适用法解释》中经常居所地已与国际上的惯常居所非常接近,包括经常居所地可以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可以指向本国和外国(地区),可以兼容住所,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但是,以《法律适用法解释》中的“涉外民事关系产生、变更或终止时”来确定管辖法院,并不适宜。因此,只有《民事诉讼法解释》中的经常居住地才能对应《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
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上的经常居住地通常被翻译为place of habitual residence,这似乎意味着,经常居住地对应着《公约草案》的惯常居所(habitual residence),*从空间范围来看,惯常居所和经常居住地是一致的,两者均指一定的“地区”,而非“地点”。参见文献[11]第88~89页。但此一翻译存在误导:前者是法律概念而后者是事实概念,两者在认定上存在诸多差异。此外,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可以包含通常意义上的住所,但是,我国的经常居住地仅在其与住所地不一致时才能发挥作用,很难说其作用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相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经常居住地必须是“离开住所地”后的某个地方。从文义来看,经常居住地和住所似乎是完全不能一致的,[12]即经常居住地完全不能包含住所,但《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了“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形,亦即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是可以一致的。此处《民事诉讼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矛盾,似乎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避免司法实务操作总是比较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而做的限缩解释,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在确定管辖权时,经常居住地不能完全对应着惯常居所,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才是惯常居所的对应者。
(二)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惯常居所的反对者
尽管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对应着《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但是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与惯常居所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1.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不能指向外国(地区)
《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是一种“双边规范”,既可能指向本国(地区),也可能指向外国(地区)。在“王斌案”、“雷莉与李金霞合同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2825号。本案中被告住所地在中国而经常居所地在加拿大,被告在管辖异议中主动要求适用第265条(仅限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情形)并被法院支持,但法院没有对该条中的“没有住所”做出解释。法院未解决的问题是:经常居住地同时适用于中国大陆和外国(地区),还是仅限于中国大陆?《法律适用法解释》中的经常居所地不限于中国大陆,这是由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冲突规范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而作为双边冲突规范连接点的经常居所地当然不限于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条并未做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其中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应当理解为仅限于我国大陆地区,理由如下:
第一,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民事诉讼法解释》,住所地总是和“户籍所在地”关联,即使《民法总则》也把“户籍登记”记载的居所放在首位,“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仅仅是补充。尽管除我国之外也有少数国家存在户籍登记制度,但此种制度并不多见,因此,不宜把住所地理解为同时适用于我国大陆地区和外国(地区)。同时,《民事诉讼法》第267条(对在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的措辞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而非“住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因此,不能认为我国的住所地可以指向外国(地区)。
第二,《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为职权性规范,不应当理解为该法为外国(地区)的法院设定了职权,因为这违反了国家司法主权(或司法独立)原则。即使认为该条中的“人民法院”构成对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的限制,即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可以指向本国也可以指向外国,也应当注意到此时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实际上仅指向我国大陆地区。
综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应当理解为仅限于我国大陆地区,不能指向其他国家或地区。
2.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客观要件的认定上过于严格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客观要件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住所地以登记为要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民法总则》第25条尽管包括了“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地),总体上还是以登记为要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自然人在放弃经常居住地后尚未取得新的经常居住地之前,住所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亦即同样适用上述期限,如“雷英与王明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纠纷案”(以下简称“王明新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44号。本案把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有关被告住所地的确定的规范,类推适用于原告住所或经常居住地的认定。和“中能公司案”中,此一解释维护了住所地作为主要管辖依据的地位。
第二,经常居住地以连续居住1年为要件。在经常居住地的取得方面,国内已有众多的学者对此一期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11]最高人民法院中也有法官提出缩短此一期限,但尚未达成共识。
此外,对于经常居住地定义中曾经争议较大的“至起诉时”是否应覆盖“起诉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中能公司案”中做出最佳判决。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以经常居住地确定案件管辖时,不仅要符合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条件,还应满足起诉时被告仍在该地居住的条件,如果公民只是因出差、旅游、休假或者就医等原因暂时离开经常居住地的,对其提起的民事诉讼可由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应当说,相对于“王明新案”,“中能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开经常居住地的认定,考虑到偶然性离开或经常居所地的放弃(相当于惯常居所的丧失),更为全面,与惯常居所的目的更为相符,即“‘惯常的’(habitual)表明此一居所不必是‘连续的’(continuous)”,“偶尔的离开不影响惯常居所的存在”[13]。
总之,严格的登记和时间期限使得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远远严格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在“中能公司案”中,第一被告人的妻子和孩子均居住于其户籍地吉林省,新的工作地位于新疆。根据刘仁山教授的“现时利益中心说”,[14]由于其刚刚被高薪挖到新公司,且其家人的居住地与其工作地相距甚远,不便于经常往返,因此,其现时利益中心应当位于新疆;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3款(同一诉讼中多个被告的连带管辖),原告可以请求户籍地吉林省的相应的法院进行管辖,相对于其工作地法院管辖,这反而不利于第一被告人。所幸,最高人民法院以侵权行为地和第二被告人住所均位于新疆而裁定由新疆相应的法院管辖,似乎隐含着对严格的1年居住期限的否定。
3.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对其他因素考虑较少
正如尼格/波卡报告(Nygh/Pocar Report)所述,在国际范围内,惯常居所主要是指“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出现,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期间。如前所述,住所地采用严格的登记标准而经常居住地采用严格的期限标准,但不考虑任何主观因素,[11]此种做法的优点是法律确定性较好,但显得过于僵化,在同时具有两个经常居住地的情形下则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姚×与余×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就是一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少民终字第09401号。该案中原告(母亲)和被告(父亲)均为外国人,双方生有一女但已离婚,女儿随父亲生活,现原告要求变更抚养关系。被告从2013年5月开始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并在北京和上海均办理了临时住宿登记,且两个临时住宿登记的办理日期至起诉时均达到1年以上。二审法院以此认定被告在北京和上海均有经常居住地,并最终以被抚养人的长期居住地在北京且北京法院先受案为由,驳回被告的管辖异议。此案裁判稍显不足的是,法院并未明确比较认定经常居住地的各项因素。以“陈诉孙案”为例,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在工作日居住在其他地方工作而周末回家且其生活以家为中心的案件中,已婚人士的配偶(如果没有分居)和子女的居住地可以占到很大的比重;但在偶尔探望配偶和子女的案件中,其配偶和子女的居住地则没有那么重要。*Chen v. Sun, Civ No. 1:13-cv-00280 (ALC) (KNF), 2016 U.S. Dist. LEXIS 7253, at 4 (S.D.N.Y. January 21, 2016).本案比较接近于前一类型,从时间因素来看,被告工作地(上海)占优,从家人居住地因素来看,被抚养人居住地(北京)占优。一般而言,家人居住地因素要优先于时间因素,因此,应当认定被告的经常居住地在被抚养人居住地。
此外,《民事诉讼法解释》中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住院就医,这似乎意味着《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劳务派遣和公务”不属于除外情形,也未规定除外情形下经常居住地的认定。应当说,住院就医、劳务派遣和公务通常都不具有“经常”居住的主观意图,但是,《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只要住院就医就不能把医院所在地认定为经常居住地,也未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因此,在认定经常居住地时,应当引入适当的参考因素,比如美国认定住所或居所的标准中,可供中国参考的因素有家人住处、工作所在地、住处的物理特征、其他住处的情况,并可以规定一般情形下的优先顺序。当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自由裁量,可能存在误用或滥用的可能,为此,要通过现有机制来防止此种误用或滥用,包括强化在判决中说理、合议庭讨论、专业法官会议和指导案例等。否则,在未来的《判决公约》下,大部分外国法院对惯常居所的认定可能不能满足我国现行的登记或期限标准,而我国大陆法院有关惯常居所的认定可能不能满足一些国家法院有关惯常居所的主观要件的要求,从而使得惯常居所这一管辖权过滤器不能发挥作用。
综上,我国目前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制度不足以对应未来的《判决公约》中的惯常居所。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传统来看,未来《民法总则》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经常居所的解释不大可能突破《民法通则意见》中关于经常居住地的解释,也就不大可能突破《民事诉讼法解释》中关于经常居住地的解释。因此,在不动摇国内民事诉讼规则的前提下,参考国际实践,另行制定我国适用于涉及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惯常居所制度,更为合适。
四、结论与建议
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判决项目外,在其他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采用惯常居所作为间接管辖权依据的尚不多见,各国的理解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公约草案》中存在的问题有:第一,自然人的惯常居所的居住期间不一致,建议把3个月作为推荐性的必要居住期限;第二,在自然人惯常居所的认定(包括丧失)中,在是否考虑主观要件和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建议以客观要件分析为主,证明标准交由各国国内法解决。
《民事诉讼法解释》中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对应着《公约草案》中的惯常居所。为更好地实施未来的《判决公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引入惯常居所制度,而不是直接适用现有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制度。未来的惯常居所制度:第一,应当能够指向中国大陆和外国(地区),即“双边”规范。第二,不应当明确规定居住期间,但可以把3个月的居住作为必要期间,6个月的居住作为充分期间,但上述期间均不应当具有强制性。第三,应当引入其他考虑因素,比如家人住处、工作所在地、住处的物理特征、其他住处的情况,并规定一般情形下的优先顺序,但是应当允许自由裁量,同时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误用或滥用自由裁量权。第四,惯常居所的取得和丧失均应当主要采用客观要件,但是应当可以从客观要件中推断出相应的主观意图;证明标准可以采用我国现行的高度优势证据标准,但如果判决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承认与执行,也可采用优势证据标准。
[1]DICEY, MORRIS, COLLINS. The conflict of laws[M]. 15th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2.
[2]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3]PARRY J T. Rethinking personal jurisdiction after Bauman and Walden[J]. Lewis & Clark L. Rev., 2015, 19(3): 613.
[4]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46.
[5]最新日本民法[M].渠涛,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9.
[6]HEINE T. Home state cross-border custody and habitual residence jurisdiction time for a temporal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family law[J]. 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1, 17: 15-68.
[7]薛童.论作为自然人生活中心的经常居所地[J].国际法研究,2015(6):118.
[8]陈成文,孙中民.二元还是一元: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4(2):31.
[9]STONE P. The concept of habitual residen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 Anglo-American Law Review, 2000, 29: 342-366.
[10]GLOVER R, MURPHY P. Murphy on evidence[M], 13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4.
[11]何其生.我国属人法重构视阈下的经常居所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13(3):89.
[12]江必新.新民诉法解释法意精要与实务指引: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8.
[13]CLIVE E. The concept of habitual residence[J]. Juridical Review, 1997, 137: 139.
[14]刘仁山.现时利益重心地是惯常居所地法原则的价值导向[J].法学研究,2013(3): 184.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郑重声明
近日发现,一些论文征稿和代发网站以本刊的名义征稿并收取高额发表费。在此本刊特别声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未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收稿件,除本刊版权页刊登的相关收稿方式外,所有投稿地址及信箱均非本刊授权。
投稿信箱:skxb@dlmu.edu.cn
编辑部电话:0411-84729280
联系地址:大连海事大学期刊社《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116026
特此声明。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17-10-13
杨育文(1981-),男,博士研究生;E-mailyangyuwencn@163.com
1671-7031(2017)06-0033-11
DF97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