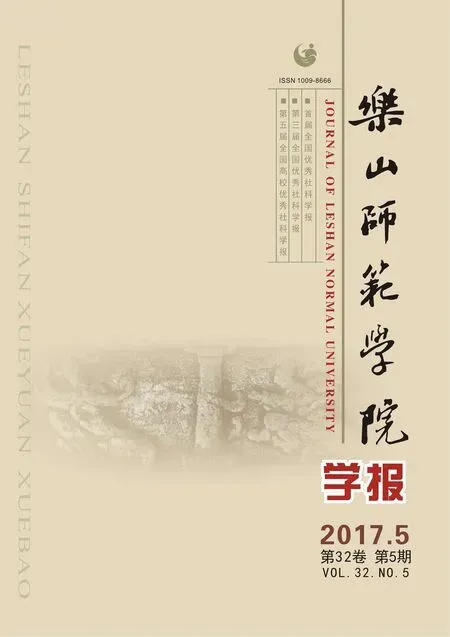论苏轼亭台楼阁记中的文体交融
——以与赋体的交融为例
2017-03-12查小飞叶帮义
查小飞, 叶帮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苏轼亭台楼阁记中的文体交融
——以与赋体的交融为例
查小飞, 叶帮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文体交融在宋代文坛上表现出普遍性。就文学大家苏轼而言,其创作不仅有“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其亭台楼阁记中亦存在与赋体交融的情况,以铺排手法的运用、文含谐隐和骚体歌诀的创作为代表,使得本以记事为主的记体文体现出赋体的特点。这对苏轼亭台楼阁记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甚至对此类记体文的革新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轼;亭台楼阁记;赋;文体交融
文体交融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体现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中。在宋代文坛上,此类现象十分突出。王水照先生曾在其著作中谈及宋代的文体交融情况:“破体为文不是个别作家一时的偶尔为之,而是大量的、普遍的现象。它睥睨尊体派的强大舆论压力,甚至违背作家本人的理论主张而勃兴。”[1]通过文体交融来实现文体创新,是宋代文学继繁盛的唐代文学之后寻求突破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宋代文坛普遍且十分重要的现象。作为宋代文学大家之一的苏轼,在破体为文方面成为宋代文人的典型代表。历来大家对苏轼作品中文体交融现象的考察多从诗词着眼,对其文集中出现的此类现象关注不多,主要在“以文为赋”、文中多议论等方面。就其文集中具体的分类而言,大家关注的多为苏文中赋的创作,而对其他大部分文体的创作情况缺乏关注。近来笔者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材料,发现苏轼的亭台楼阁记中亦存在文体交融现象。据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统计,其中亭台楼阁记共26篇。从这些记文的内容、体制结构和写作手法等方面,我们能发现其中蕴藏着文体交融的痕迹,正如杨庆存先生在《宋代散文研究》中所言:“对亭轩记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当推苏轼……吸收其他体裁的表现方式(如赋体、问答、赞颂之类)……”[2]195接下来笔者从文本出发,详细论述苏轼亭台楼阁记与赋体的交融互动情况。
苏轼一生创作了20余篇赋,其中诸多篇目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后杞菊赋》等,成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可见苏轼在赋的写作上有一定的造诣。赋与记虽被列为不同的文体,但两者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2]34记作为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与赋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清代学者孙梅在其著作《四六丛话》中谈道:“窃原记之为体,似赋而不侈。”[3]指出了记与赋有一定的相似性。随着文学的发展,记体逐渐摆脱最原始记事的功能限制,在保持本色的同时借鉴体制相近的赋体的一些写作手法,使得记文逐渐带有赋的特点。在苏轼之前,已经出现记文近赋的例子,如“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4]。苏轼亭台楼阁记亦从多方面表现出对赋体艺术的借鉴和吸收。
一、铺排
铺排本是赋体最常用的写作手法,即所谓赋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5]。细读26篇记文,发现作者多次使用铺排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对景物描写和事理阐述两方面。
(一)景物方面
作者在描写亭台楼阁及其周边景物时,好使用铺写的手法。有的表现为“以类相缀”,如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这样写道:
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鳌筍茹可以馈四方之客。
这段话句式较为整齐,连用四个“有”、四个“可以”,且连续列举了蒲苇莲芡、椅桐桧柏、奇花美草、华堂厦屋、果蔬、鱼鳌筍茹,一气呵成,关注的对象由周边各具特色的景物,到华美高大的建筑本身,再到丰富的果蔬食材,可谓穷尽了园亭里所有的景物,就连亭子本身也包含在内。在这里作者并非简单的陈列景物,还通过联想和比较来描写景物的特点,“江湖之思”写出了“蒲苇莲芡”的广袤而赋有意境感;“山林之气”凸显了“椅桐桧柏”的高大浓郁;“奇花美草”是像京都里那样的丰富而奇美;建筑是精选上好的材料建成,精美而稳固;果蔬食材之丰富,可以想见成熟之时赠给乡邻远客之美事;这些景,不仅可供观赏,是最佳的隐居之地,还能养活众人,成为生存的食粮补给;其中作者的欣羡之情不言而喻。由此可见,作者不是像汉大赋中那样简单地陈列景物以“穷形尽相”和营造气势,而是通过铺排手法来多方面揭示景物的特点,并于铺排中抒情写志。这里的铺排,没有给人冗杂之感,而是言简意赅,这与作者使用铺排是为了丰富表现内容紧密相关。
对景物的铺排描写,有的还按时空来进行铺排。如《凌虚台记》: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
在这里作者铺写了凌虚台东、南、北三方位所有的历史景观,通过选取皇家名胜的盛衰来印证“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简单的“铺列”。记文中类似的还有《超然台记》:
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相较于前面的描写,这里已不是简单的铺列,句式也不似前者整齐,铺写的方位由三方扩展到四方,同时内容也变得灵活而丰富:不仅包含景物,还思及历史人物,于简单的景物描写中蕴含了作者“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深刻感慨,意味深长,照应文眼“超然”二字。苏轼亭台楼阁记采用铺排手法,不仅体现在景物描写方面,还表现在事理方面。
(二)事理方面
在叙事说理方面,苏轼亭台楼阁记亦好采用铺排手法。如《超然台记》:
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
这是叙事上使用排比的例子。作者通过对交通工具、居住的建筑、环境三方面的例举,表达生活由好到坏的变迁,暗藏对官场浮沉的感慨。句式整齐,言意简单,有罗列的感觉,不似《喜雨亭记》中铺排手法那般灵活自然:
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前半部分铺写古人以名志喜的事例,既承接上句“亭以雨名,志喜也”,交代亭名的由来,又借此论说喜不以小大论,志喜“示不忘也”。后半部分铺写喜雨之功无处可归,遂以命其亭,照应开头,结构上安插得十分自然妥帖,全无呆板之感。这是通过铺排叙事说理的例子。此外还有专主说理的情况:
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宝绘堂记》)
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如使衣食菲恶不如吾私,宫室弊陋不如吾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虽君子安之无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坟墓而远游者,岂厌安逸而思劳苦也哉!(《藤县公堂记》)
类似这样的铺排,十分贴近赋和论的写法,作为论证内容,一为营造气势,其次力求恰当而全面,从而使论证具有说服力。这样的内容,离记体的特征已然很远。
总而言之,苏轼亭台楼阁记中采用铺排手法来体物写志和叙事说理的例文很多,有的表现为手法的简单借鉴,有的则是灵活运用,并取得丰富文章内容、言近旨远的效果,还有的全然摆脱记文的痕迹,朝着赋(指近似赋中主客问答的辩论)和论的方向发展。
二、谐隐
“《文心雕龙·谐隐》篇谓谐为谐趣,‘浅辞会俗,皆悦笑也’;隐为‘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6]110谐隐与赋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把它看作是赋的内容和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一。余恕诚先生在《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两者的关系,指出:“赋体的产生是多源的。除《诗》《骚》之外,俳谐滑稽之文、谜语笑话之类也是重要的源头。”[6]90“赋从多方面描述所赋事物的状态、本质、功能,很多话只是巧妙描摹而不直接点出,不即不离,可以看作隐语;赋中常含有微辞,托微言以讽,时或带有滑稽诙谐的成分;赋家被皇帝作为倡优看待等等,都表明赋与谐隐关系密切。”[6]111苏轼亭台楼阁记中亦多处带有谐隐的成分,篇幅或短或长,短则表现为记中偶带一两句谐语,长则通篇谐隐。
(一)篇中谐隐
苏轼在生活中本就是一位十分有趣的人,将这种性格特点带入到文章的创作中,就表现为文中谐趣的随意而生。例如《放鹤亭记》中作者就饮酒和好鹤二事,将默默无闻的山人张天骥与以南面之君为代表的为政者对比,得出地位高者为乐往往会给自己的生命和国家带来伤害,而地位低微的山人却能自得其乐、全身远害的结论,其诙谐的道理演绎,令在场的山人都为之一笑。而诙谐谈论的背后自有其隐藏的内容:“《三苏文范》卷一四崔仲凫评:他人记此亭,拘于题目,必极其所以模写隐士之好鹤有何意思,公乃于题外酒上说人好鹤,隐然为天下第一快乐,故在言外矣。”[7]221《古文眉铨》卷六十九对此亦评及:“所以如此对勘者,羡彼闲放,慨我系官,正是郡守作山人《放鹤亭记》,不是闲泛人替他作记,神味又从‘放’字来也。”[7]222这些评语都揭示了记文中作者潜在地表达了对山人隐居之乐的肯定和向往,对官场无常、拘束而不得自由的感慨之情。再如《众妙堂记》:
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蜩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
这段话读来有《庄子》中寓言故事的味道,言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能悟妙,两种普通的小动物“蜩”与“鸡”却能教人以智慧,语意之诙谐,不言而喻。此外,《盖公堂记》中叙述治病的内容同样很幽默:费尽心思寻医问药,最后却是不治而愈。作者在开篇安排如此幽默的一段,实有其行文的深意所在,他是为把文意引向对“无为”“休养生息”的论述,以隐颂盖公于国于民的大功德。这些都是篇中带有谐隐的例子,此外还有全篇都蕴含谐隐的情况。
(二)全篇谐隐
《墨君堂记》是作者为好友文与可收藏墨竹画的堂室所作的一篇记文。该记以竹为叙述中心,采用拟人的手法,称竹为“君”,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竹的敬仰之情,表现出来的严肃态度却令人喷笑。其篇末文字中的谐趣更是跃然纸上:
余虽不足以知君,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象,而藏于吾室,以为君之别馆云。
也许此处作者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但表达的方式实在有趣:作者竟将同一类的画比出“昆弟子孙族属朋友”的关系,令读者大笑的同时不得不佩服作者奇妙的联想;而文中作者仿佛又是一位拜倒在美女石榴裙下的痴情少年,爱屋及乌,想方设法来接近倾慕的对象。明人茅坤评此曰:“东坡滑稽之文,篇終却少归之于正。”[8]笔者不以为然,反觉此处是文中最为滑稽之处。这篇记文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谐趣,而《思堂记》则是既带谐趣又蕴含隐言的代表。章质夫请其为“思堂”作记,作者却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开篇即给人当头一棒,接着记文的主体内容论说的都是“无思”,且亲自现身说法,以无思之益反衬多思无益,一番论说后,作者似乎突然醒悟:“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此刻作者并不是扭转笔锋,而是继续为自我辩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最后才匆忙点题,用一反问句隐约其词:“以质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乎?”赞思堂主人思虑纯正的同时,通过质疑来批判“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表达对为名利而思行为的不屑。同《思堂记》一样,《清风阁记》也是亦谐亦隐的代表。作者在文首自言“戏为浮屠语”,即表现出游戏为文的态度,且文中反复调侃,展现戏笔的同时亦有暗讽世态的内容。苏轼亭台楼阁记中体现谐隐特点的内容还有许多,不一而足,这些内容有的表现得直露,有的表现得较为含蓄,均与赋之谐隐有着相通之处,它们使得苏轼的亭台楼阁记不仅内容丰富,还独具特色。
三、文末歌诀
除了铺排和谐隐体现苏轼亭台楼阁记借鉴赋体写法之外,部分记文结尾的歌诀也能透露出苏轼融赋入记的信息。这些歌诀与骚体赋十分相似,形式上采用兮字句,在用韵上有考虑,内容上即景抒情,意味深长。如《放鹤亭记》文末的歌诀: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斂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读罢俨然先秦楚辞和汉代骚体赋的味道。通篇采用兮字,景物描写清旷,其中塑造的翱翔于西山的“鹤”形象,“啄苍苔而履白石”,宛然楚辞中餐风饮露的高洁隐士形象。“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一句,令我们瞬间联想到淮南小山《招隐士》的最后一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而记文中的这句歌诀题为《招鹤》,由此可以猜测作者此处极有可能是模仿古人骚体赋而写就的。不独此处如此,《雪堂记》文末的歌诀亦有骚体赋的兴味: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盘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这里的歌诀同样通篇使用“兮”字,由于多次使用对偶的手法,使得形式上比前者略显整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景物描写采用铺排的手法,遣词造句选用《诗经》中的字词,不仅有景物描写,还有叙事议论的成分,这些都与骚体赋的写作手法十分相似。如果说《放鹤亭记》中的歌诀是对骚体赋的片段展示,那么这里的歌诀就可以看作是一篇完整而成熟的骚体赋。
综上所述,苏轼亭台楼阁记对赋体艺术的借鉴和吸收,主要表现为以上三方面,即铺排手法的借鉴、谐隐艺术的表现、文末歌诀仿骚体赋而作。这些内容和特点不仅使得相关文章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增强了文章表现力,还使得苏轼的亭台楼阁记别具特色,读来兴味盎然。
此外,苏轼不仅通过吸收赋体的创作艺术来写记文,同时还表现出借鉴赞颂体写记的特点,如其内容称美且对象丰富多样,体制结构的安排等都与赞颂文相近,体现出对赞颂体写法的引用。同时还有与论体文的交融,主要体现于内容、艺术手法与风格的极度相似。总而言之,苏轼亭台楼阁记中的文体交融现象是明显且多样的。细加体会,除了文体间有可供交融的条件之外,作者在创作上自觉与不自觉的行为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通过借鉴其他文体来写记体文的方法,使得苏轼亭台楼阁记区别于前人之作,表现出创新与发展的一面。具体而言,内容上不再是简单地介绍描写对象的相关情况和事件,而是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不仅包括对亭台楼阁的详细介绍(主要得力于赋体手法的借鉴),而且更多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充分展现(这主要是通过议论说理、褒贬时弊等方法实现的),据此可见苏轼已将记文由再现型转变为表现型,这是内容方面的创新;在体制手法上,则是突破陈规,广泛借鉴,由原来以叙述为主的表达方式发展为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为一体,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可读性。因此,苏轼亭台楼阁记得以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在此类记体文中独树一帜,并成为后来创作者模仿的范例,这些都与其在记文中借鉴其他文体的写作艺术来发挥自己的创作长处和革新、丰富亭台类记文的创作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就文体的发展与创新来看,苏轼亭台楼阁记以文体交融的方式进行创作,亦有其贡献所在。
[1]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70.
[2]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4-195.
[3]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18.
[4]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9.
[5]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9.
[6]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M].北京:中华书局,2012:90-111.
[7]曾枣庄.苏文汇评[G].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221-222.
[8]茅坤.唐宋八大家经典[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190.
On Stylistic Blending in Su Shi’s Narrative Prose on Pavilions——A Case Study of the Blending with Fu Style
ZHA Xiɑofei,YE Bɑnɡyi
(School of Literatur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China)
Stylistic blending showed universality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Song Dynasty.As for the literary master Su Shi,in his creation,it covers the phenomenon of breaking the stylistic boundaries to make the writing,such as“making articles into poems”and“taking poems into Ci”.For example,there is a stylistic blending with Fu in his narrative prose on pavilions.It is featured with three characteristics,namely,the skill of expatiation and parataxis,parodying words and enigmatic language,and songs in the style of Li Sao,making the narrative style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 style.This blend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Su Shi's narrative prose on pavilions and the re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rrative writings of this style.
Su Shi;Narrative Prose on Pavilions;Fu Style;Stylistic Blending
I206
A
1009-8666(2017)05-0026-06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5.004
[责任编辑、校对:方忠]
2016-09-07
查小飞(1991—),女,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叶帮义(1973—),男,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