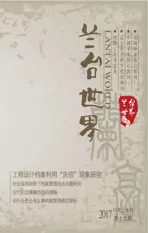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探析
2017-03-11欧阳明亮
欧阳明亮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吉安 343009)
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探析
欧阳明亮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吉安 343009)
较之传统的词学传习方式,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在教学方式、思想观念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出“词学”与“学词”的辩证统一、“词学教授”的双重身份以及新思想新文化对词体教学理念的深刻影响等诸种特点,并对现代词学研究者的培养、词坛风尚的流变以及词学学科的确立与完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国词 民国高校 词体教学 词学教授 龙榆生
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晚清民国词在词体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根源于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舞台所上演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的词人开始面对一个与前辈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创作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古典文学体裁之一,旧体词近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逐渐萎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新观念、新文化、新思想占领了文艺界的主要阵地。同时,随着传统教育模式逐步瓦解,现代教育体制开始确立,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高等院校发展壮大,词体的教学和传习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学课堂成为众多年青人接触词体、研习词体的主要场所。因此,分析民国高校中词体教学的种种特点,是我们考察民国词坛,了解民国词体的创作生态,乃至构建民国词史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词学”与“学词”的辩证统一
民国高校词体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词学”与“学词”的辩证统一。1934年,身为上海暨南大学词学教授的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文章正式区分了“学词”与“词学”的不同[1]87。显然,龙榆生清楚地意识到传统词学中存在着词学研究和词体创作纠葛不清的问题,而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词学研究的客观性,也会对词体创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后,龙榆生又发表《今日学词应到之途径》一文,再次对“学词”和“词学”的不同加以强调:
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销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个性充分表现于繁弦促柱间,藉以引起读者之同情,而无背于诗人“兴”、“观”、“群”、“怨”之旨,中贵有我,而义在感人[1]104。
在龙榆生看来,“词学”的根本在于客观、求真的态度,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审美倾向参杂其中,“学词”则重在个性,贵在有我,而个性是主观的、多元的,往往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词学”、“学词”二者的关系,会导致词学研究丧失客观性,无法真正辨明研究对象的得失利弊,或者将研究对象的某一特征普遍化,将偶然误为必然,从而也就无法廓清词史上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词学”与“学词”的纠葛不清,也会对词体创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它往往导致词人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视为词体创作的唯一标准或最高典范,因此亦步亦趋,东施效颦,走向偏执和极端,就像晚清民国词坛“梦窗热”的兴起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因此在龙榆生看来,对前代词人、词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为当下的词体创作提供丰厚的养料,而当下的词体创作也可以推动词学研究的发展,但二者自有藩篱,不能混为一体。
这种“词学”和“学词”辩证统一的观点在民国高校的词体教学中得到普遍的体现。在民国高校的词体教学活动中,“词学”与“学词”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但同时又表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
作为现代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高校词体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专业知识和进行学术训练,而并非以培养词人为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词学”是其主体部分,有关词史发展、词学理论、词体文献的整理等课程的讲授,成为民国高校词体教学的主要内容,如各大学纷纷开设“中国词史”、“词学通论”、“专家词研究”、“宋词整理法”、“诗余研究”、“唐宋词”等课程,分门别类地讲授词学学科的专业知识、梳理词体发展演变过程和具体分期,分析历代词人和词作的得失利弊。
同时,在“词学”为主的前提下,民国高校的词体教学并没有忽视“学词”的问题。对词体创作的教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设置,即开设相关课程,如1934年上海暨南大学就同时开设了“词史”、“唐宋词选”、“诗词习作”三门课程[2]2-6。从分工来看,“词史”属予“词学”范畴,而“诗词习作”显然属予“学词”的范畴。同时,在民国各高校所开设的各类“词学”课程中,也部分包含了对词体创作的教学,如李冰若在上海暨南大学所开设的“唐宋词”课程,虽然主要是讲授“词的起源,词的流变,唐五代词论,宋词论,唐宋词集提要”等词学知识,但也包含“词的界说及其作法”[3]92。不过,与专业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同,文学创作的教学必须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因此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并非仅限于课堂,而更主要的是以师生雅集结社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吴梅任教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期间,除了讲授“词选”与“词学通论”等专业课程外,还在教学之余与学生唐圭璋、卢冀野、王季思、赵万里等创立潜社,相互唱和,并编成《潜社词刊十集续刊六集》。同样,在上海暨南大学,龙榆生也指导学生成立莲韬词社,以切磋技艺,提高作词之法。
民国高校词体教学中“词学”和“学词”的辩证统一,显示出现代学术背景下词学学科的成熟与完善。同时,也正因为民国高校词体教学在以传授词学理论知识为主的同时,又注重词体创作的训练,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往往既具备专业的学术理论,又拥有相当的词体创作能力,从而对民国整体的词学研究和词体创作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兼具学者和词人双重身份的“词学教授”
民国高校词体教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词学”和“学词”的辩证统一,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存在一批精通词体创作的“词学教授”,他们既是知名学者,又是著名词人,既能从事词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又能倚声填词,以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学生讲授作词之法。同时,这批“词学教授”又和传统社会中集学者与词人二者于一身的传统文士不同,他们依身于现代教育体制下的高等院校,以教学为职业,开设课程、编纂讲义、登台授课,成为民国词学史上一道重要景观。如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号曾发布《词坛消息》,专门介绍了当时全国南北各大学的词学教授:
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据记者所知,南京中央大学为吴瞿安、汪旭初、王简庵三先生,广州中山大学为陈述叔先生,湖北武汉大学为刘洪度先生,北平北京大学为赵飞云先生,杭州浙江大学为储院峰先生,之江大学为夏臞禅先生,开封河南大学为邵次公、蔡嵩云、卢翼野三先生,四川重庆大学为周癸叔先生,上海暨南大学为龙榆生、易大厂两先生[4]220。
实际上,民国各大高校中知名的“词学教授”远不止此,像以研究梦窗词蜚声词坛的杨铁夫,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当代著名词学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集学者、报人、词家三者于一身的陈匪石,以及与丈夫合撰《中国诗史》的冯沅君等,都是民国高校中声望极著的词学教授。
这些“词学教授”一生之中往往并非只执教于一所高校,而是随着事业发展、人事变动或者时局影响,不断在全国各地高校之间流动,而各地高校为了学科发展,增强实力,也争相聘请他们担任教职。如周岸登最初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1年应安徽大学文学院聘讲授词曲,1932年受聘重庆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35年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川大,遂执教川大。王易于1922年任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23年被聘为江西心远大学教授,1927年被中央大学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1940年受聘国立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又如卢前先后受聘金陵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杨铁夫最初任无锡国专词学教授,晚年居香港,任香江广州大学教授、国民大学教授等。
与以往传统词人文士私人传授、拜师学词不同,民国高校中的词学教授面对的是以院系班级为组织、有明确学习目的的专业学生,因此他们的词体教学较之前人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授课讲义的编纂上。这些授课讲义与传统词人学者所撰写的词话、评点类的词学著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了系统地讲授词体知识,让学生对词体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有全面的了解,这批词学教授所编纂的讲义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分期、分类、分知识点等方法,来梳理词史的发展过程和其中诸多细节。如任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刘毓盘所编的《词史》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对词体发展演变进行整体梳理的论著,全书共九万余字,综述了千余年间词体的起源、兴盛、低落以及复兴的过程。吴梅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编纂的讲义《词学通论》将“论”“史”分开,前五章讲授词学理论,包括平仄、音韵、韵律和作法,后面四章则是词史的梳理和重要词人的讲解。王易在江西心远大学所编讲义《词曲史》分为“明义”“渊源 ”“ 具 体 ”“ 衍 流 ”“ 析 派 ”“ 构 律 ”“ 启 变 ”“ 入 病 ”“ 振 衰 ”“测运”等十个部分,分条析理地剖析词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曲体的关系,几乎囊括了词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正如周岸登的评价:“能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判断,俾学者读此一编,靡不宣究,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5]4总之,这批以课堂教学为目的而撰写的词学讲义,不但是民国高校词体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往往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经典词学论著。
此外,由于民国高校中的大多数“词学教授”不但具有学术理论知识,同时也是深谙作词之道的著名词人,因此他们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也注重词体创作方法的传授,如陈洵晚年在中山大学,“与诸生讲论词学,专注清真、梦窗,分析不厌求详。金针暗度,其聪颖特殊子弟,能领悟而以填词自见者,颇不乏人”[6]85。又如中央大学学生尉素秋对吴梅讲授作词之法的回忆:“我开始学填词,是在民国二十年的秋天。那时我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吴梅先生担任词学通论的课程。瞿安师教我们填词,总选些难题、险韵、僻调,把我们逼得叫苦连天,越往后反而渐觉容易了。瞿安师解释先难后易的道理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倘作词只会浣溪沙,作诗只会五言七言绝句,那是没有用处的。’”[7]108可见这些兼具学者和词人双重身份的词学教授在为学术界培养词学研究者的同时,也为民国词坛培养新一代的词人。
三、新思想、新文化对词体教学理念的深刻影响
民国高校词体教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新思想、新文化全面渗入到词体教学活动中。现代教育体制下的民国高校不但是传授知识、探讨学术的教研机构,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阵地。这些新思想、新观点自然不可避免地对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种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词体本身的认识和定位上。自晚清鸦片战争开始,随着中国传统社会逐步走向近代,作为古典文学主要体裁之一的旧体词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逐渐萎缩,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文学占领了文艺界的主要阵地,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因此在民国高校的词体教学中,如何以现代的理念来解释、分析词体的发展过程,评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成为当务之急。
1927年,胡适编选的《词选》问世,这本是为民国中等学校学生提供的一部国语读本,但它不仅在中学课堂迅速传播开来,而且在整个词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龙榆生在《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中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1]304这里虽然谈及的是《词选》在中等学校所受欢迎的程度,但它对高等院校词体教学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因为当时中等学校的师生有相当一部分在后来进入高校,或执掌教席,或研修词学,如龙榆生本人就在1928年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为教授。胡适的《词选》之所以会在民国各级学校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适的《词选》是第一部从“文学进化论”角度来编纂的词选。
总之,相较于传统的词学研究和词体传习方式,民国高校中的词体教学在教学方式、思想观念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以及旧体文学的现实境遇紧密关联,同时民国高校词体教学所表现出的“词学”与“学词”的辩证统一、“词学教授”的双重身份以及新思想新文化对词体教学理念的深刻影响等诸种特点,也对现代词学研究者的培养、词坛风尚的流变以及词学学科的确立与完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词学研究格局与词体创作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国立暨南大学.各院系各学程考试时间表[J].暨南校刊,1934,120.
[3]国立暨南大学.国立暨南大学一览[M].1936.
[4]龙榆生.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近讯[J].词学季刊,1933,1(1).
[5]王易.词曲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6]龙榆生.陈海绡先生之词学[J].同声月刊,1942,2(6).
[7]尉素秋.秋生集[M].台北:帕米尔书店,1984.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的创作生态与传习方式研究”(12YJC751060)。
欧阳明亮,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词学。
I207.23
A
2017-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