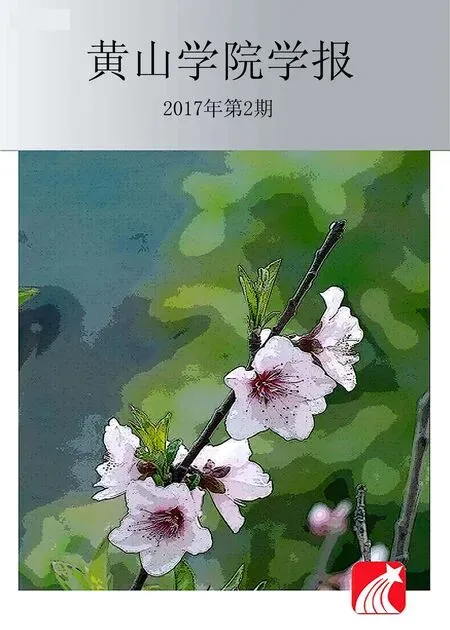《井》中海斯特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分析
2017-03-09张婷婷
张婷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井》中海斯特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分析
张婷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解读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小说《井》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通过分析海斯特的本我、自我以及由于人格内部冲突所引起的自我焦虑和相应的防御机制来了解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及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理解海斯特这一人物形象。
海斯特;本我;自我;焦虑;防御
一、引 言
伊丽莎白·乔利是澳大利亚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蕴含了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风格。乔利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类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描述了边缘人的不幸和悲伤,[1]138表现了她对边缘人物的关注与同情,对人性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反思和谅解。小说《井》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便是这样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物。跛足的老姑娘海斯特·哈伯是富有的农场主的女儿,她从修道院收养了一个年轻的孤儿凯瑟琳,之后两人便搬到了农场偏僻的一角,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天晚上她们从派对回家,凯瑟琳开车意外撞死了一个男人。两人将尸体拖进院子里的一口枯井中,于是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家中厨房里的现金不见了。凯瑟琳认为井里的男人还活着,是他偷走了厨房里的现金。她还经常在井旁和他对话,幻想他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还想和他结婚。为了不让凯瑟琳胡思乱想,也不让自己焦虑不安,最终海斯特命人将那口枯井给彻底封了起来。
学者分别从作品的主题、作者的生平、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叙事手法、象征手法等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研究,然而却鲜有人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研究该作品。试图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海斯特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分析她的本我、自我及其内在的自我焦虑和相应的防御措施,来更好地理解小说的边缘化主题。
二、海斯特的本我和自我
家庭教师希尔德·赫兹菲尔德第一次见到海斯特时说这个小女孩的双眼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小海斯特听到别人这样的赞美感到很害羞但却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夸赞她的外貌,这也激发了她内心对美的渴望。海斯特还每天用冷水冲洗脖颈,这样等到心仪的男子愿意用项链、项坠和珠宝打扮她时,脖颈还能保持优雅美观。可见,最初小海斯特心里对异性的爱仍然是充满期待和渴望的,这种爱的本能便象征着海斯特的本我。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海斯特意识到自己的残疾以及丑陋的外表,她偷偷地将自己幼时的照片收藏起来。她知道由于自己丑陋的外表,没有男人会爱上她并和她结婚。因此,在对异性的爱感到无望后,她只能在同性之间寻找爱的慰藉,而家庭教师希尔德满足了海斯特的情感欲望,她给海斯特带来了关爱与温暖。希尔德对海斯特的关爱让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父亲的介入,希尔德最终离开了自己。一天晚上,海斯特看到满身鲜血的希尔德痛苦地躺在洗手间的地上,并向她求助。海斯特不但没有找人帮忙,反而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爬上了床,用毯子包住了自己的头。海斯特很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她决不能告诉父亲自己看出了什么。虽然她的内心很愤怒,但却不敢对父亲作出任何的反抗。因此,她只能无条件屈从。希尔德的离去使海斯特的生活回到了原点,她感到很孤独,因为没有可以倾诉、交流的对象,她也变得性格孤僻,除了钱不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她压制了内心对情感的欲望,直到孤儿凯瑟琳的出现,让海斯特原本压抑的情感得到了释放。凯瑟琳天真烂漫、活泼乖巧,充满了幻想。她的到来给海斯特带来了快乐与温暖,海斯特也不再感到孤独。为了能和凯瑟琳独处,她甚至离开了自己居住多年的大房子,搬到了农场偏僻的一角,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凯瑟琳突如其来的吻让海斯特不知所措,并且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海斯特尤其喜欢观赏卡瑟琳的舞姿,凯瑟琳充满活力的动作和她嫩黄色裙子上的绉纱会让海斯特呻吟。因为“那舞蹈对她来说是唯一一种用身体表达肉体之爱的方式”。[2]114因此,在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凯瑟琳的同时,海斯特又对她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感。两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激发了海斯特内心的本能,可是这种本能冲动无法被社会认可,她只能将这份私人的情感掩藏在心中,不让别人发现。
在超我(即父权制和正常的情感道德)的压制下,海斯特的本我(即其内心的情欲)总是不断被压抑,难以得到真正释放。在无声的屈从中,海斯特的自我开始变得软弱。她无法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进行平衡,也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家庭教师希尔德离开了海斯特,这给海斯特留下了心理创伤。从那以后,她开始变得冷漠、孤僻起来。而她的父亲和祖母更不会去关心海斯特的内心想法。不仅如此,朴素的穿着加上理智而冷静的处事态度都可以看出海斯特愈加男性化的一面。直到遇到凯瑟琳,“海斯特的女性意识开始活跃起来”。[3]45两人迷上了购物、烹调美食、缝制衣服等女性所喜爱的活动。两人的交往激发了海斯特内心的本能,她对凯瑟琳的欲望也逐渐变得强烈。海斯特沉浸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但她却无法辨清这种介于母爱与性爱之间的情感,无法分清自己的角色,也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三、海斯特的焦虑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通过自我的调节,人格内部各力量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会达到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永久的,人格内部总会产生一些冲突,使得自我的机能失调,从而产生焦虑。
在小说中,海斯特的童年故事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尤其是她与家庭教师希尔德的幸福经历。而海斯特一想到凯瑟琳要离开自己,与希尔德的过往画面便会闪现。希尔德的离去让海斯特深受打击,海斯特因此对一切都变得很冷漠。每当回想起希尔德在洗手间的那一幕,海斯特便会头痛,会有一种羞耻感和负罪感。而对于海斯特来说,凯瑟琳就像当时的自己,因此她想在凯瑟琳身上延续她与希尔德的关系。她害怕凯瑟琳终有一天会像希尔德那样离开自己,所以每当想到凯瑟琳离开自己时,她就会想到希尔德,然后开始头痛,感到焦虑不安。这说明海斯特在潜意识里感到很无助,也很恐惧,她怕留不住凯瑟琳。正因为如此,海斯特在和凯瑟琳相处的过程中,一直都想独自占有凯瑟琳,不让她和其他人接触。为此,她们搬到了农场偏僻的一角,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把凯瑟琳当成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来对待,连给她穿的衣服都很幼稚。她不愿别人分享凯瑟琳的美貌,更不愿让别的男人接触她。不仅如此,凯瑟琳的好友乔安娜的来信会让海斯特胡思乱想。乔安娜的存在及到来对她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可是她只能掩藏心中的焦虑并且顺从凯瑟琳的意愿。另外,井中的死男人也是一个威胁,凯瑟琳总是幻想井中的男人是她的白马王子,想嫁给他。海斯特无法忍受凯瑟琳和其他男人结婚、生孩子,不想让天真烂漫而又纯洁的凯瑟琳被玷污,不想让她走希尔德走过的路。这一系列的威胁都会让海斯特感到头痛,因而产生焦虑。
四、海斯特的防御
人们在焦虑时,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为了试着消除这些焦虑,自我会采取一些动力机制来促进人格的发展,例如求同机制、升华机制、防御机制等。在小说中,为了不让凯瑟琳像希尔德那样离开自己,海瑟特首先采取对象丧失型求同机制来消除焦虑。对象丧失型机制是指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象或不得不放弃,他就会在自我心中建立对象,把该对象的特点吸收到自身中来,以补偿他的损失。[4]61在海斯特的眼里,希尔德像慈母一样悉心照料自己。她陪伴海斯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陪她一起成长,给予她关爱,这让海斯特感到幸福。可是那天晚上发生在洗手间的一幕让海斯特懊悔不已。由于对父权的畏惧,她没有帮助希尔德。家庭教师离开后,海斯特带着负罪感、失落感及伤痛继续生活下去。从那以后,海斯特便封锁了自己的心。凯瑟琳的出现重新点燃了海斯特内心的情感,她希望将凯瑟琳留在自己身边,来代替离去的希尔德。在与凯瑟琳的相处中,海斯特会经常回想起与希尔德在一起的种种经历,她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和希尔德作比较,还会模仿她的表达方式。她像当时的希尔德一样,细心地照顾凯瑟琳。尽管自己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参加聚会,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场合,但为了凯瑟琳,她都愿意去做。她想带凯瑟琳去旅行,因为希尔德曾带自己去旅行,并给海斯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和凯瑟琳生活的过程中,曾和希尔德相处的快乐时光总会时不时闪现在脑海中。当希尔德离去后,海斯特自我中的母亲形象便彻底丧失。海斯特不得不在自己的自我中建立母亲形象来延续她和凯瑟琳的关系。只有这样,海斯特心中的愧疚感、失落感才能消失;只有这样,她才能过曾经的那种幸福生活,不再感到孤单;只有这样她才能将凯瑟琳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除此之外,海斯特还试图通过压抑来摆脱焦虑。压抑是“自我形成后才出现的,是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别形成后才产生的”。弗洛伊德将压抑分为原始压抑、真正的压抑两个阶段。[4]63原始压抑指的是“自我拒绝本能的某些要求进入意识。本我代表的本能总是力图发泄或者满足,而自我则是由于意识到某些本能要求的实现会带来道德的谴责或招致外部现实的威胁,所以自我便尽可能地压制这些本能要求,使之不进入意识而永存于无意识之中。”[4]64在小说中,小海斯特的父亲和祖母没有给与她足够的关怀,唯一疼爱自己的家庭教师希尔德也最终离开了自己。而长大后,由于丑陋的外表,海斯特知道没有人会爱上自己并和自己结婚,所以便转向同性之间寻求爱的慰藉。凯瑟琳的到来给她带来了希望。一方面,海斯特像母亲那样悉心照顾凯瑟琳;另一方面,她又对凯瑟琳产生了一种情欲,尤其是看到凯瑟琳的舞蹈时。海斯特只想独自占有凯瑟琳,但却并不想界定两人之间的关系。可是由于传统情感道德的束缚,海斯特只能将这种爱欲压抑在心中,阻止这种爱的本能进入自己的意识。海斯特压抑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违背传统道德而带来的社会的谴责和自我的焦虑。
真正的压抑是指“在本能发泄要求被原始压抑从意识中排除之后,这些本能发泄要求可能以种种乔装或间接的衍生方式,与意识中的内容发生联系而建立起新的压抑,这即是严格意义上的压抑或压抑本身”。[4]64它 “可以使人对那些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情景视而不见,或者歪曲人的所见所闻,或者篡改其感官传达的信息,从而使自我不能意识到可能导致焦虑的危险事物或与危险相关的事物”。[5]171在小说中,海斯特内心认为凯瑟琳的朋友乔安娜是个垃圾伴侣,她甚至希望这肮脏的、满是病菌的丫头应被远远地隔离在她们鲜活纯净的生活之外。海斯特十分不满她们频繁通信,每当乔安娜来信时,海斯特都迫切地想知道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都是为了保护那女孩,怕她受到伤害。不仅如此,对于凯瑟琳不断幻想乔安娜的到来,幻想两人在一起玩耍,甚至以后可以结婚,海斯特虽然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害怕自己会被孤立、被遗忘,但她还不断为凯瑟琳辩解,认为她有那样的念头是正常的。她还假装欢迎乔安娜的到来,积极要求为她订制往返车票。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因失去凯瑟琳的爱而产生焦虑的一种真正压抑。另外,凯瑟琳坚信井中的男人还活着,并经常在井边和他聊天,她还说厨房里的钱就是被他拿走的。对此,海斯特也半信半疑,她不清楚井中的男人是否活着,但她还是试图说服凯瑟琳相信他已经死了,并让凯瑟琳爬到井底将钱取出来。最终,为了终止凯瑟琳的幻想,消除自己的恐惧,海斯特命人将井永远地封上了。因此,通过对这些外在威胁的否认及歪曲,海斯特试着消除自己的焦虑。
五、结 语
伊丽莎白·乔利常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类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而《井》中的海斯特便是这样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在小说中,由于父权制和正常的情感道德的压制,海斯特内心的爱欲受到了压抑,难以得到真正释放。在本我和超我的对立下,海斯特的自我开始变得软弱。她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因而经常头痛,产生焦虑。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海斯特采取了对象丧失型求同机制,即通过建立希尔德这样一个母亲形象来代替离去的希尔德,延续和凯瑟琳的关系。除此之外,海斯特还试图通过压抑来摆脱焦虑。一方面,为了避免因违背传统道德而带来的社会谴责和自我焦虑,海斯特将自己对凯瑟琳的情欲进行了压抑,阻止这种爱的本能进入自己的意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因失去凯瑟琳的爱而产生焦虑,海斯特对一些外在威胁进行了否认和歪曲,从而艰难地消除内心的种种焦虑。正是通过这些防御机制的建立,海斯特的焦虑得以慢慢消除,其人格也得到了发展。
[1]梁中贤.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边缘意识[J].当代外国文学,2009(4).
[2]伊丽莎白·乔利.井[M].邹囡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3]詹春娟.从边缘化人物看女性的失语:小说《井》的女性主义解读[J].西华大学学报,2008(1).
[4]吴光远,徐万里.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5]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吴 夜
An Analysis of Hester in The Well Based on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
Zhang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The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female protagonist Hester in Elizabeth Jolley’s novel The Well through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It analyzes Hester’s id,ego and anxiety caused by internal confli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fense mechanism so thather complicated inner activiti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will be understood easily,helpingusgain 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female protagonist.
Hester;id;ego;anxiety;defense
I106.4
A
1672-447X(2017)02-0073-004
2016-12-10
张婷婷(1992—),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