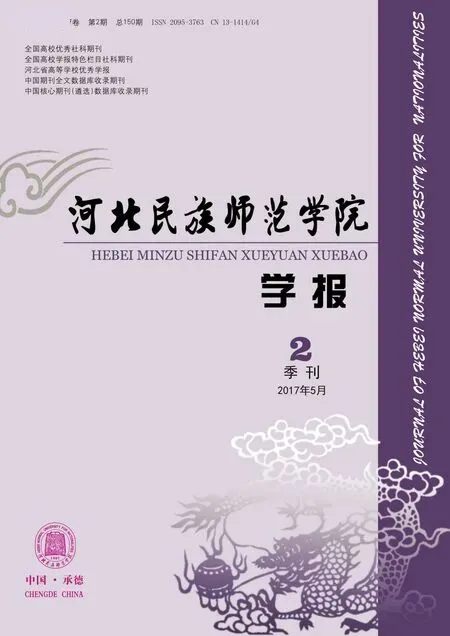从清代热河天主教的传播看十八世纪欧洲对承德的认识
2017-03-08孙亚君柳晓玲
孙亚君 汤 斌 柳晓玲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河北 承德 067000)
从清代热河天主教的传播看十八世纪欧洲对承德的认识
孙亚君 汤 斌 柳晓玲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河北 承德 067000)
热河作为清朝重要的塞外重镇,地接蒙古与东北,是塞外通往内地的重要孔道。早期清政府在热河地区实施严格的封禁政策,目的就是要隔绝内地与蒙古、东北的各种联系。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在热河的传播更是被严禁。然而,在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下,西洋传教士仍利用各种渠道在热河地区向士兵和平民传播天主教。直至鸦片战争,热河逐渐发展为天主教教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很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承德的认识。
天主教;热河;遣使会;圣母圣心会;欧洲
18世纪,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已席卷整个欧洲,工业化的需求促使西方列强以掠夺资源为前提,将非洲、美洲,以及包括亚洲东南亚各国置于殖民统治之下。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依旧是东方大国,历史悠久,余威尚存,西方殖民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诉诸武力将中国沦为像印度、东南亚诸国一样的殖民地。在西方殖民者的眼里,只要能进入中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任何手段都可以尝试。遣派传教士入华,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首选策略。此时的中国,与欧洲之间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偶然的、纯商业的接触,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有了广泛、深入的联系。
一、传教士东来
第一位尝试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然而,明朝的禁海令使他只能在距中国广州仅有30里的上川岛上望洋兴叹。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沙勿略在岛上去世[1]24,未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教的心愿。1582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 atteo)来到澳门。1601年,利玛窦以给皇帝进贡为名,进入北京,并最终留居下来。在华近30年的传教生涯中,利玛窦逐渐摸索出一套所谓“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使大批的有地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皈依了天主教。
所谓“适应”,如方豪所定义:“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方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么它必须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2]203然而仅有“适应”策略是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自古以来,华夏文化一直是周边游牧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学习的对象,对亚洲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华夏文化”大一统思想的支配下,中国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是轻视和鄙夷的。西方传教士仅以景慕“天朝声教文物”[1]18的姿态来到中国,是不会得到统治者与官僚士大夫们的尊敬,只会被作为“外化之人”和“蛮夷”来对待。利玛窦以及后来的传教士都深知此理,因此来华的传教士除具备了高超的学识外,还携带了大量如望远镜、地球仪、自鸣钟以及天文仪器等代表西方先进科技的产品。这些“西洋奇器”进入宫廷,获得了中国皇帝的喜爱。明清朝廷中的西洋传教士,就是通过这些“微末西技 ”敲开了中国宫廷的大门。
清代,在康熙帝严格禁止天主教之前,中国沿海内地都有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出现过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短暂热潮。热河因地近清王朝“龙兴圣地”盛京,又是内地通往内扎萨克蒙古部落的门户之一,因此一直被清王朝视作汉人和外国人的禁地。然而,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在京任职的天主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有机会陪伴皇帝巡幸塞外,来到热河等地秘密传教。这些传教士类属不同修会,但其传教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尽量的在鞑靼地区皈依更多的教徒。
进入热河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主要有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字克安,1665年9月1日出生于贝藏松主教区之大鲁赛镇,1698年至华,1741年9月29日在北京去世。[3]509巴多明精通物理学、文学、地理、几何、军事,汉语满语流利,深受“帝之宠眷”,常扈从康熙帝出塞巡幸,“其足迹所至之地,或发达旧有教务,或开辟新区,而其中最发达者,要为京师以北长城以外各地,与京师附近诸山,则不能不归功于多明传布之功。1710年居热河3个月,曾聚集各省来此从商之教民接受告解。”[3]5161710年,巴多明扈从出塞,在热河逗留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各省于此处经商的基督教徒集中起来接受告解,并在热河发展了16名信徒。[4]049在此之前,巴多明已经在热河地区设立四个传教所。罗德先(Bernard Rhodes)[4]556作为巴多明的助手也常随同前往热河,由于善于医术,在传教的同时也常为穷苦人和热河驻防官兵诊治疾病。阳秉义(Francois Thilisch)[3]634也在1711年至1716年在扈从皇帝北巡期间,也在热河地区开展传教工作。
乾隆末年,盛世之下所掩藏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很多地方以宗教为旗号进行反清武装活动,如山东清水教,甘肃白莲教、回教,台湾天地会等。而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直隶等地,清朝地方官相继拿获了许多西洋传教士,这使得乾隆大为震惊,将天主教与这些民间秘密宗教联系起来。恰巧广州又发生了英国商船水手打死中国民船水手的事件,这使乾隆帝对西洋人提高了警惕,开始怀疑西洋人来华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并实施了更加严厉的禁令,最终导致乾隆四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一年波及全国的最大一次禁教活动。
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禁教政策的日趋严厉,传教士进入热河地区也日益困难。这一段时期,热河地区的传教任务多是由中国籍神父担任。如中国籍神父刘保禄[3]906,其主持传教区域包括了热河、赤峰等地。值得注意的是,扈从皇帝出塞的欧洲传教士传教的对象包括了不仅有当地的平民,还有驻防官兵。而中国籍神父主要传教对象则是下层贫苦百姓。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热河地区天主教的传播是零星的,没有形成规模,皈依人群以驻防官兵和汉族移民为主。
二、遣使会、圣母圣婴会与热河教区
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将在京的多位传教士遣送回国。这些传教士多属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遣使会、传信部等修会。其后,接二连三的教难发生,传教士在北京居住传教的堂口也纷纷被迫关闭,罗马教廷在北京的天主教事业陷入停顿。来华的传教士只能通过广州,秘密潜入中国内地对平民进行传教,其中包括了遣使会士。
道光九年(1829年),为避免教难,中国籍神父薛玛窦等传教士将位于北京的传教中心迁至张家口的西湾子村。西湾子在康熙三十九年传入天主教,此后开始兴建教堂。禁教时期,地处偏远的西湾子成为教徒的避难地,天主教事业一直在暗地里发展。1835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来到西湾子,开始主持教务,其主要工作是向塞外以及蒙古地区的贫苦下层人士传播天主教义,很多外国传教士常年潜入塞外地区传教,其中包括了热河等地。
在孟振生等人的努力下,遣使会在西湾子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皈依的信徒仅在蒙古地区就约有两千人,并创立了西湾子女校。1838年,罗马教宗划出了新的教区,即将满洲里、辽东、蒙古合并为一个教区,同时指派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5]271840年,罗马教宗又下达谕令,将蒙古地区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教区。蒙古教区的边界是:南以长城为界,东以关东三省为界,仍由遣使会孟振生为新教区代牧,教区分为三大教堂:东为苦柳吐教堂,在热河赤峰境内;中为西湾子教堂,西为小东沟教堂,西湾子教堂为蒙古教区(包括热河地区)的总堂。[5]3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居留权。1844年,传教士在滦平老虎沟购买土地、房舍,修建了一个小教堂,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修建正式教堂,这是承德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又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除规定法国在中国取得英美两国在条约中规定的侵略权益外,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1846年2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清政府被迫宣布解除年雍正二年(1724年)公布的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禁令。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中国全面开放,容许洋人在中国各地游历,传教士自由传教,清政府保护传教士及中国信徒。这样,大批的罗马天主教修会以及基督教差会纷至沓来。
1861年,孟振生宣布:“因为皇帝(咸丰帝)颁行了谕令,给予人们奉教的自由,而且在北京教区有很多人进教,因此遣使会总会长便请求宗座将蒙古教区转让给其他的传教士。罗马传信部于是将蒙古教区转让给刚成立于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5]42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蒙古教区一直由圣母圣心会掌管。
1862年,比利时圣婴会主任司铎南怀义(Theophil Verbist)与几位神父筹划成立一个面向中国修会,专为中国传教的团体,取名为“圣母圣心会”(Con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从1865年到1948年之间,总共有679位圣母圣心会会士前往中国传教,其中绝大部分为比利时籍。
1865年12月,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义神父、司维业神父(Alois Van Segvelt)、韩默理神父(Ferdinand Hamer)、良明化神父(Frans Vranckx)四人来到西湾子接替了遣使会在蒙古的教务。第二年年初,韩默理和另一名神父林道远前往热河地区传教。而圣母圣心教会会祖南怀义也于1868年前往热河滦平的大老虎沟传教,不久在此病逝。良明化接替了南怀仁的工作,成为该修会的会长。1871年,圣母圣心会总院院长巴耆贤神父(Jaak Bax)被任命为蒙古教区副主教(在1874年以前,圣母圣心会在蒙古教区不设主教)。
1883年,巴耆贤向宗座提出建议,将蒙古教区分为三部分,一个是中蒙古教区,以西湾子为中心的教区;一个是以河套为中心的西南蒙古教区;最后一个则是以松树嘴为中心,包括全热河及奉天一部分地区在内的东蒙古教区。获准同意后,吕之仙神父(Mgr Theodoor Rutjes)成为东蒙古教区的代牧。
热河地近西湾子,长期以来一直受西湾子天主教的影响,因此滦平大老虎沟的天主教堂口一直得以保留,奉教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圣母圣心会为纪念在这里去世的南怀义会祖,便在此重新修建了一座教堂,当时成为热河地区天主教的中心。除教堂外,历任的神父们还在此建立了一个孤儿院和救济穷人的善会。到1883年,易维世神父(Adolf Jozef Bruylant)为本堂神父时,这个地区天主教皈依行动规模更加庞大,慕道人数也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三道营子、八沟、三十家子等地。1889年,吕之仙主教在探视老虎沟地区时,决定在玻禋沟与八沟建座小教堂,在三十家设所小学与公堂。
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模式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教友村,村子的中心就是教堂,在比较大的传教据点常设有孤儿院或简单的诊所。这种传教方式使得大量的信徒多是来自于关内的汉族移民,而蒙古人较少。
二十世纪初,热河省成立,承德成为热河省省会。1924年,罗马教廷将东蒙古教区改为热河教区,在承德市建立教堂,成为大阁、凤山、老虎沟、兴隆、宽城、平泉等天主教堂的中心。承德市天主教堂首任主教是比利时籍神父闵宣化(Muilie Jozef)。闵宣化,1886年出生,1909年被圣心圣母会初次派遣到东蒙古传教,热河教区成立后,被派往承德教堂任主教,因他胡子长的像一把大刷子,因此当地人都叫他闵大刷子。教堂成立之始,由于时任热河都统的汤玉麟也信奉天主教,因此闵宣化等传教士在这里的传教工作进行的颇为顺利。闵宣化传教的宗旨是“博爱忠诚”,在承德市传教期间曾成立“华洋义赈会承德老弱灾民收养所”一处,在承德市先后发展信徒15户30多人。[6]5401931年闵宣化离开承德返回比利时。另两位比利时籍神父——大司铎郭明道(Conar Oscar)、郝建德(Vandekerckhoye Kamiel)也曾担任过承德市教堂总管。
三、十八世纪欧洲对承德的认识
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除了传播福音外,他们还陆续写了许多的书信, 把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们传教的情况汇报回欧洲。除了书信往来,不少传教士还撰写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如在中国传教22年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撰写了著名的《中华帝国》,随后在马德里和里斯本出版。此书曾引起欧洲学者的极大关注;明末清初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用拉丁文撰写了4部有关中国的书:《中国文法》《鞑靼战记》《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中国新地图集》,其中《鞑靼战记》记录了明末清初的战争,详细介绍了有关清代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一股“中国热”,与传教士的书信、书籍的刊印有着密切的关系。
承德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康熙、乾隆二帝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在北京任职的传教士经常跟随康熙、乾隆帝前往热河巡幸,亲身历经了在这里发生的清代重要历史事件,并通过他们的书信和书籍,将这些信息反馈给欧洲。这些文字,让欧洲人通过承德这扇窗口,继而深入的了解清代政治、文化、军事、宗教、园林等方面的状况。
康熙年间法国籍耶稣会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3]451和传教士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Ripa Matheo)[7]1,曾多次陪伴康熙皇帝去塞外狩猎,记录了木兰行围的宏大场面。马国贤作为御用画家,还经常陪同康熙帝前往热河行宫,他在书中记录了热河地形,以及避暑山庄的景色和康熙帝在山庄的休闲生活。《清廷十三年》对西方人了解承德,了解中国皇帝个人生活,极具价值。这本书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的“奠基”之作。马国贤在热河行宫期间,还制作了铜版画《热河行宫三十六景》。这是马国贤利用传统中国雕刻工艺,融合了西方绘画中光影明暗的技法,成功的印刷出图画。这套雕版图画还被马国贤带回了意大利,陈设在他开设的专门培养中国传教士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里。西方人第一次从这幅铜版画里,对避暑山庄有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
传教士将承德称为“中国的枫丹白露宫”,清朝皇帝的夏宫。避暑山庄的建立,以及热河在清代政治中的重要性,都是通过传教士的书信传回了欧洲,使欧洲人对承德和避暑山庄有了近一步的了解。如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获准在避暑山庄游玩时,就曾感慨道:“热河一处,本系荒僻之乡,今乃美如锦绣、灿若春花,令吾辈得徜徉其间,饱享清福,实不得不拜谢康熙大帝之赐,而大帝开创热河之奇功,尤足动后人之敬仰也。”此话引起了大学士和禋的注意,追问他们何以得知康熙大帝和热河。马戛尔尼解释为:“强大如贵国声名威德震烁全球者,敝国人反有不知其历史之理耶?”[8]110乾隆时期,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北京宫廷供职时,专注于中国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并精通满、汉语。钱德明曾将《御制盛京赋》和乾隆帝亲自撰写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翻译为法文寄回欧洲。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为摆脱沙俄压迫,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返回祖国。乾隆帝在山庄万树园[9]75举行盛大的宴会,并在新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内树碑,并亲自撰写碑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纪念回归之盛举。同年十一月,钱德明在北京对碑文进行了翻译和说明,他写道:“朕在承德为他们举办盛大宴会,按惯例赠送礼物,朕下旨,要像正式欢迎杜尔伯特首领们或者其君主策凌的情况一样,把宫殿装饰得绚丽多彩。”接着钱德明写道“举行这一盛大活动的承德,是朕祖父康熙皇帝辟建的极为壮丽的山庄圣地,祖父在夏期炎暑移住此地,与居住在咫尺间的万里长城另一边的民众相接近,而且悉心照料。想当年,大清国征服了厄鲁特这一大国后,策凌及其属下唯一尚未向朕宣誓效忠的杜尔伯特前来对朕表示恭顺之意的地方,也是这个美丽的承德。”[10]47译文在翻译乾隆帝碑文的同时,用大量篇幅介绍承德,强调了承德在清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1773年,钱德明将此篇名为《记叙土尔扈特部落三十万人自里海沿岸东徙之碑文》译文附于信后寄赠伯尔坦君,后被收于《关于中国之记录》一书中。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修建于清王朝国势鼎盛时期,这里不仅是清帝休憩之地,更是清朝政治文化的中心,对外交往的重要场所。承德成为清朝对外的一扇窗口,向欧洲及世界展示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正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其游记《帝王之都—热河》中所说“翻阅十七八世纪传到欧洲的中国见闻记就会知道,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农桑、工业、陆路交通、邮政、水运、中央和地方行政诸方面,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10]83
四、结语
清代前中期,天主教在承德的传播并未像其它内地地区形成一个短期的繁荣,入教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承德作为东蒙古传教区的一部分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以承德为中心的天主教重要教区,其过程是曲折、艰难的。清代天主教在热河地区所遭遇到的困难,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地“封禁”政策带来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清政府对外来宗教的警惕和防范。即便如此,在京的传教士仍利用各种渠道进入热河地区进行传教,并在这里架起了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使欧洲对十八世纪承德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进而对清代中前期的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2]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1969.
[3](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4]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Ⅱ)[M].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
[5]古伟瀛.塞外传教士[M].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2002.
[6]裘凤仪.承德市区的天主教堂变迁和夏树卿神甫:承德文史文库(2)[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7](意大利)马国贤.清廷十三年[M].李天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英)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M].刘半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9]杜江.清代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象征[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 (3).
[10](瑞典)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M].于广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A Survey of European Understanding to Chengde in the 18th century from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ReHe in Qing dynasty
SUN Ya-jun, TANG Bin, LIU Xiao-li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untain Resort, Chengde, Hebei 067000,China)
Rehe as an important town connecting Mongolia and northeast in Qing dynasty is the channel between the inland area and the area beyond the Great Wall. Because of Rehe’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earlier Qing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trict policy of prohibition to cut of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inland and Mogolia as well as the northeast. As a foreign religion, Catholicism was strictly forbidden in its spread in Rehe. Howeve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still used a variety of channels to preach to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Rehe area. By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the Rehe had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atholic diocese in China. By the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y sent to Europe, the 18th century European scholars had go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 lot of this came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Chengde.
Catholicism; Rehe; Lazarists; Scheut Missions; Europe
B976.1
A
2095-3763(2017)-0014-05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03
2016-12-28
孙亚君(1966— )女,河北承德人,承德文物局避暑山庄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学;汤斌(1971— )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承德文物局避暑山庄研究所,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2016年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Z2016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