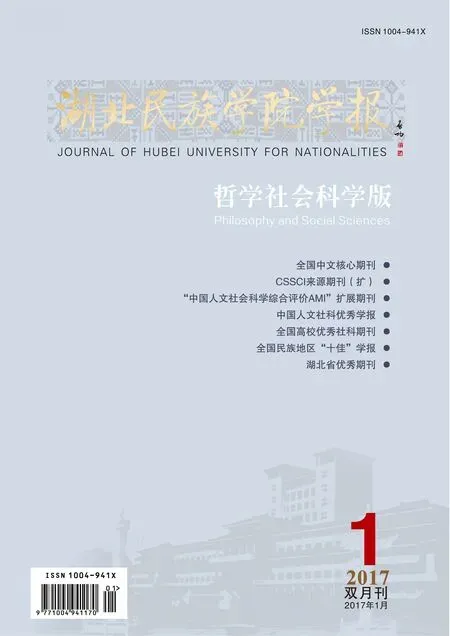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形式”的丧失与寻求:新诗的一个问题
2017-03-07李延玲
李延玲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形式”的丧失与寻求:新诗的一个问题
李延玲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新诗之“新”是语言从文言文变换成白话文,抒情方式也由古典的感时伤怀变成现代的激情迸射和说理,其生命力主要靠“内容”维持,相对于旧诗丧失了“形式”。在“形式”的寻求上,新诗的开拓者们大都把目光对准了艺术最“有意味的形式”——音乐性。在这一点上,现代诗人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西方现代文学中的“音乐性”是对诗歌整体审美效果一种更高的追求,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尤为值得注意。
新诗;形式;音乐性;象征主义
一、新诗之隐忧
“新诗”,在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与其说是名词,毋宁说是动词,人们一直在期待“诗”得到更新,不断地“新”诗。子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事情一旦上了这直线前进的链条,只能进不能退,就是入了现代性的陷阱,无暇回顾,无暇反思,人生如此繁重复杂,谁向我们保证未来就一定比今天、往日美好?诗歌的发展同样是这样,从阅读的感受上看,过去的诗未必就不比今天的诗更让人感动。很多时候,我们说现代诗如何好,倒不是它让人如何感动,其实是在说它有“价值”,什么价值呢?是先验的、预设的在进化论链条上的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价值),是一种可疑的理性上的“好”——它有某种“新的东西”,只要是“新”的,就有价值。很可能这“新”跟人的生命体验、语词经验毫无关系。也许,这可以叫“唯‘新’情结”。
一个人的疯狂是因为他灵魂、生命根基的丧失,一种文体的疯狂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实验)小说的潮流风起云涌,“写”这一行为本身,大于作家、大于文体;“写”比“写什么”重要一万倍。当孙甘露的小说出现时,人们知道,小说这一文体疯了,因为孙甘露已经拆除了小说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只有语言碎片以及碎片中混乱的感时伤怀(比如《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孙甘露将当代小说弄得像一个末世乞丐,一无所有,除了身上飘着衣服碎片、裸露在外的生殖器官和絮絮叨叨的自言自语。这一自戕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中那个在“文革”后成为疯子的历史老师,他手持利刃,在自己身上试验历史书上说过的种种刑法:剜腿肉,割睾丸……在“试验”的鲜血淋漓中大感痛快。先锋派的小说家们无疑就是这个衷情于历史书(先在的“试验”、“唯‘新’”话语)的刑罚迷恋狂。一个疯了的人能走多远?果然,不久人们就见孙甘露退出了小说舞台,其他先锋小说家也纷纷“回归现实”,比如余华的转型,他之后写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人们能看得懂、也觉得有趣的小说。
新诗之“新”,一开始就是语言彻底的变换:文言文变换成白话文、抒情方式也由古典的感时伤怀变成现代的激情迸射和说理,可以说是剜掉了腿肉、睾丸这些要命的东西,在林纾、“学衡”、“甲寅”等“复古派”看来,新诗简直是疯了,但是后来的事实是新诗不仅没有死亡,而且继续生长,旺盛至今。事实果真是这么乐观吗?新诗是真正的体质硬朗还是靠身外的强心剂?它先天的缺失为后来的成长埋下了什么隐患?
二、“诗的形式并没有”
1934年11月5日第十五期的《人间世》刊登了废名对于新诗一些问题的回答,废名这一段“新诗问答”,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什么是“新诗”“旧诗”之分的经典言论。废名说:“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废名的话与时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为什么新诗“内容”要是诗的,“文字”则要是散文的,难道他没有看到当时文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歌散文化倾向吗?为什么说如此凝练、含蓄、意象关系不紧密的旧诗,其“内容”却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但其“文字”却是诗的?我们从废名举的一些旧诗来寻觅这段话的真义:
中国诗中,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确是诗的内容,然而这种诗正是例外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所以成为诗之故,其在于文字么?若察其意义,明明是散文的意义。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确不是散文的意义,反倒是诗的,但该诗的内容用在旧诗却显得不称,读之反觉其文胜质,故而他的内容失掉了,这个内容倒是新诗的内容。
谁也没曾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夜半钟声……唐人张继于功名失意的回乡途中将这些心灰意冷的懒散词句凑在一起,反倒成了一首传世名作《枫桥夜泊》,不能否认此诗是一首好诗,时间、空间、景物、隐约的人心,叠加有致,这样的人生境地是让我们感慨境地之美还是让我们感慨人生的枯寒,着实让人感慨万千。但我们同时发现,如果我们将诗歌意象、意境按顺序翻译成白话,我们就发现这是一篇寻常的写景记叙文,或许没什么独特的感人之处。为什么几个散文化的词汇到了旧诗那里我们读起来就感动不已,而新诗若真的是这样散文化,这种感动就难以觅到。问题在哪里?——废名说,在于它的“文字”,此“文字”显然不止于那几个意象词汇,其实是指这些“文字”在一起的排列方式——诗歌的“形式”:文字的选择、句法的安排、音韵的讲究、节律的安排等整体效果。它其实是几千年汉语诗歌在情感寻求形式的表达过程中寻求到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这样的话很有味道,但是你在翻译中又会失去这味道的缘故。新诗要一下子要将这个“形式”脱离掉,其结果肯定不是像蝉蜕一样的简单,蜕了旧的,就顺利地长出新。它肯定要如经历一场凤凰涅槃一般,在漫长的火焰中挣扎,冒着失掉生命的危险,而能否“新生”还不好说。
缘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是旧诗中的例外呢?可能在废名那里,“散文的”的意思是“叙述性的”,如《枫桥夜泊》。如《登幽州台歌》和李商隐的这首是纯粹抒情的,所以是“诗的”,在旧诗中是例外,但却正是新诗的内容。李商隐此诗题为《牡丹》,全诗如下:“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群。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薰?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里“卫夫人、越鄂君、石、荀令”等指的是人。牡丹为富贵华艳之花,故此诗前六句咏其色态芳香,均借富贵家艳色比拟,或以富贵家故事作衬。废名所列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赏花人“我”面对如此美艳之牡丹,不禁联想巫山神女,思量女神梦中借“我”彩笔,画此花叶,遥寄“我”对意中也如牡丹花一样的女子的情思。李商隐这首诗翻译为白话,其意象之间的距离组织、意境的象征意味、情感的内在深度恐怕只有“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作品能及,莫非废名所言新诗的“内容”指的就是纯粹的抒情性和象征性?
由此可见,诗人废名是在鼓励新诗要摆脱散文化的倾向,要回到诗歌的“余香和回味”,但实际上,《人间世》对废名的提问还另有他意,那就是除去内容,新诗在形式层面是否有着突破前人的做法。而废名将新诗形式的生发归结为诗歌的时代促进性,可以说,是对新诗的发展有着较为清晰的诗人敏感性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新诗发展的时代性重要作用。
在1943年9月的时候,废名又发表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文章:“我的本意,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废名确实是在强调诗歌的内容,无论是纯粹的抒情性或思想上的象征主义,都是“内容”。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无边的包容现实,什么都可以写,况且,“我们的时代正是有诗的内容的时代”,诗歌只要有新的内容就行了。新诗之“新”,其根源原来这里也有。
但废名仍然没有回答新诗发展历程中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旧诗因为有了那“文字”,就“成为诗”,就有着比新诗更强大的审美愉悦和感动?在废名的言谈中,似乎还有一个隐含的信息:新诗在唯“新”运动中其实丧失掉了“形式”,新诗并没有那能使诗“成为诗”的“文字”。新诗之所以能生长下去,完全是靠“内容”撑着,它自身的“形式”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代一代的诗歌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不能从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上独立出来,就成为自然的事情。诗歌的审美态度和写作方式的变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至为了变革、造反本身的趋向也成为必然,因为在追“新”求“新”的历程中,“新”本身即是目的。靠“时代……内容”支撑的诗歌,其生命力是可疑的,当这个时代的历史与精神远去之后,人们不再熟悉或不再认同,那么承载这一“内容”的诗歌也会被人们冷落。因为诗歌的价值不止在这个“内容”,诗歌也自身那使诗成为诗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就是旧诗的“文字”方式,新诗也必须有的“形式”。
三、寻求“有意味的形式”
新诗没有自己的“形式”,是个令新诗的开拓者们一直头疼的问题,在刘半农那里,他寻找的是破坏旧陨,重造新韵、方言俚语入诗、学习民间歌谣等方式;在沈尹默那里,他汲取的是古典诗词的音韵;在废名这里,他也承认“歌谣确是可以做我们的新诗的参考,我们的歌谣是散文,但我们的歌谣也还能成为韵文,是自然的形成。我们的新诗如果像我们的歌谣那样能自然地形成,那新诗不也就有了形式了!不过在我看来这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口口相传的歌谣一经写出来,便失去了歌谣的生命,而诗人的诗却是要写出来的。”[1]
废名和开拓者们一样,都在努力为新诗寻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一种最有意味的形式——音乐性,他们在民间歌谣里为新诗寻找合适的音乐性的东西。但废名又是悲观而清醒的,作为声音和美感结合的音乐,它的存在只能是在声音当中和人的心灵感受中,它和语言的存在是不一样的。
古典诗词的音乐性是明显的,就拿张继的《枫桥夜泊》来说,除了诗歌语言负载的“凄清” “孤独”等意义之外,同样还有让读者的生命发生感应的东西,读者会觉得它有超出“意义”的另外的“美”、让灵魂震慑的东西。我们姑且将这超出诗歌所要陈述的意义之外的东西称为“音乐性”。它指的是诗歌可以朗诵可以演唱,是诗歌中存在的一种与人的生命、情感的形式相互应和、发生作用的内在结构,确确实实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用苏珊·郎格的话说,就是:“我们叫作‘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2]
新诗的开拓者们在诗歌中追求这种音乐性有没有陷入神秘主义的嫌疑?从汉语诗歌的发源来看,其实诗歌与音乐本是具有着同根生特性的。《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进一步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诗,情发乎声、声成文是乐。在《文心雕龙》的《乐府》一篇中,刘勰进一步说明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诗歌与音乐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诗歌是音乐的内容,音乐是诗歌的形式。在人类的历史演进中,音乐由于自身的特性,它相较语言有一定的优势,它有脱离诗歌独立生存的可能。而诗歌,由于人的意识的发展、理性的进步,不满足于混沌的情绪表达,试图以语言清晰地表达心灵,诗歌逐渐成为一种更加完整意义层面上的人文陈述。于是,诗歌从音乐性中独立,音乐从语言辖制中脱离出来,在器乐和声乐上生存。很显然,这一对艺术孪生弟兄的分离,是它们各自致命的损失。诗歌失去了“形式”之美,音乐失去了语言的精魂。
四、诗歌的“音乐性”
作为象征派的鼻祖,爱伦·坡对诗歌的音乐性无比重视,他说:“音乐通过它的律吕、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如此重要的契机,以致拒绝了它,便为不智……毫无疑问,我们将在诗与通常意义的音乐的相结合中,寻找发展诗的最最广阔的领域。”[3]魏尔伦在其诗作《诗艺》中直言:“音乐高于一切”,要将诗歌弄成“无词的浪漫曲”。[4]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瓦雷里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所谓象征主义,“可以很简单地总括在好几族诗人想从音乐收回他们的财产的那个共同的意向中。”T.S.艾略特的《荒原》的主题众人皆知,但是T.S.艾略特的其形式建构也是非常突出,像《四首四重奏》,就是乐盲也能感觉它们形式上的节奏感,这部诗作仿佛一场复杂的交响乐在有条不紊地行进,读者的思想、情绪节律也在随之行进。[5]
西方的诗人为什么痴迷于诗歌的音乐性?其实我们从爱伦·坡的唯美主义到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纯诗”理论,可以看出这些人寻找的是诗歌纯粹的形式上的意义。这种“形式”带来的整体之美,是作家努力的对象;在“上帝之死”的背景中,是艺术代宗教之目标的一种实现。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它有着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的思想渊源。
现代文学的精神普遍表现为人的精神分裂和内在的焦虑。而“后现代”则是一个取消彼岸盼望的时代,但它的精神仍然是精神分裂(虚空)和内在的焦虑,所以有人又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象征主义诗人正是一种在此岸仰望、期盼的姿态,无论是波德莱尔的“透国语词的森林”,马拉美对诗歌的苦心经营,还是兰波灵魂的幻觉、语言的炼金术,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他们追求诗歌近乎神秘的形式上的那种美,其实是一种切实的审美效果,他们渴盼的都是在诗歌中升起一个灵魂的栖息地。[6]
什么是象征?心理学家、原型理论的大家——荣格对象征的理解很有意味:“象征不是一种用来把人人皆知的东西加以遮蔽的符号,这绝非象征的本真含义。恰恰相反,象征借助于与某种东西的相似性,而力图阐明和揭示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这“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正是象征主义诗人所需要的,也是痛苦灵魂写作的旨归。诗歌的形式意义的“有意味”正在这里。所谓的音乐性恐怕与此有关,因为它几乎和音乐一样,托住了人飘忽的灵魂,在美与崇高的感受中人暂时得到了慰藉。
这也许就是现象学大师、波兰美学家罗曼·茵加登所说的在作品的四个基本层次(字音层、意义单位、图式化方面、被再现客体)之外的——形而上品质(metaphysical qualities),形而上品质“揭示了生命和存在的‘更深的意义’,进一步说,它们自身构成了那常常被隐藏的意义,当我们领悟到它们的时候,如海德格尔会说的,‘我们经常视而不见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的存在的深度和本原就向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了。’”[7]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西方现代文学中对于诗歌的“音乐性”观念,大于我们对于诗歌的“音乐性”的理解。诗之音乐性,不仅仅是音韵、节奏方面的,而是艺术品一种整体的特征,其美学效果在比喻的意义上如同音乐一样(而不是代替了音乐,不同艺术门类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因为各有语言方式和美学目标)。这也是为什么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说最好的诗歌是“无词的浪漫曲”之缘故。这里的音乐性其实是诗歌的整体效果,其中包含着具体形式规则的寻求,比如建行建节、音韵、节奏等等,正是这些因素,与诗歌的主题(情感、经验等)完美融合,形成一种令人感动的阅读效果,使诗真正成为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说了什么“时代……精神”的东西。这也告诉我们,一方面,对于诗歌而言,“形式”的寻求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形式”的寻求,也不应是偏颇的,不能因噎废食,脱离了“内容”。“形式”与“内容”根本不能分开,二者可以说无法脱离,对于读者来说,现代诗的“形式”,通常是那个整体的美学效果,也就是已经完成了的“内容”。
五、“形式”寻求:“在路上”
新诗对于“形式”的寻求,一直是“在路上”的状态。“五四以来的新诗,从形式方面概括地说,就是在传统的格律诗和西方的自由诗两者之间曲折地走了过来。”[8]作为中国新诗创作主体的新式诗人,他们在接触到中国新诗创作这个新的命题之前,所受到的文学影响核心部分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是难以被外来的文学精神的影响直接屏蔽的。外来文学尤其是诗歌主题的影响,是这批诗人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无法拒绝的,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规约在此时终于有了破除的可能性,难怪在当时的新诗创作中会出现大量的直抒胸臆直至呼喊式的新诗内容,它与时代环境下创作主体的内在追求紧密相关。
1959年,诗人何其芳回顾新诗的历史曾表述过如下观点,即五四时期的诗歌兼有中国古体诗与现代诗歌的样式与自由思想的多层面因素,在时代的催化剂作用下,与当时社会的特殊气质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结合之后,才形成的新诗的主要体式,且这期间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同样的较为突出,“有一部分诗作者的确搬运过或者模仿过外国的诗歌的形式。”[9]从历史发展的向度来考量,我们已经认可了文学如下的发展路径,那就是接受影响也还不等于是移植。不管怎样,五四以来的新诗,就其主要部分来说,仍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中国的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因为我感到今日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不习惯于这种形式,不大容易接受这种形式。而且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恐怕新诗的民族形式还需要建立。”[10]
[1] 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册)[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2] (美)苏珊·郎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 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M].葛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 戴望舒.戴望舒译诗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 (英)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M].付礼军,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
[7] 王岳川,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话说新诗(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谈写诗(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1-15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构建中医院校通识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4SJGLX036)。
李延玲(1966- ),女,河南许昌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I052
A
1004-941(2017)01-01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