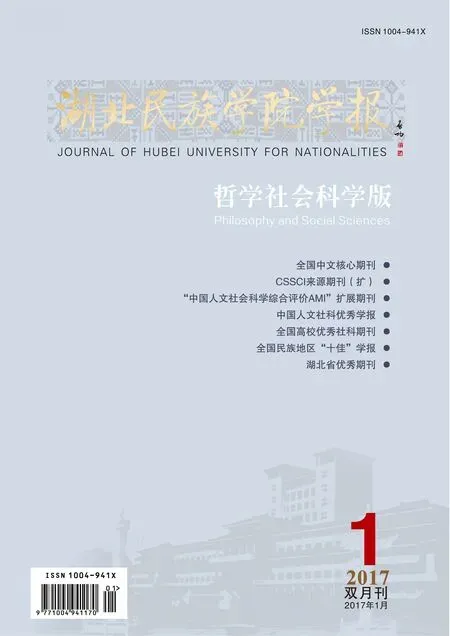口述、图文与仪式: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
2017-03-07孟令法
孟令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口述、图文与仪式: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
孟令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畲族普遍流传的盘瓠神话,除广泛存在的口头表达,谱牒书写、图像描绘与仪式展演同样成为这一神话在该族世代相沿的关键。不过,在“犬辱文化”的影响下,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显性,相反却表现得相对隐秘,实可用“内显外隐”的模式总结。虽然民族旅游已将盘瓠神话搬上舞台,但它是否能彻底缓解来自历史遗留的族际矛盾,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总之,作为集体记忆的盘瓠神话,不仅反映了畲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更对畲族社会的发展及其族群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口述;图文;仪式;盘瓠神话;畲族;利弊
盘瓠神话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应劭《风俗通》,并在历代文人的征引中,成为管窥不同族群,尤其是南方少数族群的重要资料,而作为口语演述的盘瓠神话,则是早于文字存在的语言艺术。盘瓠神话在性质上与其他民族起源神话或英雄神话一样,虽被记入汉文典籍,却非历史真实之定语,甚至与史实相悖。不过,正如拉斐尔·贝塔佐尼所言:“神话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它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它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神圣的人物和其他超人的英雄在神话中担当其角色,以其卓越的功绩和令人惊异的冒险及奇迹,超越了不容置疑的现实。”[1]125因此,盘瓠神话的历史性同样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相较于神话本体研究,对盘瓠神话流传形式的关注却很少,而畲族作为盘瓠神话的主要承载力之一,她对盘瓠神话的演绎则是多重的,除了普遍存在的口头表达,谱牒书写、图像描绘与仪式展演同样是这一神话能在该族世代相沿的关键。也许以上表现形式不独为畲族所有,但如此系统地呈现于畲族的文史记忆,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神话对畲族社会发展与族群认同的重要作用。
一、韵散相和:畲族口头表达的盘瓠神话
民间文学又被称为“‘人民的口头创作’或‘口头文学’,因为它是一种活跃在人民口耳间的特殊的语言艺术”[2]31,所以“口头性”一直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而在表现方式上,它被民俗学家划分成三大类:“(一)散文的口头叙事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二)韵文的民间诗歌(抒情的和叙事的长诗、各种歌谣)、谚语、谜语;(三)综合叙事、抒情、歌舞,具有较多表演成分的民间说唱、民间戏曲”[3]241等。可见,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和史诗虽然从属于民间文学的不同类别,但同为口语演述的艺术创作则对同一题材(内容)的表现上具有同等效力。王宪昭曾言:“《亚鲁王》作为苗族复合型的大型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史诗叙事中关于万物起源、造日月等典型神话母题具有值得关注的神话内涵与文化分析价值。”[4]30据此可知,在民间文学体裁的历时性发展中,不同体裁间的韵散互转不仅是民间口头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更是人民创造力的直接体现,而以盘瓠为核心母题的畲族口头文学,恰恰反映了散文讲述与韵文说唱的对照关系。
雷国强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浙江“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卷)”至少收录了22篇内容详略不一,但同以盘瓠为核心母题的神话故事[5]250。在这些异文中,既有以盘瓠为独立演述对象的文本,笔者称其为母本神话,如《盘瓠的传说》《畲族祖先的由来》《盘瓠出世》《亢金龙下凡》等;亦有以盘瓠为依托,讲述相关人、事、物之功绩、起源或习俗的作品,笔者称之为衍生传说,如《高辛与龙王》《三公主》《祭祖舞的由来》《猎捕舞》《悬棺葬》《畲族四姓的传说》等。尽管笔者无法还原盘瓠神话的原初状态,但事实表明,几乎所有跟盘瓠相关的畲族语言艺术,已然构成了一个庞大且多彩的特定神话丛。也就是说,盘瓠神话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文本,而是在实际演述中,不断从母本分化并衍生出众多彼此粘连却又相对独立的地方话语体系的生命综合体。进一步说,这些以人之能动性创造的艺术形式,都可被纳入——盘瓠神话=盘瓠出生+揭榜征番+变身娶妻+移居凤凰山+闾山学法+打猎殉身+族群迁徙*在笔者硕士论文中,盘瓠神话的母题构成并不完整,缺少了“闾山学法”这一核心要素,在此予以补充。(孟令法《畲族图腾星宿考——关于盘瓠形象传统认识的原型批评》,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4页。)——有机公式。不过,由于时代变迁,诞生于原始社会的神话逐渐摆脱宗教信仰(以神为尊)的神圣性,成为阐释自然、反映社会、认识自我的历史解说词,从而进入民间文学的“传说时代”。因此,以盘瓠为对象的现代口承文学在畲族社会的发生、发展与变迁,同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功能,而内中蕴含的神话因子则说明,部分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原发神圣性,甚至可在特定语境中互相等同。
从共时的文体角度看,神话与史诗是否具有前后承继的关系,实是一件难以解答的学术问题,但从历时的内容层面讲,神话与史诗则可成为同一故事的承载体。万建中认为:“以往只把神话看成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其实史诗和神话一样悠远”,“史诗的内容就是神话,神话通过史诗获得‘活’的地位”[6]139。由此可见,神话与史诗是一对可以互相转化的姊妹艺术。就盘瓠神话而言,畲族民众不仅以散文体故事表达他们对始祖的崇奉之情,并借以阐释各类生活习俗的生成,还在韵文体史诗《高皇歌》[7]的演述中呈现出一部更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史。同其他民间文学类型一样,史诗也会因口头性、集体性和扩布性而发生种种变异,而这也是《高皇歌》在演述盘瓠生平时呈现出长短不一,甚至名称各异的重要原因。从现已发现的史诗文本看,《高皇歌》有时也被命名为《盘王歌》《麟豹王歌》《龙皇歌》或《盘瓠歌》《祖宗歌》等,而浙江省云和县坪垟岗村民蓝观海所演述的《高皇歌》是笔者目前所听到的国内诗行最长的一首。与其他同类史诗一样,此歌以盘瓠生平为主线,在124.5条498句3486字的篇幅中,展现了畲族从创世到起源、从征战到发族、从创业到迁徙的整个过程。虽然《高皇歌》在诗行长度上很难媲美于其他民族的史诗,但正如朝戈金所言:“形式上诗行的多寡,并非是认定史诗的核心尺度,史诗内容诸要素才是鉴别的关键。”[8]129因此,作为民族口承文学的典型代表,《高皇歌》承载了更为全面的畲族远古史和近世生活的信息。
作为民族历史之映射的盘瓠神话在口头表达的世代传承中,虽然原初神圣性的逐渐流失让其由讲述神之崇高转向展示人之伟大,但这种变异的发生不仅加速了盘瓠神话的世俗化,更增强了人们借助盘瓠神话解释自我生活的真实性。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人类的生存所需也愈发多样化,而以纯语言为途径的艺术创作却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面临消亡。尽管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中,以《高皇歌》为代表的畲族民歌(特指小说歌)在政府的推动下,于2006年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似乎为此项民间口头艺术带来“生”的希望,但受制于演述人群体的老龄化,演述场域的空心化、娱乐化和权利化,以及族群互动的历史影响(详见后文),又怎能保障韵文体歌唱的活态可持续性,更何况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定的散文体叙事?
二、谱图固化:畲族图文描绘的盘瓠神话
畲族是否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民族书写传统,现已很难查证,即便被部分学者认定为具有一定解释意义的出现于传统手工艺产品——织带——上的纹路[9],甚至产生于上古时代的华安仙字潭图画文字[10],也很难成为畲族有过民族书写传统的有力佐证,而于畲族民间征集的大量手抄文献中,虽然有一些类似汉字却又迥异于汉字的文字,但这些数量极其有限且不成系统的符号,根本无法形成具有特定指向的文本。因此,民族语言也就成了畲族代际间传递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不过,随着封建统治力的逐渐深入,深居东南山区的畲族也在封建王权的威慑下为汉字传统所同化,而在与汉民族群的互动中,不同支系的畲民也渐渐实现族群自我的宗族化。故而,自宋元尤其是明清以来,创建宗祠、纂修谱牒则成为广大畲民不遗余力、争相而为的生活规范,而带有一定族源史性质的盘瓠神话,在以较为统一的文字表述被固化于谱牒的同时,也成为畲族区别于比邻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文化,不仅在显性的宗祠中有谱牒在远祖与近祖、历史与现实间构筑起民族记忆的桥梁,更有形象化的盘瓠神话——祖图长连——以其更为直观的图文效果,从隐性层面于民族内部的特定活动中,维系了整个人们共同体的信仰传统。
有研究表明,自北宋以来,修谱之风逐渐下移于普通大众。谱牒不仅被用于“记述家族历史和家教伦理”,也被视作“溯本清源、认祖归宗、联络血亲的重要手段。”[11]110-111在长达千年的迁徙活动中,汉族修谱以作“史规”的宗族行为深刻影响了比邻而居的畲民群体。不过,在笔者所能见到的畲汉谱牒中,汉族追溯远祖的文本虽显得格外“真实”,但相对缺乏对民族整体意识的书写,而畲族在普遍遵循“欧苏谱例”的编纂规范时,更注重民族起源与发展的整体感,即在叙写本家始源的基础上,将附有原初四姓——盘蓝雷钟——发生史的盘瓠神话付诸谱头或谱序,从而在应和《高皇歌》所唱“盘蓝雷钟一宗亲,都是广东一路人”的基础上,突显了它在族源认同上的积极作用。虽然笔者掌握的畲族谱牒将盘瓠神话记录于不同文本之下,但其内容表现得极其一致,如溪塔《蓝氏宗谱·敕封祖图公据》、新楼《蓝氏宗谱·敕书》、郑坑《雷氏宗谱·雷氏历代封姓序》、山外《钟氏宗谱·颍川郡钟氏宗谱序》*详见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蓝氏宗谱》,清光绪十九年(1893)修,复印件藏福建省民族研究所;宁德蕉城区八都镇新楼村《蓝氏宗谱》,民国八年(1919)重修,复印件藏福建省民族研究所;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郑坑村《雷氏宗谱》,民国二十一年(1931)修,复印件藏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山外村《钟氏宗谱》,宣统二年(1909)修,复印件藏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等,而雷鋐《广东盘瓠氏铭志》、钟李期《广东重建祠序》、蓝玉钟《广东重建祠序》和蓝声华《盘瓠氏重建祠宇序》*雷鋐(1696-1760),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人,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浙江督学等,为雍乾时期著名理学家,《清史稿》有《雷鋐传》,《四库全书》收其《读书偶记》,此外还著有《象山禅学考》《阳明禅学考》等。收录《广东盘瓠氏铭志》的畲族谱牒均认为此文作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桂月,但这与雷鋐生卒年相差甚大,故笔者认为此文很可能是托名之作;钟李期(生卒年不详),广东博罗新铺镇蕉岭村人,乾隆丙午(1786)科进士,曾候选为博罗县正堂,诸谱牒显示《广东重建祠序》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孟秋月;蓝玉钟(生卒年不详),亦作蓝玉种,福建漳浦一带人,曾因恩贡举进士第而候选为地方儒学左堂,相关谱牒显示《广东重建祠序》作于嘉庆戊午年(1798 );蓝声华(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清光绪间举人,曾候选为某县知县正堂,相关谱牒显示《盘瓠氏重建祠宇序》作于光绪乙酉年(1885)。可参见福安市康厝畲族乡牛石坂村《雷氏宗谱》,复印件藏福建省民族研究所;福鼎县佳阳镇双华村《蓝氏宗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修,复印件藏福建省民族研究所;丽水市遂昌县妙高镇井头坞村《钟氏宗谱》,民国二十年(1931)修,复印件藏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等。等则因作者的文人士大夫属性而被更广泛传抄于宗谱之中。此外,基于盘瓠神话而衍生出的解释性传说,同样被部分宗谱所记载,如林岭《雷氏宗谱·龙首师杖记》[12]52-53和樟坑《蓝氏宗谱·龙首师杖志》[13]13等,而这恰与雷国强收集的现代口承神话《盘瓠杖》[5]252如出一辙。整体而言,宗谱中的盘瓠神话虽被列入不同篇目之下而发生些许细节差异,但与口头表述一样,它们均未脱出上述盘瓠神话的情节公式。
在畲族文化的构成元素中,“祠堂六宝”除了上述宗谱和龙头师杖外,还有灵牌、香炉、楹联和祖图[14]170-174,它们无不从显隐两个层面构筑起盘瓠神话的整体性。其实,祖图是由一整套神像画组成的图像系统,而被畲民称之为“长连”“环山轴”或“永远图记”的故事画,才是盘瓠神话得以直观展现的民族艺术品。普遍认为,畲族祖图长连不仅不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品,也非外族人能够轻易观察到的展示品,而是在特定时刻的特定仪式中的被畲民视作具有一定灵力的法器。因此,祖图长连也被附上了浓郁的神秘性。即便如此,这一由数十个连续性片段组合而成的故事画,也在一些历史典籍中得到点滴呈现。如,王守仁在《横水桶罔捷音疏》中记述:“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尽惑群贼,悉归约束。”[15]342嘉靖《惠州府志》则记载:畲民“自信为盘瓠后,家有画像……岁时祝祭。”[16]卷一四《外志》而民国《新修丰顺县志》写道:畲民“有祖遗匹凌画像一幅,长三尺许,图其祖……自出生时及狩猎为山羊触死,更情事甚详,盖千百年古画也。”[17]卷十六《风俗》由此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祖图长连既已普遍存在于畲民社会,并成为凝聚自我的仪式用具。目前,在国内发现的五十余幅祖图长连中,绘制年代最早的是崇祯七年(1634)的“盘瓠王开山祖图”*“盘瓠王开山祖图”在2007年10月发现于浙江省遂昌县妙高镇井头坞村村民钟水寿家老屋。此图绘制于明崇祯七年(1634),白纸卷轴,其色五彩,画幅26.2cm×1066cm,破损严重,2008年下半年修复完成,并做了两幅复制品。此图现为国内发现的所有畲族祖图长连中绘制年代最早的一幅。该祖图由钟法贵、钟法旺主持绘制,绘者不明。其残损的题头上有名称“盘瓠王开山祖图”,随后为“楚皇帝上奉 天命恩承运……大隋五年(585)五月五日给会稽七贤洞抚徭卷……盘瓠王子孙世代流传,毋令违失,如有破……皇帝勒给券牒,所属州县官司陈告印押付招……原是……”。该图的主体以连环画形式展示了畲族先祖的生平神话。此长连明确指明畲族始祖坟墓在“南京”。在图画最后,署“大明崇祯甲戌岁住景宁二都油田王畈锦岱洋居住……妙(描)画祖图流传与世代儿(孙)永远千秋”,并“高祖公钟佰三十三郎”“祖钟千二十郎、钟千二十一郎”,及为首者“谨题为记”等。“盘瓠王开山祖图”原本现藏丽水学院畲族文化研究所,复制品一于丽水学院畲族文物展览室展出,复制品二由钟水寿保存。,其余皆为有清以来的作品。这些多由师公保存的“家传至宝”,除了绘画技艺的高低、色彩布局的差异外,其大同小异的画面内容不仅没有跳出盘瓠神话的情节公式,同时突显了它所蕴含的时空复模性。
蓝炯熹曾言,深受汉民宗族文化影响的畲民认为,“三世不修谱,谓之不孝”“五世不修谱,谓之有罪”[14]104。由此可见,相较于比邻之汉民对谱牒的重视程度,畲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借助谱牒对世家历史、人口组成、伦理道德的典籍化呈现,较好地维系了一张无形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而民族起源与发祥的古老记忆虽与盘瓠神话不能等同,却在汉字的固化下,彰显了不同支系间的认同理念和凝聚精神。同为“祠堂六宝”之一的祖图长连即便没有谱牒那样具有较强的公开性,可它能以更直观的形式,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仪式中形象化地述说民族起源与发祥的神奇经历。随着时代发展,进入当代的畲族祖图长连已然脱离自我封闭的族内界限,成为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博物馆收藏*目前主要有国家博物馆(一幅)、景宁中国畲族博物馆(一幅)、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两幅)、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一幅)、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一幅)、浙江博物馆(一幅)、宁德中华畲族宫(两幅)、宁德市闽东畲族博物馆(一幅)和丽水学院畲族文物展览馆(原件一幅,复制品三十余幅)等收藏有畲族祖图长连。。虽然当下发现的祖图长连与畲族支系的数量相差甚远,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绘制祖图依然是畲族内部重要的活动之一——2016年4月至7月,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桃山村的蓝土成之徒钟小波,以其师保存的祖图为蓝本,费时三月有余绘制了一幅新长连,而它将作为畲族历史文化的展品之一入藏杭州畲族馆*蓝土成(1948-),男,畲族,小学,农民/木匠,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桃山村人,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祭祀仪式)代表性传承人;钟小波(1994-),男,畲族,大专肄业,学徒,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柳山半岭村人。此图乃应著名畲族作家、“骏马奖”评委之一、杭州畲族馆馆长的钟一林先生所托而绘制。此图分上下两卷,五彩,棉布质,画幅上下卷均为750cm×50cm;蓝土成藏祖图长联绘制于1951年,上下两卷,保存完好,桐油浸泡,麻布质,五彩(模糊),画幅上卷长800cm×33cm,下卷600cm×33cm。。总之,谱牒与祖图长连的形式之别与内容之差,并未阻隔两者的密切联系,相反却在图文对照中,丰富了盘瓠神话的表达模式与内涵。
三、身体律动:畲族仪式展演的盘瓠神话
从语言表述到图文记录,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似乎已经转向静态发展的道路。不过,无论是流动的语言还是固化的图文,它们都是在身体的规律性运动中产生的民族艺术。上文之述还表明,语言表达与图文记录都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民族创造,而是能为特定仪式整合的社会习俗。仪式作为人类社会的古老行为,自19世纪形成专门术语以来,就“被确认为人类经验的一个分类范畴上的概念”而得到广泛关注。不论是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社会-结构学派”,还是后起的“历史学派”或“功能学派”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分析了仪式对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一种过渡性行为规范,人们在分离、阈限与整合的象征体系中获取不同的体验或经历,进而完成自我、他者与社会的对接。不过,“‘虚拟’是仪式情境的主要特征”,而“仪式行为方式的虚拟性、仪式表演手法的虚拟性、仪式场景布置的虚拟性以及仪式行为者心理时空的虚拟性”“共同构拟出一个仪式的虚拟世界”,并由此让仪式行为者在“超常态行为”中“感受真实”[18]33。作为一种神圣性叙事行为,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自古就有仪式活动做依托,而以长夜嬲歌为代表的日常性仪式活动和以祭祖、做功德与传师学师为代表的宗教性仪式活动则为盘瓠神话的畲族传承提供了动力支撑。
本文所谓日常性仪式活动,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但又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特殊阶段附上一定神圣性的程式化活动。“以歌代言,以歌传情”是畲族社会文化的一大特征,而嬲歌不仅与此对应,更是日常性仪式活动的典型代表。蓝雪霏指出:“‘嬲歌’是畲族关于闲暇或节日期间与外地氏族外异性对歌的原称”,而“无论是‘出行’作客,或参加歌会,嬲歌有两种不同的发生情形,一为拦路截唱,一为落寮会唱”,但不论哪种形式,都具有相对固定的对歌程式,而相较于自由度更强的拦路截唱,落寮会唱则更突显了对歌的仪式性特征[19]66-72。据笔者调查,被视为正歌的神话历史歌或传说故事歌(小说歌)是嬲歌(落寮会唱)时的必唱曲目,只不过福鼎、霞浦等地将其置于上半夜,而福安、宁德以及浙南诸地把它放在下半夜。被誉为“深山畲歌王”的蓝高清*蓝高清(1943-),男,畲族,小学文化,农民/民歌手,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山根村人。告诉笔者,正歌是以《高皇歌》《封金山》《凤凰山》《奶娘传》《末朝歌》《长毛歌》等为代表的神话历史歌和传说故事歌;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蓝观海*蓝观海(1943-),男,畲族,初中文化,民歌手/退休教师,浙江省云和县雾溪畲族乡坪垟岗村人。则指出,嬲歌在演唱内容与体裁上都有十分严格的“一对一”原则,即正歌对正歌、杂歌对杂歌,否则就是不合章法的“乱对”。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致强调,在演述《高皇歌》等神话历史歌时,现场气氛不能太嘈杂。据此笔者认为,以盘瓠神话为表现内容的《高皇歌》,即便在嬲歌的娱乐情境中,也未失去其严肃静穆的本质。
与日常性仪式活动相对,本文之宗教性仪式活动主要是指有计划或有组织地举行的具有强烈宗教信仰性的程式化祭祀行为,而此类行为的最核心要素之一便是在仪式中敬奉各类神祇或先祖。神话-仪式学派认为:“文化和艺术的起点建立在原始人类的仪式行为上”,而“伴随仪式的发展,口头表述不断成长,神话开始出现”,因此“仪式是原初的形式,神话是它的直接派生物。”[20]103据此可知,盘瓠神话的畲族生成似乎也经历了这种进化之路,但事实表明,它并未彻底脱离仪式情境而独立存在。虽然规模宏大的祭祖活动在当下已很少看到,但一些长者的记忆显示,不管祭祖活动设定在宗祠还是家堂,必不可少的法器之一便是祖图长连,而仪式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则是演述《高皇歌》《凤凰山》或《封金山》等口传史诗。尽管祭祖活动的信仰崇高性自不言喻,但相较于这种集体祭祀行为的稀见性,以丧葬为代表的传统人生礼俗依然存续于当代畲村。在普通畲民看来,做功德几乎是所有丧家都在追求的必备程序。不过,与相对俭省的一天一夜小功德相比,较为隆重的三天三夜大功德则在更为复杂的空间布置与行为程式中展开,换言之,大功德必须借助祖图长连以增强道场的严肃性,还要在仪式的最后阶段由专人演述以盘瓠逝世为主题的歌言,这在丽水畲民中普遍流传的《思念祖宗》[21]85-88既是典型。总之,不论是祭祖还是丧葬,既能在团结宗族成员的基础上完善民族发祥史的传递,也可在追思逝者的虚拟情境中,彰显祖先崇拜的虔诚心理。
畲族丧葬活动之所以出现大小功德之分,其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在于民族祭祀行为的层级规范。对广大畲民而言,逝世后能否做功德,跟成年后是否学师*“学师”全称“传师学师”,畲族民间则有“做阳”“奏名传法”“做聚头”或“醮名祭祖”等说法。密切相关。学师是“畲族世代相传的宗教活动”,它通过师公向学师“弟子”传习法术,并以此反映“盘瓠上闾山学法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23]118。尽管目前对传师学师的属性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它是集成年、入教、入社和祭祖等于一身的综合性宗教性活动。一般认为,这一由十二位师公主持,历经三天三夜六十余个步骤才能完成的仪式活动[22]168,只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才能参加,并在学师后世代相传,否则就会成为“断头师”。学师者人称“红身”,死后可做大功德,已传代者的寿衣为青色,未传代者为红色,而未学师者叫“白身”,死后只能做小功德,穿蓝色寿服。由此可见,学师与否不仅奠定了畲民个体的社会形象,更强化了他的社会地位[23]120。在传师学师的复杂过程中,虽非每个步骤都与盘瓠神话相对应,但在装点道场并强化仪式严肃性的祖图长连上,显著描绘了盘瓠闾山学法的情景,而畲民普遍传言,盘瓠是在坚韧不拔的信念支撑下,跨越九重山才来到闾山,并在习得法术后返回凤凰山,因此在仪式后期,不仅要演述以盘瓠神话为核心的表明学师阶段性成功的《兵歌》*《畲族传师学师书文汇编》写到,《兵歌》由《念祖宗》《太祖出朝》两部分组成。(浙江省畲族文化研究会编《畲族传师学师文书汇编》,2008年内部刊印,第69-77页)但并非所有畲族聚居区的《兵歌》都有盘瓠神话的内容,例如笔者从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东弄村蓝仙兰女士处看到的《丙(兵)歌》(雷乾有民国八年[1919]抄自雷法宝处)中,只有类似于《念太祖》的内容,而无后者。,同时还要模拟过九重山的艰辛过程——由师公带领身穿破衣(法衣)、脚蹬草鞋、肩背包袱的学师“弟子”,在象征九重山的九根青竹间边行边舞边唱,以此实践自己与历代先祖的灵肉对接,从而在取得“法名”并将之系于龙首师杖的同时,“象征性地加入盘瓠集团”[24]451。
上文之述表明,盘瓠神话在畲族社会的仪式展演是多方位的,并表现出一定的时序性和人生连贯性。总之,不论哪种仪式展演活动,都不是静止的图文表达,而图文在仪式的带动下变得更有活力。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包括祭祖、做功德、传师学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以身体为承载力的规律性运动都可被赋予民间舞蹈的雅号,从而脱离纯粹的信仰活动而成为民族艺术的精品,但这种简单的艺术抽离,似乎并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整体关照。刘铁梁在《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的学术讲演中指出,民俗研究应是一种身体性研究,因为文化可以改造身体,社会也会影响身体,身体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并由此认为民俗学实是一门“感受之学”[25]。因此,作为民俗文化重要组成的仪式,其每个元素的呈现无不依赖于人之身体的律动,而其崇高性的体现更无法脱离“感受”的实践。
四、利与弊:盘瓠神话对畲族发展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盘瓠既是畲族传说中的始祖,也是畲族遗存的古代图腾崇拜的象征。盘瓠传说经历沧桑岁月,依然鲜活在各地的畲族社区。伴随着《高皇歌》的传唱和《祖图》的传承,以及祭祖仪式的举行,盘瓠传说经久不衰”[24]11;亦有学者认为:“盘瓠传说不仅以口头形式为畲族群众世代口耳相传,畲族群众还把它收入族谱、绘成祖图予以记录,甚至还刻成祖杖加以崇拜,编成歌谣广泛传唱……畲族日常生活禁忌、民族服饰等等也都留有盘瓠信仰的影子,可以说盘瓠信仰已经成为畲族文化的缩影”[5]236,但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显性,相反却表现得相对隐秘,且在时代的洪流中渐失往日的多样性。换言说,盘瓠神话在畲族内部具有显著的向心力,但它的演绎主要展现于本民族成员的可见范围内,即便是公共性十分显著的祠堂活动,外族人也很难得见。因此,盘瓠神话在畲族社会的演绎,实可用“内显外隐”来总结。虽然那些记载于历代典籍的只言片语能给予后人以历史信息,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些与事实不甚相符的误差,而这不仅源于畲族在维系族群认同时,对文化传统的珍视,更在于畲汉交往的权利不对等。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强调,畲族“始终保持对始祖盘瓠的信仰,这个信仰贯穿在祖图、族谱、祖杖、传说、山歌、服饰、习俗、祭祀等方面,在畲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维系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加强民族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26]133,而畲族学者雷国强指出:“盘瓠传说群系使以盘瓠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图腾信仰文化体系趋于稳固和统一,成为畲族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基础”[5]260-261。尽管盘瓠神话在维系畲族对民族整体意识的巩固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实际演绎却未得到太多族外成分的公开,而是在相对自我的坚守中延续曾经的样貌。有研究表明,早在隋唐之际,畲族先民既已在闽粤赣交界的广大山区聚族而居,并随着封建统治力的逐步深入而加速了自己从与汉族对抗到相互交融的步伐[27]30-31。笔者并不确定盘瓠神话在畲族社会走向隐逸的原因是否与传说中的“唐畲大战”有关,也无法形成隋唐之前盘瓠神话在畲族先民中的存在状态,但畲族的千年迁徙及其后的畲汉矛盾却与此密切相连,从而间接证明了盘瓠神话在“犬辱文化”的持续发酵中逐步内化的事实。
在近世文人笔记或地方志中,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多被赋予“神秘”色彩。例如,浮云先生《畲客风俗》描述到:“囗头即盘瓠像,为畲客之鼻祖,羞为人见,故祭时必在深夜。屏去旁人,黠者假为寐,况窃窥之,始见囗头。”[28]三十一-三十二云和畲民以规避他者的祭祖形式,延续了他们对民族始祖的崇敬之情和自我认同的民族意识。《龙游县志》记载:“至深夜人尽,始取出其红布袋所储之囗头,罗拜之,恶为他人见也。”[29]卷二《地理考·风俗(畲民风俗附)》而民国《丰顺县志》则载有:畲民“有祖遗匹凌画像一幅……止于岁之元日,横挂老屋厅堂中,翌日则收藏,不欲为外人所见。”[17]卷十六《风俗》由此可见,不论是浙江还是广东,以盘瓠为主祭对象的仪式活动,在部分畲族聚居区都是比较隐秘的族内行为。此外,何子星《畲民调查记》所载丽水畲族“醮名……遍邀亲族,于深夜设祖像(即端刻囗头的木杖),相与罗拜。醮毕,男女杂坐,燕饮相贺,答歌为乐”[30]六十一,也证明封闭的族内祭祀原则不仅保证了盘瓠神话的生命力,也是维系畲民自我认同的有效机制。正和刘吉昌所言“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身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31]33是民族认同的关键一样,畲族对盘瓠神话的隐性展演,就是在保障自我文化独特性与整体性的倾向上,形成了民族成员间的文化认可与共识,从而将插花式的点状民族聚居区连接成一张庞大且紧密的认同关系网。
畲族作家雷德和在短篇小说《红祖图》[32]中以写实手法向我们呈现了一幅“生命即祖图”的壮丽画卷。其文写到,包括口述、图文与仪式在内的一切有关盘瓠的民族传统都在“犬辱文化”的背景下,为一些汉民知识分子、豪强恶霸和被前者鼓动的普通人所利用,于彼此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不断强化主客、畲汉间的不平等,促使畲族社会地位急剧下滑,成为弱者中的弱者,并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中后期达到矛盾的顶峰。乾隆四十年(1775),青田士子钟正芳为争科考权而上书青田县,并得到处州(今丽水市)畲民的广泛呼应。时任青田县令吴楚椿认为“畲民本属海琼澶良……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为异类,阻其上进之,偕是草野之横议也。”[33]卷二十九《艺文志中·文编三》而浙江巡抚阮元的亲自过问,终让处州畲民于嘉庆初年重获科考权,此事后被记于嘉庆八年(1803)颁行的《浙江畲民应试章程》[34]115-116和嘉庆十七年(1812)修订的《学政全书》[35]564。继之而后,包括居住于温州府、福宁府等地的几乎所有畲民士子都以类似方式,通过坚持不懈地上书呈文,也获得了这一丧失已久的正当权利。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记载了一则有关福建巡抚李殿图处理福鼎畲民钟良弼争取科考权的事件[36]卷百四十《国朝宦绩·巡抚》。于此,李殿图不仅严厉批评了歧视畲民考生的行为,还在分析上古神话、比较南方各少数民族情况的同时,将之上升到稳定国家秩序、保障社会公平的层面。
尽管盘瓠神话的畲族演绎并未随着内外、畲汉矛盾的持续加深而出现断层,但畲民对其的矛盾心理却一直存在。正如民国士子雷一声在《蓝氏宗谱》“序”中所言:盘瓠神话“历代典籍均无考……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由是观之,“雷一声的心情是矛盾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他想在《蓝氏宗谱》中删去有关盘瓠的内容,但是,未得到畲民蓝氏家族的允许,因为,积淀在畲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盘瓠传说已经根深蒂固”[14]24。然而,盘瓠神话对民族尊严与利益的历史性损害并未在当代“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彻底净化,相反却在部分畲族学者的民族史追溯中引发强烈反弹,从而出现大力摒弃“盘瓠”的文化思潮。对此,方清云用“群体创伤记忆”加以概括,她认为“个体创伤记忆在经过群体不断重述、传播后,随时间流逝而更加条理化和清晰化,进而超越个体记忆和个体情感体验,沉淀成一种群体对创伤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体验。群体创伤记忆往往会在群体成员知觉或不知觉的情况下,推动族群进行文化重构。”[37]30由是可知,逐层叠加的个体苦难在族群认同的强化下,被渐趋放大为民族创伤,并于民族意识觉醒的当代社会彻底爆发,进而衍生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事件[38]13-14。彭兆荣指出:“社会历史记忆作为族群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族群认同和在特殊情境下的生存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事实’与‘虚构’本身都构成了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要件。”[39]85据此笔者认为,盘瓠神话之所以为部分畲民所摒弃,实是他们面对虚构事实化的不利境遇而做出的选择性遗忘。
总之,盘瓠神话的跨民族跨地域性导致了即便是同一民族,也会产生不同的表述形式和内容,不过,无论这一现代口承神话如何变异,其在畲族社会中的立体演绎始终未曾脱离上述有机公式。目前,在大力开发民族旅游的语境下,以盘瓠神话为代表的畲族文化也逐渐走上舞台,成为打破神秘的现代艺术,可这是否能从根本上消减“犬辱文化”带来的族际矛盾,仍需时间检验,毕竟在当下的畲族文化研究中,盘瓠问题依然处于艰难的破冰期。不过,正如蓝炯熹所言:盘瓠神话“绝不可能是一个人一时的凭空捏造,而只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的精神产品,该产品的生产者是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人群,生产的过程是特定环境中的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的集体创造,是不容轻易更改的家族记忆”,而它“不仅是畲族家族内部所要辨识的问题,也是所有想了解畲族的人们无法规避的问题”[14]25,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1] (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M].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 王宪昭.神话视域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5]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畲族文化研究(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 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畲族高皇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8] 朝戈金.“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5).
[9] 雷光振.景宁金族彩带[J].东方博物,2008(4).
[10] 弘礼.福建少数民族的摩崖文字[J].文物,1960.
[11] 吕立汉,蓝岚,孟令法.浙江畲族民间文献资料价值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12(4).
[12] 钟雷兴.闽东畲族文化全书·谱牒祠堂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3] 陈国强,蓝孝文.崇儒乡畲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4] 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5]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 (明)李玘重.惠州府志[M].陈文献,易贞元,校正.刘梧,纂集.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
[17] (民国)刘禹轮,李唐,等.新修丰顺县志[M].汕头铸字局梅县分局,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
[18]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
[19] 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0] 孟慧英.神话-仪式学派的发生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5).
[21] 蓝明亮.中华畲族哀歌全集[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2.
[22] 丽水地区《畲族志》编纂委员会.丽水地区畲族志[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
[23] 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M].内部发行,1991.
[24]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5] 刘铁梁.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考[EB/OL].(2009-01-10)[2016-08-20].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5&NewsID=3736.
[26]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27] 施联珠,雷文先.畲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28] (清)浮云先生.畲客风俗[M].上海:上海虹口顺成书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
[29] (民国)余绍宋.龙游县志[M].北京:京城印书局,1925.
[30] (民国)何子星.畲民调查记[J].东方杂志,1924年第二十一卷第七号.
[31] 刘吉昌.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4).
[32] 雷德和.红祖图[J].民族文学,1997(2).
[33] (清)吴楚椿.畲民考[M]//(清)卓异侯,陆元和,潘绍诒.处州府志.光绪三年(1877)刻本.
[34] 王逍.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5] (清)童璜,等.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M].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36] (清)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M].正谊书院藏版,道光九年(1829)刻本.
[37] 方清云.少数民族图腾文化重构与启示——对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人类学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2).
[38] 孟令法.畲族图腾星宿考——关于盘瓠形象传统认识的原型批评[D].温州大学,2013.
[39] 彭兆荣.瑶汉盘瓠神话——仪式叙事中的“历史记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5(1).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2-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畲族民间文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5BMZ026);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工程”(09@ZH014)子课题“畲族史诗《高皇歌》”(项目编号:SS2016011)。
孟令法(1988- ),男,江苏沛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与畲族社会文化史。
K890
A
1004-941(2017)01-00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