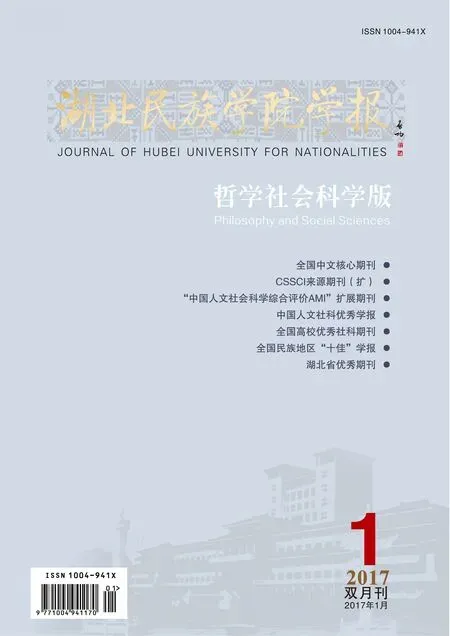改土归流与土民身份转型
——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例
2017-03-07陈文元
陈文元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改土归流与土民身份转型
——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例
陈文元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改土归流不仅包括土司,也包括广大土民。革除土司后,流官的行政干预与移民运动引发了土民社会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土民身份转型是土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为政治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的转型。土民身份转型,是地方社会变革的动态转变,反映了地方社会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历史过程。
改土归流;土民社会;身份;转型
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土家族地区的土司也逐渐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明清时期湖广地区的土家族四大土司容美土司、桑植土司、永顺土司、保靖土司等土司成为一些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容美土司位于鄂西南,为土家族的聚居地之一。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容美土司被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之后,容美土司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土民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土民社会发生了转型。土民社会转型的方面有很多,笔者拟以容美土司为研究对象,以土民身份转型为突破口,并通过对历史时期容美土司的中心区域进行田野调查与相关历史文献的研读,从土民的层面来论述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转型,探讨土民身份转型背后土家族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
一、改土归流与流官治理
清朝雍正年间,清廷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就湖广地区而言,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桑植(雍正四年)、永顺(雍正六年)、保靖(雍正七年)等湘西土司相继被改土归流,与容美土司同处鄂西南的施州卫亦于雍正六年(1728年)被裁撤。以容美土司为首的鄂西南众多土司处在被改土归流的边缘。容美土司是鄂西南最大的土司,改土归流首当其冲。雍正十一年(1733年),湖广总督迈柱向雍正皇帝进言:“楚北各土司,拟应尽行改土归流”[1],雍正皇帝同意其进言,准予着手对容美等鄂西南众土司改土归流。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迈柱在容美土司周边布置兵力,准备武力改土归流。同时,派人告知容美末代土司田旻如进京面圣陈述。是时,容美边民逃跑,中府土民“私传相约”[2],密谋暴动。不久,五峰司长官张彤柱率众倒戈,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田旻如于当年十二月自缢于平山万全洞。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安陆府通判毛峻德奉命进入容美土司地区,安抚土民及维持社会安定。之后,“忠峒田光祖等纠合(鄂西南)十五土司,呈请改流”[3]。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析容美土司地区为鹤峰州、长乐县,属新设宜昌府管辖。[4]任命毛峻德为鹤峰州第一任知州[5],张会谷为长乐县第一任知县[6]。至此,由元至清,延续了近四百年的容美土司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土民也由之前的土司治理时代进入到流官治理时代。
清廷废除容美土司建置,清除田氏家族势力,从政治、军事上对容美土司社会进行改土归流,主要涉及容美土司上层社会,并未对土民社会有较多触及。之后,清廷派遣的流官依据朝廷诏令,实施了一些社会治理措施,促使了土民社会演变。第一,改土归流后,官方废除了“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禁令,大批外地人口,特别是汉族移民,来容美土司地区垦荒种植,众多山林土地被开发,土民与移民混居,地区界限被打破;第二,流官开始清查户口与田地,分与土民耕种。鹤峰州“查土民共1921户,男妇共10367名口。”[7]“将土司之田入官田产”[8],“鹤峰州成熟土地654顷,长乐县成熟土地183顷”[9]。官方鼓励土民恢复生产,实行报认升科,土民可依据自身劳力多开垦土地。水田以六年起科,旱地以十年起科。清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免了鹤峰州、长乐县雍正十二年、十三年及乾隆元年三年的赋税。毛峻德还发布了《劝民告条》《劝民蓄粪》《劝积贮》等劝农告示,引进汉人农耕技术与经验,引导土民恢复发展生产;第三,派遣流官为汉人身份,他们依据朝廷诏令推行封建正统文化礼仪,传播汉文化习俗,鹤峰州第一任知州毛峻德还发布《禁乘丧讹诈》《禁肃内外》《禁端公邪术》等文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土民社会的一些风俗习惯;第四,官方积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土司时期,除土司家族子弟外,广大土民皆禁止入学。改土归流后,鹤峰州学宫随即创办,官方还鼓励民间办学,并给予补助,土民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官方通过行政手段对土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多领域、多层面的改土归流,引发了土民社会变革,促使土民社会转型。土民身份转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土民身份转型的表现
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民身份逐渐在流官的行政干预与区域社会的发展中发生改变,土民原有的社会形态、意识结构逐渐被随之而来的“大清”、汉人习俗、农耕经济等包含有外来社会意识的元素所取代,土民身份逐渐发生转变。
(一)政治身份:从“土王”的子民到“大清”的子民
明朝廷近三百年的政治统治,“经过容美土司的经营及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容美土司土官土民逐步建构起效忠于中央和国家的原生情感”[10],王朝的构建与地域的积累,使容美土司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国家认同。但这种认同主要存在于土司层面,土民是直接隶属于土司。
土司时期,在土司境内,土司是“土皇帝”,拥有对土民的绝对控制权。土司、土民之间身份有别,有着严格的等级。“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11]可以认为,土民是土司的“私有财产”,是他治下的“百姓”。土民接受土司管理,为土司提供赋役,并为土司效力,跟随土司进行军事争斗。中央朝廷对土司的册封与土司制度的完善,加上土司家族势力的积累与地区根基的日益牢固,促使了土司与土民之间有着强烈的隶属关系,土民的身份为“土王”的子民。土司与土民之间构建了一个牢固的政治体系,土民对土司具有强烈的政治从属性。今鹤峰县境流传的诸多“田土王”的传说中很多都带有对“田土王”权威的形象描述,内中蕴含了土民对土司敬畏与依附的历史遗迹因子。
明清递嬗之际,容美土司受战乱影响,元气大伤,土民社会凋敝,但在改土归流前,土司与土民仍处在同一个政治体系之内。清廷定鼎中原,尚未控制鄂西南时,南明永历政权尚存,鄂西南地区有夔东十三家势力盘踞,容美土司即在鄂西南众多土司中较早归顺清廷。“(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辛丑二十四日,湖广容美土司田吉麟(田既霖),以所部二万投诚。上(顺治帝)嘉之,命所司速叙。”[12]这里的“所部二万”自然包含土民。但土司带领土民归顺中央朝廷只是土司层面的政治臣属变换,广大土民依然直属于土司的控制与管理,土民政治身份并未发生改变。
然而,改土归流促使了这一状况的改变。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被废除,清廷派遣流官担任鹤峰州、长乐县两地的行政长官,修筑府州县城。“改土归流后,进入到湖广土家族区域的流官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筑府州县城,为建立自己的统治,树立自身的权威,他们异地选址重建城池,目的是削弱土司王城中的物化象征,提升皇权的威力。”[13]不过,与湖广其他府州县不同的是,清廷仍将鹤峰州城设置于曾经为容美土司中府的旧址。由此,象征土司王权的土司城已变成了象征皇权的鹤峰州城。同时,流官开始清查土地、人口,土民编籍入户,并设以保甲制度管理土民社会,把土民纳入到国家行政一体化建设当中,与主流汉族社会对接。这一过程是土司权威衰落与王朝权威构建的过程。土民直接为中央朝廷输赋应役,接受中央朝廷的礼仪与意识形态教育。这些举措无疑加深了土民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自此脱离了土司的“束缚”,正式成为了大清的子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与“父母官”,他们不再是土司的子民。土民社会的上层控制力量变成了国家,变成了“大清”。土司权威演变成了王朝权威。现鹤峰当地流传了许多对“田土王”的污名化描述,*譬如“田土王有势力啊,别人接媳妇他要睡三天,生了小娃儿他要吃三天奶;田土王问你姓什么,你说不姓田把你杀哒,你只能说你也姓田,‘野姓田’,他卡哒你,搜山,问到你姓田就不杀。”——讲述人:FFL,男,80岁,土家族,鹤峰县容美镇庙湾村民。从侧面反映了土民对流官的接纳和对容美土司的背弃。改土归流使土司原有的政治经济组织被废除,改而实行中原汉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改变让他们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随着清廷政治统治的日渐稳定,土民对清廷的认同也逐渐产生并加深,促使了他们对清廷的国家认同意识更深,使土民的政治身份正式转型。
(二)社会身份:从“土著”到“移民”
容美土司时期,曾建有中府(司署)、北府、南府、平山爵府、帅府等众多府邸。这些府邸区域既是土司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土民生活较为集中的区域。为行文的方便,结合自身田野调查,笔者拟以平山爵府作为叙述的地域对象。
平山开发较早,于明朝万历年间容美土司第八代第十一任司主田楚产营建。清人顾彩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二月初四至七月初五期间游历容美达五个月,之后写下了《容美纪游》。该纪游较为具体地描绘了改土归流前夕容美土司社会的发展情况,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顾彩在平山爵府居住了二十余日,这里摘取描写平山的部分内容:
宣慰司(平山)行署在平山街,其靠山曰“上平山”,插入霄汉,此犹其(中)平山也。司暑大街,巨石铺砌,可行十马;西尽水砂坪,东至小昆仑,长六里,居民落落,多树桃柳;诸郞君读书处在槿树园;下坡为戏房,乃优人教歌处;其西街尽头,下皆陡壁深涧,恐行者失足,以竹笆插柳,此司前大略也。行署中有怪,君(容美土司田舜年)不恒居于内,就大堂西名“延春园”以为书室,其楼曰“天兴”,初五日张乐宴钦于此。后街长里许,民居栉比,俱以粉为业,有织纴者。[14]
从上文中“西尽水砂坪,东至小昆仑,长六里,居民落落,多树桃柳”“后街长里许,民居栉比,俱以粉为业,有织纴者”可以看出,当时平山生活着众多土民,应该很多都是世代居住于此。可以认为,在清初,平山作为土司爵府所在地,该地土民的居住应当是稳固而持久的,他们的地域认同也是强烈的:他们是世居于此的“土著”。此时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距离雍正十一年(1733年)容美土司改土归流刚好30年。
现今,平山为鹤峰县容美镇屏山村,辖10个村民小组,360 户,总人口1300多人。全村土家族人口最多,其次还包括少量的汉族、蒙古族等。土家族姓氏主要有田、李、向、易、张、余、陈、王,以田姓居多。*材料由屏山村村民居委会提供及笔者调查所得。对照历史文献记载,现平山居民应该多是当年土民的后裔。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平山居民对改土归流前的历史记忆出现非常一致的“集体失忆”——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所表述出来的都是移民过来的,对于改土归流前的那段历史为空白,是在改土归流之后来的,对于“田土王”的记忆也多为负面性的描述。他们流传下来的口述史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与文献记载有较大偏差。而此类偏差更是反应在一些民间文献上。现平山上有一块年代较久的尚姓墓碑,墓碑的碑文记载了尚氏家族从四川迁移到鹤峰,“尚美三公”落业鹤峰,来到平山。这里摘录尚姓墓碑部分内容:
来历序
今夫人之宗祖大矣。后裔绳绳,无非木之本水之源,子孙昆是祖之德宗之攻。想我祖西蜀之人也,妥局大梨树土地。自尚美三公落业鹤邑创造,卒始祖之求由未传某号某名,后代之生晚不知谁宗谁族,夫竟作无主之坟,尽是他乡之鬼,先祖自此而废没,后人祭祀无凭依,且宗派于兹以杂乱,如是则遗传亦以大矣。避及宗禹公向门为婿,混乱向姓,今复更尚原以尊宗重祖之意耳。思我伯父职受昌末,为人忠厚,所娶三妻终无一子,虽胞弟之子承宗,视如比儿,但恐失烟祀祖名,后学前车,是以合族集谪爰修竖宗牌,后之人祭祀有宗,挂扫有所,派行有序,如是伯父之德更亦夫。派行并列:宗祖永开基,荣华富贵齐。兴隆光万世,自有凤来仪。*据考证该墓碑为清代墓碑,具体建造年月不详,推测为清乾隆年间建造,墓碑遗址比一般墓碑大得多,碑上雕刻装饰不同寻常,墓碑主人生前或为当地显赫家族人士。原墓碑尚存,文字为竖排,没有标点符号,本文在此摘录了部分。现存于鹤峰县容美镇屏山村4组庙坪。
笔者在平山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也有村民说祖上一直就是平山的,是最早来平山的,是和“田土王”一路来的(意为同时进入鹤峰)。这里引用当地村民的一段口述以作阐释:
我们就是平山人,来这儿有好久哒,是最早来平山的,有几百年哒,宗上派别:“宗大定邦国,开业元正秀,文明传宣绪,………(后一句讲述者记不清)”。按这个派别来看,现在已经十四代哒。孙儿就是传字派。我们跟田土王一起来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儿的。我们的进山公公就宗字派,宗字派之前的祖上湖南慈利后山,那里有祠堂,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我自己没去过。我们不是野姓田,我们就姓田,但不跟田土王一个宗派,姓范的田土王就鼓哒(意为威吓哄骗)他们姓田。进山公公一起有8弟兄来鹤峰,进山公公来平山了。我们是土家族,姓田的是土家族,我们是少数民族,政府说田、向、覃、唐都是土家族。*讲述人:TWC,男,67岁,土家族,鹤峰县容美镇屏山村民。
前文清代墓碑中的碑刻内容显示为“移民”进入鹤峰。此处讲述者也声称他们是从湖南慈利迁移到此,已经是第14代,但推算下来与改土归流的时间相印证,他们脑海中的“最早”“就是平山人”等表述体现出较强的改土归流后移民进入鹤峰的倾向。两类文献的“碰撞”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情境。我们从民间文献中也能察觉出其无法逃避的改土归流“历史印迹”。相比于民间文献,我们不必过于关注文本的真实性,而应该剖析文本背后的社会脉络与个人情感,以及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15]改土归流对土民社会的影响是剧烈而深远的。“从短时间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16]当改土归流来临时,在急促的“短时间”内“国家携带政治资本进入社区这一民间场域,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全面颠覆了土民社会,在此重建新的统治秩序”[17],他们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改变。它迫使土民选择忘却过去那段“土著蛮夷”史,改变地缘关系,脱离边缘,学习汉文化,重新建构自己的家族史——移民史,进行社会身份的转型,作为他们与大传统相适应而所作的方式。清廷对容美土司地区的政治倾覆与随之而来的土民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颠覆,是整个土民社会进入编户社会、边缘社会进入主流社会的彻底转变过程。[18]从边缘社会跨入主流社会,在这一“较长的时段”里“集体失忆”性丢掉过去的历史传统的过程是艰难、痛苦而漫长的,并非在短时间内实现转换,经历几代人的“磨合”,“在国家权力的强力作用下,平山社区的村民被迫完成了从制度、身份到文化的全面转型”[19]。社会身份转型是土民社会转型最为直接的一个方面,也是土民正式与土司之间进行彻底的政治脱离表现。
(三)文化身份:从“土俗”到“汉俗”
我们可从改土归流之后鹤峰州的一些文告中探析容美土司时期土民生活习俗的具体记载。“乃州属向来土俗,无论亲疏,即外来行客,一至其家,辄入内室,甚而坐近卧榻,男女交谈,毫无避忌。”[20]表明改土归流前土民热情好客,男女交往不受汉俗约束。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土家族人这种热情好客的遗风。“旧日土民无子,无论异姓,即立为子。有名系祖孙父子,实二三姓者”,“旧日土民无子,即以婿为子”。[20]表明土家族在当时尚没有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家族化观念。“老者冠以青帕,少者毡帽而已。衣服以粗兰布为之,履则以草柳皮织之,冠、婚、丧、祭纯用酾酒。其俗信巫尚鬼,事向王公安等神,以宿晨傩愿为要务,敬巫师赛神愿,吹牛角跳丈鼓。”[21]表明土民自身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意识。
即便如此,在改土归流前夕,汉文化在土民社会中的影响已经产生,在容美土司上层社会则更为强烈。明朝建立后,在鄂西南腹地设置了施州卫、大田所,并从外地迁入了三万多名汉族移民,经过近三百年的政治统治,“卫所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互动过程中,移民与土著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呈现出‘卫所移民土家化,土著土家人汉化’的局面”[22],而明代中期以后,卫所屯政破败,民逃夷地时有发生,产生了“夷汉互融”局面,“土俗”中已有“汉俗”的因子。容美土司地处鄂西南前端,与施州卫、建始县、巴东县等地区接壤,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机会更多。明末清初,容美土司趁乱世扩张领地、掠夺人口,同时接纳外地逃难汉族民众、拥明势力,以及与大顺农民军余部的交互等过程中客观上也促使了土家族与汉族的交流。[23]
改土归流后,“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境况被打破,大量汉族移民进入鹤峰州、长乐县,流官又对土民的文化习俗进行了改制与禁止,推崇汉俗,汉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进入土民社会,土民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建宗祠、修族谱。改土归流以前,土民“家不祀生民之祖先,子不奉生身之考妣”,但奉廪君、向王天子、田好汉等。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鹤峰州、长乐县以及流官的推动,土民社会家族观念强化,效仿汉族建宗祠、供本祖、设神龛、修族谱,进行家族化传承。笔者田野调查期间,发现众多家族修有族谱,且多有攀附历史名士,可谓对汉文化认同的一个侧面反映;二是说汉话,改汉名,习汉俗。说汉话并非在改土归流之后开始。“明代以前,清江流域土家族所使用的语言虽然有土家语的底层成分,但总体上已经转用成汉语了。”[24]但改土归流之后,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与流官的推动,土民习汉语日盛,现今鄂西南地区流传“打他(她)做么斯,才这大个娃儿,汉话都不懂!”这句俗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的使用成为土民人生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体现。官府的推动以及土民对加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与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原本在改土归流前只有土司阶层使用汉姓汉名的情况在改土归流之后广泛在土民社会普及。《鹤峰州志》中记载的“则彬彬焉,与中土无异”[25],这一过程反映了土民文化身份发生了转型。
三、土民身份转型与民族认同和社会转型
一方面,改土归流促使土民的身份发生转型,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反映了地方社会变革的动态转变。具体到土民社会当中,从文化身份转型我们看到了土民为改变文化形象、踏入主流社会的努力与愿望,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认同,但土民对清廷、流官的迎合与接纳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对“田土王”的背弃,并不意味着对汉人身份的完全认同,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不可同一而语,二者也并非协调一致。“政府倡导的改流虽为以汉易土,然而,这一进程本身又导致了土家或本土身份与认同的高涨。”[26]从改土归流后日益明显的“土”“客”之分,土家族文化受汉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的传承与延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与1956年土家族的民族识别、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可以看出土家族人对自我身份的长期坚守。
另一方面,“改土归流直接导致了土家族土司的最终覆亡,它标志着土家族历史发展上一个漫长的旧时代的结束”。[27]改土归流不仅仅只是王朝权威的渗透与制度的更迭。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地域社会的演变与历史建构过程,对土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28]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新的耕作技术,流官的劝导与行政干预,促使大量土地被开垦与农田水利建设,而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物种的引进、汉人社会精耕细作方式的采用改变了土民社会原有的游耕经济方式[29]与民族格局、社会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汉文化的强势进入与封建正统礼仪的确立,这些因素从多层面、多方位改变了土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引发土民社会的转型,土家族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土民身份转型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土司制度的割据性与中央王朝的大统一相悖,改土归流是中央王朝的政治推进,具有历史必然;王朝开拓、政治一统与土司阶层存在着矛盾,移民的进入,大量山林土地被开发,土民生存空间被挤占,移民与土民在地方资源上存在着利益纠纷。当然,土民身份转型并非由改土归流及其后流官社会改革引发而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充满了对抗、妥协与互动,包含了土司政治的残存影响与国家政治权力渗透而所表现出来的族群历史与文化认同。
[1] 朱批笔谕54册[M]//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984:36.
[2] 毛峻德.容美司改土记略[M]//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984:424.
[3] 松林等.施南府志·卷二:沿革[M].1871年刻本.
[4] 聂光銮.宜昌府志·卷三:沿革[M].1866年刻本.
[5] 毛峻德.鹤峰州志·卷下:职官[M].1741年刻本.
[6] 李焕春,等.长乐县志·卷六:职官表[M].1852年刻本.
[7] 毛峻德.鹤峰州志·卷下:户口[M].1741年刻本.
[8] 吉钟颖,等.鹤峰州志·卷五:赋役[M].1822年刻本.
[9] 毛峻德.鹤峰州志·卷上:圣制[M].1741年刻本.
[10] 葛政委.祖先再造与国家认同——容美土司《田氏族谱》和《蹇氏族谱》的人类学解读[J].三峡论坛,2013(6):60-65.
[11] 赵翼.檐曝杂记·卷四:黔中倮俗[M]//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67.
[12] 蒋良骐.东华录[M]//王先谦.东华录选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9:105.
[13] 郗玉松.改土归流与清代湖广土家族地区城市的重建——从象征王权的土司城到象征皇权的府州县城[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2):5-10.
[14] 顾彩.容美纪游[M]//《容美纪游》整理小组.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64.
[15]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3.
[1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 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5.
[17] 吴雪梅.回归边缘:清代一个土家族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87.
[18] 雷翔.民间视角:清代土家族社会的演变——景阳河社区个案研究[M]//刘伦文,谭志满.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土家族乡村社区调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90.
[19] 向晶,周绍东.历史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对鹤峰平山社区口述史的解读[J].铜仁学院学报,2010(4):.
[20] 毛峻德.鹤峰州志·卷下:风俗[M].1741年刻本.
[21] 山羊隘沿革纪略[M]//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984:491.
[22] 杨洪林.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39.
[23] 杨洪林,陈文元.论明清之交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30(3).
[24] 谭志满.族际交流与土家族语言的历史变迁——以鄂西南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6).
[25] 吉钟颖,等.鹤峰州志·卷六:风俗志[M].1822年刻本.
[26] 岳小国,梁艳麟.试论土司的“地方化”与“国家化”——以鄂西地区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5,26(2).
[27] 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37.
[28] 段超.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J].民族研究,2001(4).
[29] 雷翔.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5(2).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2-0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CMZ200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5Y101)。
陈文元(1989- ),男,湖北蕲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
C952
A
1004-941(2017)01-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