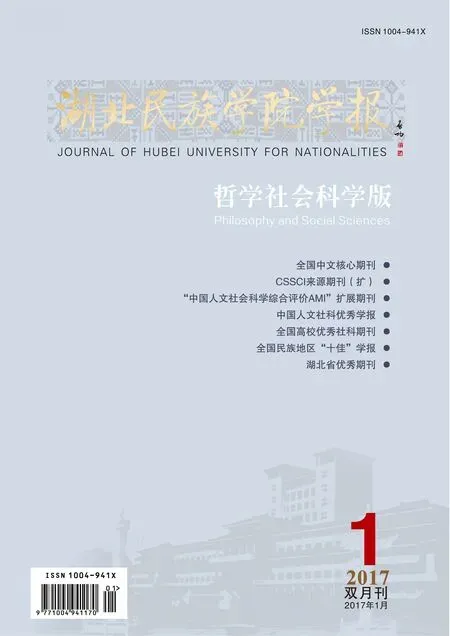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
2017-03-07黎海波
黎海波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
黎海波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对于跨越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群体”,基于其与“周边国家的纽带作用”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优势存量”。然而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相关概念的模糊与混用并不利于其与“一带一路”的逻辑连接。因此,有必要对跨界民族概念进行重新探讨。基于其客体指向与主体形成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围绕上述概念而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对于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界定最终还是要结合研究的实际对象、具体情境与内容来确定。结合中国知网的统计分析来看,“跨国民族”这一概念的认可度是最低的。结合已有研究实际来看,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仍主要是毗邻国界的同一民族。在明确了跨界民族的内涵及其特征之后,才更有利于其与“一带一路”的逻辑连接。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要求以及战略实施来看,跨界民族概念的使用是最为契合的。它既突出了地域与人文等联通优势,又强调了其国家认同基础。
“一带一路”;跨界民族;主体形成;客体指向;逻辑连接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的战略倡议与构想。“一带一路”覆盖了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和云南等主要民族省区和大部分民族聚居区,成为当前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机遇。同时,民族地区也构成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1]结合跨界民族的族际与国际(周边)关系双重内涵来看,我国不仅民族成分丰富,而且邻国众多,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接壤。因此,我国不仅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成了一个多跨界民族国家。总体而言,我国共有朝鲜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苗族、门巴族和壮族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或相近)而居,形成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地区跨越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群体”,基于其与“周边国家的纽带作用”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存量”。[2]然而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相关概念的模糊与混用并不利于其与“一带一路”的逻辑连接。跨境民族概念虽然突出了主动的跨境交往性,但是容易导致国家认同的淡化或缺失。跨国民族概念虽然强调了国家认同,但是却难以突出跨界民族的地域与人文等联通优势。因此,有必要对跨界民族概念进行重新探讨。
对于跨越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群体”,我国学术界主要是民族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了“跨境民族”“跨界民族”和“跨国民族”等不同的概念来指称、表述和界定。总体而言,基于其客体指向与主体形成等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围绕上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至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一、“跨界民族”研究中的客体指向与概念界定
“跨界民族”研究中的客体指向,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客体——跨境、跨界或跨国民族涵盖范围的不同理解与界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范宏贵在探讨了中越之间壮族与岱族、侬族之间的关系时,首次使用了“跨境民族”这一概念。[3]不过,并未对它进行明确界定。尽管从理论上而言,同一种语言中的名称与概念,其关系应是单参照性的,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一个概念、几个名称术语的“同义”现象。[4]此后,姜永兴与胡起望等相继沿用并拓展了这一概念。
姜永兴认为,跨境民族实质上就是分别居于国家边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5]这一概念界定,主要突出了跨境民族的跨界性和毗邻性,有点类似于后人对跨界民族的定义。严庆也是基于“毗邻而居”的这一特性,将此类民族概括为“实界”跨界民族。[6]
胡起望则认为,跨境民族是指分别定居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保有了一定的传统特色和认同的同一民族。此外,他还对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跨界民族是指在相邻的两国间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尽管其民族聚居地虽为政治国界所分割,但他们在自然或文化地理分布上基本是连成一片的。而跨境民族,则是指跨国境而居住的同一民族,他们的地理分布可能并不连成一片,有的甚至是从居住的第二国,迁移到第三国或第四国,甚至还可能远渡重洋,构成跨海洋而居住的同源民族。[7]由此可见,这一观点将跨界民族实际上等同于姜永兴所界定的跨境民族,其实质都是跨越边界而居,相互毗邻。而胡起望所界定的跨境民族的范围更广,包括了跨界民族,相当于后来的跨国民族或跨国移民族群这一概念。
金春子、王建民以及葛公尚等倾向于使用“跨界民族”这一概念。金春子和王建民认为,跨界民族是指基于一定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居于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同一民族。对于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概念的区别,他们认为二者的意思大致差不多,如果要区分的话,“界”(Border)比“境”(Area)显然更为确切一些。这是因为“境”一般是指一定的区域,而“界”则是明确而严格的国家边界线。[8]
“跨国民族”这一概念是由马曼丽首次明确提出的。她认为,跨国民族就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居于国界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具有相同渊源的、基本保持着原有民族认同的人们群体的一种指称和表述。之所以要强调使用这一概念,马曼丽认为主要是基于跨国民族所涵盖和囊括的范围更广,可以弥补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这样两个概念无法涵盖跨越数国,或者漂洋过海,或不毗邻的跨国民族之缺陷。[9]由此可见,跨国民族就包括了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这与严庆所提出的“虚界”跨界民族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这是因为“虚界”跨界民族的成员,他们之间要么是远隔大洲或大洋,要么是被一个或数个国家所隔开,并没有现实的毗邻边界可言。[10]
此外,周建新还特意强调了跨国民族概念中的“国”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归属。[11]在跨界民族的认同上,本身就包含有政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双重成分,而且其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而这正是基于“界”的影响,即国家边界与族群以及文化边界的交错和张力所致。如果“跨界民族”仅仅存在单一的国家认同,其族群与文化联系和影响就仅仅局限于国界之内,那么它就并不成为跨界民族。因此,如果仅仅突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认同,那么更多的呈现的只是这一概念的政治意义,而并非学术意义。对于跨界民族的认同,其“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同时拥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甚至包括宗教认同)等不同形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在个体的认同层次结构中,把何种认同归属置于优先的级序”。[12]因此,这三个概念的争议与分歧主要还是在于其涵盖范围上。
从其涵盖范围而言,涉及边疆、边境与边界这三个概念。边疆,是指一个国家较为边远的靠近国界的地区[13],既是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也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管理区域。[14]边疆这一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边疆,是指分布在边界沿线的省区,其外界是国界线,其内界则是边疆省区的行政界线。而狭义上的边疆,是相对于广义边疆的“靠内地区”而言的,专指边境地区,即指沿边界线分布的县级政区,更为精准而言,则指靠近边界线20公里以内的区域。[15]这里对边境范围的界定显然过于绝对。边界,从国际法意义而言,就是指国家的边界[16],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标定疆域范围的界线。[17]边境,则是指紧靠边界线两边的一定的区域。[18]
当今世界各国大都会在边界线内侧划出一定宽度的区域,并在此区域内实行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其划定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按照边界线内侧一定纵深的区域来划定;其二是以边境线内侧的行政区域来划定。[19]由此可见,边境区域并没有统一的面积规定,而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我国在边境的划定上,实际上也是两种划定方法兼而有之。由国家兴边富民(振兴边境、富裕边民)行动来看,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主要包括136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个边境团场。[20]
由此可见,边疆范围最广,边境其次,而边界则最小,也最为精确。而且,即使对于两个相邻国家而言,其各自的边疆与边境范围并不相同,但是其边界一定是相同的。因此,从单纯的地理或法律界限而言,“跨界”可谓是最为准确的。此外,从跨界民族的活动范围而言,其范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于边境地区,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边界和边境,也可跨越边疆甚至覆盖更大的范围。因此,跨境民族的概念既不能体现出准确的国界分割,也并不能涵盖其跨越边境之外的范围。而跨界民族则既可体现出国界的准确性分割与毗邻性,又能在国家或边疆的范围内灵活地涵盖其伸缩范围。虽然跨国也能体现出国界的准确分割性,但其范围过大,容易使研究对象丧失“毗邻性”这一特点,从而可以笼统地涵盖所有的跨国移民和散居者。最后,结合“跨境”而言,“境”还涉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就将从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从中国大陆前往台湾地区都归于“出境”。因此,跨境一词的使用也容易引起混乱和歧义。
二、“跨界民族”研究中的主体形成与概念界定
“跨界民族”研究中的主体形成,是指研究者对跨界民族形成特性与原因的不同理解与探讨,如跨界民族是被动形成,还是主动形成;是政治因素所导致,还是基于经济原因或社会原因等。
葛公尚认为,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为现代政治边界所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同一民族。跨界民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与特征:其一,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边界所分隔;其二,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边界所分割。[21]这里主要是突出了导致跨界民族形成的国家因素,实质上强调的是跨界民族的一种被动形成特性与原因。
考虑到不同课程的难易程度、重要程度不同;学生在不同时间段学习效率也不同,为使课程安排更加科学合理,可规定“软约束”条件如下:
跨界民族的形成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其一是从国家的分割性而言,政治边界分开了文化民族;其二是从民族的迁移性(基于“推拉”等因素,有主动迁移,也有被动迁移,但与被动的国界分割相比而言,更显“主动性”)而言,是文化民族跨越了政治边界。当然,这两方面的因素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跨界民族的形成也是基于二者合力的结果。结合跨界民族的形成历史与原因来看,虽然国家边界分割是主导,但是单纯地强调国家因素似乎有些狭义。即使是对于国家主导所形成的跨界民族,其中也可能包含有单向或双向迁移和流动的个人或族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内以及全球化的推动之下,跨界民族的主动跨界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曹兴对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以及跨国民族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将跨界民族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跨界民族,是指一切因政治边界与文化民族的分布不相吻合而跨界居住的民族,这主要是由国家边界分隔所导致的。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了为国家边界所分隔、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了主动迁移而跨界而居的民族。他们是在国家分隔和民族迁移双重作用之下的产物。而跨国民族和跨境民族与狭义的跨界民族相比,则是民族主动迁移和跨界的产物。跨境民族是指某一族群从一国迁徙到他国(并非毗邻边界)而形成的。跨国民族范围更广,泛指跨居两国或多国的民族。只有地处两国或两国以上交界地区的才是跨界民族,否则的话就只能是跨国民族或跨境民族。[22]由此可见,曹兴对于跨界民族的界定主要也是突出其毗邻性。此外,他又特意强调,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在于其是否跨界而居,而是在于其是主动跨境还是被动跨界。[23]因此,跨界民族并不包括那些“主动跨国界的移民”。[24]这一判断标准可能对世界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对于我国跨界民族的实际研究而言,是较为困难的。因为在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中主要是针对毗邻(虽不严格相邻,也相近)的跨界民族进行的,而往往没有确切区分(实际上也难以区分)这些民族是纯粹的主动跨境还是被动跨界。即使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分割出了跨界民族,但这也并不能阻隔跨界民族之间的迁移与交往。对于现在我国的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研究而言,族群间的迁移、流动、交往及其影响则正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即使对于“主动跨境”的移民而言,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移出的移民回流的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
三、“跨界民族”研究中的实际使用与概念界定
(一)对相关概念实际使用状况的统计
对于“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这样三个概念的实际使用情况,笔者结合中国知网(CNKI),以1980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为界,分别以上述三个概念为篇名(精确),对其进行了检索统计,具体结果见下表。
结合上述统计来看,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跨界民族”所涉论文最多,“跨境民族”其次,“跨国民族”最少;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跨界民族”所涉论文最多,“跨境民族”其次,“跨国民族”最少;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一样多,“跨国民族”最少(而且,在“跨国民族”所涉博士论文库的两篇文章中,其中有一篇为博士后研究报告)。结合这一统计数量的对比来看,学术界对“跨国民族”这一概念的认可度是最低的。
(二)实际使用倾向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的实际使用中,笔者发现“跨界”与“跨境”这两个概念在跨界民族地区通常是混用的,其意义基本相同。如在内蒙古室韦苏木额尔古纳河段调研时,笔者就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标语:“须跟群放牧,严防牲畜越境”、“为了您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幸福,请勿越界”。这里显然是把“跨界”与“跨境”等同起来。
在学术研究的实际使用中,尽管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这样两个概念仍呈现出并驾齐驱的势头,但在一些代表性论著方面,跨界民族概念的认可度却逐步居上。如葛公尚、金炳镐、王建民和吴楚克等学者在其论著中都是使用跨界民族这一概念。最为典型的是云南大学的刘稚教授,她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申旭与刘稚合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使用的是“跨境民族”这一概念,而在《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则改用“跨界民族”这一概念。
“所有概念,包括精神概念,均有多样含义,只能在具体的政治语境中方能理解。”[25]对于政治概念是这样,对于其他概念也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理解与使用。因此,对于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界定,最终还是要结合研究的实际对象、具体情境和内容来确定。
结合已有的研究实际来看,除了石茂明的专著《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属于真正的“跨国”民族研究之外,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仍主要限于毗邻(有的虽不严格相邻,但也相近)国界的同一民族。跨国民族这一概念虽然涵盖范围较广,但也容易引起研究对象的不确定和空泛。对于跨国民族研究而言,严格地说来它应该属于国际移民或侨民研究的范畴和领域,这是有别于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研究的。[26]或者也可将其归入跨国移民族群这一研究领域。
四、跨界民族的概念界定及其与“一带一路”的逻辑连接
综合以上讨论和分析,结合其客体指向与主体形成,基于实际研究对象与内容的需要,笔者将“跨界民族”界定为:跨界民族是指由于国家分割或自我迁移而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有的虽不严格相邻,但也相近),保留有一定的文化认同,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与互动的同一民族。因此,跨界民族具备三个特征:其一,基于族群渊源而保留有一定的文化认同;其二,基于地域和文化的相近而保留有一定的交流与互动;其三,基于清晰的国界划分而具有明确的国籍。
在明确了跨界民族的这一内涵及其特征之后,才更有利于其与“一带一路”的逻辑连接。
(一)从“一带一路”的战略要求而言[27],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跨界民族为之做什么?或者说跨界民族能够为之做什么?
首先,跨界民族基于地域和文化的相近而保留有一定的交流与互动,因此他们在与周边邻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如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是新疆跨界民族与周边邻国进行经贸往来与合作的重要桥梁。结合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05年以来,这一口岸每年的货运量都是在 45 万吨以上,2010年更是超过了1000万吨。[28]
其次,跨界民族基于族群渊源而保留有一定的文化认同,由于语言相通、宗教文化相同以及习俗相近等,虽然处于不同国家,但其作为同源民族所具有的亲缘、族缘以及神缘等关系依然保持和发展着,从而成为他们之间以及各自所在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在关联和重要动力。
再次,跨界民族的积极参与可以有效推动跨界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跨界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对于边境互动和跨界民族流动的治理主要是通过边境口岸和关卡等来实施管控的。这种官方正规的管控模式只是对于城镇边民和跨界民族的互动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对于山区村社跨界民族的无序流动却往往无能为力。跨界民族村社作为基层的管理组织,与基层跨界民族成员最为贴近。跨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应充分发挥跨界民族成员和村社基层组织的作用。
综上所言,跨界民族对于推动“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以及社会治理等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而言,跨界民族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
跨界民族在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跨界无序流动(三非人员、跨界通婚、边民迁出与回流等),跨国犯罪(跨国暴力恐怖活动、贩毒、走私和人口拐卖等),宗教渗透,全球化与市场化对跨界民族经济的冲击等。[29]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再加上境外敌对势力对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利用与炒作等,跨界民族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虽然跨界民族基于清晰的国界划分而具有明确的国籍,但这只是构成了他们国家认同的基础。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由于国际因素的参照和影响等,是处于复合层级结构之中和动态发展之中的。因此,应该注重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之中采取有效办法切实提升和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
总之,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要求以及战略实施来看,跨界民族概念的使用是最为契合的。它既突出了地域与人文等联通优势,又强调了其国家认同基础。
[1] 王正伟.民族地区要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大局中大有作为[J].求是,2015(14):4.
[2] 吴月刚,李辉. “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发挥跨界民族的作用[N].中国民族报,2015-11-20.
[3] 范宏贵.范宏贵集[M].北京:线装书局,2010:103.
[4] 冯志伟.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与知识本体[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6(1):10.
[5] 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1):31.
[6] 严庆,周涵.浅谈跨界民族的认同构成及调控[J].民族论坛,2012(6):6.
[7]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4):49.
[8]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的跨界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2.
[9] 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33.
[10] 严庆,周涵.浅谈跨界民族的认同构成及调控[J].民族论坛,2012(6):6.
[11] 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
[12] 于海涛.试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特点[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2(4):10.
[13]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
[14] 周平,等.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
[15] 陈为智.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
[16] 邵津.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9.
[17]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56.
[18] 邵津.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
[19] 苗伟明.边境管理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44-45.
[20] 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兴边富民行动10年[EB/OL].(2010-11-21)[2016-06-10]http://www.seac.gov.cn/gjmw/zt/2010-11-21/1290148185045066.htm.2014-06-20.
[21] 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J].民族研究,1999(6):1.
[22] 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J].民族研究,1999(6):6.
[23] 曹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39.
[24] 曹兴,孙志方.全球化时代的跨界民族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8.
[25]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80.
[26] 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
[27] 王子昌. “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J].东南亚研究,2015(3):11.
[28] 黎海波.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J].理论月刊,2014(9):158.
[29] 李俊清,黎海波.中国的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J].公共管理学报,2015(1):6-7.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12-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境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JJD630015)。
黎海波(1975- ),男,湖北荆门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与跨界民族问题。
D616
A
1004-941(2017)01-0025-05
�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概念实际使用情况统计数据库概念 中国学术期刊
总库(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跨界民族165165跨境民族158115跨国民族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