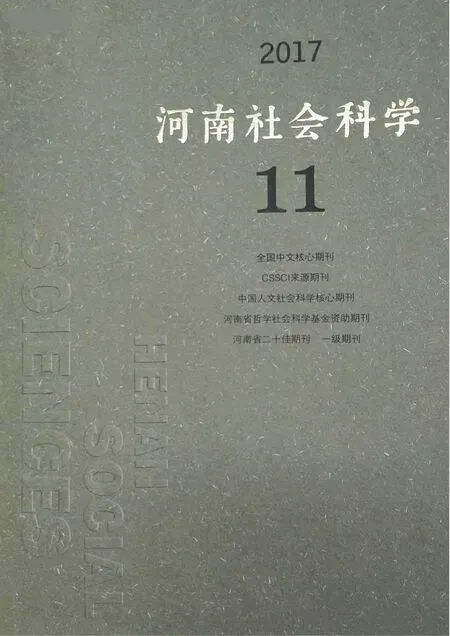社群社会视角下的在线基层治理研究
2017-03-07闵学勤李少茜
闵学勤,李少茜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社群社会视角下的在线基层治理研究
闵学勤1,李少茜2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移动互联时代基层治理受到多方主体的共同推动,正在呈现电子化、在线化趋势,并有重塑社群社会的倾向。南京市栖霞区的“掌上社区”实践探索,通过政民共在一个移动社群,并时时互动和积极回应,将政府、市场及社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在线基层治理架构。同时“掌上社区”所建构的移动社群社会,也为加强社区的参与度和凝聚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在线基层治理;社群社会;移动社群社会
移动互联技术与人类历史上前几次重大技术革命一样,正在逐渐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向社会、文化等领域蔓延,区别在于这次席卷全球的移动互联技术创新几乎同步撬动了各领域,并形成了许多混合跨界新概念,例如“社群”。新兴社群经济、网络社群营销和虚拟社群互动等糅合了商业、文化及社会理念,将每个移动终端的个体联结起来,并正在建构包含利益取向并略带理想色彩的社群社会,而这样的移动互联社群社会也正在悄然影响着基层治理。
近年基层几乎都在摸索如何从管理走向治理,而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将这一过程进行了压缩、精炼和再造,来不及过多思索,习惯了自上而下行政思维的基层直接开始了在线基层治理之旅,网络社群社会的自主创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手机网民规模已达6.95亿,其中八成在使用微信群、QQ群等移动互联平台,这为前所未有的规模化社群互动铺设了绿色通道。这一自主多点联结的网络社群看似可以跨越时空,如果没有一定的运营资本和情缘关系,多半仍属陌生社会。而基层社会裹挟了地缘性特征,一旦与移动互联结合相比其他社群多了一层黏性,也就是说只要基层政府愿意借助移动互联平台,即可与民众相对便利地实现在线倾听、沟通和协商,并建立常态化的互动关系。从社群社会的视角,这样的在线政民互动关系是否能确保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否能真正实现在线基层治理非常值得研究。
一、移动互联网下的社群社会
就一般意义而言,社群指的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具有一定的凝聚力,而且还存在着某种道德上的义务[1]。社群一直都被学界赋予理想主义色彩,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在社群中“人们愿意相互帮助并且接受其他人的指导”,他将社群区分为血缘社群(Communityby Blood)、地域社群(Community of Place)以及精神社群(Community of Spirit)[2]用以对应亲属关系、邻居关系和友谊或同志关系。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勒视野中的理想社群更富情怀,共有七大特征:(1)社群是这样一种社会团体,在其中每个人都把整个团体的起源和自尊等同于自己的起源和自尊,在社群中我们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有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2)在社群中我们对其他人的感情就是团结、友爱和亲近;(3)团结友爱成为社群全体成员的共识;(4)社群团结的制度体现就是按需分配利益的公共所有制;(5)社群不仅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是平等的,而且在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分配方面也是平等的;(6)在社群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是统一的,人们相互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7)社群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次,小到家庭、邻里,大到社会、国家,它们都是成员的团结合作精神和互助友爱的精神联结起来的[3]。社群之所以被美化和理想化,既源自个体的社会生活需要,也与个体均渴望在团体中获得尊重、友善和认同相关,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在反对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背景下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开始兴起,并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诸多领域颇成声势,影响广泛[4]。社群主义讲求团体优先、公共的善和利益优先,而这些都不是生来就有的,需在社会中养成。当然极端社群主义有时也会依附于社会政治化[5],成为专制的合法逻辑而变得与社群社会建构的初衷相背离。
进入互联网时代,平地而起的跨时空网络社群曾一度被冠以虚拟社区或虚拟社群,用以区分于现实的在地性社区,并表达网络社群的模糊边界、互动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其本质上的弱连带性。但是,当移动互联时代来临时,网络社群内的互动侵占了个体大部分碎片时间,并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它的所谓虚拟性正在被便捷性、高效率及某种意义上的黏合度和依附性所替代。相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社群,移动互联网下的社群社会已偏离理想主义轨道,正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演化。
(一)从互相需要到互动共在
人们之所以选择亲疏远近的社群生活,从本质上看还是互相需要,并因此而成为社会人,但在传统社会,哪怕是工业社会,这一过程漫长且选择机会非常有限。而移动互联社会中是否需要进入陌生社会、是否需要与他者互动几乎每时每刻都可以选择,各种免费在线社交平台确保了每个入口的低门槛和开放性,事实上一旦选择进入某一网络社群,与看不见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他者就已经处于互动共在的状态。曾有学者质疑这样的线上互动大量挤占了有效时间,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被互联网替代的活动和面对面的互动相比,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例如看电视、打电话、睡觉等。相反,互联网用户比其他人表现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并且和他们的朋友产生更多人际互动,而且使大规模的社区成员群体的沟通变得容易,原先没有直接联系的社区成员可以直接接触[6]。由在线互动而共在的社群与传统社群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阶层消融作用,不同阶层的群体因某一特定的社会属性而结群,并在同一个平台发声,它对社会的扁平化和再建构有积极的意义。
(二)从团体优先到社群认同
团体优先是社群主义面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揭竿而起的理由,但团体优先的前提是有足够的情感基础或社群认同。网络社群以松散性著称,理论上它无法与亲缘关系、友缘关系或地缘关系比情感基础,不过它的自由进出原则决定了它的维系法则必须基于认同,即便是沉默、潜水,只要不选择退出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传统的社群认同来自权威、规则及利益,网络社群其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帮助[7],但这样的外部性并非源源不断,而且一般而言人们在网络社群里会谨慎谈论共同目标、任务和事业[8],在此情境下网络社群的认同变得稀缺,认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受到挑战,这也是在网络社群中围观者数量远超发声者的原因之一。不过社群走到网络时代,维系它的基本认同已不再苛刻,它允许多元认同、接受认同的短暂移转或异化,因为网络社群对团体的依附正在向个体倾斜。
(三)从个体归依到自我建构
传统社群讲究个体归依甚至忠诚,确保社群共同目标的达成,自我的安放和建构成为次选。互联网社群以各种名目搭建,以各种主题内容来维系运营,且大部分与经济利益无关,每一个进入者都须遵从内心,在其中的表达也都更富自我的需求,并在“我不是一个人”的空间里互相观察、效仿、学习,目的是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归属感依赖社群整体的文化建构,而认同感不仅源于社群里与他者的互动,更与自我在社群中的建构和被认同有关,因此网络社群更有让每个个体发现自我、释放自我、修复自我和创造自我的效用。“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最根本的结构性影响在于它是一个个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集合,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而传统虚拟社区是无中心的,或者只是以少数意见领袖为中心的。”[9]
(四)从理念统一到目标多元
滕尼斯和米勒笔下的社群经常被另一名词所代替,即共同体。共同体既是物质利益的共享,也是理念的统一和精神的归依,但是如何实现它,路径并不明确。网络社群相对去政治化、去血缘性,它完全因各个自由主体的偏好而起,它并不追求远大的目标,个体都因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当然这样的稳定性、持久性就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相比传统社群的一些天然禀赋和较统一的文化目标,网络社群的长期互动关系需要系统运营。
二、移动社群社会对在线基层治理的渗透
移动社群社会将建构及维系成本颇高的传统社群社会电子化、即时化和去时空化,不仅节约了个体及社会的整体耗能,而且因其携带着与生俱来的互动共在、自我建构和多元认同等互联网基因,它对基层社会治理渗透的速度也超乎了想象。以往线下基层治理中最棘手的居民弱参与问题,与网络空间中的公众积极参与形成鲜明对照,当基层通过自己的行政末梢——社区——开始有计划、有准备地吸纳辖区内居民参与到微信、QQ等移动互联平台中来,“互联网+”基层治理或曰在线基层治理模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尝试接纳时,移动社群社会也被一并带到了基层治理中。
在线基层治理作为新兴治理模式,是移动互联网、公众需求和基层政府创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以PC机为终端的互联网,以手机多功能应用平台为切入口的移动互联网率先颠覆了人们的消费模式、支付模式和社交模式,而这些日常刚需行为的在线移转也开始规模化地刺激到公众的社区生活、社会生活:既然在线可以与商家沟通并最终形成交易,那么能否在线与物业、社区委交流改善小区环境、治安和停车等问题?以往工作日时间上班族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如果与社区共在一个移动互联社群,是否能在线参加社区活动、在线参与社区协商呢?社群与经济嫁接所形成的社群经济正成为新经济的一种形态,那么在线社群社会、移动社群社会为什么不能在身边兴起?这些需求和追问既是倒逼基层政府,也成为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原动力,更何况来自顶层设计中的信息政府、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等理念一直在不断下沉实践中。例如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街道推出以智能手机为载体,建立街道事务处理中心、周围商圈、社区内居民三方互动信息交流平台的“IN标签”[10];成都等地借助微信、微博等微平台开展的基层“微治理”[11];杭州市上城区在社区建设中构建“二化四网六平台”[12];深圳市罗湖区创建移动“家园网”[13]等。它们都试图打造线上各基层组织聚合的社群,回应公众对基层治理的在线需求,并打通电子政务的最后一公里。相比之下,作为民政部第三批社会治理创新实验区的南京市栖霞区,正在探索实践的“掌上社区”在线治理模式,从一开始便植入移动互联基因,围绕从线下陌生社会走向线上熟人社会的目标,经过近一年的运行,移动社群下的在线治理正初显成果。
地处南京城郊接合部的栖霞区,坐拥“六朝胜迹”栖霞山和人文荟萃的仙林大学城,下辖390.52平方公里,其九个街道119个社区几乎包含商品房小区、单位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保障房小区、小产权房小区和村改居小区等各种类型,常住人口中也融入了原住民、新移民和大量流动人口。不过与其他城区不一样的是,由于各类小区情况复杂,栖霞区政府一直以“物业托底”,即对无物业或物业较差的小区输出物业管理作为一项基本施政方针,使得被视为基层政府末梢的社区委一直保持过半以上的声望[14],因此一旦社区吹响在线建群的集结号,响应者、追随者来自各个阶层,并很快形成在线治理的初期场景。
(一)从地缘在线社群到社区在线治理
同样是微信建群,社区因有地缘优势,入群的居民会自然有在地感、亲近感,加之每天聊的都是身边事、社区事,所以栖霞以社区居委会为群主,以微信群为平台搭建的“掌上社区”从2016年年底刚兴起便获得诸多响应,截至2017年5月,像马群街道的“芝嘉花园掌上社区”“美丽宁康掌上社区”、西岗街道“晶都家园”“仙林湖片区掌上通”、八卦洲街道的“八卦花园社区居民交流群”“东江村交流群”等近500人群每天的有效活跃信息数均超过300条,从物业维修、社区治安、社区环境、养老到停车问题、宠物问题和违建问题等。只要涉及社区民生,就会有无数跟帖和响应,以往社区需要走访才能了解的民情民愿、需要座谈才能协商的问题、需要多次通知才能传达的信息在线几乎都可覆盖。社区从担心共在一个群可能会有各种不良信息或不当言论,到最先栖霞26个试点“掌上社区”的三个月良性试运行后,全区119个社区全部跟进就近搭建了基于地缘的“掌上社区”,开启居民、社区、物业、驻区单位和社区组织共在的在线治理之旅。
(二)移动社群正改变社区弱参与
社区弱参与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中社区中青年群体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参与是主要原因。与此相反的是栖霞“掌上社区”最先吸引的恰恰是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中青年群体,他们无意中发现可以扫二维码进社区群,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进群后发现都是不曾谋面的街坊邻居,每天聊的都是那些自己原本有意关心却无时间过问的社区公共事务,一下子他们的“社会人”身份就被激发:“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不知物业或社区能否来清理下”“小区安装电梯的政策文件可否在群中再发布一下?我们单元有几户常年没人,是否需要我们共担他们的费用”“有领导在吗?我们小区的停车位划分能否参照一下隔壁小区”“还有社区漫谈会一说,为什么没有早点通知我们”“我今天在小区门口菜场买五花肉,靠拐角的那个摊主居然一转身换了一堆下脚料给我,你们千万别再去他摊位上买肉啊”……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类似这样的社区关心、网上参与几乎随时都在,作为群主的社区工作人员也没有想到“掌上社区”创建的移动社群就像打开的闸门,居民们在工作场所或家中任意点击表达即可加入社区大家庭,以往线下被社区老年积极分子包裹的场景,在“掌上社区”中正被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群体取代,而这一群体对社区的理解和视角更容易击中社区问题的要害:“老实说以往社区哪里乱哪里不干净,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居民在群里一张图,几个字,再@一下你,不得不回应。”从弱参与到广泛参与,“掌上社区”对社区委的挑战也正从根本上改变基层治理的固有结构。
(三)社区的快速有效回应激发社群认同
在线下基层治理中,大多数情形下社区只能服务到弱势群体,社区当然需要积极回应他们的诉求,但他们并不要求“速回”“秒回”,而线上不同,“掌上社区”里每天等待回复的诉求不下十条,有时更多,如果社区漠视或慢回就可能引发不满,毕竟塔西陀陷阱一旦形成,短时间内就很难消解。“咱们群里是不是有律师呀,有些事情想咨询”“好几个律师,你到群成员里搜”“你是律师吗?”“我不是,我是群主,我帮你搜一下,稍等,群里就有四位”“收到,谢谢!”类似这样的快速有效回应在栖霞“掌上社区”的前十大优质运营群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多次,随着时间和事件的累积,社群认同进而对社区的认同即会自然孕育。其实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掌上社区”,最起初的想法都是“哇,这里有这么多我们小区的人啊”,慢慢才发现群主是社区工作者,不是物业工作人员也不是业主,无论以往线下对社区如何认知,线上仍是新的生态圈,所有的认同还需重新建构,而积极有效地快速回应群中大小事件,几乎是获得初级社群认同的敲门砖。“领导,这辆货车占据小区停车位好几天了,能不能管管”“我们社区规模大,能不能搞个相亲联谊活动”“小区前面的公交线路还是多少年前的老线路,城市变化这么大,能不能和公交公司谈谈重新设计下线路啊”。每天这样的诉求琐碎平凡,单靠社区一方回应,如果没有形成多方联动,社区也会不堪重负。
(四)良性的社群互动培育社区共治
传统的社群关系由于团体优先、目标统一,社群中的个体很容易被淹没。“掌上社区”中即便有群规,一般个体只要好好说话,发言几乎不会受限,那么一旦信息呈现,群中的互动全凭群内日常养成的氛围:“我们小区打篮球去哪里?百水芊城派出所吗?”“还可以去中山学院,我每周都去。派出所那个球场人太多”;“咱们这谁家出租房子啊?精装修的那种,干干净净的”“是的,我这里有房子出租”;“我刚才出门有事,一开门一只狗对着我乱跳狂叫,吓死我了。养了小狗在门口,既影响环境,也打扰别人休息,门口卫生很不干净”。五分钟过后,有群内居民回复,“三种办法:(1)上门友好协商,此为上策;(2)找物业,让物业清理公共空间的卫生。此为中策;(3)实为无奈之举:打110要求警察按照犬类管理规定进行处理”。事主回复“感谢您的好点子,我现在已经把事情告诉业主了,请他协调解决,这房子是一帮女孩子租的,谢谢您”。就运行大半年的“掌上社区”而言,群中这样的互动非常常见,沉浸其中的居民可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参与社区共治,而社区若能发现或有意识地培养那些积极良性互动的居民成为社区精英,社区既可借力亦可获得更多社区资本,为制度层面的社区共治奠定基础。
三、在线基层治理重塑社群社会
如果说基层治理的创新有相当多来源于顶层设计或上级政府的行政需求的话,那么基层治理的在线化趋势更多发端于自下而上的涌动,这里的“下”包括百姓对基层政府的电子化、在线化需求,也包括基层政府本身接地气。移动互联网时代与百姓沟通绕不开免费的社交平台,为了提升治理效度和到达率,他们自主需要建构电子社群、移动社群来应对基层社会的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各类创新实践逐渐影响到他们的上线政府。
像南京栖霞区这一“掌上社区”在线基层治理形式,看似基层政府与百姓可以每天“不见面”互动,互相增进了解,互相磨合成长,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地缘、邻缘的移动社群社会的萌发,并且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成本、情感成本及行动成本颇高的社群社会的重塑。首先,这里的“重塑”涵盖对社群社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新定义,从线下关系相对固着、理念相对统一和团体相对忠诚的传统社群社会到线上互动扁平频繁、认同多元丰富和随时切换更迭的移动社群社会,这一跨越更贴近人性之日常,由此更易激活社会中的每一分子。其次,这一“重塑”裹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在一个场域,他们每天为社区日常对话,喜百姓之喜,忧百姓之忧,即便有争吵、有怀疑,也不乏群里的冷嘲热讽,不过到哪里能找到三者无时无刻的社群共在?假以时日,若各自学会了有序、宽容地互相面对,那么所谓“大政府”向“强政府”转型、“小社会”向“强社会”过渡也未尝不可期待;再者,“重塑”的社群社会若能被悉心维护,它对后单位下每个个体的在地心灵归属,对社区多年期盼的强参与和凝聚力都是极大的平台支撑,更何况在线社群可以通往线下,并与线下融合形成立体的社群社会,为各个阶层、各年龄群体都营建一个充满能动性和关怀度的新兴场域。
当然,无论是在线基层治理也行,还是移动社群社会建构也好,都还只是刚刚勃兴,所有的参与者都还未完全准备好,也没有通达平顺的路径可循,各社会主体在其中的角色扮演也都边界模糊、切换频繁,但是由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变迁清晰可见,社会生活、特别是社区生活的在线移转与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一起正在建构一个不可估量、极具想象的社群。
[1]Robert Nisbet,The Social Philosophers:Community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ThomasY.Crowell Company,1973,1.
[2]Ferdinand Tönnies,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edited by Jose Harris,translated by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Holl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6—27.
[3]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78-80.
[4]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70—76.
[5]Sandermann,P.The Transnational Social Politicization of Communitarianism in Germany.[J].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2014,4(1):73—88.
[6]Barry Wellman.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J].Science,2001,293(5537):2031—2034.
[7]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4):68—73.
[8]Pape,B.,Reinecke,L.,Rohde,M.,Strauss,M.E-Community-Building in WiInf-Central.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acm,8-12 Jan.,2003,Florida,USA.
[9]彭兰.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J].国际新界,2009,(5):87—92.
[10]朱琳,刘晓静.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社区服务公众采纳实证研究:以打浦桥街道“IN标签”为例[J].电子政务,2014,(8):27—37.
[11]郭祎.成都基层微治理的探索及完善建议[J].中国国情国力,2016,(12):33—35.
[12]汪锦军.城市“智慧治理”:信息技术、政府职能与社会治理的整合机制——以杭州市上城区的城市治理创新为例[J].观察与思考,2014,(7):50—54.
[13]张志安,范华,刘莹.新媒体的社区融合和公民参与式治理:以深圳市罗湖社区家园网为例[J].社会治理,2015,(3):111—119.
[14]闵学勤,贺海蓉.掌上社区:在线社会治理的可能及其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17,(3):16—22.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A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rian Society
Min Xueqin,Li Shaoqia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jointly propelled by various subjects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is gradually being electronized and realized online,which tends to reshape the communitarian society.Mobile Community explored by Qixia District of Nanjing has formed a new framework for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It integrates government,market,and society through their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active responses in the mobile communitarian wherethe governmentand the peoplecoexisttogether.Besides,thismobile communitarian established by the mobile community has provided a powerful platform for strong degre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hesion.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Communitarian Society;Mobile Communitarian Society
C91
A
1007-905X(2017)11-0114-05
2017-06-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035);南京大学文科双重项目(010914902122)
1.闵学勤,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公共社会学研究;2.李少茜,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编辑 张志强 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