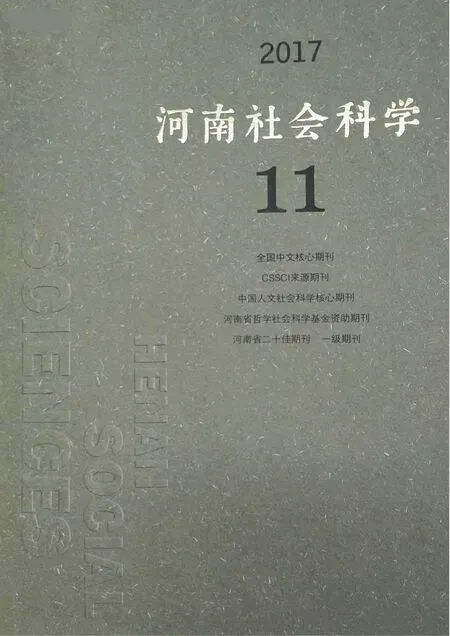论诉前委托调解的法院干预
2017-03-07刘亚丽
刘亚丽
(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上海 200233)
论诉前委托调解的法院干预
刘亚丽
(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上海 200233)
人民法院委托有关组织进行诉前调解,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虽有轻微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将民事纠纷完全排除在司法解决之外。如果受委托机构是人民调解组织,诉前委托调解就兼有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的混合属性。基于维护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和纠纷解决的公正高效之目的,法院对诉前委托调解可以给予相应的干预,但应坚持谦抑和适度原则。
人民调解组织;诉前调解;委托调解;适度干预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诉前调解(先行调解)一般委托设立于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实施。经司法机关调查,一些地方法院近年的诉前调解只分流8%左右的案件,成功率甚至低于诉讼中的调解,法院、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对诉前调解的信心有所降低①。显然,作为落实“调解优先”政策的诉前调解入法,隐含着减轻司法负担的功利性目的②,法院若片面将解决纠纷的压力转移给社会,必然使诉前调解面临信任危机。当然,在诉前将民事纠纷委托给其他部门调解,某种程度上观照了“调审分立”的理念,但“调审”无论分与合,关键在于恰当把握“调审”分合的尺度③。该纠纷解决方式的前提是当事人已提起民事诉讼,行使了司法裁判请求权,即使暂时同意调解,其纠纷仍有随时进入审判程序的可能性。那么,法院是否完全置身于诉前委托调解之外?法院当以何种措施维护当事人的司法信赖利益?本文通过对诉前委托调解属性的分析,提出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诉前委托调解的混合属性
诉前委托调解具有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混合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这一命题的展开。
(一)诉前委托调解的司法调解属性
诉前委托调解处于司法权作用之下,并有一定的司法强制性,因而具有司法调解属性。
1.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处于诉讼状态
诉前调解存在的时间段为起诉后立案前,如果当事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法院立案受理,即产生诉讼系属,我国诉前调解的文义应理解为诉讼系属前的调解。但是,司法权对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并不是在诉讼系属之后才发挥作用。尽管我国确立了立案登记制,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起诉无须通过任何合法性审查。倘若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法院可以要求其补正;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无法补正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对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在立案阶段,法院、当事人的前述行为毫无疑问是诉讼行为。诉讼自起诉时开始,而非起始于诉讼系属之时④。为将民事纠纷的司法解决与诉讼系属相区分,德国提出诉讼状态的概念:虽然诉讼系属在法院将起诉状审查并送达对方当事人之后才发生,但自当事人递交起诉状起,法律争议就进入未决的诉讼状态,法院可以对处于未决状态的法律争议行使司法权⑤。由此可见,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因其提交诉状而发生的未决状态实际上处于诉讼状态,此时民事争议就已经存在于司法权的作用之下。在诉讼状态下,法院将本应属于自己处理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人民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当然就赋予了委托调解的司法属性。
2.调解程序启动存在一定的司法强制
诉前调解并非强制调解,但不应忽视其蕴含的拓展我国强制调解形态的积极意义。尽管绝大部分法院在启动诉前委托调解时,均小心翼翼地防止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要求法官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然而在当事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对调解合意的引导,不可能完全排除对当事人心理上的强制。法院应如何引导当事人,目前尚无相应的具体规范,很难避免法官超出程序说明的范畴,通过间接的实体评价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使得调解引导在不少情况下变成调解劝导。当事人为寻求实体上的有利结果,不得不与法官启动委托调解的意见相妥协。立案前促成当事人的调解合意,客观上会对其心理形成一定的强制。当下民事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预立案,然后引导当事人同意将民事纠纷交由人民调解机构调解,以降低当事人对法院拒绝裁判的担忧。该做法虽展示法院与当事人合作解决纠纷的意愿,但仍不能消除启动调解程序的司法强制因素。
(二)人民调解属性
人民调解组织在诉前委托调解中,因须遵守《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具有人民调解属性。
1.人民调解室的独立性
司法实践中的诉前调解大部分委托给设在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室,因而有学者认为已经形成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格局⑥。此观点有失偏颇,法院附设调解以法院为主持机构,并受法院的指导,这种程序虽然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但与诉讼程序又有制度上的一定联系⑦。由于驻法院人民调解含有司法属性,就认为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如同日本等境外的法院调解委员会一样具有附设特性是不正确的。此认识忽视了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与境外法院调解委员会的基本差异。人民调解工作室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调解组织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立性。而境外附设于法院的调解委员会属于法院的内设机构,虽然大部分成员由社会人士组成,但成员的遴选权归于法院,并接受法院的指导和管理。因此,驻法院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尽管与法院存在业务上的协作,但独立于法院,属民间调解组织,组织建设及调解活动受《人民调解法》的保障,法院不能主导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活动。
2.人民调解程序的独立性
《人民调解法》突出反映了非诉讼调解向司法程序观念靠拢的倾向。人民调解中包含当事人自愿平等、调解中立、禁止阻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规定以及关于调解文书、档案制作管理等规定,增添了人民调解正式化、程序化以及准司法化的特色。尽管部分学者担忧这种立法倾向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治社会的片面认识,忽视非正式调解,将发展人民调解的重心放在正规化、专业化的调解机构和调解队伍建设方面,从而抑制调解的便利性和灵活性⑧。但是,调解程序的司法化还是为人民调解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程序规则,该程序规则并不与诉讼程序相重叠或交叉,形成独立于法院调解的程序体系。各地在“大调解”的实践中,大多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各类调解的程序性规定,以满足民事纠纷当事人偏好司法原则的需求,同时也不会以民事司法取代民间调解的活动。
诉前委托调解并非单一属性,而是兼有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混合属性。诉前委托调解的运作必须同时观照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要求。为防止偏离司法属性的约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司法权对其干预的问题。
二、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正当性
所谓法院对诉前委托调解的干预,是相对于受托机构主持调解过程本身而言的,而非针对诉前委托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结果的执行。其正当性依据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限制裁判请求权的弥补义务
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要求法院提供诉讼救济的权利,与民事诉权相对应的是,法院负有不得拒绝审判的义务⑨。当事人依据诉权享有裁判请求权,如果当事人起诉,法院必须通过民事司法权对裁判请求权予以回应⑩。诉前委托调解中,法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回应,而是引导当事人接受调解,对其产生一定的心理强制。从法律意义上讲,法院的调解引导事实上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造成轻微限制。司法救济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如果法院限制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哪怕是轻微的限制,也将造成当事人一定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负担。鉴于诉前委托调解的司法属性以及调解结果固有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纠纷解决成本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追求司法程序正当性的角度看,确有给予补救之必要。故而,法院应当尽可能满足当事人的两个基本诉求:一是促进调解程序的进行,力图减少调解过程中不合理的成本支出;二是促使当事人的纠纷解决符合法律规定,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司法信赖利益。欲达此目的,法院必须保留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权力,作为对限制当事人裁判请求权应尽的弥补义务。
(二)司法权持续作用的结果
若从结构上分析,混合属性框架下诉前委托调解的司法调解属性与人民调解属性并非等额构成。因当事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民事纠纷处于司法权作用下的未决状态,且法院将应由自己处理的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故人民调解的机构受托进行调解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司法解决纠纷的一部分,从而决定了司法属性是诉前委托调解的主要属性。此时的调解进程始终笼罩在司法解决之下,人民调解属性只能是诉前委托调解的次要属性。基于此,调解工作委托给人民调解机构后,司法权并未消失或者退出。只要纠纷未得到解决,司法权就当然持续不断地作用于该调解过程。法院不仅有决定或者解除诉前委托调解的权力,也有权力和责任根据委托调解的状况进行干预。可见,这种持续作用的干预权力不是司法权的延伸,而是司法权既已存在的状态。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当事人行使了裁判请求权而交由其他部门调解的民事纠纷,同样明确法院具有全方位的干预权力。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诉前调解由附设在法院的调解委员会负责⑪,为保证调解的合法性并能与诉讼程序有效衔接,诉前调解始终处于法院的控制之下⑫。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官可以选任调解委员,指定主任调解委员,确定调解的首次期日,审查调解处所变更等⑬。《日本民事调停法》对诉前调解也有类似规定。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建立在诉前调解为法院调解的基础上,其诉前调解为司法严格监督之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⑭。在我国大陆的诉前委托调解中,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前述法院的内部调解来处理,但因司法权持续作用而产生的干预后果则与之相同。
(三)契合社会公众的程序正义偏好
法治社会化是从精英法治向大众法治转化的过程。但是,民事诉讼调解对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产生一定制约,其力量是有限的⑮。人民调解立法的司法化倾向从侧面反映一个事实,即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非程序化问题,这与人民调解队伍的法律素养有待提升尤其是程序意识不强有密切关系。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法律观念已经处在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的演进过程中,形成重视司法程序正义的偏好,不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也随之出现司法化倾向。申言之,人民调解尚不能完全满足民众追求司法原则的需求,特定情况下有补强的必要。在诉前委托调解中,因当事人已提起诉讼,其会按照司法原则形成对纠纷处理的预期。诉前委托调解与普通人民调解有很大不同,具有浓厚的司法色彩,人民调解员面临着对调解的正式性和非正式性关系处理的更高要求。因此,诉前委托调解也蕴含着较大风险,如果调解失败,当事人就会负担诉前调解和审判的二次纠纷解决成本,其诉讼负担不减反增。而损害弱势当事人的交涉平等权以及进行压制性交涉,也是调解中极易出现的问题。仅靠人民调解组织的努力,往往力有不逮。概言之,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即指导、监督甚至直接参与调解,不仅使当事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处于司法解决的心理氛围之中,能够提高调解的可接受性,更有弥补人民调解能力不足之效果,从而更能契合社会公众的程序正义偏好。
(四)纠纷快速解决的目标驱动
追求民事纠纷的快速解决是社会大众的共识。诉前委托调解中,当事人始终对司法解决存在相当的信任度,在必要情况下,希望法院及时介入并发挥促进调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法院的监督、指导,可以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避免调解过程费时过久。除此之外,纠纷快速解决的目标亦驱动法院对可能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作必要准备。只要当事人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或者撤回诉讼,诉前委托调解就有随时产生诉讼系属、转入审判阶段的可能。如果调解并不顺利,法院通过适度干预介入其中,可以获得促进审判进程的如下信息:首先,便于法院明确纠纷当事人。调解过程中,如果调解主持人发现其他案外人与民事纠纷存在利害关系,可以通知其参加调解。得知当事人已经起诉的利害关系人也可能向法院提出参加诉讼的请求,法院审查后认为其符合条件的,可以通知调解主持人。这些调解参加人往往成为以后审判程序中的共同诉讼人或者诉讼第三人。其次,有利于法院厘清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当事人在调解中要提出自己的请求主张和抗辩,使调解主持人明了双方的争执点,这些争议焦点亦可能成为其后诉讼中审理的内容。由于调解与审判的机理不同,调解不实行辩论原则,上述内容的确定是相对的,调解中确定的当事人和争议焦点不当然成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和内容。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经历了调解过程而对主张及理由的提出有了准备,更利于审判中同类行为的进行,从而减轻其对审判的陌生感,便于诉讼协同,以促进诉讼的快捷性。
三、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方式和限度
前述诉前委托调解的实践困境,凸显出法院干预的必要性,法院应以实现调解过程的程序正义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为目标,裁量决定干预的方式和力度。
(一)干预的方式
1.间接干预
此方式是指法院不直接参与已经委托给人民调解机构处理的民事纠纷案件,而是采取指导、监督的方式推动调解。委托调解的特质是法院和社会组织分享调解权力,人民调解机构受委托进行调解应遵守《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大部分情况下,法院要与人民调解机构的活动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妨碍人民调解的灵活性和便利性。间接干预的具体方式首先表现为对委托调解个案的指导,现有法律依据为《人民调解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即“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这里所说的业务指导应理解为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指导,也包括个案意义上的指导。而在诉前委托调解中,法院业务指导的范围包括对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理解、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内容。间接干预的另一方式是对调解活动的监督,即法院发现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2.直接干预
此方式是指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直接参与诉前委托调解,或者决定终止调解程序。《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机构可以请求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参与调解,那么法院同样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其中,直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参与调解以法院认为确有必要为前提,例如调解中出现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等。此处只限于个别具体问题的处理,应排除法院全过程参与其中,否则就与法院自行调解几乎无异。同时,诉前委托调解由法院启动,但不一定由人民调解机构终结:如果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该纠纷就以人民调解的形式终结;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法院认为已无继续调解的必要,即使受委托的人民调解机构仍坚持调解,法院也可以直接决定终止诉前调解,对当事人的起诉予以立案,通过审判程序解决纠纷,以防止人民调解机构在程序控制上出现偏差,造成久调不决。
(二)干预的限度
基于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属性的协调,法院不能按照纯粹的司法调解来对诉前委托调解进行控制,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应坚持谦抑和适度的原则。首先,在目标定位方面,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目标在于维护调解的合法性和促进调解进程。一旦调解活动违法,法院可以主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而促进调解进程是一个柔性目标,采取何种手段提高调解效率,通常难以量化评价。况且促进调解也不意味着尽快在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对于调解成功可能性甚微的纠纷而言,经过充分交涉,明了双方当事人的态度,只要能尽快得出调解成立或者不成立的结果,都可以理解为调解的高效。只有受托机构的调解措施明显不当,对事实认识和法律理解出现错误,显著妨碍调解结果的形成时,才可以理解为不利于调解目标的达成,法院方有干预的必要。其次,在干预方式方面,以间接干预为主,直接干预为辅。法院对受托机构的指导监督,尽管主要针对个案,但背后蕴含着强烈的规则传播意义,此“公共产品”的提供更优先于具体个案的解决⑯。其目的在于帮助调解机构提升能力,更好地分解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负担,增强当事人选择诉讼外方式解决纠纷的信心。就此而言,应严格控制法院直接参与调解过程,法院应主要采取被动参与方式,在调解机构提出请求并且确实存在调解能力不足的困难等条件下,法院的参与方为适当。法院决定终止调解程序的直接参与应采用主动方式,诉前委托调解时限性较强,已经起诉的民事纠纷迟迟不能发生诉讼系属,会过度妨碍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对达成和解无望或者拖延过久的纠纷,法院应主动终结诉前调解,尽快立案。
另外,作为有限干预的保障,应控制诉前委托调解的基本面,减少法院干预的机会。若法院自行调解更为适宜,就无必要委托给人民调解机构,从而避免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权力的过度使用,节约司法资源。同时,高效也是法院干预适度性的一种保障。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司法手段的运用日趋广泛,调解工作逐步网络化,诉前委托调解越来越多地采用远程调解方式,法院可以尝试将网上立案、远程调解、远程审判系统进行一体化整合,在法院、人民调解机构、当事人以及证人等其他参与人之间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交流体系,利用网络系统实施材料审查、调解委托、调解指导和监督,甚至直接参与调解,为高效的、适度的法院干预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四、结语
法院干预诉前委托调解的权力不应视为一种新的权力创设,而是民事司法权自有的调解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其他社会机构后,所应保留的另一部分权力。随着诉前委托调解实践的深入,法院的干预权已经无法回避。该权力存在的前提是,法院与人民调解机构通过诉前委托调解的方式实现权力分享,社会力量因分担法院压力而向司法靠拢,促成对司法权布局的新理解。同时,法院也不能在任何条件下对社会机构行使部分司法权的合法性、有效性置之不问。因此,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既造成司法权某种程度的社会化,也必然使得法院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一定程度的干预。唯有如此,方不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过度分离,从而坚持共同的法治正义目标导向。
(本文写作中,有关资料收集、文章框架设计得到上海师范大学李峰教授的指导,谨表谢意!)
注释:
①任国凡:《先行调解面临的司法困境与出路》,《法律适用》2013年第12期。
②吴英姿:《民事诉讼轻视程序保障观念反思》,《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③郑金玉:《调审分合的尺度把握与模式选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0页。
⑤⑩[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44、686页。
⑥谢国伟、钟毅:《法院附设非诉调解机制的构想与论析》,《法律适用》2007年第9期。
⑦范愉:《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⑧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法学家》2011年第2期。
⑨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讼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
⑪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诉前调解均被理解为当事人起诉前的调解,这与我国大陆地区当事人起诉后立案前的诉前调解在时段上有所不同,但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分流案件、减轻法院压力的目的是相同的。
⑫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⑬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6条、第407条、第410条之规定。
⑭肖建国、黄忠顺:《诉前强制调解论纲》,《法学论坛》2010年第6期。
⑮刘加良:《民事诉讼调解模式研究》,《法学家》2011年第2期。
⑯闫庆霞:《人民调解前置制度之反思》,《法学家》2007年第3期。
The Court Intervenes Pre-litigation Entrusting Mediation
Liu Yali
People’s Court entrusts related organizations to conduct pre-litigation mediation.Although it has slight limits to the parties’request for adjudication,it doesn’t mean that civil disputes are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the judicial settlement.If the entrusted institution is people’s mediation organization,the pre-litigation entrusting mediation has mixed attributes both of people’s mediation and judicial mediation,with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parties’faith to the justice and justice and efficiency in solving disputes.The court could give the moderate monitoring to the pre-litigation entrusting mediation,but should insist on the tolerance and moderation.
People’s Mediation Organization;Pre-litigation Mediation;Entrusting Mediation;Moderate Intervention
D9
A
1007-905X(2017)11-0058-05
2017-09-20
刘亚丽,女,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政策、城市法治研究。
编辑 潭 影 王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