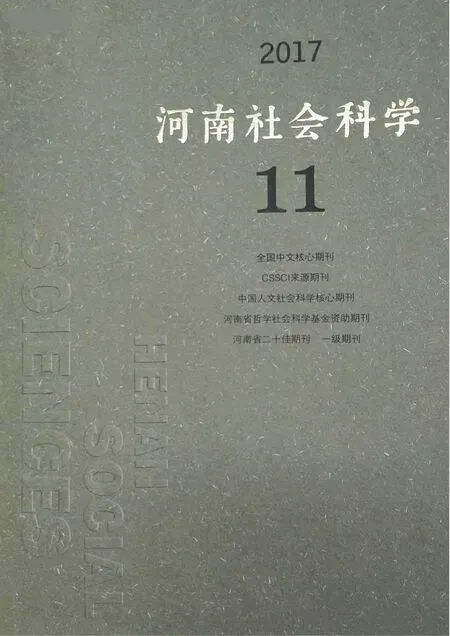行政诉讼时效延长的困境与调整
2017-03-07徐继敏
杨 丹,徐继敏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行政诉讼时效延长的困境与调整
杨 丹1,徐继敏2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将诉讼时效延长至6个月,对于保障原告诉权具有积极意义,但给部分行政管理措施带来障碍,并影响行政效率。6个月较长时效、起诉期限未类型化以及错误将诉讼时效与行政管理措施挂钩是造成新诉讼时效难以平衡行政管理与权利救济的主要原因。建议修改行政管理领域法律法规,取消部分诉讼时效与管理措施的挂钩。基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应重新确立时效起算点,采用“短时效”主义与类型化相结合的方式,以期兼顾行政管理与个人权利保障,推进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
起诉期限;行政效率;相对人权利保障;时效类型化;起算点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案将行政诉讼时效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这对于保障原告诉讼权益、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诉讼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不少法律将行政管理活动与诉讼时效挂钩,如《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据该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条件是行政诉讼时效届满时原告未提起行政诉讼,那么诉讼时效延长意味着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延长。另外,《行政强制法》规定查封、扣押措施的期限为1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1个月。对于行政程序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案件,行政诉讼时效延长,意味着行政机关在申请强制执行前必须解除查封、扣押措施,导致原本可以强制执行的行政案件因解除查封、扣押措施而无法强制执行。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时效是否合理,与行政管理期限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如何解决诉讼时效给行政管理带来的问题?本文拟对《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规定的期限与诉讼时效予以梳理,剖析诉讼时效延长所导致的行政管理困境的原因,并在现代公共行政和行政法三元社会①关系的视域下,思考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措施。
一、行政诉讼时效延长对行政管理的负面影响
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行政诉讼时效是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时效主要分为四类:(1)一般案件起诉期限为6个月,明确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适用该期限;(2)经复议的案件起诉期限为15日;(3)不动产案件最长起诉期限为20年,一般案件为5年,未被告知起诉权或起诉期限的案件起诉期限为2年;(4)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的案件不受上述三类期限的限制。6个月、15日、20年、5年、2年和无期限限制的起诉期限,以广覆盖性推动行政诉讼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利救济。行政诉讼时效由3个月延至6个月的初衷在于解决期限过短给相对人造成的入讼困境,使之在相对充裕的期限内认识行政争议并准备行政诉讼事宜,对于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权具有积极意义,但对行政管理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导致部分行政管理措施实施困难。
(一)诉讼时效延长对部分行政行为效率的负面影响
我国部分法律将行政诉讼时效与行政管理行为挂钩。如《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应在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的条件下行使。《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行政强制法》对此条规定作了部分修订)其他违法建筑物拆除则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一般起诉期限。
对于非法占地的违法建筑物,当事人在15日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且被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在6个月内审结案件;当事人如果不服一审判决需在15日内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受理后3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一旦判决支持行政机关,自作出强制拆除决定至最后拆除至少需经历10个月,其他违法建筑拆除则需要15.5个月。经行政复议的违法建筑,最长可在14个月后才能实现强制拆除。一旦进入诉讼阶段,强制拆除的决定不具备强制执行效力,其间若当事人继续建设或使用违法建筑,经10个月、15.5个月或14个月之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辐射作用,再行强制拆除将遭受巨大阻力。或者,当事人在接到自行拆除命令时,选择行政复议或诉讼以阻止行政机关的强制拆除行为,再通过补办手续执照等满足程序性要件使之合法,将使得行政机关强制拆除对象落空。
过长的诉讼时效,导致行政强制难以实现或行政效率降低。行政决定作出后,如果行政相对人知道诉权但不同意行政行为,应当限制其在较短时间之内提起诉讼,延长时效对其权益保障并无特别意义。
(二)诉讼时效延长导致行政强制执行困难
我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查封、扣押和冻结的期限为30日,情况复杂的最长为60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强制执行的实现。行政机关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后,可能作出两类行为:一类是确认无违法行为或不需要作出行政决定,以及作出没收或依法销毁违法物品的行政决定;第二类是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罚款或要求其缴纳一定财产的行政决定②。若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均应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还需具备:(1)已经或即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2)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3)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
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起诉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执行,自作出强制措施决定至申请执行期限约为150日至180日;情况复杂的,约为120日至180日。超出的150日或120日,被采取措施的财产应当如何处置?若重新采取强制措施,行政机关重复行为对相对人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不解除强制措施,故不可行;若解除强制措施,则导致财产不在行政权控制范围内,将无对象供法院执行,先前的强制措施将丧失意义③。延长诉讼时效意味着在申请强制执行前就应当解除强制措施,此时将无财产可供法院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权将被架空。
我国“或复议或诉讼”的权利救济体系决定只要任一救济程序的期限届满,行政机关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行政相对人未明确表示复议或者诉讼,那么行政机关可自由裁量选择适用利己程序。那么,在行政诉讼时效延长的情况下,强制执行时间也随之延长,行政机关作出首先适用复议期限届满的选择将可能成为常态。
(三)诉讼时效延长影响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这类法律关系是行政机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基础。那么,行政决定或裁决与行政裁判的作出可能涉及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纠正与创新,直接作用于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人。倘若有效行政决定久拖未决或未及时执行,将有损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诉讼时效越长,证据消灭、记忆削弱的可能性就越大,证明较久远发生的法律事实远比证明新近发生的法律事实要难,因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缘故会加重行政机关承担的诉讼风险,而且久拖未决的客观法律事实也可能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诉讼争议的解决。此外,与民事诉讼时效相比,行政诉讼时效的特殊性在于其对行政管理活动的约束:督促行政机关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履行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以及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期待利益。如果一项行政决定或裁决因法律允许相对人过长时间的懈怠而遭到质疑,那么行政机关可能面临长期的“提心吊胆”,直接影响其对“平静”利益④的期待,执法权威持续受到威胁可能导致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瞻前顾后和力不从心,从而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二、行政诉讼时效制度困境解析
(一)部分挂钩行为错误解读行政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为发挥其基本功能,即解决行政争议、实现权利救济以及权力监督,应当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⑤。叶必丰教授指出,诉讼时效是诉讼法针对行政行为的形式确定力所作的制度设计⑥。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对相对人而言,其应当且仅能在此期间提起行政诉讼,那么诉讼时效既是对起诉权的保障,也意味着法律对相对人懈怠履行这项权利的容忍期限;而行政机关则在期限届满且相对人无任何诉讼行为的情况下确定行政行为不会因司法裁决而改变。
如果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停止执行,此时行政行为与诉讼时效的挂钩就有必要。从表面上看,确定不变的诉讼时效可以保证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威,但却错误解读了行政诉讼时效的实质。适用诉讼时效的初衷是实现行政决定的不可撤销性以保障其后续执行力和稳定性,但行政决定作出之时即具备不经法定程序不能随意撤销的效力。而诉讼时效是为规范相对人起诉行为而设置的程序性要件,用以判断行政争议能否进入司法审查;又或是为了督促相对人积极履行行政决定并保证行政机关不作为诉讼被告,却以剥夺相对人诉讼权利为对价,致使行政行为规避司法制约,明显违背行政诉讼法基本功能的实现——保护相对人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诉讼时效应为实现司法救济目的服务,法院终局裁决效力不仅约束相对人和行政机关,更辐射了与之关联的行政决定或行政行为。但如果诉讼时效在行政程序中就发生作用,相对人丧失司法救济权的概率将增加。
(二)诉讼时效延长未兼顾行政效率,且混淆权利救济功能
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推行“国家行政”与“社会行政”并行,积极吸纳市场与个人参与政府治理,形成公私合作治理新形态,促进现代公共行政发展,使得行政法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扩大。行政法不仅追求依法行政的民主、法治价值目标,还要追求行政法的效率价值。所谓行政效率,是指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能时,耗费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人员、最低的经济成本,高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诉讼时效延长较难保证行政管理效率,与现代公共行政目标相悖。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时效导致拆除违法建筑物可能发生在决定作出至少10个月之后,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因强制措施时限与诉讼时效衔接不当而无法执行。又如,交警在行使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权时,当场向相对人交付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其所享有的诉权和诉讼时效,如果相对人在6个月起诉期限快届满之前起诉,客观上将导致行政机关证据收集困难,且要分身应诉,可能严重影响交通部门的管理效率。
“允许公民、组织在何时提起行政诉讼,关系到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公民、组织的权利救济。”⑦尤其是2004年“国家保障和保护人权”入宪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逐渐加大对相对人权利救济的力度,促使诉讼时效的天平向相对人倾斜。但这样的进步也存在风险,即过分强调相对人一方权利救济而忽视行政机关职权与社会公共秩序之间的密切关联。延长诉讼时效是进一步降低对相对人懈怠的容忍标准,却治标不治本。《行政诉讼法》修改陷入误区,认为目前相对人权利救济不足主要是由诉讼时效太短导致的,故而认为将诉讼时效延长至一定期限就能保障相对人有充裕期限实现权利救济。但即使延长诉讼时效也不能强制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只要相对人不提起或无能力提起行政诉讼,“长时效”也难以发挥作用。
实际上,诉讼时效起算点才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关键。修正案既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或“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为一般起算日,也以“收到复议决定或复议期满之日”或“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客观标准,前者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原则上,行政机关一旦作出决定或裁决,应当采取公告、通知、邮寄等客观形式送达相对人,方便相对人知晓行政行为和诉讼权利。实践中的做法仍主要体现行政便利,忽略了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常晚于行政行为作出之时,甚至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才获知。换言之,在现有起算点制度的语境下,相对人认知的滞后性往往导致其丧失司法救济的最佳契机。此外,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内容也是存在争议的:究竟是得知行政机关、行政决定内容、诉讼权利或诉讼期限之一即视为“知道”,还是应在行政机关的注意提醒下获知前述所有内容?又或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计算时效——基于权利救济?
(三)起诉期限类型化混乱,未充分体现行政诉讼的基本目的
经过修订,行政诉讼时效以6个月为一般期限,15日、2年、5年和20年为例外,但适用标准仍然混乱,导致起诉期限出现类型化混乱。比如,未修改诉讼时效之前,经复议案件给予相对人提起异议的期限为75日(复议申请60日+起诉期限15日),已经在3个月的基础上人为减少15日;延长诉讼时效后,这类案件允许相对人怠于行使起诉权的期限少105天,但在复议阶段并没有特别措施弥补其损失的时效利益。有学者认为,区别对待经复议案件的诉讼时效是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但复议机关的审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司法审查,即使被视为“准司法”程序,其本质上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程序。相对人选择适用行政复议,如果在此阶段即解决行政争议,自然不会进入司法程序,从而实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这应当是相对人“用尽行政救济”的初衷。将经复议案件的起诉期限缩短归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范畴,有违行政诉讼的平等原则。
此外,修正案仍然沿用区分最长诉讼时效适用的规则,以是否涉及不动产为标准。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有关“受案范围”涉及的行政行为,多以损害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为界定标准,并未特别区分“动产”与“不动产”。这样一来,容易产生歧义:(1)行政诉讼具有两个最长诉讼时效,与“最长”自相矛盾;(2)只要涉及不动产的一律适用最长起诉期限20年,不再考虑行政行为类别或侵害的权益属性。
但是,“是否经行政复议”与“是否涉及不动产”也只是撤销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标准。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因各种不同的诉讼请求设置不同的诉讼规则,所有行政案件完全采用撤销诉讼一元化的规则和标准审理。生搬硬套地把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适用于所有诉讼类型,很难通过诉讼时效体现相对人不同的诉求。
三、完善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建议
经前文分析可知,诉讼时效延长造成强制执行困难等管理措施障碍,并严重影响行政效率。为解决这一难题,应当取消诉讼时效与管理措施挂钩的规定,另行确定管理期限,以满足行政管理的需求。在借鉴域外经验并考察我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一)改革行政管理措施与诉讼时效挂钩制度
美国诉讼时效的确定除部分领域法定以外,主要交由法官裁量。法律规定以行政处罚作为执行方式,如果这种处罚的方式需要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在当事人不遵守时,往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尽管法律并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但若当事人不履行,行政机关仍可采取执行措施⑧。《美国联邦税法典》赋予税收机关强制征税的权力,手段主要包括扣押或出售,这一点与我国存在不同。当扣押实际执行,即表明强制执行的开始,也就不存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扣押一定期限后再作出是否执行的决定。大陆法系国家则采行“行政权优位”原则,大量案件无需通过法院即能得以执行,诉讼时效的运用甚少,但却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各执行阶段的期限。比如,德国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执行权,除非执行机关为普通的行政机关,无直接强制能力的,得请求警察机关协助执行。
在我国,诉讼时效延长或缩短都将实质性影响法院强制执行的启动。笔者建议取消诉讼时效与强制执行等管理措施之间的挂钩,依据行政管理规律与特点设置相应时效。首先,厘清立法先后逻辑,明确行政管理类法律法规在事前、事中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发挥《行政诉讼法》的事后救济功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掀起政府行为规范热潮,在促进行政法体系完善的同时也使得部分行政立法过分迎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将诉讼时效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时效要件,致使部分管理期限相应延长,行政效率受到影响。因此,应正视行政管理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避免行政法领域过分依赖诉讼制度。其次,行政管理措施应遵循效率性和合法性原则。设置管理时效应当体现程序规制作用,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履行法定职责。再次,笔者认为,借鉴美国司法审查中“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保留“复议期限届满”是可行的。行政复议是重要的行政救济手段,在行政系统内部通过监督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来保护相对人权益,即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相对人在放弃行政救济时仍可以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
(二)改变行政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诉讼时效的长短体现了对相对人诉权限制的宽与松,而何时开始计算时效与司法救济的启动关联紧密。准确确定起算点有助于诉讼时效发挥实质功能,对破解当前司法困境有积极作用。但是,学界对行政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重视不足,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对此也未作调整。
国外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规定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以尽量客观化的标准来计算时效,一般以行政决定公布、通知、送达之日作为起算点;另一类则强调相对人的主观认知,以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决定开始计算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民事诉讼时效起算点兼采“主观主义起算点与短期时效结合,客观主义起算点与长期时效结合的两种情况”,旨在平衡债权人利益与交易外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问题,兼顾实现安全性和伦理性的双重目标⑨。这种做法是值得《行政诉讼法》借鉴的。行政诉讼“长时效”适用客观标准,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开始计算起诉期限,这是学界通识。争议焦点在于,采用“短时效”应从何时起算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建议行政诉讼时效起算点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开始计算。《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行政行为成立至相对人认为其权益受侵害的期间内,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没有任何异议,自然不存在行政争议,起诉权基础和行政诉讼对象不存在,无需计算诉讼时效。一旦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即产生行政争议,适格主体才可能启动行政诉讼程序。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应从行政争议产生之日起计算,而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并不一定会产生行政争议。这里有两个关键要素需要把握:(1)“认为”是判断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标准;(2)“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内容,同时也明确行政争议——“诉因”的产生。一般情况下,确定“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是法官窥探相对人主观认知的过程,需要借助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行政机关以公示、告知或送达等形式明示告知,是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前提,但仅根据获知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和内容即推断相对人意识到其权利受侵害恐有不当,具体裁量权应交由法官行使。至于行政赔偿、环境侵权等特殊行政纠纷,因其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具有长期性和隐秘性,对于是否造成损害、何时造成损害以及造成何种损害均可能存在认识盲区,实践中可结合医院诊断书、环境监测评估等文书予以佐证。
(三)起诉期限宜采用“短时效”主义,即适用少于6个月的期限
关于行政诉讼时效的修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延长诉讼时效至6个月或1年,认为只有更长的起诉期限才能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表面看修改后的诉讼时效较为符合世界主流趋势,但“6个月起诉期限更合理”的说法无充分实践支撑。为何仅6个月较为合适,而4个月、5个月甚或1年则不可?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维持3个月的“短时效”期限。日本通说认为,诉讼时效的设置是对“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的惩罚⑩,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使得大多数行政争议很难在3个月的期限内得到法院受理,于是延缓制度、中断制度以及起算点利于相对人等做法被视作“短时效”期限的重要部分。这样一来,也使得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角色更加灵活且重要,强调法院在时效审查中的独立性与决定性。我国延长诉讼时效仍属于问题导向型的修法措施,短期内能够提高行政诉讼受诉率,但从本质上较难维护权利救济与行政效率的平衡,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持续到法定期间,其获得公力救济的权利归于消灭的制度⑪。有学者认为,“需要一定的制度来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和考虑自己的处境,防止其躺在权利上‘睡觉’,以免增加法院在确认事实真相上的困难,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因时间的消逝所带来的不公正,保护被告在真正的事实再也无法被证明时免于有欺诈心的原告提起欺诈性的诉讼”⑫。那么,行政诉讼时效应是对相对人起诉权的限制,一旦相对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并超过法定期限,起诉权消灭,相对人很难再寻求司法救济;随即,行政机关获得执行行政决定或裁决的抗辩理由。
诉讼时效赋予行政机关抗辩权,有助于行政管理秩序良性运行,为行政效率原则的实现提供程序上的保障。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对立法目的的修改,兼采“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和“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⑬。一方面,充分保障个人权利是各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使“解决行政争议”回归至行政诉讼的基础功能,通过肯定或纠正行政行为以促进社会管理秩序的发展。行政管理活动面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一定时域、地域内,行政机关制定或实施的管理规则约束域内的公民行为。当行政权威遭遇相对人的挑战并诉诸诉讼,最终裁判关系着行政管理规则是否重筑、公民行为是否改变。可见,诉讼时效应当同时调整行政机关、特定相对人和不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设定或修改起诉期限是对相对人有限制的救济,不纵容其依仗法定期限恣意破坏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笔者建议我国行政诉讼时效采用“短时效”主义,即适用短于6个月的起诉期限:一方面,前文已对6个月诉讼时效可能带来的弊端进行较为充分的论证,且由于缺乏大量实践支撑,诉讼时效的延长需要谨慎;另一方面,结合起算点制度,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时效,即使适用“短时效”也能充分实现个人权利救济,满足现代公共行政对行政管理的要求。
(四)建立健全类型化和规范化的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学界呼吁对行政诉讼类型予以确定,据此配置不同时效方能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类型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赔偿判决等。有学者提出根据判决类型来划分诉讼类型,但这样的做法存有争议:其一,判决类型反映的是法院采取何种方式纠正或维持行政行为,虽体现了一定的诉求,但判决基础是法律依据和法律事实;其二,所列判决类型仅仅是时下行政诉讼能考虑到的范畴,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补偿采取何种判决形式尚需探讨,故不宜禁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其三,维持、撤销、履行等形式是合法性审查后的决定,若据此配置诉讼时效,有“未审先判”之嫌。
大陆法系国家在确定行政诉讼类型时基于各国法律传统而确定。比如,日本在《行政诉讼法》总纲中确定了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以及机关诉讼四种诉讼类型,又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分为处分的撤销诉讼、裁决的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和禁止诉讼等诉讼类型⑭,6个月时效仅适用于撤销诉讼,并受最长1年限制,其他类型如确认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则不受期限约束。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撤销之诉、课予义务之诉、确认之诉和规范审查之诉,撤销之诉和课予义务之诉适用1个月起诉期限,规范审查请求适用2年,政府草案则为1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撤销诉讼中心主义”⑮,15日、6个月、2年以及5年多适用于撤销诉讼和课予义务之诉。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精细化与成熟化。不同的诉讼类型反映不同的诉讼请求,应当有不同的诉讼规则与之匹配,包括原告资格、起诉期限、受理范围、审理程序、判决形式等。笔者建议我国《行政诉讼法》划分行政诉讼类型,据此配置不同的诉讼时效,促进合法性审查的准确性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高效性。但是,公益诉讼、行政补偿、行政指导等尚未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从全局上否定现有诉讼时效是不可取的。
首先,如何划分诉讼类型是确认诉讼时效的关键。有学者赞成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划分,包括撤销诉讼、给付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和确认之诉⑯,再根据具体诉求划分,如撤销诉讼可分为行为的撤销和裁决的撤销,确认诉讼可分为无效的确认、违法的确认等。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是可行的:一方面,划分标准由当事人诉讼请求决定,有利于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另一方面,较为概括的分类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预留了空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涵盖具体行政行为和附随审查规范性文件,但未涉及新兴行政行为以及部分行政法律事实等。
其次,应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设置不同的诉讼时效:(1)作为主要的诉讼类型,撤销诉讼所涉行政争议与社会管理秩序联系紧密,短期内更能减少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并保障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赋予其“短时效”更合理。“无论是3个月的普通起诉期限,还是行政机关未履行教示义务情况下不超过2年的时间限制,以及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情况下的5年或者20年的最长起诉期限规定,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目前的起诉期限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⑰,故笔者建议撤销诉讼继续适用3个月期限。(2)课予义务诉讼因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有及时性和迫切性要求,诉讼时效过长易使相对人长期处于不利状态,可以借鉴德国《行政法院法》的做法,使课予义务诉讼适用撤销诉讼“短时效”规定。(3)给付诉讼是基于既有法律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确认之诉是基于既有法律关系是什么而提出的确认请求权,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均既不会对现有秩序产生影响也不会产生新的法律秩序,不用设置特别的短时效予以限制,但应当受到最长诉讼时效的约束。为了促使相对人正确选择适用诉讼类型和诉讼时效,确认诉讼的适用应在其他诉讼类型均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才得适用。因为短时效对相对人积极履行诉讼权利有较高要求,一旦相对人怠于行使而故意选择不受期限限制的确认诉讼,将打破诉讼时效类型的平衡。
注释:
①徐继敏教授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规律应当逐渐发挥作用,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二元关系演变为政府、社会组织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参见徐继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回应》,《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
②参见徐继敏:《行政强制法实施面临问题分析》,《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6期。
③胡建淼教授将行政强制措施的特质归纳为“保障性”,即“为了保障一种秩序遵守”和“为了保障后续行为的作出和实现”。参见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④所谓“平静”利益是指“潜在被告的心平静下来,不用担心被起诉”。参见[美]沃德·法恩斯沃思:《高手解决法律难题的31种思维技巧》,丁芝华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⑤参见应松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⑥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16页。
⑦参见杨伟东:《行政诉讼制度和理论的新发展——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评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⑧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卷),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565页。
⑨参见包晓丽:《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与取得时效的衔接问题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⑩参见[日]山本敬三著、解亘译:《民法讲义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432页。
⑪参见肖泽晟:《我国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
⑫ See James R.MacAyeal,The Discovery Rule and Doctrine as Exceptions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for Civil Environmental Penalty Claims,15 Va.Envtl.L.J.589,591(1995—1996).
⑬德国采用“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认为行政诉讼法的功能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客观秩序的维护只是衍生的附随功能。英美国家实行司法审查制度,注重对“人权”的维护,即在公正、公平的司法理念下,主要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法国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狄骥则主张通过行政诉讼所获得实体权利的维护,也是对社会既定法律规则的遵守,是对客观秩序的坚持与维护。参见邓刚宏:《论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及其理论价值》,《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
⑭参见王丹红:《诉讼类型在〈日本行政诉讼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
⑮所谓“撤销诉讼中心主义”是指,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而构建,忽视其他诉讼类型的特殊性,而将行政撤销诉讼的规定适用于所有行政诉讼活动的一种现象。参见熊勇先:《论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及其缓和》,《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6期。
⑯参见吴华:《行政诉讼类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章志远:《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8—99页。
⑰参见林俊盛:《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Dilemma and Adjustment:Prolonging Timing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YangDan,Xu Jim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amended in 2014 has prolonged the timing when the plaintiff is allowed to sue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and the duration has been extended to 6 months after the agency makes the decision.This amend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tecting plaintiff’s right to sue,but creates new obstacles to several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resulting in low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The main reason why new timing can not make a balance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right relief is that the duration of 6 months is relatively too long,not typed and even incorrectly attached to some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It is quite critical to remo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iming and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by amending some laws and regulations.Based on particularities involved in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we suggest that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hould redefine the timing to start counting the duration,and adopt the short duration mode combined with classification,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iming system completed perfectly.
Sue duration;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Protection of Plaintiff’s Rights;Classification of Duration;Timing to Count the Duration
D9
A
1007-905X(2017)11-0051-07
2017-06-05
1.杨丹,女,四川大学法学院2014级宪法和行政法博士研究生,美国EmoryUniversity法学院2015—2016年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研究;2.徐继敏,男,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研究。
编辑 潭 影 王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