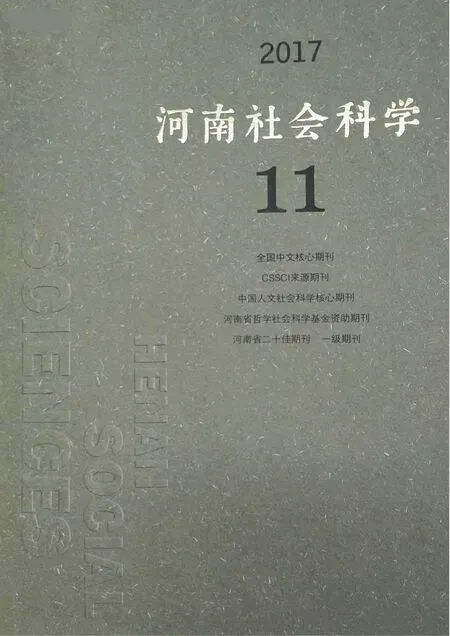权力规制:政治秩序场域中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
2017-03-07雷振文
雷振文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权力规制:政治秩序场域中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
雷振文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随着社会结构、利益和观念的分化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利益集团”①已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成为政治秩序场域中极其重要的行动者,以至于政治过程论的创始者本特利发出诸如“如果能解释利益集团,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了”②的感叹。针对利益集团介入政治过程、影响政治生活的事实,尽管一些人抱着热情支持的态度,但还是存在着很多理性批评的声音,“它们试图通过影响与它们自身有关的公共政策来提高或促进集团内共同的利益”③,“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④。正是基于对利益集团介入政治过程的怀疑和批评,欧美一些国家对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其中的一些成果对中国而言不无裨益。
一、政治秩序场域中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表现
就利益集团和政治秩序关系而言,政治秩序是利益集团行动的既定政治场域,利益集团是影响政治秩序的重要行动者。作为政治秩序场域的重要行动者,利益集团对政治秩序的消极行为值得警惕。
(一)利益集团侵蚀政治实体
政治实体指的是包括政府、政党和公民个体等在政治秩序场域中活动并对政治秩序的运行过程及其状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行动者。利益集团对政治秩序的消极行为常常是从影响或试图影响不同政治实体开始的。
(1)利益集团“俘获”政府。“俘获”政府指的是政府部门或其工作人员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而导致公权私用、失去自主性的现象。可以说,这种现象从利益集团出现并介入政治过程就开始不断地发生,这在西方国家尤为普遍。就此现象,奥巴马甚至喊出了“华尔街是令人愤怒的势力”的声音。在非西方国家,“俘获”政府现象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不同程度出现了利益集团控制政府、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勾结瓜分公共财产,乃至为维护既得利益设置垄断,以牺牲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代价牟取个别集团利益的现象⑤。而且,纵观当今许多国家的政治过程,一定会看到“俘获”政府现象在其政治生活中已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俘获”方式也越来越深入和隐蔽。例如,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财政资金的分配和染指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集团独占化;通过手中掌握的大量政治或经济资源行贿各级政府官员,使政府官员参与决策的公共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扭曲和截留政府推行的公共政策使其无法有效落实和执行。自然,政府在利益集团的裹挟下,其独立性、公共性常常变异走样,失去其在政治秩序运行中的自主性。
(2)利益集团弱化政党能力。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普遍运行的政治现象,政党是政治秩序场域中的关键行动者;不从政党的视角去把握一国的政治秩序,是不可能清醒地理解一国的政治的。亨廷顿认为:“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也认为“高度组织的政党占据着政治结构的中心位置”⑦。可见,对政治秩序而言,政党能力特别是执政党的能力是决定其运行状况的关键因素。然而,政党能力却不断地遭受来自利益集团的各种挑战。例如,利益集团通过立法的方式,堂而皇之地将自身局部利益合法化,歪曲执政党的执政指向;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排他性以及分裂的集团意识形态,加剧了执政党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难度。同时,利益集团的资本与执政党的权力的媾和会导致执政党内部出现权钱交易、利益交换等腐败现象。事实上,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秩序的失序、混乱甚至坍塌无不是与利益集团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能力的销蚀相关的。
(3)利益集团撕裂公民个体的政治情感。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以公民个体为基础,公民个体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最广泛、最基本的单元。对此,王沪宁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本身的政治发展。”⑧然而,现代政治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公民个体基础越来越受到利益集团的消融。利益集团凭借在利益链上的优势地位攫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造成公民个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财富差距悬殊,导致公民个体间利益分配失衡;利益集团凭借其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社会阶层流动机会上处于先天的有利位置,并造成阶层固化、阶层鸿沟的现象产生。而利益是公民个体最敏感的神经,其对政治秩序的基本情感常常也是维系在自身利益是否得到公正的关照、对待之上的。利益集团的掠夺所导致的公民个体间的利益失衡和固化现象必然撕裂公民个体对政治秩序的情感,造就的要么是愤懑的公民个体,要么是冷漠的公民个体,绝不可能是政治秩序的支持者,而没有或缺乏公民个体认可、支持的政治秩序一定不会走远。毕竟,“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稳定的政治秩序不仅是指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心认同和信仰”⑨。
(二)利益集团破坏政治规则
政治规则是特定政治体系用以规范、调整体系里所有个体或群体形式的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是政治秩序可能形态的直接决定因素,因此,对政治规则的侵蚀是利益集团的重要目标。
(1)利益集团消解政治制度效力。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秩序是政治制度得以持续创新和得到严肃认真执行的产物和体现,缺乏政治制度的持续创新,政治秩序不可能长期维持;没有政治制度的严肃认真执行,政治秩序也难以稳定运行。可是,一些利益集团却罔顾政治秩序的安危,一心为谋取自身利益而竭力消解政治制度的效力。譬如,制度创新是政治秩序持续发展和稳定运行的动力和基础,但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也常常是特定制度的结果。为保持既得的利益并从既有利益格局中持续获利,利益集团具有天然的制度惰性,极力阻碍制度创新。正所谓“特殊利益集团一旦从某种制度安排中得利,为了保守住他们的利益,就不愿推动制度创新。他们拒绝对迅速变化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决策或行动迟缓,对凡是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概排斥,并且为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而不惜牺牲全社会的利益”⑩。另外,制度的效力必须以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为前提。同样,对政治秩序而言,其生命力也在于政治制度的贯彻和落实。然而,一些利益集团为了维护集团的局部利益,通过歪曲、扭曲和架空等非法手段,掣肘既定制度的有效执行,使制度的运行流于形式、失去效力,从而影响政治秩序的具体形态。
(2)利益集团毒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反映的是支撑和引导特定政治体系的各种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状况的综合运行环境,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是政治生态的集中体现。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利益集团不但消解着显性的政治制度效力,而且也破坏了隐性的政治规范的约束力,秉持狭隘、自私甚至堕落的政治价值取向,视国家、民族、公民为一己私利的绊脚石,无任何大局、全局观念,无点滴家国情怀,无半点敬畏尊崇人民的情感,严重毒化着政治生态。例如,一些利益集团在执政党内以“山头主义”的形式出现,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视执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如儿戏,败坏了党风;一些利益集团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法手段染指政府公权力以达到其利益最大化之目的,败坏了政府风气;一些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上,致使社会上“潜规则”盛行,积累和形成与文明进程极不适应的落后文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些利益集团干扰资源配置,扰乱市场秩序,使交易成本增加,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幅降低;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着意把资本逻辑注入政治关系,使政治关系庸俗化、功利化、短视化,严重影响政治体系的政治文明进程。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个体层面等不同领域的肆意横行所造就的恶劣政治生态,必然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
(三)利益集团干扰政治控制
政治秩序的具体运行过程和最终呈现形态常常取决于政治控制这一环节。政治控制不科学或软弱无力不但严重制约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而且也直接关系着政治秩序的认同度。因此,政治控制自然也成为利益集团重点干扰的对象。
(1)消解政治权威。就现代政治体系而言,政治控制是权力与权威相辅相成的政治过程,不能仅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威慑,更应是一种以自觉服从为基础的政治权威的宣示。“政治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权威的过程;民主的目标,就在于把权力转变为权威。”⑪政治权威涉及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是一种获得人民广泛、自觉支持的合法性力量,也是政治控制在现实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能够规范、调节政治关系,引导政治行为的重要原因。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利益集团通过消解政治权威而干扰政治过程的方式可谓是全方位的。例如,通过“俘获”政府,使政府失守自主性,不能客观公正地作出相关决策,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对这种失去自主性的政府而言,政治权威自然就是一种奢望,更遑论其政治控制的效力了。又如,通过“绑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降低普通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使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失去公信力而降低政治权威。再如,利益集团利益排他性的本质及其带来的利益分配差距扩大化的后果所导致的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加剧,进而冲击现存政治体系的政治权威。
(2)侵占政治控制资源。政治控制资源是政治体系开展政治过程,规范、调整或约束体系中所有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维系自身稳定持续运行所凭借的一切人力、物力和精神性力量等的总称。政治控制是与这些资源的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政治控制则无以展开。通常而言,政治控制资源的多寡与政治控制功能实际效果具有线性关系。因此,围绕政治控制资源的争夺,利益集团更是动作频频。例如,通过向政治体系输入自己的人员,培植在政治体系的代理人;通过赤裸裸的资本、资源优势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抢占公共资源、染指公权力;通过扭曲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机制,使政治控制主体能够有效运用的资源急剧流失。此外,一些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还通过媒体、行业协会、专家论坛等形式和渠道抢占公共话语权、引导舆论走向,以达到为特定集团利益服务之目的。利益集团在政治控制资源方面的这些消极行为,必然使政治控制的秩序实现功能难以奏效。
(3)弱化政治控制机制。政治控制机制是政治控制主体在实施政治控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实际上,政治控制体现的是政治控制主体应用一系列刚性或柔性的政治控制机制,对政治控制对象进行规制、调节和引导的政治过程。政治控制机制的多寡、强弱、合法与否,直接决定政治控制的秩序实现功能的状况。利益集团深谙此道,在弱化政治控制机制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政治生活中常见的诸如权力腐败、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就是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对政治控制机制进行各种形式的消解,从而导致政治控制秩序实现功能弱化的结果。例如,法律本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控制机制,但是利益集团凭借其在经济、社会地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和与政治体系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法律的制定、颁布和执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强势的话语权,破坏着法律的公正性,影响法律的秩序诉求。又如,政治道德是公权力履行者的内在约束,是政治行为的基本遵循,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规范秩序作用的政治控制机制。然而,在利益集团的腐蚀、诱导和扭曲下,政治道德的规范作用常常被击得粉碎,使得一些公权力履行者一再突破政治道德底线,腐败频发。作为政治控制秩序实现功能的直接“工具性”手段的政治控制机制被利益集团肆意践踏,必然导致政治控制的虚无,无法实现由可能秩序到现实秩序的转变。
二、政治秩序场域中对利益集团规制的他山之石
在欧美一些国家,虽然“利益集团数量特别庞大,而且处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可听到它们的声音”⑫,但是其行为却常为人所诟病。奥尔森就很担忧利益集团会“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体制、政策与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动力越来越被抑制”⑬,最终导致政治秩序的失序、混乱或崩塌。为此,欧美一些国家在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方面作出了较为丰富的探索。
(一)以坚守政府自主性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
政府是政治秩序的能动性要素,其能否客观公正地施政,关系着政治秩序的潜在方向。这就涉及政府自主性问题了,政府自主性程度深刻影响着政治秩序的状况,政府自主性是政府在切实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基础上所表现和发挥出来的对社会特殊势力的超越性。亨廷顿认为,政府自主性程度主要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⑭。
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秩序的消极影响常常是从侵蚀政府自主性开始的。洛伊指出,利益集团使政府的政策受到歪曲,使现代民主政府腐化,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期望,对民主基本上是不尊重的;它使政府无能,不能计划;它以关心管辖权限,即由哪些采取行动的人作出决定,来代替关心正义,致使政府道德败坏⑮。谢茨施耐德也认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即具有强烈的上层阶级和商业倾向,直陈“多元主义天堂里的弊端是,天堂唱诗班的音调里充满了上层阶级口音。大约有90%的人与压力体制无缘”⑯。于是,他们提出要在厘定政府权力限度和能力的张力中坚守政府自主性以应对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消极行为。他们深信,只有厘定权力的限度,使政府归位、守位,才能有效防止政府的“扶持之手”蜕变为“掠夺之手”,从而减少政府被利益集团侵蚀的机会;而权力的能力则是政府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偏好的保证,有助于政府独立自主地运用公权力去推动公共利益的落实。因此,欧美一些国家常常致力于“强化政府权力以提高政府抵制利益集团影响的能力;强化政府整合能力,以提高政府利益综合与公共利益实现功能;提升政府道德纯度,以求能够在各利益集团奉承讨好和游说压力下站稳立场,自觉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坚持公共利益取向”⑰。
在非传统西方国家,对政府自主性也非常重视。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经济与政治是规则不同的两个领域,一旦经济精英,尤其是掌握巨大财富的经济寡头进入政治领域、掌握政治权力,就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巨大危害,甚至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⑱。于是,普京严禁利益集团向政权渗透,明确要求他们“只赚钱,别夺权”,决不允许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普京竭力维护政府自主性,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之物……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⑲。
(二)以提升政党能力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
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来看,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这一事实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了。在政党政治下,作为政治秩序的能动性要素,政党无疑占据着政治秩序的中心位置,是政治秩序的核心政治实体的承载者,对政治秩序的运行状况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古德诺就认为:“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才能分担政府职能。”⑳亨廷顿更是强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㉑
对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利益集团再明白不过了,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对政党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诱导政党的行为、理念和决策,从而最终实现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在研究英国政治的过程中,塞缪尔·比尔就发现,利益集团的竞争使政党再也不能根据全民族的利益来制定政策,而只是力图赢得更多利益集团的支持。但由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要求在许多问题上又彼此内在冲突,从而导致“公共选择的瘫痪”㉒。事实也表明,在一些政党衰弱和政党腐败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利益集团常常十分发达、众多,也非常不均衡,一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巨大。因此,政党及其能力的提升就被寄予厚望,希冀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在美国,有学者甚至呼吁: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政党已被利益集团所压倒,而在于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全国性政党领导层还没有产生。由于缺少这样的领导层,政党就不能利用他们的优势,只能被利益集团所骚扰。如果没有强大的全国性政党领导,那么谈论利益集团的控制就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因此,除了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外,没有一种民主的办法可以使公众免受利益集团的侵害㉓。毕竟,只有具备强大能力的政党,才能够整合社会多元的利益诉求,从而避免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才能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持续运行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三)以加强法制建设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
法律既是政治规则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又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控制机制。依托法律来厘定利益边界、遏制利益膨胀从而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是一些西方国家特别倚重的手段。
美国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规制的相关法律相对比较完善。诺曼·杰·奥恩斯坦认为:“将院外活动公之于众是国会和公众评价集团合法性的一种方法。”㉔为此,美国早在1946年就颁布了《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规定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信息必须公开,对利益集团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进行了刚性规范。2002年,美国通过了《竞选资金改革法》。该法案对竞选捐款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详细的规定,严格限制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进行利益输送。在规制和防范利益集团消极行为方面,美国还通过《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院外活动集团公开法》《联邦竞选活动法》等法律对利益集团试图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同时,为限制和规范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与利益集团发生不正当的经济、政治行为,美国通过了《从政道德法》《从政道德改革法》《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等法律对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进行规范,防止公职人员或所在机构被利益集团所绑架。
加拿大也重视法律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规制作用。为防止公职人员沦为利益集团的帮凶或猎物,加拿大制定了《利益冲突法》。该项法律对公职人员履职过程中大量潜在的风险境况都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警示,要求公职人员自觉避免那些能够对其带来或造成益处的场景。加拿大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较好地限制了政府公职人员与特定利益挂钩的可能性,减少了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机会。
三、政治秩序场域中利益集团规制的中国途径
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成长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逐步收缩、还权于社会的必然结果。犹如奥尔森所言:“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㉕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回事儿。某些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是另一回事儿。世界各国对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都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对当代中国而言,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警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012年1月,汪洋在广东省委全会上谈及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与此同时,学界也对利益集团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2006年,学者江涌就警示:“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㉖2014年,学者黄世坤提出,我国目前已至少形成了“黑商”利益集团、“外损”利益集团、买办利益集团、西化利益集团、贪腐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僵化利益集团等七大类阻挠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团㉗。
党的十八大以来,利益集团及其消极行为问题越发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把利益集团尤其是党内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与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结合起来思考,在多个不同场合严肃地谈及此问题。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就鲜明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利益集团”;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提到“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郑重告诫党内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学界和社会公众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一定程度的共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公开、罕见的警示,都表明了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严重性及其治理的必要性。因此,为防范利益集团消极行为对政治秩序的影响,我们应在吸收、借鉴他国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再出发,从推进我国政治秩序持续稳定运行的高度探寻自己的应对之途。
(一)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要增强政治实体的防范能力
政治实体是政治秩序的建构者与维护者,利益集团对政治秩序的各种消极行为通常是以政治实体为首要作用对象的。因此,应对利益集团的侵蚀,政治实体必须具有坚定的防范能力。
一是要着眼于政府自主性,增强政府的防范能力。政府是一种重要的、经常的、普遍的政治实体,对政治秩序的建构、运行与维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否客观公正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介入政治过程,将直接影响着政治秩序的具体形态。为此,要在准确厘定和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问题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并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政府运行机制,使各级政府权责分明、边界清晰,避免政府职能越位和错位,切实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提升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只有打造透明、开放的政府,坚守政府应然定位,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才能斩断公权力和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脐带,切实坚守政府自主性。
二是要着眼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执政党的防范能力。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政治秩序的中心,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政治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秩序的具体形态有着决定性意义。政党政治的逻辑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秩序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丧失或不能保持先进性的政党不可能长期成为政治秩序的中心,不可能推进政治秩序的持续稳定运行,不可能决定政治秩序的具体形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重视这一历史经验,切实持续不辍地搞好自身建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㉘的警示,不断提升应对各种利益集团侵蚀的防范能力。
三是要着眼于公民个体的政治理性,增强公民个体的防范能力。公民个体,作为一种基础而又为数最多的政治实体,不但是政治秩序的最基本的行动单元,也是政治秩序运行状况的评判者,对政治秩序的具体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秩序能够无视公民个体的感受。公民个体的政治理性是政治秩序的重要变量,政治秩序的优劣、运行状况、持续时间等都与其息息相关。利益集团消极行为不仅侵蚀着政治秩序,更直接的是损害着公民个体的利益。因此,要达到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有效规制,必须把有政治理性的公民个体找回来。如果没有或缺乏公民个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尽管有的政党、政府的力量确实很强大,但是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规制恐怕也会事倍功半。杰瑞米·波普指出,公众对于这些不良行为的感知以及那些被证明是正当的公众的愤怒才是社会的最后防线㉙。为此,提升公民个体的政治理性是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重要途径。
(二)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要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
政治规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以显性的政治制度和隐性的政治规范对包括利益集团在内的各政治实体发挥着刚性调节作用,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既定环境。在一些利益集团看来,政治规则就是他们的“拦路虎”。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诋毁、攻击、扭曲和破坏。因此,落实并体现出政治规则的效力,是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有效之策。
一是要在政治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政治制度是政治规则的重要表现形式,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首先就要凸显政治制度的效力。尽管政治制度是对政治实体意志的制度性表达,但政治制度并非始终是被动的,相反,它一旦被建构出来就对政治实体有普遍的、刚性的约束作用,毕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秩序是政治制度得到普遍遵循的结果,它们之间存在着正向对应关系,政治制度越是得到严格执行,政治秩序越是持续稳定。对此,亨廷顿断言:“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和地区性的欲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㉛因此,防范一切冲击或试图冲击政治体系的行为,严格执行政治制度,切实发挥其内在的对政治实体的普遍约束作用是一种重要途径。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面对来自利益集团的种种阻挠,不能对“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㉜听之任之,而是要严格落实并发挥制度的威力,扎紧、扎牢防范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篱笆。
二是要在增加政治制度的供给中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制度执行不力是导致利益集团消极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同样,制度供给短缺也给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发生提供着方便之门。然而,制度供给短缺似乎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制度的创设、配套、系统化等都是一个实践问题。事实上,尽管我国政治领域较早就走上制度化之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体系,但是,在政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制度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制度真空、制度冲突和制度空转等现象。这就给利益集团造成可乘之机,他们常常利用制度真空、制度冲突和制度不配套等制度供给短缺现象向政治体系发难,影响政治秩序持续稳定运行。对此,有学者已经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畅通的熔炉式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就会加剧多元利益的摩擦与冲突,妨碍社会稳定。”㉝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政治制度体系化进程,并切实提升相关制度的科学性、配套性,不给利益集团消极行为以“飞地”。
三是要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政治生态既是政治规则的结果,同时又是巩固政治规则的原因。通常而言,科学并得到遵循的政治规则对应着优良的政治生态,优良的政治生态强化着科学的政治规则。因此,营造一种优良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政治规则在政治生活中扎根,有利于政治规则内在固有的普遍性约束效力的发挥。因此,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规制可以从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着手。具体到中国,就是要发动包括政党、政府和公民个体等其他政治实体全面投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活动中去,贡献各自的力量,使利益集团成为一种遵纪守法的社会力量,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正能量。
(三)规制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要切实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
政治控制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实现及其具体呈现形态。是反映人们共同意志为人们所认可支持还是仅仅追求局部狭隘利益为少数群体所张目,政治秩序的这种分野同政治控制的水平息息相关。毕竟,“善的生活”的愿景、科学严密的政治规则,在拙劣的政治控制情境下,只能成为利益集团的玩偶。因此,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还要着力提高政治控制水平。
一是要在强化政治权威中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政治权威表征的是一种主体被客体自我认同并自愿服从的精神性力量,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政治控制不是主体单方面的肆意妄为,而是需要客体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就二者关系而言,政治权威是政治控制的重要支撑,缺乏或没有政治权威,政治控制要么难以为继,要么堕落为单纯的政治强制;而无论是政治控制的“缺场”还是单纯的政治强制,都无助于政治秩序的持续稳定运行。政治权威与政治控制之间的这种线性关系,说明政治控制水平的提高必须以政治权威的增强为条件。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以持续性社会合理要求的输入和有效政治产品的输出不断赢得广大人民的认同;必须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警惕权力的自我膨胀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㉞,把权力转变为权威,压缩利益集团消极行为发生和存在的空间。
二是要在掌控政治资源中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控制尽管不是或不总是血雨腥风,但也绝非请客吃饭、一团和气,同样需要以强大的政治资源为后盾。不掌握权力,缺乏政治资源支撑的政治控制,难免成为政治控制客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取其辱。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控制的水平取决于政治资源的掌控程度。政治资源掌控得越多,政治控制的水平就越高;尽管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但政治资源的多寡对政治控制水平的影响确实存在。因此,尽可能地掌控更多的政治资源,就成为提高政治控制水平从而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明智选择。对中国而言,尽可能地掌控政治资源对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保证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等国家公器和其他重要公共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防止利益集团巧取豪夺,形成“山头主义”;必须坚守意识形态的主战场,牢牢掌握报刊、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的主导权,防止利益集团抢占公共话语权,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必须积极主动地引导以互联网、电子传媒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舆论走向,防止利益集团利用它们寻求非法影响。
三是要在彰显法治中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政治控制是一项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必然存在联系两者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各种政治控制机制,它可能是政策,可能是道德,可能是行政命令,也可能是法治等。当然,尽管不同的政治秩序会有不同的政治控制机制的运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法治形式的政治控制机制。对以民主为政治发展目标的中国而言,彰显法治在政治控制机制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毕竟,民主需要制度化、程序化,而“法律的作用不在于束缚人类的一切行为,而在于引导人们走正确的道路,从而建立起确定的社会秩序”㉟。为此,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㊱,形成“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㊲的良好局面,使法治真正成为规制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利剑。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利益集团”,仅指那些具有共同的利益或价值观,以利益联盟为纽带,为占有或支配公共资源而影响或试图影响政治体系的特定组织。
③⑫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5页。
④㉔诺曼·奥恩斯坦:《利益集团、院外活动与政策制定》,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33页。
⑤⑩杨帆、张弛:《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一个跨学科的综述》,《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⑥⑭㉑㉛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⑧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⑨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⑪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⑬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⑮ Theodre J.Lowi,The End of Liberalism,New York:Norton,1969.
⑯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⑰龙太江:《西方国家利益集团规制思路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⑱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⑲普京:《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⑳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9页。
㉒ Samuel H.Beer,Britain Against Itself: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Collectivism,New York:Norton,1982.
㉓ Willam J.Keefe,Morrs S.Ogul.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Process,6th ed.Englewood Cliff s,N.J.Prentice-Hall,1985.
㉕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㉖江涌:《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
㉗黄世坤:《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利益集团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㉘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第2版。
㉙杰瑞米·波普:《制约腐败——建构国家廉政体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㉚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226页。
㉜陈泽伟:《突出反腐四大制度建设》,《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期。
㉝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0页。
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㉟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0页。
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
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Party Discipline:Research on Powe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f power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It is not only the key to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the core of the party to build a clean government and combat corruption to solve problems,but also the important way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The serious challenge fac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its supervision of power.The ultimate goal is to find out the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self-monitoring under the long-term rule of the party.In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Merge Work System of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ommittee,it is pointed out tha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ystem is the merge work of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lies 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tegration of supervision subjects,object,content and means,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improvement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anti-corruption work,optimization of the ma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system of power supervi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he Debate of Public Benefits and Private Interests: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urpose of Power Supervision,it is pointed out that while the existence of the private interests is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but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private interests will restrain the proper efficiency of power supervision,and trigger the mutual suppression and imbalance of power and rights,and aggravate the degrad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refore,the purpose of power supervision should be public welfare,and mutually beneficial so as to regulate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and ensure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balance and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upervision.InThe Negative Behavior of Interest Groups in Political Order Field and Its Regulation,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gulation of negative behavior of interest group in China should be focused on government autonomy and the ruling party itself,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 citizen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political entities.The other focus is on the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increase in suppl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ecology.All three articles have real insights and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mor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work practice of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cpc.
National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tem;Merger Work System;Power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olitical Order;Interest Group;Ecology
2017-08-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ZZ002);2013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Z1304)
雷振文,男,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