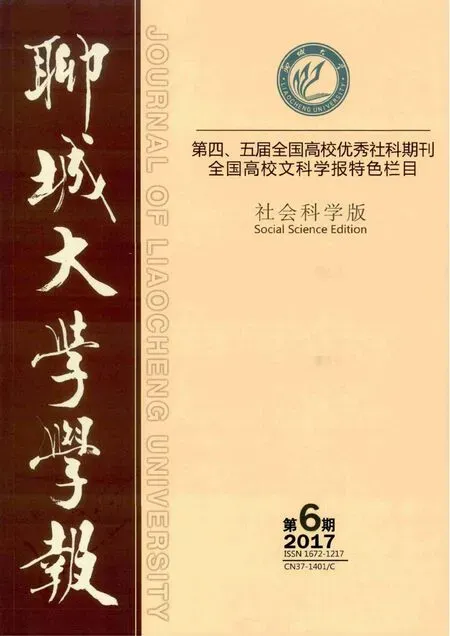清代皇子教育与经筵制度关系探析
2017-03-06许静
许 静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北京 100009)
清代皇子教育与经筵制度关系探析
许 静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北京 100009)
清代的皇子教育制度随着清朝的建立、发展、强大,逐步趋于完备,即使在清末国势衰败的情形下,皇子教育依旧是政务中的重点;经筵制度恰恰相反。清代的经筵制度在康熙朝前期达到鼎盛,康熙中期以后经筵制度开始衰落,之后经筵制度成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典礼。两种制度呈现出互为消长的趋势,皇子教育不完备时,经筵制度普遍受到关注并得到了有效的实施;随着皇子教育逐渐完备,经筵制度具有的教育功能大大减弱,最终流于形式;到了清朝晚期,皇子教育模式甚至完全替代了经筵制度。
清代;皇子教育;经筵制度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统治,使“人”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而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更是其核心部分。因此,皇子教育制度与经筵制度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
中国古代皇子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已有了辅导太子的官职。《大戴礼记•保傅》记载:“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保谓安守之;傅,傅其德义,傅犹敷也;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①[汉]戴德:《大戴礼记》卷3,《保傅》第4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师”、“保”、“傅”便成为太子老师的专称。师保如何教导太子,《通志》中有详细的记载:“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昬焉,以怵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②[宋]郑樵:《通志》卷92,列传第5,《申叔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这里,《春秋》、帝王世系、《诗》、礼仪、音乐、善言嘉语、先王法令、历代兴衰故志、训诰典志,都是太子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教育太子发挥着它们各自的功能。
经筵制度亦有其渊源,有记载:汉武帝时,兒宽见帝语经学;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论五经于石渠阁;光武平陇蜀后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唐太宗时,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又命孔颖达讲五经正义;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选耆儒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③[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10,官制门,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筵”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于宋初,历经几朝皇帝,在仁宗朝,经筵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专门官员诸多要素齐备,经筵制度完备并最终确立。《宋大事记讲义》中记载:“祖宗好学,世为家法。盖自太祖幸国庠,劝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其所以示后世子孙者源远而流长矣。自太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乾兴末,双日御经筵,体务亦不废,而日御经筵自仁宗始。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置侍读,中丞始御讲习,宰相始御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①《宋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御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历史上的经筵制度可以说是作为皇子教育的补充形式出现的。在皇帝幼年登基、没有接受完整教育的情况下,经筵显得格外重要。以清圣祖玄烨为例:玄烨八岁登基,虽然他自幼在祖母孝庄文皇后那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毕竟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因此,他登基后更加笃志于学习,开经筵、重儒学;另外一种情况,皇帝即使成年登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如明熹宗朱由校。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后,皇太子朱常洛即位不久亦死去,由十五岁的长子朱由校即位。由于朱翊钧对朱常洛并无好感,对皇孙朱由校漠不关心,以至于朱由校一直未能出阁读书,直至即位后才开始接受教育。此时,经筵制度尤为重要。天启元年(1621)正月,韩爌、刘一燝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月即开经筵”,从之,自后日讲不辍。②《明史》卷240,列传第128,《韩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清代的皇子教育制度与经筵制度发端于皇太极时期,并伴随“尊孔崇儒”这项重要国策的实现逐步完善与发展,成为了满族贵族认同与接受儒家文化、实行“崇儒重道”的统治政策的重要方面。
早在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就认识到“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③《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的治国理念。天聪五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深深触动了皇太极,在这次战役中,明朝官兵在弹尽粮绝的境况下仍坚持死守。皇太极认为这种行为“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④《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条。于是,皇太极更加重视让满洲子弟学习儒家文化,命诸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者读书习文,以达到讲明义理、忠君亲上的目的。⑤《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条。这应当是清代较早的提出以儒家伦理教育子弟的记录;与此同时,大臣中开经筵的呼声也渐渐出现。天聪六年(1632),汉官王文奎等人提出将《四书》、《孝经》中的章句翻译成满文,每日向皇太极进讲,从而使皇太极能够“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越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⑥《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天聪朝臣工奏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应当是清代最早提出开经筵的记载。
皇太极认识到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从而产生了以儒家文化教育皇子及宗室子弟的想法;王文奎提出了用儒家经典来启迪君心、培养君德。至此,儒家文化在统治阶层政治教育中占据了主导的位置,清代的皇子教育与经筵几乎同一时期被提出,并走向制度化。也是在这一时期,两种制度被确立了共同的原则,即: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保留本民族的特点,防止全盘汉化。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召诸王、大臣听讲《金世宗本纪》,听后,皇太极为诸大臣讲解心得,他将金国的灭亡归咎于“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并表示自己不会效法金国尽学汉俗,而是要时刻不忘满洲旧制,不废骑射。⑦《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条。
于是,清代的皇子教育与经筵制度在清初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端并逐步发展。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子教育和经筵制度的实践与发展是在满族贵族接受儒家文化、利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的这一统治思想的指导下相互交替中进行的。进一步探究却发现,这两种制度在清代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清代的皇子教育制度随着清朝的建立、发展、强大也逐步趋于完备。即使在清末国势衰败的情形下,皇子教育依旧是政务中的重点;经筵制度恰恰相反。清代的经筵制度在顺治晚年得以确立,康熙朝前期达到鼎盛,康熙中期以后经筵制度开始衰落,之后便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典礼。两种制度呈现出互为消长的趋势,大体上来说,皇子教育不充分的时期,经筵制度普遍受到关注并得到了有效的实施;随着皇子教育逐渐完备,经筵制度具有的教育功能大大减弱,最终流于形式;到了清朝晚期,皇子教育模式甚至完全替代了经筵。下文将分阶段对其进行阐释。
一、皇子教育的阙失与经筵制度迅速发展——顺治朝及康熙朝前期
皇太极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军事战争和内部各派的权力斗争都在激烈的进行,巩固新政权才是当务之急。因此,皇子教育制度仅仅处于草创阶段。皇太极死后,满族新政权内部围绕着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明争暗斗,五岁的福临最终被拥立为帝,多尔衮摄政。福临幼年即位,并在复杂的内外斗争中长大,因此他并没有获得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康熙帝即位时情况亦然。康熙帝即位时不满七岁,再加上顺治帝本人在皇子的教育问题上并无更有效的实践,使得康熙帝在皇子时代缺乏系统的学习。康熙皇帝晚年回忆他皇子时代所受到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孝庄文皇太后:“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无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①康熙《庭训格言》,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所以,清前期的皇子教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开经筵势必成为朝中满汉大臣所关注的焦点。顺治、康熙初年,不断有大臣纷纷上书请开经筵:
顺治元年(1644)十月,户部给事中郝杰上奏疏:“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尊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②《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申条。
顺治二年(1645)山西道监察御史廖攀龙奏云:“圣学之宜早讲也。皇上天亶聪明,无待学。正惟天亶聪明,最易学。今天气和煦,时候清闲,经筵虽未遽开,请于视朝之暇,集满汉端方博雅大臣,取往古治乱兴亡之迹,进讲数条,以资启沃。则知为君之难,为首出开创之君尤难,而万年有道之长肇基于此矣。”③《皇清奏议》,卷1,《山西道监察御史廖攀龙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顺治九年(1652)四月,礼部在议覆科臣杨璜的疏言中亦认为:“春秋各举经筵一次,礼不容缺,今应于文华殿旧基,从新建殿。”④《清世祖实录》,卷64,顺治九年四月乙丑条。
顺治九年(1652)九月,“工科给事中朱允显请举行经筵日讲,慎选满汉儒臣,请求至道,疏下所司。”⑤《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辰条。
顺治十年(1653)七月,刑科给事中陈忠靖上奏:“若不速开经筵,于前代所以格天勤民之学,实实讲求,终无裨益,文华殿又以钱粮不敷,暂许罢工,如此因循,恐非汲汲集求治之盛意也。”⑥《清世祖实录》,卷77,顺治十年七月辛酉条。
顺治十年(1653)九月,工科给事中朱允显再上请开经筵一疏,彰显汉臣欲顺治勤学、培养君德之心切,“臣前具有开经筵一疏,礼臣覆以文华殿修成为期,窃以天下之治,由乎君德,而君德之成,本于经筵。讲幄之设,历代首重。我皇上以尧舜自期,动合古道,此时正宜好学深思,俯咨下问,广选满汉儒臣,召见便殿,朝夕考究,于经、史之外,随事询访。”⑦《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九月戊寅条。
顺治十年十月,兵科给事中张睿再次奏言开经筵,曰:“又见诸臣疏请经筵日讲,屡奉谕旨,仰见皇上典学图治之盛心也。请于临朝听政之暇,命儒臣取《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详悉敷陈;复取宋臣司马光《资治通鉴》,列为法戒。”①《清世祖实录》卷78,顺治十年十月戊辰条。
可见群臣要求开经筵之迫切。
康熙朝亦如此。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刚刚即位尚未改元之际,就有大臣迫不及待的要求开经筵,以加强对少年皇帝的教育。之后,陆续有满汉大臣提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熊赐履。康熙六年(1667)六月,熊赐履上“应诏万言疏”,其中提出择选儒臣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尤其强调研习《大学衍义》,“《大学衍义》尤为切要下手之书,其中体用包举,本末贯通,法戒靡遗,洪纤毕具,诚千圣之心传,百王之治统,而万世君师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②《清圣祖实录》卷27,康熙七年九月癸丑条。
顺治、康熙初年满汉大臣这种对开经筵的请求,一方面是清初汉族大臣对于满族皇帝接受汉族儒家文化的一种迫切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朝中大臣认为皇帝幼年即位、教育阙失,亟待依靠经筵进讲来弥补这一不足。顺治帝亲政后也逐渐意识到了儒家文化对于佐治理的重要意义,他最终也不得不感叹儒家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③《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二月壬戌条。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顺治帝作《资政要览》,并亲自作序:“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如大匠以规矩而定方圆,乐师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于圣经者莫不蕴含事理,成一家言。”④《资政要览》序,南京 :江苏广陵书社,2003年。最终在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清代首次经筵在保和殿举行。此后直至顺治帝去世,经筵都能做到如期举行,分别是顺治十五年的二月、八月,十六年的三月、八月,十七年的三月。日讲进行的也较为顺利。康熙帝则更加重视经筵制度。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礼部议定:经筵,参照顺治十四年(1657)例,每年分春、秋二次举行,定于次年二月十七日午时首开经筵。康熙十年(1671)二月,首开经筵。从这一年开始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十五年间,经筵制度进入了鼎盛期,康熙皇帝勤勉好学,对开经筵呈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康熙帝对日讲也十分重视,他于康熙十二年(1673)下令此后寒暑不必辍讲,将日讲变成了他日常的功课,甚至出行、战事期间亦不间断。他的刻苦程度甚至让日讲官都跟不上进度。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翰林院奏:“皇上聪明天纵,好学敏求,洵从古所未有。臣等会同詹事等官,正在昼夜撰拟日讲讲章。伏乞皇上少缓进讲,俾得陆续撰拟进呈。得旨:仍著按日进讲。其讲章尔等撰拟后节次进呈。”⑤《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丁未条。这一时期的经筵讲求实效、重视实际内容。康熙帝多次表示反对经筵中经筵官空谈,他说:“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⑥《清圣祖实录》卷43,康熙十二年八月癸亥条。
二、经筵制度的转折和皇子教育制度发展——康熙朝中、后期
经筵制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发生了转折。当年闰四月,康熙帝谕翰林院学士张英等人:“尔等每日将讲章捧至乾清门预备,诣讲筵行礼进讲,为时良久,妨朕披阅功,著暂停止。《春秋》、《礼记》,朕在内每日讲阅。其《诗经》、《通鉴》讲章,俱交与张英,令其赍至内廷。”⑦《清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己未条。于是,康熙停止了日讲。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开经筵的次数减少,已经不能保持每年春秋两次,甚至不能保证每年都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康熙帝此时的精力集中在了对皇子、尤其是太子的教育上面。康熙帝一生在皇子教育尤其是对太子的教育上倾尽心血,他一直强调皇子教育的重要性,深信“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他在加强自己学习修养的同时,也逐步开始进行皇子教育的实践。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岁的皇太子允礽已经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了,康熙帝便下令议定“太子会讲礼仪”。规定:“每岁二月、八月,驾御经筵后,钦天监择吉具题,皇太子行会讲礼。是日,皇太子恭诣传心殿抵告礼成,升主敬殿座。各大臣官员,排班序立,行二跪六叩礼,退,立原班。满、汉讲官诣讲案前,一跪三叩,以次进讲。先四子书,后五经。讲毕,同大臣官员等出殿外丹挥下序立,仍行二跪六叩。礼毕,各退。讲章由詹事府先期送进。讲官满、汉各二人。”①《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153,文渊阁四库全书。太子会讲礼仪基本上是照搬经筵仪式。同年,康熙帝命翰林院官任太子日讲官,并规定了“太子日讲礼”:“日以讲官满一人、汉二人轮直进讲。正本先期送进,副本由司经局正字誊写,讲官恭奉进讲。每日早,讲官进至内左门外坐,赐茶。候内监出,引至毓庆官惇本殿,行一跪三叩礼,进至讲案前。皇太子先讲本日书毕,满、汉讲官,以次进讲。先讲四子书,后讲五经,讲毕各退。日讲之期,新岁开印后,请旨开讲。退躬祭坛庙与三大节庆贺日停讲、忌辰停讲外,虽寒暑斋戒日期及封印后均不停讲。至岁暮拾祭斋戒日姑暂停。”②《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153,文渊阁四库全书。太子日讲礼与皇帝日讲礼基本相同。
康熙帝同时加紧了对诸皇子的教育,《康熙起居注》中对此有所记载:“天潢衍庆,圣子众多,上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③《康熙朝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94页。正是在康熙朝,皇子教育逐渐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康熙帝挑选了当时著名的儒学大臣作为诸皇子的老师,如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徐元梦等,他们教授的内容有儒家经典、历史典籍等,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
康熙帝对皇子读书要求十分严格,汤斌曾因天气暑热,“恐皇太子睿体劳苦”,提出“皇上教皇太子过严”。而康熙帝是这样答复的:“皇太子每日读书皆是如此,虽寒暑无间,并不以为劳苦。若勉强为之,则不能如此暇豫。尔等亲见,可能有一毫勉强乎?”康熙帝以自己读书的标准来要求诸皇子:“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教太子及诸皇子读书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足,朕殊不以为然。”④《康熙朝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4-1645页。
康熙帝常常对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康熙帝在汤斌、耿介等大臣面前对诸皇子的功课进行了一次考核,地点在畅春园无逸斋。考核过程如下:
当天早晨,皇太子在无逸斋读书,师傅达哈塔、汤斌、耿介侍读,起居注官德格勒、彭孙僪亦在场。皇太子诵读《礼记》、《经义》数篇,并写了数百字楷书。不久,康熙帝亲临书斋,询问起居注官皇太子读书情形。少顷,康熙帝回宫,命皇太子赐饭诸臣。之后,康熙帝带领皇太子、皇长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一同来到无逸斋,命尹泰、德格勒传谕:“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今诸皇子虽非大有学问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读书。朕非好名之主,故向来太子及诸皇子读书之处未尝有意使人知之,所以外廷容有未晓然者。今特诏诸皇子至前讲诵,汝等试观之。”康熙帝随其取下十余本经书授予汤斌,让他“信守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汤斌随揭经书,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以次进前,各读数篇,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康熙帝又命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而一向在宫中被皇太后亲自抚养、不谙汉文的皇五子也不逊色,他虽不曾读汉书,但是对于满文却是精通,康熙帝命他当场诵读满文,读的“段落清楚,句句明亮”。⑤《康熙朝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4-1645页。
当时皇长子十六岁,皇太子十一岁,皇三子十一岁,皇四子十岁,皇五子九岁,皇七子八岁,皇八子七岁,诸皇子的表现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康熙帝绝不夸赞,也不允许别人称赞,“诸皇子在宫中从无人敢赞好者,若有人赞好,朕即非之”。①《康熙朝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4-1645页。
诸皇子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也须学习满语、骑射,不忘满族之根本。皇子们自入上书房读书起,甚至封爵分府、娶妻生子后还须入上书房读书。雍正皇帝的童年、青年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渡过的。
三、皇子教育的完备与经筵制度的衰落——雍正朝直至咸丰朝
雍正即位时已四十五岁,不仅掌握了儒家经典、史书、满蒙文字,在政治上也已经是久经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雍正一朝的皇子教育制度也愈加完善。雍正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是皇子教育制度得以完善的关键。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命鄂尔泰、张廷玉任上书房总师傅,又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为诸皇子的师傅。②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7页。在皇子教育问题上,雍正帝一改康熙帝过度维护皇子权威的作风,规定了皇子拜见师傅礼:“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杌子四张……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③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1页。康熙帝虽然在教育皇子方面十分用心,但是他忽略了“尊师”的重要性,他曾因为皇子学习成绩不佳而迁怒于师傅徐元梦,命令侍卫在诸皇子面前杖笞徐元梦。“客观而论,康熙帝在具体之事与技能的传授与培养上,教子十分成功,但相对忽视对诸子的品行教育。所以,他将皇太子与诸皇子培养成为文武兼备之才的同时,也在亲手埋下皇储矛盾与储位之争的导火线,使其成为康熙朝后期妨碍皇权集中的最大掣肘力。从这一角度看,康熙帝无疑又是一位教子的失败者”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随着皇子教育的日益完善,弘历在皇子时期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六岁就学,先后受业于福敏、朱轼、蔡世远等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他们的指导下,弘历很快便已经熟读《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和《通鉴纲目》、《史记》、《汉书》等史籍。⑤弘历:《乐善堂集》,朱轼序,光绪五年铅印本。乾隆帝自己也认为自己“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⑥《清史稿》卷303,列传第90,福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乾隆帝十二岁时被引见到康熙帝前,此后深得康熙帝喜爱,被带到宫中抚养。因此,少年时代的弘历在祖父那里也接受了良好的教导。康熙帝不仅教他典籍章句,还令弘历陪他批阅章奏,甚至引见官员时弘历也随侍左右。所以,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治国理念方面,弘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皇子教育制度在乾隆朝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乾隆元年(1736)正月,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令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徐元梦、福敏等为皇太子的师傅,并规定:“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弹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⑦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乾隆帝把皇子教育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在登基之后立即实施。不仅如此,乾隆帝非常重视皇子教育实效,反对务虚,他曾经以康熙第二子允礽为例,指出了过早立储为皇子教育埋下的隐患,认为雍正帝实行的秘密立储对提高皇子教育质量有很大的作用,“皇考……不事建储分府,惟择老成宿望之大臣如朱轼、鄂尔泰、福敏、张廷玉、蔡世远等劝读内廷,亦惟慎简师傅,俾之熏陶德性,读习经书日有课程,其视出阁就傅有名无实者相去为何如耶?”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4,学校考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乾隆帝为顒琰选择师傅时,时任上书房总师傅的刘统勋推荐了翁方纲、纪昀、朱珪三人备选,最终乾隆帝选择了朱珪,理由是“如翁某、纪某者,文士也,不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②昭槤:《啸亭杂录•续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诸多师傅之中,朱珪最受顒琰敬重。他博学广识,不仅教授顒琰丰富的知识,在品德与行为方面,都以自己的风范影响着顒琰。朱珪曾对他讲过“勤学者有余,怠者不足,有余可味也”这样的话,顒琰牢记师傅的教诲,对其一直心怀感激,把自己的书房名之为“味余书室”,并著有《味余书室记》。朱珪在《味余书室全集》的跋语中称赞顒琰“好学敏求,诵读则过目不忘,勤孜则昕夕不怠”。③《味余书室全集》序,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嘉庆帝即位后,选择秦承业、汪廷珍、万承风、汤金钊等人任诸皇子的师傅。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帝谕:“近日上书房四阿哥均系按日授经,二阿哥三阿哥不立课程,二阿哥尚间日撰作诗文,三阿哥则经年累月诗文俱置不作。……阿哥等日在书房并无他事,又无旗务管理,若仅由卯入申出,不肯留心学问,岂不竟成佚旷。夫人之心志不专于此必移于彼,岂可别有所好,关系甚巨。奚若游艺诗文、发抒经史,可以陶冶性情,增长知识,且日有常课亦以收其放心,其获益实非浅鲜。后二阿哥、三阿哥每日俱应作诗,间三五日必作文一篇,不可间断,使业精于勤,勿荒于嬉,以收逊志时敏之效。着将此旨钞录一通,交上书房存记,必皇子皇孙等触目傲心,永远钦奉。”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4,学校考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此时,二阿哥旻宁已有三十五岁,三阿哥绵恺也已二十二岁,而嘉庆帝仍然关注上书房的皇子教育,可见他对皇子教育之重视,对皇子管教之严。
道光帝即位后,命令奕詝六岁入学,选择杜受田为老师。道光十七年(1837)令翁心存入直上书房,教授六阿哥奕读书。虽然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国运衰退,但都没有影响皇子教育的实施。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帝任命祁隽藻、杜受田教皇四子读书,又命翁心存入直教授八皇子读书。⑤《清史稿》卷19,本纪19,宣宗本纪三。之后的咸丰朝仅仅有十一年,且充满了内忧外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还是早早的安排好了皇子师傅的人选,彭蕴章、祁隽藻、徐桐、翁心存都曾任职于上书房。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从雍正朝开始直至咸丰朝,皇子教育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已经成为每位皇帝即位之后首要关注的事务了。如此规范有效的皇子教育制度,使每位皇位继承人在即位之前都接受了全面、良好的教育。再加上这一时期每位皇帝都是成年后即位,除了良好的教育背景之外,还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经验。因此,他们即位后并不再需要儒臣在御前的讲席,他需要的是依靠经筵这种形式来体现他的文治政策。于是,这一时期的经筵制度随之发生了变化,逐渐趋向仪式化,成为了清代“崇儒重道”政策的标志。
雍正一朝十三年,共举行了十三次经筵。也正是从雍正朝开始,经筵制度开始仪式化,基本成为了一种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外在表现形式。雍正三年(1725)八月,首次经筵大典举行,这次的经筵大典已经呈现出了内容空洞、形式化严重的特点。此次经筵上,基本上是讲官讲四书毕,雍正帝发议论,讲官赞皇帝;讲官讲五经毕,雍正帝再发议论,讲官再赞皇帝;最后,诸经筵讲官赞雍正帝:“圣学高深,洞悉天人一理之源。是以开示精切,发前儒之所未发。臣等今得与闻,诚不胜欣幸之至。”之后,经筵结束。⑥《雍正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8页。于是,经筵典礼已成为了皇帝彰显学问、讲官称赞圣学的场合了。
乾隆即位后,他显然不再依靠经筵官解读章句、传授治国理念,因此,乾隆一朝共开经筵五十一次,都不能保证一年开一次。而且,乾隆朝经筵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皇帝发御论,群臣跪聆御论的环节。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咸丰朝。
从乾隆三年(1738)春首举经筵之时,乾隆帝便亲制御论以宣示。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共产生经筵御论九十八篇。乾隆帝退位之前,命人将九十八篇御论装订成册,共六册,命陈于文华殿。①《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94,《春仲经筵》,光绪五年铅印本。《会典》中记载了乾隆朝经筵中群臣跪聆御论的情形:满汉讲官进讲四书毕,皇帝阐发书义,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进讲五经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②乾隆朝《大清会典》卷25,礼部,仪制清吏司,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讲官跪聆御论使经筵成了乾隆皇帝训导臣下并展示自己才学的工具,而宣示御论成为了乾隆皇帝在经筵的主要目的。乾隆六十年(1795),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把经筵一事委托给颙琰:“明年丙辰正月上日即当归政,嗣后经筵为子皇帝之事,予可以不复文华亲讲矣。”③《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94,《春仲经筵》,光绪五年铅印本。这“亲讲”二字足以说明此时的经筵对于帝王教育来说已经是无足轻重了。
顒琰即位后,依旧延续了经筵制度。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共举行经筵二十四次,大约平均每年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御史唐鉴奏请恢复日讲官轮班等事宜,遭到了嘉庆帝的拒绝:首先,嘉庆帝认为天子之学与经生寻章索句不同,应重在“贯彻天人,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他不需要儒臣为他解读经典章句。他还提及康熙帝停罢日讲和乾隆帝停止儒臣进呈讲义,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召儒臣进前讲读已经沦为套路,并发出“轮班入对,其能阐圣贤之精义,陈古今之治忽者能有几人”这样的质疑。并且,他深刻体会到了经筵日讲中的弊端,“抵拾陈言,数衍入奏,或以颂扬塞责,甚至妄议时事,岂非徒乱人意乎”。④《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47,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在嘉庆帝看来,御前讲读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道光、咸丰时期的经筵制度延续了嘉庆朝的惯例,不能达到每年一次,在实际内容上也没有变化。道光帝在位三十年,御经筵二十五次;咸丰在位十一年,御经筵十次。这一时期,中国充满了内忧外患,朝中有志之士无不以强国为第一要务,学术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道光以下的学术精神从古典研究转为经世致用,大体上说,有两个比较显著的趋向:第一是理学的抬头,第二是经世之学的兴起”;“道光以下的理学与经学是一事之两面,统一在实践这个观念之下;所不同者,理学注重个人的道德实践,经世则强调整体的社会、政治实践”。⑤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98-299页。曾国藩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他景仰被群推为经世儒宗的顾炎武。他提出要求恢复经筵传统旧制,讲求实效,并仿照康熙前期旧制,在经筵后继续日讲。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身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上奏折请求举行逐日进讲,并请求“广开言路,借臣工奏章以为考核人才之具”。⑥《曾国藩年谱》卷1,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曾国藩还拟定了日讲的具体条款,共十四条,详细规定了日讲的讲官、地点、内容、仪式、讲义的编写等内容。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咸丰帝同意了曾国藩的提议,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咸丰帝发布上谕中表示支持:“便殿日讲,为求治之本……著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查例详议以闻。”⑧《清文宗实录》卷5,道光三十年三月癸卯条。
不过,曾国藩的提议在朝中遇到了阻力。穆彰阿和孙瑞珍为代表的势力提出了“日讲于圣学无益”的理由:“帝王之学,以实而不以文,贵要而不贵多。自来经史之昭垂,儒先之疏义,所以资研究供观览者,固已惟人惟备。后人所见,不能出其范围。今若再选儒臣,排日进讲,仍不外蹈袭旧说,缀辑成文。窃谓圣学之增崇,不恃乎此”①《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咸丰帝最终不得不妥协,咸丰元年(1851)正月谕:“朕念深典学,御极之始,即欲举行日讲旧典。礼臣以乾隆、嘉庆年间,两朝训谕皆以此事易滋荒弊,徒尚虚文,俱奉旨停止。是以斟酌未行。然朕心未尝不念兹在兹也……儒臣进善于君,援古以证今,纷纷论列时事,恐启挟私逞臆之端,转失讲道沃心之义。朕机务余暇,将于翰詹诸臣中轮流选派,亲命题目,各拟讲义,分日进呈。”②《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47。于是,恢复经筵旧制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曾国藩提出恢复经筵旧制,到反对派反对,曾国藩的计划最终破产这一过程来看中,可以看出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恢复经筵旧制的目的已与皇帝治学无关了。曾国藩明确提出“借臣工奏章,以为考核人才之具”,他主要希望咸丰帝借助日讲来考察臣工;第二,经筵日讲本身的作用受到质疑。反对派提出“今若再选儒臣,排日进讲,仍不外蹈袭旧说,缀辑成文。窃谓圣学之增崇,不恃乎此”。而咸丰帝本身也认为“儒臣进善于君,援古以证今,纷纷论列时事,恐启挟私逞臆之端,转失讲道沃心之义”。
由此可见,经筵制度发展到此时已经背离了它的初衷,完全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没有了实际内容。清廷也正是因为这项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崇儒重道”的象征作用才仍旧坚持一年开一次或者几年开一次。
四、皇子教育完全取代经筵制度——同治朝直至清末
咸丰十年(1860),皇子载淳不满五岁,而咸丰帝就着手安排他的学习事务了,他为载淳选择大学士彭蕴章为师傅。载淳即位后,虽然是慈禧太后当政,她也依旧按照祖宗家法,精心给皇帝安排师傅。同治元年(1861)载淳入学,师资阵容很强大,先后有祁隽藻、倭仁、李鸿藻、翁心存、徐桐、翁同龢。③《清史稿》卷385,列传第172。但是,慈禧太后以皇帝年幼为由,命“渴陵、御门、经筵、耕藉,拟请暂缓举行”。之后,终同治一朝都没有举行过经筵大典。可见,同治朝的皇帝教育完全是按照清朝皇子教育旧制进行的。
光绪初年,慈禧太后给仅仅五岁的载湉安排学习事务:选则翁同龢、夏同善为师傅,读书的地点定在毓庆宫,并命醇亲王负责:“著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皇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著派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皇帝读书课程及毓庆宫一切事宜著醇亲王妥为照料,至国语清文系我朝根本,皇帝应行肄习,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等事,亦应兼肄,著派御前大臣随时教习,并著醇亲王一体照料”。④《清德宗实录》卷23,光绪元年十二月乙亥条。
按照太后懿旨,光绪帝于第二年四月正式入学,“上诣至先师前行礼,诣毓庆宫殿升座受师傅、谙达、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礼,上揖师傅入座读书。自是日始,每日御殿读书,岁以为常”。⑤《清德宗实录》卷30,光绪二年四月壬午条。光绪帝也是一位勤勉好学之君,他将来能够接受变法思想、启用维新派进行变革图强,这一切都是于他的刻苦读书密不可分的。
光绪十七年(1891),御史高燮曾奏请恢复日讲,光绪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朕自亲裁大政,每日召见臣工,于人才之贤否、政治之得失,莫不虚衷考察、实事求是。几余披览经史,复与毓庆宫诸臣讲习讨论,不敢稍自遐逸。该御史所请轮值进讲,看似延访儒臣,勤求治理,实则有名无实,流弊甚多。自乾隆十四年罢以后,迄未举行。若徒抵拾陈言,或以硕扬塞责,甚至妄议时事,岂非徒乱人意所奏著毋庸议。”⑥《清德宗实录》卷294,光绪十七年二月乙巳条。
光绪皇帝首先认为自己每日在毓庆宫学习经史,“不敢稍自遐逸”,无需用日讲的方式来典学;其次,他认为日讲已经有名无实、流弊甚多,于典学毫无裨益了。
末代皇帝溥仪也同样有固定的学习程序。溥仪的外籍教师庄士敦记载:“我第一次入宫时,皇帝的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上(夏天五点半,冬天六点),陈宝琛先进宫,大概七点半左右,陈宝琛讲课结束,准备出宫。……八点半左右,就轮到满族帝师伊克坦授课了。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左右,就轮到我了。我一般讲两小时左右。”①[英]庄士敦:《暮色紫禁城》,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由上可知,同治朝之后直至清朝结束,经筵制度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皇帝典学完全依照皇子教育的规制进行。皇子教育完全取代了经筵制度的功能。
结论
皇帝典学与皇子教育制度历来是国家制度中重要的两项内容,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清初,随着政权的建立,清帝逐渐开始认同中原的儒家文化,并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学习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皇子教育制度与经筵制度逐步确立、发展并制度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项制度呈现出了不平衡的发展趋势:皇子教育制度从清初确立以来,逐步趋于完备,并成为有清一代重要的“家法”被历朝所奉行直至清朝结束;经筵制度与之不同,从清初经筵制度确立,至康熙朝前期达到鼎盛,之后逐渐务虚而仪式化,咸丰朝以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出现这种情况绝非偶然。清代经筵制度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子教育从清初以来不断完善、发展的结果。皇子教育的成熟与完备,再加上清雍正朝以后直到咸丰朝的皇帝都是成年即位,这些因素使得皇帝不再依赖经筵制度获取知识,导致经筵制度所具有的皇帝御前讲席的这一功能逐渐削减,最终丧失。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Princes and Jingyan(经筵)(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emperor) in Qing Dynasty
XU Jing
(Palace Department of the Lmperial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81,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princes was more and more regula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grandness of the Qing Empire. But Jingyan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t trend, and it was more and more decadent. On the whole, the two systems were in the state of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each other. Even in the final state of the Qing dynasty, Jingyan was taken over by educational system of princes.
Qing dynasty;Educational system of princes;Jingyan
[责任编辑 山阳]
K249
A
1672-1217(2017)06-0073-10
2017-09-13
许静(1979-),女,山东临沂人,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