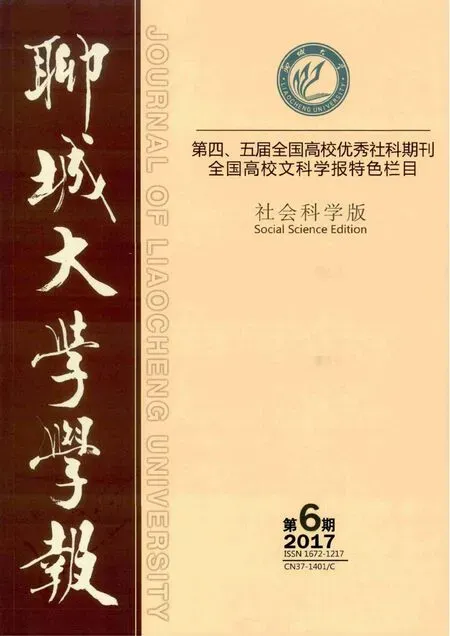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编创
——从其编修私史谈起
2017-03-06武迪
武 迪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编创
——从其编修私史谈起
武 迪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小说家,李渔受到当时世风、学风、士风的影响,和当时不少遗民一样,都有私史著作布流于世。他的拟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的编创与其私史著作的编修几乎是同时展开的。私史著作的编修,为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编创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在私史修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整理相关史料为他的拟话本小说编创提供了大量新鲜素材;第二,编修私史,促使李渔更加主动地接触、学习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于小说创作的营养。第三,李渔在对纷杂的史料进行整理、辨别、证误的过程中,培养其辩证思考的能力和勇于质疑的气魄。
李渔;拟话本;私史;编创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李渔,字笠翁。浙江金华兰溪人,生于江苏如皋。十余岁时随父兄搬回家乡,顺治八年(1651)前后,搬往杭州,七年后再次移家至金陵,此后寓居金陵近二十年。晚年搬回杭州,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悄然辞世。李渔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小说家、戏曲家。著有拟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十数种传奇作品以及《古今史略》《论古》《闲情偶寄》等史传、杂著作品。
一
明末清初是一个乾坤板荡、战乱频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人辈出、思想纷呈,文学史上百花齐放的时代。晚明心学空疏学风所带来的危害,随着明王朝的飘摇与覆灭逐渐被世人察觉,经世致用之学越来越受士林人士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需求,催生出一大批小说家、戏曲家和书商,如冯梦龙、凌濛初、李玉、李渔、丁耀亢等等。这些从事小说、戏曲创作的文人,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中有不少人还博取了功名、经历过宦海沉浮。他们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大环境中,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无视时局变化,脱离现实的影响,这个时代的世风、学风、士风都对小说的编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家以遗民身份投身私史修撰便是这个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受到当时学风变化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
作为一种明清之际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私家修史主要发生在由明入清的遗民身上。究其心理动机,与明清之际的历史震荡和治学风尚转变密不可分,带有明显的从实践中走出而用以“致用”的特点。正在当时实学风气的影响下,士人对天文、地理、历法、物理、兵事等实用内容的兴趣尤其突出,还往往大胆发言评议历史、针砭是非。以“三大儒”为代表的士人对晚明心学导致的空疏风气的反感,推动了类似私史修撰这样的文化现象在明清之际大量涌现出来,“由于满清贵族的入关,……有心人士以血泪写下来数以千百计的明末野史,也就是当时的现代史,……这时所写下来的历史才可以看出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史迹。”
谈到明清之际的学风,谢国桢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中的分析是很有概括性的,他说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黄宗羲整理宋明的学术思想,王夫之潜心明理。关中的李颙主张自我改造,他的教学方法很贴近群众,认为农商皆可早就学者。孙奇逢有匡时济世之心。北方的颜李学派养成了注重实践之风,提倡“六府三事”,魏禧讲学以致用为宗等等。①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16页。谈到那些在明清之交挣扎求生的士林中人的思想,大体不外乎要受晚明左派王学与清初“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影响,归根到底多数人仍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关于明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现如今可谓是硕果累累,谢国祯、嵇文甫、罗宗强、左东岭、夏咸淳、樊树志等学者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研究一个大时代之下某位作家的思想和文学活动,仅从宏观的角度去概说,常会失之笼统,探得些牝牡骊黄罢了。像李渔这样,一位鼎革之际才渐露头角的“思想家”,他的内心世界同易代之际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都是极其复杂的。像他这般自晚明走来的文人,其思想深受左派王学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毕竟不同于冯梦龙、凌濛初等前辈话本小说家,李渔的人生正处于一个由明入清的剧变时局当中,而他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天崩地坼”之后开展起来的。因此,清初的思想界的潮动和变化,势必会波及李渔,私家修史的大潮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修史热潮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些共鸣,这与中国古代小说本身的特点有关。古时的小说家要想创作出比较成功的作品,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才能——史才、诗笔与议论。②历史方面的学习与积淀,为他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史传作品又为其提供了创作小说的基本技法。诗词歌赋等韵文的学习和应用对小说的创作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古代不乏诗性小说,采诗词如小说的做法在小说创作中是通例。对社会、历史中的人、事的基本归纳、演绎、分析、阐释等能力,是小说家所需具备的最基本的文学创作条件。纵观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大凡是成功的作品,都离不开作者(或写定者)出色的编创能力。与后两方面相比,作家的“史才”与小说创作之关系又是更为明显而突出的。③史传作品对小说的影响不仅是为它提供了一个素材的宝库,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叙事方法。同时对小说家“尚实”的文学观念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以胡应麟、张尚德、甄伟、蔡元放等都主张历史演义小说应该切合历史真实,对虚构、幻笔的使用是比较谨慎的。蒋大器等许多小说评点家虽对小说的虚构有很充分的认识,但他们也同样认为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使用是有限制的,不能天马行空,必须要人情物理加以约束。这种表现的或明或暗的“尚实”的观念在小说创作和评点中是极为常见的,这正是与史传文学产生的一种共鸣。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史传中脱胎出来的,二者是一种“同源而异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且复杂的。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以史家视角指出“小说”来源于稗官,其性质是与正史有别的“街谈巷语”,是道听途说而来的。究小说之实际作用,则如桓谭《新论》所说:“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里提到的“小说”一词虽与后世“小说”的含义及外延不尽相同,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已经明确地表露出来,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无数小说家的文学创作。
同时,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书中多少都蕴含了后世小说的文化因子。《山海经》和《汲冢琐语》又称古今“语怪”“纪异”之祖,影响了后世小说浪漫尚奇的倾向。两汉马、班的《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更为后世小说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并在创作手法、艺术构思、议论形式等方面“导夫先路”。具体来说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传与小说的关系,除了上述所指的历史因素外,还不能忽视私家修史热潮这一重要的时代因素。应该说,大凡时局动荡的年代——先秦、汉魏、两宋之交与明清鼎革——修史、立说都蔚然成风,并深刻地影响同时代的文学活动。
李渔作为生活在易代之际的“文学生产者”,一位热销读物的创作者,同时还有着另一个身份——私史的编修者。他在编创拟话本小说的同时曾编修过两部有关历史的著作:一种是成书于顺治年间的《古今史略》,另一种是成书于康熙初年的《论古》。①此外,当时李渔还专门搜罗前代及当时官衙案情、判词、文书等,编辑为工具类书籍《资治新书》。某种程度上也保存了不少他生活时代的民间事情。《古今史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起于盘古混沌时代,迄于明崇祯,遍数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主要人事。李渔在《序言》中曾对自己编修私史的过程和方式有过介绍,他说自己每日列陈书籍数十种,本着“汰繁去芜,取其精当、有所详略”的态度加以修订,又说“略于古不敢于今,而尤不敢略于熹、怀二庙。盖以历代有史而明无史,怀帝以前,尚有《通纪》可考,而熹庙以后,遂无书可读故也。略所有而详所无,倘亦于见闻有裨邪。凡今之人,有欲考古鉴今而苦厌倦者,请以此药之。”②[清]李渔:《古今史略》,《李渔全集》(第九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全书共十二卷,前七卷记述明代以前的史实,后五卷专载有明一代的历史,保存了许多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史料。因此,他的《古今史略》实则可算作记录有明一代史料的“当代史”。其目的正在于“存明”,即为“无史”的明王朝保存一些史料。通过记述当时的历史事实,总结一代兴衰的经验教训,探究历史人事的成败得失,记述动荡时局的悲欢离合,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③明清鼎革之时,士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是否通过慷慨赴死来表明自己杀身成仁的决心,而在于当国家、民族与文化面临崩溃危机时,如何找到一条合理的、可行的出路“救亡图存”。既然不能选择“慷慨赴国难”,又不能试着举起屠刀杀向敌人,于是那些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和伦理困境,忧心于世俗社会的讥讽与冷眼的知识分子们,大多选择了通过“修史”以“存明”作为其实现人生价值的出路。因为,只要有所行动,便比生存在道德重压之下苟延残喘却毫无作为来得有意义。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亦所以报故国也”的思想,就使得作为“遗民”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极大地彰显出来。在这一点上李渔与当时诸多热衷于私家修史的遗老、新贵并无二致。。晚出的《论古》则是一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专论性评点的史料汇编,包括订误、正伪、辩疑等方面,多是些翻案、疑古性的内容,评论以“笠翁曰”启首,模仿《史记》“太史公曰”的形式,善抓关节、反复诘问,分析尖深、透辟入理,极富启发性。全书亦按照时间为序,但不再罗列史实,而是针对单一历史人事的论述。
李渔在编创拟话本小说的同时,还进行了私史修撰的工作。编创小说与修史两者间多少会产生一些互交性影响,那么,李渔修撰私史对其拟话本小说编创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二
从李渔编辑史学著作的情况分析,其史学素养在“业余”修史者中亦属不弱。他整理、编辑、评述史料的工作与他的拟话本小说编创是几乎同时开展起来的。修私史的工作势必会对拟话本小说的编创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④话本小说的创作受史传影响很明显。特别是它发展到明末清初时,因受时局变迁、王纲解纽带来的外部环境的陡变,已表现出与明代不同的特点:首先,此时的小说家们已不再拘泥于改写旧篇了,话本小说文人独创的成分增强,随之产生了一批富有作者个人主观色彩的作品,特别是带有自寓性、翻案性、实用性的作品迭出,诸如李渔的话本小说,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取材大多是依照当时的社会现实,熔铸了个人的思想情感,便显出一种明显的个人色彩。第二,受纷乱的易代思想大潮的影响,话本小说亦如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开始肩负起“抒情述志”的作用。小说家们不仅要叙述情节、敷衍故事,还将个人对于历史、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中的体悟、思考有机地揉入了小说之中,议论部分在小说中越发占有了重要位置,甚至压缩了叙事空间,代替了话本小说中原本的“入话”“头回”部分。那么,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在编修私史的过程中,李渔得以接触到许多关于明代历史的史料。特别是那些散见于民间杂书中关于中晚明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有不少如今已经散佚难见了,有赖于李渔的搜集得以保存下来。李渔对中晚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加工是有意识的、系统性的工作——他“尝日进古今纪载数十种陈于前,澄其神而读之”,①当时编修私史获取资料的来源除了李渔所说的“古今纪载”外,还有道听途说、博采时闻,通过采访时代的亲历者的办法,诸如计六奇《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都有这种采访形式的体现。客观上为他的拟话本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李渔拟话本小说所依托的本事,有不少是发生在明清之际的长江流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事性特征。这些发生在明清之际的民间故事,本来流传范围很小,影响也不甚大,能够被李渔采入小说并加以敷演,不能不归功于他日常整理、搜集的工作。比如,《合影楼》的故事见于胡氏《笔谈》,《鹤归楼》见于段氏《家乘》,这些书如今已经非常稀见,可能已经亡佚,李渔在小说结尾也提到这些书是向无刻印的,因此在清初也绝少得见。可以说,这些故事如果不被李渔拿来加以整理、改编,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了。再如《女陈平计生七出》所载故事实为“崇祯八年”发生的一件实事,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也有记载。在发现本事记载之前,一般认为这篇小说乃是李渔独立创作、虚构而成的。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此篇拟话本应当也是照实敷演的。当然,《女陈平》的故事并非直接采自计氏记载加以编创的,而是他在修撰史书、杂著的过程中搜集材料时发现的。又如《美男子避祸反生疑》所述故事,与朱素臣传奇《十五贯》的前半部熊友蕙事几乎全同,而当时流传在苏州一带的明初贤臣况钟断狱的故事,大约是其本事来源。李渔与朱素臣多有往来,在留寓苏州期间获知此事也不是奇事。整体看来,李渔拟话本小说的题材大多取自当时江南几省的民间故事、野史笔记,这自然与他编修私史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编修《古今史略》的过程中,李渔着墨较多的是关于明末战争纷乱的描述,将这些记述与李渔拟话本小说中的描写作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存在很多相似性,比如《奉先楼》《生我楼》中的描写:
独有邻舍人家见他生下地来不行溺死,居然领在身边视为奇物,都在背后冷笑,说他夫妻两口是一对痴人。这是什么缘故?只因彼时流寇猖撅,大江南北没有一寸安土。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甚至有熬取孕妇之油为点灯搜物之具,缚婴儿于旗竿之首为射箭打弹之标的者。所以十家怀孕九家堕胎,不肯留在腹中驯致熬油之祸;十家生儿九家溺死,不肯养在世上预为箭弹之媒。起初有孕,众人见他不肯堕胎,就有讥诮之意;到了此时,又见种种得意之状,就把男子目为迂儒,女人叫做黠妇,说他:“这般艳丽,遇着贼兵,岂能幸免?妇人失节,孩子哪得安生?不是死于箭头,就是毙诸刀下,以太平之心处乱离之世,多见其不知量耳!”(《奉先楼》)
原来乱信一到楚中,就有许多土贼假冒元兵,分头劫掠,凡是女子,不论老幼,都掳入舟中,此女亦在其内,不知生死若何;即使尚存,也不知载往何方去了。(《生我楼》)
《奉先楼》所讲故事,就情节而言与凌濛初“二拍”中的《李将军错认舅》相似,与《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一样都是敷演的金定和翠翠的爱情故事。不过,李渔却在《奉先楼》中说这个故事是采自明清易代之际的一桩实事,“这场义举是鼎革以来第一件可传之事,但恨将军的姓名廉访未确,不敢擅书,仅以‘将军’二字概之而已。”②[清]李渔:《十二楼》,《李渔全集》(第九卷),第248页。李渔丝毫没有避讳“事有所本”对小说虚构和创造性的妨害,大概在当时确有一桩实事存在,只是与《翠翠传》相似罢了。《生我楼》上述所引的材料讲故事发生在宋元易代的湖北,与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中的记载相同。《香艳丛书》中载严思庵《艳囮二则》“蒋老”事也与《生我楼》相似,只是故事发生地有所差异。陈维崧在《妇人集》中引董以宁《楚游闻见录》“郑妗”事,说“张献忠假杨嗣昌兵符破襄阳……(郑妗)闻贼尽斫城中妇女纤趾囊之,酒间赌胜。”大概此类事件在明清鼎革之时,普遍存在于北兵南下渡江的过程中。不过,谈及当时战乱年代的种种情状,《古今史略》中的记载更为血腥、恐怖:
是时流盗杀戮之惨,亘古未闻,有缚人夫与父,而淫其妻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之父,淫其女以为戏,而后杀之者;甚至裸孕妇于前,共卜所孕之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者。时取人血和料喂马,使腹状而能冲敌。所掳子女甚众,临行不及携,尽杀之而去。
此段记录与《奉先楼》所述历史背景大体相当,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这一描写自当来自李渔修私史过程中所收集的材料。应该说,修史的工作极大丰富了李渔的见闻,为他在同一时期的拟话本小说创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编修私史,促使李渔更加主动地接触、学习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于小说创作的营养。比如,史传的议论说理的方法和形式,对具体叙事艺术手法的学习与借鉴,对史传文学“尚实”倾向的继承等。
其一,李渔在编创拟话本小说时,特别重视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并适时将现实与虚构加以融合,形成一种附着“奇幻”色彩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他笔下的故事大多具有时事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即在选材时,侧重于选取带有新鲜感与及时性的材料,这是保证拟话本小说得以新奇的最基础的条件之一。同时,李渔所选取的材料大多是他亲身所见、所闻或周边地域流传的故事,现实性较强。李渔立足于时代和现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创造、虚构对材料的变形和改造,编创了一个又一个尖新奇巧的故事。这种兼容虚构与现实的倾向,一方面得力于拟话本小说创作本身对“幻化”“虚构”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明显与史传传统和当时小说观念“尚实”的倾向发生了共鸣。李渔在《合影楼》的最后对整个《十二楼》进行了全方位的概况,“如今编做小说,还不能取信于人,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阁也”,这正表明他对小说现实性的一种承认。
其二,李渔在结撰故事时,尤其重视对事件的前因,特别是引发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的描述,对事件的结果一般是一笔带过,这一点与《左传》记史方式类似。在叙述大事件时,条理清晰、环环相扣,常将事件起因放置在重要位置上,加以强调;马、班《史》《汉》也善于在列传中通过抓捏琐碎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使得人物在多维度的视角中变得丰满生动。比如,在《乞儿行好事》中,作者对乞儿“穷不怕”侠肝义胆、乐善好施的品德进行反复的渲染,着重描述了他在面临艰难选择、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最终下定决心,拿出银子救济受豪绅欺压的母女。不想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惹祸上身,还因此差点儿送命。故事发展到高潮时,迅速出现反转,以正德皇帝的出场,解救了危难中的“穷不怕”,惩治了贪官墨吏。
其三,清初以李渔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偏好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强加”到叙事当中,并对整个故事进行“旁观”式的评述,这种做法在明末“三言”“二拍”等作品中还比较少见。然而到了李渔生活的时代,这种情况便比比皆是了。究其原因:一来,易代之际的士人对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晚明以来空疏的学风、世风进行痛批。以顾、黄、王三大儒为代表的思想家力主“清议”,鼓励士人通过议论发出自己的声音。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小说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多少受到了当时风气的影响。二来,史传传统对小说家的影响。古代史著在编撰时,为了明确表达史官的褒贬是非的态度,往往采用“太史公曰”或“某某曰”一类的形式。这一做法在明清两代的小说和评点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便是一个例证。李渔在《论古》中所采用的“笠翁曰”的形式也是直接承自史传的。虽然,在《无声戏》和《十二楼》中并没有这一形式的使用,但李渔在小说中插入议论时,仍旧是以作者身份来进行的。抛开“叙述者”或打断叙事跳到读者面前“现身说法”。虽无“笠翁曰”之名,却仍有“笠翁曰”的实质。
其四,在具体的叙事艺术手法上,一方面李渔是直接学习、借鉴前代话本小说作品的技巧;另一方面则是从史传文学中汲取养分。李渔和他的前辈冯梦龙等人一样,都善于抓住小事件、小因素,特别注重小与大的对应关系,善于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构建复杂的故事情节,许多故事的缘起、转折、发展都是在毫末之间完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敷演起来便是气若汪洋。譬如《夏宜楼》的故事精妙绝伦,而关节所在,乃是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千里镜。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都与此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至于男主角瞿吉人可以借此博得一桩好姻缘。《美男子避祸反生疑》中的一连串误会和巧合,让人惊觉,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借由案卷失窃,才真相大白:一切的误会皆不过源自一只挖墙打洞的老鼠。《说鬼话计赚生人》中的顾云娘之所以上演了一段精彩的复兴家业的好戏,正因为机缘巧合之中发现仆人在墙缝中私藏的米粮。《鬼输钱活人偿赌债》中一家的兴衰居然全在“拈头”二字,《女陈平计生七出》关节则在于一粒小小的巴豆。
其五,这种小中见大,于细微处看全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手法,同样也运用在表现作者个人思想感情及褒贬倾向上。中国最早的一部私史《春秋》中就有“微言大义”,一字之内寓褒贬的笔法。李渔在小说中援引最繁者之一便是《春秋》。杜濬在评点李渔的拟话本小说时,还曾将他的创作技巧作“春秋笔法”。在《谭楚玉戏里传情》中很难看到李渔对主人公的赞扬,但他通过描写谭楚玉为爱情自甘下贱,为爱投江而毫不犹豫,为爱无子却不另娶等几次行动,已将谭楚玉的形象提升到了“完人”“痴人”的地位上,褒贬立现。在《美男子避祸反生疑》和《男孟母教子三迁》中通过描写清官审案前后的荒唐情状,从侧面揭露了那个时代清官暴戾施虐甚于贪吏,断案多受主观臆断干扰的现实情况,与史书所载海刚峰、施世纶的情况多有雷同。在无需明断是非的情况下,便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褒贬立见。
此外,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和事物名称的命名,也往往寓含褒贬之意。比如谭楚玉之名,是比附和氏璧而来的,刘藐姑之名则取自姑射山之神人等等,在命名之初便带有深层的文化含义。同时,每当小说人物登场之时,作者便有书写一段有关人物姓氏、祖籍、生计等基本情况的介绍,这种情况在古代小说中是很常见的。甚至小说家在结撰情节时,对文中所使用到的新奇物什也多要花些心思加以介绍。譬如《夏宜楼》中关系西洋科技望远镜、显微镜等几种镜子的介绍,除了千里镜的介绍比较符合叙事的需要外,其他镜子的介绍略有逞才之嫌。
(三)清初编修私史的大潮催生出一大批私史、杂著,在对纷杂的史料进行整理、辨别、证误的过程中,培养了小说家们的辩证思维的能力和勇于质疑的气魄。李渔在修私史时,特别是在写作《论古》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剖析、质疑锻炼了他的辩证分析能力。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对传统观念的反拨,新奇诡谲又透彻入理的议论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修撰私史的训练。
清初以来,出现了一批带有翻案性的小说,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等。①圣水艾衲居士,生平不详,大抵是杭州一带的人。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中将《豆棚闲话》的作者定为“或云为范希哲作”。范希哲,清初钱塘人,与李渔友善,有托名李渔所作的传奇八种,似也为范氏所作。在李渔《论古•周纪》中有一篇《论晋文公赏从亡者不及介子推》,与艾衲居士《介子推火封妒妇》的故事类似,都是翻案性的文字,且两者同时提及了相传为介子推“邀功”时所作的四言诗。诗曰:“有龙矫矫,顿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李渔认为如果历史上的介子推真如此段流言所说,那么他必然是先有请赏之心,而后割股救主的。若此,晋文公不赏介子推不仅无错,反而有理。对于这首四言诗,李渔认为似黄口小儿初学所作,毫无含蓄蕴藉之美,当为伪作。介子推割股救主之饥饿,而非救主之病痛,于情于理皆不通。艾衲居士在结撰小说时,为介子推安排了一位善妒的妻子,介子推被火烧死,竟然是因为妒妇难驯。两位文人在解读介子推时似乎有类似的看法,可能是在日常交往中互相影响的结果。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翻案性的文字,不过因为数量较多,情节也比较复杂。比如《黄英》描写菊花精黄英与丈夫生活中的诸多差异,表现了好货、好利的商人思想与传统儒家理念的冲突,并借黄英之口,指明陶渊明之安贫乐道,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动荡时局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足为范。不过,同为翻案,李渔与艾衲居士的小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中有些故事是采自前代的,诸如西施与范蠡、介子推与晋文公故事等,作者在具体的敷演过程中,将不同于历史通识的内容加以铺展,用来表现个人对历史的思考。这种做法主要立足在已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去捕捉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的差异性,并加以分析得出不同于通常看法的结论。而李渔的小说选材都是市井生活,未涉家国大事。因此,他笔下小说的翻案性主要源于他个人的思考和认识。在《无声戏》《十二楼》的议论部分中,多有对圣人经典、传统观念、社会风俗、民间习语的新意解读,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和怀疑精神的体现,是成体系的个人思想的表露。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为深入地对“约定俗成”的叛离。
对史料的整理、编辑、订伪、考辨,促使李渔在表达个人见解的同时,将个人的人生体悟融入私史的修撰中去,而其小说也是古代小说史上较早出现自寓性倾向的拟话本小说作品。
绾而言之,李渔在顺治年间的一系列文学活动构成了一个复杂且紧密相关的“有机体”。他在编修私史以及整理、出版实用工具书的同时,也完成了《无声戏》《十二楼》的编创工作。这些被收集、整理、筛选出的史料,也包括当时的案牍、文告、条议等在内,都为李渔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分。李渔在编修私史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直击时代的现实材料,或采自史书,或道听途说,他从这些繁芜的素材中甄选出了一批新奇、怪诞的故事加以创作,为读者奉献了一场文化与娱乐的饕餮盛宴。
Li Yu Nihuaben(拟话本) Novels’Creation——Starting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WU D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China)
As a famous novelis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Yu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tmosphere, style of study, the intelligentsia,Li Yu and many adherents had edited history books. He wrote novels“Silent Drama”and“Twelve Towers”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almost simultaneously launched. Compilation of history books for Li Yu Nihuaben novels creation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fluence: First of all, compilation of history books, and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historical data consciously provided plenty of fresh material for his novels;Second, editing history let Li Yu more actively learned and inherited 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 and learned from a number of beneficial nutrition novels. Third, in the process of sorting, identifying and proving the historical data, Li Yu cultivated his dialec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daring to question.
Li Yu; Nihuaben; history; creation
[责任编辑 唐音]
I207.41
A
1672-1217(2017)06-0027-07
2017-09-13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HB17ZW011):宋代文言小说研究。
武迪(1992-),河北保定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