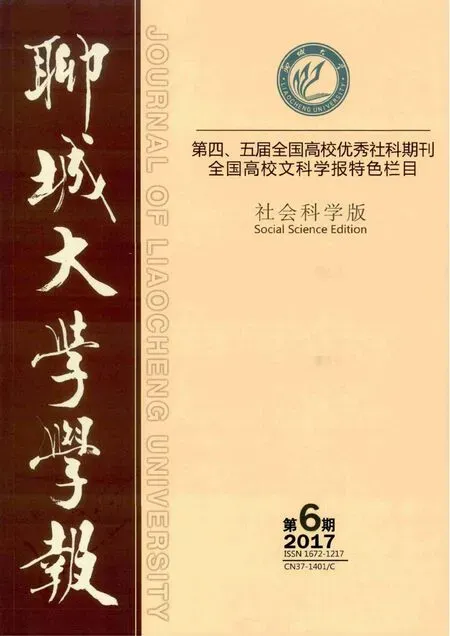西方现代戏剧的解释学转向
2017-03-06马慧
马 慧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西方现代戏剧的解释学转向
马 慧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西方现代戏剧的审美过程非常重视读者向度。它将读者作为戏剧的关键参与者,将读者的理解作为实现戏剧作品意义的必要途径。现代戏剧的意义阐释呈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打破了以往戏剧在意义上追求明确和稳定的取向,出现解释学转向。戏剧意义在阐释倾向的转变与现代戏剧审美过程重视读者向度有着密切联系。以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观照现代戏剧的意义阐释,可以更深刻理解其阐释倾向缘何发生以及这种倾向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承认合理的“前见”及理解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的“视域融合”的过程等观点为现代戏剧的阐释转向的发生提供了深入解读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现代戏剧的读者转向发生的合理性。两者之间的契合也显示出现代戏剧的这种新特点之所以会以强大生命力延续于19世纪末之后至今的戏剧史,是因其更深层次上吻合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20世纪的文化旨归:现代文化的相对性、多元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质。
现代戏剧;解释学;转向
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戏剧阶段是指19世纪最后30年至20世纪中叶。相对于以亚里士多德理念为圭臬的古典戏剧,现代戏剧在文本意义阐释倾向上发生了明显改变。虽然各种现代流派繁复芜杂,理论主张和实践体系均有鲜明差异,但总体上可以认为文本意义由传统的明确性和稳定性转向模糊性和多义性,出现解释学转向。现代戏剧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特点共同造就了这一特征。这一问题已经探讨较多,但尚未充分涉及这种倾向背后的动因及蕴含的某些规律。本文力图跨越哲学和文学的界限,打破学科间的藩篱,将西方戏剧的现代转向置于哲学解释学的视域内予以观照,挖掘这些在剧本内容、艺术形式和剧场艺术方面的深刻变革所反映出来的文学及文化规律。哲学解释学作为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可以深入探究以往戏剧所忽略的某些方面或被否认的某些问题,更好地理解为何这些被忽略或被否认的区域中蕴含着改变的潜质及其价值,并最终形成戏剧史上的明显转向,且引发热烈跟随。
一
现代戏剧呈现出审美向度的明显转变——对读者向度的高度重视。现代戏剧的精神特质与传统戏剧相比发生了巨变,戏剧意义的发生不再是依据作者的意图及其在剧作中的设定,而是更多将读者或观众的理解作为意义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解过程受到空前的重视。离开了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文本只是文本,不能称其为作品。自象征主义戏剧起始,读者或观众就成为戏剧意义的实现者之一,随着现代思潮的更迭,要求读者参与解读的程度越来越高。可以说,离开了受众这一维度,现代戏剧就无法全面理解和领会。
现代戏剧内容的主要表现对象舍弃了外部的客观世界转向内部的主观世界,尤其重视人的非理性疆域的重新发现。现代主义戏剧的理论和实践无不将人的非理性存在视为人的本质之一,视为生活的唯一真实。这使现代主义不仅有别于现实主义,也有别于以主观情感抒发为主旨的浪漫主义。
象征主义决然断开与客观世界的表面联系和深层联系,倾尽全力建造一个完全的精神世界。它的主题基本都是人的精神建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宇宙意义的彻底追问。由此神游于天地的无尽浩渺和人的最终归处,脱离了有着明显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的客观世界的束缚。对于精神世界的执着,往往使象征主义戏剧呈现出鲜明的神秘色彩,很多重要的剧作家同时都是神秘主义者。他们对世界持不可知论,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捉摸和掌握的力量,人注定要听命于它,听从这种神秘力量的召唤。对灵魂和精神的通力表达,使得剧作家的角色也发生改变。他们抹去了自己身上作为一个社会人绝大多数的特征,不再为社会现实浪费笔墨,而是成为一个“通灵者”,即通过戏剧这个媒介使得观众(在大一点的范围说是人类)去倾听、领悟及崇拜宇宙间的神秘力量,产生类似于宗教的庄严肃穆的效果。这些剧作家与现实保持着自觉的距离,将身心都沉浸于一个灵性世界中去。无论是梅特林克的《青鸟》《群盲》还是叶芝的《猫与月》《三月的满月》,都将精神探索推向极致。叶芝在1898年的随笔《身体的秋天》中提到自己最开始乐于描写周围的生动世界,但逐渐地“我失去了描写外部世界的热望,并且发现如果不是有关精神和隐形的事物,我从书中已经不能获得丝毫的快乐。”①叶芝著,王家新编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文集:书信•随笔•文论》(卷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0页。他们就像一个灵界的使者,致力于传达生命的启示,暗示宇宙中的无形力量以及渲染灵魂的某种默契的联系,努力让读者或观众进入到这种情境中去。
如果说象征主义戏剧表达的是对精神建构的渴望和努力,是对永恒本体的永久向往,那么表现主义戏剧表达的就是人类精神的沦落境况。它也以象征为媒介,但与象征主义的建构不同,它更多是解构。它表现的也是精神主题,主要是人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精神的沦落、崩溃以及人格分裂的过程。分裂意识是表现主义着重突出的,这种分裂意识是“第二意识”,是理性控制的真空地带。所以梦、梦魇、妄想、幻想幻听等与梦有关的形式成为表现主义戏剧的重要表现内容。如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主人公在疯人院里睡了三个月,在梦里看到了过去的所有人物,忏悔神父历数那些人的恶行,并为他做长篇祈祷,表现了人物罪孽深重,恐惧末日审判的忏悔意识。表面看来有情节,看来是一个故事,但缺乏真实性和现实性,充斥其中的是模糊不清的飘渺之感。第二意识比意识潜藏着更多的主体奥秘。在语言的所指层面,表现主义戏剧里并不拒绝现实生活,但如果仅在这一层面上去理解其内涵,则极难到位。准确的说,它表现的是一定精神状态投射的现实,是内心世界的幻化,映照的是人格分裂的过程,和精神崩溃的宣泄。由此,世界失去本来的面貌,只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疯癫混乱情绪的臆造,只是焦虑歪曲心态的敞开。因为面对危机的沉重和无奈,剧作经常进入表现丑陋、黑暗、狂妄、分裂、战栗的潜意识,这些正深入挖掘了人在精神重压下灵魂无处皈依的境地。正如斯特林堡所说:“一切都会发生,一切都是可能和合乎情理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在微乎其微的真实基础上展开想象,形成新的图像:把记忆、经历、杜撰、荒唐和即兴混为一体。”②斯特林堡:《斯特林堡戏剧集》,高子英、李之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4页。
面对社会大潮下的精神危机,象征主义戏剧家将人的终极关怀指向神秘的未知力量,以作品营造出顽强的精神追求。表现主义戏剧则承认了这种精神危机,承认了人在其中必然失败的命运。象征主义剧作和表现主义剧作作为现代潮流的早期代表,虽然理念不同,风格不同,但共同的基本点是发掘精神世界,不管它是建构的还是解构的。这就使现代戏剧在开创之时与古典戏剧分离在不同的道路上。而精神世界的难以言说与相应艺术手法造成的模糊效果,使得读者或观众对戏剧的认识遭遇很大冲击。
对于读者向度的重视在19世纪开始酝酿,到19世纪末开始占据主流,绵延于整个现代戏剧史。以哲学解释学为视角来解读这一发展趋势,可以加深对现代戏剧的理解。当然,就哲学解释学和现代戏剧开端的时间差距来看,不能说前者直接给了后者理论启发,而应该说后者给了前者实践支持。挖掘两者的契合之处可以更深刻认识现代戏剧的读者向度转向之必然性和合理性。
解释学古已有之,最初的涵义即是明确词篇等文本的意思,排除歧义,显示意义。19世纪的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系统化了,使其由仅针对文献的技术性的诠释上升为适用于多种学科的系统性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是解释应该尽可能还原文本产生时的历史语境,深入写作背景,恢复作者注入文本中的原义,避免对文本的误解。在读者如何可以把握作者的原义这一点上,施莱尔马赫建立了自己的依据。他认为虽然作者和读者有时代、个性、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但具有普遍的人性和共同的情感,这就保证了两者具有相通和理解的桥梁。以此为基础,读者以自身具备的条件去主动理解作者的创造意图和过程,形成符合后者原义的解释。施氏对理解过程的重视,使得解释学成为一种认识论。接下来狄尔泰又将解释学的对象由文本文献推广到人类的历史和生活,归根结底,解释学要解释的是人的生命表现。解释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研究方法,只有通过这种解释的方法,社会科学才能得以真正理解。由此,他努力使解释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他的“体验”“表达”“理解”等概念对此后的解释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解释学也由认识论推进到方法论。两位哲学家促成了解释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
哲学解释学作为20世纪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及文化思潮,对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哲学解释学由海德格尔开创,他以存在的本体论研究“理解”,将解释学上升到本体论层面,从而使其摆脱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成为一种哲学体系。理解构成“此在”,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成为此在的本体论条件。理解本身就是人在世界中的方式,是人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进一步论述了理解和解释的关系。理解构成解释的基础,解释则为理解的发展。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是哲学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后者延续了前者的本体论观点,即解释学不是认识论,也不是方法论,而是人存在的模式。对文艺作品而言,理解亦是其存在方式。“正如任何其他的需要理解的文本一样,每一部艺术作品——不仅是文学作品——都必须被理解,而且这样一种理解应当是可行的。因此诠释学意识获得一个甚至超出审美意识范围的广泛领域。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这不仅仅是一句涉及到问题范围的话,而且从内容上说也是相当精确的。这就是说,诠释学必须整个反过来这样被规定,以致它可以正确对待艺术经验。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传承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①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31页。传统意义上的对文本的解释完全不能囊括解释的本体论涵义。
“哲学解释学的中心关注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最基本的状态,关注人类理解活动这一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的共同属性。”②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探求理解这一模式的规律,明确理解的条件,显现人的世界的经验,辨清人与世界的关系,寻觅人生的真理,才是伽氏的哲学解释学的目的。现代戏剧表达的是神秘经验和精神体验,这决定了戏剧整体呈现含混、游移、晦涩的美学风格。和基本具有确切、固定、明晰这些特征的古典戏剧相比,现代戏剧本身对读者而言就是超越了期待视野的异质存在。这种异质是现代戏剧有意为之,意图就是实践新的戏剧标准。现实主义戏剧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凝练,自然主义戏剧对日常生活的尽力摹仿,都使观众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产生熟悉感和掌控感。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语言,让观众的心理对戏剧产生似曾相识的归属感。现代戏剧则打破这种归属感,有意与观众心理保持距离,创造出陌生感。所有这些都让戏剧的意义处于一个未明状态,而读者或观众正是使未明走向可明的必然要素。对现代戏剧而言,审美理解的过程,即是完成作品意义的过程,而观众也通过此种审美理解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树立和人生意义的观照。所以审美理解亦即实现人的存在的途径。戏剧作品的意义不能脱离开观众而独自存在或实现。读者或观众的创造行为是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作品的解读是揭示文本意义的必然途径,而非其自然生成。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这种哲学上的本体论为现代戏剧的审美解读提供了新的视域和理论支撑,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界限。
二
既然读者理解对于现代戏剧的意义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就自然产生另一个问题:由读者理解的不同可能会使戏剧意义产生多种答案。那么这种多种答案存在的合理性在哪里?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观点可能会提供一定启发。
相对于古典戏剧意义阐释的明确性和稳定性,现代戏剧的意义阐释则明显体现相反的特点:模糊性和多义性。古典戏剧的作者是作品意义的规定者,读者或观众对其的理解就是要尽可能地接近于作者的原义,而非做出自己的解读。作者会努力赋予其作品完整而统一的意义,读者或观众也习惯于去发掘这个完整而统一的意义,两者的心理都指向一个作品中所蕴含的那个明确和稳定的意义。现代戏剧一个重大的转向就是打破意义的明确、稳定、完整和统一。面对这样的作品,读者或观众首先是惊愕,因为这是一种与以往的戏剧完全不同的阅读或观看感受。继而他的兴趣被激发,感觉被激活,开始尝试运用自己的知识、背景、经历、感受去理解作品中不甚明了的意义的答案。自然,也就有了对作品意义多样的解读。
现代戏剧有意抹去了现实生活的色彩,舍弃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和自然主义的摹仿论,而是指向人和宇宙的终极意义,哲学色彩浓厚。表现内容的变化相应要求思维方式由摹仿改为象征。象征思维在现代戏剧中普遍使用,成为其特色之一。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是古已有之,但具有随意性和零散性,没有固定化和系统化。在现代戏剧中,尤其是象征主义戏剧中,象征的地位空前提高。它不再作为艺术手法之一,而是成为整个戏剧构思的框架。在象征框架下,角色、情节、语言、结构等戏剧要素都成为象征的外化,而缺乏具体所指。象征给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留下了无限解释的空间。一部现代作品,读者或观众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视域出发作出迥异于他人的理解。如叶芝的《炼狱》,人物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老人十六年前杀掉自己的父亲,此时又杀掉了少年——自己的儿子。作为其晚期的代表作品,戏剧的抽象和晦涩达到极度。老人的行为如何理解,杀死父亲杀死儿子意味着什么,场景中那所破败的大房子和干枯的大树又作何解释,这些都需要读者或观众调动自己的视域和作者的视域实现互动,前者最终形成的理解是在后者的提示下完成的,但又不被后者限制。梅特林克的《青鸟》人物及情节等通篇是象征,青鸟和小孩的行为到底象征什么,通篇寓意是什么,都可以有多重解释,只要自圆其说,都被允许。表现主义作品亦是如此,以象征来统领,如凯泽《从清晨到午夜》,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等作品改变常规给观众带来的舒适感和熟悉感,使用了很多求异的艺术形式,大量使用空白、跳跃、断裂、梦幻等元素,时空的模糊性改变了线性叙事的模式,象征的广泛而全面的运用等,这些都增加了作品意义的含混性。相对于摹仿的思维方式,象征的思维方式无限扩展了表达对象的时间和空间。作者像在制作一道神秘的谜题,热情邀请读者或观众参与进来,说出自己的答案,并大度地广泛认可。“艺术象征的本质在于,它的意义永驻在象征本身。艺术作品作为象征,形成巨大的‘解释学空间’,几乎具有无限收摄的能力。”①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象征是一种主动的邀请,它向理解者敞开意义存在的无限可能。
审美理解是理解者带着自身的历史性、前见和视域去观照文学作品,在观照的过程中与作者的视域相融合,能动地对作品进行体验和欣赏,寻求和探定作品的意义。理解并非重构和复制,而是一种读者带有自身的标识和偶然性因素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会而且必然会超越作者。理解者的前见和视域不同,对同一作品的诠释亦会不同。作者的写作意图为作品意义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而通过文本和读者之间的潜在对话才能实现辩证理解。对话过程中文本和理解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也是一直互动的。
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每个人都是处在一定情境中,每个人独特的情境就是其理解世界的立足点。以此立足点出发,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就形成其“视域”,即他的观点、理念或立场。视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而非静止。理解对象有其特定视域,理解者也有其特定视域,前面说过,因为历史性的主观存在,两者的视域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异,而不会完全重合。面对这个差异,如何进行理解?古典解释学秉承客观性原则,尽力清除掉理解者的视域,无限贴近理解对象,进入其原有视域中。哲学解释学则认为两个视域并不是截然对立,只取其一的关系。清除理解者视域,完全进入理解对象或者清除理解对象的视域,完全以理解者视域为主导都不能说明理解的真正过程。而应该是理解者从自身视域出发,与对象的视域结合,生发成一个不同于两者任何一个的新的视域,即“视域融合”。理解必须要考虑对象的视域,同时也必然结合理解者的前见和视域,体现了对象涵义和理解存在的渗透联系。伽达默尔对理解对象的视域和理解者的视域之关系的论述中,主张的“融合”既没有完全抛开理解对象这个出发点,从而导致解释的极端主观性,也没有全然舍弃理解者这个能动力量,从而导致解释的过度考据的拘泥。两者的融合所生成的新的视域,才是理解对象存在的方式。伽氏的“理解”,在理论上论证了解释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为西方戏剧的现代转向提供了文化标识。
狄尔泰一直避免主观性,追求达成理解的客观有效性。与之相对的,伽达默尔承认了主观的必要性。由此,作品意义并不必然地向作品和作者寻求,而是读者在自己拥有的历史现实性上进行的孤独探求,以审美理解把艺术真理所具有的历史性和主观性发掘出来。现代戏剧的解读中,理解者自身的视野是被充分承认和允许的。这个过程以作品为基础,尊重作者的视域,同时又充分重视了理解者的创造性解释。每种解读都被允许,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很多现代作家在被问及自己作品的意义时,都含混其词或者直接以不清楚不知道做答。因此,理解现代戏剧的意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模糊性与多义性。正是这种距离形成了观众理解的无限张力。观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激发,审美注意很自然集中到戏剧中去,在主动理解的同时实现创造感的满足。现代戏剧创造了这种距离,但总体来说还是遵循了基本的心理规律,观众有兴趣去探知新的戏剧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具备这种能力。而后现代戏剧在这条路上就走得更远,内容和形式上的过于新奇以至于作品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过大,经常使后者难以理解和接受,张力因为太过无限反而不存在了。作品的产生只能属于一个时代,但对它的解读却可以在其产生之后的任何时代。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视域与原作者的视域结合,从而得出不同的理解过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审美理解的多样性造就了戏剧文本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动态的理解过程才是发现艺术真理的过程,这个理解打破了文本的静止,也打破了审美主体的孤立。在二者之间架起动态的桥梁,只有通过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真正的戏剧意义才会实现,艺术真理也才会被发现。
三
西方现代戏剧对于读者向度的高度认知和身体力行,以及在意义阐释上的模糊性与多义性都使戏剧走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解释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更深层次上吻合同时也创造着20世纪的文化旨归。
(一)现代戏剧的意义阐释中对于解释主体的依赖使其具有了浓厚实践性的特色。实践的多样性客观上就造成了解释结果的多样性。解释和理解不是强制的规定,而是主动的创造。如同哲学解释学突破了传统解释学对于作者原义无限靠拢的努力,现代戏剧也拓展了文本意义生成的途径,使之立足于实践性之上。读者或观众的视域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构成理解戏剧作品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解读都从过程中实现,而不是满足于唯一的作者原义的揭示。每种解读实践都体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特性,对于具体的历史的承认和开掘必然将戏剧理解指向相对和多元。可以说,现代戏剧的实践性使其符合了20世纪文化的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做出坚决的拒斥姿态。
(二)现代戏剧的解释学倾向蕴含着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高度认可。以哲学解释学来观照,戏剧文本意义的追寻过程强调了背景的整体和统一。社会、历史、心理、宗教等等文化因素都是做出文本阐释的有效条件。这些有着无尽变量的因素在理解中的参与,构成了对意义生成的整体观照。文化学的系统分析法将各种文化形态视为一个统一体,将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视为互动因素,坚持了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现代戏剧的文本阐释同样打破了局限于文学范围内的追索,而是将多种文化形态纳入其范围之中。开放视野下,戏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研究成为应有之义,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拓展了戏剧研究的疆域,也必然地将意义这一戏剧的基本要素增加了许多文化研究内容,形成了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新特征。
(三)现代戏剧中象征思维方式的确立。最早的象征思维主要体现于神话和童话。它在现代戏剧中的复兴,是因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及其造成的混乱。象征思维方式面对的是主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按黑格尔的说法,所有象征都要解决精神怎样自译的问题。现代主义艺术的向内转的倾向主要由象征思维方式来体现。它完整展示了20世纪人类精神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向内转的过程。现代戏剧的创作过程是直觉过程,并非依靠逻辑的意识,而是跳跃的潜意识。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人物和构建的结构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如象征主义认为真正与世界沟通需要的是直觉和体悟,是一种神秘经验,与逻辑的思考链条无关。随后的表现主义和荒诞派戏剧逐渐把这一理念推向极致。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直觉,这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要求一种整体观。直觉不能被分析,不能被切割,只能是以象征面貌出现。象征思维方式也决定了现代戏剧意义的阐释与主要是基于再现思维方式的传统戏剧意义的阐释的巨大差异。深刻理解意义阐释中的象征是理解整个现代戏剧的必要前提。
由上述可知,跨越哲学与文学的学科边界,积极引入哲学理念进入文学研究中,有其积极意义。以哲学解释学为参照,将关于戏剧现代转向的文化讨论引入一个相对开阔的领域,或许可以为更加深入理解现代戏剧的特质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探求。以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观照文本意义阐释问题,能够认为现代戏剧的意义阐释将着重点从文本本身转移到交流过程,这成为20世纪戏剧的重要特点,也成为其范式转变的推动力。哲学解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存在的方式,将理解置于本体论地位,强调任何理解都是对象与主体的视域融合,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现代戏剧的文本意义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具有了模糊性和多义性的特性。它充分肯定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对以往所忽视的戏剧规律的强调,因而也为戏剧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增添了时代特质。现代戏剧意义阐释的特性自19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其后的戏剧发展中一直得到高度呼应和不同形式的延续,这正是因为其符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现代文化相对性、多元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质。
The Hermeneutic Turn of Western Modern Drama
MA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China)
Western modern drama aesthetic proces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ader. It takes reader as the key player in drama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 is seen as the necessary way to the meaningful dramas. The meaning of the modern drama presents fuzziness and ambiguity, which breaks away from previous explicit and stable meanings. From the point view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explaining of modern drama could be understood as why this could happen and what is behind the culture.Hermeneutics’ views, for example, understanding is the way, foreseeing,provide the deeper reading of modern expression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readers, 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of reader-oriented modern drama. The fusion, at the same time, explains the powerful vitality of modern drama from the late 19 century until the whole 20 century.
Modern drama;Hermeneutic;turn
[责任编辑 唐音]
I053
A
1672-1217(2017)06-0015-06
2017-09-20
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哲学解释学视域中的西方戏剧之现代转向。作者简介:马慧(1981-),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