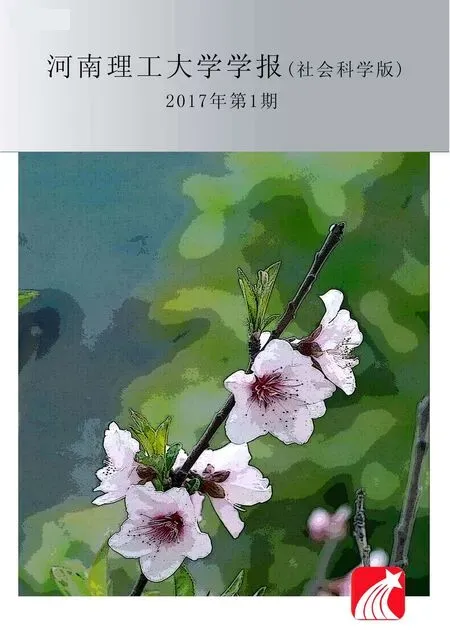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
2017-02-23杨勇
杨 勇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
杨 勇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是中国进入统一政权后最大规模的基于“轻重”原理的财政经济思想在现实中的新尝试。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从“轻重”制度本身的特点、优势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贤良、文学亦不否认这种合理性,但却从官员腐败导致完全走向反面为据而反对之。盐铁会议后,均输、平准逐渐废弛。汉宣帝、元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对均输、平准制退步了的继承。王莽“五均赊贷”则因腐败问题困扰而完全走向失败。
盐铁会议;“轻重”之争;均输平准;常平仓;五均赊贷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汉朝因连年大规模出击匈奴,耗费巨大,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此情况下,汉政府仅凭固定的税收已不能应付国家正常的开支,遂多渠道扩大财源,实行盐铁国营、算缗告缗、货币改革、均输平准等兴利政策。这个过程正如《盐铁论》所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兴利政策的实行,极大地改善了汉政府的财政状况,但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汉武帝去世六年后,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汉政府召开了由当朝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与上一年所举荐的来自民间的基层儒生贤良、文学进行对话的政策咨询会。会上,贤良、文学对上述各项兴利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学术界对于这些争论的考察,多集中在盐铁国营之争的问题上,单独对均输、平准的考察不够,更没有注意到盐铁会议后这两项政策的实际发展状况。均输、平准政策,实是先秦“轻重”经济思想在汉代的一次新尝试,本文拟对这两项经济政策作一详细考察。
一
均输、平准之法的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轻重”原理。“轻重”之法,是一种政府利用雄厚的物资基础参与市场运作,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买进与卖出,使市场发展趋势向相反方向运动以获利的经济理论。如市场价高(重),就使其低(轻);市场粮食或商品少(轻),就使其多(重);货币面额大(轻),就使其小(重),其本质是“利用物价涨落和供求关系变化,凭借政治权力从中取利”[1]。
“轻重”原理在先秦时就已被提出,但其主要是用于粮食调配。《史记》有“设轻重九府”“贵轻重,慎权衡”之记载。《汉书·食货志》则详载了管仲首行的“轻重”之法:“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以此为据,由国家出面根据各年农业丰歉度适时收购或售卖粮食,防止商贾操纵粮价,这样既增加了国家收入,又稳定了物价,还保证了农民的利益。管仲既是“轻重”原理的提出者,又是第一位将其成功运用于国家层面的创始者,其实行的结果是“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轻重”原理也第一次显示出了其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妙用和功效。此后又有魏国的李悝平籴法。李悝的政策与管仲一样也是针对粮食行业的,利用的同样是“轻重”原理。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李悝将年成具体划分为上、中、下三熟,并根据年成制定详细的国家粮食收购量和比例。此制实行后也收到了“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的效果。管仲、李悝两人将“轻重”理论运用于粮食市场的成功,初步奠定了“轻重”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
关于“轻重”原理,除了关注管仲、李悝这些政治层面的人物外,《史记·平准书》还载有与李悝同时的商人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及《史记·大宛列传》有汉使至西域“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之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商人白圭、出使西域的汉使是把“轻重”原理运用到个体商业经营上的一次积极尝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原理,“轻重”之法不仅运用于国家层面,也被商人成功地应用到了商业层面。因此,“轻重”原理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对于经济原理的深刻认识,这无疑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经济思想之一[2]。
汉政府运用“轻重”原理始于桑弘羊。桑弘羊是洛阳商人之子,受商业文化的熏陶,从小精于计算。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被任命为大农丞后,即开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史记·平准书》)。均输一法由此始。均输法虽然是根据各地物资信息对物资进行调配,实则是“轻重”原理的运用。然而此时,桑弘羊开展的仅是小范围实验,影响及效果均不大,直至五年后的元封元年(前110年)他升任治粟都尉,才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同时,还新设平准一法,调控全国物价。至此,均输、平准之法成为一项经济制度在全国实行。
至盐铁会议召开当年,均输、平准之法已在全国实行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曾有人明确反对均输、平准之法。史载:均输、平准在全国正式推行的当年,在前一年因反对盐铁国营而被从御史大夫贬为太子太傅的卜式,即因当年发生旱灾,就借机向武帝进言烹杀弘羊:
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3]97。
“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即指均输、平准之法。卜式要求直接处死桑弘羊,可见其反对态度之强烈。然而此时,桑弘羊正处于上升期,卜式的言论引起了汉武帝的严重不满并再一次贬斥了他,此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时隔卜式烹弘羊之议近30年后,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就均输、平准之法的存废直接与桑弘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二
盐铁会议双方对均输、平准之法利弊的论争,主要集中于会议初期。在会议上,桑弘羊的反驳意见为: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4]1。
欲罢盐、铁、均输,忧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4]2。
桑弘羊在此关注的是各项兴利政策对保证财政收入的意义,这也是他坚持兴利政策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据史载,均输、平准之法在诸项兴利政策中对财政的贡献尤其大,《史记·平准书》记曰:
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3]97。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3]97。
上面乃是针对全部兴利政策笼统而论,随后他又专论均输、平准制度: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4]3-4。
另外,他还专论平准一事:
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4]12。
桑弘羊的上述发言,实际上是用“轻重”原理本身的效用来说明其“平万物而便百姓”的优势。桑弘羊对于“轻重”思想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准确的,他既指出了“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4]4之道理,又言及“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4]5之意义。这些论述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活动中“轻”与“重”之间的转化。我们看到,虽同属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兴利事业,但平准、均输之法较之前所实行的盐铁国营、货币改革、算缗告缗等事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三项兴利之事虽早于均输、平准之法,且经济效果也比较显著,但却是在国家出现严重财政危机时临时统制直接抢夺民间财富的紧急行政性兴利活动*一些学者认为,“武帝时期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如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等,可以说都是这种‘轻重’思想的具体实践”。我们认为,算缗、告缗、盐铁官营、酒榷,包括元狩四年的货币改革,其虽是国家以行政力量采取的经济统制政策,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没有运用“轻重”之法。赵靖也指出,“‘告缗’严格说来并不是‘轻重论’范畴的经济政策”,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具体见参考文献[1-2].,本质上是“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5],尤其以后两者为甚。而平准、均输之法则是汉武帝君臣为适应商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新经济政策,它是利用传统的“轻重”理论,使国家以经济人的身份参与经济运行,即“在国家的权力下统摄了物流”[6]。国家不但在此过程中获利颇丰,而且还打击了市场投机行为。这是一种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它不但优化了资源配置与组合,而且还实现了经济运行、物资流通达致高效的效果。
均输、平准之法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从物品种类来看,正如冯友兰指出的,“《管子》中所说的‘平准’其范围仅及于粮食,桑弘羊所说的‘平准’其范围包括所有的货物”[7]。均输、平准之法,是将“轻重”理论运用到粮食以外的其他物品。平准即是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4]97,而均输所调节的范围也是各种物品。第二,从地域范围来看,管仲、李悝只是将“轻重”之法用于诸侯国,地“不过千里,制驭较易”[8]125,而桑弘羊则是将其“行之于一统之世”[8]125。因此,从这两点看来,桑弘羊的均输、平准之法实在是一次比管子、李悝复杂得多的“轻重”理论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桑弘羊“是汉代‘轻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9],无疑是对其十分公允的评价。但是,桑弘羊的辩论发言,却有极力掩饰均输、平准之法对国家财政的直接效果以及与用兵匈奴关系的嫌疑。他的“均输以足民财”[4]3论点,是在极力宣传均输对民间的正面作用。同时,他又把均输对财政的贡献与救灾挂钩,其言:
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4]4。
这里所言之水灾,是指汉武帝年间继元狩三年后关东地区发生的第二次大水[发生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左右]。据《史记》记载:“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3]95汉武帝一方面积极安排赈济,一方面安排灾民就食于江淮一带。均输此时尽管未在全国范围推广,但产生的一些收益用来救灾是可能的,不过其作用应该十分有限。
其实和盐铁国营一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才是均输、平准之法的最终目的。桑弘羊的下属御史大夫在会议上指出,桑弘羊“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4]32,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均输、平准之法的巨大财政功效,事实上也完全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平准、均输之法“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为国家财政开辟了一个新的利源”[10]373,是“桑弘羊推行各种财政政策中最成功的一种”[11]。桑弘羊在这里主要论述了平准、均输之法有“平万物而便百姓”、促进物资交流的优势,但却极力回避其财政利源之效,这一点值得关注。究其原因,他是在极力回避为政府聚财这个事实,并从给民间带来的实惠与好处出发,以避免贤良、文学多从民间疾苦出发的责难,可谓用心良苦矣!但御史大夫的发言,并没有使贤良、文学停止责难,其中文学云:
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4]1。
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4]49。
所谓“市井之利”,即为国家通过市场活动所获的均输、平准之利。文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反对盐铁国营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从儒家的富民思想出发的。随后,文学对于当时均输、平准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一段详尽的发言:
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4]4。
此处,文学所反对的似不在均输、平准之法本身,重心在“古之均输,齐劳逸而便贡输”。虽然他们在《盐铁论·力耕》《盐铁论·通有》篇以农本为据反对商业的过分发展,但此处却不以商业本身来反对平准、均输之法,这与卜式以“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从商业过程本身来反对平准、均输之法,也是绝大的不同。其对平准、均输之法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官员腐败问题上,指出官员谋取私利使得均输、平准之法完全走向了其所追求目标的反面。这也是贤良、文学的一大策略。
对于汉武帝朝官员的腐败问题,双方有激烈的论辩。从桑弘羊一方不得不承认盐铁国营中出现的“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4]13的情况来看,平准、均输之法实行过程中出现腐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其与盐铁国营制中官员公开鲸吞国家财产、降低产品质量等直接腐败行为不同,均输、平准之法中的腐败是一种极具隐蔽性的腐败。由于“轻重”由人把握,如果不按照“轻重”规律调节——事实上这种调节的标准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稍微反其道而行之,腐败就滋生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历史随后所产生的各种基于“轻重”原理的经济政策实践中都面临的困局。班固在论及“轻重”时指出的“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12]已注意到了官员自身行为与这种制度正常运行之间的关系。在汉武帝朝,官吏晋升途径不拘一格,但主要以入财*如《史记·平准书》载元朔二年筑朔方城后,“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军功*如《史记·平准书》载元朔五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得官为常态。作为获益巨大又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均输、平准之法,继盐铁国营后再次成为各级官吏乘机谋取私利的凭借是完全可能的。只是这种腐败在当时的程度到底如何,现在难以准确定论。
三
尽管贤良、文学在会上极力要求废除各项兴利政策,但会议的结果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卖,作为兴利政策主体的均输、平准制度则与盐铁国营一并被继续保留。那么,均输、平准制度在盐铁会议后执行的实际状况又如何呢?对此,史籍并无明确记载。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一直被忽略。我们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会议第二年桑弘羊因谋反罪被诛杀后,均输、平准之法就逐渐废弛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推断。
第一,从均输、平准相关官职来看,《汉书》的各个章节都有记载,如《汉书·食货志》载,桑弘羊元封元年将均输、平准推向全国时,“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官……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任命隶属大司农的大农部丞,在各郡国基层置均输官,又在京师设平准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汉书·汉官仪》也有“平准令一人,秩六百石”的记载。然而,盐铁会议后,即不见有均输、平准官活动之记载。《汉书》倒是记载了两位担任均输、平准官的人,即黄霸“察补河东均输长”(《汉书·循吏传》),然而此事应在汉武帝末、汉昭帝初;赵广汉“举茂材,平准令”(《汉书·赵广汉传》),此事应在汉昭帝初期。可这两个例子根本看不到盐铁会议后均输、平准之法实际执行的情况。当然,史书也没有废除均输、平准官的记载。从《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败亡前“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来看,平准令在新莽之时仍存。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是围绕均输、平准之法的职能在正常运转?运转效率如何?我们在盐铁会议之后的汉代史料中,竟找不到一条关于他们活动的材料,如果均输、平准之法尚在正常运转,应不至于如此。似乎可以隐约看出,均输、平准二丞在盐铁会议后即便没有被废除,其组织均输、平准的职能也已渐渐不被重视了。
第二,从均输、平准制度的性质来看,作为桑弘羊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的首创,并于元封元年(前114年)在全国实行的制度,是一个以大农丞为领导,以京城的平准官和遍布全国各郡国的均输官为网络,在同级与上下级之间进行各种物资调配、转输和物价调节的复杂系统工程。这样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经济物流调控系统,实需要管理者具有相当高超的管理和领导能力,以及相当的经济知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只有桑弘羊能担当此任。正如班固所总结的,“弘羊均输”*这里的“均输”,实为“均输、平准”的省略,就如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虽以“平准”为篇名,但也是“均输、平准”的略称。。这几个字值得推敲,它告诉我们,均输、平准之法的兴废是与桑弘羊个人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桑弘羊既已诛,环顾当时,并未见有卓越的理财专家出现。由此看,均输、平准之法即便没有被正式废除,这个复杂系统也势必难以正常运行,时间既久,渐入荒芜也是必然的了。
第三,盐铁会议所讨论的没有在会议后被废除的经济诸政策,如盐铁国营、钱币铸造权、公田苑囿等事,在西汉后期屡遭儒者反对,盐铁国营还一度在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夏四月被罢除。唯独均输、平准之法,不见儒者反对。若均输、平准之法当时尚在正常运行,这种情况是难以解释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均输、平准之法已经渐渐废弛以致湮灭,其影响已不值得儒者反对了。
四
作为一种传统“轻重”思想的成功运用,均输、平准之法虽然在桑弘羊被诛杀后逐渐废弛,单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13]494的功效和全新的运作方式就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出现类似桑弘羊这样的商业天才时,它就会再度以新的形式重现人间。这种新的形式,即为汉宣帝时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关于常平仓,见于《汉书·食货志》)。
耿寿昌任职于大农丞,“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13]479,萧望之也认为他“习于商功分铢之事”[13]480。可见,他的才能与桑弘羊颇为类似,即擅长财经计算。他所奏设的常平仓,利用国家力量,一则调节粮价,二则因所筑仓在边境,更好地解决了边防的粮食供给。就原理上来讲,常平仓与桑弘羊“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的平准法较为类似,可以说是平准法的一个近承。然而就其复杂程度来讲,桑弘羊均输、平准之法是“兼及百货”的,而“常平之法,谷而已矣”[14]101。常平仓又回复到管子“轻重”原理与李悝的平籴之法了,其影响也仅限于北部边境附近的地区。从这一点来讲,常平仓虽是桑弘羊平准的继承,但除了在解决北边军粮这一点上颇有实际创建外,这个继承却是一个退步和缩小了的继承。它说明,类似桑弘羊那样高超、复杂的理财专家,已经难以在汉代历史舞台上重现了。
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在当时也的确发生了良好的功效,《汉书·食货志》言此制“民便之”,河南太守严延年府丞义也认为“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15]1363。这种功效实是“轻重”原理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儒者的心目中,一是认为国家参与经济流通过程,剥夺了生产领域农民的所得;二是愤恨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官吏腐败现象。从东汉刘般反对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14]130来看,常平仓制度也有贤良、文学所指出的均输、平准之法实行过程中官吏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这使得常平仓也同样受到了儒者与类似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均输、平准之法一样的反对。史载:“寿昌奏设常平仓,上善之,望之非寿昌。”[15]1223名儒萧望之在常平仓设立之时就加以反对,可见儒者对于常平仓的基本态度。严延年对常平仓也颇有微词,埋怨“寿昌安得权此”[15]1363?尽管汉宣帝没有采纳这些反对意见,然而在实行不到10年的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常平仓就在诸儒的一片反对声中,与盐铁官一同被罢除了。但与盐铁官不久再度恢复不同,常平仓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这种态势表明,汉代儒学在对基于“轻重”原理产生的流通领域的经济政策的反对上,取得了比盐铁国营制更大的成功。
及至王莽,这种“轻重”原理再一次被重视。王莽设立五均赊贷制度,在长安与洛阳、临淄等重要城市设置五均官,《食货志》载“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12]230。五均官之功能,主要是调节物价,防止豪民操控价格,在此过程中利用政府力量获益。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以四季中间的月份定物价,分上、中、下三种价格,对物价进行干预,防止高于官方所定价格。“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12]230-231由此看来,就原理与形式来讲,五均赊贷与桑弘羊的“平准法”十分类似,但在精确计量上却继承了李悝平籴法的精神。
然而,“轻重”原理在王莽这里遇到了一个矛盾,即从思想倾向上讲,王莽也是汉代儒生中的一分子,少时“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15]1509,从这个角度看,王莽必须继承贤良、文学、萧望之、初元五年诸儒等人的主张,反对利用流通领域 “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然而,就其所处的位置来看,作为一个新建王朝的皇帝,正如阎步克所指出的,王莽“也不能不借助帝国体制的财力动员和政治控制力量”[16]。他必须为国家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考虑,他的位置要求他必须再度运用各种兴利手段,包括实践“轻重”思想。面对这个矛盾,王莽采用了一种十分巧妙的对策,其言:
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今开赊贷,张五均……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13]492。
王莽的这段诏书,通篇不讲五均的财政意义,却引儒家典籍以证明其政策合乎儒家经义。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新创建!他在这里极力想证明的是,儒家思想也是允许进行五均赊贷制的。王莽在这里充分发挥其“文《六艺》”的思路,将五均赊贷包含进儒学体系中去。按照这种解释,上述思想与位置上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其直接效果是王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推行五均赊贷制,而不觉得与儒家思想有抵牾了。
然而,在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可以说毫无实行这种制度的条件。当时的吏治是“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13]494,未能出现像桑弘羊那样水平的大理财家,全靠一帮只为自己谋利的商人。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均变成了官僚富豪互相勾结、贱买贵卖、从中渔利的手段;赊贷这个便宜也不是好沾的,过期还不上钱,就会被罚做罪徒。”[10]378结果是其所追求的功能完全得不到正常发挥,其弊端却暴露无疑,进而引起了普遍反对。其命运也只有和盐铁国营制一样,最终随着王莽的覆亡而灭亡。“轻重”原理与儒家理想主义结合的畸形怪胎五均赊贷制,成了先秦两汉“轻重”原理实际运用中最为失败的一次尝试。
[1] 杨一民.《盐铁论》和西汉社会[J].先秦、秦汉史,1984(12):65-72.
[2] 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 中华书局.《史记》精华[M].王麦巧,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 汪锡鹏.重评汉武帝“盐铁专卖”[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60-67.
[6] 渡边信一郎.汉代的财政运作和国家物流[G]//刘俊文.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73-405.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5.
[8]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 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6.
[10]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20.
[12] 班固.汉书:第02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232.
[13] 班固.汉书: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5] 班固.汉书: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6]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97.
[责任编辑 杨玉东]
The argument of “heavy v.s. light” at The Salt and Iron Meeting in the historical view
YANG Yong
(SchoolofHistor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Henan,China)
The system of “Junshu and Pingzhun”, proposed by Sang Hongyang, is a great attempt on the largest scal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heavy v.s. light” after China established a unified regime. At The Salt and Iron Meeting, Sang Hongyang expound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ystem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while Xian Liang and Wen Xue objected to the system considering the serious official corruption.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Junshu and Pingzhun” was gradually abolished after the meeting. The system of “Changpingcang”, proposed by Geng Shouchang in the period of Han governed by emperor Xuan and emperor Yuan, is an inheritance of the system of “Junshu and Pingzhun” on a smaller scale. The system of “Wu Jun She Dai”, proposed by Wang Mang, completely failed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corruption.
The Salt and Iron Meeting; heavy v.s. light; the system of “Junshu and Pingzhun”; the system of “Changpingcang”; the system of “Wu Jun She Dai”
2016-1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6FZS007)
杨勇(1983—),男,云南鹤庆人,白族,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政治史、思想史研究。 E-mail:xia_2160337@163.com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1.017
K205;K234.1
A
1673-9779(2017)01-0098-07
杨勇.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J].2017,18(1):0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