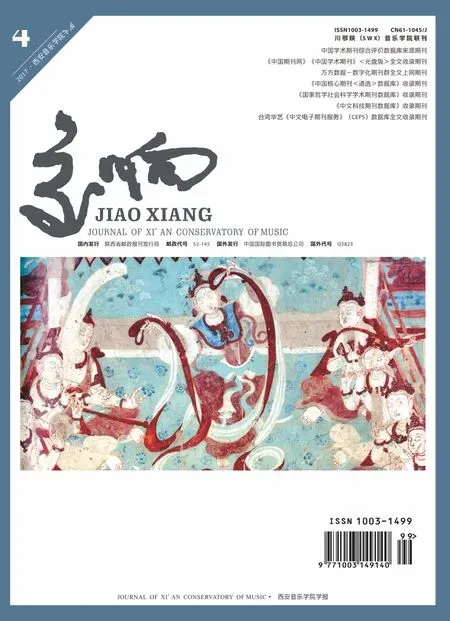藏区天主教音乐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以香格里拉茨中教堂为例
2017-02-08张富兰
●张富兰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100031)
茨中,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是一个遥远的滇西北村落,它位于滇、藏、川三省的交接地带,历史上,这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门户。茨中的“茨”藏语意为“村庄”;“中”藏语意为“六”旧时该村伙头管辖六村,故名。[1]村内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种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2]一座钢索吊桥连通着茨中村与外界的交通,之字形的爬坡山路只容得下一辆汽车经过,在当今依旧恶劣的交通环境下,我们很难想象传教士是如何跋山涉水让天主教在这里生根发芽的。
2017年4月笔者第二次来到云南香格里拉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进行采风,这一次在姚神父的允许下住进教堂,是一件十分难得和幸运的事情。在姚神父的引导下,笔者一个人来到传教士的墓地。墓地旁的蓝桉树印证着法国传教士百年的思乡记忆,站在蓝桉树下,恰好有一颗种子从树上落下,一段穿越历史的对话仿佛从此打开。
一、冲突、创造并成为传统:天主教的传入、法国传教士的探索与《Chants Religieux Thibetains》
茨中的天主教、天主教音乐是在百年之中,与当地宗教、民间音乐、民间文化不断调和与发展的产物。从巴黎外方传教士们进入藏区传播福音的探索到神父与地方精英为当地传承藏区天主教音乐所做的创新,都为茨中天主教音乐的传承与再发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新道路。茨中教堂的天主教音乐在百年的历史脉络里随着政策的革新、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着新的变化、形成新的传统。
(一) 天主教的传入
根据可信的史料记载,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代初期的贞观年间,当时称为“景教”。此后,又于元代有较大规模传入,当时称“也里可温”。[3](P17)至清代,随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云南天主教活动开始日益活跃,并试图开辟从滇西北进入西藏的道路。[3](P105-106)17世纪中叶以后,为摆脱葡萄牙独享东方保教权所带来的种种限制,打破耶稣会对中国的垄断,罗马教宗在1600年允许其他修会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他国家的传教组织进入亚洲各国开展活动。此时,法国的两位主教陆方济(Franciscus Pallu,1626年-1684年,又译巴吕)和朗柏尔(Lambert de lamoffe,生卒年不祥)于1653年建立了一个修会组织。在此基础上,罗马教宗于1657年任命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陆方济为越南东京(越南北部)宗座代牧主教,并署理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四川五省教务。[3](P78)185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顾德尔(Goutelle,Jean-Baptiste,1821年-1895年)潜入康边藏族地区,由于进藏传教的目的受阻后,被滞留于德钦县,由此,天主教正式传入德钦县。
(二) 法国传教士的探索
在天主教传入茨中之前,这里一直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管辖之下,异教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为了避免与当地喇嘛的正面冲突,西藏教区派遣余伯南(Jules-Eienne Dubernard,1840年—1905年)神父和蒲德元(Pierre-Marie Bourdonnec,1859年—1905年)神父带领几十个藏民进入德钦县茨菇村及其周围地区,以交朋友、馈赠礼物等手段收买了当地的土目头人,让他二人得以在此居住。传说他们曾用两包草烟,购买了茨菇村一块土地筹建教堂。同时,西藏教区将康定的六户四川籍教徒举家迁来,以巩固这一传教点。[3](P106)然而,由于宗教势力间的相互冲突,使得天主教在德钦县的传播并不十分顺利,茨菇教堂乃茨中教堂的前身,1905年在维西教案中被毁。
至此,西方早期对于藏族康区的探索已经开始萌芽,最早将康区这块神秘的土地介绍到西方的主要源自于当时入藏的传教士。在清代的各类关于藏地研究的著作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要数法国传教士古纯仁编写的《川滇之藏边》。当时天主教在康区传播大概有70年,他们对康区的了解为古纯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古纯仁于1907年入藏,在康区的15年中,他学会了汉文、藏文,游历于康区各地,将康区的地理、宗教、政治、经济、交通、人口、语言等各方面介绍到西方。书中关于茨中地区的记载见于《维西》一章的附文:《旅行怒江盆地》,这是由康藏与西藏地方边界经云南茨菇至茨曲龙的短途笔记。书中所记康区各大地区的历史、政经、地理交通、道路、民族、风俗等内容是珍贵的康藏民族志史料。[4]据作家范稳了解,他30多岁进入康区,离开时已逾70岁,被称为“天主教西藏第一通”。
(三) 当《Chants Religieux Thibetains》成为传统
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进入藏区后,传教士们为了有效地传播福音,对藏区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语言习俗、地方音乐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为了能够更好地使西方的天主教以当地居民更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开来,传教士们努力向当地喇嘛学习藏语,在不断地探索中,将欧洲的四线谱与藏文相结合,诞生了在藏区流传的藏文圣歌谱本《ChantsReligieuxThibétains》,这是目前在藏区发现的唯一一本藏文圣教歌集。
这本藏文圣歌谱本是传教士对于天主教音乐与藏区调和的产物,谱本中的藏语经文使藏民们更利于接受和传唱,拉丁文圣歌标题与欧洲四线谱更有助于遵循西方天主教传统。圣歌谱本于1894年出版于IMPRIMERIE OBERTHUR-RENNES,谱本中共包含有22首圣歌,依据孙晨荟在《一本珍贵的藏文天主教歌谱
圣歌谱本《ChantsReligieuxThibétains》多见于盐井教堂,教友们几乎人手一本,在日课中所听到的圣歌相比于云南德钦县的茨中和茨菇两座教堂,旋律性更强,更多的遵循圣歌谱本上的传统,但已被藏区教友们演绎出了更多的藏族民歌风格。
盐井教堂的天主教音乐更多的是遵循传教士时期的“传统”,由于盐井教堂目前处于无神父的宗教状态,不能在周日举行完整的弥撒仪式,教友们便在早晚日课和周日原本的弥撒时间聚在一起唱圣歌。圣歌全部来自于圣歌谱本《ChantsReligieuxThibétains》。
二、传统的创造与继承:《圣教经课》
在茨中村和茨菇村,只有部分老教友拥有圣歌谱本《ChantsReligieuxThibétains》,谱本并不会在日课和弥撒中使用,而是作为珍藏。在茨中村流传最广的是由肖杰一老师翻译的《早晚课经》,肖老师运用汉语标注藏语经文的发音,通过这种独具创造力的方式,使得茨中村及周边的茨菇村、维西县、贡山县等地的藏语经文得以传承下来。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教友们虽同在藏区,但对于藏文的掌握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经过询问得知,盐井与茨中两个村落,虽同处于藏区,相距也并不远,但是盐井位于西藏省、茨中位于云南省,茨中的年轻人们在学校中已经不再学习藏文,因此,即便是村中的大学生也仅能够听、说藏文,盐井的年轻人都在学校中接受过藏文教育,因此依然能够读懂藏文。
在茨中村,新一代年轻人不懂藏语,藏族经文就无法继续传承下去。年近90岁的肖杰一老师作为茨中村著名的“活字典”,精通拉丁语、法语、藏文、傈僳文、苗语。作为村内公认的最了解茨中教堂历史和天主教的“专家”,他主动承担起了传承天主教藏语经文的重担,历时七年,为藏语《圣教经课》标注汉字发音,用这种独具创造力的方式使藏语经文流传下来。用汉字标注藏语经文发音的方式一方面能够使传唱天主教的藏文圣歌的传统保存下来;另一方面,由于《圣教经课》仅用汉语标注藏语的音节与发音(例如:“天主”被音译为“闹吉打包”),并无任何明确的含义,因此,对于教友们理解天主教经文、教义毫无帮助。但是口头传唱藏文圣歌的传统就此保存下来,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口头文化传承方式使民间自主积极传承宗教音乐文化的很好的范例。例:《圣教经课》中的《圣母经》:
结,玛利亚,正吉共为,气拉下才罗,气当林吉打宝玉,细玛哪吉哪乃形劳吉,印巴当,气吉冷吉这不耶稣,形劳当邓巴印,劳大比玛利亚,闹吉打宝以用,气吉尼讷地巴金吉,顿杜打得当,尼哪吉为才,瑟瓦地巴说,地打印吉。
译文:万福,玛利亚,您充满盛宠,主与您同在,您在妇女中,受赞颂,您的亲自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
这本《圣教经课》于2002年在大理教堂出版,茨中村及附近的茨菇村教友几乎人手一本,对于《圣教经课》中的常用经文《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等已达到人人能够背诵的程度,但是很多依然爱把这本经课随身带着,有意无意地在念经时翻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信仰的标签。
笔者在调查中,通过参加茨中教堂的复活节弥撒、弥撒及日课的仪式,在多次聆听教友们的念经后,也逐渐能够拿起《圣教经课》跟随念读部分简单的经文。《圣教经课》中的大部分经文的旋律偏向于念诵音调,旋律性不强。通过对肖杰一老师和见证茨中教堂历史的老教友们的采访得知,目前茨中教堂内念诵的经文与传教士初到茨中教授他们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圣教经课》虽然旋律性不强,但是却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弥撒仪式中的经文分为齐唱式和应答式。齐唱式如《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应答式如《耶稣祷文》。茨中教堂的教友们在教堂中进行活动时,男、女教友们会自觉分坐于教堂两边,女教友坐于教堂左侧,男教友坐于教堂右侧,应答式圣歌由男女教友交替演唱。
茨中教堂里依然保存着传唱藏语圣歌的传统,一方面得益于地方精英(例如肖杰一老师)的努力;另一方面,驻堂神父姚神父的对于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观念也是其传承的必要条件。笔者在弥撒仪式、复活节弥撒、拜十四处苦路图仪式和日课中均发现,这位来自汉族地区的姚飞神父也会随同教友们一起唱藏语圣歌。在与姚神父的访谈中,笔者也得知,姚神父是一位非常尊重和热爱传统文化的神父,他认为,在弥撒中使用藏语,当地的教友也会觉得亲近,因为语言是一个最亲近的交流工具。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不能丢掉的。在姚神父的支持下和当地教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藏语经文一直流传至今。
三、融入与发展的传统:汉语圣歌谱本《禧年之声》
不得不承认,汉族地区的神父被派遣到少数民族地区作为驻堂神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步为当地的天主教、天主教仪式、相对应的天主教音乐注入了更多新鲜的血液。自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以来,一批神父来到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当地教友服务。自教堂有了驻堂神父以来,许多教友从艰苦的宗教环境中解脱出来,当地的宗教生活、宗教礼仪也逐步走上了规范的道路,教友们每周期盼的弥撒、领圣体仪式也能够如期举行。由此,神父为更加规范天主教的仪式,也为当地的教友带来的汉语圣歌,使当地的天主教音乐更加完整和丰富。
例如,在茨中教堂的常见本——河北邢台教区备修院2000年出版、2002年再版的《禧年之声》,此唱本由邢台教区的高保金神父编写。此唱本广泛应用于云南大理教区各教堂中。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圣乐歌集,歌集中所包含的圣歌选自于传统的、通俗化的宗教圣乐或弥撒曲。歌集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弥撒(包括季节弥撒、节日弥撒、通用弥撒、弥撒套曲以及圣事礼仪);二、圣体降福歌曲;三、圣歌(包括季节歌曲、节日歌曲、黎明之歌、心颂、泰泽祈祷以及年终赞主诗等)。歌集中包含歌曲共计621首,10套弥撒曲。涵盖教堂礼仪音乐与教友生活、聚会场合中的祈祷用乐等,曲目数量大、分类全,便于教友们进行选择。
笔者在参加2016年茨中教堂周日弥撒、2017年茨中教堂复活之夜、复活节弥撒时发现:茨中教堂的弥撒仪式虽然依然保留着念诵藏语天主经文的传统,但其中已经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圣歌。通过观察,笔者在弥撒仪式中发现,对于藏语经文部分的念诵,虽然当地很多人已不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大多都烂熟于心,几近“人经合一”程度。然而,由于汉语圣歌在此流传时间较短,大多数老教友还处于“跟不上”的状态,都是在神父的提示下由几位中年教友大声带领教友们大声唱。在弥撒仪式中,汉语圣歌的加入使得整个仪式更加完整和规范,在一年仅一次的复活节弥撒仪式中,教友们对于这个仪式的过程处于有点“不知所措”的状态,仪式间各个步骤的衔接经常需要神父在其中稍作提醒,当然这也是在日积月累中将藏区天主教仪式逐渐规范的过程。教堂中传唱的汉语圣歌全部来自于《禧年之声》,主要应用的歌曲为以下几首:《欢呼歌》《天主经》《祝你平安》。此类歌曲如《祝你平安》,笔者在北京的宣武教堂听到过相同的音调,无论是在汉族地区还是在遥远的滇西北藏族村落,这首歌都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中国自主自办教会的政策对于全国各地宗教的影响、对宗教音乐的影响。
自天主教第一次进入中国藏区至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洗礼,无论是在茨中村、茨菇村还是上盐井村,甚至是藏区的其他村落里,年迈的教友们对于当年来到这里的传教士仍然有着深刻的记忆。在茨中村,曾经被神父收养的阿拉迪卡奶奶的家中仍旧挂着法国洛神父的照片;家中也收藏着曾经在教案中遗留下来的天主十诫碑块。当地本土的教友已经发展到第四代、第五代,然而条件依然是艰苦的。目前茨中教堂的驻堂神父是姚神父,旁边的茨菇村,刚刚在今年培养出了一位年轻的藏族本地神父——马神父,解决了茨菇教堂没有神父做弥撒的困境,同时,教友们也为培养了一位年轻的本民族神父感到欣慰和骄傲。
结 语
天主教在藏区的百年碰撞与交流中,经历了冲突—调和—和谐的局面。在传教士进入藏区之初,他们带来了拉丁文四线谱,随着对藏文的学习和掌握,逐步将拉丁文歌词翻译为藏文,以藏民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福音,并创造性地让传统的欧洲四线谱、纽姆记谱法在藏区流传。“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禁止,处于无宗教时期。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颁布和中国独立自创自办教会的政策,当地教友也重拾信心,积极合理地恢复当地的宗教活动,运用创造性的方式将藏语经文传承下来。后来,由于神父来到,在逐步规范了当地宗教仪式、宗教生活的同时,也让当地的宗教音乐更加丰富和完整。而在此刻,肖杰一老师虽已年迈,却依然没有停滞为教会服务的脚步,他将自己编写的《圣教经课》重新修订,将藏语经文的逐句翻译,为经文增补了汉语释义,以此解决教友们不懂经文的难题,并为《圣教经课》加入了藏文圣歌。新的《圣教经课暨藏文圣歌选》很快就会问世,茨中天主教音乐的发展也将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网址:Http://www.diqing.gov.cn/whdq/zjwh,文化迪庆专栏之宗教文化,《天主教》,2016年1月4日。
[2]云南乡村数字网网址:http://www.ynszxc.gov.cn/provincepage/default.aspx,茨中村,村情概况,2014年7月13号。
[3]刘鼎寅,韩军学.云南天主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4]赵艾东,石硕,姚乐野.法国传教士古纯仁《川滇之藏边》之史料价值——兼论《康藏研究月刊》所载外国人对康区的记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0).
[5]孙晨荟.一本珍贵的藏文天主教歌谱《ChantsReligieuxThibétains》解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