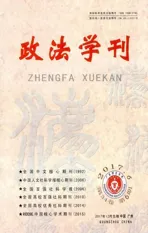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理论与实践之评析
——兼论《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解释适用
2017-02-05易高翔
陆 剑,易高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的规定是我国民法有别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独有制度之一,立法史上可以追溯到前苏联,但是在传统民法理论和比较法中找不到直接与之相对应的概念。[1] 161198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最早使用了“恶意串通”的概念。①《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其后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保留了相关表述。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此外,除民事基本法外,其他民事相关法、行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此亦有规定。③如《票据法》、《拍卖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可视为对现行法规定的沿袭。但关于恶意串通规则的内涵,上述民事相关法、行政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阐释,致其在规范含义、构成要件、适用范围等方面较为含糊,且与我国现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代理制度、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等存在竞合,与传统民法理论中的通谋虚伪制度亦难以界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滥用恶意串通之规定的现象,即原本可以通过其他规则裁决的案件却被当作恶意串通行为裁决,甚至同一事实在不同法院的认定情况也大不相同,导致民法体系构成与规则适用上的混乱。本文拟对我国现行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从学说观点、立法演变、与传统民法上通谋虚伪之关系及其司法适用状况展开分析,全面反思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规则,以期全面评析《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立法利弊。①关于恶意串通之规定,学界已有的论述参见:黄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无效规范的存废——基于体系的一项检讨》,载《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卷第1辑;杨代雄:《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朱建农:《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6期;陈敦:《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陈小君:《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立法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
一、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的规范分析
究竟何谓恶意串通,我国民事立法并没有明确,学界亦没有统一意见。兹列举代表性观点如下:穆生秦认为:“恶意串通是指互相勾结,共同作弊,为牟取私利而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2] 71彭万林认为:“恶意串通是指法律行为的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故意合谋,弄虚作假所实施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3] 154王家福认为:“我国民法上的恶意串通,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上的通谋虚伪表示,即双方通谋而为内心真意与外部表示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另一种是指双方本身作出的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主观上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客观上发生了他人利益受有损失的损害后果。”[4] 344魏振瀛认为:“恶意串通,是指行为双方为牟取不正当利益,互相勾结串通而实施的有损于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5] 165
对上述各学者对恶意串通所下定义进行比较观察,可发现学说对此众说纷纭,并未达成统一意见:其一,在行为主体范围方面,有认为仅指参与实施恶意串通的当事人。有认为恶意串通之主体还应包含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其二,在恶意串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方面,有学者认为恶意串通与传统民法中的通谋虚伪等同;也有学者认为恶意串通既囊括传统民法中的通谋虚伪,即行为人所为的内心真意与外部表示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也包括行为人所为的内心真意与外部表示一致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具有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故意和他人利益受损的客观后果。还有学者认为恶意串通并不等同传统民法中的通谋虚伪。其三,在恶意串通损害对象方面,依《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之文义解释,应包含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但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相重复,也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直接由《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制即可,无须由《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规制。对此,《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采纳了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删除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表述,仅保留“他人利益”表述,立法应值赞同。
(二)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表示之比较
我国学者在论述恶意串通之含义时,往往与传统民法理论和比较法中的通谋虚伪相比较。厘清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之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恶意串通之内涵与外延。
所谓通谋虚伪表示,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称之为虚伪表示,指意思表示的发出人与意思表示的受领人串通而作虚假的意思表示,其构成要件有三:(1)须有意思表示;(2)须外部表示与内心的真意不相符;(3)须双方存在通谋行为。[6] 360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八十七条第一款列有明文①②该款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转引自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一)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规定的规范分析,《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条第(1)项规定亦有类似规定。上述国家或地区的通谋虚伪表示之概念与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的规定确有相似之处。首先,无论是通谋虚伪表示还是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原则上都为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此无疑问;其二,由于两者都存在串通行为,因此两者的参与者均须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而不可能是单方法律行为;其三,恶意串通行为客观上造成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损失,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为了达到某些非法目的。如甲出卖房屋与乙,后来房价涨幅较大,甲不愿继续以原价格出卖,随与丙假装作出关于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致使乙无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但通谋虚伪与恶意串通之区别也甚为明显,传统民法上的通谋虚伪表示,并不是一个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概念。[7]其一,通谋虚伪表示理论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也即某一个行为是否构成通谋虚伪,与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关。所谓的通谋虚伪表示行为,可以出于各种动机。通谋虚伪表示通常多在欺诈第三人,但不以此为必要。[6] 360而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须行为人主观上具备恶意。正如日本学者我妻荣所言:“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立法目的乃至于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至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状态并不是通谋虚伪制度需要考虑的。”[8] 272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民法中的通谋虚伪表示理论是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恶意。其二,通谋虚伪表示并不考虑客观上是否有损害发生,传统民法上通谋虚伪表示之所以无效,乃基于意思真实原则。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既然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内心真意并不是想使其法律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则法律没有理由使其法律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而于恶意串通行为,之所以无效,除主观上恶意之具有道德谴责性外,其客观上对国家、集体、第三人之利益的损害是其无效之根源,乃出于保护社会之公益的需要。其三,就意思表示而言,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为真意保留的虚伪意思表示。而恶意串通行为中,除包括虚伪的意思表示外,还包括双方为不法之利益,实施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客观上造成他人利益受有损失的情形。
综上,传统民法理论中的通谋虚伪表示理论属于意思表示的范畴,其无效乃基于意思表示真实原则,因其意思瑕疵而无效,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对其意思表示内容进行限制的结果。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虽与通谋虚伪表示具有相似之处,在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方面,包含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但其构成要件上却要符合“主观上恶意+客观上串通+利益损害”模式,也即必须有利益之损害的存在,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共利益。因此不论从形式上的构成要件来看,还是从立法目的来看,我国恶意串通之规则无法替代传统民法中的通谋虚伪表示。《民法通则》并未规定通谋虚伪,恶意串通制度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通谋虚伪表示的调整功能,但是两者并不等同,恶意串通除强调“串通”的虚伪性外,还强调“恶意”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也正是由于其概念的模糊性导致在司法适用中出现混乱,极易被滥用误用。
二、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规定之司法适用状况
(一)司法实践中对恶意串通行为认定混乱
自《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解决具体问题的裁判数量很多。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实务中人民法院对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情况,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网搜集了大量实务中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整理分析,笔者发现实务中法院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的案件类型大体上可以归为以下五类:一是代理行为中的恶意串通行为,其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行为人与第三人合谋损害行为人的被代理人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①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乔某、郑州市新源石化公司与中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销售分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的“(2010)豫法民二终字第41号”判决。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678617.html?keywords=%EF%BC%882010%EF%BC%89%E8%B1%AB%E6%B3%95%E6%B0%91%E4%BA%8C%E7%BB%88%E5%AD%97%E7%AC%AC41%E5%8F%B7&match=Exact。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2月28日。一种是将双方代理行为中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损害被代理人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①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鹏娜影视咨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雨虹广告有限公司、王某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作出“(2008)高民终字第 837 号”判决。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108112.html?keywords=%EF%BC%882008%EF%BC%89%E9%AB%98%E6%B0%91%E7%BB%88%E5%AD%97%E7%AC%AC837%E5%8F%B7&match=Exact&tiao=1。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2月28日。二是将行为人恶意转让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②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与周某、西安市中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日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案”作出的“(2008)陕民一终字第 12 号”判决。北大法定: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114086.html?keywords=%EF%BC%882008%EF%BC%89%E9%99%95%E6%B0%91%E4%B8%80%E7%BB%88%E5%AD%97%E7%AC%AC12%E5%8F%B7&match=Exact&tiao=1。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2月28日。三是将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损害所有权人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③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张某与吕某、娄某、上海浦东交通巴士长途客运有限公司一般经营合同纠纷案”作出的“(2009)徐民二终字第 0562 号”判决。四是在财产权多重转让场合将转让人的后一个恶意的财产转让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如“一房二卖”等。④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某、余某与保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甲、严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作出的“(2010) 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753 号”判决。五是担保合同中的恶意串通行为,主要表现为借款人与贷款人等主合同当事人为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恶意串通实施的虚假行为等。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对“石家庄市商业银行金桥支行与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河北公司、河北省际货运代理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作出的“(2001)民二终字第 116 号”判决。通过对以上司法实践适用相关恶意串通之规定所作出的判决整理分析,笔者发现实务中对恶意串通这一概念的理解极不统一。在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解决具体案件时显得比较随意,而事实上上述实务中常见的五种适用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的案例在传统民法理论和比较法中都可以通过其他民事制度、民事规则予以调整,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同样可以找到替代规则。但实务中却不加区分,将“恶意串通”当着可以认定法律行为(合同)无效的兜底条款,结果导致民法体系上的混乱和司法适用上的混乱。[9]
(二)适用恶意串通规定之案件类型评析
1.恶意串通逃避债务
将行为人恶意转让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从而否定其转让财产行为的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之规定和法理。首先,行为人恶意转让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属于“债之保全”规则(《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五条①《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调整的范围。因行为人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而利益受有损失的债权人完全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主张行使债权人之撤销权,而且此撤销权受《合同法》第七十五条除斥期间的限制。如果将行为人与相对人串通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从而适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否定其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此时行为人的恶意转让行为为自始、当然、确定、永久无效。[10] 261而且利益受有损害之人主张其为无效法律行为(合同)是不受诉讼时效或者除此期间的限制。这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认定的在债权人撤销之前,债务人的恶意转让行为是有效的相悖。此外,法律行为之无效理论乃出于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场合,并无公共利益需要保护之必要。基于此,将行为人恶意转让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认定为属于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的适用范围,从而不承认其法律效力,既与法律行为(合同)无效制度的保护功能相悖,也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意旨相悖。
2.恶意串通与无权处分
就恶意串通实施无权处分而言,对于无权处分行为,大陆法系民法理论认为无权处分的行为原则上效力待定,不同的是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认定效力待定的是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原则上是有效的。《合同法》明文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待定。因而在我法制中,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处分他人物品的情形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和《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处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待定,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或者权利人追认的,始生效力。《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并不当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须符合善意取得要件始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实务中直接适用上述规定即可达到保护原权利人的目的,无需再将行为人恶意串通处分属于他人所有物的行为认定为属于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之规定的适用范围,从而不承认其法律效力。
3.恶意串通与“一物二卖”
就恶意串通实施财产权(物权、股权等)多重转让而言,最典型的是交易中的“一物二卖”行为。以“一房二卖”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下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区分“后一买受人对前手交易知情”和“后一买受人对前手交易不知情”两种情形,分别予以不同的法律规则规制。于前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设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场合,如果出卖人已经就房屋与先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则出卖人应该信守承诺履行交付合同项下房屋并移转房屋所有权的义务,基于此,若出卖人与后一买受人恶意通谋,另行订立以该房屋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并将房屋移转给后一买受人,导致先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此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后一买卖合同属于我国民法上的恶意串通行为,从而不承认其法律效力,而先买受人得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合同项下房屋并移转所有权的义务。于后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设有明文规定。在“出卖人与第三人没有恶意串通”的场合,也即后一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前手交易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院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后一买卖合同的效力。由此可见,最高法院似乎认为在“一房二卖”场合,出卖人与后一买受人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将成为决定他们之间买卖合同效力之关键。一般来说,所谓的恶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或者没有理由不知道其行为对社会、他人有不利影响,仍然希望或者放纵这种结果的发生。所谓的串通,包括双方当事人事前勾结通谋,也包括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行为的默示。但是由于债权具有相对性,其效力仅存在债之关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11] 219因此在交易当中,当事人对标的物是否存在债权往往是很难了解的,而且法律也不苛求也不能苛求当事人对此负注意义务。[12] 727但是即使是后一买受人已经知晓前手交易情形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被认定为属于我国民法上的恶意串通行为,从而使出卖人和后一买受人的买卖合同无效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依据市场特征和债权的非公开性特征,后一买受人作为与前手交易当事人不相关的第三人,并不负有尊重前手交易的义务,法律也不能苛求后一买受人负注意义务,否则行为人的自由将受到过分限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基于自由竞争的原理和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卖方有权自由选择交易对象。此外,无论是前一买受人还是后一买受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而同一标的物上的债权具有平等性。换言之,即使是后一买受人最终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其行为也不能认为是构成对前一债权人债权的侵犯。因此不能认为此时债权成立在先的债权人的权益存在损害,而构成恶意串通行为须以客观上损害发生为要件,在“一房二卖”的情形下,债权成立在先的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受到侵害,因而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但先买受人的权益仍然可以通过其与出卖人的债之关系获得救济,或主张违约之债,或解除合同。否则,如果认为先债权人有权申请法院认定出卖人和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为无效,则无疑是使先债权人的债权具有像物权一样的对世性,其义务人将不仅限于债务人,其他一切人都成为义务人,而债权具有非公开性特征,打破债权的相对性特征无疑会限制一般人的行为自由。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侵犯债权的行为都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是采取有违社会公共道德的方式侵犯他人的债权,则其债权则可能因为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而无效。参酌比较法的经验,德国也有不少判例认为此种情况下后一买卖行为无效可资借鉴。[13]530德国学者弗卢梅也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得因行为人的债权行为因为违反社会公共道德而不予承认,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并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自当无效。”[14]455-466但是即使是在此种情形下,出卖人与后一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也不宜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而使之无效,如此则难以解释特定第三人的个人利益缘何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事实上,更恰当的做法是适用《民法通则》或《合同法》之规定,将其完全涵盖于因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的规定中。于此,更符合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保护功能。
4.担保合同中的恶意串通行为
在债之担保中,主合同当事人为骗取担保人提供担保而串通一气时有发生。此外,担保人与债务人串通,虚构债务人或者保证人责任财产以骗取债权人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担保法》第三十条也明确规定在此种情形下,承担保证责任的一方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该条规定似乎认为在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为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保证合同应归于无效。实务中据此而认定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形很多,学术界上也确有学说认为我国民事基本法上的恶意串通规定与该规定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15] 118但是,这一观点并非不可挑剔。如果保证人因为主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因此受有欺诈而致使其在违背自己内心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保证合同,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欺诈行为,因而保证人完全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保证合同从而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使是国有企业利益因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欺诈行为而受有损失,国有企业也同样可以主张撤销权,如果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是对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的特定保护,那也应该依据该项之规定主张该合同无效,而不应该借助于恶意串通之规定来主张合同无效。
(三)小结
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保护功能在于保护社会之公共利益,只有当法律行为危及到社会公益时,才能将其归于无效,而如果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仅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时,则应当属于效力待定的范畴,由利益受有损失的特定第三人来决定是否主张其无效,法律不应该过分介入私人生活,“其主要理由是每个人权益最合适的保护者是他自己,因而个人充分的自由对于格保护,社会进步有重大帮助。”[6] 15当然如果某一法律行为直接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同时也危及社会之公益,则应认定其无效而非效力待定,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可涵盖个人之利益。基于此,上述司法实务中常见的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而认定其无效的五类案例实质上都不应轻易认定其为无效,若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则属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制范围。若损害的是第三人利益,则需分三种情况讨论:其一,如果其损害的只是某一个特定人的利益,则其应属于效力待定的范畴而不能归于无效范畴,这是因为法律行为无效制度原则上只保护社会之公益;其二,如果其行为损害的或者其行为潜在的可能的受害者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则应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范畴;其三,如果其行为既损害了某一个特定人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则完全可以认定其行为触犯公益,因而不应承认其法律效力即可。因此立法没有必要过分介入私人生活,没有必有对个人利益予以特别保护,使任何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都归于无效,否则将适得其反。
三、《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适用与解读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探寻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客观意旨)。如果法律条文在制定之后,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法律条文的含义发生改变(歧义乃至多义)以至于适用中难以把握,则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寻求立法之初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并辅之以目的解释,以探求立法者制定该条文立法目的在当下有无恰当性。
就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规定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1956年12月制定完成的第一部民法草案,该草案第四十五条最早使用了“恶意通谋”表述;①此处的“恶意通谋”即是后来《民法通则》中使用的“恶意串通”的雏形。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最早“恶意串通”的含义仅指本人的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前后共四稿在表述恶意串通之规定时,皆使用了大体上相同的表述:“一方采取恶意串通之手段,使对方违背本人意志实施的法律行为”。[16]377-442可见,恶意串通行为的参与者实施恶意串通的结果是使得第三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实施违背其自身意思的法律行为。显然,于双方法律行为当中,不可能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实施恶意串通,只能是其中一个当事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使得对方当事人实施了违背本人意思的行为。而一方当事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使得对方违背本人意志实施法律行为,这实际上属于欺诈行为。然而上述四个《征求意见稿》对欺诈都有明确表述,立法不可能重复规定,极有可能的是这四部民法草案与新中国1956年12月制定完成的第一部民法草案关于恶意串通的理解是一致的,即仅指代理活动中的恶意串通行为。这一时期学者的著述也大多将恶意串通行为限于代理人滥用代理权行为。可见在我国早期民事立法中,恶意串通行为主要指的是本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实施损害本人利益的法律行为。然而正如法律哲学家Radbruch所言,“法律似船,虽由领航者引导出港,但在海上则由船长指导,循其航线而行驶,不受领航者之支配。”②加之《民法通则》出台以后,立法和司法机关一直未对恶意串通之规定作出解释,导致司法实务中恶意串通之规定的适用范围失之宽泛以致被误用,某些本应适用其他规则规制的行为却适用恶意串通规定规制,并导致本不应该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
①草案规定:“由于行为人的一方,同对方的代理人或第三人恶意通谋而做出的法律行为,经申请后,法院得确认宣告为无效。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参见何清华,李秀清,陈颐:《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转引自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总之,恶意串通之规定系我国民法上独特创举,其立法之初衷乃在于规制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滥用代理权行为,与传统通谋虚伪表示并不等同。由于其规范内容的模糊性,学界对此也莫衷一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其适用范围越来越大,从而造成法律规范体系的混乱。从司法实践中的效用来看,实务中所判定的适用恶意串通之规定的除恶意代理外的四种情形,在现行民法上都可以用其他规则(债权人撤销权、欺诈等)来替代。《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在保留恶意串通之规定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删除 “国家、集体利益”的表述,仅保留“他人合法权益”的表述,在立法上颇值赞同,系一大进步。但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已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的情形下,恶意串通规则已然被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完全替代,《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继续保留恶意串通之规定应作限制解释。从解释论的角度,宜回归立法初衷,将恶意串通之规定限制解释为仅产生规制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效果。
[1]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穆生秦.民法通则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3]彭万林.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魏振瀛.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6]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黄忠. 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无效规范的存废——基于体系的一项检讨[J]. 人大法律评论,2014,(01):188-212.
[8]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新订民法总则[M].于敏,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9]杨代雄. 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J]. 比较法研究,2014,(04):106-121.
[10]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3]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5]谢怀栻,王家福.合同法原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何清华,李秀清,陈颐.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