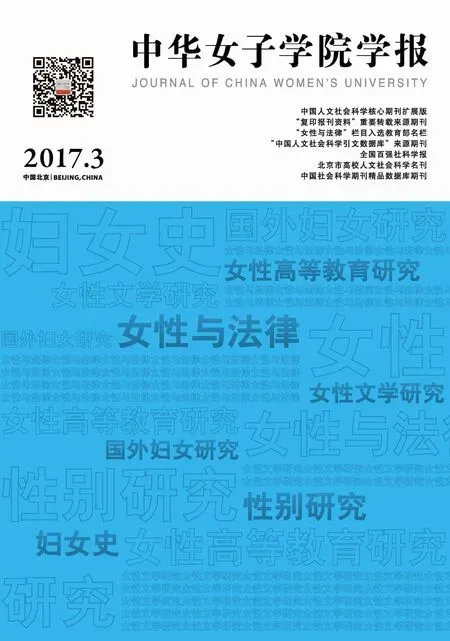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童心”铸就的“纯真”美者
2017-01-28陈娇华
陈娇华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童心”铸就的“纯真”美者
陈娇华
沈从文以仁爱之心和赤子情怀主要铸塑了纯真的少女、赤诚的妓女和良善的妇人等三类“纯真”女性形象,她们承载着作者的理想之梦,寄寓着他独特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也是其自身人格和性情的艺术呈现。这些女性形象发散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美光泽,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但与当时现实女性的生存境遇存在一定距离,她们更多是承载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人性理念,泄露了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念。
童心纯真;女性形象;女性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不仅是一位独特的田园牧歌抒写者,为读者奉献了《边城》《三三》《月下小景》《长河》等优美篇章;也是一名优秀的女性形象铸塑者,为文学史画廊增添了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夭夭(《长河》)、如蕤(《如蕤》)、萝(《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母亲(《菜园》)、老七(《丈夫》)等纯朴善良、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学术界对于这些女性形象颇有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发掘这些女性形象呈现出的作者“妇女解放意识”[1]或者男权意识[2],或是对女性既崇拜又轻视的矛盾女性观等。[3]二是从创作理念出发,探讨这些女性形象体现出的作者人性理想[4]、生命诗学[5]和乡土意识[6]等。三是从悲剧意识角度出发,探究这些女性形象悲剧的成因及其丰富内涵。[7]四是从女性与水的关系出发,探讨这些女性形象蕴含的地域文化及其审美理想。[8]此外,还有从形象原型及生态意识角度等进行研究的。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要么沉浸在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津津乐道中,忽略或者无视其都市题材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要么把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等放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没有看到“其实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沈从文借以表达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尤其是爱欲苦闷——的修辞手段或者说艺术风景”。[9]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以李贽的“童心说”来阐释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打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都市空间、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等之间的人为割裂,使之融为一体,并由此探析作者潜意识中的女性观。《童心说》开篇不久即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0]409沈从文创作伊始便是秉着一颗童心,即初心和真心从事创作,同时,又以一颗饱满的仁爱之心铸塑很多优美动人、良善美好的女性形象。他曾深情地说:“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倾向的。”[11]98因而不论是翠翠、三三、萧萧、夭夭等湘西边地女性,还是如蕤、萝及《看虹录》中的女主人等城市女性都是非常质朴、善良的“纯真”美者,正是她们,承载了作者的“梦的希冀”,也艺术化地呈现了作者的人格、性情及其被压抑的“爱欲之梦”。
一 、“纯真”美者的各类型铸
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曾说:沈从文“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对美的东西有着一种炽热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欲的感情。美使他惊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12]10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纯真”美者——女性形象的铸塑鲜明体现了作者对于美的敏感和炽热。此处的“纯真”意指纯朴、真挚,也就是指没有被世俗道德、文化观念及习俗时尚等所染指的人的最初性情和本性,即前述所谓“童心者,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沈从文笔下的“纯真”美者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纯真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黄牛寨寨主女儿(《龙朱》)、会长小女儿(《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蕤及萝等。她们容貌漂亮,天性单纯,或者像自然界动植物一样生长和长大。《边城》中翠翠便是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日晒风吹中长大的,没有到过大都市,也没有上过学和接受过任何现代文明熏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13]6夭夭也是在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长河》)。或者任性恣情地生活,不受伦理道德观念束缚,也不为时风流俗影响,完全听凭自己感觉和性情处事。正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所言:“我想我应当做的是去生活。我欢喜的就是好的。我要的就去拿来,不要的我就即刻放下。”与人交往和选择爱情都是秉承自然本性,厌弃虚伪、造作的公式化生活和公式化爱情。因此,萝最终选择认识才三四天的单纯、粗鲁和直率的宗泽。如蕤则厌烦那些因爱她而使自己丧失人的尊严,变成一只狗的男人,因而再次选择离去。总之,这些少女或者清纯如水,貌美如花,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首诗,一幅画,一道转瞬即逝的彩虹;或者艳丽狂放,勇迈直率,充满青春活力和不羁野性,本身就是一片云,一团火,一阵席卷而去的狂风。她们个个本真纯朴、率性自然,是沈从文“某种受压抑的梦”的艺术呈现,一切都充满了善,充满了美,充满着“完美高尚的希望”。
另一类是良善的妇人,如《逃的前一天》中的磨坊妇人、《一个妇人的日记》中的妇人、《一个母亲》中的母亲、《或人的太太》中的太太、《船上岸上》中的卖梨子妇人及《菜园》中的母亲等。这类女性心地善良,具有慈悲心肠和赤子情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良善和仁慈的一面。在沈从文看来,人之初,性本善。未受现代文明、道德习俗等侵染之前,人的自然本性是良善、美好和仁慈的,因此,他在作品中不停地抒写和赞美这种初心。《逃的前一天》中磨坊妇人,虽然年纪大了,但心地善良、纯朴,对年轻人充满同情和怜恤,给准备当晚逃走的“他”以无限的温暖和关爱,这是“一种说不分明的慈爱,一种纯母性的无希望的关心”。《船上岸上》中的卖梨子老妇人也是如此,四十钱一堆的梨子,太便宜了,“我们”多给了她一点钱,她不肯白要,又多添给“我们”几个梨子。妇人不肯多收钱的诚实、纯朴、善良和好心肠,感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全像我伯妈”,给人无限温暖和爱意。即便是《一个母亲》和《或人的太太》中因陷入婚外情而愧对丈夫的妻子们,也是心地善良、纯朴和温柔,她们痛苦、悔恨,害怕丈夫受到伤害、陷入痛苦不幸中而痛苦。如果说作者对前面那些有仁慈情怀和菩萨心肠的老妇人充满了敬意和感激;那么对这些陷入痛苦缠绕情感中的妻子们,作者也是充满理解和同情。在《一个母亲》中,他借叙述者之口道出:“一个平常的女子,常常陷到矛盾的自谴中,又常常为一些无益于生存的小事难受。她也是这样的女子。……世界上女子全是这样。她也没有特别使人可以称赞的地方,因为她对付事情并不与其他女子两样。”[14]298作者善良、仁慈和厚道的品格于此显露无遗。
还有一类是赤诚的妓女,如《丈夫》中的老七、《都市一妇人》中的妇人、《边城》中的妓女、《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中的女人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妇人等。这些女性,虽然靠出卖身体生活,花里胡哨地装扮自己,穿假洋绸衣服和印花标布裤子,把眉毛扯成一条细线,并且在发髻上涂抹香味浓俗的油类(《边城》)。但天性纯朴,自由坦率,热烈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13]13《第一次作了男人的那个人》中的妓女也不肯多收男人的钱,面对男人的泪水不知该如何表达的她动了真情,不仅认真做好娼者的义务,而且竟说出“我愿意嫁你”,“我爱你,我愿意做你的牛马,只要你答应一句话!”这种不顾一切、率直任性、赤诚热烈对待情感的态度,无不彰显她们身上未曾失却的“纯真”和“童心”,尽管这些只会给她们带来磨难与不幸。
总之,这些女性纯真善良、热情真挚和果敢勇迈,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和良善,都源自于作者的审美理想和生命体验,是作者“近乎荒唐的理想”和“希望之歌”。1934年冬天,作者回到家乡凤凰县,发现一切都不同了,什么都已改变或者正在发生改变。过去农村社会的那种纯朴、善良、热情和诚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几近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唯实利的庸俗势利的人生观和人际关系。尽管如此,他依然希望古老民族的热情、正直和勇敢等美德能够保留在年轻人的血液和梦中。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那些天真纯洁、善良诚挚的边城儿女身上,寄托在《边城》中翠翠身上,寄托在《长河》中三三身上,也寄托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水手和妇人身上,等等。因为正如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指出,这些边城儿女身上保有的那种纯朴、善良、热情和诚挚的爱里依然还“闪耀着一种悠久的民族品德的光。”[12]30换句话说,这些女性的纯真善良、热情真挚和果敢勇迈,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作者希望它们“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15]18同时,这些情绪、情感或者单纯素朴或者复杂纠缠的自然状态,既是本真纯粹人性的自在呈现,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复杂情感意欲的艺术呈现。正如作者在《一个母亲》中借隐含叙述者口吻对那位出轨妻子的评论:“她哭,她笑,她做一些看来似乎够荒唐的梦就吃惊,但当到把自己置身到那荒唐情境中时,又很感动地几乎还天真地扮演了那一角。她是没有可疵议的,因为世界上女子全是这样。”[14]298可见,作者使人陷入痛苦、矛盾与纠结的情爱状态为人性的自然状态中。关于这点,有论者指出: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文学小庙里供奉的“人性”实则是以其念慈在慈的“爱欲”作为根底的,“所谓‘爱’在很大程度上又都集中于人类在‘爱欲’上的矛盾、纠结与挣扎,这在沈从文心目中乃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而沈从文所说的他的文章是一种“情绪的体操”中的“情绪”,很大程度上也是指人的“情欲”或谓“爱欲”。[9]因为沈从文本身就认为文学艺术是使人的情欲或爱欲上的烦恼、哀乐、痛苦和纠结等情感和情绪得以变形发抒和宣泄的体操。再则,沈从文在现实中确实遭遇过一段复杂、纠结的情感问题,即他在与张兆和订婚后至结婚前的那段时间里,与高青子等女性的情感纠葛,为此曾写信求助于林徽因。不过,后来经过痛苦的挣扎、思虑和权衡,最终还是与张兆和结婚。作者自身这段复杂情感经历,自然会移到纸上,正如他在《水云》中谈到《边城》时所言:“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16]111因此,这些纯真、善良和热情的女性形象不仅承载了作者的理想和希望,而且也是其独特的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艺术呈现。
二 、“纯真”美者的神采意蕴
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指出:沈从文创作的哲学思想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7]456换句话说,沈从文创作是试图将湘西边民身上的勇敢、热情、正直及善良等原始美德注入高度文明的、老态龙钟的中华民族身上去,刺激他,好激活他的生命活力。苏雪林的这一观点深得沈氏创作的思想精髓,也与李贽的《童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李贽认为:童心就是真心、初心,是人刚一出生就拥有的原初心态、心情和心绪。这是人的最真实、最自然和最本原状态,即所谓赤子之心。可惜,后来随着“闻见”日多日广,功名利欲之心渐起,童心便慢慢失却。“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以至“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0]409李贽“童心说”表达和强调的显然也是对人的自然人性的尊重和重视,特别是强调对人们习染已久的文化观念和道德习俗的冲击和反叛,释放出被压抑和被禁锢的人性。因此,沈从文笔下的这些纯真、善良和热情的女性形象凸显和实现了其创作哲学思想,展现了作者以善良、美好人性重铸民族美德的创作意图,也是沈从文本人善良、仁慈和厚道品性的真挚外现。
首先,这些涤荡了社会文明观念的“纯真”美者——女性形象的铸塑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人性的讴歌与赞美。作者曾说他的文学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里的“人性”其实就是前述的包括“爱欲”在内的自然人性。这在上述三类女性形象身上得到了充分呈现。如果撇开历来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所做的城/乡、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划分,那么这三类女性形象实际上代表和体现了人的自然生命成长的三个不同阶段:“纯真的少女”体现的是人的天真活泼、懵懂清纯的少年时代;“赤诚的妓女”体现的是人的热情狂野、自由任性和生命力勃发的青年时期;而“良善的妇人”体现的是善良温柔、仁慈厚道的生命沉静的中老年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是一种权宜之策,而非绝对。事实上,三类形象之间有交合之处。如第一类女性形象中的如蕤和萝可以划归第二个生命阶段;而第二类形象中的年轻妻子等也可划归第二个生命阶段等。每个生命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清纯、天真”,第二阶段是“热情、赤诚”,第三个阶段是“善良、仁慈”等,它们与各自所处的生命阶段的个体生命本真相吻合,符合了生命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里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等的自然表征。《边城》里翠翠这个在大自然风雨里长大的小女孩,她的爱情很清纯、质朴。正如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所言:它是“那样的纯粹,那样不俗,那样像空气里小花、情操的香气,像风送来的小溪流水的声音,若有若无,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那样的真”。[12]48这是一种典型的刚进入情窦初开少女时期的朦胧诗意爱情。而《如蕤》中的蕤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容貌漂亮而又聪明睿智,引得无数男人追逐和爱恋,但她们依循自然心性生活、行事及处理感情,不为那些虚伪、浮华和肤浅的情感所困,始终坚持不为某个人所独占原则而任性恣情生活,但一旦遇到单纯、真诚和可靠稳重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托付终身。这些女性对待情感的态度和方式具有鲜明的青春期特征,显示了生命的自由、勃发和任性恣情状态。《逃的前一天》中的磨坊老妇人,善良、热情,她不知道他当晚就要逃走,热情地向他介绍她的那些可爱的小鸡,还说要把大的留给他。“一种说不分明的慈爱,一种纯母性的无希望的关心,都使他说不出话”,只能对着她笑。老妇人身上自然发散出的涤荡社会文明观念、返璞归真的神性温柔、慈爱和善良,不仅感动了“他”,也照亮了作者和读者。可见,纯真、质朴、热情和真诚等体现人性自由、本真的品德和质素,贯穿了前后三个阶段。正是它们点燃了作者的梦想和民族的希望,也寄托着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
其次,作者喜欢把女性形象置于自然界的动植物中描写,或者以动植物来比拟这些女性形象,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自然万物和谐交融的生态观念,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这些女性形象身上的动植物性,即自然人性。沈从文早年北漂时,在北京各高校旁听,听过周作人的课,也读过他不少著作,因此,他的人性论观念不可避免受到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影响,认为人性包含兽性和神性,是两者的结合。这样一来,作为体现其创作哲学思想的女性形象自然也会具有动植物性(或者说兽性),且与自然万物交融一体。《三三》中描写道:“这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树林里,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因为一个人在屋里玩厌了,就出来坐在废石槽上洒米头子给鸡吃;在这时,什么鸡逞强欺侮了另一只鸡,三三就得赶逐那横蛮无理的鸡,直等到妈妈在屋后听到声音,代为讨情才止。”[13]209-210三三与青藤、葵花、枣树及鸡们交融一体,是和谐自然画面一分子,其天真、活泼、童稚的形象在这幅自然风景画中悠然自现。特别是,自然界动植物勃发旺盛的生命力也会唤醒和催生女性身上的原始生命力,激发她们的野性活力。《采蕨》中,在那“桃花李花开得如此好,鸟之类叫得如此浓,太阳如此暖和,地下的青草如此软”[18]254及五明如此大胆撒野情形下,阿黑虽装成生气样子,心却“跳得不寻常”且“感到受用”,也就任由五明在她身上撒野。可见,美好的天气和花草催发了阿黑身上的原始生命力,使之同大自然的花香鸟语交融一体。此外,作者还以拟物化手法,把女性比拟为动物。如《边城》中的翠翠天真活泼,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乖顺、温柔,如山头一只黄麂。《看虹录》中的女主人像一只母鹿,她自己也自命为猫,一只好看而不喜动弹的暹罗猫。《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夭夭“是个美丽得很的生物”。《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会长女儿“真是一个标致的动物!……一朵好花”。这些拟物化描写不仅写出了女性的美丽、娇媚、温顺,如流水般的柔美特质;也写出了她们纯朴、童稚、原始的动物性特征,彰显了这些源自作者“童心”铸就的“纯真”美者的至朴与至美。
此外,这些纯真、善良和热情的女性形象还体现了作者本人生性的纯朴、善良和厚道。张充和在沈从文墓碑上刻写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敬诔,是对沈从文一生的中肯评价,也是知己之论。沈从文是一位热情、善良、纯朴和厚道的谦谦君子。据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回忆,吴祖光有一次跟他说:“你们老师不但文章写得好,为人也是那样好。”[12]14凌宇也说:沈从文“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19]5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自己也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以看出。”[20]1因此,沈从文这些善良、天真、纯朴和温爱自然会倾注到笔下女性形象身上,从而铸塑如许纯真美者的优美形象。关于这点,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也曾说道:“沈先生用手中一支笔写了一生,也用这支笔写了他自己。他本人就像一个作品,一篇他自己所写的作品那样的作品。”[12]25其人如文,更文如其人,沈从文的文章和女性形象正是他本人人格和性情的一种外现。可以说,正是沈从文的这些善良、纯朴、天真的人格和性情,成就了他那些满溢诗意和悲悯的作品;也正是沈从文的赤子情怀和菩萨心肠,铸塑了这些观音菩萨似的纯美女性形象。沈从文在1934年1月16日曾对张兆和说:“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湘行书简》)也自然而然会铸塑出纯真、善良和充满慈悲情怀的女性形象,以之存留一些已成陈迹的悠久古老民族的品德之光,便于在“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长河·题记》)从而引导读者从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引起……对人生向上的憧憬”。(《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21]45实现作者创作的理想和希望。总之,这些纯真的女性形象既承载着作者的理想之梦,寄寓着作者独特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也是作者自身的人格和性情的艺术呈现。
三、“纯真”美者背后的女性观念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如果一定要说有目的,那就是以“很单纯地说出自己的感觉”为目的。[22]14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受到过周作人影响,某种程度上,沈从文创作也是以说出自己对人、对生活的美、善感受为目的。而他又是一位对人、对生活充满热情和爱悦的人,在《湘行散记》中,他对张兆和说:“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23]23乡下人的固执和燃烧着的感情使他坚持在作品中诉说着真善美的感受,在文学园地里执着地建造一座小庙,供奉人性。或许它不如“五四”时期主流文学——启蒙文学那么深刻,那么振聋发聩,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文学审美范式,一曲人性美和善的颂歌。而这些“纯真”美者——女性形象正是作者别样的文学审美思想的形象载体,她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正如苏雪林谈到沈从文作品带来的别样审美感受时所言:那些“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好像在沙漠炎日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17]453同样地,这些女性形象除了能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16]66
但应当看到,这些发散着人性美的光泽的纯真女性形象与当时现实女性的生存境遇还是有距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更多是承载作者审美理想和人性理念的载体和工具,而不是为了反映当时社会女性生活和生存的真实状况。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复杂,战乱频繁,人们生活贫困,尤其是乡村社会,沉重的阶级压迫和连年的战乱更是导致许多家庭破产,百姓流离失所。20世纪30年代初期涌现的社会剖析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生活、命运肯定不会像沈从文笔下女性这样充满质朴的诗意和人性美的光泽。只要联系罗淑的《生人妻》、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吴组缃的《樊家铺》及萧红的《王阿嫂的死》《生死场》等作品中女性的不幸生活和悲惨命运便可以看出,沈从文是如何艺术化和审美化其笔下女性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如同样是叙写女性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的作品,沈从文的《丈夫》几乎清除了女性在这一屈辱事件中的心理活动,女性似乎不以卖身为苦,倒乐于以此为业,“用一个妇人的好处,热忱而切实地服侍男子过夜”,只是因为丈夫不堪忍受最终被带回家以示反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则从人伦情感的被蹂躏角度写出了“典妻”事件带给女性的痛苦和悲剧,女性内在情感的悲痛和煎熬、精神生活的困苦和悲惨在作品平易质朴的叙述中得以醒目凸显。后者的社会批判控诉力量显然胜过前者。又如,同样是写演艺圈女性生活的作品,沈从文的《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主要写萝沉浸于演艺生活,如鱼得水,在男人们间逞强任性,恣情生活,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是对女性的物化和消费。相反,丁玲的《梦珂》则叙写梦珂看不惯某些演员的轻浮狎昵举动,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赏”,后来是走投无路才被迫屈就这种“纯肉感的社会生活”,这显然具有揭批社会的作用。当然,沈从文创作及塑造女性形象本来属意不在此,而在于对纯朴、热情和善良的人性美的讴歌及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展现。[24]231确实,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注目社会历史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的是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声称自己创作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就决定其创作不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因此,用传统的道德意识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纯朴美好的人性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主题[25]221-222,而这也决定了他对笔下女性形象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倾向。
同时,这些纯真女性形象型铸忽略了对女性主体内在的复杂情感和意欲的发掘与表达。如前所言,作者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主要凸显她们纯朴、诚挚和善良等美好品性,因此,这些形象与其说是具有复杂丰富和深刻多样的人性内涵的圆形形象,不如说是具有纯真、善良、诚挚等美好人性的类型化形象。虽然《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的萝、《如蕤》中的蕤、《薄寒》中的“她”及《一个母亲》中的母亲等女性形象似乎也展现了女性内在复杂的情感和意欲,但事实上,她们仍服务于展现作者人性理念中的人性的纯朴率性和生命力的狂野不羁,也即为了展现“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换句话说,人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多面体,而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她们内心的思想、情感和意欲应当更为复杂丰富和矛盾纠结,但沈从文笔下的这些女性身上显然缺失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只要比较她们与几乎同时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女人的心》和《象牙戒指》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便不难发现,丁玲和庐隐笔下的女性大都陷入了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等复杂矛盾的冲突中痛苦与纠结,也正是在这些矛盾纠结中,女性作为主体的内在情感和意欲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得以鲜明呈现。如同样是写妓女题材的沈从文的《丈夫》与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丈夫》主要从丈夫视角、感受来叙述故事,老七迫于生计到城里为妓,“做了生意,慢慢地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在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14]36-37最后,她在丈夫自我意识的觉醒下被带回家。作者从自然纯朴的人性观出发虚构了一个女子的堕落和获救过程,却几乎没有触及老七的所思所想及她的内心感受,有的仅是“她为人性的堕落提供了一种表征——她是春河上一个文明的奇观;她为丈夫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种中介——她是人性受到戕害场面中的一份刺激;她为人性的复归提供了一种标记——她是自然人性获胜的一次奇迹”。[26]相反,《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则采用妓女阿英的视角来叙述,从而敞开了她内在的感受和意欲:她对嫁人生活与妓院生活的权衡,她对不同男人的打量和比较,以及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妓院且享受这种生活的心理状态等。在这里,重要和值得注意的,不是阿英最终主动选择做妓女这一风尘生活方式的行为,而是她这一主动选择行为背后所体现出的女性对于自我内心欲望的正视和确认,也正是在这种敢于正视和肯定自我欲望的行为和意识中,女性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得以鲜明呈现。可见,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仅是体现其理想人性观和审美观的载体,因而难免不被理想化和符号化,缺失作为主体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
有论者指出:沈从文的女性观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是复杂而矛盾的。作者一方面具有“女性崇拜意识”,另一方面又对女性存在轻视和偏见;一方面从生命的审美高度艺术化地描写女性美,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男性视角来鉴赏女性;一方面是一个女性“善美”论者,另一方面又视女性为尤物。因此他虽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女性的爱和美,却无法逃避其男性价值和审美观。[27]事实上,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看似矛盾的女性观其实统一于作者对纯朴、自然和诚挚的人性的讴歌与赞美。换言之,沈从文之所以对女性充满崇拜、欣赏或者把她们当作善美的化身来书写,其实正是因为这些纯真和善美的女性形象很好地传达了其“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人性理念和讴歌人性美、人情美的审美理想。而其作品所流露出的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及视女性为尤物的意识,又无意中泄露了作者潜意识深处的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念。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曾明确地指出:“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28]192沈从文虽然是一位温和、谦恭,充满人性关怀的作家,但他自身毕竟是男性,其与生俱来的性别本能及几千年男权文化的侵染和熏陶等,不可避免地会给其创作及女性形象塑造打印上性别文化的印记。因此,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没有逃脱历来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念施加于女性身上的“天使”或“恶魔”的文化预设。这些纯真的女性形象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作者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纯真女性形象的善良、热情和纯朴背后还隐匿着一层淡淡的现代隐忧和宿命哀伤,即如沈从文在《水云》中陈述《边城》创作意图时所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16]111这种隐忧和哀伤的形成既有民族历史文化自身的复杂原因,又有不可知命运和偶然宿命的因素,它们为这些“纯真”女性形象的性格和命运增添了神秘色彩。遗憾的是,在后来孙犁、汪曾祺等人笔下的同类女性形象塑造中则几近失传,这既是时代社会更替造成的,也是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结果。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需留待后续研究。
[1]何宇宏.沈从文小说的女性言说空间[J].求索,2007,(7).
[2]向亿平.沈从文男权意识下的女性观[J].三峡论坛,2011,(6).
[3]孙丽玲.论沈从文的女性观[J].求索,2002,(2).
[4]魏家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5]刘丽宁.生命的美丽与哀愁——沈从文小说生命意义初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6]津守阳.沈从文女性形象中蕴藏的“乡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2).
[7]周军.论沈从文笔下女性悲剧成因[J].小说评论,2014,(2).
[8]袁淑俊.试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水与女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9).
[9]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
[10]李贽.童心说[A].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3)[Z].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2]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13]沈从文.边城及其他[Z].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14]沈从文.八骏图[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5]沈从文.题记[A].长河[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Z].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17]苏雪林.沈从文论[A].苏雪林选集[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4)[Z].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19]凌宇.沈从文传[Z].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4.
[20]沈从文.题记[A].边城及其他[Z].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2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Z].长沙: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2]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3]沈从文.湘行散记[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6]唐利群.一扇不好打开的门——《丈夫》与《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对读[J].名作欣赏,2003,(6).
[27]丽玲.论沈从文的女性观[J].求索,2002,(2).
[2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杨 春
Female Images in Shen Congwen’s Works:‘The Beauty of Innocence’Moulded by‘Childlike Innocence’
CHENJiaohua
Shen Congwen has created three types of pure female images which are the pure girls,the sincere prostitutes and the good women with love and pure feelings.They not only carry the writer’s ideal dream,express his unique feeling and life experiences,but also present artistically his own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A kind of simple and pure human nature beauty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emale images bring readers a different kind of aesthetic feeling.But there is a certain distance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artistic images,which carry the author’s aesthetic ideal and human nature and reveal the deep-rooted subconscious male-centered cultural values.
childlike innocence;pure;female images;female views
10.13277/j.cnki.jcwu.2017.03.012
:2017-02-05
I206
:A
:1007-3698(2017)03-0077-08
陈娇华,女,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21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