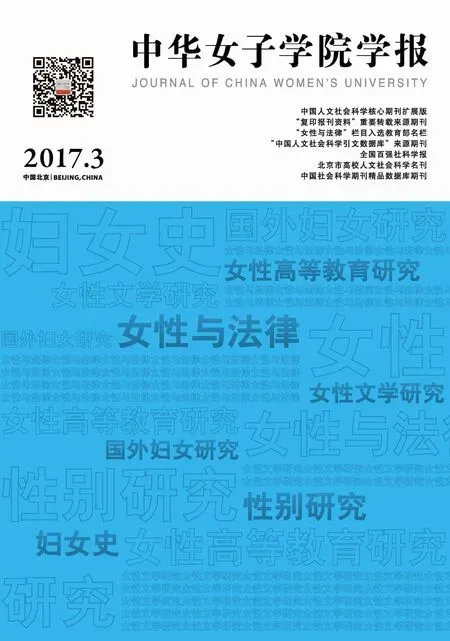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基于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思考
2017-01-28谢秋慧罗树杰
谢秋慧 罗树杰
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基于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思考
谢秋慧 罗树杰
通过深入调查仫佬族聚居村落,在获得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性别作为研究视角,梳理出仫佬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入赘婚”、“嫁娶婚”、“两头走”的婚姻形式。同时探究不同婚姻形式下仫佬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话语权等,展现当下仫佬族两性的性别建构,预测出两性和谐平等观念的植入以及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更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
仫佬族;婚姻形式;社会性别
婚姻既是个人行为,又是社会设置。婚姻涉及多面性,婚姻赋予结婚者的居住形式、地位、角色、性别分工、权利、义务等,无不体现了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规范。婚姻形式的不同,妇女的社会地位获得也不尽相同。研究婚姻形式的变迁,对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仫佬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广西境内的仫佬族绝大多数居住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统计局《2014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记录,该县仫佬族人口126845人,分布在四把、东门、小长安、黄金等11个乡镇。广西其余仫佬族散居于宜州、柳城、柳江、忻城、都安等地。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研究仫佬族的学者,他们对仫佬族族称与族源、人口、风俗节庆、岁时礼仪、民歌、民居建筑、儿童教育等内容进行研究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以仫佬族妇女为对象的研究却相对薄弱。1949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一夫一妻婚姻制、男女同工同酬、计划生育政策等从不同领域坚持了保护妇女的基本原则。虽然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没有经历西方为争取妇女劳动权、受教育权、政治权、选举权等而进行的三次革命浪潮,但我国的女性主义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还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
仫佬族婚姻经历了入赘婚、嫁娶婚和“两头走”的婚姻形式变迁,妇女在不同婚姻形式下获得了不同的婚姻自主权、决定权以及社会赋予的“第二性”。
鉴于此,本文以社会性别作为研究视角,对不同婚姻形式下仫佬族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平等权利获得进行探究。通过探究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下不同婚姻形态中仫佬族妇女社会性别的获得,旨在与同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主流理论进行对话,展现当下仫佬族妇女社会角色与社会权利的获取情况,从而为国家了解仫佬族以及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提供参考。
一、仫佬族婚姻形式的变迁
(一)早期的“入赘式”
历史上,仫佬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母系社会。在1956年确定仫佬族族称前,有学者调查发现:“先祖来时,讲的是汉话、官话。因娶当地讲仫佬语的土人(一说苗人或侗人)为妻,所生子女,一切风习言语从母不从父。”[1]5可以推测,在较早时期,仫佬族家庭经历过赘婿时代,赘婿遗俗在当今仫佬族社会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他族入赘婚,一说男子家贫不能娶妻,身入妇家作质,地位低下,无独立人格;二说实则男尊女卑宗法制度的附属,整个社会男权至上。此说法是建立在多子贫家或有女无子之家才成立,如大元《通制条格》规定:“止有一子不许出赘,若贫家止有一子,立年限出舍者听。”[2]仫佬族赘婿如行走江湖之士,或逃难,或经商,或迁移。“今罗城东门镇中石村大银屯银氏四冬、五冬族谱序称:银姓系穆柯公之苗裔,原籍乃宋金人氏,生居帝胄。时因叛乱(即成吉思汗伐金),迁居河南开封府无锡县。恐被驱而戮之,遂去金而银姓。”[3]10罗姓仫佬族“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朝代,罗姓子孙均有出仕。适元朝中期,罗玉公由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桥头镇镇众桥迁至广西柳州府罗城县”。[3]9
由于仫佬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因而考察早期入赘婚的经济效力和法律效力,没有相关民族文献史料可作为参考。但从多个族谱记载或口口相传的传说发现,仫佬先祖独自与地方女子成婚,婚后从妻居,生子大多从父姓,生活习惯遵从妻方,而后与夫家无太多往来。由此说明,仫佬族入赘婚在形式上是男嫁女娶,夫从妻居。仫佬族入赘婚的婚姻形式是以妇女家庭为中心,一切生产、生活以女方为本位。从族际交流而获得的社会效应看,妇女是主导地位,赘婿相应也获得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仫佬族赘婿不一定是多子家贫的情况,有关赘婿地位低下、不受尊重的结论并不成立。赘婿不仅不改随妻姓,而且赘婿婚后所生子女大多从父姓,赘婿所生子女继承妻子的那一份财产,这说明该时期仫佬族父系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不十分强烈。
在以入赘婚为主的仫佬族发展史上,仫佬族还有传统的青年男女社交“走坡”习俗。不过这一习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淡化。“走坡节”那天,“青年男女穿上节日的盛服,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坡场来,等待着与意中人相见。......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撑着花伞,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站立在山坡绿荫间的青年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并没有沉浸在欢乐的人海里,而是哼着悦耳的山歌,与自己的知音互相传情”。[4]103通过走坡唱歌传情及相互了解,仫佬族青年男女自由选择意中人,女子有选择婚恋对象的绝对权力,父母不强加干涉。
仫佬族女子婚后有“不落夫家”①“不落夫家”指已出嫁的女子,除节日喜庆丈夫专程接至夫家外,婚后生育以前不能住在夫家。女子要在娘家生活直至有了身孕,才去夫家长久居住。的习俗,以及生育后“做外婆”的习俗。“做外婆”是指仫佬族妇女在女儿出嫁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把去女儿家当作一个喜事。她们会准备丰厚的礼品,包括背带、花帽、五彩刺绣、布料、玩具、粽粑等。“外婆的地位在人们的心中仍然相当重要。它反映了仫佬族人民传统的心理状况,也反映了‘从母不从父’的母系社会的历史痕迹。”[4]135这表明仫佬族妇女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二)从“嫁娶式”到“两头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男女平等,并在制度、法律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予以保障,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以及社会文化的推进,仫佬族婚姻形式适时而变。笔者通过对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凤梧屯、田心屯、德音屯、四把镇大梧屯的妇女进行调研采访,发现仫佬族婚姻形式经历了由入赘婚到嫁娶婚,再到“两头走”的形式变迁。仫佬族通婚范围扩大,“剩男”、妇女离婚、妇女再婚等比例上升,这些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赋予了妇女权利新的内容。
通过对40—60岁仫佬族妇女婚姻形式的调查,发现该年龄段的妇女通婚范围主要限于罗城境内。这一时期的仫佬族通婚圈主要以本村寨为中心,辐射到附近其他村寨和乡镇,离村寨越远,通婚则越少。该时期仫佬族妇女的社会交往主要是依附家庭关系,“结婚并不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是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5]129-132仫佬族妇女受到乡土社会的地域限制,在婚姻观念的形成上主要是传统家庭的耳濡目染或父母的口口传教。选择勤劳、肯干、忠厚等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对象成为婚姻标准。调研还发现,40—60岁的仫佬族妇女虽然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但也招婿上门或嫁在本村,在问及“有兄弟为什么不外嫁”时,她们回答最多的就是“家里劳动力少,在家①指招婿上门。养家”。
1949年以来,我国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政策,生产方式由家庭为单位转为集体劳动模式。而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妇女由“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务分工模式变成“同主内外”,妇女获得了更大自由度的劳动权、经济权,由此带来了观念的转变。“我有自己的钱”、“我赚的不比他少”、“有无男人没差别”等成为妇女们说得频率比较多的话。此外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仫佬族人口增长的幅度大大降低,少子对家庭的影响就是“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外嫁”,因此这一时期“两头走”成为主流,仫佬族男子的“娶妻进”和仫佬族女子的“入赘婿”比例大大下降。仫佬族妇女在嫁出去或招赘婿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选择权。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妇女来说,家里经济条件较好、所在村寨交通较发达的女子大多选择了入赘婚形式;而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偏远村寨的仫佬族妇女选择了嫁出。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妇女由于受到外来婚育观念和性别观念的影响,为照顾双方家长的感受,开始选择新型的“两头走”婚姻形式。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进性别文化,仫佬族妇女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家庭条件不再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标准,而是更注重个人素质。仫佬族妇女偏向于选择性格开朗、阳光活泼、社交能力强、有一技之长的对象,而一些勤劳却老实、不善言谈的男人就比较难娶妻。由于仫佬族妇女的择偶及婚姻形式都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因此父母对子女恋爱婚姻的干涉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夫妻感情成为维系婚姻家庭的重要纽带,妇女可以说完全享有自由择偶权和婚姻自主权。这一时期,妇女初婚年龄表现出降低的趋势,由于感情的变动导致的离婚率上升,妇女再婚的比例也有上升。仫佬族妇女希望通过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表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获得家庭地位;而由于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也给身为女性的她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价值效应。采访中,她们多表达出“这个社会男多女少”、“只要是个女的就不怕没人要”、“离婚有什么,很多离婚的照样再嫁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等观点。
这一时期的妇女个性越来越明显,而妇女的话语权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有明显不同,二元结构表现出了差异性。然而,差异并非对立,差异激发了两性生理性别(Sex)。所以在生理差异基础上,应充分发挥社会性别(Gender)的能动性,从而使两性在家庭中的分工需求、两性关系的期待上趋于平等。
二、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社会性别建构
(一)“差异”中的“平等”
早期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6]309“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6]309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这一观点为认识、思考女性角色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性”指区别于男女两性的生物学特征,是由后天的社会制度、社会习惯等影响而造成的特定的女性特征,意指女性被男权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心理等要素影响、束缚、制约而建构出来的女性角色和表现出来的女性气质,表现为社会地位相比男性更为低下,不受重视或尊重。20世纪60年代,在波伏娃“第二性”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出现。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两性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衍生的,而是长期以来的男权思想和父权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而我们研究的仫佬族社会及家庭由于其特有的文化源流,并不存在两性针锋相对的时期,相反还拥有开放、不保守的文化特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仫佬族妇女一直享有特权,能招婿上门,也可嫁人不顺再回门,现在还可“两头走”,这些是与其掌握一定的家庭和社会资源分不开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要想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最为关键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赋权。唯有如此,才能打破男性中心文化,使女性获得话语权。仫佬族妇女在自由婚恋的基础上,通过自我实现的经济价值而掌握了一定的家庭权利。加之,由于男多女少的性别比失衡带来的性别资源优势使得仫佬族妇女获得了在家庭中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21世纪20年代后,仫佬族妇女的婚姻形式将进入“两头走”的高峰期。新的时期正在促成新的性别观念的形成。妇女在婚姻里的性别角色期待也相应调整,经济独立能力更强、自我意识更觉醒、家庭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要求更明显等,这些也均将成为仫佬族新型婚姻形式中妇女社会性别的再建构特性。由于妇女不断的自我提高,其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同时共存共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与建构和谐家庭。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家庭问题如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赡养老人模式的变化、家庭规模扩大等将会伴随产生,仫佬族家庭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夫妻婚姻感情的维系方式、处理家庭矛盾的技巧、普及性别平等观念已经成为仫佬族家庭极度关注并渴求获得的知识领域。为促进两性和谐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要突破宣传口号阶段,以专家下乡辅导和开展培训会等形式,或通过现代科技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推出家庭和谐相处常识等,解决家庭现实问题,切实为两性情感、性别和谐、家庭和睦提供建议,从而实现新时期两性家庭的和谐,开启仫佬族两性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二)“合作促和谐”的建构路径
仫佬族的婚姻形式从来都不是在“闭关”的状态下完成变迁的,而是在不断与中原汉族、周围壮族、苗族、侗族、毛南族等民族产生文化冲突、融合,加之在各种社会浪潮的冲击下,表现出新的婚姻形式和特征。仫佬族婚姻形式内涵保持着传统的包容性特征,但同时赋予了对两性社会性别期待的新内容。纵观整个中国社会,新时期社会性别建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而在婚姻形式中,两性的对立与联系显得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性别特征并没有被任何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们注意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妇女地位和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将妇女问题浓缩到她们的工作能力上,而对于家庭的讨论则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李银河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提到:“妇女被赋予了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家庭像妇女自身一样,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文化的产物。”[7]2西方女权主义者把妇女和家庭视为独立存在的两个体系,毫无相干。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赞同男性权力无处不在,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作政治领域来看待,试图为家长制权力找到一个历史的位置,以此去理解它与其他统治形式的关系。性别文化规范固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这些观点和理论并不能指导仫佬族婚姻形式下的社会性别建构。新时期仫佬族性别文化如何规范、社会性别如何建构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较小私人领域婚姻形式的选择上,西方女性主义从来没有一个严密的理论思想体系对其进行指导。它指向的只是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性别获得,以及追求男女平等的宗旨。在仫佬族婚姻形式中,妇女有权选择婚后居住模式。可以说,“两头走”是仫佬族两性在婚姻形式中权衡社会性别的体现。同时也要认识到,“两头走”未必是性别建构达到和谐的表现。只有出现一种超越两性社会性别期待的“不娶不嫁”的自然婚姻形式,两性关系才会达到平等。正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要尊重两性生理差异,允许表达女性生理上的特殊性,解构私人领域(婚姻家庭中)的性别等级,以实现“差异中的平等”,从而实现男女性别平等。不论是何种婚姻形式,仫佬族社会性别的构建都应以此为目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深化两性平等和谐,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
当前,仫佬族婚姻形式下的社会性别建构主张要吸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在建构性别文化上更要注重男性的参与、合作,以合作促和谐。新的婚姻形式走向赋予其性别平等的内容,包括在六礼中削弱以经济形式表达的礼节以及聘礼与回礼的对等;亲属称谓不因不同婚姻形式而变化①,等等。民间的传统是分散的,却有自己的脉络,正如仫佬族婚姻形式的变迁是其吸收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自觉应对的结果。这对于仫佬族两性社会性别的建构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这种民间自觉行为需要国家在充分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对社会性别的建构上实现政府主导,实现制度革新,例如对一些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或陋习以村规民约进行规范;同时需要少数民族自觉提升性别观念,继续保持传统文化中包容性、平等性等先进性别观念,以此来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关注和参与,促进社会性别更加和谐。
三、结语:一种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
仫佬族这一个案呈现出在无国家力量引导和推动作用下婚姻形式变迁的性别观念重构,说明了婚姻形式的变迁是如何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建构,并作用于新观念的再生产。具体来说,通过对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看到仫佬族婚姻形式变迁中男女两性权利的斗争、交织、“中和”,女性的任何一种婚姻选择都是社会化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是女性自身话语权和社会赋予其话语权的博弈。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地发起宣传男女平等的运动,但一直在探索男女平等的路径,也曾建立起一套宣传机制,服务于社会主义性别建构的整体,以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使男女两性在婚姻形式中享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以促进家庭和谐稳固发展。即便如此,客观上讲,国家实行干预或推行的政策,并不是畅通无阻的,来自个体的观念接受以及不同社会体系思潮的冲击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推行的阻碍。更有甚者,“男女平等的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公共的政治理想,它更触及变革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空间和相处方式,而性别观念的展现恰恰属于日常化的生活实践领域。”[8]40如何在家庭内部构建去性别化的平等观念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它的实现不仅会通过文化传播和渗透的力量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进行斗争,而且会在博弈的过程中实现性别平等观念的再更新、再改造。一种全新的去“性别化”社会主义性别建构也应当根植于家庭中,并且发芽、开花和结果。
[1]《仫佬族简史》编写组.仫佬族简史[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
[2]郭成伟.大元通制条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肖永孜,陈洁莲,等.中国仫佬族人口[Z].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4]李干芬,胡希琼.仫佬族[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7]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
[8]郭燕平.农村性别观念的现代性改造——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流动放映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6,(6).
责任编辑:张艳玲
①仫佬族不同婚姻形式下有相对应的亲属称谓体系。对于“两头走”这种婚姻形式,一些称谓如“外祖父母”、“舅舅”、“姨妈”等不存在,两边都被认为是主体家庭。
Socialist Gender Construc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Sex:Reflection Based on Change of Marriage Forms of Mulam
XIE Qiuhui,LUOShujie
This paper uses gender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gender role and the voices of Mulam minoritywomen in different forms ofmarriage,showingthe gender construction ofMulamethnic group.It predicts that the implantation of gender harmony concept and the socialist gender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the harmonious healthy development ofgender relations.This not onlyenriches the theories on the gender research in China,but alsoprovides a case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Mulamand formulatingcorrespondingnational policy.
Mulamethnic group;forms ofmarriage;gender
10.13277/j.cnki.jcwu.2017.03.007
:2017-03-15
C913.68
:A
:1007-3698(2017)03-0047-05
谢秋慧,女,仫佬族,河池学院政治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仫佬族两性文化。546300;罗树杰,男,壮族,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530004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罗城仫佬族人口均衡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5CSH001)、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罗城仫佬族留守人口社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KY2016LX270)、2015年广西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困境与出路:仫佬族人口‘流’与‘留’的博弈”(项目批准号:GXRKJSY2005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