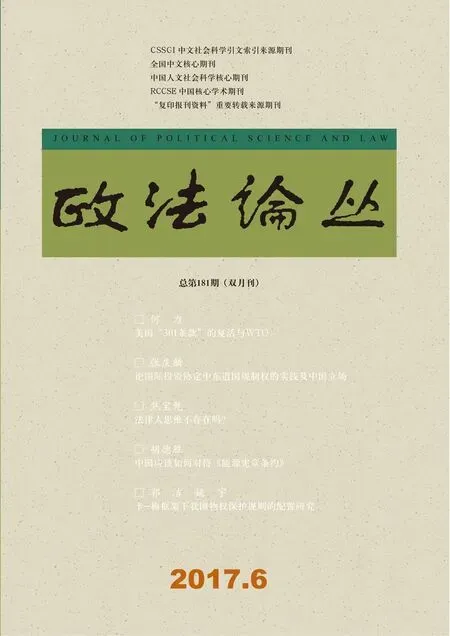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法律强制措施*
2017-01-26刘宇琼
刘宇琼
(《法学杂志》编辑部,北京 100164)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法律强制措施*
刘宇琼
(《法学杂志》编辑部,北京 100164)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将结果归责原则适用于逮捕的做法,值得肯定。突发公共事件要求限制国家机关的赔偿责任,但采取了结果归责原则的刑事强制会使国家机关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产生顾虑,矛盾由此而生,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通过完善制度,行政强制完全可以满足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而且其条件程序较为宽松,责任追究方式也较刑事强制更易为国家机关所接受。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强制优于刑事强制,应在一定范围内用行政强制取代刑事强制。
突发公共事件 行政强制 刑事强制
一、风云乍起:国家赔偿结果归责原则引发争议
《国家赔偿法》自制定以来历经两次修改,其中2010年的修改争议较大。2009年10月27日至31日,《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按照学者的估计,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将于2010年6月生效。然而该法意外出局,最终没有交付大会表决。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何绍仁介绍,没有交付表决的原因为:“在审议中,有些常委会委员对草案的有些规定,如赔偿原则和赔偿程序方面的规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规定”具体何指?“不同意见”又是为何呢?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认为主要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依照草案,对于刑事拘留和逮捕,只要出现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的结果,公安和检察院就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是草案规定,决定要不要赔偿时,法院赔偿委员会采取书面审查为主;三是草案决定赋予国家机关赔偿申诉权,也就是说,国家机关不愿意赔,可以找上级法院告状。”①这当中排在首位的争议是应否将刑事赔偿责任中的结果归责原则推广适用至刑事拘留、逮捕。有观点认为,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为了平息事态,维护社会稳定,在紧急情况下,“该抓的抓了,抓了以后,通过甄别,该放的就放”,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对所有错抓的人都“适用国家赔偿法,操作起来有难度”。也有观点认为在此类特殊事件中,当场抓捕的人,一般至少都存在违法行为,可以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免除国家责任,如果确实错抓了完全无辜的人,国家就应该老老实实地赔偿。②
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后的《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基本上是采取了拘留从宽、逮捕从严的折衷式调整,即刑事拘留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而逮捕采用结果归责原则。这种折衷式的调整略近于立法上“各让一步”的妥协,并未真正解决矛盾:采用违法归责原则的刑事拘留仍不具备理论正当性,而采用结果归责原则的逮捕仍会使国家机关缚手缚脚。
问题的核心在于突发公共事件中应如何看待国家机关的赔偿责任。通常情况下,针对国家机关的刑事强制措施采用结果归责原则不会引发太多争议。与行政补偿类似,刑事赔偿的理论基础也来自“特别牺牲理论”。该理论认为,刑事赔偿所要弥补的,实质上是公权力机关为实现刑罚权或为实施教化、矫治等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执行羁押、收容、留置或有期徒刑,致其身体自由、生命或财产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的特别牺牲。③既然是弥补特别牺牲,那就自然应坚持结果导向或结果归责。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赔偿领域,被羁押的受害人被判决无罪的,对错误羁押的赔偿,如仍需以公务员的故意或过失作为国家赔偿的前提,无论如何对受害人而言是苛刻的。因而,以行为的结果违法性而非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过失作为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刑事赔偿制度在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单独规定的重要原因。”[1]P44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对此也有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总则第2条去掉了“违法”的表述。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对于保护公民权益无疑是有利的,但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未必公平,某种程度上会挫伤他们的执法积极性。通常情况下,这种代价我们可以接受,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则未必。在紧急重大危险发生之时,哪怕执法者有一点点的犹豫,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本文尝试解决以上问题,核心观点如下:第一,《国家赔偿法》对刑事强制作出的修正具备制度基础,符合法学原理,顺应世界趋势。第二,为调动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应限制国家机关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赔偿责任。第三,以上两者存在矛盾,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并未真正解决该矛盾,解决之道在于超越刑事强制与刑事赔偿制度,跳开违法归责与结果归责的窠臼,走“第三条路径”,运用行政强制与行政补偿制度予以解决。具体而言即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赋予行政机关一定强度的即时强制权以部分取代刑事强制权,同时部分以损失补偿取代损害赔偿。
二、与时俱进:国家赔偿映射刑事拘留与逮捕
实际上,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已经把刑事拘留、逮捕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该法第15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其中的关键词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而判断“错误”与否的标准是该条所表述的“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和“没有犯罪事实”。另外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60条和第61条的规定也为判断“错误”与否提供了标准。尽管这两种标准有不一致之处,④[2]但总体上来说,都贯彻了《国家赔偿法》第2条所确立的违法归责原则。相比之下,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对刑事拘留保留违法归责原则,而对逮捕适用结果归责原则。对于这样一种变化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
(一)刑事强制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具备制度基础
从立法层面来看,尽管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条在总的归责原则上确立了违法归责原则,但整部《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并非统一。表现在刑事赔偿方面就是,该法第15条第1、2、4、5项,第16条第1项和第19条第2、3款,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⑤而该法第15条第3项,第16条第2项和第19条第1、4款,采用的是结果归责原则。⑥由于审判领域的结果归责原则早已确立,所以此次修改《国家赔偿法》针对刑事拘留、逮捕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可以看作是结果归责原则从审判领域向刑事强制领域的拓展,而这种拓展也就意味着刑事赔偿范围的扩大。⑦[3]P113[4][5][6][7]从实践层面来看,1994年《国家赔偿法》生效以后,司法审判中运用结果归责原则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在唐文祥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中,法院认为:“赔偿请求人唐文祥被原一、二审法院错判有罪,2008年11月12日被新宁县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无罪,其被错误羁押侵权的事实已获得确认,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⑧在闵耀明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中,法院也认为:“赔偿请求人闵耀明因诈骗一案,被一审法院定罪判刑,二审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此案经本院提审,撤销了原判,对赔偿请求人闵耀明作出了宣告无罪的终审判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本案作出原生效裁定的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应承担其侵犯赔偿请求人闵耀明人身自由权的赔偿责任。”⑨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李伏运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中,法院也是持类似观点。⑩由此可见,在刑事强制赔偿领域适用结果归责原则的制度基础已经具备。
(二)刑事强制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具备理论基础
围绕《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主张:有学者认为刑事赔偿应当采用结果归责原则。理由是,如果采用违法归责原则,将导致赔偿范围狭窄,不利于保障人权。[8]P87-91[9]P843[10][11][12]有学者认为刑事赔偿应坚持过错归责原则为主,结果归责原则为辅的归责体系。理由是,确立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即客观上给受害人造成一定损害后果,同时刑事司法人员主观必须要有过错。只有涉及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以及公共利益,或者难以查明主观罪过,或者查明主观罪过对是否决定赔偿没有多大意义的情形可以采用结果归责原则。[13]P18-21有学者认为应将刑事司法行为区分为合法的刑事司法行为和违法的刑事司法行为,前者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后者采用违法归责原则。理由是,“就一般而言,合法所致的损害是国家补偿而非国家赔偿。但在国家赔偿理论中,往往将合法刑事司法行为所致损害归入赔偿范围,这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决定的。”[14]P57有学者认为刑事赔偿应采用违法归责原则,引入结果归责原则要慎重。理由是,“国家赔偿法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贯彻法治原则是国家赔偿立法的理论基础。如果国家宣布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就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合法是没有意义的,刑事赔偿的范围也会不适当扩大。”[15]P177
以上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也都存在一定不足。第1种观点从人权保障和赔偿范围的角度立论,较为全面,但仅从保护普通公民的角度论证,说服力有限;第2种观点同时从刑事司法机关和公民两方面考虑,兼顾了双方利益,但没有考虑到刑事赔偿的特殊性,有欠公允;第3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结果归责原则;第4种观点完全站在刑事司法机关的立场,不利于保障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失之偏颇。确立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应当从赔偿理念和赔偿范围两方面进行考虑。从赔偿理念而言,从过错归责原则到违法归责原则再到结果归责原则,其责任分担明显是越来越有利于公民,表面上似乎对行政机关不公平,但是考虑到刑事司法是国家运用最强公权力的领域,对公民的潜在威胁也最大,因此在赔偿责任分担方面向公民进行倾斜性也是应该的。从赔偿范围而言,从过错归责原则到违法归责原则再到结果归责原则,客观上刑事赔偿的范围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国家赔偿压力的增大。应该说,在国家赔偿法刚颁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财力尚不足以支撑结果归责原则所对应的刑事赔偿要求,但是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刑事赔偿上全面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已完全可能。
(三)刑事强制采用结果归责原则顺应世界趋势
刑事赔偿采用结果归责原则在我国不仅符合法学原理,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制度选择。比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在诉讼程序中被临时羁押的人,如果在程序结束时不予起诉、免予处罚或无罪释放的决定已确定,而且羁押给他造成显然不正常的损害或特别重大的损害,可以给予赔偿。”其中的关键词是“不予起诉、免予处罚或无罪释放的决定已确定”。除此之外,德国《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第2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14条、奥地利《刑事赔偿法》第2条、美国《对于人民受联邦法院错误判决之救济法》等也有类此规定。以上域外制度实践的共同特点是,这些国家不仅在刑事赔偿中采用了结果归责原则,而且结果归责原则适用的范围一般包括了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
总体来看,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将结果归责原则扩展适用至刑事强制的做法,具备制度基础,符合法学原理,也与当今主流国家的做法一致,是值得肯定的。
三、疑窦丛生:结果归责原则对国家机关的掣肘
反对将结果归责原则扩展适用至刑事强制的意见,理由主要在于突发公共事件下,国家机关应享有灵活处置权,国家机关的赔偿责任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对此观点我们应当如何认识?
(一)应限制国家机关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赔偿责任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的权利结构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结构都将发生变化,在国家权力结构方面,有国家紧急权力制度。所谓国家紧急权力,是指“民主立宪国家为保持其国家的生存及维护现存的立宪秩序,于非常事态发生时,所享有的采取暂时性应变措施的国家权力。”[16]P15这种国家紧急权力的核心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灵活处置”,具体而言其特征至少有四点:权力的扩张性、程序的简化性、司法审查的宽松性和国家赔偿责任的有限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责任的有限性。
由于结果归责原则的存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并不一定意味着刑事强制违法。这样看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限缩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既然国家赔偿与国家违法并不一定划等号,那么国家赔偿就不会成为国家机关积极采取恰当措施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障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我国并非如此。国家机关的执法积极性本质上来源于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在国家赔偿领域,历经国家无责任、国家代位责任和国家责任三阶段后,国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责任与执法人员的个人责任得以区分。表面上看,国家承担责任不会影响到执法人员的积极性,然而并非如此。一方面,《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不符合上述追偿条件,国家机关也可能通过内部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对执法人员进行问责。以公安机关为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三)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案件主要犯罪事实错误,检察院不予批捕、不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七)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或者超过法定期限办案情节严重的”单从这条规定来看,有关公安机关内部问责的制度设计,已经将国家赔偿与国家违法进行了分离(第7项),甚至与国家过错进行了分离(第3项),制度设计不可谓不先进。然而针对修改后《国家赔偿法》的讨论中仍然出现了公安机关的反对声。其中的原因在于:1、普通公众的观念认识中,国家赔偿责任就是作出行为的国家机关的责任,因此即使是由于结果归责原则而承担国家责任,公安机关的行为也会被普通公众认为有错;2、普通公众对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识会重构甚至架空现有公安机关内部问责的制度设计,使得该制度的运行偏向结果归责原则,也即结果错必追责;3、在舆论压力和受此影响的内部问责制度的驱使下,公安机关会本能地对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产生恐惧和排斥。[17]P101-102由此来看,经由国家责任——执法责任制——公众认识的链条,原本理论上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是由国家和执法人员共同承担的。对国家进行结果归责无可厚非,但对执法人员进行结果归责就存在问题。这在原理上与法官责任制、检察官责任制类似,一般不能对法官和检察官采用纯粹的结果归责原则。对法官而言,“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只对其在履行司法职责的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从司法规律的要求来看,发现错案后应当纠正与有错案需要追究责任,是两回事。因此,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18]P122对检察官而言也是类似的,比如有学者认为:“对检察官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且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应追究责任:1、因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导致错误发生的;2 、因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导致错误发生的;3、因法律规定的模糊性而引发对法律适用的认识分歧,导致不起诉、判决无罪等发生的。”[19]P131
(二)有限责任原则与结果归责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机制运行的前提是普通公众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基本认识,而该种认识的水平一般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提高,[20]所以我们不妨将这种机制作为我们进一步立论的前提:在国家机关本能地对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产生恐惧和排斥的前提下,是否会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就将成为国家机关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个重要顾虑,而这种顾虑会直接影响到突发公共事件的恰当处置。因此,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国家赔偿责任应当限制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无论从制度基础、理论基础还是从域外经验来看,针对刑事强制采用结果归责、扩大国家赔偿范围都是大势所趋,由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背景下,有限责任原则就与结果归责原则产生了矛盾。
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没有对常态下的刑事强制和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刑事强制进行区别规定,即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安机关的刑事强制权限与平常相比没有扩大,刑事强制程序没有简化,相关的司法审查也没有宽松,这些都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恰当处置留下了制度隐患。[21][22]即使通过修改相关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更多的刑事强制权限、更简化的刑事强制程序和更宽松的司法审查,也未必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以上矛盾可能会对国家机关的执法行为形成掣肘。有学者在研究司法警察的执法行为后认为:“人民法院赋予了司法警察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司法警察职能。但是,如前述,一方面,司法警察采取强制处分措施不符合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另一方面,司法警察使用武器警械权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只说按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相关规定执行。对于警察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使用警械武器的规定较模糊,在突发事件控制过程中,既要能达到有效控制事态发展,各种手段的运用又要符合比例性原则,这一要求有些强人所难。现实中,强制性措施的运用极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以至于警察在执法时会感到茫然无措。无论‘为’还是‘不为’都要承担责任,都将陷入巨大的责任风险中。不依法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属于失职;依法采取了相关措施,由于突发事件本身的后果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事态扩大甚至造成了伤亡,再加上舆论的不当干预,就会被认为处置不当,激化了矛盾,被迫承担相应责任。这导致司法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不敢使用正当的警察职权。”[23]
四、柳暗花明:法律强制措施的“第三条路径”建构
解决该矛盾比较好的办法,是跳出《国家赔偿法》、《刑事诉讼法》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的视野局限,走“第三条路径”:由于行政强制相较于刑事强制的若干优点,应完善《行政强制法》,规定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在一定范围内以行政强制取代刑事强制,以行政补偿取代刑事赔偿。具体而言,首先,行政强制所提供的强制手段基本能够满足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其次,行政强制所提供的程序选择较刑事强制更灵活;再次,行政强制所附随的行政补偿与刑事强制所附随的刑事赔偿相比,国家机关更容易接受前者。
(一)完善《行政强制法》与《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事件“大”、“急”、“公”的特点决定了针对其采取的处置措施必须迅速及时,因此行政强制中的即时强制也就成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较为理想的手段。[24]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50条的规定,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机关可以采取的即时强制包括:1、交通管制;2、现场管制;3、强制隔离;4、其他必要措施。除此之外,有些实定法所规定的即时强制也可以被运用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中,包括:1、盘问检查。盘问检查分为现场盘查和留置盘问。2、传唤讯问。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3、强制检查。如《客船治安管理规定》第6条。4、强制检疫。强制检疫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细则》、《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等。5、强制保全。强制保全又包括查封、扣押、冻结、证据保全等。6、强制销毁。比如《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17条。7、取缔。比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14条。[25]P 204-220
以上对实定法所提供的能够应用到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若干即时强制进行了不完全列举。综合这些即时强制我们可以看到,针对财产的即时强制包括强制检查、强制检疫、强制保全、强制销毁、取缔等;针对人身的即时强制包括盘问检查、传唤讯问、强制隔离等;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即时强制比如交通管制、现场管制,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兜底条款所预留的其他即时强制。比照解决突发公共事件的手段要求以及刑事强制所能提供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手段,实定法所提供的现有的即时强制手段基本能够满足解决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只是对比刑事强制,行政强制所能提供的对人身的强制手段强度较轻,尚不足用。强制隔离只能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以真正可以用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对人身的行政强制手段只有盘问检查、传唤讯问和一个不确定的其他即时强制手段,整体感觉比较单薄。
再看一下《行政强制法》所提供的可选项。《行政强制法》第9条所列举的即时强制包括:1、限制自由;2、查封;3、扣押;4、冻结;5、其他即时强制。兜底条款不论,“限制自由”一项显得模糊不清: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人身自由?有学者认为:“对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醉酒的人或意图自杀的人,以及正在施暴、斗殴的人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全的人,不管束不能救助、保护该人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预防危害发生的,行政机关可采取约束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前述即时强制措施,不得超过24小时。”[25]P293《人民警察法》第9条第2款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第37条也将对人身的即时强制时间限定在24小时以内。综合来看,对人身的即时强制应保持在极低限度。因为如果对人身的即时强制不保持在极低限度,那么行政强制就成为变相的刑事强制了,对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非常不利。但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人身的即时强制限度应当有所放宽,以赋予行政机关以更大的选择余地。只要严格将放宽限度后的对人身即时强制限定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提下,并辅之以比例原则的制约,这种即时强制被滥用的危险就会被降到最低。
《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采用的是一般法规定加特别法规定的立法模式。因此建议首先对《行政强制法》第9条进行完善,对“限制自由”一项的限度进行明确,以不超过24小时或48小时为宜;其次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进行补充,增加其中对人身的即时强制的强度,并辅之以比例原则进行制约。[26]P55-57
(二)采用更灵活的行政强制条件程序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即时强制的条件与程序进行规定,不过依据大陆法系对于即时强制的一般认识,即时强制本身即包含着条件缩减与程序简化的要求。
在即时强制的要件方面,德国《行政执行法》第6条规定:“非法行为应处以刑罚或治安罚款,为阻止其发生,或为防止紧急危险,行政机关应立即采取行动并在法定职权内行事的,可无需事先作出行政处分而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德国理论界将该规定所表述的即时强制要件浓缩为“特别紧急情况(危险)”,包括1、虽然具备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条件,但因为特殊紧急情况而不能作出行政行为;2、具备使用各种强制方法的法律条件;3、有特殊紧急的需要。如果从觉察到危险到出现预期的损害之间的时间很短,以至于因作出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迟延导致不能有效排除危险或者甚至加重了排除危险的难度,这种情况就是特殊紧急的需要。[25]P297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为阻止犯罪、危害之发生或避免急迫危险,而有即时处置之必要时,得为即时强制。”陈敏教授将该规定所表述的要件概括为“指存有当前之危险,亦即产生危害之事故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27]P720综合来看,即时强制所要求的“紧急危险”与突发公共事件有着天然的契合性,或者可以说,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已经具备了采取即时强制的全部要件。相比之下,采取刑事强制的要件并不会因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而有太大缩减。在即时强制的程序方面,由于即时强制本身即为无法定义务下的行政强制,所以其强制程序非常简化,符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一般的行政强制程序包括作出决定、催告履行和强制执行三个环节,而即时强制只有强制执行这一个环节,其中的程序要求仅有出示身份、告知等。因为一般行政强制的程序设置是为了达到先督促行政相对人自己履行,然后再强制执行的目的,而即时强制所针对的则是无法由行政相对人自己履行(如冻结财产)或来不及由其自己履行的情况(如强制隔离),因此即时强制的程序性设置并没有太大意义。相比之下,采取刑事强制的程序性要求并不会因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而有太大简化。
更关键的是,如前所述,由于国家赔偿责任的存在,即使放宽突发公共事件中刑事强制的条件程序限制,也不能完全打消国家机关的顾虑。
(三)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补偿制度进行专门规定
如前所述,刑事强制如果违法,国家将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刑事强制合法,如果出现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的结果,国家仍然应当根据结果归责原则承担赔偿责任。有了这样的顾虑,国家机关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未免缚手缚脚。相比之下,行政强制如果违法,国家也将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行政强制合法,而其又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那么此时行政相对人可以向行政机关请求合理补偿。在填补损失方面,与刑事赔偿相比,行政补偿是以合法行政行为为前提的,在名义可接受性上要优于刑事赔偿。
为什么同样是行为合法,国家机关对采用结果归责原则的刑事赔偿难以接受,而对行政补偿就可以接受呢?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惯性。由于国家赔偿法很早就打出“违法必究”的大旗,因此在普通公众的观念认识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就意味着国家机关承认错误,国家行为违法,普通公众不会也没有能力对国家赔偿法中实际存在的结果归责原则进行仔细甄别。如前所述,普通公众的这种观念认识又会对国家机关形成无形的压力。相比之下,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国家补偿法,但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领域的单行法已对行政补偿进行了规定,2004年行政补偿更是被写进了宪法,因此行政补偿的制度实践早已深入人心,普通公众也早已在观念中将行政补偿与行政违法区隔开,从而行政机关也就不会因为普通公众对行政补偿的观念认识而承受额外的执法压力。以上解释的证据之一就是目前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种执法责任制中,在内部问责事项里列入行政赔偿一项的屡见不鲜,但列入行政补偿一项的则几乎没有。因此,未来在制定《行政补偿法》时,应考虑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补偿问题专门进行规定。[28]
综上所述,无论从条件程序的灵活性还是从名义可接受性上,行政强制、行政补偿都较刑事强制、刑事赔偿更易为国家机关所接受。如果说行政强制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力度方面稍有不逮,那也可以通过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的方式解决。[29]如此,修改后《国家赔偿法》所存在的刑事拘留、逮捕归责原则问题也将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试图阐明的是,法治的要义之一是系统化思维,[30]P97对于能够采用行政强制处置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尽量采用行政强制,刑事强制只有在迫不得已或最后关头才可动用,而且刑事强制一旦动用,就必须坚持结果归责原则,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注释:
① 参见新浪网:《国家赔偿法草案因有异议未通过将继续审议》,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9-11-01/083318951145.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月12日。
② 参见南方报业网:《微观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为何意外夭折》,载http://www.infzm.com/content/36903,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月12日。
③ 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 670 号大法官解释,载http://www.rootlaw.com.tw/JudicialSearch.aspx,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月12日。
④ 实际上,在判断“错误拘留”与否的标准上,1994年《国家赔偿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差不大,因为后者第61条所列诸项基本上可为前者第15条第(1)项所表述的“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所涵盖;而在判断“错误逮捕”与否的标准上,运用简单的形式逻辑即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法》放宽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逮捕条件,从而实际上缩小了后者所认定的“错误逮捕”范围。
⑤ 除掉第15条第1、2项外,相关条文表述为:“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⑥ 相关条文表述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政赔偿领域出现了与刑事赔偿领域截然相反的动向,即通过引入过错要件缩小行政赔偿范围,而且这两种动向在本次国家赔偿法修改过程中同时体现出来了。
⑧ 参见(2009)邵中法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
⑨ 参见(2003)鄂高法委赔字第6号赔偿决定书。
⑩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4期。
[1] 丁晓华. 刑事赔偿标准的发展及完善[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6,2.
[2] 杨小军.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与归责标准[J].法学研究,2004,6.
[3] 高家伟.国家赔偿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张越.行政侵权归责原则初论[J].行政法学研究,1999,1.
[5] 刘影春等.行政赔偿责任缺失位现象及其对策[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
[6] 张芳.论行政责任归责原则的多元化[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1.
[7] 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6,5.
[8] 顾雷、汪纲翔.刑事损害赔偿[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
[9] 沈德咏.国家赔偿法法律适用与案例评析[M].新华出版社,2000.
[10] 樊崇义、胡常龙.走向理性化的国家赔偿制度:以刑事赔偿为视角[J].政法论坛,2002,4.
[11] 于德恒.论国家赔偿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行政与法[J],2003,1.
[12] 王宏.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缺失[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13] 张雪林等.刑事赔偿的原理与执法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 陈茂华、向本阳.论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
[15] 应松年.国家赔偿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16] 马怀德.应急反应的法学思考:“非典”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 韩思阳.行政裁决纠纷的诉讼选择[J].政法论丛,2014,4.
[18] 李佑标.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论纲——以办理刑事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为视角[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6,2.
[19] 项谷、张菁.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实践的理性认识——以上海市检察改革为视角[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6,2.
[20] 韩思阳.论案例研究的两种角度——制度导向与先例导向[J].政治与法律,2013,3.
[21] 付子堂.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4.
[22] 李晓安等.我国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法制路径选择[J].法学,2009,8.
[23] 崔海梅.司法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职权行使研究——基于注释法学的视角[J].法治研究,2014,12.
[24] 杨小敏、戚建刚.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必需之法则[J].法律科学,2009,5.
[25] 胡建淼.行政强制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6] 余凌云.增设突发事件中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建议[J].法商研究,2007,1.
[27] 陈敏.行政法总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8.
[28] 高景芳、杨琳.行政补偿法立法刍议[J].当代法学,2003,4.
[29] 于安.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J].法学杂志,2006,4.
[30] 赵运锋、孙培福.以刑制罪的法哲学面相与规制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7,6.
DiscussingonLegalEnforcementinPublicEmergency
LiuYu-qiong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Law Science Magazine,Beijing,100164)
It’s proper for "Compensation law" to apply the result-attributable principle to criminal detention and arrest. State agencies should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deal with crisis in public emergency, but the result-attributable principle applying to criminal enforcement will make state agencies hesitate. Through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can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andling public emergency. With less stringen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and more acceptable accountability means for state agencies than criminal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s better than criminal enforcement in public emergency, and the latter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former within a certain range.
public emergenc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criminal enforcement
1002—6274(2017)06—141—08
DF312
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治理中社会矛盾化解与法治保障研究”( 13BFX009)的阶段性成果。
刘宇琼(1976-),女,湖南怀化人,《法学杂志》副编审,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行政法、科技法、司法制度。
(责任编辑:黄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