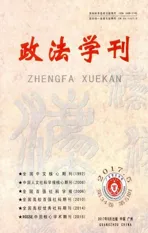冒犯原则与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
——以公开性交为例
2017-01-24胡莎
胡 莎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冒犯原则与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
——以公开性交为例
胡 莎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英美自由主义的犯罪化正当性语境下,公开性交淫秽行为是一种令人感到恶心、厌恶、肮脏、震惊、羞耻等极其不愉快或令人满足窥私窥淫欲的公然极端冒犯行为,而极端冒犯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是冒犯原则。冒犯原则有别于、独立于损害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具体适用准则和客观权衡机制,主要包括冒犯行为具有严重性、被冒犯者难以合理避开、冒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性和被冒犯者的反应必须是理智的,只有首先满足该个限定条件的冒犯行为才有可能被予以犯罪化。而同样作为犯罪化正当性原则的损害原则和不法原则,不能为公开性交犯罪化提供正当性根据。某种冒犯行为被犯罪化除了需符合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还需考量犯罪化替代措施。
冒犯行为;公开性交;冒犯原则;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损害原则
在英美自由主义的犯罪化正当性之刑法哲学语境下,公开性交 (Public Sex)一般是指公共场所成年男女合意性交。这个淫秽的极端冒犯行为(Extreme Offensive Behavior)例子来源于美国著名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 (Joel Feinberg) (以下简称范伯格)的《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冒犯 (第2卷)》一书中所举的第16、17个极端冒犯行为,即公交车上男女相互给对方手淫,并最终开始交媾。[1]13这种“公共场所成年男女合意性交”(以下简称“公开性交”)是冒犯行为 (Offensive Behavior)中最极端的冒犯行为例子之一,它是一种令人感到恶心、厌恶、肮脏、恐惧、羞耻、尴尬、焦虑、使人倍感被冒犯、或令人满足窥私窥淫欲的公然淫秽行为。[2]256其中冒犯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但规范层面来说,冒犯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给他人造成不愉快的心理体验、令人讨厌的主观精神感觉状态、并令人感到不便的不当行为。详细地说,冒犯行为会带给被冒犯者各种令其感到厌恶、恶心、尴尬、不便、愤怒、怨恨、震惊、害怕、蒙羞、不满、心里不舒服等各种高度分散人注意力的、负面的、消极的、不良的情绪。[3]10-14而对于公开性交这种极端冒犯行为,范伯格主张可以将其予以犯罪化,而犯罪化根据是冒犯原则 (Offense Principle),范伯格认为该原则总能为入刑建议提供充足的理由,还认为入刑可能有效防止行为人以外的人受到严重冒犯(与损伤或损害不同),而且入刑对实现该目的也可能是一种必要的途径 (若无其他方法能够以更小的价值成本产生同等的有效性)。[1]1
虽然我国79旧刑法将公开性交规制为流氓罪,但97新刑法废除流氓罪,没有将公开性交规定为犯罪。至于我国现今有关“公开性交”的实例,就笔者目前所知,虽其猎奇性的网络新闻较多,但引发我国刑法学界这两年来广泛关注的只有北京优衣库试衣间事件,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刑法学车浩教授从教义学的角度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公共场所”。而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这种公开性交的极端冒犯行为,在应然层面上,立法者是否应该将其入刑,暂时缺乏犯罪化的专门研究,而范伯格对极端冒犯行为在刑法道德哲学的探讨上,可为我们提供诸多有价值的参考、指引和借鉴。同时,立法者将某种行为入刑如何具备正当性,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学上一直是一个理论困惑点,而研究公开性交这种极端冒犯行为是否应该入刑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深化和强化我国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of Criminalization)理论;除此之外,对作为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之一的冒犯原则的专门研究,可以进一步廓清刑法的界限或边界问题,从而有利于指导我国立法实践摆脱入刑的随意性、被动性,也可以防止过度犯罪化问题 (Overcriminalization Problem);[4]另外对冒犯原则是否可为公开性交入刑提供犯罪化正当性理论根据的详细充分论证,也可为今后其他各种冒犯行为入刑与否的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冒犯原则是一个独立于损害原则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
广为人知的是,范伯格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只有损害原则 (Harm Principle)和冒犯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入刑根据。而冒犯原则作为范伯格自由主义学说中最薄弱的一环,很多自由主义者反对将该原则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而保守主义者认同冒犯原则是一个独立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并不断寻求扩充该原则,以此希冀国家禁止各种冒犯行为。[5]120而本文站在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冒犯原则可以作为一个与损害原则平起平坐、等量齐观、独立存在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
(一)冒犯本质上有别于并独立于损害
范伯格认为冒犯原则作为刑事立法根据理论之一,是一个独立于损害原则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具体来说,冒犯行为给被冒犯者造成极其不愉快的各种心理体验,而在这种负面的主观感受、心理伤害或精神损害的影响下,被冒犯者难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从而对被冒犯者的利益产生影响,而将冒犯行为予以犯罪化,可以有效地减少或预防这种严重冒犯他人的行为。由此可见,虽然范伯格认为“冒犯 (Offense)”和“损害(Harm)”是两个不同种类、相互分离的行为,但事实上,范伯格并未详细地分析“冒犯”和“损害”的区别。[6]883反而从范伯格对冒犯原则的定义中可看出,范伯格对“冒犯”的定义,本质上和“损害”一样,都是“利益受挫” (Setback to interests),只是冒犯行为中利益受挫的强度、持续时间、发生频率等比“损害”要轻微。因而,严重深度的冒犯,例如“情绪稳定性这一利益受挫”,就相当于“损害”,所以冒犯原则不能作为独立的规范犯罪化理论,它实质上附属于损害原则,是损害原则的一部分。冒犯原则只能在损害原则的指导下,将冒犯行为视为轻微的损害,借此发挥冒犯原则作为犯罪化理论根据的作用。[7]364的确,冒犯原则能否独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损害”的理解。如果将“损害”理解为“利益受挫”,而这种“利益受挫”又包含了个人情绪不稳定、个体福利康乐减少、生活质量的下降等。那么“冒犯”作为给他人造成不愉快的心理体验、令人讨厌的主观精神感觉状态、并令人感到重大不便的行为,确实会导致个人情绪不稳定、个体福利康乐减少、生活质量下降,此时冒犯成为损害的众多表现内容之一。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将个人情绪不稳定、个体福利康乐减少、生活质量下降等定性为属于“损害”的“利益受挫”,未全面客观地反映生活事实,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情绪不稳定”有时候可能意味着是狂喜,而“个体福利康乐减少”有可能意味着祸兮福之所倚,很难说这是一种“利益受挫”;其次,将“损害”本质理解为不法的“利益受挫”,这导致刑法中的“损害”严重泛化,从而严重弱化损害原则天生所具有的限制国家刑法权的自带功能;最后,对“损害”的这种理解,也严重忽略了冒犯行为的独特性。在本文看来,对“损害”概念内涵的理解,应采用后果论,即损害是指刑法所保护的是公民生命被剥夺、身体健康和肢体完整性遭受残害、私人基本财产和生活资料遭到毁坏等实质、真实、重要的基本利益。只有对“损害”如此理解,才能显而易见、简单易行地明确行为的犯罪性 (Criminality)。因此,本文认为极端冒犯行为本质上是不愉快的心理体验、负面消极的精神状态等被严重滋扰冒犯的强烈主观负面体验,属于每个个体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刑法上明显有别于并独立于“损害行为”。
(二)冒犯原则有可操作性强的具体适用准则
确立“冒犯”有别于“损害”后,冒犯原则有可能成为与损害原则平起平坐、等量齐观、独立存在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应先明晰冒犯原则作为犯罪化正当性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 (Mediating Principles)。一般来说,某种行为会令人产生被冒犯的痛苦情绪或感觉,不能成为此种行为被犯罪化的正当根据,但在两种情况下,冒犯行为有可能被犯罪化。一种是该冒犯行为侵犯了公民个人隐私和自治权,它迫使被冒犯者对自己内心的精神领地或内在属性失去正当控制。另一种是通过对冒犯行为的调合或衡量,只将对社会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影响力程度深或危害后果重的冒犯行为予以犯罪化。[1]27很明显,对于第一种情况,公民作为独立、坚强的个体,有足够的理性能力控制自己内心的精神领域或内在属性,而无需通过外在的国家行动来调整个人情绪,否则会导致“烽火戏诸侯、博爱妃一笑”似的滥用刑罚权。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应廓清冒犯行为的调和或衡量准则 (Mediating Principle),即冒犯原则的指导适用准则,该调和准则包括四个限定条件:第一,必须对冒犯行为的严重性进行判断,这具体包括三个因素:冒犯行为所产生的反感强度或程度、持续时间和感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人员波及范围。[1]29但很明显,这三个因素都针对被冒犯者的内心感受或心理活动,较抽象、粗略,客观具象性不足,难以具体测量,而后文会据此结合公开性交事例具体详细地分析该因素;第二,观者合理避开冒犯场景的难易程度。但“避开”的合理性如何确定?这还需要后文结合具体的冒犯情形予以具体分析。第三,这种冒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性,判断冒犯行为的是否具有合理性主要具体包括六个因素:冒犯行为之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个体重要性,例如能否增进个体福利安康;实施冒犯行为是否是行为人在行使表达自由权,因为畅通无阻的自由表达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用;冒犯行为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冒犯者是否怀有恶毒、恶意或故意使人恼怒的动机;这种行为在该区域是否很普遍,人们是否习以为常;有无只产生较少冒犯感的其他时间、地点;[1]30第四,被冒犯者的反映必须是理智的。总而言之,当某个冒犯行为满足冒犯原则的四个限定条件后,即该冒犯行为具有严重性、观者无法合理地避开、这种冒犯行为不具有合理性和被冒犯者对该冒犯行为的反映是理智的,那么立法者可以将这种冒犯行为予以犯罪化。由此可见,上述内容详细、构造精细、可操作性强的冒犯原则具体适用准则之存在,足以说明冒犯原则可成为与损害原则平起平坐、等量齐观、独立存在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
二、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在公开性交犯罪化中的运用
通过以冒犯原则为理论指导,将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运用于公开性交案例中,我们发现经过对所有因素进行权衡,当“公共性交”之深度冒犯行为同时满足四个限定条件时,这种极端的冒犯或滋扰行为可以被立法者予以犯罪化。如前文所述,这四个限定条件条件分别是: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必须具有严重性、被冒犯者不可能合理避开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性、被冒犯者的反应必须是理智的。由此可见,虽然令社会公众感觉不愉快或看不顺眼的行为范围极其广泛,但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像一个漏斗或筛子,将一些不应予以犯罪化的行为剔除,从而直接抵御刑法的过度犯罪化问题。例如因为看不惯他人将头发染成鲜绿色而禁止这种行为,这明显剥夺了公民染发的自由,这种刑法禁令简直是匪夷所思。[7]358
(一)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必须具有严重性
一般来说,冒犯行为的严重性是根据冒犯行为的幅度来判断,具体包括强烈度、持续时间、当场持续被波及的人群范围等因素。而对于范伯格假设的公交车性交案,由于公交车是在路面行驶,且每隔几分钟还有固定的停靠站,所以乘客被冒犯的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公交车厢面积较小,容纳的乘客或“观众”也不够多。鉴于此,我们可以在范伯格公交车案例的基础上,假设一个更加严重的在飞机上公开性交的例子。在北京飞往伦敦的坐满乘客的中国航空乘客舱内,一对中国男女在飞机高空飞行的10个小时内,持续地不断相互抚摸性器官、衣不蔽体地性交并发出呻吟声或其他各种奇怪的声响,而空服员们因某些原因行动不便而无法介入。当设身处地地假想这种画面场景,我们一般会明显产生各种强烈的恶心、憎恶、震惊、愤怒、羞耻、反感、排斥、尴尬、焦虑、痛苦等五味陈杂的负面、消极情绪或不愉快体验外,还会在心理层面上感觉到我们国人的爱国情感被伤害了、而且这对中国男女也违背了不得行邪淫的基本生活理念。具体来说,这种冒犯行为的严重性主要体现在:行为强度大——该行为除了动作激烈的公开性交行为外,还伴随着呻吟声和其他奇怪声响,而且衣不蔽体,时而毫无遮挡,甚至是毫无避讳的赤裸裸;持续的时间较长——该冒犯行为在空中封闭的国际机舱内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该冒犯行为直接当场波及的人群范围广:波及到的人员是飞机上大多数乘客。当然,这里所指的波及人群,是指那些一直被迫目睹或耳闻这种公开性交行为的被冒犯者,而不包括那些喜欢看公然淫秽行为而自愿持续地暴露在被冒犯的状态的人。如果观者自愿观看、或者如饥似渴地偷窥甚至是怀着性欢愉期待感欣赏这种行为,那么这类人并未被冒犯,那么实施公开性交的行为人不能凭此被入罪,否则违背观者自愿原则。另外,冒犯原则中所指的波及人群,主要指能感知被冒犯之普遍严重程度的一般正常大多数,而不能单独包括属于少数类的精神病或情绪、心理、道德情感极端敏感的人,因为对于那些易感性极强或极端敏感的人,事实上只有一般程度的冒犯行为,在他们看来却到了严重的程度,而这种严重程度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不能单独根据这类人的被冒犯程度来判断冒犯行为的严重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判断公开性交冒犯行为的严重程度,很有难度。因为在相同的具体处境下,由于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理念、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宗教信仰等等,每个人对某种冒犯行为的感觉、情绪感受或心理体验是不同的,我们不能专断地认为在场的其他人和我们的感觉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各种心理感觉或精神感受一直随着境遇在变化,有些甚至变得很快。总而言之,这些心理感受具有不确定性、专断性、易变性、转瞬即逝性、个体差异性,让人琢磨不透,所以我们很难对其加以判断。但是很难判断并不代表不可能判断,因为不言自明的是,我们亲眼目睹公开性交行为时,一般人会强烈地感受到鄙夷排斥、恶心作呕、羞耻愤怒、震惊错愕、难堪尴尬等极其不愉快、心理特别不舒服的负面情绪,而且这种负面情绪对一般人来说是终生的羞耻烙印,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判断这种极端冒犯行为的严重性。
(二)被冒犯者不可能合理避开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
空中飞行的飞机是一个人员高度集中的封闭空间,而在上面公开性交,会高度分散其他乘客的注意力,乘客们为了不被分散注意力,却难以避开或离开该飞机,而且飞机行驶过程中一般应关掉电子通讯设备,乘客难以通过互联网或其他便捷通讯设备向外界求助,因此一般的乘客都会被这种冒犯行为所引起的恶心、震惊、尴尬、羞耻、愤怒等强烈负面情绪所控制或攫住,导致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在飞机上睡觉、交谈、看书、玩手机、打电脑等等。那么乘客们除了离开飞机之外,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合理的方式避开这种令人极其不舒服的情境,例如某些乘客不断提醒那对男女安静点、或注意自己的行为,或换个地方做这种事等。但如果这段男女在提醒后停止,一个小时后又顽固地开始公开性交,那么这又需要乘客去直接目击这种不堪入目的行为和直面那对淫乱男女,提醒她们不要做这种事。很明显,这种情形下,乘客们没办法轻而易举、毫无困难的合理避开这种极端冒犯行为,所以这种情形下,被冒犯者不可能合理避开公开性交这种冒犯行为,那么立法者可以将该行为予以犯罪化,那么民众可以对这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合法的扭送权,或者刑法上自助的正当行为,从而重新夺回飞机上的空间的控制权和支配权。
可能有民众事后从网络或报纸上得知在飞机航班上公开性交之事而倍感被冒犯,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民众通过媒介“单纯知道” (Bare Knowledge)有男女公交性交而倍感冒犯,而据此考虑将这种行为予以犯罪化。因为不在场的事后民众完全可以看到这种文字图片报道后,立即轻易地将这类报道挪出视线,或在网络上看到类似标题时不点击进入、或进去后马上关掉页面从而合理地避开。同时结合冒犯原则的第一个严重性条件,这种“单纯知道”对公民的冒犯程度太轻微,可以忽略不计。[8]86
(三)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性
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与其他冒犯行为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极其淫秽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肮脏、野蛮、粗俗、下流、荒唐等的代名词,它明显是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冒犯他人的道德情感。[9]1952当然,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的不合理性,不能过于简单地仅根据朴素的道德情感来判定,而是要结合具体的六个因素来判断,即公开性交对行为人是否具有个体重要性;公开性交是否是行为人在行使表达自由权;公开性交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公开性交者是否怀有恶毒、恶意或故意使人恼怒的动机;公开性交在该区域是否很普遍,人们是否习以为常;有无只产生较少冒犯感的其他时间、地点。这样可以减少冒犯行为合理与否判断的随意多变性。
1.公开性交在刑法上对行为人不具有个体重要性。行为对个人的重要性,对于意志自由、成年理性的行为主体来说,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毕竟个人最擅长对自己事情进行利益衡量。而本文公开性交例子的行为主体是成年男女,实施这种行为对她们的重要性,主要可能是满足本能的性需求,但这种性需求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私下满足。而且如前所述,刑法保护的是公民财产、身体完整、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基本人格尊严等等客观真实的状态,这状态或结果是公民个体在社会中生存或维持基本生活的最基本保障,这些才是作为最后保障法之刑法旨在保护的具有个体重要性之行为。因此,上文中飞机上的公开性交行为在刑法上明显不具有个体重要性。
2.公开性交在刑法上不是行为人在行使表达自由权。表达自由权 (Freedom of Expression)是指所有公民表现、展示或向社会呈现自己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生存常态之基本权利,其本身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是公民在社会上不言自明、与生俱来的自由。因此,如果实施冒犯行为的行为人在行使表达自由权,那么我们不能因为多数人反感或不喜欢某种冒犯行为,而惩罚实施这种冒犯行为的人。但是公开性交这种冒犯行为中的成年男女,不能以行使表达自由权来进行免责辩护,因为公开性交并不是现代公民的生存常态,不是行为人在行使表达自由权,而是在颠覆、嘲讽表达自由权本身。与之相反,属于公民行使表达自由权的相关亲密行为,主要是在公共场所牵手、抚摸身体非敏感部位、亲吻身体非敏感部位、个体私密空间的性行为等等,因此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排除了这些身体亲密行为而框定了飞机上的公开性交行为。
3.公开性交本身在刑法上不具有社会价值。一般来讲,公开性交行为除了能满足具有社会上拥有猎奇类性嗜好或特殊的性癖好的群体性需求外,其余的都是社会负面价值,即损市容、毁景观、丢国人脸面等等。在刑法上,公开性交行为也不具有社会价值,它给大众群体带去强烈的被冒犯负面体验,严重滋扰了普通民众。因此飞机上的公开性交男女,毫不顾及大众群体感受、极其不尊重大众群体,导致大众群体产生各种强烈的被滋扰感,看不出这种行为有何社会价值。
4.公开性交者怀有恶毒、恶意或故意使人恼怒羞耻的动机。即使飞机上公开性交中的双方辩称男方是怀着使女伴受孕造人的良好动机,而并没有怀着恶意或令人恼怒羞耻的动机,但是这种辩护不成立。因为在刑法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动机,是依据一般人事后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而不是行为人事中主观的判断。很明显,公开性交者即使不是怀着恶毒或恶意的动机,至少是怀着使人恼怒羞耻的动机。
5.公开性交在该区域不普遍。毋庸置疑,在飞机座位上公开性交,不具有普遍性。而如果是在飞机的厕所内、公园的丛林深处、商场的洗手间或试衣间等区域,那么这种行为较为普遍,甚至某些地方有人在打野战,人们都习以为常,而对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人们并未感到被深深地冒犯或滋扰,那么刑法不应予以规制。
6.有无只产生较少冒犯感的其他时间地点。显然,在飞机公开性交的案例中,那对男女完全可以在产生较少冒犯感时间、地点实施性交行为,例如全天宾馆房间内、全天在自家的卧房、客厅、厨房或相对封闭的阳台、全天在私家车内等时间地点内,都可以实施这种行为。因此,飞机上公开性交的男女符合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
(四)被冒犯者的反应必须是理智的
如果被冒犯者对某种冒犯行为充满了偏见或歧视,他们对冒犯行为的强烈负面情绪反应是不理智的,那么我们不能据此对该冒犯者施加刑事制裁。例如对飞机上公开性交例子稍加改动,将剧情变换为在主要乘客为中国人的航班上,一对男同性恋者亲密地接吻,动情地相互抚摸身体非敏感部位,还发出粗重的呼吸声。这种情况下,航班上的大部分中国异性恋乘客,都会觉得极其恶心、厌恶、反感等,但是这种被冒犯的强烈反映是不理智的,是带着对同性爱者固有偏见和隐形歧视做出的剧烈反应。如果是异性爱男女在飞机如此行径,乘客可能也会觉得恶心、厌恶或反感,但不会像对同性爱者那样强烈。因而,被冒犯者对某种冒犯行为的反应必须是理智的,而不能是社会固有偏见或隐形歧视支配下的反应,我们不能仅因为大部分人有这种不理智的反应,而得出国家应采取刑罚措施禁止他人实施这种行为。[10]561但有群体可能会辩称,看到同性爱者尽情地接吻觉得特别恶心,这是正常的不自主反应,自己不能控制,也无法改变这种反应。但是正常反应并不代表理智反应,正常反应是基于自己内化于心的传统道德信念作出的,而理智反应是通过冷静理性地详细论证、全面分析、深入推理而得出的反应,如果那些持正常反应说的群体,仍辩称自己无法通过理智去说服自己或使自己摆脱这种没有道理、不合逻辑、没有缘由的恶心厌恶感,那么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恐惧症,[10]568国家不能根据这种非理智的恐惧症或单纯地负面情绪来发动刑法。
而乘客对飞机上公开性交冒犯行为的反应是理智的。因为这对男女违反公共空间隔离或分区的使用规则。众所周知,乘客机舱作为公共空间是共享的,所有人都可利用这个空间,而这对男女在机舱内实施这种无法合理避开和抵制的高度分散乘客注意力的行为,抢占、操控了他人的注意力,以此霸占和剥夺了乘客享受这个空间的权利,极端顽固地滥用空间,这完全违反了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
四、损害原则不能为公开性交犯罪化提供正当性根据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立场下的犯罪化正当性原则除了核心原则——损害原则外,还包括不法性原则 (Wrongdoing Principle)、罪责原则 (Culpability Principle)和冒犯原则等等。只要某种行为符合其中一项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即可被犯罪化。其中损害原则,也被界定为法益保护原则,其涉及众多学说纷争,如前所述,本文对此采取后果说,即某行为导致公民生命被剥夺、身体健康和肢体完整性遭受残害、私人基本财产和生活资料遭到毁坏等实质、真实、重要的基本利益受损害的后果时,该行为入刑才有可能,而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并未损害他人实质、真实和重要的基本利益,因此天生对刑法具有限定功能、批判功能的损害原则反对将公开性交这一典型的极端冒犯行为予以犯罪化。
(一)刑法中的损害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伤害
虽然在日常对话中,公共性交会产生损害后果,例如由于公共性交场地不干净、不卫生或不整洁,而可能导致当事人罹患性病、或导致女方意外怀孕、或因为该混乱的男女关系而破坏男女双方有关的婚姻家庭;但在法治语境下,行为人应为自己自愿且有效同意的日常行为负责,由于不采取安全措施的随意性行为导致自身被感染性病或意外怀孕,行为人应该自我负责,应承受得性病或意外怀孕的恶果,而如果对方因而承担牢狱之灾,这违反责任自负原则或个人自治原则。至于公开性交会破坏男女相关的婚姻家庭,这种后果极有可能是臆想出来的,因为一般有婚姻家庭的人几乎不会从事这种恬不知耻、饥不择食的泄欲行为,毕竟他们已经有固定的性欲疏导对象,反而是那些极度饥渴、空虚无聊、没有婚姻家庭生活的单身男女是此类风流事件的常见当事人。除此之外,可能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这种不顾及他人感受、对他人表示不敬的公然性交行为,会使被冒犯人倍感生活安宁受到影响、个人能力和能力发展机会也就此遭到破坏、对本可无障碍利用的公共资源被他人无理由的剥夺、被冒犯人的社会参与度也就此而受限等等。但在刑法规范理论看来,这些在恐惧、焦虑心理支配下而被无限假想延伸的损害,离最终真实的生命被无情地剥夺、身体健康和肢体完整性遭受残害、私人基本财产和生活资料遭到毁坏等刑法应予保护的实质重要利益都太遥远。而且这些损害都无实质性证据予以客观证明,更多的只是行为人的一种无限发散式的负面、消极的主观感受。如果将这种负面、消极的主观感受扩大解释为刑法中的法益或损害,这会导致刑法上的“损害” (Harm)沦为充满感情色情的日常用语——伤害 (Hurt),从而直接严重削弱法益或损害原则天生所具有的限制国家刑法权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导向。[11]
(二)法律道德主义立场下的性道德不属于损害原则中的损害
从基本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极端地偏离普遍的常规性道德标准,最先开始毫无掩饰地冲击了性阴私、个人感、隔离感等公民基本的道德情感,[2]261严重违背社会性风俗,并直接败坏、毁灭社会的基本性道德规范,会导致出现社会性道德体系崩溃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将有伤风化、有违公德、性道德败坏等道德上的不利状态,等同于刑法规范中的损害,否则会导致损害原则虚置、架空甚至是坍塌。展开来说,虽然公开性交会引起一般公众强烈广泛的抱怨和愤恨,且伴随着强烈的耻辱、恼怒、厌恶、震惊、愤怒等情绪情感。特别是那些对性持羞耻心态、保守态度、抵制立场的公民,他们会强烈地感觉到自身的道德情感受到公开的冒犯。但如前所述,我们无法忽视社会中也有占总人口中很大比例的群体,在强烈的好奇心、窥淫欲、性刺激等主观心理支配下,热衷于观看他人公开性交,这种行为对这类群体来说,甚至是一种额外福利或意外惊喜,他们会抓紧机会,拿稳手机或其他录像设备拍照或录像,捕捉下这种公开的、免费的活春宫图。因此,公开性交虽然违背公民日常作息秩序、社会基本性道德,肯定会使一部分人心理感到极其不舒服,但并无怀着强烈个人诉求的特定关联被害人直接控冒犯者,也并未产生严重的真正损害或损害的危险,且该行为并不涉及每未公民的基本生存利益,也不涉及最终的真实实质性损害,不能根据损害原则而主张借助最强制暴力的刑法对这行冒犯行为进行干涉。总而言之,损害原则排除国家动用刑法规制那些极其不道德的性行为,否则是用多数人的道德压制其他特定少数群体的道德,这是属于另外一个犯罪化正当性理论立场,即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Legal Moralism),而不是本文的自由主义的犯罪化正当性理论立场。换言之,虽然法律道德主义也可为公开性交这种本身极其伤风败俗、违反基本道德情感的不道德行为之犯罪化提供正当性理论根据,[12]但这种正当化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具有批判性的损害原则之抵制,[13]因为法律道德主义利用刑法推行道德,为所有人强行带上刑法贞操带,这与提倡个体人格尊严、个人主义、道德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有明显的冲突。
(三)禁止公开性交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现代性文化禁忌
从性学角度来说,我国主流社会认为性本身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文化禁忌 (Cultural Taboo),讨论、展示、渴求或满足性,会使人堕落,使其人格遭受贬低或抹杀,当事人对此也充满耻辱感和羞愧感。所以,如今在这种具有不可名状之强大威力的性禁忌影响下,虽然现代社会对性越来越开放,但社会主流性文化还是相当避讳对性加以讨论、展示,至于渴求或满足性欲,那是私底下的私生活,一般人并不敢违背这种强大无比的性禁忌。而男女在光天化日下色胆包天、公然违背现代性禁忌,肆无忌惮地在展示和满足双方的性欲,这在现代性文化禁忌的语境下,是此男女肮脏不结、荒淫堕落的明证,其人格尊严也荡然无存,甚至是该事件所涉的路人、旁观者或本文的作者,因为沾染到了这种肮脏不洁之事,也有人格堕落、低下的重大嫌疑。进一步说,根据社会主流的禁止公开性交之性文化禁忌,公开性交行为在主流话语中,一直被强烈地谴责、被猛烈地责难、被广泛地鄙视和嫌弃,涉事男女也在这种文化禁忌中被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即使是旁观者、讨论者或研究者都被这种文化禁忌所污名化。但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公开性交的发生,事实上难以动摇“禁止公开性交”这一性文化禁忌,更不会破坏这种文化禁忌,反而会不断地强化这种文化禁忌,还使其更加稳如泰山。至于在刑法语境下,我们刑法所保护的现代性文化禁忌,是那些属于社会的核心精神文化组成部分、支撑社会客观存在之根基的性文化禁忌。这些性文化禁忌不仅极其容易遭受行为人直接正面的攻击、颠覆甚至是被完全打破,而且该行为会直接侵犯到社会弱势群体,即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健康、身体完整、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从而直接危机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现代性文化禁忌,主要是指禁止未经他人同意强行与他人性交、禁止性侵犯未成年人、禁止从事儿童淫秽色情相关的行为、禁止奸淫尸体等等。而公开性交行为并未直接损害到他人刑法上的利益,在神武无上的性文化禁忌作用下,利用最具强制暴力性的刑法对该行为予以禁止,显得多此一举。
(四)性羞耻心被伤害无法成为犯罪化的正当理论根据
从性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性立法应多考虑当事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14]而公开性交这种极端冒犯行为,对儿童、未成年人和妇女的性心理所造成伤害后果,尤其触目惊心、引人担忧。这种极端冒犯行为直接侵犯了人人天生皆有的对性的羞耻心,它使人强迫自己压制性欲,是一种令人感到痛苦、折磨、悔恨、侮辱的情绪或感觉,具有特殊的敏感、脆弱和私密的特性。但即使我们与生俱来的性羞耻心特别敏感、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我们也不能据此把严重伤害到我们性羞耻心、使我们充满强烈负罪感的公开性交行为规定为犯罪。因为事实上公开性交行为对观者性羞耻心的伤害,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毕竟并不是所有人的性羞耻心皆被伤害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风流韵事与自己毫不相干,而只有在行为人与被波及的受众是朋友、家人、老师、老乡或其他类似紧密关系时,特定“被害人”的性羞耻心才可能被伤害,才可能导致受众对性有强烈的负罪感、厌恶感、排斥感。而且,虽“性羞耻心”和众多被冒犯的感觉一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痛苦情绪或感觉,但“性羞耻心被伤害”的外在具象表现是谈性色变、缄默不语或羞于启齿,公权力无法对这种特别敏感、脆弱、私密的心理带去半点抚慰,只有避而不谈才是最好的抚慰和保护,因此,不能单独以性羞耻心被伤害而求助于刑法。至于公开性交行为会对儿童或未成年人带去伤害,我们也能据此将该行为予以犯罪化,因为绝大多数冒犯型犯罪并不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而被刑法规制,[11]这种行为本质上侵犯的是家长对未成年人专属的性教育权益,这种权益的恢复或重建,无需刑法这把牛刀,家长即可轻而易举地完成,家长甚至可以此事件为导火索,帮助未成年人上一堂生动地性教育课,从而更加明确而牢固地树立自己对儿童性教育的专属权。
(五)成年女性同意公开性交即无损害
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这种公开性交行为,即使是一对成年男女合意而为,但由于传统或普遍的性交模式及其行为本身由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一般处于被动状态,因而公共性交实际上是男性公然玩弄女性、公然猥亵女性,是在贬低女性,践踏女性尊严,因而这也是一种变相地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这种行为的发生会显著增加女性在一些公共场所的不安全感。但在笔者看来,女性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个体,属于同意且自愿地从事这种行为的主体,成年女性有效的同意(Consent)即无损害,这种行为并未导致性别歧视问题,也没有体现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这种获得女性同意的行为中,女性并不是客体,不存在女性被主宰、被羞辱或被剥削的情形,而且这种行为也并没有特意贬损女性之意。当然,可能会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女性的男伴、或被妓女接待的男嫖客,由于之前看过一些公开性交的新闻报道,而可能要求该女伴或女性性工作者与其在野外发生性关系,以寻求刺激、应生理之急或节约房费等等。这种情况的确会给一些女性很大的压力,但这并不是对女性的一种实质损害,而且证据表明这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15]87
五、不法性原则不能为公开性交犯罪化提供正当性根据
根据犯罪化正当性原则之一的不法性原则(Wrongdoing Principle),假设未来我国立法者欲将公共性交这一极端冒犯行为予以犯罪化时,立法者必须考虑此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不法性。当然,我们不是望文生义、简直直白地将刑法中的不法性理解为刑法条文有明文规定或某种行为违反了刑法规定,因为即使某行为已满足刑法有明文规定的这一法律依据或条件,也无法表明立法者这种已有的犯罪化具有令人信服的正当理论根据。因为刑法哲学层面上为犯罪化提供正当性根据的不法性原则,其强大说服力不是来源于实证法的既有规定,而是来源于某种行为上本质上具有不法性,即这种行为本质上会引发全体公众的深切关涉,可以将这种特性简称公共性 (Public Concern)。但我们不能将不法原则中的“公共性”简单地理解为在公共场所发生,而应该是指该行为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的实质性利益,这种实质性利益的侵害会使整个社会的公众为之感到担忧、恐惧或焦虑等。此外,根据不法性原则,可以被犯罪化的行为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宽容或宽恕,即不被容许。[16]20-21
(一)公共性交之冒犯行为不具有不法原则中的公共性
刑法是公法,保护的是由无数个人基本权益融合而成的国家和社会之公共利益,虽然刑法现今有被私法化的趋势,即越来越趋向于着重保护公民个人基本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但仍无法侵蚀刑法的公法性。至于公开性交行为,虽然不是社会商业行为或社会性交易行为,这种成年男女之间的合意性交也未违反传统男女正常结合这种社会主流伦理道德,但是这对异性恋男女直接严重冒犯了现实、具体的个人,即那些在事发现场被迫或被动地目睹这种行为的旁观者或其他路人,从而导致被冒犯者的心理状态和对性的道德情绪达到近乎完全的困惑和紊乱。[1]22因此,这种行为是一种对特定场合下的旁观者的严重冒犯或深度滋扰,扰乱了这些特定旁观者或路人享受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宁处境,而难以将此行为定性为是对由无数个人基本权益融合而成的国家、社会、集体等公共利益的侵害。而且刑法理论上中所理解的法益侵害,是一种在故意或过失主观罪过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破坏性、毁灭性、强烈震撼性、深度打击性的行为,它损害的是直接关联到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这种基本生存利益的损害,会使社会每个公民都感到担忧、恐惧或焦虑。而公开性交这一冒犯行为或深度滋扰行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只是伤害了无法躲避的特定旁观者,特别是给那些不愿目睹这种行为的特定旁观者,带去各种不愉快的复杂心理体验和令人讨厌的主观精神感觉状态,而并未直接关联到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利益,也未使每个公民都感到担忧、恐惧或焦虑。
(二)公共性交之冒犯行为容易得到公众的宽容
某种行为除了具有公共性,还需要满足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宽容或宽恕这一条件,只有这样才符合不法性原则的要求。至于公开性交行为,除了给在场的观众带去各种不愉快的复杂心理体验、以及令人讨厌的主观精神感觉状态之外,还会给自愿停留观看的现场观众或网络观众带去性愉悦感、性满足感、感官刺激等令人爽快的心理体验,因而这种行为是可以得到对性持开放或渴求态度的社会成员的宽恕、宽容,甚至是悦纳欣赏。比如欲火中烧的成年男女、男男性行为渴求者或者男同性恋者,深夜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公园厕所中或私人轿车里,自以为秘密地实施像满足本能性欲的交媾行为,虽然这种违背了公共场合基本行为准则的行为有一定隐蔽秘密性,但还是会使察觉到此事的过路者产生尴尬、惶恐、恶心、厌恶、愤怒、肮脏、羞耻等消极心理状况,但对于那些也有这种“打野战”性癖好的人、或性欲萌发蠢动者、或专门为刺激公众眼球的新闻记者来说,这算是一件不期而遇的头等幸事。因而公开性交不仅不会使整个社会或社会绝大部分成员为此担忧、恐惧或焦虑,反而很容易得到很多理性公民的宽容。至于那些被公开性交所冒犯而产生各种负面、消极心理体验或日常生活之不方便的被冒犯者,根据心理学实验,被冒犯者也可以通过宽容或宽恕本身,直接、快速、持久地释放个体内部各种不良情绪,以此彻底地恢复心理平衡,脱离被冒犯的状态。[17]另外,社会学研究也直接表明这种行为不仅容易得到大多数公民的宽恕,甚至会得到一些公民的默许、支持或响应,例如有些公民会搜集这种公开性交行为发生地或时间段的各种信息,从而前去蹲点守候、专门偷窥这种行为或者自己找准机会也偷偷地实施这种行为。
六、冒犯原则中公开性交行为的犯罪化替代措施
如前所述,冒犯原则是指如果将某种冒犯行为入刑可能有效防止行为人以外的人受到严重冒犯,而且无其他方法能够以更小的价值成本产生同等的有效性,那么入刑可能是一种必要的途径。由此可见,冒犯原则在指导犯罪化时,除了有上文详细阐述的具体适用准则,而且还包含能实现刑罚目的的犯罪化替代措施,[18]即如果对某种冒犯行为采取犯罪化替代措施可以更小的价值成本产生同等的有效性的话,那么根据冒犯原则,不应将该行为入刑。
(一)治安处罚
要将公开性交之冒犯行为入罪,实施公开性交行为者主观上必须具有罪责性,即主观上必须具有罪过,否则这种罪名适用范围难以明晰,即使假如我国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肯定会面临存废之争。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公然猥亵罪,但该罪名存废本身存在很大争议,如今为限制其适用范围而要求主观意图是“供人意图观览”,并突出“刻意显露于公众”。[19]鉴于此,我们可以发现公开性交者的主观意图,是故意或过失地通过公开性交激起他人恶心、愤怒、羞耻、不安、恐惧等强烈负面情绪或消极心理感受。很明显,行为人并无实施侵害刑法中实质、真实法益的罪过意图,因而这种行为不应入刑,在应然层面上,可以考虑依据无需罪责性的治安处罚法对其以公然猥亵施以行政处罚。根据我国《治安处罚法》,违者一般被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治安处罚,这可以对公开性交者起到威慑作用,有效地防止今后公开性交行为再次严重冒犯他人。但对于公开性交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对行为人施加剥夺自由的监禁处罚,可能会有过于严苛之嫌。例如《德国刑法典》中公开性交是犯罪行为,但有学者建议删除或修改该条文,而只对行为人施加罚款,而不施以关押措施。[2]272-274
(二)人言可畏的社会道德舆论
社会共同体根据基本道德准则形成人言可畏的舆论洪流,在道德情感、个体人格评价体系上,早已当场将那对实施了遗臭万年丑事的“狗”男女贬低、鄙视、嘲笑、否定、谴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媒体时代,冒犯者将一直遭受道德报应,风流成性、不知检点、下流下贱、肮脏恶心等各种道德骂名将会伴随冒犯者一生,朴素的道德正义很容易被实现,同时这种道德正义也将持续不断地保持在彰显状态,无需公权力借用刑法实现刑法报应。辩证地看,被冒犯者在这种人言可畏的舆论洪流中,也可释放出因被冒犯而挑起的各种大量复杂的负面不良情绪,使不同个体可较快地宽恕冒犯者,个体负面消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可凭此得以舒缓、抚慰和平复。
(三)公开性交行为会自招一些非刑法的惩处
公开性交极易触犯众怒,激怒在场民众对二人实施肢体暴力、绑架和强行扭打等公民自我联合防卫行为或者其他仇恨犯罪行为,例如最近有新闻报道,因亲热声音过大,惹怒了隔壁房旅客,男方遭到近10人殴打。而如果二人在人烟较稀少地性交,更可能遭遇他人偷拍、盗窃衣物、敲诈勒索、殴打、抢劫、强奸、杀害等“惩处”。另外,如果二人被代表着大众良心的新闻媒体捕捉后,还会导致二人被人肉搜索,二人所有个人信息都会被曝光,个人生活将会进入特别紊乱直至完全失控的状态,网络暴力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二人自杀。[15]72-76
(四)公开性交者自愿公开道歉
假如二人成网红,经过长期遭受自责、内疚、悔恨、懊恼、羞愧、耻辱、绝望等负面情绪的折磨后,可能会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公开道歉、认错悔过,并请求原谅,以求重建与被冒犯者,即部分社会公众的关系。这种方式简单、成本低廉、社会影响也广泛深远,在安抚被冒犯者方面也很有效,还可直接使冒犯者与被冒犯者达成和解,而且,无论冒犯者最终得到宽恕与否,都不倾向于再次伤害被冒犯者。[17]这利于促进社会宽容和睦,那种相互厌恶、蔑视、仇恨等负面情绪相对抗的紧张情景也得以终止。
(五)其他犯罪化替代措施
还有一些社会制度处置冒犯者,例如根据劳动人事制度,冒犯者会因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拒招,或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也会因这种惊世骇俗的低俗淫秽行为被免职。另外,在强大婚姻家庭制度里,其父母或兄弟姐妹也可能会与其逐渐疏离甚至是断绝关系,或将其逐出家门。这些社会制度不仅成本更低,且比入刑这一防止冒犯行为的途径更有效。事实上,消解因被冒犯而产生的各种负面消极情绪体验的最有效方式是宗教制度,比如佛教中讲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20]372-373总之,在飞机上公开性交的极端冒犯个案中,如只运用冒犯原则的具体适用准则,这种行为有可能被犯罪化,但如果结合冒犯原则对犯罪化替代措施的要求,这种公开性交的行为,无论发生在飞机上,还是地铁车厢内,都没必要入刑。由此也可得知,冒犯原则内部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还需进一步的精炼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冒犯原则在犯罪化正当根据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9]1958且不被政治家根据政治处境利用或操控。[6]894-896
[1]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 (第2卷):对他人的冒犯[M].方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Tatjana H rnle.Offensive Behavior and German Penal Law [J].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2001, (5):255-278.
[3] Joel Feinberg.Offense to Others: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方泉.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兼评乔尔·范伯格的限制自由原则 [J].法学,2012,(8):111-121.
[5] Michael D.Bayles.Book Review:Offense to Others: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by Joel Feinberg"[J].Law and Philosophy,1986,(2):113-120.
[6] Harlon L.Dalton."Disgust"and Punishment,Book Review:Offense to Others: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J].Yale Law of Journal,1987,(4):881 -913.
[7] Thomas So/irk Petersen.No Offense!On the Offense Principle and Some New Challenges[J].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2016,(10):355-365.
[8] Peter Jones.Religious Belief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Is Offensiveness Really the Issue? [J].Res Publica,2011.(17):75-90.
[9] Robert Amdur.Book Review:Harm,Offense,and the Limits of Liberty[J].Harvard Law Review,1985.(98):1946-1959.
[10] David W.Shoemaker."Dirty Words"and the Offense Principle[J].Law and Philosophy,2000,(19):545-584.
[11]杨春然.冒犯型犯罪的根据:伤害行为对法益保护原则的一次超越——兼论犯罪的本质 [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2):33-40.
[12]郑玉双.为犯罪化寻找道德根基——评范伯格的《刑法的道德界限》 [J].政法论坛,2016, (2):183-191.
[13]劳东燕.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 [J].中外法学,2008,(3):399-418.
[14]李银河.中国当代性行为法律批判 [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1):21-31.
[15] Sean Hennelly.Public Space,Public Morality: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Sex in Public Places[J].Liverpool Law Review,(2010),31:69-91.
[16] A.P.Simester,Andreas von Hirsch.Crimes,Harms and Wrongs,On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isation[M].Hart Publishing,2011.
[17]张田,傅宏,薛艳. “得寸进尺”还是“适可而止”: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 [J].心理科学,2016,(1):116-123.
[18]李正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根据思考 [J].政法论坛,2017,(1):61-73.
[19]陈国坤.大陆与台湾地区妨害风化犯罪比较探析[J].西部法学评论,2012,(2):75-85.
[20]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Offense Principle and Legitimacy of Criminalization Principle-Taking Public Sexual Act as an Example
Hu Sha
(School of Law,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0,China)
In the liberalism context of legitimacy of criminalization principle,the obscene public sexual act is a kind of blatant extreme offensive behavior,which makes the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extremely disgusting,outraged,ashamed,shocked and agitated or satisfies the extreme offense behavior of peeking the privacy and lust.The offense principle,as different,separated and independent from harm principle,which is another kind of legitimacy of criminalization principle specially providing the rational f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extreme offensive behavior.In addition,it has delicate mediating principle and strong applicability.Comparatively speaking,we shall not regard the harm principle and wrongdoing principle as the rational choice f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ublic sexual act.In addition,the criminalization of public sexual act is also required to meet with the last resort principle contained in the offense principle.
offensive behavior;public sexual act;offense principle;legitimacy of criminalization principle;harm principle
DF626
A
1009-3745(2017)05-0053-11
2017-07-25
胡莎 (1988-),女,湖北仙桃人,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林 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