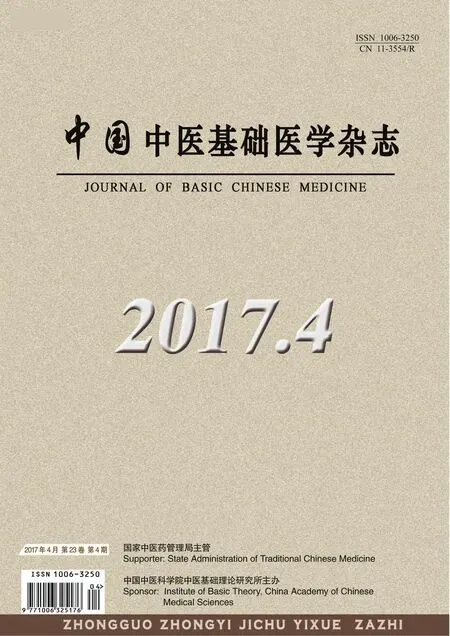针灸治疗面瘫的实验研究概况❋
2017-01-16张二超李晓燕刘志丹
张二超,李晓燕,刘志丹△
(1.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上海 201999; 2.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南京 210046)
【综述】
针灸治疗面瘫的实验研究概况❋
张二超1,2,李晓燕1,刘志丹1△
(1.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上海 201999; 2.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南京 210046)
面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最适宜针灸治疗的病种之一,也是针灸科就诊量较大、最主要的几个病种之一。针灸治疗面瘫有悠久的历史、系统的理论及成熟的临床实践。故旨在探讨近10年来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瘫的实验研究进展,从解剖形态学机制、神经电生理学、病毒学、血流动力学等方面进行综述。针灸在治疗周围性面瘫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疗效,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针灸;周围性面瘫;实验;综述
面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最适宜针灸治疗的病种之一,在中国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针灸科,是就诊量较大、最主要的几个病种之一。针灸治疗面瘫有悠久的历史、系统的理论及成熟的临床实践。尽管国内有些随机对照研究及系统评价认为针灸有效[1],但从世界范围看,该结论尚缺乏强有力的循证医学支持[2-9]。这主要与既往的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学缺陷有关,并不能完全否定针灸的临床疗效。
因此要为针灸治疗有效性提供依据,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实验的角度解释其内在的生理、神经生物学机理。为此,本文综合、梳理了现有实验研究报道,从解剖形态学、神经电生理学、病毒学、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综合评述此领域的研究概况。
1 解剖形态学机制
面瘫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显著的面神经解剖形态学改变。动物实验研究发现,面神经局部缺血导致面神经核细胞超微结构[10]和面神经纤维轴索[11]发生明显的病理变化。在游离家兔面神经并破坏其外周血管系制成的面瘫模型中,研究者发现,面神经局部缺血导致面神经核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如其轻者,细胞内微丝增生、核周粗面内质网扩张,线粒体空泡样变性等;其重者,面神经核细胞可见核膜溶解,界限不清,核内出现包含体等。在以上相同的面瘫模型中,面神经局部缺血导致面神经纤维轴索发生显著的病理变化。实验后第2周轴索内微丝呈现出增生性改变,第3周以轴索内微丝破坏、线粒体肿胀变性为主,第4周以轴索溶解为主。
雪旺细胞有许多神经递质的受体和离子通道,对神经系统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12]。研究显示,电针可以减轻神经纤维周围充血、水肿及神经根纤维脱髓鞘变,并使雪旺细胞结构保持基本正常[13]。睫状神经营养因子(ciliary neurotrophic factor, CNTF)主要存在于周围神经中,在神经损伤时由雪旺细胞释放,其有助于髓鞘的生成及再生。研究显示,针灸可以改善雪旺细胞的功能状态,使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 NGF)的分泌量增加[14];针灸可以提高CNTF受体的表达,继而促进面神经损伤的修复[15]。另有研究[16]发现,针刺可提高表情肌组织中CNTF的产量,使雪旺细胞CNTF及其受体产量提高,从而维持损伤的神经元存活和促进轴突再生。因此,CNTF在面神经损伤修复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针灸不仅影响雪旺细胞,也对某些特定的蛋白产生影响。线栓法造成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模型[17]后发现,针刺可以促进缺血性大鼠髓鞘碱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 MBP)基因的转录。针刺组的脑MBP m RNA 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高,在造模后第1天、第3天、第5天、第7天均明显高于模型组,说明针刺治疗能明显激活脑的自然恢复机制,或者可能通过激活某条信号传导通路来增加 MBP基因的转录,使MBP合成增多,从而促进髓鞘的再生。
2 神经电生理机制
面瘫的病理性生理改变主要是神经水肿、脱髓鞘改变和神经变性,进而影响神经纤维的生物电传导。有研究[18]认为,生理性传导阻滞可能是由于髓鞘板层结构松散,使轴突流内外离子失平衡,造成使神经兴奋性受抑制的离子浓度增加,短暂性地降低神经兴奋性,经过短时间恢复离子平衡,使神经兴奋性恢复正常。动物实验研究证实,针刺可以提高周围性面瘫大鼠[19]和兔[20]的面神经传导速度。大鼠压迫造模后发现,针刺能够提高面瘫大鼠发展期的面神经传导速度。运用神经卡压法造成兔左侧面神经损伤的模型后发现,针刺后左侧面神经的传导速度明显增快,并且电针组面神经核内神经生长因子蛋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蛋白、BDNF mRNA 及其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模型组,从而增强对面神经的营养,促进面神经轴突的生长,对面神经损伤后再生修复起作用。
大量的临床实践发现,粗针神道穴(第5胸椎棘突下凹陷中)平刺治疗面瘫的疗效显著[21-25]。实验研究[26]表明,粗针平刺神道穴可以改善周围性面瘫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面神经兴奋阈和面神经电图波幅以及能够明显提高周围性面瘫大鼠的肌电图:实验后第1周与造模组比较无明显提高;第2周粗针组明显高于造模组的2倍左右。以上研究表明,针刺在神经电生理方面对周围性面瘫具有特定的影响,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3 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机制
面神经麻痹可能与多种病毒相关,其中Ι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HSV-Ι)的感染可能是主要原因[27]。但Pitkäranta A等[28]提出,周围性面瘫并非全部为病毒感染所致。研究者[29]通过小鼠造模后发现,无论小鼠有无面瘫,在周围和中枢神经都可能出现HSV DNA阳性,说明病毒对神经系统的侵犯并非是发生面瘫的惟一条件。
目前国内还倾向于认为,HSV-Ι可能会诱发并加重周围性面瘫,其病理学基础可能是病毒感染后引起的面神经脱髓鞘性改变。动物实验[30]发现,在小鼠腮腺后上缘面神经内滴加HSV-Ι型病毒液造成的面瘫模型中,针刺合谷、颊车等穴,运用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Ι型单纯疱疹病毒DNA发现,实验后第3天、第7天、第14天与模型组比较,针刺组面神经麻痹小鼠膝状神经节细胞中均有降低。另外,在本次实验中通过观察电针对NF-κB信号途径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针刺组面神经麻痹小鼠面神经元和雪旺细胞NF-κB mRNA表达极显著降低,表明电针可以有效抑制NF-κB的活化,并减少其数量,从而达到抑制病毒复制、减轻感染程度的目的。
4 血流动力学机制
有研究[31]认为,针刺能够调控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内皮素与微循环之间的关系,而血浆内皮素产生的血管收缩或血液动力学改变与面神经麻痹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通过改良血管栓塞法建立大鼠缺血性面瘫模型[32]后发现,粗针大鼠神道穴能够有效促进缺血性面瘫大鼠的恢复,其产生疗效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组织低氧 诱导因子- 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1α)的表达及血清一氧化氮、内皮素含量。如治疗第7天、第14天与正常组比较,HIF-1α均呈现出增长趋势。另有研究[34]表明,粗针督脉平刺后,大鼠口唇血流灌注量值不断降低最后接近正常:治疗后第1周大鼠口唇血流速度与西药治疗组比较降低幅度较小,第2周大鼠口唇血流速度比西药治疗组显著降低最后接近造模前水平,这说明针刺对周围性面瘫大鼠血液动力学有正向影响,这也可能是治疗面瘫病的机制之一。
5 讨论
综上,相关研究已经在解剖形态学、神经电生理学、病毒学、血流动力学等方面提供了针灸治疗面瘫的部分机制,即针灸是如何对面神经结构、功能产生影响的。但面神经局部缺血与面神经传导速度的提高是否存在某种负反馈效应,目前相关实验研究报道不多,其具体机理需要深入研究。神经电生理检查虽然可以量化,但是人为的干扰仍然无法排除,容易出现假阳性等缺陷,因此如何克服电生理检查的欠精准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病毒感染方面,NF-κB信号途径的引入很好地解释了针刺抑制HSV-Ι病毒复制的作用途径,但是如何深入了解针灸对NF-κB信号途径的影响,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难点。
另外,在神经免疫学方面,免疫机能失衡可能是本病的发病机制之一,但相关研究尚不多见。目前还主要停留在研究某个单一细胞与面瘫的关系上。如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和体液免疫应答,可能在周围性面瘫疾病的发生演进方面起关键作用[34-36]。自身免疫T细胞的神经保护作用主要可能是拯救逃脱原发性损伤的濒危神经元,从而减轻损伤引起的继发性损害[37]。CD4+T细胞可以保护裸鼠面运动神经元(facial motoneuron, FMN)数量,使其数量达到野生型的水平[38]。神经损伤后第2周,适度的T细胞活化能够提高面瘫小鼠肠系膜淋巴结T细胞上CD69+的表达,通过机体适度的T细胞活化这一免疫应答,启动全身免疫调控网络的监视机制,而异常机体的过高/过低的T细胞活化水平,则对机体意味着神经病理过程的发生,即自身免疫/免疫缺陷[39]。国内研究也发现,面神经轴切损伤第3天,颈部引流淋巴结存在T细胞活化并上调,第2周肠系膜淋巴结也出现低水平的T细胞活化,表明急性期的局部免疫应答向全身免疫应答方向转化[40]。
机体免疫应答的某个或某些环节的改变都有可能是面瘫发生的因素之一。目前尚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是何种免疫应答机制参与面瘫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针刺是否可以改善或提高面瘫患者或实验动物的免疫应答而达到治病作用。因此,具体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1] 李瑛,梁繁荣.用循证医学方法评价针灸治疗面瘫的临床疗效[J].中国针灸,2002,22(4):265-267.
[2] 李宁,张俊,彭先镜.针灸治疗面瘫的随机对照研究文献质量评价[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4):49-51.
[3] ZHOU M,HE L,ZHOU D, et al. Acupuncture for Bell′s palsy[J].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2009,15(7):759-764.
[4] 何俐,周沐科,周东,等.针灸治疗Bell′s面瘫疗效的系统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5,5(2):106-109.
[5] 徐秀梅,徐彦龙,杜元灏.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现代文献计量分析与评价[J].江西中医药,2010,41(325):60-63.
[6] KIM JI, LEE MS, CHOI TY, et al. Acupuncture for Bell′s pals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2,18(1):48-55.
[7] 潘江,章薇,陈武善,等.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急性期)的系统评价[J].针灸临床杂志,2011,27(4):60-63.
[8] 陈璐,李素荷,曾侠一,等.针刺治疗急性期贝尔麻痹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中医杂志,2012,53(22):1921-1926.
[9] CUMBERWORTH A, MABVUURE NT, NORRIS JM, et al. Is acupuncture beneficial in the treatmentof Bell′s pals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2012,10(6):310-312.
[10] 薛景凤,王笑茹,张炎.面神经局部缺血对面神经核超微结构的影响[J].解剖学杂志,2005,28(5):549-551.
[11] 薛景凤,李健,王笑茹.面神经局部缺血对其超微结构的影响[J].解剖学杂志,2008,31(6):838-840.
[12] 白丽敏,李亚东.神经解剖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17.
[13] 吴耀持,张彩红.针刺对腰神经根压迫症模型大鼠受损腰神经根超微结构及炎性介质的影响[J].上海针灸杂志,2003,22(9):32-34.
[14] 佟帅.针刺治疗周围神经损伤机理的实验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2.
[15] 孙运花,李瑛,张薇,等.急性期电针对面神经损伤模型兔CNTFR表达的影响[J].辽宁中医杂志,2011,38(11):2271-2272.
[16] 牙祖蒙,王建华,李忠禹,等.家兔面神经损伤后穴位针刺对神经营养因子及其受体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00,6(4):234-236.
[17] 段建钢,刘鸣.针刺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MBP基因表达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9,24(3):240-243.
[18] MAY M, SCHLAEPFER WM. Bell′s palsy and the chorda tympani nerve: a clinical and electron microscopic study[J].The Laryngoscope,1975, 85(12):1957-1975.
[19] 张建明.针刺对周围性面瘫大鼠面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J].中国社区医师,2008,10(19):134.
[20] 卫彦.不同针刺参数对实验性周围性面瘫兔面神经损伤再生修复影响的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6.
[21] 宣丽华,王丽莉,侯群,等.粗针神道穴平刺促进面神经炎面肌功能恢复的研究[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7,14(1):6.
[22] 宣丽华,虞彬艳,高宏,等.粗针神道穴平刺治疗面神经炎临床多中心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1):18-20.
[23] 陈君,宣丽华.粗针神道穴平刺对周围性面瘫面神经电生理的影响[C].浙江:浙江省针灸学会,2013:60-63.
[24] 虞彬艳,宣丽华,吴翔,等.粗针神道穴平刺与传统针刺治疗不同损伤程度面神经炎的比较研究[J].中国中医药科技,2014,19(2):99-101.
[25] 万意佳,宣丽华.粗针神道穴平刺与传统针刺治疗不同病程面神经炎疗效比较[J].上海针灸杂志,2015,34(2):152-154.
[26] 陈君. 粗针神道穴平刺对周围性面瘫大鼠面神经电生理的影响[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14(1):17-19.
[27] 史文峰.贝尔麻痹的病因学说和治疗方法回顾[J].中国医药指南,2008,6(1):3-5.
[29] 刘稳.单纯疱疹病毒Ι型致小鼠面神经麻痹及病毒性动物模型中面神经[D].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6.
[30] 唐宏智.针刺治疗病毒性面神经麻痹小鼠的NF-κB信号通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4.
[31] 郭飞,阮春鑫,马艳,等.针药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瘫后遗症期的疗效及对血浆内皮素影响的观察[J].浙江中医杂志,2010,45(11):791.
[32] 虞彬艳,宣丽华,吕善广,等.粗针督脉平刺治疗缺血性面瘫大鼠的机制探讨[J].上海针灸,2015,34(3):256-259.
[33] 吕善广,宣丽华.粗针督脉平刺对周围性面瘫大鼠口唇血流速度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32(5):1123-1124.
[34] IEZZI G,SCHEIDEGGER D, LANZAVECCHIA A.Migration and Function of Antigen-Primed Nonpolarized T Lymphocytes in Vivo[J].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01,193(8):987-994.
[35] ARMSTRONG BD, ABAD C, CHHITH S, et al. Impairment of axotomy-induced pituitary adenylyl cyclase-activating peptide gene expression in T helper 2 lymphocyte-deficient mice[J].Neuroreport, 2006,17(3):309-312.
[36] JONES KJ, SERPE CJ, BYRAM SC, et al. Role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the maintenance of mouse facial motoneuron viability after nerve injury[J].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005,19(1):12-19.
[37] SCHWARTZ M. Beneficial Autoimmune T Cells and Posttraumatic Neuroprotection [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917(1): 341-347.
[38] 全世明,高志强,等. CD4+T 细胞移植对裸鼠面瘫模型面运动神经元存活的影响[D].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7.
[39] RAIVICH G, JONES LL, KLOSS CU, et al. Immune surveillance in the injured nervous system: T-lymphocytes invade the axotomized mouse facial motor nucleus and aggregate around sites of neuronal degeneration. [J].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998, 18 (15):5804- 5816.
[40] 全世明, 高志强, 葛平江,等.小鼠面神经损伤急性期T细胞 CD69 表达的研究[J].中华耳科学杂志,2007, 5(1):89-93.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药科研基金项目(2014LQ016A)-利用核磁共振和神经电生理技术研究急性期电针介入治疗贝尔面瘫的临床机制;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杏林新星计划项目(ZY3-RCPY-2-2041);上海市宝山区卫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项目(bswsyq-2014-A05)
张二超(1990-),男,江苏宿迁人,住院医师,医学本科,从事针灸临床机制研究。
△通讯作者:刘志丹(1981-),男,主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针灸治病机理研究,E-mail:liuzhidan @vip.163.com。
R246.8
A
1006-3250(2017)04-0583-03
2016-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