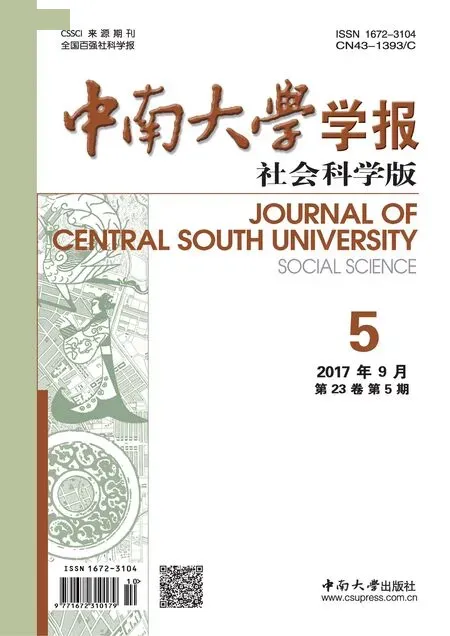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探论
2017-01-12黄珍德
黄珍德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探论
黄珍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国民党开始训政后,以地方自治作为训政实施的中心工作,为此制订了较完备的地方自治制度,主要是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单位和层级、自治组织的构成与职权、自治事务的内容、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地方自治制度尽管在自治单位、财政等方面与孙中山的理论有所背离,但大致遵从了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通过地方自治发展民权和建设地方的构想。然而,自治制度不能在地方有效落实、自治事务的范围过广、缺少独立的自治财政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并严重制约了各县办理自治的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训政
1928年北伐基本完成后,国民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根据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国民党在确立和强化以党治国政治体制的同时,陆续制定了各项训政时期的政策,将地方自治作为实施训政的基础工作和重点内容。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欲求直接民权能够训练成功,使真正民意能够表现,并且能够在深厚的基础上度过了训政时期,而达到宪政,那末,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实现总理所详细规定的地方自治了。”[1](618)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宣言明确提出:“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实施地方自治,为训政时期主要工作。”[2](124)为此,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许多涉及地方自治的法规,如《县组织法》《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县组织法施行法》等等,从而制订了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制度。根据这些制度,各县纷纷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区和乡镇自治组织,举办调查户口、修筑道路、设立警卫等自治事务。
对于民国地方自治问题,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关于其理论和制度渊源、不同时期地方自治政策以及不同地区的地方自治实践,都有学术成果论及[3−7]。不过,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而言尚有不少可议之处。比如,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颁布的《县组织法》,地方自治制度主要由自治的单位和层级、自治组织的构成与职权、自治事务的内容、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等因素构成,而它们均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即试图对上述构成因素进行梳理,着重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并见微知著,从一个角度检视国民党实施训政的社会成效。
一、自治单位和层级
在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中,县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他指出:“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8](290)他提出了实行民治、建设民国的方略,即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五权分立、国民大会。其中分县自治是第一步和实现后三者的基础与前提,强调中华民国的建设“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9](35−36)。因此,他认为,训政时期“除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10](497),途径是“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11](103)。孙中山以县为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缘于他的直接民权思想。孙中山民权思想虽然主要来自于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但他反对中国在推翻专制制度后采用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代议制下的间接民主。他认为在代议政体下面,国民仅享有一种权利,即代议权,“不是真正民权”。只有当国民享有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的直接民权时,“始可谓之行民治”[12](26−27)。他明确指出:“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美、英、法虽主张民权主义,仍不是直接民权。兄弟底民权主义,系采瑞士底民权主义,即直接底民权主义。”[13](476)他说:“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终落于人后。故今后国民,当奋振全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俾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14](323)以县为单位进行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乡区域之分”,但是“范围有限,凡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而且“其范围狭小,人民辨别较易,以其身家攸关,公共事业之善否与是非”[8](290)。故孙中山坚持以县作为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
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声明恪遵孙中山遗教,以县为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但1928年9月所公布的《县组织法》及1929年6月所修订的新《县组织法》均没有明确县的自治地位,明文规定:“县设县政府,于省 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15](90)显然,这里仍然将县视为代表国家对地方进行管理的政府机关,尽管提出了一个“监督地方自治事务”的权限,但与地方自治的单位还是两码事。故在《县组织法施行法》中只有县以下区长、乡镇长和闾长、邻长民选,即使当一县完成筹备而成为“完全自治之县”,也没有提到县长民选。对于此点,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第二次临时全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推进地方自治案》也指出:“《县组织法》第三条之规定……以全县行政与地方自治相对列,且与前者名之曰‘处理’,后者名之曰‘监督’,一若前者为主目的,而后者反为副目的,殊与以县为自治单位之旨相抵触。”[16](13−14)
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而言,地方自治主要属于县以下的区、乡镇、闾、邻。最初,《县组织法》仿效山西村制,将县以下分为区、村里、闾、邻四级,规定:县内百户以上之乡村为村,百户以上之市镇为里,每区至少由二十村里组成。村里以二十五户为闾,五户为邻。《县组织法》实施后不到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修订。1929年6月修订的新《县组织法》颁布。与旧法相比,新《县组织法》最大的变化是将村里改为乡镇,正式形成了县以下区、乡镇、闾、邻四级,其中五户为邻,五邻为闾,百户以上之乡村为乡,街市为镇,每区由20至50不等的乡镇组成。区长、乡镇长和闾长、邻长均为民选产生,负责各管地方的自治事务①。
从表面上看,根据《县组织法》,县以下的地方自治制度包括了区、乡镇、闾、邻四级。不过,区和乡镇作为地方自治的两个单位是没有疑问的,但闾、邻是不是也同时纳入自治层级,则是个较有争议的问题。当时一些学者称县以下地方自治制度分为区、乡镇、闾、邻四级,魏光奇认为这种说法失之笼统。他指出:从法律规定和实际实行情况看,区和乡镇有固定地域、专职首领人员和常设机构,存在形态较为完整的自治行政,而闾和邻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是一种编民组织[5](187)。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民国时期十分熟悉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制度的杨开道就撰文说:县以下乡村自治只有区和乡镇两级,“至于闾、邻两级,都是名誉阶级;在外国固然没有,在中国也不过是聊以备位,没有多大的关系”[17]。
二、自治组织
地方自治是地方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或团体来实现的,因此,自治组织或团体的产生、组成和行使相应的自治职能至关重要。孙中山生前就十分重视自治组织在地方自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介绍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时,他指出:“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18](491)在介绍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时,他亦着力于介绍地方自治机关及其运作[14]。他甚至认为“自治团体愈多而愈佳”[19](37)。不过,孙中山有关自治组织的论述往往只是从原则上提出自治组织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在地方自治中居于首要地位,至于各级自治组织的组成、职权、行政运作等问题均没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国民党开始训政后,以山西村制为蓝本,明确了自治组织的构成和职权。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制订的相关法规,训政时期区和乡镇自治组织主要由居民大会、自治公所、监察委员会组成。居民大会包括区民大会和乡镇民大会,前者由区长每年召集一次,后者由乡镇长每年召集两次。如果区长和乡镇长遭到纠举,则由区和乡镇监察委员会召集。居民大会的主要职责有:选举及罢免各该区长、乡镇长和区、乡镇监察委员,以及区公所和乡镇公所其他职员;制定和修正各该地方自治公约;审议上级交议事项、区公所和乡镇公所提议事项及有关地方自治的单行规程;议决财政预算决算。自治公所包括区公所和乡镇公所,分别设区长一人和乡镇长一人、副乡镇长两人,均由区民和乡镇民选举产生。自治公所的主要职责有:管理和执行本区、乡镇法定或区民大会、乡镇民大会决议交办之各项自治事务;将任期内之经过情形以书面报告区民大会、乡镇民大会;在区民大会、乡镇民大会上提出上年度财政决算和次年度财政预算;对于区和乡镇调解委员会不能调解的事项,根据调解委员会报告呈报上级,并函报有关司法机关等。监察委员会包括区和乡镇两级,监察委员均由区民和乡镇民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有二:一是监察区和乡镇财政,可以随时调查区和乡镇公所的账目及款产事宜,对于区和乡镇公所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当的地方,区和乡镇监察委员会可以随时呈报给上级纠正;二是监察区长和乡镇长的作为,一旦发现区长和乡镇长存在违法失职之处,可以纠举并自行召集区民大会和乡镇民大会[20]。
一些论著称区和乡镇自治组织还包括调解委员会。《区自治施行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确实有对调解委员会的设置,规定区和乡镇分别设置调解委员会。乡镇调解委员会负责办理本乡镇民事调解事项和依法得撤回告诉的刑事调解事项;对于乡镇调解委员会未曾调解或不能调解的民事和刑事调解事项,则由区调解委员会办理。调解委员选举产生,区长、区监察委员和正副乡镇长、乡镇监察委员均不得被选。但是,调解委员会实际上是自治公所附设的下属组织,并不具独立性,故在《区自治施行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中都没有和监察委员会一样单列。除调解委员会外,区公所还附设高级小学和国民补习学校及国民训练讲堂,乡镇公所附设初级小学和国民补习学校及国民训练讲堂,分别负责各该地方的教育事业。
综上,区和乡镇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居民大会、自治公所和监察委员会三种,相当于议决、行政和监察三权的分立。其中,居民大会权力最高,地方自治的所有重要事项均由居民大会审议和决定,其拥有的职权很大,包括了选举和罢免自治首领人员、制定和修正地方自治公约、审议和决定地方自治事务等,是地方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从与自治公所的关系来看,自治公所相当于居民大会的执行机构,根据居民大会的决议举办相关的自治事项。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于区和乡镇自治组织的规定应该说尚属不错,组织较为严密,议决、行政和监察等三权分立,地方居民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政权。而且在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的严催赶办下,各县大多能够按照上述制度规定办理自治,不管进展和成效如何,至少形式上基本都能认真、积极地开展。到1934年底,各省已经基本完成了所属各县划分自治区和乡镇区域以及编定闾、邻的工作,并召集乡镇居民大会选举正副乡长、镇长和成立乡镇自治公所,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河北、广东、安徽、江西、山东、河南、云南、甘肃、青海、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所属多数县成立了区公所,其中广东各县的区公所委员是召集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各省所属各县的区长基本上是由县长委任产生[21]。当然,自治实效是要大打折扣的,由于社会环境的掣肘和自治经费的不足,“规定的不能行之于事实”,多数地方的自治组织不能行使各自的职权,以至于多流于形式,有名无实[22]。
除了区和乡镇自治组织外,《县组织法》还规定了县一级自治组织——县参议会——的组成和职权。县参议会由县参议员组成,规定以所属各区为选举区,乡镇为投票区,在乡镇公所设投票所,投票完毕送到区公所,由区长在区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开票,票数多者若干人当选为该选举区参议员。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1/3。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县参议会既是县的议会机关,又是县自治机关,职权主要包括议决县财政预算决算及募债事项、议决县单行规则、建议县政兴革事项、审议县长交议事项等。不过,如前文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于县地位的规定模糊,没有明确县作为地方自治的单位,因此,全面抗战前大部分县并没有经过选举成立县参议会,县自治实际上流于空文,毋庸赘述②。至于闾、邻,因没有固定地域,不能算是地方自治的单位,尽管闾、邻分别召开居民会议选举闾长、邻长,但闾长、邻长的主要职权是“襄助乡长或镇长办理主管之乡公所或镇公所事务”[20](158),没有类似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的常设自治组织,因而不存在形态完整的自治行政。
三、自治事务
对于训政时期地方自治应举办的事务,孙中山在1920年写成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进行过规定,认为包括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6项,并且提出上述6项事务“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如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此外,更有对于自治区域以外之运输、交易,当由自治机关设专局以经营之”[23](220−224)。按照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地方自治的构想,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自治事务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除了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等6项内容以外,还包括其他很多事项。根据《区自治施行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各级自治组织完成后应办理的自治事务包括户口调查、土地调查、建筑公共设施、举办教育、办理保卫、推进国民体育和卫生、发展农工商业和垦牧渔猎、植树造林、组织合作社、风俗改良、举办救济、确定自治经费等等,范围极其广泛,除了军政、外交、司法等方面以外,凡是地方上的事务几乎统统包括在内。
自治事务的范围如此广泛,当然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是可以增强国民的主人翁意识,推动地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有弊的地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无所不包和追求规模宏大,内容十分繁多和复杂,必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合和协作、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充足的人才和经费以及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循序渐进地推进。而这些条件在当时都不具备。时间方面,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严格的期限,要求从1929年开始至1934年结束,6年内实施完成。这显得过于急促,不可能按期完成,严催赶办的结果往往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流于形式。后来的实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像公安保卫、经济建设、合作事业、交通设施等本来就应该交由相关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去实施,就组织单薄、人员不足和缺乏必要自治经费支持的自治组织来说,根本没有条件去实施如此之繁多和复杂的所谓自治事务。对此,杨开道形容为“贪多务得,并蓄兼收”的病态,以为自治事务应当作轻重缓急之区分和循序渐进地办理,各级自治组织首先应“把几件最重要、最根本的事业办好,然后再去办理其他的工作”,如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所规定的地方自治事务,尤其是清户口、立机关、设学校,待这些事务办有成绩后再办理农业改良、修筑道路、合作事业等[24]。此论颇具见地。
四、自治经费
自治财政是地方自治的基础。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地方自治事业是难有成绩的,注定无从建树。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在设计地方自治制度时,特别规定了各县办理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其中,区自治的经费来源有4项,分别是区公产及公款之孳息、区公营业之纯利、依法赋与之自治款项和省县补助金;乡镇自治的经费来源有5项,分别是乡镇公产及公款之孳息、乡镇公营业之纯利、依法赋与之自治款项、县区补助和特别捐[21]。从上述规定来看,地方自治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为公产公款和公营业,二为政府拨给和补助,三为特别捐,似乎体现了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的宗旨,与地方自治的精神相符。但实际上,各县办理自治普遍存在着经费严重短绌的问题。
公产及公款之孳息被列为地方自治的第一个经费来源。由于地区差异,各县公产公款不尽相同,以寺产、族产为多,要么由县政府掌握移作他用,要么为寺庙、宗族等控制,区公所和乡镇公所难以过问。至于公营业之纯利,由于各级自治组织尚属筹备或草创,各项自治事务繁重,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都较为困难,“绝无能力举办公营业,安得有纯利收入”,故同公产公款之孳息一样,“实同虚列”[25]。
接下来是县政府的拨给和补助,这要依赖于县财政的多寡程度。本来,孙中山生前意识到了自治经费问题。故《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训政时期“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要”,“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 十”[26](128)。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的《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只是将中央和省的收入标准进行划分,至于县财政,要求各省“自定之”[27](207−208)。由于当时省财政普遍紧张,各省“不得不将仅有财源紧紧握着”,规定所属各县财税收入除留支极少数作为县行政和司法费用外几乎全部缴交给省库。处于下级的县财政从而“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县库匮乏成为全国范围的普遍问题[28](69)。财政困窘,但作为“推行政务的枢纽”,县政府需要完成的事务层出不穷,“不管是教育、民政、建设、公安、卫生、实业种种,每不管是中央各部院的行政计划,或是省政府各厅处的施政方针,负责执行者,总是县政府”,县政建设经费因此膨胀,结果就是“财源困窘,经费膨胀,两面夹攻,县地方财政之陷于焦头烂额”,对于区和乡镇自治的拨给与补助微乎其微就可想而知了[29]。
上述数种经费可望而不可得,各地自治经费实际上就只能依靠特别捐了。所谓特别捐,就是以办理自治为名抽捐加税,就地筹措自治经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未明确特别捐的对象、范围和额度,仅要求各地依照地方情形分别筹措,因此各地抽收自治捐税的种类和方式五花八门,数量不一,流弊百出,不少地方“苛细夹杂,名目繁多”,甚至到了“横抽滥捐已骇人听闻”的地步[3]。这必然会增加一般民众的经济 负担,使一般民众“未得自治之益,而先蒙自治之 害”[30]。
关于各县筹措地方自治经费的实际情形,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的高秉坊总结各省的调查上报材料,指出:
各省自治经费中关于区公所的一部分,大都以田赋等附加为主要来源,由省款补助者占少数,而补助数额亦甚微;间有就地自筹者。至乡镇公所经费,除少数例外,几至多是就地摊派。但区公所经费中亦有名义上虽已确定来源,而实际则因财政支绌,分配为难,仍不得不另想妙法,更有因不能如数征收或省政府虽决定补助,而实际并未给予实惠等种种原因,发生两重困难,就是(一)要办无钱;(二)要钱难筹。其他边远贫瘠之省,如甘肃区公所自征经费,竟有超过规定额数倍以至十倍者,贵州所征杂捐达二十种之多。每县多者六、七种,少者亦有二、三种,收入之用于自治者无多,而人民受累实属不浅,为害颇巨,亟宜革除[29]。
这段话掷地有声地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缺少独立而充足的自治财政。其后果将是两个:一是经费短绌,各级自治组织穷于筹款,自治难有成绩,甚至徒有虚名;二是抽捐加税,就地筹措自治经费,将大大增加农民负担,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对。
五、结语
综上关于地方自治的单位和层级、自治组织的构成与职权、自治事务、经费来源与筹措等问题的梳理,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总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较为完备。尽管在自治单位、经费筹措等方面与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有所背离,但基本上遵从了孙中山关于训政时期通过地方自治发展民权和建设地方的构想。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在自治单位、组织、事务和经费等方面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尤其是缺少独立的自治财政,无疑将严重地制约各县举办地方自治的实践,而且相关的制度规定不能在地方落实更导致地方自治制度难有成效。
进而言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自治制度还存在着官办色彩浓厚的问题。根据《县组织法施行法》和《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县以下自治组织的设立总体上包括两个程序,即首先划分区、乡镇和闾、邻自治区域,训练训政人员,自上而下地先后组织县、区、乡镇自治筹备机关,然后由自治筹备机关举办调查户口、办理警卫、修筑道路等自治事务,指导和组织当地群众自下而上地先后选举闾长、邻长、正副乡镇长和区长,并分别设立乡镇公所和区公所等自治机关。可见,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办和自下而上的民选相结合的过程,但基本上以前一个程序为主,从制度设计到自治筹备机关的成立再到各项实际筹备工作的进行,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县政府及其委派的办理自治的职员。自治官办的情形与孙中山“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31](324)的地方自治构想背道而驰。本来,孙中山出于对民众民主素质低下的忧虑,坚持训政的必要性和政府的作用,强调由政府“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从而预备宪政。但是,由政府“协助人民”自治与官办自治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依然肯定人民的主体地位,孙中山就曾明确提出“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 治”[32](67);后者则将政府置于自治的中心位置,实际是自治名义下的另类官治,从而会导致各县的自治实践流于形式。
注释:
① 1934年以后,有关县自治的层级和组织又有了新的变化。如1934年12月公布的《县自治法》取消了区的设置,县以下设乡镇、闾、邻三级,各级所含居民户数亦相应发生了变化。同年,保甲制开始向全国推广,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以上为乡镇,地方自治已经发生了变质。
② 广东是少有的例外省份之一,在1934年夏季时所有县都成立了参议会,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县自治组织。
[1]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荣孟源, 孙彩霞.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2] 中国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宣言[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3] 梁漱溟. 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M]. 济南: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1.
[4] 李德芳. 民国乡村自治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5] 魏光奇. 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 王兆刚. 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 周联合. 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8] 在“俄国皇后号”邮船上的谈话[C]//王耿雄, 等.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9] 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C]//王耿雄, 等. 孙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0]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5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1] 制定《建国大纲》宣言[C]//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等. 孙中山全集(第1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2]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6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5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3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5] 县组织法. 徐秀丽. 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6] 第三届中央第二次临时全会决议案[C]//荣孟源, 孙彩霞.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17] 杨开道. 农村自治的单位[J]. 农业周报, 1930(28): 721−725.
[18] 在上海与李宗黄的谈话[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4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9] 发扬民治说帖[C]//王耿雄, 等. 孙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0] 乡镇自治施行法[C]//徐秀丽. 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1] 内政部. 内政年鉴(民政篇)[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753−758.
[22] 赵如珩. 怎样实施地方自治[M]. 上海: 华通书局, 1934: 2−3.
[23] 地方自治实行法[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5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4] 杨开道.农村自治事业(续)[J]. 农业周报, 1930(37): 987−990.
[25] 《推进地方自治方案》草案[J]. 自治月刊, 1931, 2(1): 3−12.
[26]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C]//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等. 孙中山全集(第9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7] 国民政府通令照办之《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28] 朱博能. 田赋附加与县财政[C]//汗血月刊社. 新县政研究. 上海: 汗血书店, 1936.
[29] 高秉坊. 财政与地方自治[J]. 地方自治专刊, 1937, 1(1): 34−36.
[30] 中山县村治现状[J]. 村治, 1930, 1(11~12): 4−5.
[31]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8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2] 中国革命史[C]//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7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编辑: 苏慧]
On the local self-governing system at the early stages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UANG Zhend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When the Kuomintang (KMT) implemented the political tutelage,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as its central work unit,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stipulating complete self-governing system, including establishing local autonomous units and levels, their components and rights, contents of self-autonomous affairs, financial sources and monfy-raising. The local self-governing syste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departed partly from the theory of Sun Yat-sen in the units and financial sources of the self-governing, but generally complied with Sun Yat-sen’s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rights. However,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system had such fatal weaknesses as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too wide range of self-government affairs and the lack of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inevitably restricted the practice of self-government in each count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local self-governing system; political tutelage
K263
A
1672-3104(2017)05−0190−06
2017−03−28;
2017−05−0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战前中国的训政实施与社会变迁”(GD13CLS01)
黄珍德(1973−),男,湖北黄梅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