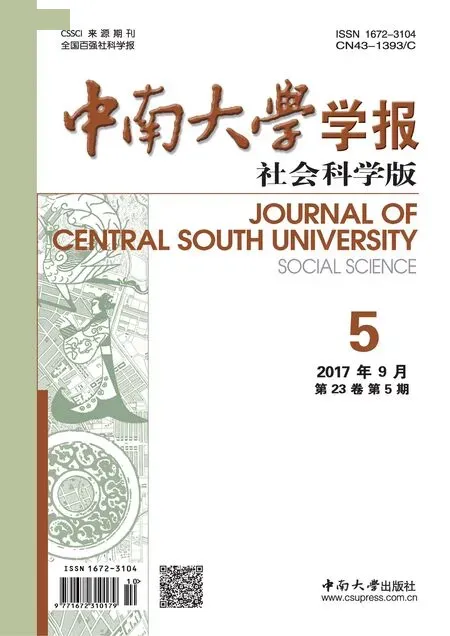论马克思民主观较熊彼特民主观的高位格品质
2017-01-12张卫良胡文根
张卫良,胡文根
论马克思民主观较熊彼特民主观的高位格品质
张卫良,胡文根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马克思民主观与熊彼特民主观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民主议题上两条完全不同的水道,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种民主观,有助于还原民主的实质,澄清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为确证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提供思路。从本质上说,熊彼特民主观是一种“经济政治学”民主观,马克思民主观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民主观,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秉持唯物史观与人民主体立场。熊彼特的民主观在方法论上以现代生产的经济技术形式抽空了民主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和人民主体立场;马克思民主观则始终秉持唯物史观与人民主体立场,故其在民主结论、民主起点、民主方法及民主场域上,较熊彼特民主观有着高位格的理论品质。而从实践层面考察,马克思民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模式较熊彼特民主观指导下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民主模式,在民主形式、民主对象与民主传播上也具备高位格的实践品质。
马克思民主观;熊彼特民主观;高位格;理论品质;实践品质
熊彼特民主观奠定了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方法论基础,即以能否建构精英主义的政治竞争选举程序,作为民主的唯一衡量尺度,较大程度地“回避”了古典民主理论中的“人民”概念不明、“人民权力”边界模糊、“人民统治”与“社会公意”并不完全匹配等问题,为反思与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民主理论的抽象性开辟了新的论域。因而,有舆论认为熊彼特民主观已经跳出了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辨,把民主从抽象领域成功带到了实证领域,不像古典民主理论那般在“正义”“公平”“自由”等元问题上喋喋不休、滞步不前,而是通过建构起一种现实的方法模型,达到对以往民主理论的“超越”。然而,熊彼特民主观真的能够通过“回避”来“超越”吗?实现民主真的就只有熊彼特所设想的精英主义政治竞争选举这一条路径了吗?更进一步地说,民主作为观念与政治的上层建筑,难道真的能简化为政治主体与政治方法的集合吗?
比较而言,马克思民主观肯定与继承了古典民主理论对“人民”诸问题高度尊重和深度聚焦的品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厘清了民主问题的实质,认为其乃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互动中的社会交往问题。当经济基础以生产资料私人排他性占有为主要标识时,不民主的经济依赖关系便会上升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而只有摒除这种私有制及实现去阶级化的全民解放,“人民”才会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民主的主体、对象、承载、方法及精神内核。所以可判定,马克思民主观与熊彼特民主观都缘起于对古典民主理论关切的反思,但由于前者采取“直击”策略、后者采用“回避”策略,这就昭示着前者必然具备对民主议题更深刻的理论性与更唯物的实践性。
一、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
要定义熊彼特民主观,必须精准把握它的“总问题”。有观点认为熊彼特民主观表现为一种精英民主观,因为熊彼特提出民主的历史细节之处都体现为社会精英的权威建构,人民只在过程中提供相应的民主能量;也有观点认为熊彼特民主观就是一种程序民主观,因为熊彼特提出民主难以达成绝对圆满的结果,对民主程序的把控比对民主结果的把控要容易得多。上述两种观点并没有把握“总问题”,熊彼特民主观的“总问题”在于,民主如何借助经济之力来独立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熊彼特作出了“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1](10)及社会主义民主可能存在的判断之后。这反映出熊彼特民主观中所蕴涵的“经济政治学”逻辑,即完全从经济学视角来观察政治领域的民主问题,在与经济社会运行的类比中,主观推导出政治社会民主进程。具体可从三方面进行阐释。
第一,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体现为理性由经济向政治领域的蔓延。熊彼特认为民主的前提是理性态度的建立,而理性的前提是可使人们获得思想与行为训练的日常经济工作,毕竟绝非所有人都有时空闲暇或意愿来学习消化与现实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理论。这就是熊彼特常谈到的一个观点——“经济模式是(理性)逻辑的母体”[1](198)。那么经济模式指的是哪种经济模式呢?怎样的模式会指向民主所需的理性前提呢?这种理性指向是如何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的呢?熊彼特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因为它肩负起“甩掉人类肩上的贫穷”[1](207)的重任,且在极大创造出生产力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对封建主义传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精神祛昧,让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角色得以彰显。熊彼特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魔力,是它能把经济中的货币单位转化为计量整体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内生出来的“成本−利润”计算法[1](199)强行将社会运转的逻辑扭转至经济理性轨道上来。这样便使前资本主义社会僵化的阶层结构得以打破,社会公共空间得以延展,社会公共道德升华为人民法权得以实现,民主诞生的全部条件于是乎得以补全,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的理性原则及理性由经济转向政治层面的传导链条。
第二,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反映出方法推崇与主体矮化的结合。既然理性已经在政治领域确立了,理性人的角色也已在经济理性的逻辑中确证了,民主是否可由理性直接得出呢?熊彼特认为并不能直接得出,因为民主的标准尚未被确立,理性无法与标准实现无缝对接。那么民主的标准是什么呢?熊彼特提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1](359),标准则是民主方法是否合理且无漏洞。至于结果论者所强调的利益或理想等状态下的民主价值,则并未被纳入考量范围,这是因为民主时常会遭遇诸如“不民主的方法导致了民主的结果”等悖论。熊彼特所推崇的民主方法是竞争选举方法,这种竞争方法源自于经济市场中的竞争,“正如他们(实业家)在经营石油,我(政治家)在经营选票”[1](416)。把民主看成是一种竞争行为是较为客观的,毕竟“权力竞争是民主不可或缺的”[2]。而不客观的方面,在于推崇竞争方法时矮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熊彼特对人民存在两种担忧:一是人民的“暴民化”及基于此产生的民主“压迫”,二是人民对民主的无限制期待、无条件忠诚及其导致的民主“自身纠错机制”的丧失。所以从表象层面看,人民直接对接民主似乎难以收获好的结果,人民似乎也无相应的能力与技术来实现民主,那么理想的民主状态应当把“人民治理”矮化为“人民批准”[1](364),按照竞争选举方法“批准”相应人士或集团来达成民主,这就是熊彼特丢“主体”之车保“方法”之帅的策略。
第三,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揭示了相对论之上的严苛民主条件。民主并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熊彼特对此也有清晰认知。他提出应在民主议题上持有“一向表明的严格的相对论”[1](421),这种相对论指的是,虽然“民主可简化为民主方法”已得到论证,但不能认为民主方法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都可奏效,方法能否成功运行往往取决于民主“装置”以外的诸条件。即,不应不假思索地对某种民主方法采取盲从或盲斥姿态,任何民主方法的成功都是相对于外部条件而言的。那么实现民主的条件有哪些呢?熊彼特认为在现代大工业国家范围内,至少要满足这么四个条件:一是存在善治与治善的中产社会阶层,该阶层致力于为政治事业提供精英人才;二是政治决策应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防止权力滥用导致的政治腐化;三是形成一个专门的官僚机构,来充当民主政治技术的操作者;四是在结合民族性的基础上,确立制度层面的“民主自制”原则,使民众与政治家同时受到该原则的制约。[1](421−430)这四个条件归纳起来其实就一句话,民主过程的可持续应立足于严苛的“自动性限制”[1](434)——由人才限制、范围限制、技术限制与制度限制构成的条件,当然这些条件是资本主义这种“创造性毁灭”[1](144)制度所无法提供的。那么社会主义又如何呢?熊彼特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国家管理范围扩大,便认定社会主义违反了条件二与条件四,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将导致个人自由的受限和民众利益的牺牲,苏联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将会被证明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虚伪”[1](438)。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
与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相对立,马克思的民主观体现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民主观。虽然二者都强调“经济”之于民主的巨大作用,但熊彼特民主观中的“经济”是一种具象化的经济概念,所搭建起来的世界观图景,与古典经济学时期所宣传的那种资本主义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论调并无二致,因为他事实上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竞争”视域,反映到政治民主领域也仅表现为一种经济手段的政治化倾向。而马克思民主观中的“经济”是一种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概念,以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视民主论域中的人民诸问题,来确证民主的阶段性、阶级性、斗争性及社会主义转向的必然性。总的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不仅摆脱了古典自由主义、旧唯物主义、浪漫主义等限制,更站在批判立场上鞭笞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民主虚伪性。具体可从三方面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释析了经济史中的人民定义。人民之于民主的不同定义,是马克思民主观延续古典民主理论核心论域且与各类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实现理论分野的原点。人民概念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中,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更确切说是一个经济史概念,尔后才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从唯物经济史的逻辑出发,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以劳动实践为创造或改造动力的全部经济要素的价值生产者或价值消费者,无论是在商品生成史、货币生成史、资本生成史等视域中,还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域中,人民都是作为历史的决定主体身份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将民主的缘起追溯到了唯物经济史中的人民概念,以一种“科学抽象”方法确定民主的实质乃是人民之间的某种秩序化关系,并且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民主的关系缔结者与权力享有者,即人民民主才是民主的最高阶形态。马克思的人民定义是对“几乎所有的‘伟大政治理论’都倾向于精英统治论”[3]的反叛,对用怀疑眼光看待大众统治的民主偏见进行首创性批判;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所有古代朴素民主设想或启蒙时期虚构民主理论的抨击,民主的自我规定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4]的民主只能是人民民主。
第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澄清了经济依赖中的阶级依赖。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5](107−108)资本主义时代就处于这一看似矛盾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独立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法权制度下人与人的自由平等,人身依赖或人格依附被制度化禁止了;而“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反映出该阶段自由平等的表象性与虚假性特征,人身或人格依赖关系被更为隐秘的经济依赖关系所取代,这种隐秘的经济依赖关系以资本之物为基础建构起来了。因而可以说,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独立性”是一种被隐匿了的经济依赖关系所生产出来的“虚假镜像”,故该时代的民主也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空有其名的形式。然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民主观并没有驻足于经济依赖关系上,而是进一步挖掘经济依赖中的阶级依赖。随着生产力飙升、社会分工精细、社会化需求增强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程度到达峰值,阶级依赖关系逐步从经济依赖关系中凸显出来,民主表现得越来越迎合雇佣劳动与资本增殖的需要从而发生异变。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在方法层面上提出了阶级分析法,以经济依赖中的阶级依赖程度作为宏观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即民主的程度与阶级依赖程度呈负向关联,民主的彻底实现必定是在阶级依赖完全破除的场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中。
第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致力于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统一。既然民主只能等到阶级依赖关系彻底瓦解时才可成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主无法提前有所作为呢?换句话说,民主在被确证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精神与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范畴时,能否突破对经济关系客观必然性遵循的“亦步亦趋”状态呢?在马克思的理解中,通过技术上的民主与专政相统一方法,可跨越民主的“卡夫丁峡谷”,即在不成熟的经济基础上超前实现民主。那么由此便衍生出了两个问题,即:一是民主与专政如何实现有机统一,二是超前实现民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何在。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马克思认为有机统一是指对人民民主及对敌人专政的统一,在保证民主主动权与主导权为“最大多数”所掌握的前提下,再来强调人民公意与人民监督的合一。从形式上看,这不可避免地在民主机构设置上出现对以往政权公共职能的模仿与继承,但这只是“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归还给社会承担责任的勤务员”[6]而已。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超前就意味着时间上的节约,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统一实质是对民主阶段性发展时间的节约。这种统一使“经济成熟→民主成熟→民主性质变革”的常规逻辑转向了“民主性质变革→民主成熟→经济成熟”的非常规逻辑,先确立民主的意识形态站位,再思考民主的质量水平,可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时间节约因此成为可能。马克思提出,时间节约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首要规律,“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123)。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统一有助于实现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重”时间节约:一方面,超前实现民主意味着,能把节约出来的时间规导到形成社会共识的议程中,而非浪费时间于导致社会撕裂的行动中,这样可遏制住民主发展过程中的“泛民主化”与“泛专政化”冲动,保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有效契合;另一方面,超前实现民主还昭示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上层建筑可更早地激发对不成熟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能够拓展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而形成以“时间节约论”为中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良性互动关系。
三、马克思与熊彼特民主观的理论品质之异
从熊彼特的“经济政治学”民主观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民主观的内容阐释中,可发现二者有着诸多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二者都将经济视为政治要素的前提,都从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出发为民主寻求发展道路。所以戴维·赫尔德才会对二者有着这样的评价:“与马克思一样,他(熊彼特)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发展和充满活力的性质。和马克思一样,他断言更大的企业必然主导商品生产和分配。而且,与马克思一样,他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7]但是,熊彼特民主观没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将民主过分局限于表象化的精英治理与技术化的程序逻辑中,而把人民这一民主的历史主体矮化,故其得出的民主结论仅具备片面的深刻性。比较而言,马克思民主观从人民历史的角度探寻民主的应然轨迹,明确经济之于民主的作用不只在于政治理性的培育,更在于人民历史主体角色的确证,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民主观在结论、起点、方法、场域等方面较熊彼特民主观的高位格理论品质。
第一,民主结论上的“唯一性”与“可能性”。熊彼特基于“经济政治学”给予民主过多的“限定词”,得出的是民主“可能性”结论,而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得出的是民主“唯一性”结论,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彰显民主的真正内涵。熊彼特认为,除非是在完全成熟的大工业条件下以民主方法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并有足够治国理政能力的官僚阶层,以及全部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坚决遵循民主竞争的原则,同时还必须摒弃生产领域对劳动者严格纪律要求等等,否则所得到的民主都是失败的。但任何民主都不是预成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他所提出的各种限制性条件决定他的民主只能停留在空想乌托邦层面。而马克思认为实质比程序和方法更为重要,取得民主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要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支撑制度的经济权力来一场必然的“革命”——当然这种“革命”是依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和平还是非和平的,在集体主义视域中唯一真实的民主才会登上舞台。
第二,民主起点上的“制度本质”对“制度形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民主制’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8]马克思较熊彼特的起点高位格,在于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视为是一种制度本质而非是制度形式。具体来说,熊彼特民主观中探索民主定义、追溯古典学说中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考量政治中的人性、思考竞争政治领导权应用原则、勾勒民主方法成功条件等理论环节,都旨在弥补资本主义的民主缺陷。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定位的偏差,以及其对官僚制过分推崇,断定只有官僚制才能将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民主勾连起来,导致其在规划民主细节上出现重大问题,其内核依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民主的桎梏。而马克思民主观遵循着“定言推论”逻辑:只有先确立人民规定性就是国家制度规定性,然后才可在国家与社会二分条件下进行民主制度形式的实践转化,也即是说先有一般概念上的民主,才有具体的民主建构。并且,马克思预言最终政治的胜利必将是民主的胜利,国家也不可避免走向消亡,当作为阶级、国家等人的对象化产物的全部社会基础消亡之后,民主制才能大放异彩。如道格拉斯·拉米斯所认为的:“民主最好不要被描述为一个‘体系’或一揽子制度,而是一种存在状态,向民主的转变不是一种制度创立,而是一种‘状态转变’。”[9]可以说,马克思的民主是面向终极目标的超越性民主,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体现为一种理想、状态与现实的运动。
第三,民主方法上的“阶级分析法”对“技术分析法”。为何熊彼特强调“技术分析法”?因为他惧怕民主权力一经人民之手便会失去民主色彩,即臆想民主必然出现“多数暴政”。而这种观念其实是荒谬的——其一,相信权力来源于多数人的意志,但又否认多数人具备掌握与分享权力的权利;其二,只过分强调通过技术手段来达到民主,而忽视容纳这类技术手段的社会经济基础。而马克思坚信“阶级分析法”,强调应当“通过阶级属性的修饰,民主成为副词,阶级成为主词,一切对于民主的理解都需要纳入到阶级属性的分析当中去”[10]。而有学者提出质疑:“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11]也就是他们对阶级凝聚力是否会大于民族主义情结存在疑虑,那么“阶级分析法”能否回应这种质疑呢?事实上,“阶级分析法”没有忽视民族共同体而只突出阶级共同体,它并非是一种民主的唯阶级论,而是以阶级共同体作为主体分析框架,把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性别共同体等一些非经济性要素融入其中,并在实践中为民主配套各种辅助秩序或制度。这样便能极大延展民主方法的弹性,填补“技术分析法”的主体矮化及方法悬置漏洞,最大程度地将民主的关联要素纳入考量范围。
第四,民主场域上的“非限制性范围”对“限制性范围”。民主适用于何种场域呢?熊彼特认为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竞争基础上的领导权,民主只有停留在政治竞争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得出了民主场域只能是严格的“政治管理范围”的错误结论。马克思则解决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矛盾,他认为政治问题根源于经济问题,更确切来说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这又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核心。因而,所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因素都可作为民主发生、提炼、实践、转型等的场域,因而马克思民主场域是非限制性的,所以马克思的民主范围扩大有助于理解非政治领域中的“非民主”现象。确实如此,马克思民主观的场域非限制性,决定着民主的逻辑能够嵌入到所有的社会议题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职能与社会职能日趋统一的情况下,这种民主逻辑的嵌入是可行的且是应当的。因此,民主在马克思民主观中并不单纯属于政治领域,也不仅仅关照经济领域,而是创设一类“场域集”,在其中可将以往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异化现象进行彻底地扭转改造。
当然,这种分维度的理论品质对比是不能割裂视之的,结论、起点、方法、场域等这些不同的民主评判维度间存在着显著关联。之所以马克思较熊彼特在民主结论上更为科学与革命,是与其所确立的起点、秉持的方法、观察的场域密不可分的;而之所以马克思在民主起点、方法、场域上也更为合理与精准,亦是与其预判与致力于实现的结论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此,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决定的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较熊彼特民主观高位格的理论品质。
四、马克思与熊彼特民主观的实践品质之别
民主的对比研究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回过头来研究民主的实践,其结果只是会沦为阿尔都塞所言的“哲学空谈”与“意识形态的幻梦”[12]。马克思民主观较熊彼特民主观有着高位格理论品质,但在实践中能否同样具备这种品质呢?这就要事先界定二者在实践当中的具体民主模式。可这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及当前流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分别继承了马克思与熊彼特的民主“衣钵”,它们代表了马克思民主观与熊彼特民主观分别指导下的最生动民主实践。通过观察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展示出其在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上的高度自信与斐然成果,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则陷入到无中心主义的民主困局中。
第一,民主形式上的“本土化”对“民粹化”。从民主观到民主制度是一个从“应然”到“实然”的具象化过程,也就决定着民主的实践建构必然会受到各种内在衍生产物的影响,即民主观到民主形式的过渡。熊彼特民主观的衍生实践形式是泛滥于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思想和行动,民粹主义的诞生在理论层面上可视为是熊彼特民主原则中“唯经济论”和“唯技术论”的直接产物,强调把民主直接等同于民主斗争的过程,以“公民抗命”对所谓“政治正确”“既定秩序”“腐败精英”的无条件反对和无理由抨击,以煽动方式使受斗争对象“他者化”,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本土主义,本质上就是偏激的一元主义取代民主的多元主义[13]。而马克思民主观的实践衍生形式,就体现为中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民主本土化努力,将马克思民主观与中国儒学政治传统、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时期民主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进行综合考量,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在民主制度上,创立了人民民主、基层自治民主、协商民主等;在民主发展上,正经历党内民主、法治民主、国家民主的统整与变革;在民主表述上,核心价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等意识形态话语都将民主放置在显著位置,这些都是马克思民主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新运用。显然,通过这种“本土化”民主形式与“民粹化”民主形式的对比,孰优孰劣便可一目了然。
第二,民主对象上的“全民性”对“左倾性”。民主实践诸议题中最为核心的要数对民主对象的界定,即民主要针对于哪些人、民主的照顾原则又将施加于哪些群体、如何保证民主在对特定人士存在制度倾斜时不发生质变异化等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民主的质量和生命力。熊彼特民主观中的“中产社会阶层论”,在经历20世纪末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后,逐步变化为在欧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对象“左倾性”原则。即,社会民主主义在“激进主义左派”与“中间派化了的右派”的双重挤压下,要想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借助与分化光谱中最为接近的激进主义左派力量,将民主的聚焦点向左转移。诸如目前活跃于欧洲政坛上的德国社民党舒尔茨、英国工党科尔宾、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等,都采取“左倾”战术保证民意支持。尽管“左倾化”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处于经济劣势地位的普通劳动者,但也人为地制造出民主对象的分裂,裂痕在不断扩大且不可调和。反观马克思民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马克思民主观中的“全人类解放论”决定着民主对象的“全民性”,也就是说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将民主的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到民主治理的版图当中,真正实现人民作主与人民自主以及寻得民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实践中马克思民主观对熊彼特民主观在对象上的高位格品质。
第三,民主传播上的“共享式”对“霸权式”。民主传播是国际政治交流中无法回避的议程,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民主的观念、制度、举措等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间发生交流与碰撞,在借鉴对比中取长补短。而熊彼特民主观指导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期待着建立起一种欧美式民主意识形态的霸权格局,希冀利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势差”,来强迫其他国家或民族走他们相同的道路。并且公然宣称苏联解体直接昭示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终结”以及资本主义民主的“普世”,利用“人权宣言”“占领运动”“颜色革命”等迷惑性极强的手段妄图干涉他国内政、人权、主权等。而当它的民主输出出现一定程度的“异体排斥”或“消化不良”等情况时,便往往虚以委蛇地以诸如“超过其他民主的价值”“民主本身就是那个最不烂苹果”等说辞来进行“合理化”推托。比较而言,马克思民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在民主传播上讲求的是“不争霸”“不称霸”“不与其他利益进行捆绑”,充分尊重其他国家或地区特定的文化风俗、民族心理、政治惯性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欢迎其他国家或地区来搭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及变革世界的“顺风车”,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是一种“共享式”的民主制度,深层次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世界意义,更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正依托中国智慧与中国担当,逐步实现对以往任何民主形式的实质超越。
当前,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将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进行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更是一项关键的时代任务。而澄清两种意识形态站位基础上的民主观的品质差别,便是这种结合的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话题向来都是倡导某种主义、批判另外一种主义的最有力武器。当然,论证马克思较熊彼特民主观的高位格品质,其意义并不仅是对这两位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作优劣判定,也不只是用以强调中外民主实践上巨大反差来进行褒贬,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引导我们如何更为深邃且合理地思考全人类的民主未来。而通过对比后我们可以断定:只有洞察且把握到了马克思民主观的理论与实践实质,对资本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地批判,才可真正预见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未来。
[1]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2] 伊安·夏皮罗. 政治的道德基础[M]. 姚建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39.
[3] 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M]. 彭斌, 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116−117.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8.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6.
[7]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M]. 燕继荣, 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29.
[8] 林尚立. 建构民主的政治逻辑——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出发[J]. 学术界, 2011(5): 5−18.
[9] 道格拉斯·拉米斯. 激进民主[M]. 刘原琪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43.
[10] 徐圣龙. 马克思民主思想与“暴力美学”辨析——比较J.L.塔尔蒙与理查德N.亨特关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叙述[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15(3): 1−6.
[11]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M]. 李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
[12]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0.
[13] 林德山. 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J]. 当代世界, 2017(3): 20−23.
[编辑: 谭晓萍]
On the higher quality of Marx’s democratic view compared with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
ZHANG Weiliang, HU Wengen
(College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Marx's and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s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s on democratic issues. In ideology, the former is socialism and the latter is capitalism. By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paths of democratic view, we can restore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and clarity the mistakes people have made in understanding democracy so as to provide a better method to verify the priorit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 essence,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olitics, while Marx’s democratic view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whether it adheres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 people’s subjective view. On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vis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subjective view in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 have been removed by the modern form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while Marx’s democratic view has always been adher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eople’s subjective view. Hence, either on the conclusion, the starting point, the method or field of democracy, Marx’s democratic view has higher quality than Schumpeter’s in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Marx’ democratic view is higher in democratic form, democratic object as well as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than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guided by the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
Marx’s democratic view; Schumpeter’s democratic view; higher quality; theoretical quality; practical quality
A811
A
1672-3104(2017)05−0122−07
2017−06−13;
2017−08−0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培育的文化认同机制及创新途径研究”(15BKS101);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重大项目“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逻辑与路径研究”(2016ZDAM05)
张卫良(1960−),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胡文根(1990−),男,江西高安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