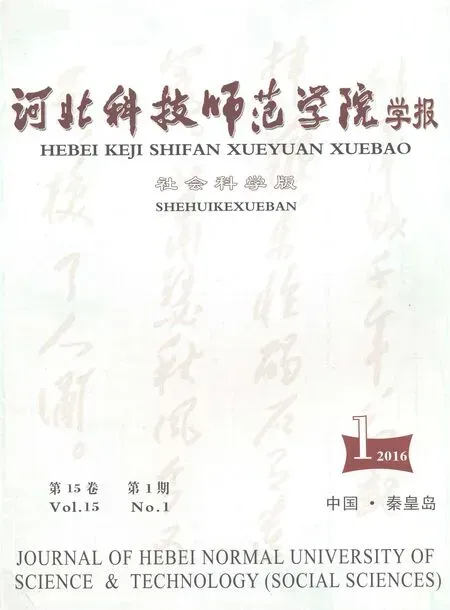介词“于”语法化再谈*
2016-12-20魏金光
魏金光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
介词“于”语法化再谈*
魏金光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
殷商时期“于”的及物性和语义概括性决定了它在“V+于+N”结构中成为语法化源词的首选者。当V编码位移事件时,“于”的[+位移]和[+方向]丢失特征未丢失,而是处于“动介词”阶段;当V编码非位移事件时,其“语义溢出”使“于”“去语义化”为介词。“语境泛化”是动词“于”介词化的基本句法机制,它存在“动词 > 动介词 > 介词”这一语法化“斜坡”和“动介重新分析”的过程。
“于”;语法化;介词;语境泛化;语义溢出
“于”属最古老的核心介词。关于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源于连动结构中的动词“于”,二是源于原始汉语的格助词。郭锡良认为,在“V+于+处所” 结构中,“于”与V的运动方向是否一致促使了其动介转化[1]131-139;梅祖麟认为原始汉藏语有个“往,行”义的动词,它在上古汉语演变为及物动词“于”,并在“往/步/出+于+处所”中开始语法化[2]323-332。时兵认为介词“于”标识多种语义关系且结构位置不固定,这与同期介词的差异性是原始汉语转型期(SOV>SVO)用前置词替换后置格助词的结果[3]343-347。
确如张玉金所认为介词“于”源于格助词难以确证[4]16-22,郭锡良和梅祖麟早已指出,介词“于”的语法化源义和源词为“往”义的动词“于”[1]131-139; [2]323-332。 殷商时期“于”具有位移动词的用法。如:
(1)a.壬寅卜,王于商。(合33124)
b.贞:呼去伯于冥。(合635正)
c.贞:王去刺于敦。(合5128)
一、 “于”的动介转化
(一)语法化环境
关于介词的语法化环境,Claude Hagège从类型学角度指出,汉语作为VO型语言,其介词是“N+V1±N1±V2±N2”序列框架中产生的,V1或V2演变为介词(preposition)[5]152-153。何洪峰指出在汉语的“V1·N·V2”式连动结构中,V1的介词化及其程度与N和V2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6]15-23。郭锡良和梅祖麟认为,“于”的语法化环境是在V2位置,而非V1位置,具体来说是在“V+于+N”结构中实现动介转化的[1]131-139,[2]323-332。
“于”在连动结构的后一位置上成为语法化源词的首选者,与其句法能力有关。
“于”作为及物动词对方所论元具有强制性需求。据朱习文统计,殷商时期“于”做位移动词12例,均带有方所宾语(如例2a、2b)[7]21-28。当“于”与其他位移动词共同编码位移事件时因其强及物性而用在连动结构的后一位置(如例3a、3b)。如:
(2)a.于向无灾。(合28947)
b.……午卜,在商贞,今日于毫无灾。(合36567)
(3)a.翌日壬,王其于向无灾。吉。(合277990)
b.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无灾。(合36501)
殷商卜辞中,位移动词主要用于编码位移事件,但其及物性强弱有所不同,对“于”的需求也有差异。如表1部分位移动词的用于表达位移事件所用句式情况:

表1 殷商位移动词及物性强弱比较❶
❶本表数据依朱习文对甲骨文位移动词统计所得,尽管数据不完全,但仍可反映出动词及物性的强弱趋势。参见朱习文的《甲骨文位移动词研究》,重庆: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2.
❷即“ ”,“赦戒镇抚”义,参见张玉金的《介词“于”的起源》,汉语学报,2009(4):16-22.
据朱习文统计,殷商时表达位移事件的句子见有2 150例,其中,单用位移动词1 054例,占总数见的49%;位移动词直接带宾语仅有239例,占11%;而“V+于+N”结构有535例,占总数的25%[7]21-28。及物性弱的位移动词(如“往”、“步”、 “ ”等)多借助于“于”标示位移“标的”(Goal)来表达位移事件。 殷商卜辞常见“V1+V2”式连动结构(包括位移动词连用,以及与非位移动词连用),但“往、先、延”等位移动词一般出现在V1位置,而不在V2位置。
与“于”同义的“往”因其及物性很弱,难以在V2位置带方所宾语来标示位移“标的”(Goal),也就不会成为语法化源词的首选者。“往”有300例,其中单作谓语74例,直接带方所宾语仅19例,而用于“V1+V2”结构有132例,在V2位置带宾语形成“V1+V2+O”结构仅5例[7]17-28。
因此,“于”的强及物性使之位于连动结构的后一位置上带方所宾语表达位移“标的”(Goal)。那么,“V+于+N”结构中“于”是如何语法化的呢?
(二)语法化机制和动因
1.“运动方向相左”说
郭锡良的“运动方向相左”说触及了“于”语法化的语义动因,认为“于”与V1位置“往”、“步”、“出”等运动方向一致,而与“来”、“入”、“至”等方向不一致,导致了“于”的抽象化和动介转化[1]131-139。
但“V+于+N”结构中“于”的语义如何实现“去语义化”的,还不甚明晰,需要离析“于”的语法化源义特征。
2.“于”的源义特征
Levin和Hovav把位移动词分为三类*至达类(arrive-class),如“arrive,come,go,depart”;滚类(roll-class),如“roll,slide,move”;跑类(run-class),如“run,walk,gallop”。:至达类、滚类和跑类[8]252-258。“至达类”编码位移的“方向”,而“滚类”和“跑类”则编码了位移的“方式”,后两类区别在于,“滚类”有“直接的外在致使力”,而“跑类”没有。
三类位移动词的语义特征:
至达类:[+位移]、[+方向]、[-方式]、[-致使]
滚类:[+位移]、[-方向]、[+方式]、[+致使]
跑类:[+位移]、[-方向]、[+方式]、[-致使]
据此,可把朱习文所总结18个位移动词*分为两类:第一类,“跑类”的如“步、行、从、涉”,这几个都编码了[位移]和[方式],都具有及物和不及物性,以不及物为主;第二类,“至达类”如“往、来、去、至、归、出、入、于”等都编码了[位移]和[方向],“来、归、去”是不及物动词,“往、至、入”大多数时候是不及物[7]21。
作为及物动词,“于”主要编码了“位移事件”的[+位移]和[+方向]这两个语义内容,这是其语法化的语义基础。
“于”之所以成为语法化的“候选者”还在于其词义的概括性。Heine,Claudi和Hunnemeyer指出语法化的“候选者”需要两方面的因素:“语义概括性”和“使用频率”[9]38-42。
从“语义概括性”看,“跑类”位移动词表义具体:“行”指用脚运动,“涉”指在河上运动或穿过河,指去打猎这种运动,指“渡河”,它们都编码了某一具体的运动方式。而“至达类”位移动词也编码具体的运动方式:“出”指从内运动到外,“入”从外到内,“至”描述的到达某一既定位置的一般运动,“去”是指离开某一特定位置的运动,“归”指回到位移体出发的位置,“往”描述的是离开说话者的运动,而“来”则是面向说话者的运动。只不过,“跑类”动词没有编码[方向],“至达”类动词编码了[方向]。
“于”不同于其他“至达”类位移动词,它指称一般的位移运动,语义概括性度高,具有[+泛向]或[+不定向]特征。而其他位移动词表义具体,位移方向具有[+矢量]或[+定向]特征。相较而言,高语义概括度的“于”更适合标示位移“标的”(Goal)。
3.句法和语义相宜
郭锡良的“运动方向相左说”有一定解释性[1]132,而依语法化理论的“语义漂白”机制*18个位移动词及其在殷商卜辞中的频次:至162、出354、 7、往300、延139、于12、从55、涉59、来254、归131、步328、去41、入51、先38、行13、复19、走1、 342.。参见朱习文的《甲骨文位移动词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2.,“于”的介词化过程应该有[+位移]和[+方向]特征的丢失。
但是,笔者发现表述位移事件的“V+于+N”结构中“于”的语义特征并未“漂白”。
殷商卜辞535例的“V+于+N”结构中V多为“步66*“步”等词的下标数字指该词用于“V+于+N”结构中的频次,数据是据朱习文的殷商甲骨卜辞位移动词的统计而得。、从19、涉7、287、5、延8”等“跑类”词约占70%;而“往69、去6、至18、归6、出35、入9”等“至达类”词仅占30%。
语义表达上,“跑类”词(“步、行、从、涉、 、 ”)的[+位移,+方式,-方向]语义特征与“于”的[+位移(一般),-方式,+方向]特征相洽相宜。“跑类”词的[-方向]特征因“于”的[+方向]特征而得到语义补足,得以表述位移的“标的”。如:
b.……申卜,方其 于东?(合11468)
c.贞:我勿涉于东 。(合8345)
“至达”类词(“往、来、去、至、归、出、入”)的[+位移(具体),+方向(矢量)]特征与“于”的[+位移(一般),+方向(泛向)]虽有语义特征矛盾和赘余,但也句法上相洽相宜。如“往”和“出”因其弱及物性而对“于”有句法需求。如:
(5)a.丁卯卜,争贞:王往于敦,不左?(合7945)
b.丁巳卜,宾贞:王出于敦。(合7942)
两类位移动词进入“V+于+N”结构频次差异表明:“跑类”词的[-方向]需要“于”的[+方向]来补足,而“至达类”词的弱及物性也需要“于”带宾语,二者均表现出表达位移事件的句法语义相洽相宜性。
以上可看出,“于”在“V+于+N”结构中编码位移事件时具有标引“标的”的功能,但还未丢失词汇语义,有时仅是V与“于”运动方向相左。如:
(6)a. 贞:勿归于商。(合7820)
b.辛酉卜,壳贞:今二月王入于商?(合7774)
c.贞:方其来于沚?(合6728)
当V是“来”义位移动词(“入”、“来”、“至”)时,“于”与之表现出语义矛盾,有意义虚化倾向,可看作是处于“动介重新分析”阶段,但其[+位移]和[+方向]特征未丢失。
语法化理论把“语义漂白”看作是语法化机制或特征之一,但表达位移事件的“于”并未“去语义化”,反而因V的句法或语义需求而得到“语义凸显”,用以标示位移“标的”。
4.“于”的语境泛化
“语境泛化”(Context Generalization)也叫“扩展”(Extension),何洪峰认为它是汉语动词介词化的基本句法机制[6]16。
在“V+于+N”结构中当V由位移动词“扩展”类推到“动作动词”(包括“取予动词”、“祭祀动词”、“攻伐动词”和“言说动词”等)或“静态动词”(如“心理动词”)等非位移动词时,“于”的“语境泛化”,相应地“于+N”编码的语义随V的“扩展”而不同。
笔者发现在“V+于+N”结构中V的语义特征的变化触发了“于”的变化。
Leech的“语义溢出”论认为,谓词的语义特征支配着其论元特征[10]194-197。若V是位移动词,其[+位移]特征相应地支配后面N的[+空间]或[时间]特征;若V是“动作动词”,[+让予]特征要求与之搭配的N必须具有[+对象(人或物)]特征。如:
(7)a.先刍于盾。(通释1456)
b.贞:作大邑于唐土。(合1105)
c.丙戌伐人方于笋。(英2526)
d.土方征于我东鄙。(合6507)
e.甲子卜,其祷雨于东方。(合 30173 )
f.甲辰贞:其祷禾于丁未?(合33331)
g.己酉卜贞,王其观于泉,无灾? (合24426)
“刍”、“作”、“征”、“伐”、“祷”、“田”、“观”等作为动作动词,不具有明显的[+位移]特征,“于”与之“语义域”不同。动作动词的“语义溢出”影响和支配了N的[+空间]/[背景]语义,因此,“于”的[+位移]和[+方向]特征丢失,发生了“语义漂白”,具有了标示动作[+空间]/[背景]的功能。
在“语境泛化”下,非位移动词的“语义溢出”促使了“于”的“去语义化”,使之成为具有标示和引介功能的介词。如殷商卜辞中的“畀、见、来、乞、取、受、以”等“取予动词”和“祷、酒、御、侑”等“祭祀动词”后面的N均为“于”引介的[+对象]。如:
(8)a.甲戌卜:草以牛于大示,用?(小屯南地00824)
c.辛未贞:其祷年于高祖?(合32028 )
d.乙丑,出贞:大史必酒,先酒其侑祊于丁三十牛?(合23064)
因此,“于”的介词化是从编码位移事件到编码非位移事件的变化中实现的。在介词化过程中,“于”首先表现为了“句法和语义相宜”,在形式上具备了介词的标示和引介功能,V的“语义域”扩展相应地支配了N的语义,“于”也随之实现了“去语义化”,成为了“纯介词”。
二、“于”的动介程度
Hopper和Traugott指出,语法化过程存在“并存”阶段:A>B/A>B[11]36,94-129。据此,梅祖麟也描述了殷商卜辞“于”的句法结构链和语法性质链[2]328-330:
动宾>动介宾或动1动2宾>动介宾
动词>介词/动词>介词
王于商>王往于 >其来于沚
这一单向性链条表现了“于”的动介程度问题。
笔者认为,殷商时期“于”的语法性质链应为:
动词>动介词>介词
殷商卜辞中“于”做动词用法常见。郭锡良据《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识别了5 000多“于”字用例,其中动词用法占5%,多用于6种结构中:“名十于+处所名词”、“自+处所名词+于+处所名词”、“先+于+处所名词”、“使/令/呼+名词+于+处所名词”、“ +于+处所名词+无灾”、“步/往+于+处所名词/动词“田”[1]131-134。张玉金认为只有第一和四种结构中的“于”为动词,其余应看作介词[4]17。
笔者认同张玉金等关于动词“于”的认定。但是,其他四种结构中的“于”并非“纯介词”,而是处于动词和介词之间的“动介词”(coverb)。 Lehmann ,Christian指出,“动介词”是指在连动结构中变为介词的序列动词;它处于实动词和介词之间,但它具有介词的功能,与介词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可看作是连动结构中表主要动词和名词的副词性关系词[12]30,93-94,150。
在“V+于+N”结构中,当V是“至达类”和“跑类”位移动词时,“于”的[+位移]和[+方向]语义特征并未发生“漂白”现象,仍保留了动词的词义特征,但是具有了类似介词的标示和引介功能,这种既具有动词句法特征,又具有介词功能的状态符合“动介词”的句法表现。
从“语义域”看,“于”与“跑类”词同为位移动词,语义同域,其后的N同为二者的方所论元,只不过“步”、“行”等带宾能力弱。“于”与“至达”类词也同为位移动词,语义同域,只不过有时出现语义矛盾,“于”具有介词的特征。
当V是“跑”类词时,于”与V“语义域”相同,其动词性未丢失,“V+于+N”可看做连动结构;当V是“至达”类词(如“至”、“归”、“入”),“V+于+N”结构两可看待,具有“动介重新分析”(V>P Reanalysis)的特征。特别“来”义动词(“来”、“入”、“至”等)与“于”“运动方向相左”,具有语义矛盾现象,“于”的确具有“意义虚化”特征,但还未语法化为“纯介词”。
显然,处于“动介词”状态的“于”还未完成“去范畴化”,仅是形式上属动词范畴,功能上具有了介词的特征,“V+于+N”结构有“动介宾”或“动1动2宾”的两可分析。因此,殷商卜辞中位移动词V和“于+N”之间可以有停顿或可断开。
当V“扩展”至非位移动词时,“于”发生“语义漂白”现象,[+位移]和[+方向]特征丢失(如例7),“于”成为介词。
笔者以为,殷商卜辞“于”的句法结构链和语法性质链可修正为:
动宾或动1动2宾>动1动2宾或动介宾 >动介宾
“于+N”/“跑类V+于+N”>“至达类V+于+N”>“非位移V+于+N”
动词>动介词>介词
三、余论
就来源看,汉语的介词属动源型,由于形态缺乏,有时动、介词不易确认,考察动介转化过程既需要弄清语法化源词和源义特征,又要找出动词“去语义化”的路径、机制和动因。
在“V+于+N”结构中主要动词V与N“动—名”语义关系促使了次要动词“于”的“去语义化”过程。“于”在连动结构的后一位置首先语法化出了引介空间所至的功能。据张玉金,在殷商卜辞“于”引介空间所至和时间所至达的“于”很常见,可作状语,也可作补语;然而引介空间和时间所在的功能很罕见,且只能作状语[13]75-77,66,68。
根据语言演变的普遍性规律,“空间域”可投射到“时间域”,为什么“于”引介空间所在功能少见,且在补语位置不能投射到“时间域”?“于”的各语义功能在系统内是如何发展和消长的?诸如此类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1]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J].中国语文,1997(2):131-138.
[2]梅祖麟.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J].中国语文,2004 (4):323-384.
[3]时兵.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J].中国语文,2003(4):343-347.
[4]张玉金.介词“于”的起源[J].汉语学报,2009(4):16-22.
[5]Claude Hagège.Adpositions[M].Cambri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何洪峰. 动词介词化的语义机制[J].语文研究,2014(1):15-23.
[7]朱习文.甲骨文位移动词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2.
[8]LEVIN BETH, MALKA RAPPOPORT HOVAV.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Verbs of Motion: The Perspective from Unaccusativity[M]//M Roca.Thematic Structure: Its Role in Grammar.Berlin:De Gruyter,1992:247-270.
[9]HEINE BERND,ULRIKE CLAUDI,FRIEDERIKEHUNEMEYER.Grammaticalization:A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0]LEEC, GEOFFREY N.Semantich[M].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11]HOPPER,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93].[12]LEHMANN,CHRISTIAN.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M].Erfurt:Seminar für Sprachwissnschaft der Universität,2002.[13]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母华敏)
Discussion Again on the Grammarticalization of the Preposition “Yu”
Wei Jinguang
(Humanities and Media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2,China)
Owing to the transitivity and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the word “Yu” has become the source word of the grammarticalization in the “V+Yu+N”in Shang Dynasty. When the V encpded the motion event, the semantic feature ([+displacem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word “Yu” didn’t lose, but was in the gradation of the “coverb”. When the V encpded the non-motion event, the “semantic overflowing”of the V brought about the lost of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the word “Yu” which became into the preposition. The context generalization was the elementary syntactic mechanism that the full word “Yu” became into the preposition. The “desemanticization” of the word “Yu” made it become a preposition. For the full word “Yu”, the “grammarticalization cline”(“verb>coverb>preposition”) existed, and so did the “V>P Reanalysis”.
“Yu”;grammarticalization;preposition;context generalization;“semantic overflowing”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1.0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法化视野下的介词更新研究”(11BYY075);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古汉语介词即时查询系统构建”(13GZQN22)。
2015-12-12;
2015-12-23
魏金光(1980-),男,山东省费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史和方言研究。
G127.22
A
1672-7991(2016)01-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