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意”:王若虚创作论思想细析
2016-12-20殷亚林
章 辉,殷亚林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尚意”:王若虚创作论思想细析
章 辉,殷亚林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王若虚的主要文学理论都可以视为围绕着“尚意”命题的系统化,从而成为金代文论的高峰。简言之,他发挥了前人“以意为主”的思想,主张贵“天然”,重“自得”,反对创作中外在成法的束缚,其目的就是避免以辞害意。其意义在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打破了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桎梏和江西诗派以来的形式束缚,为文学创作倡导更多的自由天地。
尚意;自然;自得
金代最重要的文论家当属堪称“北朝双璧”的王若虚和元好问。王若虚(1174~1243年),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石家庄)人。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他的文学观点集中反映在其《滹南诗话》、《文辨》等著述中,大体上可以视为围绕着“以意为主”命题的系统化,从而成为金代文论的高峰。王若虚的文学批评观体现在创作论方面,概括说来就是“尚意”。
一、王若虚“尚意论”的理论准备
“言意之辨”是一个中国古代的重要命题。它最初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即语言符号能否和怎样表达意义的问题。后来又演变为一个文艺美学问题,即语言形式技巧和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
(一)金代以前的理论源流
“言意之辨”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的“得意而忘言”[1]66(《庄子·外物》)。魏晋王弼(226~249年)做了发挥,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2]609(《周易略例·明象》)的命题。二者虽然说法不同,其实质都是说,如果形式(言辞)过分突出,就会束缚观照者,影响、干扰人们在审美观照中所获得的对于宇宙、历史、人生的感受和领悟。只有重意轻言、得意忘言,不去刻意于言,才能真正达到意的领会。后来南朝宋的范晔进一步提出:“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3]1830(《宋书·范晔传》)唐代杜牧(803~约852年)亦提出:“文以意为主……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4]182(《答庄充书》)如果说,庄子、王弼的命题还具有普泛意味的哲学色彩,那么范晔、杜牧的论断则意在给文学创作领域以专门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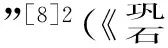
(二)金代前、中期的理论准备
到了金代,金初词坛盟主宇文虚中(1079~1146年),反对宋代江西诗派“冥搜巧绘”的形式主义流弊,不屑为文造情、钩章棘句。他形容自己的诗作是“语不复锻炼,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9]4(“穷愁诗满箧”诗题)。稍后的的朱弁(1085~1144年),字少章,文学理论家。他赞赏钟嵘:“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5]4(《诗品序》)之语,反对西昆体念念不忘典故、转语和代语,认为“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10]99(《风月堂诗话》卷上)在他看来,最优秀的诗篇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观古今胜语,皆自肺腑中流出,初无缀缉功夫。”[10]115(《风月堂诗话》卷下)这实已开启了金代言意之辩,是后来王若虚“肺肝中流出”之论的先声。
金代中期,南北讲和,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文化风气也渐由崇尚质朴转为浮华闲适。而此时的科举大开和词赋取士,更使得文坛推重语言的雕琢,如蔡珪、刘迎、王琢、王寂、王庭筠等人,出现了追求工丽、尖新的形式主义流弊。周昂(?~1211年)较早对此加以批评。他在传授其甥王若虚文法时有一段著名的议论,为后来王若虚的理论崛起做了准备:
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11]2(《滹南诗话》卷一)
周昂这里的“意”,就是文章在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对周昂来说,“意”是统摄作品的主宰,而语辞只是仆役,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他又曾说过:“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11]2(《滹南诗话》卷一),“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12]425(《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四》)显然,周昂所谓的“内”、“本”,也就是“意”。在他眼中,雕琢是对“意”的伤害,词巧而意拙的作品,可以一时逞奇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金代中后期的文坛盟主赵秉文(1159~1232年)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意”与“辞”是目的与手段(工具)的关系:
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为文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13]20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五,《竹溪先生文集引》)
但赵秉文的“意”,较之周昂,其内涵更加确定:“至于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13]231(《答李天英书》)可见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与历代“文以载道”的理论相吻合。《乐记》中曾有“乐胜则流”的论断,即指出偏重形式会导致人心的放荡,而赵秉文也提出了类似的“质华观”:“质胜华,则治之原也;华胜质,则乱之端也。国家之兴,未有不先实而趋华;华之极,则为奢为僭,为奸为伪,则日趋于乱矣。”[13]191(《总论》)在他看来,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形式大于内容,则是国家祸乱的开始。因此,他崇尚务实,反对“务奇之为尚”[13]205(《竹溪先生文集引》),反对当时金代文坛“钩章棘句,骈四俪六”[13]188(《商水县学记》)的浮华之风,感慨“今之士人以缀缉声律为学,趋时乾没为贤,能留心韩、欧者几人!”[13]233(《答麻知几书》)基于此种思想,在当朝文士中他尤其赞赏党怀英,因为党的文风平淡自然,同那些崇奇斗巧的风气完全相反。赵秉文自己的文风,也被元好问称为“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14]403-404(《闲闲公墓铭》),以达意为目的,不受形式的束缚。
二、王若虚“尚意论”细析
较之赵秉文的学说,王若虚所倡的“意”更平实而近乎人情。他引南宋惠洪的话说:“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此当论意,不当泥句。”[11]2(《滹南诗话》卷一)因此,他的“意”不是囿于儒家政治美学的内容,而是着重于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和真情流露,赞赏一己心中流出而非刻意造作或陈词滥调。简言之,就是崇尚真实、自然和自得之情,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他对前人“以意为主”主张的发挥,打破了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桎梏和江西诗派以来的形式束缚,意在为文学创作倡导更多的自由天地。以下分三点加以详述。
(一)“天生好语,不待主张”
在朱弁的基础上,王若虚更加大力倡导诗文创作之道在于文辞的天然流露。他引用当朝前辈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12]233(《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二,《新唐书辨上》)又引周昂的主张:“自然之势,诗之大略,不外此也。”[11]2(《滹南诗话》卷一)
他称赞陶渊明,说“《归去来辞》本是一篇自然真率文字。”[12]388(《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文辨一》)他论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时又有这样的著名议论: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予谓天生好语,不待主张,苟为不然,虽百说何益?[11]2(《滹南诗话》卷一)
孟郊和白居易的诗分别因格调孤寒和太过浅易受到后人鄙薄,然而王若虚却认为他们的诗都达到造化妙境,关键就在于有真挚的感情和真切的感受:“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11]6(《滹南诗话》卷一)在他眼里,白居易充满天然的“元气”:
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12]524(《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三,《高思诚咏白堂记》)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辄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11]6(《滹南诗话》卷一)
宋人多讥病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认为其体制不可为法,而王若虚却力反众议,认为它:“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12]40(《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文辨三》)。他也赞赏苏轼创作中的“信手拈来”:“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衮衮笔头倾。”[12]551(《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评东坡山谷四绝》)赞赏他游戏而不刻意的创作态度:“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11]11(《滹南诗话》卷二)
王若虚又从反面指出,如果过分地求工于外,雕琢太甚,就会伤害其总体精神意绪的表达:“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11]2(《滹南诗话》卷一)将上述诗论结合起来可见,王若虚的创作论就是一种贵“天全”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道家的庄子。《庄子》一书中,“全”出现了近50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庄子把保持人的“全”视为核心价值。并且,他不仅重视“形全”,更重视“德全”,反对人为机巧对它的伤害。而道家的“德”,并非仁义道德,而恰恰是指人的自然天性。显然,王若虚的贵“天全”思想,与道家美学极为相合。
他要求诗人直抒胸臆,反对矫饰。他认为黄庭坚作品的失败就在于雕琢形式而真意流露不足:“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11]12(《滹南诗话》卷二)又说:“黄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11]18(《滹南诗话》卷三)针对金代诗坛求奇尚巧重雕琢之风,王若虚有很不客气的批评。北宋以来,轻视白居易的言论时有所见,主要讥其浅白而寻常。金代亦如是,例如王庭筠,晚年就有“近来陡觉无才思,纵有诗成似乐天”[12]552(《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评王子端四绝》)的嘲讽之句。王若虚批评王庭筠,认为白诗没有雕琢:“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11]6(《滹南诗话》卷一)在他看来,白诗恰恰好在明白晓畅,胜过王庭筠后期作品斗靡贵巧的习气。他还批评友人高思诚的创作风格,说他“子则雕镌粉饰,未免有侈心而驰骋乎其外,是又未可以乐天论也。”[12]524(《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三,《高思诚咏白堂记》)他对当朝“师心派”中刻意求怪的李纯甫、雷渊等人更有不客气的批评。因为他“贵议论文体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只欲如家人语言,……与屏山之纯大不同”[15]88(《归潜志》卷八),故而批评李“好做险句怪语,无意味”[15]88《归潜志》卷八),又质问雷“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15]88(《归潜志》卷八)他甚至为此与雷渊不和,据记载:“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故雷所作,王多改之,雷大愤不平。”[15]89(《归潜志》卷八)
(二)“文章自得方为贵”
从我国传统语境来看,古汉语的“自得”一词,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自己感到得意和舒适,另一种则指主体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心得体会。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这乃是第二义,它表现了创造性对君子求道的重要意义。由于反对向外求工,故而王若虚主张作诗不可以句法为要务,而首推“自得”:
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11]17(《滹南诗话》卷三)
宋代郑厚认为魏晋的作诗唱和是以文寓意,而宋人的次韵诗是为文害意,为文造情。王若虚赞赏他的见解,认为即使苏轼也有此弊,有害于天然、真诚的文意:“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分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11]9(《滹南诗话》卷二)金代次韵诗成风,并且到了“韵益狭,语益工,人多称之”[15]90(《归潜志》卷八)的病态程度,王若虚反对这种为诗而诗、了无新意的做法,故有此论。
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讲究师法古人,或沿袭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内容上的陈陈相因而无新意。对于江西诗派一味从古人字句中讨生活,却自夸“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做法,王若虚批评他们是因袭别人诗意,略改一二字,自以为工,是“特剽窃之黠者耳”[12]479(《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下》),而倡导“自得”:
昔之作者,初不校此(按:指夺胎换骨之说);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己。[11]17(《滹南诗话》卷三)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己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更何人?[9]291-292(《中州集》卷六,《论诗诗》)
金代中期,学习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的袭古风气盛行,在王若虚看来,古今文章互有短长,只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即可,一味拟古,就丧失了“自得”之意,也就毫无价值了:“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12]383(《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文辨一》)
(三)“文岂有定法”
从贵“天然”,重“自得”出发,王若虚反对创作中外在成法(如体制、句法、格律)的束缚,其目的就是避免以辞害意。他这样讽刺当时死抠格律而无真意的流弊:“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耳’,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11]9(《滹南诗话》卷二)所以,他对用韵的态度是:以达意为主,“意到即用,初不必校”[11]19(《滹南诗话》卷三)。
朱弁是讲究自然真意的,他反对宋初西昆体的格律拘束,却认为黄庭坚能用西昆体的形式营造杜甫的浑成之意:“(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8]16(《风月堂诗话》卷下)对此,王若虚坚决反对。他认为,昆体格律必然限制浑厚真意的表达,二者天生是矛盾的:“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盖二者不能相兼耳。”[11]18(《滹南诗话》卷三)在他看来江西诗派虽号称宗杜,黄庭坚虽善为新样,但气乏浑厚,因此并未得法。而陈师道仅从格律、句法等形式方面着眼学杜,更不过是舍本逐末而已。因此,王若虚反对作诗以句法为要务:“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11]17(《滹南诗话》卷三)所以他嘲笑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僵死地追求句法形式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11]11(《滹南诗话》卷二)
黄庭坚的诗歌究竟有没有自然流露的真意,学界至今还有所争论。不过平心而论,无论昆体功夫,还是黄庭坚、江西诗派所讲求的诗法,虽可令学者有法度可循,但也容易带来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形式主义弊端。在金代中期文坛形式主义有所抬头的时期,王若虚反对朱弁的黄庭坚之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他借贬宋而诫金,是美学史上对北宋文学流弊的第一次认真反思。
在散文这一文体上,王若虚也做出了很多反对形式束缚的理论阐述。他在回答“文章有体乎”的提问时说“定体则无”,因为“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11]22(《滹南诗话》卷三)?在他看来,写文章“唯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而“其他皆得自由”[12]426(《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四》)。所以,他主张为了“意”的自由抒发,不要拘束于“言”的形式,即文法、句法、文体的限制:“夫文岂有定法哉?意之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12]415(《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文辨三》)更具有革新意义的是,他还主张扫除整个文坛上雕琢害事的形式主义骈体文风:“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骈俪浮词,不啻如俳优之鄙……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12]426(《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四》)
不仅如此,王若虚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散文创作理论。例如,他提出文章和题目之间的言意之辨,指出题目的语言形式会影响文章“意”的表达。所以题目和文章不能出现冲突,不能出现小题目、大内容,大题目、小内容或文题无本质联系等失误。文本中的各部分要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贯通全文的“意”。文章首尾必须互相照应,求得“意”之完整等。文之胜在意而不在言,一味注重材料的丰富,实无助于凸显文意。此外,对“铭”这种文体,他说“今人做墓铭,必系以韵语……然古人初不拘此。”[12]391(《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文辨一》)即反对那种一定要用韵文来写墓志铭的做法,因为那样会过于雕琢而损害文意的自然表达。他还反对作序论及写作的缘起,认为“凡作序而并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12]394(《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文辨二》)这是因为序言是要概括文意而用的,不能跑题。
结 语
总之,王若虚的主要理论都可以视为围绕着“以意为主”命题的系统化,从而成为金代文论的高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和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几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都针对苏黄诗风而发,但二者的侧重却有差别。苏黄诗风对北方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人对尖新诗风的追求、对字句的雕琢,而对南方的影响则是诗中用典使事,卖弄才学,并以议论为诗,以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形象思维。因此,严羽以禅宗为基础,主张的是“别材别趣”、“不涉理路”的妙悟说,而王若虚以传统儒学为基础,注重的是内容自然真率、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故而其文艺思想也具有北方质朴尚实、宗经致用的特色。但难能可贵的是,王若虚没有像赵秉文那样将“意”过于狭窄化为“明王道,辅教化”的东西,他的“意”相对较为宽泛,并不如腐儒般局限于儒家政治美学,而是崇尚真实、自然和自得之情。《剑桥中国文学史》称王若虚是“金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16]513,这也体现了他在文学理论上为世界所承认的视野、格局和影响力。
[1]王先谦.庄子集解(二)[M].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1988.
[2]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3]沈约.宋书(第六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4]杜牧.杜牧集[M]. 长沙: 岳麓书社,2001.
[5]何文焕.历代诗话(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魏庆之.诗人玉屑(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8]朱弁,吴可,黄彻.风月堂诗话(及其他二种)[M]. 北京: 中华书局,1991.
[9]元好问.中州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0]惠洪,朱弁,吴沆. 冷斋诗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M].北京: 中华书局,1988.
[11]范晞文,王若虚. 对床夜雨·滹南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2]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M]. 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沈阳: 辽海出版社,2006.
[13]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
[1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上)[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5]刘祁. 归潜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6]STEPHEN OWE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Volume I)[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责任编辑:刘 燕)
“Emphasizing Contents”: An Intensive Analysis of Wang Ruoxu’s Creation Theory
Zhang Hui,Yin Ya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China)
Wang Ruoxu’s main literary theory may be regarded as a systematization of the statement “Emphasizing Contents”, and by this it became the peak of literary theory in Jin Dynasty. In sum, he played the thought “Focusing on Contents” of his predecessors, emphasizing on “natural expression” and “experience of one’s own”. He was against the external bondage in writing so as not to let the words interfere with the contents.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he made the breakthrough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the formalism bondage of “Jiangxi School”. By this, he promoted more freedom for literature.
advocating contents; natural expression; experience of one’s own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1.004
2015-10-15
章 辉(1975- ),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中国美学研究。
I206.2
A
1672-7991(2016)01-001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