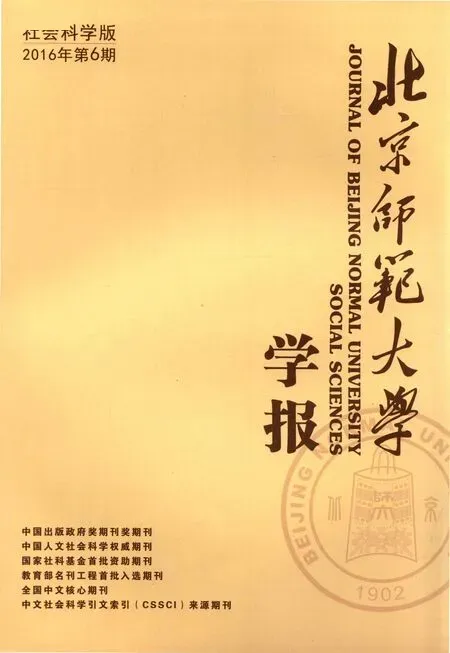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2016-12-18商浩文
赵 远,商浩文
(1.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519020;2.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赵 远1,商浩文2
(1.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519020;2.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并且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2016年“两高”制定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基于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精神,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确定,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额基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定主要考虑行为造成的物质性、经济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以体现死刑适用的慎重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则主要从贪污受贿主体、发生领域等角度考虑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贪污受贿犯罪;司法解释;死刑适用标准
一、前言
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是我国死刑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法结构、公众对于反腐败的认知以及死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等重要问题。作为典型的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贪污受贿犯罪,基于死刑的法治缺陷以及贪污罪、受贿罪的罪质特征、产生原因等因素,贪污罪和受贿罪死刑的废止是中国刑事立法发展的必然前景。但是受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尤其是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制约,从法律上立即废止或者在短期内废止严重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尚不现实,因而需要对严重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从立法和司法上予以严格控制。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了修正,将其由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的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4条第1款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补充,即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具体确定为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修法后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相对更为明确,也具有较大的司法可操作性,有助于减少司法中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促进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科学化、合理化①参见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然而《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解释》中所确立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仍然相对比较抽象,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在逐步减少并最终废止死刑的死刑改革趋势下,我们应当在司法中严格控制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而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则关系着死刑适用的现实效果,因而合理地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就成为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落实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死刑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之立法嬗变
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立法改革和司法适用问题是触发民众敏感神经的诱发物,成为当下中国刑法改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指导下,我国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立法规定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从动态上了解贪污罪、受贿死刑适用标准的历史变迁,进而为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立法改革和司法适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1997年刑法典颁行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及其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三反”、“五反”运动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惩治贪贿。为了更好地惩治贪贿犯罪,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我国有关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的有关规定最早见之于该《条例》。该条例将受贿罪涵括在贪污罪的概念下,贪污罪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的行为,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等行为。该《条例》第3条第1款对此种广义上的贪污罪定罪量刑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1项规定:“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亿元*此时为旧币制,旧币10000元=新币1元,因而当时的旧币1亿元等于后来的新币1万元。以上者,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条例》为体现对死刑适用的慎重,对于其他梯度内的刑罚采取的是绝对的具体数额定罪量刑标准,但是在对死刑的适用时,兼采数额与情节标准,也即,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1亿元以上并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方可考虑适用死刑。《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制定的一部重要的刑事法律,在1979年刑法典生效之前一直是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基本法律依据。
另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也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期间因为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刑法立法一度受阻,但是自1950年至1979年刑法典通过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陆续拟定了38个刑法草案稿。尽管多数稿本对贪污罪设置了死刑,但是在具有代表性的13个稿本中,对受贿罪规定死刑的只有5个稿本*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94、151、172、185页。这五个稿子分别是1950年7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1963年10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第33稿)》、197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联合修订组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稿)(第34稿)》、197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组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2稿)(第35稿)》。,其他8个草案稿中,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19、130、140、161、198、208、221页。这八个稿子分别是1956年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13次稿)》、1957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196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27次稿)》、1963年10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第33次稿)》、1979年3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法制委员会修正一稿)(第36次稿)》、1979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法制委员会修正二稿)(第37次稿)》、1979年6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86次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也不断完善。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在其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刑罚进行了有关规定。1979年刑法典仅对贪污罪的刑罚配置了死刑,该刑法典155条规定,“贪污公共财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对受贿罪并未配置死刑,其法定最高刑仅为15年有期徒刑*1979年刑法典第185条规定:收受贿赂,“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法典第40条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在规定贪污罪死刑时,改变之前《条例》规定的“数额+情节”二元定罪量刑标准,采用的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一元标准。
1979年刑法典实施后不久,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大规模的走私、投机倒把等系列经济犯罪活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受贿、索贿并包庇、纵容经济犯罪活动。为此,1982年初,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开展旨在严重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此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包括受贿罪在内的6种犯罪*另外5种为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了死刑*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上述决定仅仅解决了相关犯罪的刑罚问题。为进一步解决相关犯罪在犯罪主体、认定标准等方面的问题,1988年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1979年刑法典和《决定》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数额的多少和情节的严重,将贪污罪和受贿罪划分不同的量刑幅度。其中,关于贪污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为“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该《补充规定》第2条第1款第1项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⑴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为“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该《补充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处罚;受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补充规定》对贪污罪采取的是绝对确定的死刑立法例,而对受贿罪设置的是相对确定的死刑立法例;对于贪污罪采用的是“具体数额+概括情节”的死刑适用标准,而对受贿罪确立的是“具体数额+相对确定情节(危害结果)”的死刑适用标准。
(二)1997年刑法典颁行之后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及其分析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该刑法典第383条第1款将贪污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规定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第385条规定对于受贿罪依据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相比较1988年的《补充规定》,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受贿罪适用死刑的标准由“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统一修改为贪污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同时,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受贿犯罪采用的是绝对死刑的立法模式,其适用标准是“具体数额+概括情节”的标准,即除了要达到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上的标准之外,还要求案件情节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立法的这种规定显然是出于慎用死刑的考虑。但由于贪污受贿数额过于刚性,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条件又太过于概括和抽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应对防治腐败犯罪的现实需要。
为了因应腐败犯罪治理的现实需要并贯彻严格控制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精神,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贪污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即我国贪污罪、受贿罪适用死刑要求是贪污受贿行为危害最为严重的情形。《刑法修正案(九)》改变了贪污受贿犯罪绝对死刑的立法例,将无期徒刑和死刑同时作为严重贪污受贿犯罪的可选择刑罚,同时修法后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相对更为明确,并具有较大的司法可操作性,使得司法人员有一定的刑罚裁量空间,能够依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处以不同幅度的刑罚,进而有助于促进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司法限制。这一立法修改有两点显著的进步:(1)明确了贪污罪、受贿罪死刑适用的条件,限制了死刑适用范围。较之于修法之前的贪污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这一标准更为明确,并且将贪污罪、受贿罪死刑适用的条件严格限定为“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这唯一情节上,立法更为简洁、更为明确,有助于促进死刑适用标准的明确化、规范化,有助于促进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2)摒弃了贪污罪、受贿罪绝对死刑的立法模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受贿犯罪采取了绝对确定的死刑立法模式,即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只能适用死刑。这种立法模式不利于通过司法途径限制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的适用。《刑法修正案(九)》将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列作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犯罪适用刑法的可选择刑种,使得司法人员能够依据具体案件的具体犯罪情节进行合理裁判,有助于严格掌握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标准。
(三)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之立法变迁分析
1.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
由上可见,我国刑法立法对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规定经历了从具体数额与情节相结合到只规定情节,再到具体数额与相对确定情节相结合,又回到具体数额与概括情节相结合,最后才确立为“概括数额+相对确定情节(危害结果)”的历史发展脉络。笔者认为,由于死刑作为贪污受贿犯罪中最为严厉的刑罚,因而也应只适用于犯罪情节最为严重的犯罪。是故,对其死刑的适用标准应当极为严格,需要严格控制。一般而言,犯罪数额也属于犯罪情节,但是犯罪情节过于抽象、概括,不利于明确死刑适用的情形。而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中所起作用较大,而且犯罪数额又易于判断,在是否适用死刑时,一般都会将犯罪数额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单独的数额标准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贪污、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且数额标准过于僵化,因而必须与“柔性”的情节标准相结合,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贪污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参见卢建平、赵康:《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这也是我国历来刑事法律中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绝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二元标准的重要原因。
然而犯罪情节则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判断,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罪前、罪中、罪后等体现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各种主客观要素*参见王莹:《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如果刑法立法仅仅对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规定一个笼统、抽象的情节标准,势必不利于司法实践对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统一掌握。更何况,死刑是最为严厉的刑罚种类,对其适用应当慎之又慎、严之又严。如果犯罪情节标准过于抽象,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滥用。因而应当从立法上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确立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情节标准确立为“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体现了死刑适用标准立法的相对明确化。
2.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
不同时期的货币代表的社会财富不同,不同时期的贪污受贿数额所征表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因而具体的数额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很大,相同时期的不同区域的相同贪污受贿数额,其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容忍度也不一致,具体数额显然很难全面适时反映贪污罪、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国既往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立法中多次采用具体数额标准实为不妥。而确立概括的数额标准有助于司法机关依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较为灵活地确定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数额标准,以全面、及时反映贪污、受贿数额所体现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就此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中确立概括数额标准的模式较为科学,有助于司法者及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对死刑适用的数额标准进行调整,也可以有效避免刑法立法的频繁修改进而保障刑法的稳定性。事实上,“两高”《解释》也在此基础上对死刑适用的概括数额标准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细化,该《解释》第3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贪污受贿犯罪应当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
绝对确定的死刑,是指立法者在对相关犯罪仅仅配置单一的死刑刑种,而没有配置其他种类的主刑。由于绝对确定的死刑不利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司法人员对于具体案件的合理裁量,因而在现代刑事立法中已极为少见*参见王志祥:《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政法论丛》,2016年第3期。。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要结合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由于绝对死刑排斥了相关量刑情节对于案件量刑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量刑失当,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明确强调反对适用绝对死刑*参见赵秉志、徐文文:《〈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
在1952年的《条例》中,立法者将贪污罪(实则包含受贿罪)的死刑确立为绝对确定的死刑。也即“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亿元以上者,且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1979年刑法典仅对贪污罪规定了死刑,规定的是相对确定的死刑,即“贪污公共财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1982年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在对受贿罪配置死刑时,采取的也是相对确定的死刑立法例。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采取的是绝对确定的死刑模式,即“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对受贿罪设置的是相对确定的死刑模式,即“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1997年刑法典将受贿罪和贪污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并设置了绝对确定的死刑模式,即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由于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违于刑事责任公平原则之要求,故而此种死刑立法例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饱受诟病*参见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罪、受贿罪绝对确定死刑的法定刑模式改为相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有助于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也大有裨益。
三、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之司法确定
不可否认,《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的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较之于以前的立法模式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相关量刑情节均相对概括,仍然具有较大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为了进一步区分贪污受贿犯罪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量刑标准,“两高”《解释》第4条第1款对于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作了进一步具有强调性和补充性的规定,即“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两高”《解释》关于“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是对《刑法修正案(九)》的照应性规定、强调性规定,而关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规定则是合理的补充性规定。
(一)“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之确定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依据修法后的规定,其首要条件是需要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这是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数额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正确指导定罪量刑,上述概括数额必须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数额。笔者认为立法上概括数额的确定属于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不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而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来掌握适用的数额标准,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规范法官裁量权。因而笔者赞同在借鉴以往行贿罪、介绍贿赂罪、挪用公款罪等腐败犯罪的数额标准认定之方式,由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司法解释对相关的数额标准进行明确*参见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2016年“两高”《解释》第3条将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明确为贪污受贿300万元以上*2016年“两高”《解释》第3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虽然行为人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标准,但是这里“数额特别巨大”既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条件,也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处罚条件之一。那么死刑适用标准之“数额特别巨大”中的数额是否与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中的“数额特别巨大”相等同呢?笔者认为,判处死刑的“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有自己的适用标准,而不宜与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数额特别巨大”相同,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的经验以及基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思想的指导下,确定显著提高的死刑适用数额基点。主要理由在于:首先,从犯罪数额所表征的社会危害性来看。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其对应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应当是最为严重的。不同刑罚对应的犯罪数额应当有所区别,如果将“数额特别巨大”中的具体数额作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适用的相同条件,这样不利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而死刑适用标准之“数额特别巨大”中的数额标准应当在300万元的基础上有显著的提高,以利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既往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中,行为人单纯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元也都未判处死刑,尤其是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故而司法实务中对于死刑适用标准中的“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从严掌握。其次,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的角度来看。“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当下中国死刑政策的基本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死刑适用的数额标准,是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死刑政策的需要,体现了慎用死刑的法治思想。虽然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必须同时具备数额标准和危害结果标准,但是只有对每一种适用条件加以严格限制,方能更好地控制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再次,从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统一标准来看。2007年1月1日,我国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判处死刑的裁决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方可生效。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只有确立不同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适用数额,才能在死刑复核时确立统一、易于操作的复核标准,否则将会引发复核标准的混乱。至于具体死刑适用标准中数额基点的确定,笔者建议,在参考司法审判的经验以及基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思想的指导下,较为理想的选择是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在确定一定的死刑适用数额基点后,一旦低于该基点,就绝对不应适用死刑;而如果达到这一犯罪数额,则有可能判处死刑,但也不一定适用死刑,是否适用死刑还需结合案件的多种情节进行综合考量,毕竟犯罪数额仅仅是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标准之一。
(二)“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之认定
“损失”,从字面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名誉、财物、利益等丧失”。在刑法学界中,“损失”一般被理解为行为造成的“财物、利益等减少或者丧失”。关于“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这是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危害结果”标准。在以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中,明确指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受贿案件有胡长清和郑筱萸受贿案等案件。但是司法裁判中并未对该“重大损失”情节进行相关论证,该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力有多大,难以明确,从而不利于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裁量。因而基于刑法明确性以及司法操作的便利性考量,应当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进行适当明确。
关于“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类型化的解读,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罪质较为类似的渎职犯罪中认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标准,对此进行明确。我国刑法典对渎职犯采用的是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犯表述方式。对于损失的认定,2006年之前的关于渎职案件的立案标准主要是从物质性的损失方面进行认定的,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不仅对物质损失作了较为具体的列举,也列举了非物质性损失的危害结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施行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也将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等情形。区分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可以结合质的标准、量的标准以及质与量相结合的标准来认定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于不能以货币计算其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有时难以认定其损失大小。如果能够借助于其具体造成的物质性损失程度,大致可以推断出其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失的程度。因而在认定时,才能从“量”和“质”的统一上来确定损失的数额和程度,正确把握损失的标准。借鉴渎职罪认定“危害结果”的方法,我们在认定贪污罪、受贿罪死刑适用标准时,也可考虑将“特别重大损失”划分为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但是由于“两高”《解释》已经将“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单独作为量刑评价因素,此处的“特别重大损失”应当重点考虑贪污受贿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质损失等犯罪情节,并且以相关指导性案例和量刑指导意见加以明确,以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能够相对统一、明确,从而有助于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统一和死刑的司法控制。
物质性损失主要是指犯罪结果表现为物质性变化的形态,一般来说是有形的、可测量的*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贪污受贿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性损失一般表现为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亡、人的健康损害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失。贪污受贿造成人员伤亡比较好理解,然而司法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贪污受贿犯罪的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并不能截然分开。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职务义务的行为,一般会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此时造成重大的物质性损失的同时也会附随地产生非物质性的损失。
(三)“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之认定
“两高”《解释》中增加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作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补充。对于“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一般是指贪污受贿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失,即非财产性和人员伤亡性、健康伤害损失。司法实践中的物质性损失相对容易掌握,但非物质性损失往往难以具体量化。一般而言,非物质性损失呈现出不可量化、多样性、常识化等特征*参见范艳利:《认定渎职犯罪“重大损失”需解决三个问题》,《检察日报》,2015年6月17日,第3版。。对于非物质性损失的衡量,迄今尚无较为明确的司法解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施行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中的非物质性损失界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刑法典第412条商检失职罪和动植物检疫失职罪中的非物质损失解释为“引起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严重影响国家外经贸关系,或者严重损害国家声誉的”。再如第398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中的非物质损失被解释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防安全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这些表述非常抽象、笼统,难以对司法实践给予明确的指导。
因而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相关情节进行明确。虽然,对非物质性损失作出明确界定较为困难,但是有必要确立相对具体、明确的标准,以指导司法实践。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渎职犯罪中的非物质性损失界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由于贪污受贿犯罪和渎职罪同属于职务犯罪,可以参考渎职犯罪司法解释中认定“非物质性损失”之标准,明确界定贪污受贿犯罪的非物质性损失。根据现有的刑法理论界的相关研究,结合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性质和特点,笔者以为,对于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中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量:第一,贪污受贿主体为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公信力。第二,贪污受贿行为发生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贪污受贿行为对国计民生、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第三,贪污受贿行为在相关部门、地区引起不好风气,导致系统性、塌方性腐败。第四,贪污受贿行为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我国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威信与被信任度在国际上严重受损,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造成恶劣影响。
(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确立
以上是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数额标准和危害结果标准。但是,即使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符合相应的数额标准和危害结果标准,也不一定就判处死刑。因为《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是相对确定的死刑立法模式,符合上述标准,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判定贪污受贿分子是否适用死刑,还需结合刑法总则中关于死刑适用的总体标准来进行判断,即不仅需要考虑社会危害性,还需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只有综合相关事实,罪行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方能判处死刑*参见储槐植:《死刑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1.行为人主观恶性极其严重
主观恶性是行为人支配其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7页。。主要是通过犯罪本身的各种事实,特别是犯罪构成事实和重要的量刑情节表现出来*参见彭新林:《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6页。。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所有权,受贿罪的罪质在于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因而在判定行为人是否适用死刑时,行为人出卖公权力的动机与目的,是反映行为人贪污受贿行为危害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这种主观因素可以通过案件中的相关情节加以反映。一般来说,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主要通过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故意程度、犯罪手段等因素表现出来。例如,贪污受贿犯罪所得的用途(是否用于非法活动)、行为的连续性程度、犯罪的形态(共同犯罪抑或单独犯罪)、行为的持续时间、具体行为的实施时间(顶风作案抑或闻风停止)*这一点在中纪委的相关通报中已经有所反应。例如,2015年2月中纪委在对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长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等人的查处通报中,明确指出他们在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再如,2015年10月16日,中纪委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的通报中提到,余远辉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纪党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等等。
2.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
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我国刑法的一般理论认为,案外情节是揭示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反映了行为人对犯罪肯定或者否定的认识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案外情节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考量。一般来说,人身危险性主要是从犯罪分子一贯表现、个人情况以及罪后态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衡量的*参见彭新林:《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7页。。在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中,除了要考虑刑法典中规定的自首、立功、坦白、积极退还赃物、认罪悔罪等法定情节外,还应结合司法实践考量一些基本的酌定量刑因素,比如,犯罪后是否外逃、是否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串供、是否打击举报人、犯罪后是否为对抗侦讯继续实施犯罪、犯罪后是否向查办人行贿,等等。大体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具有肯定适用死刑及死刑执行方式选择的作用,而人身危险性一般起着否定死刑适用或者影响死刑执行方式选择的因素*参见赵秉志主编:《死刑个案实证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
3.其他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犯罪情节,一般是指具体案件中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情况。死刑案件一般都存在体现其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情节。如果不具备最严重的情节,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由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上文已作详细论述,此处的犯罪情节主要是指体现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情节。犯罪情节主要结合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客体、犯罪对象等因素进行判断。比如,行为人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募捐等特定款物的;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等。此处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其主要考量的是司法解释中已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之外的能够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相关情节,这就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的因素考虑的更为全面,体现了死刑适用的慎重性。
四、结语
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达到了上述死刑适用标准,原则上都可以选择适用死刑。但是在“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指导下,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已很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绝大多数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贪污贿赂罪犯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制度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优先适用方式。事实上,“两高”《解释》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即使行为人符合该条第1款的死刑适用标准,但是如果“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死缓是对于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执行方式之一,属于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最为严重的刑罚执行方式之一,对于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死刑缓期执行能够满足广大民众要求严惩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社会心理,也能够从事实上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更何况,《刑法修正案(九)》也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更为严格,因而对于特重大贪污受贿罪犯适用死缓,一般就不会再被实际执行死刑。而且《刑法修正案(九)》中确立了对严重贪污受贿犯罪的死缓犯予以终身监禁的制度,该制度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这样将会导致死刑立即执行在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中逐步没有适用的余地,进而将会从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停止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因而为了进一步发挥死缓制度限制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功能,我们有必要充分发挥贪污受贿犯罪相关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适用之影响力,将死缓制度作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优先适用方式。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孟大虎)
R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Death Penalty Standards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
ZHAO Yuan, SHANG Hao-wen
(1. School of Law,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519020;2. School of Law,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Through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on death penalty of corruption crim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can be drawn that death penalty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has taken the dual standard of “amount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plus gravity of circumstance”. Penal legislation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on death penalty is appropriate for estimated amount, and the absolute mode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and the People’s Supreme Procuratorate in 2016 enacte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cases on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to a number of issues”, which established specific criteria of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s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on the basis of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x)”. 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trict control of death penalty, the determination of “extremely huge amount”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shall be decided on judicial experience; the judgment of crimes that ”cause heavy losses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should be focused primarily on material and economic losses; the standard of “particularly serious crime” mainly emphasizes the overall provision of death penalty, which should reflects on the caution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ularly bad social impact” i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corruption body, occurrence area, among others, which may cause bad influence to the society.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tandards of death penalty
2016-09-05
中国法学会“反腐法治研究方阵”。
D914
A
1002-0209(2016)06-01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