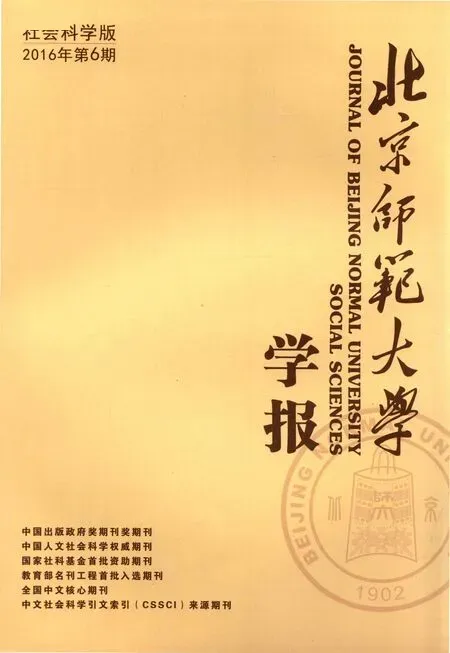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
2016-12-18周剑之
周剑之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
周剑之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启文是宋代士人在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后依然保持骈体写作的一种应用文体。就使用频率而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几乎覆盖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启文的应用语境,是以科举制度和职官选任制度为基础所形成新型士人关系网络。这种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直接影响了宋代启文的发展方向及语体选择。宋代启文以应酬为核心功能,礼仪性得到充分强化,并展现着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文学才能。同时,宋代启文也深度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启文与士人关系网络之间的微妙互动,折射着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风貌与人文关怀。
启;宋代骈文;士人关系网络
在宋代士人的写作生涯中,应用文体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分量。宋代应用文体不但种类繁多、应用广泛、与士人生活密不可分,而且以审美性与实用性的交互融合,构建着宋代文学的整体风景。然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文体的地位并不相称。研究者往往聚焦于诗、词等审美性更为突出的文体,而对表、启、书、疏等应用文体有所轻视。如此呈现出来的文学史面貌,是不完整的。
对应用文体的深入考察与系统观照,是宋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方法上看,研究应用文体的关键,是对其应用语境作细致的探究。唯有如此,才能揭示该文体的核心功能、文体特性及演变趋势。而“启”是宋代覆盖面最广的一种应用文体,因此,本文对宋代启文及其应用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代启文的“新变”与“不变”
从性质上说,“启”属于书信的一种。古人写作书信,依据对象的不同,在文体选择上是有所区别的。所谓“尊卑有序,亲疏得宜,是又存乎节文之间”,若是亲密友人,可用书牍、简帖,多用散体,较为自由;而“施于尊者,多用俪语以为恭”,亦即多用启文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四六丛话》对启有极为精准的定位:“若乃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明慎之旨,侔书为有余,则启是也。”②孙梅:《四六丛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启”的恭敬程度,介于“表”与“书”两种文体之间。就“启”的发展历程而言,其出现大约始于魏晋,到南北朝时已具备相对固定的形制,作为一种文体基本成熟;唐代启文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但大体延续了六朝时期的文体特征③参见钟涛:《试论晋唐启文的体式嬗变》,《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而到了宋代,启文的发展骤然呈现井喷之势,不但极度繁盛,并且衍生出不少值得注意的现象。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宋代启文的繁盛程度。宋代启文使用频率之高、写作数量之多,均远超前代。就使用频率而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四六标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96页中。。几乎覆盖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写作数量而言,今存宋人启文极多,难以篇计。宋人文集大多收录启文,且数量不在少数。欧阳修有《表奏疏启四六集》收“启”五十余篇,而这仅是欧阳修启文的一部分。周必大编欧阳修文集时曾指出,应用性文章在欧阳修文集中留存不多,“监司、邻郡往复书启,亦仅有之。”*《欧阳修全集》,卷九六,《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七,《与颍州吕侍读贺冬状》后周必大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80页。欧阳修实际写作的启文应比文集所收更多。王安石《临川集》,收启近百篇。苏轼《苏文忠公全集》,收启百余篇。到南宋时,人们愈加注重启文的收录,周必大《文忠集》,卷二一至二七收录启文共二百五十余篇。又如孙觌《鸿庆居士集》,仅贺冬启就占一卷,贺正启又占一卷。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全为启文的别集,李刘《四六标准》四十卷、李廷忠《橘山四六》二十卷、方大琮《壶山四六》一卷,所收全为启文。这类以启文单行的书籍,同样前所未有。在宋代诸文体中,就应用的广泛性而言,很少有文体能与启相提并论。
与这一“新变”形成鲜明映衬的,是宋代启文在语体上的“不变”——以骈体行文。启文用骈体,是该文体自诞生以来形成的写作惯例。从六朝到唐代,虽偶有散体启文,但总体上以骈体为主流。从这一点上说,宋代启文使用骈体,是对前代传统的延续,是一种“不变”。然而,联系北宋散文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不变”却十分耐人寻味。
我们知道,北宋古文运动改变了文章写作的骈散格局,散文取得了优势,骈体的影响在许多文体中日渐消退。不过骈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非但没有退出,反而在一些文体中得到强化,形成骈文与散文分疆而治的局面。宋代骈文有“宋四六”之称,是骈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启”即是宋代保留骈体的文体之一,也是宋四六的代表性文体之一。宋启对骈体的贯彻,比宋前更为彻底。宋前尚有不少散体启文,如柳宗元、杜牧等人的作品,宋代散体启文则非常少见;宋前启文会不时杂入散句,与四六句式间错而行,宋代启文则更为严格地遵循四六句式与骈对规则。如此看来,宋启对骈体的坚持并非被动的“不变”,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以上的“新变”与“不变”,都是启文发展到宋代显现出来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启”这一文体在宋代的演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疑问:为何启文会在宋代出现空前繁盛的局面?为何在历经古文运动的淘洗以后,启文仍然选择了骈体?启文在宋代士人的写作生涯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二、宋代启文的应用语境:新型士人关系网络
从本质上说,启属于一种应用文体。作为应用文体,必定是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有其具体的应用语境。其文体形态的生成,往往植根于应用语境的需求。而应用语境的变化,也往往是促使文体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因此,要想解释宋代启文的“新变”与“不变”,对这一文体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必须回归其应用的语境。
那么,宋代启文究竟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被使用的?其应用语境与前代相比是否发生了变化?又在哪些层面发生了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宋代文集中启文的分类方式入手。这是既直观又便利的一种考察方式。因为古人在对同一文体的不同文章进行分门别类时,很自然地会依据该文体的用途、性质、等级等作进一步的区分。乍看貌似普通的分类,实际上包含着当时人们对这一文体及其应用的基本认知,也是对其应用语境的充分呈现。
如《文苑英华》卷六五一到六六六收录启文,共分十二类:谏诤、劝学、荐士、贺官(附杂贺)、谢官、谢辟署、谢赐赉、杂谢、谢文序并和诗、上文章启、投知、杂启。这些类别主要是依据启文的具体用途来区分的。《文苑英华》是宋初编定的大型总集,广收《文选》以下、宋代以前诗文。其对启文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北朝至唐代启文应用的基本情况。
与《文苑英华》相比,宋代对启文的分类要复杂得多。宋人魏其贤、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下文简称《播芳大全文粹》)是一个极佳的样本。这是一部宋代文章总集,收录作者达五百二十家,涉及三十多种文体,网罗极富,因而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其中卷八至卷四十九为启文*魏其贤、叶棻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卷四十九为通启状,一半是启,另一半是状。。对比《文苑英华》,该书的启文分类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多层级的分类。《文苑英华》的启文分类仅有一个层级,而该书分类有两个层级。第一层级相对简明,按照启的用途,分为贺启、谢除授启、谢到任启、谢启、上启、回启、通启七大类,与《文苑英华》相似。不过在这些大类之下,还有第二层级的分类。
其次,第二层级的分类极其琐细。七大类中最琐细的是贺启,分为:
师保、左相、右相、元枢、大参、知枢、枢贰、签枢、使相、八座、西掖、翰苑、琐闼、馆阁、经帷侍讲、大坡、小坡、察院、中司、南床、副端、贰卿、承辖、都丞、卿监、史掖、史馆、学官、爵封、加职、迁秩、被召、宫观使、致仕、宰执除帅府、宰执除帅守、侍从除帅、帅臣、京兆、都督、宣抚、太尉、制置、察访、总领、总管、奉使、茶马、泉使、舶使、漕使(按,由于卷二十阙,此处应还有其他分类)、宪使、仓使、两外宗、太守、治中、帅司属官、诸司属官、州官、县官、监官、兵官、试中科目、贺正、贺冬、生日、杂贺。*见《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目录,下文所举细目则见于每卷卷首。
将120 mg上一步得到的核壳结构SiO2/Fe3O4-C颗粒分散于60 mL超纯水中,再加入0.3 mL 25%的氨水,室温下搅拌30 min。得到的混合液转移至密闭的高压反应釜中,于150 ℃下水热反应6 h。反应结束后,待产物冷却至室温,用磁铁将其分离出来,超纯水清洗3次后,即可得到最终的Fe3O4-C磁性空心微球[8]。
考虑到书中阙了一卷,则贺启第二层级分类当不少于上面所列出的67种。更令人吃惊的是,不少二级类目下还注明了更细的类型,如“西掖”类目下注云“中书、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馆阁”下注云“修撰、秘阁、校理”,“贰卿”下注云“吏侍、户侍、礼侍、兵侍、刑侍、工侍”,“试中科目”下注云“馆职、贤良、状元、及第、发举”等等。这些细目甚至可视作第三层级的分类。其余几大类之下的二级分类方式,大同而小异。分类繁琐的程度,几乎令人目眩。
这种分类方式并非《播芳大全文粹》所独有。南宋李刘《四六标准》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部全由启文组成的别集,同样由两级分类构成,不过稍有不同的是,繁琐的是第一层级,主要类目为:
言时政、贽见、荐举、举科目、谢座主、谢到任、谢解任、通交代、谢除授、谢辟置、举自代、宣赐、被召、进职、转官、改官、宫观、致仕、杂谢、谢惠诗文、科举、及第、生辰、婚姻、师传、宰相、参政、枢密、中书、史掖、六部、枢属、台谏、寺监、学官、宫教、六院、架阁、制帅、经略、安抚、总领、都大、提舶、漕使、宪使、仓使、宗正、太守、倅、诸司属官、教官、州官、武官、寄居官、宰、丞、簿、尉、监官、学职、进士、贺正、贺冬。*李刘:《四六标准》,目录,《四部丛刊续编》本。
第二层级则按用途分为谢启、贺启、回启等不同类型。如“荐举”一类,就包括谢荐举、求荐举、回他人谢荐举等三小类。也就是说,其分类的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恰好与《播芳大全文粹》对调。形式虽有小异,实质却相差不远。
《文苑英华》与《播芳大全文粹》《四六标准》,对启文的分类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繁琐的分类,是在宋代才出现的。宋前启文的应用情况,远没有这么复杂。这充分说明,“启”在宋代的使用不但日益增多,而且日趋专门化,《文苑英华》那样的分类方式,已远远无法涵容宋代启文的复杂性。
为何宋启会有如此琐细的分类?这种分类方式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妨回头再看《播芳大全文粹》,寻找其分类的依据。第一层级按用途分谢启、贺启、回启等,这与前代是相似的,因此关键在于第二层级的分类依据。上文所引的贺启分类,除了最后的贺正、贺冬、生日、杂贺外,其余类目均为职官名称或升迁情况。类目名使用了许多职官的简称或通俗称法,如“元枢”指枢密使,“大参”即参知政事,“南床”指侍御史等。可见,第二层级分类的主要依据,是收受对象的身份,而这个“身份”,确切来说指的是职官。宋代启文写作者和收受者的关系,通常与亲情、友情关联不大,而主要体现为与职官相联系的一种社会关系。
从具体的作品也能看出,启文确实与职官选任密不可分。士人请谒,需要投启。参加州府解试,中选者需以启谢主考官。进士及第,也需谢启,欧阳修有《谢进士及第启》以及代当时状元王拱辰所写的《代王状元谢及第启》。若得馆职,“例有谢启”*王铚:《四六话》,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页。,秦观除正字,有《谢馆职启》。如遇官职升改,则需以启谢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如刘敞《知永兴军谢两府启》、苏轼《登州谢两府启》等。上司、同僚官职升改,则需贺启,欧阳修致仕时,苏轼、苏辙、毕仲游等皆有《贺欧阳少师致仕启》。到某地任职,向本地官员或邻郡官员致意,则为通启。离任时对于继任官员,又有交代启。收到他人的启文,还需回复,如方岳知南康军,主持发解试,中选者均有谢启,方岳第一一回复,其《秋崖集》卷二十三存其回复南康军举人第一名至第十五名的启文……种种应用类型,已可以从《播芳大全文粹》《四六标准》中大致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启的使用可能要比文集的分类更广。启文可说伴随着士人仕途的全过程。
由此可知,相较于宋以前,宋代启文的应用日趋复杂化,职官制度成为启文应用的重要依据。以职官制度为基础所形成新型士人关系网络,此即宋代启文的应用语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新应用语境是如何生成的、它对启文又有怎样的新诉求?
三、宋代启文的核心功能与文学选择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领导阶层亦即士大夫阶层,也正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从血统决定的门阀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决定的科举士大夫*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对这一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宋代已基本进入科举士大夫占据领导地位的时代,不但科举制度完全定型,职官选任制度也日渐成熟。与此相应,通过科举、进入职官选任体系、加入士大夫行列,成为宋代士人*本文所说的“士大夫”、“士人”,采用学界通行的定义。“士人”取其广义,既包括以成为士大夫为目的的士人,也包括已成为士大夫的士人。普遍追求的人生道路。既然士人的立身依据发生了变化,那么士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随之改变。在门阀士大夫居于领导阶层的时期,士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建立,更多依赖血缘、婚姻等方面的联系。而在科举士大夫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士人之间的联系,则更多建立在科举制度与职官选任制度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
与旧的士人关系网络相比,宋代新型士人关系网络具有两项突出特征。第一,这一关系网络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只要达成某些条件,即有希望跻身其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情形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相较于一经生成便难以改变的血缘关系和门阀体系,职官的升降是复杂多变的,因而这一关系网络时常处于变动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富于开放性与流动性的关系网络中,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加以维系,或促成转变。第二,加入这一关系网络并参与其流动的必备条件,是对古代典籍知识的掌握及诗文写作的能力。这是科举考试最为核心的要求,是职官选任制度尤为重要的依据,因而这也是士人身份的证明,是加入士人关系网络的基本资格。
这个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需要新的建构方式。参加科举当然是其中最核心的方式,而围绕着科举与仕途,又衍生出许多具体形式。比如士人干谒的行为,通过谒见有影响力的官员或名人,以获得他们的赞赏和推荐,从而使仕途道路更为顺利。又比如入仕后与各级官员的公私交往,妥善处理与上级、平级和下级的关系。基于这样的需求,新型士人关系网络召唤一种与之相应的文体,这种文体应当同时承担两项功能:一、普泛地建构关系的功能,能够通过这一文体来实现士人关系的普遍勾连;二、直观地反映才学的功能,能够鲜明体现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文学才能,并维持士人阶层的特性。这两项诉求,源自新型士人关系网络的基本特征,并直接影响了宋代启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启文“新变”与“不变”的深层原因,也都植根于此。
首先,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促使启文进一步朝着应酬化方向演进。“启”成为宋代最基本的应酬文体,广泛参与着士人的日常交际。与宋前相比,宋代启文的应酬性更为突出,事务性则趋于弱化。《文苑英华》所收的宋前启文中,许多都包含了非常实际的、事务性的诉求,尤其是谏诤、劝学、荐士等类目下的启文。作者希望通过启文达成某些具体的结果。也是由于这一点,宋前“书”与“启”这两种文体有时是极为相似的。而在宋代,事务性的启文日趋减少,应酬性诉求占据主导地位。启文写作大抵基于应酬的需要,作者通过启文所传递的,主要是感谢、祝贺这样一些类型化的情感。而真有事务性诉求时,宋人更倾向于选择“书”或其他文体。我们会发现,同一作者写给同一个对象的“启”和“书”,会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如刘克庄写给贾似道的贺启《贺贾相启》,极尽恭维之能事,而在同时所写的《与贾丞相书》中,则引周公、谢安事典,试图说明立功名易、保功名难,戒其勿蹈覆辙*对二文的分析参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前言部分。王蓉贵、向以鲜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二者的区别,本质上是两种文体功能的差异。规诫之语,可在书信中说。而应酬用的启,则只能是称赞颂美。
应酬是与礼仪紧密相连的。启文的投递,在宋代成为基本的交际礼仪。宋人相当重视启文写作,因为这关系到对他人的礼貌与尊重。据《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宋庠知扬州时,签判代作贺启三首。宋庠对其中一首不甚满意,于是提笔修改,涂抹殆遍。后人看到手稿,不由感叹:“前辈于礼仪语言间,谨重如此。”*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5页。启文写作作为一种基本礼仪,成为士人交际应酬中的惯例。宋仁宗时,王随知杭州,见隐士林逋的居处颓坏不堪,拿出自己的俸禄加以修缮,林逋为此专门作启,表达感谢*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宋徽宗时,蔡子由推荐隐士陈易入朝为官,陈易以启表示回绝:“心若死灰,枉被吹嘘之力;身如槁木,难施雕琢之功。”*彭乘:《墨客挥犀》,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1页。本应不问世事的隐者,在与士大夫交往时也不得不遵守基本礼仪。可见启文写作已成为士人阶层的潜在规约,是生活在这一社会语境中的士人的必要行为。宋代启文应用的范围与频率远超前代,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其次,宋代启文之所以使用骈体行文,也与其所承载的功能相关。一方面,骈文能够更好地满足士人之间交际礼仪的诉求。“施于尊者,多用俪语以为恭”。尽管宋人推崇古文,但在涉及礼仪问题的时候,宋人对骈体是持正面态度的。司马光虽以不擅骈文的理由拒绝出任知制诰*司马光:《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诰启》,《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他却颇为严格地遵循书启往来的惯例,并未因不擅骈文而有所轻视,甚至比许多人注重这一点。据《四六谈麈》所言,谢伋曾亲眼见到司马光认真答复外地郡守的贺启,反倒是徽宗以后,“宰执多不答外郡书启”,不如司马光那么遵守礼节*谢伋:《四六谈麈》,《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宋人曾言:“岂应用之文特礼不可废者?”*韩元吉:《跋邓圣求除拜帖》,《南涧甲乙稿》,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8页。宋代的“应用之文”,指的就是骈文。朱熹虽然反对以词科骈俪取士,但对于骈文所体现的礼数,仍然表示认同:“作应用之文,此等苛礼,无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3页。宋人吴奂然在《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言中则说:“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叶棻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明王宠父子合抄本。在酬酢应用当中,骈文有着古文不能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宋代启文选择骈体,又与其所承载的第二项功能有关:直观体现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文学才能。如前所言,对古代典籍知识的掌握及诗文写作的能力,是科举考试的核心要求,更是士人阶层的基本特性。就呈现文学才能的直观性而言,骈文胜于散文。骈文写作既需要深厚学养作为支持,又需要相当娴熟的文学技巧,还需要敏捷的才思,因而被称为“敏博之学”*② 刘壎:《骈俪·总论》,《隐居通议》,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页。。这是士人必备的技能,“不者,弗得称文士。”②被认为是士林华选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任,在内外制的撰写中,也是以骈文为主的。因此,启文写作并不单是应酬而已,还是身为士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展现士人才能的直观有效的方式。那些优秀的启文,总会获得时人的称赞,并播于众口。如秦观《谢馆职启》云:“西蜀中郞,孔明呼为学士;东海钓客,建封任以校书。虽为将相之品题,且匪朝廷之选用。”特意选取历史上秦姓人物的典故,即所谓的“当家故事”:被诸葛亮尊称为学士的秦宓,被张建封奏请授予校书郞的秦系。秦观将自己与二人对比,说自己既有“将相之品题”,又得到“朝廷之选用”,比二人更加幸运。用典贴切精当,得到时人一致称赞*《四六话》,卷下,第18页。。宋代的笔记、诗话及文话中,有许多对启文名篇名句的赞赏,可见士人阶层对文学才能的重视。宋代启文选择骈体,与士人阶层的文学特性相契合,有利于作为文化主体的士人阶层保持其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权威。这是宋代启文选择骈体的又一原因。
总之,随着科举制度与职官选任制度的成熟,宋代形成了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构筑了启文应用的新语境,并在新语境中滋长出相应的诉求,直接决定了宋代启文的核心功能及文学选择。
四、宋代启文的“联网”效应
在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应运而生的宋代启文,反过来也对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联网”效应,参与着宋代士人阶层的发展与演生。
启常常成为士人关系建立的契机,或增进士人关系的润滑剂。许多士人的结交,始于启文的相互投递。韩驹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著名士大夫,绍兴初年寓居临川,汪藻知抚州(治所在临川),二人以启相通。韩启今已不存,汪藻回启《知抚州回韩驹待制启》则见于《浮溪集》。其中有云:“服膺有日,识面无繇。……承作者百年之师友,为斯文一代之统盟。何幸余生,获陪胜会。载酒而问奇字,将每过于扬雄;登楼而赋销忧,愿少留于王粲。”*汪藻:《浮溪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影武英殿聚珍本。表达了对韩驹的仰慕之情与追随之志。汪、韩二人自此结交。
对不少投启者而言,启文无异于一张名片,既是礼貌的需要,更是一个向在位者展示自己的机会。不少在位者则通过启文来辨识人才并加以提携。谢绛曾以启谒见杨亿,其中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化用经语,有如己出,杨亿赞不绝口,将这四句题写在扇子上,称赞“此文中虎也”。谢绛的名声由此传扬开来*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又如李元亮以启拜谒蔡薿,蔡薿激赏其启,不但留宴连夕,赠以五十万钱,而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李元亮“遂登(大观)三年贡士科”*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三,“李元亮诗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4页。。
优秀的启文能够有效达成士人交往的目的。如能准确判断写作者与收受者双方的具体情况,对二者关系有恰如其分的掌握,并通过恰当的事典和精美的字句加以呈现,这样的启文,能在士人交往中带来正面的影响。杨亿以神童知名,年纪轻轻就被授予馆职,他在给馆阁前辈的谢启中说:“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徐度:《却扫编》,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页。第一句中的“绛”“灌”指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汉代贾谊年纪轻轻却受到重用,引起了他人嫉恨。周勃、灌婴等人诋毁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与欲擅权纷乱诸事。”*司马迁:《史记》,卷八四,《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492页。汉文帝因此渐渐疏远贾谊,后将其贬为长沙王太傅。杨亿反用这个典故,以贾谊自比,说馆阁前辈非“绛、灌”之徒,都是贤明之人,愿意提携年轻人。后一句也用了汉人典故,邹阳、枚乘、司马相如都是文学名家,邹、枚二人先成为梁孝王门客,司马相如后来才与梁孝王相遇,“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第2999页。。杨亿借助这些典故来说明前辈对自己的接纳,并表示感谢。短短一联,叙事达意皆有分寸,既褒称先达以示尊敬,又暗以贾谊、相如自诩才能;既显露其才学,又大方得体,不卑不亢。对于初入馆阁的士人来说,通过一封启文来协调与同事、前辈的关系,是极其必要的。杨亿启文不但充分展示了自己,而且切合初入馆阁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不过,启文在士人关系网络中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尽管作者总是试图建立或维系某种人际关系,但未必都能成功,有时甚至还有反作用。胡旦贬谪商州,久未获用,听说李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以启相贺:“吕参政以无功居左丞,郭参政以酒失为少监。辛参政非才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启中提及的都是此前任参知政事的大臣,胡旦历数他们的无能及过失,试图以此凸显李沆的优秀,从而达到依附李沆的目的。然而正直的李沆不吃这一套,说:“乘人之后而讥其非,吾所不为。”李沆为相期间,始终没有起用胡旦*李元纲:《厚德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4页。。又据《梦溪笔谈》记载,郑獬自负时名,但在国子监考试中仅名列第五,心中不平,谢主司启云:“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沈括:《梦溪笔谈》,卷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郑獬《郧溪集》卷十三收此文《国学谢解启》,其中作:“以李广之才气,孰谓无双?若杜牧之文章,止得第五。况某者,拙不晓事,技无他能。”“巨鳌何知,固有灵山之在上;骐骥已老,甘为驽马之争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原文并无不逊之意。然若有心曲解,还是很有可能因“骐骥已老”这样的句子产生记恨的。,因此得罪主司。后来廷策之日,该主司仍担任考官,打算黜落郑獬,见到文风相似者,立即斥逐。幸有糊名制度,郑獬才侥幸逃过一劫,得以第一名及第。
由于士人关系网络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启文又是宋代政治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情境下,启会成为政治运作的手段,甚至引发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参与政局中的风云变幻。韩侂胄当政时,傅伯寿投启曰:“人无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则异欤,独仰韩公之斗。”“右相”指史弥远。傅伯寿怒斥投靠右相之人为“无耻”,表现出对韩侂胄的强烈依附之意,因此被擢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页。。又如,秦桧欲向金国乞和时,胡铨进呈了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秦桧,以致被贬。陈刚中同样反对乞和,特意以启贺胡铨:“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在胡铨被贬的情况下,陈刚中的这份贺启,实际上是在表白自己的立场,表明对胡铨行为的全力支持。既然陈刚中与胡铨站在同一队列,秦桧自然不能放过,随即将陈刚中贬为安远县令*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启文对于士人阶层自身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启文写作需要丰厚的知识学养和精细的写作技巧,对于宋代士人整体素养的提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欧阳修在学写古文以前,曾“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这些“时文”主要指骈文。尽管欧阳修不喜骈文,但回思往事,又不得不承认:“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第661页。启文的写作与此同理,虽为应酬文章,但对士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士人不但需通过读书来充实自己,而且要磨练遣词造句、构思剪裁的能力,士人的文学修养由此得到普遍的提升,对宋代诗歌等其他文学体式的演进也有积极的影响。就启文自身而言,宋代骈文能够成为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并以独特风貌影响后世骈文的发展,启文堪称一大主力。
可见,在充满开放性与流动性的士人关系网络中,启文扮演着丰富而多面的角色,在践行其应用属性的同时,深度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进而塑造着宋代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
五、余论
宋代士人关系网络促进了启文的繁盛,但也导致了启文存在一些弊端:许多作品过分注重文学技巧的展现,结果隶事太冗,使才太过,缺少真情实感;一些作者怀抱着功利性目的,产生了不少褒贬失当、砌词作假、甚至有违道德的文章。据《挥麈后录》记载,曾布执政时,与蔡京、蔡卞为敌,有文士投启于曾布:“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而在不久之后,曾布被贬,蔡卞当国,此文士略变启语,再献蔡卞:“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9页。这样的投机行为,着实令人不齿。“是以骈俪之文,其盛也,启之为用最多;其衰也,启之为弊差广。”*孙梅:《四六丛话》,卷十四,第280页。对于一种应用性极强的文体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我们既不必讳言其失,也不可一味苛求。
总而言之,宋代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决定了宋代启文的发展走向;宋代启文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又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影响着士人阶层内部的沟通与交流;宋代启文对知识学养和文学技巧的要求,提升了宋代士人的整体素养,塑造着宋代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通过对宋代启文这样一种典型应用文体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将某种特定的文体作为普泛的社交工具、将写作才能与文学技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技能,这样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文化选择,折射着中国古代传统特有的文学风貌与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QIWEN in the Network of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ZHOU Jian-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China)
QIWEN, a prose pattern characterized with rhythmicality in the form of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was maintained by Song scholars after the Tang-Song Movement for Classical Literary Style. So far as its frequency of use is concerned, this style was pervasive in all respects of the then scholastic life.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using this style was the newly formed scholastic network based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asting about 1,300 year from Sui 581-618 to Qing 1636-1912) and the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per se. The network had a straightforward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the stylistic selection of Qiwen. The Qiwen pattern bears the principal func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reinforces its ritual characteristic and embodies the literary talent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cholastic clas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ttern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scholastic circles. That is, there is a delicat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se pattern and the scholastic network that reflects the particular literary current and humanistic concern that the ancient China has.
Qi (open up; enlighten); rhythmical prose in Song; network of scholastic relationship
2015-01-2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14ZDB06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宋代骈文文体研究”(SKZZX2013074),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I109
A
1002-0209(2016)06-0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