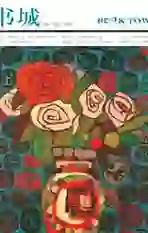马尔克斯的睡美人故事
2016-12-01许志强
许志强
一
《苦妓回忆录》(轩乐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后一篇小说,其创作灵感得之于川端康成的《睡美人》。此前在《飞机上的睡美人》(朱景冬译)一文中,作家便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篇日本小说的兴趣。他讲述客机头等舱里的一次邂逅:身边坐着一个美女,旅程中她戴着眼罩睡觉,而他坐卧不宁,情思绵绵,“不得不克制着随便找个借口摇醒她的诱惑”;明知界线不可逾越,那颗蠢动的心却跃跃欲试,为徒然的钟情和欲念备尝折磨;他于此体会到川端笔下的“日本老人”的痛苦:无所作为地陪伴“睡美人”,只准看不准碰。用《睡美人》(叶渭渠译)中的话说,“活像与秘藏佛像共寝”。
川端的带有几分荒唐的淫冶构思,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原创性,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写过这种“老丑”的故事(“……还有什么比一个老人躺在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身边,睡上一夜更丑陋的事呢?”那些老年嫖客的行为,“难道不正是为了寻觅老丑的极致吗?”)。
也许没有作家像马尔克斯,对川端的构思发出实实在在的回应,在一篇散文和一篇小说中借用“睡美人”的意象。川端笔下服了麻醉药、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在《苦妓回忆录》中以更撩人的姿态袒露出来:
她有着深色的皮肤,让人感觉温暖。已经按照程序给她做了清洁和美容,甚至连她阴部初生的绒毛都没有忽略。还为她卷了头发,用天然的甲油给她的手、脚指甲染了色,但她糖蜜色的肌肤却显得有些干燥和缺乏保养。刚刚开始隆起的乳房还像男孩子的一样,但看上去即将因某种隐秘能量的涌动而爆发。她身体最好的部分是那双会迈出悄无声息步伐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一般。尽管开着电扇,她却浸在闪着磷光的汗水中……无法想象出那张被胡涂乱抹的面孔的原本模样……但任何装扮都无法掩盖她的特点:挺拔的鼻梁,相接的双眉,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幼嫩的斗牛。
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一篇书评中指出,马尔克斯的妙语连珠的描述“读起来有种天鹅绒般的快感”,同时也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文字流露出的“恋尸癖”倾向,让人想起作者长期以来对“活死人”的兴趣。
库切的评论(黄灿然译)则认为,这篇小说的“目标是勇敢的:替老年人对未成年少女的欲望说话,即是说,替娈童癖说话,或至少表明娈童癖对爱恋者或被爱恋者来说不一定是绝境”。
小说开篇交代说,“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故而库切的文章有“娈童癖”一说。比起“恋尸癖”,这个说法更贴切些。但小说读下去就知道,这癖那癖(包括“处女癖”)其实均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九十高龄要最后一搏,试图让肉体和精神获得新生。
开篇第一句话概括了故事要旨,且能反映马尔克斯一贯的风格特色:大胆、夸张、淫猥并饱含幽默。虽说创作灵感是得之于《睡美人》,构思却有明显差别。《苦妓回忆录》撤除了川端小说中的禁忌,等于是取消了“睡美人”这个构思的内在张力。换言之,九十岁老人花钱找小处女睡觉尽管荒唐,但仍是普通的嫖妓行为,谈不上涉足一个幽深而变态的魔性世界;而那些欲念的魅影(连同罪感的冷酷和哀感的缠绵),只有进入这个魔性世界才会对人绽放出来。这当中,禁忌扮演重要的角色。构成“睡美人”诱惑的本质是由相关的禁忌所定义的。一旦禁忌消除,其独特的诱惑力(美感和哀感)便不复存在,其密室的剧场效应(罪感)也就无从产生了。川端的作品大量涉足潜意识,探索一个深渊般的官能世界,便是和它内在的禁忌意识密切相关。而在《苦妓回忆录》中,这一层关系的处理是弱化的;它撷取“睡美人”意象,敷陈一个颇具拉美特色的故事:妓院鸨母善解风情;嫖客按清单付费,尽可以对雏妓为所欲为;出租车司机会大声祝福嫖客:“干得愉快!”……一个情欲旺盛、咋咋呼呼、鲜廉寡耻、火热生动的世界;人们为解除禁忌的狂欢而生存,其巴洛克式的浓艳中别有一种单纯明快。将川端的小说移植到这个汗涔涔的热带背景,还能不被烤煳吗?那种密室独白的清苦气息,非戏剧性的诗意的升华之美,岂不是要蒸发殆尽?
马尔克斯当然只能讲他自己的“睡美人”故事,也必定要改写川端的构思。他让老人与处女共寝的情节加以发展,添加了老人遭遇滑铁卢的细节,由此呈现不同的叙述逻辑:不是隔着禁忌的面纱孤独地陪伴睡美人,而是因身体无能而不得不放弃行动,陷入赤裸裸的羞耻和伤感。川端的“老丑”主题到了马尔克斯笔下进一步现实化了,变成什么都可以干却没能干成的尴尬遭遇。
鸨母指责老人对妓女缺乏尊重,并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但第二夜和第一夜一样,他能做的是替女孩抹去身上的汗水并唱道:“黛尔加迪娜,黛尔加迪娜,你会是我亲爱的宝贝。”老人体验到“无尽的欢愉”,那就是替妓女擦汗并且唱歌。他认为自己不仅从长期奴役他的性欲中摆脱了出来,而且遭遇了一个奇迹,“一个在九十岁时逢遇人生初恋的奇迹”。作为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改变写作宗旨,无论什么文章都是在为黛尔加迪娜而写,事实上他把专栏写成了一封封大众情书,得到读者的热烈反响。他继续和他的黛尔加迪娜共寝,为睡梦中的她读书。她是工厂的缝纽扣工,不是童话里的公主黛尔加迪娜。但只要他活着,她就是他的“真爱”,他的“睡美人”,他的公主黛尔加迪娜。
和川端试图表现“老丑的极致”相比,这种重述和改写终究是要低一个档次。诠释性的构思总是试图破解原创性的构思所包含的谜,因此艺术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和冲淡,或是出现更为圆熟的解答或补充。川端的小说抑制戏剧性的变化,所要避免的或许就是那种过于圆熟的处理;它执着于“性的不可估量的广度和性的无底深渊”,不去减弱这个主题的黑暗性质。作者的创作勇气也体现在这里。
但也不能只是将《苦妓回忆录》视为对《睡美人》的回应。马尔克斯的写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渊源。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页就能确认是他的手笔,正是出于那种令人一望而知的口吻和风范,无可置疑地包含着艺术及思想的教谕性质。从渊源上讲,《苦妓回忆录》和他此前的创作一脉相承,主要是遵循他自己的创作逻辑,这是下文要讲到的一点。从特点上看,马尔克斯的夸张和幽默在这篇并不魔幻的小说中仍显得很突出,不仅是细节和语言,也包括整体构思。他要诠释的命题是,九十岁的老人能否遭遇初恋?回答是肯定的。可以说这是带有嬉戏的夸张,也可以说是含有教谕的幽默。对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关注,将他的构思和川端的完全区别开来。虽说《苦妓回忆录》不是一篇魔幻风格的小说,但它那种构想的方式,将狂想和现实熔于一炉的做法,正是马尔克斯的鲜明标记。
二
库切写过一篇长文,对《苦妓回忆录》的创作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认为,该篇是在续写《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个情节,即弗洛伦蒂诺和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不伦之恋。由于弗洛伦蒂诺移情别恋,阿美利加自杀;这个被年长者引诱然后被遗弃的女孩,将内心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库切的文章指出,马尔克斯没有去探讨“弗洛伦蒂诺因伤害她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这是小说在道德处理上的漏洞;而新作试图弥补这一漏洞,让“处女信任的破坏者变成她忠实的崇拜者”,促成人物的道德新生,因此,把该篇“视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某种增补,是最有意义的”。
新作中的“无名叙述者”和弗洛伦蒂诺的形象如出一辙,都是“终身王老五”“胆怯和其貌不扬”“业余诗人”“忠诚的音乐会的常客”,而且都有一份征服女性数量的备忘录(前者有“五百一十四个”,后者有“六百二十二个”)。此外,阿美利加十四岁,新作中的雏妓也是十四岁。库切认为,“两本相隔二十年的书之间的呼应,瞩目得无法忽视”。
鉴于马尔克斯的创作主题的持续性和模式发展的阶段性的特质,对其创作源流加以归纳显然颇有必要。如果说《百年孤独》综合了前期创作成果,尤其是和《枯枝败叶》构成呼应,《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晚期作品之间则同样是建立了主题性关联,正如库切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将《苦妓回忆录》视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某种增补”,这是一个独到的发现。但是,我们的考察还不能停留于此,不能局限于作家晚期“带有秋意色彩”的喜剧所包含的道德框架。
马尔克斯的创作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孤独”和“爱情”。前期侧重于写“孤独”,后期偏重于“爱情”,这从他两部代表作的标题中也能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些都是大主题,常见的文学主题,并非为他一人所专擅,但也确实构成了他颇具标志性的主题链。可以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承上启下的一部作品,将“孤独”和“爱情”的主题重新诠释,而且让“爱情和老年”的主题出现在叙述中,书写其情感浓烈的新篇章;从诗学上讲也是一次引人瞩目的凯旋:《百年孤独》的愤世嫉俗的洪流终于汇入明净宽广的河床。作家对加勒比地区的反复书写,呈现出一条深入反思基础上的诗学变化的脉络,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抵达一种诗与思交融的圆满之境。同时代的小说创作鲜有这种经典品格。这也是他最后一部史诗型作品,其后的创作大抵是延展和增补。《苦妓回忆录》续写“爱情和老年”的主题,是一次回顾和重述;这部篇幅短小的夕阳之作,将作家长期以来颇感着迷的形象和心理情结再度串联起来。
该篇的“无名叙述者”的形象不仅和弗洛伦蒂诺相关,也和《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以及《枯枝败叶》中的法国医生相关,甚至和《族长的秋天》中的独裁者也不无关联。他们是从同一个想象的源泉中诞生的形象,不妨称其为马尔克斯式的浪荡子。作家终其一生为这个形象着迷:单身汉、诗人气质、女性征服者。不管赋予怎样一种身份(存在主义者、军事独裁者、船务公司经理或报刊专栏作家),其形象的内在定义是不变的,如作家本人所阐释的,“胆怯”是源于(和性征服有关的)大男子主义,“孤独”是源于“爱的无能”。在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前期创作中,蕴含此种心理情结的形象以悲剧的方式刻画出来;而在以《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代表的中后期创作中,喜剧取代了悲剧,爱的力量战胜了胆怯孤独。创作逻辑的这种变化却并未改变形象的固有特质,无论是弗洛伦蒂诺还是“无名叙述者”,其孤独的表征仍是一种含有悲剧性的精神疾患,丑陋而阴暗;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和《苦妓回忆录》中的女仆都成了此种心理顽症的牺牲品;这是不可救药的“爱的无能”,正如九十岁的“无名叙述者”所说,“我从来没有爱过。”
那个“异性鸡奸”的细节岂不说明问题?“无名叙述者”长期和他的女仆发生关系,总是en sentido contrario(从背后)骑上她,以至于她变成老妇时仍是个处女。这个细节在《族长的秋天》《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篇中都出现过。
马尔克斯的可贵是在于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形象的属性,而非像库切所说的那样去弥补道德漏洞,让弗洛伦蒂诺或“无名叙述者”成为“道德上改过自新的人”。这倒不是说,他是个不道德的作家,对人物的“道德新生”不抱关注。他和同时代的拉美大师(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等)的一个区别,正是在于他对人物形象和主题的重视;他的创作不仅更多地保留小说体裁的经典品格,甚至大有主题先行的意味;而他对“孤独”“爱情”这些主题的思考,是基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关怀,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批判的性质。在他看来,奥雷良诺上校、弗洛伦蒂诺这些人物,包括马孔多所喻指的整个加勒比地区,不仅在道德和政治上不具有救赎的希望,在性欲和爱情方面也是严重的人格不健全。他从未离开“爱的无能”的范畴去探讨爱和新生,将人物纳入一个欧化的道德忏悔的框架,而是以独特的悲喜剧方式,诠释“孤独”这个词所包含的文化现实心理。“奥雷良诺们”的孤独是能够救赎或缓解的吗?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对弗洛伦蒂诺、“无名叙述者”来说,爱情更像是一种生机论和原始繁殖力的表达,带有轻喜剧的特点;与其说是“道德新生”,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抗拒;爱情如同劫数、瘟疫和鬼魂附体,也是一种令人恐惧和令人怜悯的社会生活的写照。
马尔克斯书写“孤独”和“爱情”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否打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印记,其本质都是属于提供全息立体画卷的社会小说,包含作家深刻的洞察、悲悯和反思。《苦妓回忆录》尽管篇幅短小,但仍是一部社会小说,涉及文化时尚、爱欲、老年和死亡等多个主题;它富于“秋意色彩”的轻喜剧风格,能够反映作家晚期风格的特质。
三
爱德华·萨义德未完成的论著《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探讨艺术家自我发展的最后阶段,即有关“晚期作品”“晚期风格”的现象,提出一个“适时”的概念。在他看来,“人类生活在实质上的健全,与它同时间的契合、彼此完全适合,有着极大的关系”。那么,艺术家的“晚期”能否算是一个“适时”的阶段?如果通常情况是,衰老和死亡的阴影侵入创作,那我们还能作此断言吗?
在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等剧作中,在索福克勒斯、威尔第等人的创作中,萨义德认为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显而易见,一种“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特殊的成熟性”,一种“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在他们的后期创作中反映出来,能够恰当地说明“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他认为,在一些艺术家(例如伦勃朗和马蒂斯、巴赫和瓦格纳)身上甚至能看到“晚期作品使一生的美学努力得以圆满的证据”。但是,相反的例证也并不难找,例如晚期的贝多芬,其“不合时宜与反常”的创作,造成令人瞩目的“断裂的景象”;还有易卜生、格伦·古尔德等,他们均非“和谐”的例证,“适时”的概念对他们是不适用的,没有多大意义。
萨义德追随阿多诺的思想(“晚期风格”的论题便是后者提出来的),把“晚期”理解为“一种放逐的形式”,作为艺术家超越时间、表现死亡的诸多形态中的一种,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而“不和解”的精神正是构成《论晚期风格》一书的主旨。在他看来,那种与适时的成熟迥然不同的晚期,无论是悲剧性的、喜剧性的、讽刺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均须突显其内在张力和“不可调和性”,而非顺当地解决自身与时间的抵牾。
以此观之,马尔克斯的晚期创作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它同时间的契合”所形成的“适时”状态,其感知特质与表现形式均可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特殊的成熟性”来考量;一方面它又保持“自身与时间的抵牾”,以喜剧风格传达精神上的不和谐。
《苦妓回忆录》通过一个九十岁专栏作家的遭遇,“适时”地描绘有关衰老和死亡的末期体验。它蕴含着一个古典的时间框架,那种求得人生阶段性平衡的观念;“老年和爱情”的主题正是协调于这个时间框架。马尔克斯不像科塔萨尔,后者的创作始终呈现为“一种放逐的形式”;而马尔克斯末期创作的双重性,其实是一种折中主义,似乎并不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张力;《苦妓回忆录》尽管写得大胆而淫猥,却没有什么“不合时宜与反常”的东西;因为,艺术创作“不合时宜”的本质是在于思想性对世俗性的超越,正如萨义德评论阿多诺时所指出的,“对阿多诺来说,没有任何思想可以被解释为任何别的对等物,而思想的严格性却促使他传达出精确性与绝望。”即便在川端的《睡美人》中,我们也能领略到一种溢出现实对等物的“精确性与绝望”的表达;因此,使作家显得怪异难解的所谓晚期症状的表现,是不能离开这种内在本质来谈论的。
马尔克斯的晚期作品,既非对自身创作的超越,亦不能被视为思想性对世俗性的超越。其喜剧手法的运用,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是一种再现社会生活的手段,在《苦妓回忆录》中则成了抵御衰老和死亡的面具。换言之,社会生活的宏大背景一旦缩减,成为故事中点缀的有限衬景,其叙述的能量也就相应衰减,这是《苦妓回忆录》显得不太有分量的一个原因。这么说并非要给作品挑刺,而是试图强调:像马尔克斯那样依赖“世俗性”的作家,风格化的精练其实并不重要(这一点他和米兰·昆德拉不同),艺术再现的幅度和综合性才是关键;当喜剧成为仪式化的面具而非客观化的调解手段时,喜剧便沦为幕间插曲式的表演,逗趣,诙谐,其感伤的色彩加重,冷静观照的程度便降低了。说《苦妓回忆录》的叙述有些主观,欠缺内外的综合性,便是就这层意义而言的。
萨义德形容阿多诺的一番话,适用于马尔克斯—“一个世俗的人,即法语‘尘世(mondain)意义上的世俗性。他是都市的、有教养的和深思熟虑的,令人难以置信地能够找到要说的有趣的事情,甚至在说起一个分号或感叹号那样的事情时也能毫不装腔作势”。马尔克斯作为小说家的禀赋和气质,这样来描述是恰当的。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现代意义上擅长讲故事的人,是有教养的都市人;只是他们不再处于伏尔泰发现“世俗性”那种单纯的解放意义的时期,而是处在思想的相对性和多元性的境地中,因此,他们(马尔克斯、昆德拉等)时而成为“世俗性”的敌对者,时而成为“世俗性”的协同者;当他们的趣味和倾向契合于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气候时,艺术上便具有引人注目的教谕性质,反之则容易遭到忽略。
马尔克斯的晚期创作不乏佳作,像《爱情和其他魔鬼》,就其叙述语言的精妙而言,并不亚于托尔斯泰的中篇佳构,但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 “反天主教”的主题显得有些过时了。虽说作家对“性和激情”的关注,对“老年和爱情”的探讨,还远不能说是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