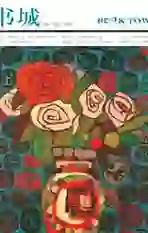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
2016-12-01邹振环
邹振环
第一次听说苏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其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京师同文馆译书出版的论文。那些年两岸交流受限,尽管已从他人论文的引述中得知苏精教授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五年先后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馆》和《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两书,但仍然无法获取这些著作。记得学校参考阅览室的一位老师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台湾有两个苏精,一个是研究同文馆的,还有一个是研究藏书家的,著有《近代藏书三十家》。若干年后才恍然大悟,其实研究同文馆和研究藏书家,是同一个苏精的两张学术面孔。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苏精,一九七二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一九七六年进入台湾“中央图书馆”工作。由于不满意既有的关于晚清同文馆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首先完成了全面梳理同文三馆数据的《清季同文馆》,一九八四年又修订增补,进一步从同文三馆的教师和学生生平及著述入手,完成了新作《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使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同时,他浏览馆藏善本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书家累累钤印和朱墨圈点的题跋,发愿收集和整理藏书家的资料,完成了《近代藏书三十家》,从盛宣怀、叶昌炽、卢靖、李盛铎、梁鼎芬、叶德辉,一直讨论到张元济、董康、梁启超、丁福保、郑振铎,介绍他们的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等相关行实。一九八三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二○○九年经作者修订由北京中华书局重版,至今还被认为是“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的论著。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七年,他以将近半百之年先后在英国利兹(Leeds)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与书目、校勘、出版史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九七年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研究者身份的华丽转身。之后他以西方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出版史研究专家的全新面貌出现在学界,二○○○年完成出版了《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二○○五、二○○六年先后推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两书,又再接再厉,写出了《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二○一四年七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推出了他的新作《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下简称《铸以代刻》)一书,该书简体字版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铸以代刻》一书主要探讨基督教传教士自一八○七年来华至一八七三年为止的六十余年间输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详细地描述了传教士们是如何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全书除“导言”外,分为十二章,一、从木刻到活字:马礼逊的转变;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三、麦都思及其巴达维亚印刷所;四、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五、初期的墨海书馆: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七;六、伟烈亚力与墨海书馆;七、香港英华书院:一八四三至一八七三;八、美国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开端;九、澳门华英校书房: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一八四五至一八六○;十一、华花圣经书房迁移上海的经过;十二、姜别利与上海美华书馆,后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作者在讨论这一“变局”的过程中突出独创性,不仅对于他人的研究力求避免重复,对于自己以往的成果所涉及过的内容也不再重复讨论,如对伦敦会为主的墨海书馆的研究尽量做到略人所详而又详人所略,而于长老会部分,如澳门的华英校书房和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则详细展开,尝试绘制西方印刷术来华传播比较完整与清晰的画面。作者谨守专业,就题论说,甚少引申发挥,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使全书的叙述格外严谨。
一、档案如是说
“档案如是说”是苏精博客的一个总标题。让“档案”来言说,充分运用中外档案,堪称苏精所有研究论著的最大特色。在英国留学期间,苏精几乎每天都与传教士的档案和手稿朝夕相对,一九九七年回国后,他继续沉浸在缩微胶卷的英文档案中,这些档案包括伦敦会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马礼逊父子档案,以及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美部会档案、圣公会传教会档案等,至二○一○年先后抄录了二百六十多万字的传教士档案。上述《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等三书,都是他孜孜不倦地利用英国各图书馆档案机构保存的传教士档案,如伦敦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的档案等,辨析相关史实,以多个崭新的角度呈现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中文出版之关系,以及马礼逊的亲友同工斯当东、米怜与马儒翰;马礼逊施洗的华人信徒蔡轲、梁进德、屈昂等的生平行事。而《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一书,则是他利用在新加坡设立布道站的四个英美传教会档案,重新建构并解释了基督教传入新加坡的背景与经过,讨论传教士对华人的讲道、教育、出版与医药等事工内容,并从档案中发现这段期间共有十三名华人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迹,从而更正了以往认为当时没有华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误解。《铸以代刻》与作者之前所撰写的所有著作类似,均据第一手数据—传教士的手稿档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将视野范围从之前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档案扩大到长老会的手稿档案,从中抄录了四十五万字的书信内容,透过对大量资料之爬梳,发掘许多鲜为人知的印刷机构的历史、印工的故事,探讨了传教士的印刷与铸字工作。
档案言说的主要功效,就是能够对很多史实作出较之前人更精细的结论和更准确的判断。麦都思和墨海书馆是苏精硕士论文的选题,也是他传教士中文出版研究的重要起点。该书第五章根据伦敦会档案提供了麦都思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抵达上海开始筹建,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将印刷机器带到上海,并于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正式印书的准确时间。也让读者知道了该馆印刷的第一种新书是《真理通道》,是该馆初期“最重要的一种传教出版品”,总印数超过六十万页(《铸以代刻》,第175、188页)。墨海书馆是近代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内地创办的新式印刷机构,但该馆究竟停业于何时,学界至今说法不一。作者根据现存的伦敦会华中地区的档案中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八日慕维廉写给同会秘书梯德曼的信,说明墨海书馆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由自己经手管理,其间还印刷了十万部《新约》与《五车韵府》。一八六六年八月,他曾向穆廉斯汇报结束这一书馆的进度,可见该馆结束在一八六六年(《铸以代刻》,第225-227页)。美华书馆从一八六○年创办至一九三二年结束,前后持续七十一年余,也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华设立的最重要的新教出版机构之一,遗憾的是至今尚无关于这一机构的专门研究论著,即使关于该馆初期的馆址究竟在哪里也是众说纷纭。作者通过详细的档案材料的比对,准确地说明了一八六○年该馆是设在上海虹口长老会上海布道站购买的紧邻克陛存住宅旁的一处房地上,一八六二年迁至小东门外的新馆舍,一八七五年十月迁往北京路(《铸以代刻》,第473-478页)。一八六七年该馆出版的《美华书馆中文、满文与日文活字字样》一书中出现了戴尔(Samuel Dyer,又译台约尔)活字,这一点曾让专家深感困惑,作者通过长老会和伦敦会两个教会档案的对勘,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中外档案中蕴含着大量的亟待开发的新材料,新材料往往支撑着学术新课题的延伸和拓展。《铸以代刻》中有不少直接从第一手档案中提取出来的宝贵材料,对于新课题的拓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如记述一八六五年姜别利在美华书馆曾亲自教导没有西式两面印刷装订经验的女工学会折纸和缝线(《铸以代刻》,第520页),表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该馆已有从事印刷装订的女工。相比而言,目前仍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史权威资料引用的、孙毓棠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书中有关印刷业的资料,主要来自《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编、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之印刷术》等二三手的资料。或以为中国最早的女工是出现在纺织业,一八七二年陈启沅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曾“容女工六七百人”。一八六五年较之一八七三年要早八年,中国最早的女工是否可能首先出现在印刷出版业中呢?我以为很值得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晚清天主教与新教曾经就基督教的术语和圣号等的翻译,以及如何既尽可能地关照输入地的文化语境和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又能尽量保持基督宗教的本真性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辩。《铸以代刻》通过档案告诉我们,作为新教传教机构附设的印刷所,墨海书馆初期的产品中,有以天主教书籍内容为本的《圣教要理》和《圣经史记》,而且一向对中文造诣自视甚高的麦都思还再三对《圣经史记》的“最纯粹的中国经典笔调”表示崇高的敬意,为此还引发了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罗类思的强烈抗议(《铸以代刻》,第189-190页)。以往研究墨海书馆的学者,都很喜欢引用该馆用牛作为滚筒印刷机动力的事实,作者通过档案给出了美华书馆用牛拉动滚筒印刷机的形象画面:“两头牛轮班拉动转轮,转轮的皮带再发动印刷机,因此得雇用一名工匠照料牛只、一名工匠在机器印刷时上纸,再一名领班照料整件事。”(《铸以代刻》,第502页)档案中还保留了很多足以反映传教士品格的有趣的细节,如以往研究者很难找到这些来华传教士收入的材料,作者在该书第六章中以大量的档案说明伟烈亚力就婚后的年薪增加问题,如何与麦都思发生争执,甚至为自己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使用了粗暴的语言并拒绝道歉,但最终传教士们还是宽容大量,彼此冰释前嫌。还有发生在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三年间的因范约翰从事土地房屋投资被华人告进官府,轮值担任上海布道站主席的姜别利因为抨击范约翰的行为而遭到后者的反击,为此两人甚至“举拳相向”,争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为中国近代外人在华传教史提供了很多生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铸以代刻》,第211-217页、第482-483页)。
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是晚清出版史学者颇为注重的一个出版机构,该机构究竟出版了多少书,至今争论不休。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指出,一八四四至一八六○年间该机构共出书刊一百零六种,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八十六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属于天文、地理、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二十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九;而黄时鉴在熊月之统计的基础上曾有所增补,龚缨晏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则进一步修正了上述的数据,将种数增补为一百三十五种(杭州出版社2010,第188-189页)。苏精根据《长老会印刷所历年书目》等资料,统计出从一八四五至一八六○年的十五年半期间,该书房的出版物不下于二百一十种,并认为如果将再版或多版都一并计入的话,出版物总数甚至高达三百二十六种以上(《铸以代刻》,第408、411、426页)。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广州、福州、厦门,几乎可以和同一时期上海的墨海书馆相媲美,堪称当时全国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重要中心,实在是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作者能够整理出一份关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物的简明书目和分类统计表的话,那么,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档案中所记录的那些出版物的具体名称和内容,一定会大有裨益的。
充实的档案史料,是《铸以代刻》一书研究的前提,通过对大量英文传教档案艰苦和细致的爬梳剔理,整理资料,阐幽发微,来重构晚清印刷出版的史事,堪称该书的第一特色。不过由于作者所利用的主要是英文教会档案,据作者自述,教会档案中几乎很少涉及非传教作品,也很少涉及关于华人翻译合作者的记载,即使有些关于华人的记述,如王韬等,也是因为他协助翻译圣经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缘故。所以,虽然作者已竭尽全力将档案中有关非传教性作品的材料予以析出,如关于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美华书馆非传教性书籍的分析,但书中在讨论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的过程中,涉及世俗的科学和人文书籍翻译出版的史实尚欠充分,而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些非宗教读物的影响力往往要远远大于宗教读物,且中国学界对于这些科技和历史译本的研究兴趣,也要大大超过基督教宗教读物。这可能是主要利用英文教会档案的《铸以代刻》一书,留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遗憾。
二、不疑处有疑
学无止境,新材料的发现会使原有的结论受到证伪,甚至被推翻。不轻信所谓“常识”,不迷信前人的权威著作,敢于挑战中外学界既存的权威结论,是苏精全部著作的突出特点。在晚清印刷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中,有若干公认的权威论著,如一八六七年出版的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该书是伟烈亚力亲历、亲睹和亲闻的“三亲”著作,一向被人视为第一手的最可信资料。该书曾经记述《遐迩贯珍》创刊时的主编是麦都思,第二年由奚礼尔继任,一八五五年再由理雅各接手编到停刊。由于伟烈亚力是与麦都思一起共事者,两人关系密切,尽管曾有王韬称“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但不被学者重视,后人无从怀疑伟烈亚力这一说法的可靠性。《铸以代刻》的第七章通过《北华捷报》等数据的考订,确认麦华陀才是《遐迩贯珍》的真正主编(《铸以代刻》,第276-284页)。
晚清来华后转而替美国长老会服务的英国传教士麦根陶(Gilbert McIntosh,1861-?,或译“金多士”“麦金托什”)所著的《在华传教会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美华书馆1895),也是流传甚广的有关宁波和上海长老会在华所办印书机构的权威论著。麦氏长期专注于美华书馆的研究,还撰写过美华书馆五十年、六十年和七十周年三本纪念性的文献,因此该书在学界也几乎被视为无可置疑之作。麦根陶认为当时担任华花圣经书房主任的姜别利,鉴于上海已是中国商业与传教的中心,认为将书房迁至上海更适合长老会出版事业的发展,他的提议获得了宁波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支持,因而在一八六○年将书房迁至上海。这一观点影响很大,为一些重要的印刷史著作,如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等沿用。《铸以代刻》的作者利用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包括姜别利在内的上海与宁波两地传教士与外国传教部通讯秘书娄睿之间的来往信函,指出迁往上海的建议首先并非出自姜别利,而是宁波长老会不少传教士的一种共识。早在一八五二年底,袆理哲就指出华花圣经书房所在位置的卢家祠堂附近是稻田和大片死水的大池塘,环境非常潮湿,有害健康,实在不适宜传教士长期居留。在上海布道站的传教士克陛存也有类似的看法,即认为迁沪的好处一是上海比宁波或其他通商口岸更易于接近内地;二是迁到上海后易于接受更多其他传教会的订单而降低印刷所的成本;三是较之宁波更易于收受从美国运来的油墨、铸字金属等材料。当然他也承认迁址面临的问题,即书房在宁波的专用房舍将被废弃、在沪需重建新址而增加开支;另外是迁沪后会面对来自墨海书馆的竞争等(《铸以代刻》,第442-444页)。可见,当时在宁波和在上海的长老会传教士,似乎都认识到同时存在的对书房迁沪所存在的推力和拉力。华花圣经书房迁址上海之举,前后历经七年多,在宁波、上海和纽约三地之间进行讨论,这项迁移的原因和经过,绝非一般所谓姜别利鉴于上海的发展性而搬迁如此简单的过程,这项迁移关系着长老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布局,也牵涉到基督教各宗派扩充在华势力的合作与竞争(《铸以代刻》,第454-469页)。作者力图通过繁复的档案数据来证明,历史所呈现出的面向,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从宁波到上海的空间转移,是一种历史的合力。
一九二一年上海别发洋行推出的兰宁(G. Lanning)和库寿龄(S. Couling)所著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上海史研究中权威的汉学名著。该书认为麦都思仅仅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是从伟烈亚力才开始的,特别强调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发展中的作用。且以往学者多认为伟烈亚力来华前是学了六个月的印刷技术,其实即使六个月也实在太短,因为传统的手工印刷学徒需要经过三四年才能学成出师,《铸以代刻》根据档案,证明伟烈亚力在伦敦仅仅学习了三个月,而工业革命期间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印刷工匠,绝非三个月所能养成,于是作者就伟烈亚力印刷技术不内行的问题,再引出对兰宁和库寿龄《上海史》中错误结论的批评(《铸以代刻》,第202-210页),就很令人可信。
《铸以代刻》一书不仅为传教士的旧著纠错,对近人的研究,也多所采纳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一书,自二○○四年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颇受学界好评,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力作”,二○○五年获得了第四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最佳亚洲人文科学研究奖”。该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宁波官员和当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一八四六年发生的事,那位官员非常欣赏长老会宁波布道站的华花圣经书房西式中文印刷的质量,因此携来一部节录自中国史书的抄本,请求传教士以活字为他排印,不料最后传教士却予以谢绝了,理由是这将会有碍于华花圣经书房的非商业形象。《谷腾堡在上海》认为这件事代表着西式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初期,不仅以大量生产为能事,让中国人惊叹不已,其良好的生产质量同样让中国人心向往之。书中曾四次提到此事,可见芮哲非相当重视这件事的象征意义。《铸以代刻》一书却通过长老会档案中两件关于此事的函件,证明芮哲非对于这个故事的说法和史实恰恰相反,传教士是同意为宁波官员印书的,反而是官员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价格后打消了原意(《铸以代刻》,第437-439页)。
《铸以代刻》一书的作者不为印刷出版史上的今昔中外权威之所惑,在他人不疑处寻找疑点,用多种材料互相印证比对,在被认为常识的不疑处存疑,与之进行批评和对话,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三、“典范转移”的历史合力
所谓“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又称“范式转移”,该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科学史家及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这一术语原是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从根本假设的改变,后来亦指凡是一个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巨大转变,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典范”,如建筑领域有“建筑典范”,图书印刷出版领域也有自己的“典范”,当一个稳定的“典范”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时,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典范转移”,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许多“变局”。
中国图书出版发展史上有几次重大的“典范转移”,都与文献复制手段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唐宋时期从之前印章、拓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雕版印刷技术、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使知识传播的媒介从写本转变为印本,而这一“典范转移”很可能与佛教的经文和道教符咒的刻印有关。图书复制流通数量增多,知识信息的传播交流加快,从而导致了阅读、研究、携带和流传等传播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印本图书的发行数量庞大,使图书版本多元化,图书成本较之写本抄本低廉易得,使真正的图书市场得以形成。印本图书的流通和典藏,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意义重大。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第二次“典范转移”是在晚清。中国印刷出版,直至十九世纪为止主要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第二次“典范转移”是以近代的石印术、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机械印刷代替手工印制。这一巨大的转移还伴随着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的技术变革,这些变革首先反映在图书复制的速度大大加快,产量也明显增多,成本下降带来了书价的低廉而使知识普及范围空前拓展;其次,由于铅印本体积开本缩小,页数取代叶数,板框栏线消失,版面趋于简化,之后又采用洋纸两面印刷,不仅有助于节约图书的用纸量,也使图书的典藏空间大大缩小;再者显示在图书面貌的改观,线装都改为平装或精装,直立插架代替了平直存放,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如同中国图书出版的第一次“典范转移”与佛教传教相关一般,第二次“典范转移”也是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联系在一起。西方传教士引介西方印刷术原是为了便于传教,结果却远超出预定目的之外,不但改变了中国已有千年传统的图书形制,而且促成了近代中文报刊的出现。传教士们把自己日常生活环境中理所当然的一种新的传媒形式—报刊带到了中国。晚清报刊虽也有采用木刻,但铅印和石印方式还是占了几乎一半以上,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的图书出版业。这种转变还反映在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变化上,传教士出版机构一改传统中国书坊内部管理单一的形式,采取了较为现代的管理体系。印刷技术的变化,也促发了中国出版业销售方式的变化。这些都为中国图书的出版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印刷术扮演了重要的传播工具角色。如果说历经千年的手工制作的雕版印刷是中国图书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技术基础的话,那么这一技术基础却在十九世纪内遭遇了西方传教士引进石印术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战,印刷生产方法的改变是近代中国图书文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环节。
《铸以代刻》所研究的是十九世纪第二次“典范转移”过程中,传统雕版印刷被传教士西式活字印刷普遍取而代之而形成的“变局”。西方的铸字印刷术东传,不仅全面取代了中国木刻印书传统,更深刻地影响了百余年来的图书出版。西式活字印刷术自谷腾堡发明以来,在十九世纪传入中国之前,在西方已通行了四百年,但要将之应用于中文印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中西活字印刷术的不同,中国的活字是逐一以手工刻制而成,同一页文字内容出现几个同一字,就要刻几个同一字,因此每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每个活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西式活字与之不同,拼音文字只需打造一百多个字母、数字与符号的钢质字范(punch),再以字范在铜版上敲出字模(matrix),接着以字模铸出铅活字(type)即可。但拼音文字与方块字不同,要在每个只有零点几公分见方的坚硬钢材上雕刻几万个象形汉字的字范,是几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有所变通。一个方式是只打造常用字,伦敦会的传教士就耗费了三十年工夫铸造了大小两副活字,每副各有六千个汉字,二是以部首偏旁拼合成字,如美国长老会美华书馆陆续拥有的巴黎、柏林、上海等三副活字,每副各有四千至七千多个活字,分别可拼成两万多个汉字。两种方式各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前者在遇到非常用字时则以木刻活字替代,有损版面的美观;而后者以机械生硬的部首活字拼合,也会牺牲汉字字形笔画的匀称(《铸以代刻》导论,第2页)。这是活字印刷传入中国初期所遭遇的难题之一,也是为何初期在沿海口岸城市主要流行的是西方石印术的原因。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在中国推广使用西式活字印刷。《铸以代刻》讨论的就是基督教传教士自一八○七年来华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六十余年间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全过程,以及他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作者将这个过程大致分成讨论与尝试(1807-1839)、准备与奠基(1840-1870)、发展和本土化(1871-1898)三个时期。作者主要讨论前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前,主要处理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及东南亚各地尝试各种印刷中文的方式,这一段与作者之前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主题相同,但范围、内容有别,有相当的篇幅是研究麦都思及其巴达维亚印刷所,该所先后采用了中文雕版印刷、石印和西式活字印刷,具有丰富中文印刷经验的麦都思在一八三四年《中国丛报》上发表了比较三者的成本与优劣的长文,得出了西式活字印法最为合适的结论(《铸以代刻》,第102-103页)。自鸦片战争到同治朝的约三十年间,西式中文活字进入了实用阶段,并因而奠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铸以代刻》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讨论这一阶段的变化。从技术上看,传教士不仅继续以西方传统工序铸造中文活字,特别是姜别利从一八六三年起,在五年内陆续完成了香港活字、上海活字、柏林活字、戴尔活字、巴黎活字等大小六副活字的新创、改善和增补,也以价廉工省的先进电镀技术大量复制(《铸以代刻》,第507-514页)。这一时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备了和木刻竞争的技术与生产条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方法,终于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和士绅阶层,如郭嵩焘、王韬和一位住在广州的翰林等,也对此感到兴趣,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之一洪仁玕也来商洽购买印刷机和活字,上海道台丁日昌甚至计划购买英华书院的字模,尽管传教士理雅各意识到这种出售可能给自己带来商业风险,但他还是愿意卖给丁日昌,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官员真心重视和使用西方知识的一个指标(《铸以代刻》,第294-296页)。
近代的机械印刷代替手工印制,西式活字取代木刻,逐渐达到与石印术旗鼓相当,并最终取代石印术成为传播新知识的主要载体,这一过程构成了近代的第二次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这一堪称“出版革命”和“知识革命”的“典范转移”,同时伴随着这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在空间上由南而北的转移。《铸以代刻》十二章的描述,正巧呈现出从巴达维亚、澳门、香港、宁波到上海的空间移动。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带动的这一巨大的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还有一个复杂的本土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即这一从麦都思巴达维亚印刷所到墨海书馆,从澳门华英校书房、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到上海美华书馆的书局搬迁过程,同时伴随着这些书局如何从中国文化比较疏离的地区,向中国文化的核心地—江南的北上转移,而此一时期的上海,也正面临着江南腹地的书业的区域移动,大批江南书业的商人迁来沪上,这种区域移动与外国传教士西式印刷技术的由南而北的空间转移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有哪些复杂的历史合力,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