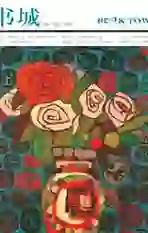何敢自矜医国手
2016-12-01张宪光
张宪光
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四十岁,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招,赴鄂商办芦汉铁路,对他来说实是天赐良机。前一年他向翁同龢赠送字画,试图借机营办铁路,结果被翁氏称为“邪蒿”。这一次赴鄂,他身上似乎也只有一张向洋人借来的一千万两的空头支票,动的是以无搏有、以小搏大的念头。一个介于体制夹缝中的人,要想办成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必须疏通官场门路,承认当时官场的一些潜规则,刘鹗为了一展宏图不惜行贿、开假支票,折射出的恰恰是当时的官场生态。
关于这次武昌之行,蒋逸雪《刘鹗年谱》说:“时之洞左右,言路政者首推盛宣怀,宣怀嫉其能,觝排不遗余力,所拟芦汉路委员名单竟无鹗。”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说法也相近,并补充说:“盛是实缺道,特保的四品京堂,先生不过是一个候补知府,从官阶上说他也是上司,不能有什么争衡。两人当时的争执,据我分析,焦点在利用外资方面。因当时两人都主张借款办路,盛主张借比国,先生主张借英款。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幕后的帝国主义者就必须排斥其他一方,斗争表面化以后,就成为个人之间的争衡。”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刘鹗此行并非完全失败,而是开始了一段和盛宣怀的合作关系。现存盛宣怀档案中,保存了刘鹗致盛宣怀书信二十余通,从未被披露,尚可以让我们窥见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节。
这批书信中,有一份刘鹗进呈盛宣怀的履历单,相当于今天的个人简历,记录了刘氏早年的一些事迹:
发往山东差委选用知府刘鹗谨禀呈令陈:卑府现年三十七岁,江苏镇江府丹徒县监生,于光绪五年报捐同知,不论双单月选用。十五年正月,蒙前东河督宪吴调办郑工善后分局提调。十六年三月,蒙前山东抚宪张调办河工文案。十八年,蒙山东抚宪福奏送总理衙门考验西学,十月蒙总理衙门奏请录用,奉硃批着交吏部带领引见,十一月初六日引见,奉旨着以同知发往山东差委,十二月领照到省。十九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委办黄河下游提调,九月霜清,蒙山东抚宪福以三泛安澜保奏,奉上谕发往山东差委同知刘鹗,着免以选同知,知府选用。十月,丁母忧,回籍。二十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托委就近在籍办理山东赈捐。二十一年十一月起复,须至履历者。
这份履历单的写作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二年武昌拜见张之洞之后,希望能够投奔盛氏,目的在于从接下来的铁路修筑中分得一杯羹而已。其中多有与年谱不合处,可据以补正年谱的缺失。
综合考察“盛档”中的这批书信,可以发现刘鹗一直与盛宣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应盛氏之命赴汉阳铁厂为郑观应诊治疾病,也曾为盛氏谋划购买福公司的股票。《老残游记》中所写老残留有太多的刘鹗的影子,之所以把他写成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既与刘鹗精于医术有关,也植根于他对时事的基本判断。他在《〈老残游记〉自评》中说:“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种病症,非先醒无法治。”梁启超在与刘鹗的唱和诗中也有同样看法:“自古文明第一州,卧狮常在睡乡游。狂澜不砥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块垒,蛞蝓空画旧墙楼。漏卮真成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所以《老残游记》中的“睡”与“病”皆有隐喻意,上承龚自珍《尊隐》,下开鲁迅“铁屋子”的比喻。不过与龚自珍“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同,刘鹗要为大清王朝更换一个新的“西洋罗盘”,已充分认识到“古时丹”已经不能适应动荡的时局了。在医学方面,刘鹗著有《温病条辨歌括》《要药分剂补正》,其医学思想现存文献很少涉及。这批信札表明,刘鹗曾任天津海关官医,并奉海关道长官盛宣怀之命赴沪行医,自愿施诊,其医学思想也体现得更明确。其上盛宣怀禀云:
卑职屡奉面谕,谓中国医学日废,理法尽弛,动辄伤害人命。即有一二稍负时望者,又必故高身价,取资索酬,每出意外,穷苦商民,实受其害。此风上海更甚。并谓卑职如果自爱,日后随至沪上,当资以目下薪水,俾得驻沪行医等因。卑职闻命之下,曷胜惶悚,自惟学浅识卑,何敢当此重任。惟以数年荫庇,教养多方,所诊各衙署、各税关、各公馆,数年来幸无陨越。从此奋发黽勉,实才实心,或不至有负大人期望。……窃念卑职至沪,既得所赐薪水,于早晚两次进诊大人福体后,尽有闲暇时刻,何敢苟安延玩旦夕,可否咨行上海招商、电报两局,俾得局中腾有一席空地,驻足其间,施诊上下等人。及轮船到岸,遇有猝发等病,除每月津贴油烛纸张数元外,自愿效力,不取分文,实于局中窘苦人等、轮船到岸猝发等病及卑职长久驻足效力之处,诚谓两有裨益。
倘若不看到这封信,我们很难相信刘鹗曾依傍过盛宣怀这棵大树,充任其贴身医生,并试图借盛的力量为穷苦人行医治病。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刘氏后人在塑造刘鹗的形象时为什么从不提及这段隐秘的历史,莫非完全不晓得二人之间有这样一段瓜葛?在另一封致盛宣怀的信中,刘鹗则系统地比较了中西医学的优劣:“惟外国医学,自哈斐创言回血管而后形体始烛其微,医学始有要领。伊攻中国营卫荒谬之说,所言非无至理,而于中国六经气化标本虚实之理,实未能知其毫末,以致医法医药茫无头绪。”刘鹗在医学上很注重中医的气化标本虚实之说,认为“泰西医理虽劣,而学业殊勤,药物甚精,行之殊慎,非中国所能及也”,“中华医理虽优,而学者无人,药物多伪,行之殊欺”,中医在迭经丧乱以后已经衰落不堪。因此刘鹗主张融合中西医学:“学医者,当学古圣气化标本之理,操之渐熟,兼看泰西所译之书,细究其真,默会贯通,出医自有把握,不必效欺世误人误己也。求医者,当求夫辨症之精详,医法之精当,所言之应否,不必弃华医而不论,中西皆可取也。”这种沟通中西医学的观点,与刘鹗主张输入西洋技术、利用外资的开放胸襟是完全一致的。
刘鹗与盛宣怀交往的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即为盛氏购买福公司的股票。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五日,刘鹗曾致盛氏一函:
股票事前日晤哲美森,嘱其将伦敦来电钞出,并嘱翻译生译出恭呈钧鉴。又闻九江路有利安号者,亦可经手代购。又有长利号,皆著名经理买卖股票事宜者也。可否派人兼访有无可以取巧之法,盖为款甚巨,倘能省一先令,总数即在万金以外。福公司股票,自广西事起价一落,中俄事起价又一落,正、二月间至每股九个先令,今者已长至十五个先令,进步不为不速。宫保如欲办,总以从速为宜,倘一经出煤,价币数倍,此后则日长之势也……
档案中尚有意大利商人开办的义丰银行大班既济的一封短函,由刘鹗请人译出,大意云盛宣怀通过义丰银行购买福公司股票四千股,每股十五先令,表明盛宣怀听从了刘鹗的建议。其中,盛宣怀最后成功认购三千股,刘鹗认购一千股。据报载:“山西河南福公司矿路股票,总名曰山西股票,利息甚好,刘铁云观察在京欲设法使华人多购,冀收利益,而华人卒无购者。”刘鹗之所以希望更多的政府高官、富商认购股票,为的是在让他们获利的同时,可以推动福公司在华业务的扩展,可是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这一新事物,故而应者寥寥。而盛宣怀深知其中奥妙,故而有眼光、亦有实力购买福公司的股票。由于目前尚不明了的原因,刘、盛之间后来的相处并不和睦。刘鹗壬寅(1902)正月二十七日记云:“薄暮赴子谷之约,因闻盛有电来云:改路须俟芦汉铁路成再定准驳,直疯矣。”此时刘鹗已经傍上了王文韶、庆亲王这样的高枝,或许已不太把盛宣怀放在眼里了。
二
刘鹗身背的最厉害的骂名,不是买办,而是汉奸。其实在许多人眼里,买办基本上等于汉奸,这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的《中外日报》以及留学生杂志《浙江潮》刊登了很多攻击刘鹗及其同伙出卖路矿的文章,措辞激烈,意气激昂。如一九○三年八月十二日第六期《浙江潮》刊有《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一文,对刘鹗进行了声讨:“咄!刘铁云何人?意大利何国?浙江路矿何物?乃胆敢私以一纸书,与外国人私相授受乎?意大利之欲谋我浙江也久矣,往岁要我三门湾,大吏亦几许之,幸以中止,然固未尝一日忘浙江也。浙之矿,浙之髓,而路浙之脉也,髓竭则枯,脉绝则死。路矿既失,虽有浙江,犹无浙江也。无浙江问浙人,居何住?族何居?子孙何所产养?外人之谋人国也,朝吸其精焉,夕得其膏焉,奄奄待毙,则土地自为我有,其于中国亦然,唯我中国不肖孙子,贪目前之末利,忘百世之大害,与订矿约,与订路约,日以万金不可买得之家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唯恐其不受。今刘铁云又以此施之于我浙江矣,浙人非尽亡者,顾不闻其事欤,何竟无一人焉,出其全力以为我浙江与刘铁云一搏也。”保卫路矿主权无可厚非,是民智苏醒、民权发展、舆论干预政治的一种历史进步,但这些言论本身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煽动性和暴力色彩,带有二十世纪所特有的泛政治主义话语色彩。此外,当时的社会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既没有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外交观念体系,更不用说现代企业的契约精神了。而乡绅阶层的指责还要概念化,“不计国家利害,不顾舆情顺逆,只期自饱私囊,实已阴伤国本”之类的语言乃是公牍套语,根本与刘鹗“养而后教”的思想背道而驰,但是作为“全浙公敌”的刘鹗在这类话语面前所做的抗争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另据年谱载,庆亲王奕劻与丁宝铨有一段对话,也很有趣:
奕劻询曰:“刘鹗为汉奸,汝知之乎?”宝铨对曰:“汉奸之名,忌者诬加,王爷久知之,何以今日又想问?”曰:“汝与为亲戚,确知其不为汉奸乎?”曰:“少同学,长同游,即不为亲戚,亦敢保其不为汉奸也。”曰:“知否刘鹗现为外人在浦口买地?”曰:“绝无此事,虽令以全家相保,亦敢任之。”事得暂寝。
然而第二年刘鹗还是被逮捕,流放新疆,最后死在那里。
关于刘鹗被逮的原因,汪叔子先生写过一篇 《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利用清廷外务部档案进行了扎实而富于新意的研究。汪文认为外务部奏章中所奏列的戊戌垄断矿利、庚子盗卖仓米两项罪名均为诬词,而“丁未走私辽盐”这一罪名“则自乙巳迄丁未,勾结外人,越境走私,违律犯法,确属有据”。姑且不论一个人是否会将自己的犯罪事实毫无隐讳地记录在日记中,即便真的是走私贩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家产籍没、流放新疆、永远监禁的重刑,所以这份奏章确如汪先生所言属于“官样文章”,其真正原因有可能与高子谷、钟笙叔的泄密案有关。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高、钟二人将朝廷密电码出卖给外国使馆,与之交易的多达十四国,被袁世凯奏明拿办。高子谷为刘鹗妻舅,钟笙叔则为高氏妻舅,故三人是一个很亲近的利益团体,而刘鹗与“高、钟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将机密出卖给英人、日人,因而刘鹗亦难逃“汉奸”之罪。但是这一结论仅是推理而已,目前尚未发现刘鹗与高、钟泄密案有关的直接证据,日记中所写到的诸多电报往来很可能在当时并不是违禁之事,故刘鹗可以从容记之。据学者研究,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在袁世凯等人的领导下厘定了《泄漏电报章程》,保密措施不断加强,但是“因循弊混,营私误公”的现象实在很普遍,甚至于前一天的政府要件第二天已经全文登载在报纸上,管理混乱可见一斑(参见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这也就可以解释刘鹗为什么可以看到那么多密电了。换个角度看,高、钟泄密案也有可能是袁世凯打击王文韶的一个手段。
高子谷,原名高尔嘉,其兄高子衡原名尔伊,出身于杭州双陈巷高家,其父高白叔为著名商人。《凌霄一士随笔》引《兰隐斋笔记》云:“袁爽秋昶,戊戌六忠之一,全椒薛怀生侍御之婿也。其女适高子衡观察尔伊,世为杭州首富。尔伊四十余以疾卒,袁夫人欲改适,子衡之弟尔嘉,号子羡,王夔石相国之孙婿也,跽请于嫂,幸无夺志,家非不足于财者。有侄数人,听择为嗣,且年近五十,宁又更贻家门羞也。袁夫人曰:‘君言诚有理,惟贞节之说,迂儒不近人情之谭也。吾当力破此戒,以开风气,无庸更为烦聒。于是嫁一大腹贾而去。子羡后与我相见京师,尚垂涕而道也。”这段记载恐不确。据《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高子衡一九五○年尚健在,活到七八十岁。尔嘉则曾奉袁世凯之命,与法国商人沙札郎合办华兴银行,估计未能成事。泄密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钟笙叔,原名钟镛,后更名广生,号愻庵,浙江余杭人。曾任国史馆校对、肃亲王善耆咨调,流放新疆后受到王树柟的赏识,参与编纂《新疆图志》,辛亥革命以后长期任职于东北军政部门,著有《新疆志稿》《逊庵文集》《逊庵诗集》等。其《记同绳碣》一文,记叙刘鹗西行访碑的事迹,而未见称引:“吾友刘子铁云,博雅嗜古。戊申遣戍西行,途辙所至,辄搜求金石文字,所见遗碑残碣,未尝不流连摩挲而不忍去也。冬十一月,道出安西州之三道沟驿,据驿舍数武,有断碣偃官道旁。其字半漶漫不可读,爬垢剔翳,久乃辨,所谓同绳篇者。”篇末议论,也颇有意味。巧的是钟氏在东北期间与曾经抢夺刘鹗浦口地产的陈浏长期共事,友情甚笃,并为之作行状。其中谈到争地始末:“光绪季年,津镇铁路议起,丹徒刘君铁云逆策地形,必改道津浦,乃醵资买入洲地数万顷以待之,已而亿中。公(陈浏)怒其罔市利,执持短长甚力。刘坐此得罪,地多没入官。及公自闽中归,洲地折入于势家,恒挟官力振商市,以牟取私利,公又创民埠以抗之。平心而论,刘之亿中,若六博然,欧美谓之投机,非必为罪,所谓匹夫怀璧者也。至势家效尤朋分其罪,实浮于刘。然比年界画,商埠屡起屡仆,官且无力,又焉用抗。余尝与纵论前事,惜其为计之疏,而又怪其快意当前,坐致颠困而不悔也,岂非天哉。”此论最为笃实可信。可见浦口争地一事,祸首全在陈浏一人,而刘鹗受害最深。
三
作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刘鹗并不满足于为人治病,而是隐隐地以“医国手”自居。《老残游记》的寓言性,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证据。
《老残游记》从蓬莱阁写起,写到了“浑身溃烂”的“黄瑞和”,写到了那艘千疮百孔的清帝国的大船,疾病的隐喻一开始就笼罩在小说中。刘鹗自评引元稹诗句:“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他显然是把自己视为谪落人间的“仙吏”,来拯救这艘即将沉没的帝国大船。同时他又把自己写成一个摇串铃的医生,也是想为千疮百孔的黄河文明贡献自己的救命良方。小说的开头如是,结尾亦是别有深意,“九曲珠”“千日醉”“返魂香”云云,皆有所影射。小说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的意象,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也象征着黄河文明进入了一个万物皆枯、孱弱不堪的发展阶段。在一个集游记、公案、政治隐喻于一体的叙事框架中,《老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寓言色彩。例如《老残游记》第一回关于梦的描写,也是一个隐喻,似刘鹗这般“具菩萨心,得异人口诀”的醒世者,其百般主张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免不了“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了底”的命运。《老残游记》的写作开始于一九○二年,这一年旧历五月初四刘鹗坐船北上,初六日“拟看日出,见东方有黑云幕海,未几大雾”。初七日,刘鹗做了一梦:
一点开船,二点后雨。因困,略睡。梦至一高楼,月三立于侧,云:再上为催速转佛之居,黄三先生见过,作颂赞之矣。予升梯入,见佛紫面,大口,厚唇,与予握手为礼。予亦作颂赞之曰:“天旋地转,有常度兮,不可催而速也。日月运行,寒暑往来,有恒节兮,不可催而速兮。圣人去兮,人心弊矣,世运之转,不可缓也。我佛慈悲,其催之乎,吾之望也。吾人业识,痼蔽深矣,吾佛慈悲,为我转之,吾所求也。克转克速,我佛慈悲,弗敢忘也。”颂成而觉。
刘鹗的梦中颂赞,表现了他对时局进展缓慢的深重担忧,有一种人力不可为的无奈。一周之前,黄葆年恰好也做过一个梦,“升至极高之曲”。戚先生云:“至此地位,盛衰二气俱脱粘矣。赵明湖衰气未脱粘,屈平之流亚也;刘□□盛气未脱粘,苏张之流亚也,皆不可升孔孟之堂。”刘鹗闻之警悚。可见《老残游记》开头的这个梦并不是无缘无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太谷学派背景,来自刘鹗个人对时局发展缓急的判断。写作续集的时候,刘鹗意犹未尽,在序言里又发了一通关于梦的言论。时局如梦,催不得,亦缓不得,只能让人徒唤奈何而已。
《老残游记》第八到十一回对桃花山的描写,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隐喻,历来众说纷纭。作者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老残所在的充满了清官虐杀的、万物萧疏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申子平所拜访的带有“桃花源”色彩、景物绝俗、意境奇丽、人物卓异的山中世界。《老残游记》整本书都在写一个发生在冬天的故事:现实世界的冬天哀号遍野,玉贤、刚毅一般人物见识庸短、卑劣残忍,山中的玙姑、黄龙子等人则超凡脱俗、有林下气象;现实世界的玉贤、刚毅如乳虎立豕吃人不吐骨头,理想山中世界的老虎则“一声虎啸,四山皆应”,与人和谐相处;现实世界是黄龙子所说的阿修罗的部下“让这霜雪寒风出世,拼命的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而理想的山中世界则昭示着“文明华敷”“灿烂可观”的“花萼之象”。这个山中世界,我以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龚自珍的《尊隐》,一个是来自太谷学派“极乐国”的想象。龚自珍在《尊隐》中提出岁有三时、日有三时,而清帝国则处于日夕之时:京师则贫、贱、轻、日短、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则实、贵、重、“泊然而和,冽然而清”;朝士“寡助失亲”“僝焉偷息,简焉偷活”,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刘鹗笔下的山中世界,黄龙子、玙姑诸人皆是山中之“傲民”“悴民”,具有深邃的思想和洞彻古今的智慧,如虎啸龙吟,充满了生机。相反,现实世界则是“端毓刚徐赵李伦,兴高采烈杀洋人”“回思众恶盈廷日,天纵神拳不住夸”的混乱局面。其次,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带有仙境色彩的桃花山有可能是以张积中的黄崖山为原型而写作的,但同时也是对于太谷学派三教圆融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在刘鹗所参与的太谷学派活动中,一九○二年举行的愚园雅集意义非凡,刘鹗一直念念不忘,专门请胡仲尹另写一本,并作序赋诗:
愚公园,愚公谷,黄山之南蒋山北,中有青青万竿竹。瑶琴锦瑟张高秋,玉液金泥应丹篆,仙人如麻颜如玉。朝看素女采玄芝,夕览青童荐黄菊。峡蝶图中梦可寻,希夷榻上书堪读。愚公园,极乐国!
诗中的“瑶琴锦瑟”“仙人如麻颜如玉”“素女玄芝”,以及序文中“煮茗吟啸”及“群花怒发,清芳袭人”,小说中似多有照应之处,仿佛描绘了一个更为奇丽绝俗、异人丛集的“极乐国”,凸显了“道在山林”“道在民间”的思想。
林语堂曾说:夫时代之不了解,乃先觉之常刑。刘鹗身上固然留存着那个时代投机者的种种缺陷,却是一位先知先觉的知识人。他在一九○七年写的《风潮论》已预言了清朝的灭亡:“诗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文亦乱,无孙文亦乱。当轴诸贤,宜去其忌讳之心,直陈于上,而速筹挽救之法也。不然者,一二年后即不堪设想矣。”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清朝就呜呼哀哉了。细细地阅读他的《呈晋抚禀》《矿务合同》《上政务处观察书》《创办大清银行节略》残稿诸篇,会发现刘鹗对晚清赔款造成的恶果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主张在路矿建设中大量利用外资,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养民富民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一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殉道者的精神,无论受多大挫折亦不颓唐,不退缩。他在一封与同门的信中写道:“夫人学道如牛毛,成道如麟角。是何因缘?有三难故:学道不明道,与不学等;明道不能行,与不明等;行道不能力,与不行等。”可见他行道的决心。不幸的是,他最终成了晚清政治斗争的陪葬品,他所描绘的山林终究只是一个虚幻的图景。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来说,再好的医术也难以妙手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