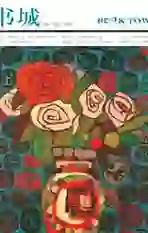为同代人写作
2016-12-01黄子平程德培吴亮
黄子平 程德培 吴亮
编者按: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思南公馆举行了关于长篇小说《朝霞》的对话,这是本年上海书展一个面向公众的阅读活动。参与对谈的有评论家黄子平、程德培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吴亮。他们三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活跃于文学评论领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作为评论家的吴亮突然现身长篇创作园地,让许多人惊愕不已,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话题。本刊征得三位对谈者和主办方同意,这里摘要发表对谈内容。
这次活动由上海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现场主持人是同济大学张屏瑾教授。
黄子平:听说吴亮写长篇小说我是吓一跳。对于批评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替他捏一把汗。居然五个月写出来了。后来他不断地微信给我,说最想听我的意见,我回复说还在断断续续地看,确实也是。我整个上半年参加一个世界华文的长篇小说奖的评奖,看六本大部头长篇小说,加起来两百万字,处于“长篇小说中毒状态”。要有一个清醒的、干净的阅读状态,才好来进入老朋友的冒险历程。
批评家,我自己的体会,基本就是一个人称位置,比较好处理。批评家的“我”就是我,而作者、人物对“我”来讲都是界限分明的“他”。小说家必须把这些个“他”变成“我”,进入到每一个人物,进入到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情境。“他”变成“我”来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就是小说家的想象力,或者叫移情能力。吴亮作为批评家,通晓了各种小说的招数,那些玩过的他都知道了,等到他自己来玩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拒绝批评的。一旦拒绝就会激起我们批评的欲望,拒绝就是邀请。可是发现被他邀请进去以后吴亮把我们该干的活全干了,这个作家一边写小说一边拆小说。你刚想把《朝霞》的结构捋一捋,半道上他把提纲放在那里等着你呢,然后又说这是未必要完成的计划。所以如何应对批评家写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我一直读的是电子版,来了上海以后把纸版好好地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很为吴亮激动。我一直认为吴亮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和散文家,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替他捏了一把汗的。长篇小说新秀闪亮登场啦!
从这么复杂的文本里我想提炼一些可以说的,首先就是今天的对谈题目“为同代人写作”,我听说吴亮要写小说的时候,很本能的反应就是写给我看的。有一年我回到上海,在上海老朋友那么多年以后再次见面,不知道讨论什么问题,吴亮很激动地说有人问他是否不再写文学评论了,他说不是不再写了,而是子平都不在内地还写什么文学评论?我很感动,他写什么都把它看成就是为我写的。好像我们都把“读者”这个概念理解得非常狭窄,极为排他,其实恰恰相反。
对“同代人”,我以前理解得比较狭窄,指的是同年龄的人或是同时出道的人。听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介绍吴亮的时候都加了一个形容词,这就是那个“八十年代的那个吴亮”,我也蛮认同这个标签,刚才进来的时候有年轻的听众说“我是读您八十年代的文章长大的”,我就很受用。但这是我以前比较狭窄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同时代人?后来我读到意大利的哲学家阿甘本有一篇文章讨论什么是同代人,或是另外一种译法什么是当代人,至少有三点很有启发。第一,用的是尼采的说法,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镶嵌在这个时代之中但是又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有一种距离,得以看清楚时代。那些跟时代贴得很紧,方方面面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的人,反而不是同时代人。第二,他是能够凝视这个时代黑暗之光的人,其实所有经历过当代性的人,都能体会到所有的时代都有它的晦暗,所以当代人是像蘸着墨水一样蘸着这个时代的晦暗来书写的人。第三,阿甘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人都不是直接出现在“当代”的,不同的人都是由不同的“古代”来到这个时代的。有些人从“李白的盛唐”或者“苏轼的北宋”进入这个时代,我的一些朋友非常固执地要从“鲁迅的五四”进入当代,吴亮呢,好像他非常固执地要从青少年时期的七十年代进入当代,在他的“罗陀斯岛”上跳舞。吴亮忽然发现很多九○后都很喜欢《朝霞》,也许他们正是他所期待的“同代人”。
程德培:我曾经在一间办公室里跟吴亮面对面坐了十年,两个人当然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名字,吴亮是上下结构,程德培是左右结构。他有时候比较圆滑,我有时候比较直爽。他有时候是个愣头青,我有时候是个胆小鬼。关于这部小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编按:指程德培关于《朝霞》的评论文章《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见《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我从同代人的角度评论吴亮,可是比吴亮年轻一代的,比如张屏瑾或是她的同代人,他们怎么看吴亮?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几年前,我第一个看《繁花》打印稿,写了评论,谁想到它现在的名气如日中天。自从有了金宇澄和吴亮,大家都在说,上海的老男人到了六十岁以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我差不多,我就非常感慨,年纪大了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半夜经常想这个事。比如里弄,我小时候住在虹口区,比金宇澄描写的环境稍微差一点,评了他们的小说以后,我经常想小时候那个叫三德坊的里弄。我们一起长大的小朋友,有一个是汉奸的儿子,他父亲是日本人的翻译,那时每天在里弄扫马路,有一个是副食品公司党委书记的儿子,还有一个出身非常地道的工人阶级家庭,当然还有另外几个。我们几个最要好,但是我们的友谊绝对不会因为家庭成分不一样、父母在里弄的地位不一样而受影响。因为有了《繁花》《朝霞》,我们一起聚会时,大家经常喜欢回忆里弄的生活。里弄有几个层次,比如沿着外面的一圈有二房东、三房东,里弄中间有一些都是独门独户,做医生的、做律师的,还有一个过去是国民党报纸的主编。汉奸的儿子尽管地位比较低,住的房子却比我们的大,身份比较纯粹的人住得很小,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房子多的人被搞出来了,分给那些身份比较纯粹的人。
我有时候在想,那时候竟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一个小说家,如果写写里弄里各种成分的人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应该是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是做舞女的,解放以后不是很光彩,走在街上总被人家指指点点。转眼之际,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想过解放以后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如果我脑子清楚,或许能写得很精彩,但是我容易遗忘。现在里弄也拆掉了,我的记忆力不好,所有的故事也随着遗忘而流失。还好金宇澄观察人生比较仔细,还好吴亮的记忆力比较好,吴亮抓住这点点滴滴的记忆,抓住他小时候成长的故事,他留下了记忆,变成了《朝霞》,我则变成了“晚霞消失的时候”。
吴亮:去年八月的一天,金宇澄跑到我办公室来,他写了《繁花》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聊他的作品。那天我们私下里聊得有些八卦,我说听说你的小说里写了好多我们都认识的人,我就问小说里的某某是不是我们周围的某某,他就笑了,说吴亮你很俗,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金宇澄说你不妨自己写写看。
于是我就写了。因为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一写就很放肆,还一段段发到网上。网上有人会看,我用一个笔名作掩护,所以有些不在乎,也不在乎人家看不看。写到后来,子平跟我说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观感,我对他也是作了零零碎碎的描述,有深层的交流。写这个东西,并不是一开始有很大的野心,是写到一定程度时野心就慢慢滋长了。不过,我目标很清楚,比如我有一个理想的读者群,包括我的同事小张、小黄,都是我的读者,但是肯定还不够,但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不相识的人交流。
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我觉得我的写作可能是写给作家看的,应该是写给评论家看的,因为它有一定的阅读难度。文字叙事必须是面向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人,里面涉及各种信息、知识、观点和各种多样性,对形式有研究的人,对小说风格有点了解的人,才不至于把它作为一种障碍,而能够作为一种乐趣。甚至,我对当代文学并不满意,包括那些写上海的文学,或是那个年代的叙事,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想,我要写一个给你们看看,心里面憋着这样一股劲儿。当然,金老师已经作了很大的突破,但我跟他的叙事完全不同,虽说金老师写芸芸众生,我也写芸芸众生,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不过,我的写作不是要去填补当代文学的什么空白,一切都是由于机缘、兴趣和冲动。
我在工厂那些年,曾经有些领导或是上级公司发现吴亮有点才华或是什么,想要把我弄到宣传部门,我都拒绝了,我宁可做工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一些偶然因素,我的机会来了,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文章发表时总是被删了这段删了那段,在那种困难状态下我就可以不写作,因为对我来说无所谓。七年前作家协会让我做《上海文化》主编,我说我可以试试看,领导当时问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不会以一般读者为目标,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这份刊物只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我们的刊物果然成了公认最好的文学评论刊物,不仅出了好文章,也发现了很多人才。
每次有机会我都坦然陈述本人没有大学教育的经历,我非常自豪地在我的小说附页上写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对于有大学教育经历的人,我并没有任何嫉妒与偏见。我只认人,比如我对刊物的两个同事说,你们都来自复旦大学,但并不是复旦给你们带来了荣耀,反过来说是你们给复旦带来了荣耀。我总是把人才摆在第一位。马克思、尼采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可能许多人都说不上来,这不重要,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精神具象。
我相信一个个具体的东西。小说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面对一个一个的人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种经验今天也跟子平讲了,我这次写作因为要钻进不同人的状态中,我的自我开始放弃,放弃自我才能写作,虽然他们说我的小说充满吴亮风格,但是我在写作中经常放弃自己,只有放弃自己的时候你的世界才能变大。因为有这种情况,我现在反而有点忐忑。
黄子平:我最深刻的感受可以简单地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讲(让我们回到十九世纪陈旧的批评方法)。吴亮最早的书名叫“无处藏身”,我读出来是一个逃亡的主题。从一开始马立克从新疆跑回来,中间还有很多微型的逃亡,伪造病假条等一系列这种小逃亡,到最后小说的结尾,阿诺做梦梦到马思聪—那年月最有名的逃亡者。大大小小的“逃离”反复地缠绕,这么复杂的文本中还是可以勾一条比较明显的主题线,但我今天不想发挥。我比较想说的就是《朝霞》的形式,我把它归纳为—借用法国人布朗肖的概念—叫作“无限交谈”。交谈对话的形式非常明显,首先是它文本内部本身的对话,因为他把文本切得很碎,刚刚这一段讲的是上海里弄里面那些俗不可耐的无聊透顶的生活,紧接着来了一段抒情的充满哲理的遐想,然后又被打断,一段戏剧化的,甚至包含了舞台装置的提示。文本当中充满了对话,我最喜欢的就是吴亮提供的很多他自己命名叫作“日常杂语”的部分,这种杂语都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经常是离题的。跟这种“日常杂语”相对应的是“严肃交谈”,比如三个教授之间的对话,或是大学生和初中生的知识上的传授,经常带出来一个提示“这你就不明白了吧”,或是讲完一段马上叮嘱“不要在外面说”,这样一种提示使它从“日常杂语”的混沌中浮出来。这种对话在何种意义上是“无限的”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断地被打断,被情境打断,被外在的压力打断,打断产生新的对话。如果这个人滔滔不绝,那就没有对话。在《朝霞》里有一种声音是不能跟他对话的,因为他滔滔不绝。吴亮只能用无数的东拉西扯来掩盖这个滔滔不绝的声音,稀释他的滔滔不绝。对话有几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因为这些对话的人都是哲学上说的“不充分的存在”,他不能完美无缺,说话是自相矛盾的,或是不完整的,别的人要来补充他,反驳他,这是基本的前提。
吴亮设置的这些对谈里面充满了对话的动力,就是因为不完美。不完美会直接带来一个“不可预测性”,你不知道他的回答从哪一个角度切入,或是从哪一个情境引申,这就使得对话能够不断地进行下去。但是也有停止的时候。其实对话中总有一种倾向希望能够达到共识,我们这代人有根深蒂固的使得对话终止的“辩证法”思维,来把分歧达至一种虚假的综合。如何使对话重新启动?我觉得吴亮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才能使对话重新启动。裁判,这不是说这个人说的对,那个人说的不对,他自己提供一个完美的答案,不是的。“中立的裁判者”的功能就是不断把答案转化成问题,使得这个对话重新启动。我是这样来读《朝霞》里面的关于《圣经》的一些摘记,当我们涉及中立裁判者的时候只能想到“上帝”,它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所有的表述都转化成问题。
在这些无穷的交谈里面的很重要的主题,跟逃亡相平行的一个主题是“知识和真理”。叙述者肆无忌惮地引入了大量的摘抄,人造卫星,集邮知识,烟草种植,南斯拉夫电影等等,越来越杂。要把这个小说变成一本百科全书似的。这些杂知识其实是无用的,又对应于那个“知识无用”的时代,跟又红又专的“红”没有关系,甚至跟“专”也没有关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头一尾,最重要的跟哲学有关系的命题就是“真理”。这一点被大量的关于权力斗争的历史叙述遮蔽了。大概是一九六四年,有一篇文章《人的正确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文章不长,我们当年都会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跟吴亮聊天,说他小时候产生了疑问,人的错误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好像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大为震惊,我就想为什么当时我不会这么想。到了七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个大家比较记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头一尾,都说那是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其实这都关乎“真理”。《朝霞》里交谈杂乱无章,在那个“阳光灿烂”(因而看不见朝霞)的日子里,有人滔滔不绝,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沉默无语,但是所有交谈都在指向知识和真理,因而无法停止。
程德培:这里不得不重复自己写过的文章,再简单概括一下。我这个人不管写得怎么样,还是相当严肃的,我不会因为吴亮是我的朋友就一味说他好话。一开始吴亮总是盯着我,你看怎么样?我一直不表态。后来他写到差不多的时候,有一次实在熬不住硬要我讲,我就讲了一些印象,觉得他开头不怎么样。他马上把我打断,你不要说了,我连结尾都想好了。从此一起吃饭时我就不谈他的作品,一起去南京开会我也不提这事情,他半夜敲我房门我也不应。他写完了,我也差不多把小说读完了。我表了个态,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原来对它有一个比较低估的评价,读完后我说越写越好。一开始,我觉得整个内容到形式,或是先锋,或是反现实主义小说的那套东西。他写着写着好像关系理顺了,就像是他小说中说的,回到了巴尔扎克,或像他讲的向巴尔扎克致敬。这是指观念上对人的认识。这个到底好不好我不下判断,他开始集中写人物,一个个人都站起来了。这个小说就某些方面而言相当反现实主义,而某些观念上又回到了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很纠结的现象。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小说写作过程很复杂,这可能就是吴亮。
其次就是对话。吴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处理对话的经验,最早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笔墨很生动,兴趣上来了可以写很多。对话是吴亮最初进入文学批评的一个文体,这次书展期间他也有一本与艺术家对话的新书上市。他喜欢对话。这种对话技巧,也是《朝霞》这部小说向前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力量。我觉得《朝霞》里的对话也是对应碎片化的写法。一开始我对他的小说不满意,很担心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能搞得下去吗?结果发现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所以我在文章里讲到,吴亮可能天生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写作中不断向现实主义的某些观念回归,或是像他刚才讲的,忘记自己,进入人物内心。我们不能以为,观念是旧的因而就写得不好,我感觉是写得特别好。
只要认真比较一下《朝霞》与《繁花》,你会觉得吴亮和金宇澄对女性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女性观或是某一部分的人生观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另外写文章比较。吴亮八十年代经常讲,一个人如果在路灯下丢了钥匙,怎么办?他说只能在路灯照到的地方去找这个钥匙。这使我想起我写他的评论,一篇评论你写得再好,再花工夫,也无非是开了一扇窗,或是开了一盏路灯,只能在这个路灯下寻找你的钥匙。其实,吴亮的钥匙可能在其他的光束之下。
吴亮:德培对我的了解让我自己都很吃惊,他把我多年来出版的二十多本书全都拿去看,这让我非常感动。好多人都说,程德培写了那篇评论别人就没法再写了。子平半个月前说,想看看程德培的长文,看完后说德培的眼光就是与众不同。
我前面说了小说的生成,确实没有考虑到读者,但是现在读者出现了,特别是今天看到各种年龄层次的读者都有。《朝霞》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大学里面,在电视台、美术馆都讨论过好多次,我一直注意读者的年龄结构。有一次也是在这里,走走主持的,听众年纪大的人比较多,提问题的都是我的同代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代人。那天下雨,有几个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说到记忆中的各种往事。有意思的是,因为我写了小说,我那些老邻居们在微信上拉了一个群,经常跟我聊天。他们以前只知道隔壁的阿亮是写评论的,现在写小说了,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起劲。我想幸好是虚构,要是真写张三李四就麻烦了,所以这些读者的生成现在看起来非常重要,这个事情在发生。
还有一次在饭局上,孙甘露也在,旁边有两个复旦的学生,那两个女孩都是九○后。大家前边的话题东拉西扯,中间一部分讲到我的《朝霞》,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谈起共同经验,后来有人问那两个女孩,她们居然都看过,还说都很喜欢。我说你们真的都看了吗,她们说真的看了,真的喜欢。这部小说开始写的时候,我都没有给自己的同事张定浩、黄德海看,因为他们是七○后,我以为他们可能不会有兴趣。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成见,没有相应的人生经验,他们不会看。可是那两个女孩很仔细地听我们聊天,说他们(饭桌上那些年纪较大的人)看你的小说看的是里面的真实性,看的是感同身受,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对你的文体有兴趣,对你的文本有兴趣。我说你们会向自己的父母打听“文革”的事情吗?她们说从来不问,他们也不说。她们并不很清楚那些情况,但是她们对我的小说有兴趣。
这部小说出来后,我以前的一些邻居,还有我姐姐都来跟我谈那些事情,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知道我有这样的爱好。可见小说的力量很大,一方面是虚构,一方面又将虚构转化为一种真实。一切都在于对人的兴趣。
黄子平:必须重新界定“同代人”的概念。从这个题目扯开来,其实跟交谈、对话都有关系。德培一早就看出来,吴亮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文章就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家伙,“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什么的。什么人可以对话?其实我们总是不断挑选交谈的对象。刚才德培说他们里弄那些家庭背景很不一样的人常在一起聊天,这里面就有一个挑选作用,中国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些人疏离了,有些人离开了,小说里面要不断引入新的情境、新的对话。譬如有些人物在熟人圈里很沉默寡言,但是他出去碰到一些陌生人反而一拍即合跟人家谈笑风生,谈论那个年代的敏感话题。
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感觉这部小说是越写越好,觉得后面越来越像长篇小说。因为前面确实很碎,你要适应这种碎片化写作不是那么容易。写到大概接近最后四分之一篇幅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完整的段落出现了。比较长的一个至少有二十页,这是很重要的段落,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叙述的连续性很强,在一个饺子店里,里面都是交谈,非常有意思的交谈。四个小男生在一起,聊着那个时代的种种谣言,或是传说等等。吴亮的妙处是加进两个小女生来打岔,说这些人真没劲又谈政治。这样那几个小男生没什么好聊的,就聊照相机之类还是男生的话题,聊了半天,你发现又开始谈政治,这个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恰恰是那种日常杂语中的政治。那两个小女生的插入或是干扰,非常重要,反而显示了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年代,政治的无所不在。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段落。
另一个相对集中的段落,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就是关于老鼠和猫,引入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动物话题。小说里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神秘的东西,比如死了好多年的人给他写信,或是影子从窗外一晃,等等。这些都是小说里面最吸引我的,反而巴尔扎克式的写实没有那么吸引我。最后至少有三个人非常神秘地不知道去哪里了。吴亮设计了一些情节,情欲主题跟一直若隐若现的动物主题交织起来了。对应小说开始,我回过头读的时候,发现那只猫在第一节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是一句两句,“猫这玩意太张扬”什么的,那个伏笔已经埋下了。我们都知道动物主题是长篇小说里边必不可少的。
程德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讲述的事情,所叙述的人物,慢慢在你心里开始成形了,或者长大了,或是形成了悬念,或是引起你想知道这些人最后的命运,他的走向,或是世界的发展。像这种写法,东一段西一段的,一开始很难进入,可能结构本身也有这个问题。或者把吴亮估计得低一点,他写到十分之一的时候,肯定开始要想后面是怎么样,不然无法写下去,这样就越写越写进去了,人物也立起来了。
吴亮爆发力很厉害,我和他去广东时,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还有他老婆给他买的iPad,躲到房间里去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写下一篇长篇的提纲,可能一不小心几个月下来,又一个长篇就出来了。
吴亮:这部小说完全是去年的一个冲动,当时没想过要发表。我总觉得,匿名写作的你就不是你,你在网上什么都敢说,用真名就不敢这么放肆了。所以,写着写着,我觉得这个小说不大像小说。
小说写到十万字以上的时候,人物已经有了雏形,可是在哪里停下来,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整个人有点神经质了,生活当中的事情全都忘了,脑子里全是虚构的东西。我不能不专注一些技术问题,要留神时间不能弄错,性别不能混淆,不专注技术很容易犯这种错误。这部小说写好多人物,其中有三四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它不会错。人物的名字取了很多,很难取,它像不像一个人,要好好想想。有些小说里面名字就不像一个人。但问题是,它的性格、它的样貌,不清楚的时候我会搞错,要写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不会搞错,这些人物慢慢地都活起来了。这样,每天都有一帮人跟着我读,弄得我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不能再看闲书,只能翻翻资料。我原先说要写四十万字,可是这样写下去我身体受不了,我说我就写二十万字吧,以后再写二十万字,总要有一个结果。结果二十万字变成二十五万字结束了。小说写完以后一段时间,一直有朋友(包括金老师)问下一部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我本来的想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到新世纪初,四十年的跨度,本来是这样的计划。因为中间的变化,到了二十五万字结束以后总感觉没有完成。我要写下一部,我可能会写,但不会延续这一部的故事,这部小说是没有办法写续集的,我没有能力把每个人的命运继续写下去。而且正像子平说的,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它必须停止,所以它才能开始。
有人问我,你写小说是不是在写第一个字之前就有一个提纲?提纲里面你的目标是什么,或是你心目中的读者是什么人?你是否考虑过改编电视剧的可能?等等。这些问题中包含着一整套艺术生产与投资的理念,譬如改编成电视剧就要考虑它的票房问题。我的写作不是这样,我是个体写作者,不是要组织社会生产,这不是商业化的。当然,作品能够发表上市它就成了商品,那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承诺过它是一个产品。
写作在很多时候是希望能够发表,因为可以跟有共同经验的人进行交流。比如《我的罗陀斯》是我第一本叙事的东西,跟现在这部小说有点关系。那本书是《书城》杂志约稿而形成的,起初他们让我写书评,我很清楚那份杂志的读者,我说不能写书评了,我可以写写自己少年时的事情,当然也包括阅读经历。也许好多人都看过那些文章,《书城》的格调我很熟悉,他们有一部分人也喜欢我的文章,我们的共同经验很多。我对《我的罗陀斯》不满足的地方在于它的叙事比较单一,事实上那里边的事情是有延展性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所以,我想写一个更混沌的东西。
写作过程中许多事情非常复杂,一个个问题都要非常具体地去解决。比如要考虑到阅读体验,有的时候一定要刹车,不能再说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我要马上改变视角,在电影当中就是镜头,比如子平说的那段有点像长镜头,中间可能要跳一跳。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一个资料问题,有时候是一个灵感。这些东西充满了我的写作过程。至于读者那里根本不去考虑,潜意识当中读者只是我的朋友,写得好的话我就拿出来,写得不好就不拿出来。这是我给我自己写的,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写成以后我才发现,读者生成了,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批评?那都是你们的事情。以前我对别人的批评很苛刻,现在别人对我的批评我只能全盘接受,因为重要的不是我是否同意。
黄子平:我们读吴亮这部小说,里边很多人物是有某些共通性的—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物。要么是“吃闲饭”的社会青年,要么是从新疆那边逃回来的,还有一些“文革”开始后像我们这样年纪稍大的学生。主体是那几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毕业,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就被迫中断了学业的少年。由这些人来思考七十年代,是很重要的设计,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完全在“外面”进行。它的思想主流跟绝对权威有很大的差异,提出来的问题也许是跟形势完全格格不入,或是进入的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这反而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切都证明了那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是失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时代脱节了,出现了断裂。为了使年轻人都能够思考那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吴亮没有选取在任何方面完全顺应那个时代的人。
即便在那个时代里获得很多利益的人,也表现出某种逆取的姿态。最有意思的是孙继中的父亲,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文革”初参加工人赤卫队站错队了,后来转向一个享受生活的形象,热衷养热带鱼、养鸽子、集邮等等。他所提供的丰富的杂知识显然跟“三大革命实践”毫无关联。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劳动模范形象,尤其是在上海,在一个革命热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很明显的是,上海这些所谓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顽强地存在着,因为他们尚有欲望、追求和想象,不像别的地方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吴亮写了很多阴暗的地方,你感觉到在这样的角落里面才能看见 “朝霞”。
本刊编辑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并经对谈者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