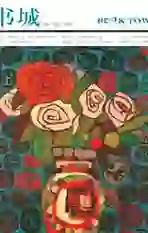司马氏与淮南三叛
2016-12-01李庆西
李庆西
曹魏后期,司马氏擅政,人心不稳,数年间发生三次兵变。嘉平三年(251),王凌谋立楚王彪,未及起事被人告发,司马懿亲率中军逼降;正元二年(255),毌丘俭矫太后诏,与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司马师,结果一战而溃;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征为司空而被褫夺兵权,遂联结东吴兴师抗拒,司马昭以二十六万大军合力剿灭。三次兵变首领均为督师淮扬的重要将领,史称“淮南三叛”。这些事件,起因与始末主要见于《三国志·魏书》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王基诸传,三少帝纪及裴注所引各史,《晋书》宣、景、文帝各纪亦有记述。
在三国叙事中,魏、蜀、吴各方内斗要算曹魏最为酷烈。蜀汉仅有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讧争,实无碍大局。东吴则先有孙峻杀诸葛恪,后有孙綝废立君主而被丁奉斩之,皆谓祸起萧墙,烛光斧影只在宫苑之内。曹魏一方情况特殊,自司马懿灭了曹爽,宗室外戚势力虽已扫除八九,一些握有重兵的将领却成了反对派。方镇哗变,各有其衷,盖因不能自安、自适。如果说早先诸镇割据之时还是“士无定主”,而魏国既建,三十年来曹氏以所谓“唯才是举”收拾人心,制度礼法已养成相应的政治伦理;但司马氏攘夺曹氏天下,不啻又重新洗牌,再度颠覆了君君臣臣的权力秩序。
“淮南三叛”这几个故事里,人物命运都很乖舛,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荒诞与悖谬:叛逆即是忠诚,而忠诚者却不能以忠诚而自适。
王凌之叛缘于废立之事。他是汉司徒王允之侄,早年跟从曹操,正始初已是统辖扬州军政的假节都督。后进为太尉,仍掌握扬州兵马,至起事之日经略淮南有十年之久。《王凌传》谓:“是时,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按,平阿属扬州淮南郡,屯兵平阿是为防御东吴)。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王凌和令狐愚密谋废除魏主齐王曹芳,拥立楚王曹彪。传曰:“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楚王彪是曹操侧室孙姬的儿子,其时正值壮年,而齐王芳年仅十七八岁。齐王为明帝养子,《魏书·三少帝纪》称“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其七岁践祚,在位多年只是个牌位,曹氏政权实际上丧失在他手里。嘉平元年九月,也就是司马懿诛曹爽半年过后,令狐愚两度派人与楚王曹彪暗中接洽。裴注引鱼豢《魏略》云:
(令狐)愚闻楚王彪有智勇。初东郡有伪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呜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于王,言“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
其中“伪言”与“谣言”亦见《晋书·五行志》。白马是地名(就是关羽斩颜良的地方,在今河南滑县),曾是曹彪的封邑。据《楚王彪传》,曹彪初封寿春侯,后多次改封,黄初七年徙封白马,太和六年又改封楚王。在曹操二十五个儿子中,除文帝曹丕、任城王曹彰、陈王曹植,最有故事的大概就是这楚王彪了。曹植有一首著名的赠答诗《赠白马王彪》,以“丈夫志四海”与曹彪共勉,对这位异母兄弟颇有期许。谣言由地名演绎白马之迹,有如龙马出河之传说,自是举事者煽惑人心的谶语。云“白马素羁西南驰”,乃谓直诣阙下登基上位,魏都洛阳和旧都许昌均在白马西南。
可是,当时曹彪封国在楚(地属淮南郡),方位完全不对。凌传称:“嘉平元年九月,(令狐)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卢弼《三国志集解》提出质疑:“彦云(按,王凌字)都督扬州,屯兵寿春,与楚王近在咫尺,何事不可协商,乃必遣将远至东郡之白马,事之离奇,无过于此。千古疑狱,留此破绽,以待后人之推求。承祚(按,陈寿字)之笔,亦谲而婉矣。”卢氏似乎怀疑这是一种伪叙事,其“亦谲而婉”,殊不可解。
令狐愚联络楚王彪未久竟因病身亡。王凌迟至一年之后才起兵,以东吴堰塞涂水(即今滁河)为由,“表求讨贼”而结集部队。不料,接替令狐愚的兖州刺史黄华出卖了他。这边刚举事,司马懿即发兵南下。史书没有记载双方部队行进的具体路线,但据凌传“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军到丘头”数语,可知王凌应该沿淮水、颍水往上游进发,而司马懿则从蒗荡渠顺流而下进入颍水。双方在颍水之滨的丘头(后改名武丘)相遇。丘头位于项城东南,即今河南沈丘与安徽界首之间。两军并未交战,王凌见这阵势,自己先怯了。据凌传描述的情形看,司马懿对付这种事情极有手腕。凌传曰:
……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
百尺,即蒗荡渠汇入颍水处的百尺堰,就在项城附近(见《水经注》卷二十二),距离丘头不过几十里。《宣帝纪》亦云:“凌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曰:‘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帝曰:‘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司马懿此际软硬兼施,又还其印绶、节钺,是要稳住王凌。凌传、宣纪所述均取自《魏略》,但二者都略去一个重要事实,即王凌自缚认罪的真正原因。裴注所引《魏略》载有王凌给司马懿的书信,其中说到“今遣掾送印绶,倾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可知王凌投降是因为有魏主诏令。王凌让人把自己反绑了去见司马懿,是不欲与朝廷对抗。
可是,王凌兴师目的是要废黜魏主齐王芳,如何又听命于这少帝的诏令?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王凌被解送京城途中,刚走到项城,便饮鸩而亡。裴注引干宝《晋纪》曰:“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按,贾逵字),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王凌以贾逵相譬况,自有故事。当年曹操死时,贾逵负责丧典,曹彰从长安来奔丧,索问魏王印绶,贾逵正色拒之:“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魏书·贾逵传》)太子就是曹丕,后来成了魏文帝。贾逵维护了曹魏祧绪的合法性,赢得忠臣名声。然而,王凌欲迎立楚王彪并没有那种合法性,这本身已属大逆不道,他想做拯救曹魏的忠臣,没那么容易。他主动投降似乎是不想把事情做绝,最后却难以证明自己的心迹,绝望中朝司马懿大喊:“卿负我!”司马懿回答很干脆:“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国家”一词,当时乃天子之谓(如,魏中书令李丰之子选尚齐长公主,《夏侯玄传》裴注引《魏略》云李丰“自以连婚国家”),司马懿将“国家”攥于手心,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才是忠臣。
王凌起事时年届八旬,死时仰天叹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裴注引《魏略》)事败,楚王彪亦被赐死。这次兵变谋划日久,部队进至项城一带,距许昌只剩二百里路,往洛阳亦略近半程,却突然土崩瓦解。司马懿兵不血刃,手段着实高明。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没有写王凌之叛,小说家竟不愿在此多费笔墨。
王凌欲废齐王芳不成,但三年后,齐王芳却让司马师给废了。《三少帝纪》以“太后令曰”列述其罪:“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按,实为司马师等表奏太后之语,见裴注引王沈《魏书》)废黜皇上用男女罪名,甚奇。
司马师搞废立,正是毌丘俭起兵根由之一。《毌丘俭传》裴注引毌丘氏等上表,列司马师罪状十一条之多,其六即是“矫废君主”。但俭传、景纪都不提这一茬,倒是《三国演义》特为强调此事。小说第一百十回:“(毌丘俭)闻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心中大怒。长子毌丘甸曰:‘父亲官居方面,司马师专权废主,国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这里说的“国家”,已非天子之谓,而是指魏国。产生于宋元以后的小说叙事已将“忠诚”表述为一种政治意志,而“国家”“社稷”一类词语则代入更广泛的集体想象。
毌丘俭是曹魏名将,起事时以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其同伙扬州刺史文钦应属曹爽一党,是曹的小同乡(小说作“曹爽门下客”)。此人亦是一员虎将,俭传称文钦“骁果粗猛”。俭、钦以寿春为根据地,很快将战场推至项城左近,这几乎复制了王凌的进军路线。从《毌丘俭传》和《晋书·景帝纪》看,司马师军事部署相当厉害,一上来就摆下三路大军: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项城西侧的南顿,与毌丘俭对峙;让诸葛诞率豫州兵马从安风津渡淮,直取寿春;又考虑到淮南将士多为北人,用青、徐诸军在谯郡断其后路。关键一战,则在项城西北的乐嘉布下陷阱,以兖州刺史邓艾所部为诱饵,吸引淮南军袭城。在小说中,此节演化成文钦父子偷袭司马师大寨,文鸯(文钦之子)杀得天昏地暗,却被赶来救援的邓艾搞了个反包围。按俭传、景纪,是驻扎汝阳的司马师突然杀到乐嘉。文钦力战不敌,结果落败而逃,投了东吴。毌丘俭见大势已去,只得逃往淮南,在慎县被人射杀。
说来,对于毌丘俭、王凌这类人物,史家最难定论。《三国志》不设“叛臣”“逆臣”之目,列传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邓艾、钟会五人置于一处(卷二十八),显然视为窝里反一族(邓艾属“疑似”而冤枉)。但看卷末“评曰”,先褒后抑,言语耐人寻味,其曰:
王凌风节格尚,毌丘俭才识拔干,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塗地,岂不谬惑邪!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闇于防患,咎败旋至……
陈寿不讨论叛逆与忠诚,回避了伦理究诘,大概也是觉得这“君臣之义”本身就乱了套,往哪边说都未能允当。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心大志迂”“闇于防患”,不能说是肯綮之论,却多少也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习凿齿《汉晋春秋》持晋承汉祚之见,以曹魏为篡逆,对毌丘俭却是大加赞扬。裴注引习氏曰:“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君子谓毌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对于毌丘俭这样的叛逆者,史家多以节操看取大义。
毌丘俭起事前一年,也即废齐王芳半年之前,即嘉平六年二月,洛阳宫内还发生了一起针对司马氏的未遂政变。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密谋,伺机诛杀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代之为辅政。《魏书·夏侯玄传》称,起先李丰暗使其弟兖州刺史李翼请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因未能获准,便计划在宫内典仪中动手。司马师听到风声,先下手干掉李丰,又逮捕夏侯玄、张缉等,皆夷三族。此事亦见《晋书·景帝纪》。
毌丘俭因为“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见俭传),自有物伤其类之痛感。这也是毌丘俭表奏司马师罪状之一。李丰等举事未与毌丘俭结援,或是其谋划不周。其实,后来兴兵反叛的诸葛诞亦未尝不可倚恃。诸葛诞与夏侯玄有着更铁的朋党关系,又曾是患难之交(明帝反“浮华”,一同被罢官)。夏侯玄是夏侯渊族孙,也算魏宗室,又为士林领袖,早晚要被推上风口浪尖。《魏氏春秋》有一细节,足见夏侯玄之人气爆棚:司空赵俨死时,司马氏兄弟为举办丧宴—“宾客以数百,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司马师)由是恶之。”(见本传裴注)以夏侯玄之名望,结援方镇最有号召力,可是他并未出头。也许正是因为曹氏三世持续压制朋党交游,而司马懿诛曹爽又进一步打击大族名士,魏晋之际的反对派实难以同忾相求。如,王凌欲废黜之主,毌丘俭却拼死维护,士者与“国家”到底是怎样一种政治关系,已有不同解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国家”已不再是可以庇身的神器。一方面,他们的忠恪无以寄托;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亦无所适从。他们在迷惘中攘袂而起,只是以求自解。
平息第二次淮南之叛,诸葛诞有大功。他率部攻占寿春,抄了毌丘俭老窝,战后即都督扬州。可是仅仅两年之后,诸葛诞自己却反出江湖。此际以身家性命相搏,这是为什么?《三国志》交代得不是很清楚。本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毌丘俭、王凌等相继夷灭,使之“惧不自安”,暗地里早已厚养死士,固结人心;二是“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征为司空以释其兵权,于是“愈恐,遂反”。所谓“朝廷”,自然不是魏主(魏主已被司马师换成高贵乡公曹髦),而是大将军司马昭(讨伐毌丘俭之后司马师就死了)。如果只是恐惧与猜疑,这理由听上去有些牵强。诸葛诞拥兵反叛,司马昭兴师讨伐,双方都需要一个明面上的说法。
相比之下,小说家的演绎倒是更合乎逻辑,《三国演义》写诸葛诞之叛,根子仍在于忠诚二字。第一百十一回,相府长史贾充藉慰劳部队为名,来淮南刺探诸葛诞的底牌—
诞设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诞曰:“近来洛阳诸贤,皆以主上懦弱,不堪为君。司马大将军三世辅国,功德弥天,可以禅代魏统。未审钧意若何?”诞大怒曰:“汝为贾豫州之子,世食魏禄,安敢出此乱言!”充谢曰:“某以外人之言告公耳。”诞曰:“朝廷有难,吾当以死报之。”充默然。
诸葛诞出语凛然而掷地有声。誓言以死报国,小说亦藉以表述君臣大义。贾充是贾逵的儿子,当年其父维护曹魏祧续被誉为忠臣,让他来鼓吹由司马氏禅代魏统,直是妙义横生。以忠诚为叙事逻辑,简单而清晰,这样诸葛诞的行动就有了公孙杵臼、程婴之于赵氏孤儿那种士者之义。其实,此节本于诞传裴注所引《魏末传》,诸葛诞原话是“若洛中有难,当吾死之”(当然,这是史家的表述)。其谓“洛中”,俨然代指魏主,可是何不直言“帝”或“朝廷”?
还有一个疑问。当初毌丘俭、文钦起事,派人联络诸葛诞,希望他率豫州军民响应。诸葛诞不知怎么想,却将他俩给卖了。本传谓:“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有道是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此决绝地划清界限,那是为何?其实,之前王凌那回他也站在司马氏一边,率军进剿扬州。似乎,唯一的解释是,在诸葛诞看来,司马氏擅政柄国与禅代魏统是两码事。王凌、毌丘俭两次造反都为废立之事,而诸葛诞本来并不在意废谁立谁,司马氏如何专权也还是替曹家人看护天下。从司马懿到司马师,亦似温水煮青蛙的升温过程,可是到了司马昭这儿几乎抵达临界点—由贾充禅代之议,革除曹魏的意图已昭然可揭。
据裴注引《世语》之说,以征为司空解除诸葛诞兵权,亦是贾充的主意。贾充从淮南回来对司马昭进言:“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征,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征,事迟祸大。”此谓以征逼反,乃为上策。又,《魏末传》透露,扬州刺史乐綝觊觎诸葛诞的都督权位,打小报告诬告其暗通东吴,这也是逼反诸葛诞的一个原因。所以,诸葛诞起事前先把乐綝给杀了。《魏末传》载有诸葛诞给朝廷的表奏,如谓:
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讨綝,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
从这篇文字看,诸葛诞的忠诚是有条件的,“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这是追问与究诘。“圣朝”是否仍是他心目中的朝廷,要看朝廷怎么看待他了。诸葛诞不想一棵树上吊死。他联结东吴不假,但究竟是早已暗中交通,还是兵变之日才投靠过去,据现存史料难以定论。也许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诸葛诞的忠恪已失去具体对象—司马氏篡逆搅乱了君臣之义,诸葛诞只能以自己信守的士者之义为本位。
战事始于甘露二年五月,诸葛诞用兵思路与王凌、毌丘俭迥然相异,他没有向洛阳方向进军,而是盘踞寿春,闭城自守。又将自己儿子送往东吴为质,请求救援。东吴方面自然大喜,派全怿、全端、唐咨等率三万人马接应,前已投奔东吴的文钦也加入其中。这时魏方王基都督扬、豫诸军已包围寿春。七月,司马昭挟魏主和太后东征,征调青、徐、荆、豫诸军直下淮南。二十六万大军围城八阅月,最后城内粮尽,军心涣散,几乎是不攻而克。卢弼集解引何焯曰:“俭、钦犹出至项,诞闭城自守,专倚吴救,弥为下矣。”将胜算都押在东吴一边,实在是失策。其实东吴人马在外围根本打不进去,而先前突入城内的文钦、全怿等人还尽给诸葛诞添堵。结果全怿被钟会用计策反,率部出城投降,文钦则与诸葛诞讧争而被杀。破城之日,诸葛诞率麾下数百人企图突围,在城门口被司马昭手下胡奋斩杀。
在《三国演义》中,寿春守城战事见诸第一百十二回,与史书所述出入不大。总的说,小说描述的毌丘俭、诸葛诞两次兵变未能给读者留下太深印象,因为这些故事处于小说叙事焦点之外。但就历史而言,淮南三叛都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而且涉及深层次的政治伦理问题。这三次兵变,数诸葛诞这回历时最长,论其规模、影响亦最大。从王凌、毌丘俭到诸葛诞,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诸葛诞干脆联手东吴,慨然打破君君臣臣的伦理禁忌,其实不是因为他缺乏忠诚,而是忠诚的目标已经失焦。
司马昭挟魏主和太后两宫出征,此举非同寻常。天子躬征不足为奇,司马昭上表亦用汉高祖、光武帝亲征黥布、隗嚣的故事(见《晋书·文帝纪》),可是为何要将太后拽上战场?《通鉴》胡三省注谓:“(司马)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此说甚确。司马昭当然不能只带魏主上路,太后留在宫里难保不被别人当枪使,当初毌丘俭矫太后诏起事即前车之鉴。
太后不啻是一张王牌。正始十年(改元嘉平元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就是以太后“令敕”名义表奏天子罢黜曹爽。这位太后原是明帝郭皇后,从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到陈留王曹奂,三任少主期间做了二十四年太后。《魏书·后妃传》谓:“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司马氏父子诛曹爽搞废立诸令,无不假太后之名,这是司马氏的家数。后来,魏主曹髦贸然自讨司马昭,死后还被这郭太后下诏废为庶人。
不过,搬出太后自有另一层意思。这种以母仪统政的节目,实质乃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挟天子,司马氏挟太后,意在君臣大义之外确立一种政治伦理的合法性,也即以仁孝廉让为准则的家国体制。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鲁迅有一个很浅白的解释:“(魏晋)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就是说,既然已是君不君、臣不臣,其统辖人心的核心价值观只能侧取孝道。亦如钱穆所说,“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个‘孝字,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国史大纲》第十二章)。
从曹操篡汉到司马氏篡魏,或以为后者只是复制前者而已,其实不然。说来前后局面大不相同。曹操挟天子之日,汉室早已衰微,董承、王子服之后朝中没有几人敢质疑曹氏的合法性,反对者只是杨彪、孔融一类文士。而司马氏柄国之时,曹魏国势方隆,跟他父子作对的不但有宗室、外戚、士族人物,更有督师方镇的军界大佬。所以,司马氏之篡弑是一个更加血腥的过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有“魏晋禅代不同”一则,分析很透辟。
二○一六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