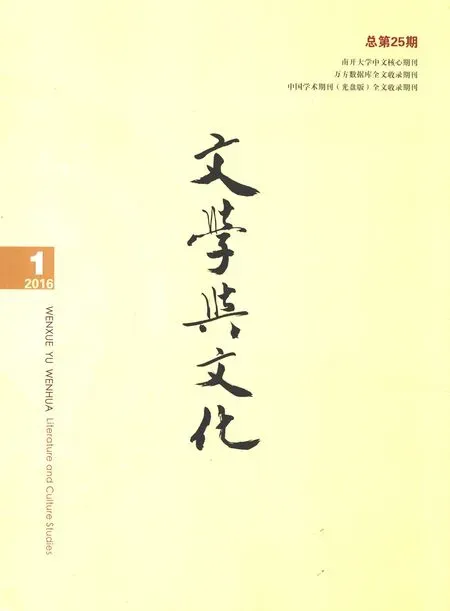从词的起源看丝路上的文化交流
2016-11-25叶嘉莹
叶嘉莹
从词的起源看丝路上的文化交流
叶嘉莹
其实,无论是从历史的知识还是从地理的知识来说,我都不是一个正式研究丝路文化的人。湛如法师请我来做这个讲演,他本来预定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诗情与画意”,大概是他看到过我的诗集里有几首关于赴丝路旅游的诗,所以要我讲诗中的诗情画意。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题目——“从词的起源看丝路上的文化交流”。
我是一个从小就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人,是一个古典诗词的爱好者。我是从内心喜欢诗词。我喜欢读诗词,我也喜欢把我所感受到的那一份诗词中的美好传递给年轻人,这就是我一生一世所从事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丝路上的文化交流真是太重要了,因为它使我们中国的韵文当中产生了词这种体式,这对我们中国的韵文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词这种体式,我们就不会有当年的李后主、韦庄、冯延巳,也不会有后来的辛弃疾、李清照。
在正式演讲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几张我当年在丝路上旅游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看这一张是我骑着骆驼的照片,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现在行动都要人搀扶的老太婆,当年也还有过骑着骆驼踏在沙漠之上的“英姿”。那是1996年,我们在新疆开了一个会议,我当时72岁,现在我差不多是92岁,20年了,流年似水,我现在再也没有骑到骆驼背上走上沙漠的勇气了。大家看底下这一张,这是当年高昌古城的遗迹,高昌古城就在吐鲁番市东45公里的地方。后面还有一张照片,刚才我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看这个高昌古城的遗迹,现在这张是我亲自走到了这个颓塌圮坏的高昌古城的遗迹的脚下了。还有一张是我经过“玉门关”的图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古人认为“玉门关”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而我现在是来到了“玉门关”。这里其实还不是玉门城关的遗址,而是当年它的烽火台的遗址。原来“玉门关”之所以叫“玉门”,是因为我们中国从周朝、汉朝一直都是喜欢玉器的。“玉”,在我们中国是代表一种文化,代表人的修养、人的品行,所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而我们中国当时产玉并不多,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很多美玉,要从这里经过,所以把它叫做“玉门关”,是要把这个玉从丝绸之路运到中国来。下面还有一张伯孜克里克的图片,伯孜克里克是吐鲁番市附近一个山上的石窟,也叫做“千佛洞”,里面有很多非常精美的佛像,都是当年在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以上是我介绍我当年确实是曾经到过丝路。
接下来我就要讲中国的词曲与这个丝路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几首我论词之起源的诗。我曾经写过一系列的论词绝句。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缪钺先生说希望跟我合作写一本关于词之发展史的著作。他的理想是都用论词绝句的形式来写。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论诗绝句和论词绝句,即如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三十首》,辞句都很美丽,但是太简略了,没有理论的说明,人们看不懂。所以我当时就跟缪先生商议,我说我们能不能把古今中西结合在一起,在每个论词绝句后面附上一篇论文,说明我们这个绝句所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理论,对词有什么样的体会。缪先生同意了,于是我们写了一系列的“论词绝句”共86首,其中缪先生所写者37首,我所写者49首。本来我们曾经把这些“论词绝句”分别出版过,最近缪钺先生的孙男缪元朗根据缪钺先生的本意,把缪先生跟我的“论词绝句”合起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灵谿词说正续编》。在这一系列的“论词绝句”中,开端的《论词之起源绝句三首》是我写的:
其一
风诗雅乐久沉冥,六代歌谣亦寝声。
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
其二
曾题名字号诗馀,叠唱声辞体自殊。
谁谱新歌长短句,南朝乐府肇胎初。
其三
唐人留写在敦煌,想像当年做道场。
怪底佛经杂艳曲,溯源应许到齐梁。
我们说,“诗”与“词”是不同的。无论是最早的四言诗,还是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甚至是骚体、楚歌这样的体式,在最初被创作的时候,都是徒歌。《诗经》——“诗三百”,也可以弦歌,甚至可以配合音乐来舞蹈,可是那都是后来的事。因为它们是先有了“诗”,然后才配上乐的,这与“词”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写诗,是以我们语言的节拍为主。而我们中国的语言,跟世界所有的——不管是西方还是其他东方各国族的语言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我们是单音独体的方块字的语言,他们是字母组合的拼音语言,我们说“花”,一个汉字一个音节,英文说“flowers”,多个字母多个音节。我们念一个字“东”,没有一个rhythm,没有一个节奏,念两个字“东方”,也还是没有节奏,所以要四个字二二才开始有节奏。而古人说“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你心里有所感发,就作了一首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你把你心里面的情志用语言说出来了,这就是诗,所以诗都是语言的节奏。我们所有的原始的古诗,不配合音乐的那个最初的诗的节奏,无论是二二、二二一,还是二二二一,都是语言的节奏。
可是有了“词”这种体式,就非常奇妙了,因为它不是以语言为节奏的,而是以音乐为节奏的。它为什么以音乐为节奏?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管它叫做“词”的原因。我们说“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古人说:“诗者,(是)志之所之也。”“之”是往,就是你心动了,是你的心往那里去了。我在加拿大给小朋友讲诗,我说你的心会走路吗,他说不会走路。我说你老家在哪里,他说我老家在河南。我说你来到加拿大,你想到你老家的亲戚了吗。他说我想我姥姥姥爷,我说你这一想,你的心就走路了,走到河南去了。佛家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仁者心动”。你为什么有诗,是因为你的心动了。你把你的心动用语言写出来了,这就是诗!那么“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最早的“词”这个字,意思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歌词。歌是音乐,我们给音乐配上的文字就是歌词,用英文说就是song words。所以“词”,就是配合音乐的歌词。
配合什么音乐的歌词?我们说《诗三百》也都可以配合音乐来歌唱,是先有文字再配合上音乐的。可是“词”,是先有了乐曲,你按照乐曲的节拍然后填写上的歌词。为什么如此?就因为从汉唐以后,从西域传过来很多美妙的音乐。所以我的第一首绝句就写的是:
风诗雅乐久沉冥,六代歌谣亦寝声。
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
什么叫“风诗”“雅乐”?我们中国古人把音乐分为雅乐、清乐、燕乐还有法曲。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我们先说“雅乐”。王国维曾经研究过殷墟甲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殷周制度论》,考察商周之间的制度。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考古,但是王国维先生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在这种看似科学的、死板的考古文章之中,寄托了他的理想。他为什么要写《殷周制度论》?他不是单纯地在考古。你要知道王国维是生在晚清跟民国交替的时代,他自沉昆明湖的时候,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本来周武王当时推翻了殷商,是一个革命;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也是一个革命。王国维的意思是,革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只是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那就世界大乱了,就像现在的中东,不是随便讲一个民主、推翻一个政权就是革命了,一个革命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是在于它革命以后有没有建立一个完备的美好的制度。所以王国维这篇文章就叫《殷周制度论》,是说周朝之所以能传世久远,就因为周公制礼作乐,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根基,这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中国本来是把古人的这个礼乐称作“雅乐”。但是后来到了秦朝以后,周朝的这个古老的雅乐,就逐渐地丧失了。在全世界的古文字之中,我们中国保留下来的最多,从殷墟的甲骨、先秦的大篆、秦代的小篆到后来的各种书体,我们不但能够认识而且能够书写。而世界上其他古文化——古埃及的文化、古巴比伦的文化、古印度的文化,都灭绝了,我们中国的古文化,不但没有灭绝,我们现在还能读、还能读得懂。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不但能够读得懂它,我们现在也仍然可以写作“诗经体”的四言诗。中国文化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它历经几千年却没有像其他文化一样灭亡,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甚至仍然可以写作出来跟古代一样美好的诗文。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之所以宝贵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最可惜的一点,是文字传下来的时候,音乐丧失了。当然音乐的丧失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当时没有录音,也没有很完整的乐谱,所以从秦以后,“雅乐”就逐渐地丧失了。
六朝的新乐我们就叫做“清乐”。其实,这个外族的音乐不是一直到唐宋之间敦煌写的曲子才传进来的。我们讲中国的诗歌的历史,就会发现汉朝时就记载说,当时很多古乐都亡佚了,人们不能够整理出来很完整、很美好的古乐,所以汉武帝设立了乐府,让李延年做协律都尉,而李延年的特色就是善“为新变声”。什么叫做“新变声”?汉武帝在设立乐府的同时,也派遣张骞出使到西域,当时的张骞就曾经带回来一些胡乐,而李延年就曾把这些传进来的新的乐曲谱在其中了,所以,这个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由来已久,从张骞通西域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从秦以后,雅乐就不存了。汉武帝时,李延年“为新变声”,于是就有了崭新的、跟古代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而且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就有各种的新乐曲兴盛起来了,你看一看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记载,有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多少的新曲子,那就是所谓的“清乐”,就是历代的“新声”。
到了唐朝天宝十三载,玄宗“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法曲”就是宗教的乐曲,宗教的诵经、唱诵一直是有音乐的。我曾经到美国加州的法界大学讲杜甫诗,也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法事的聚会,他们每天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在大殿之中开始唱诵《华严经》。我,算是客人,也很早就起床,我觉得他们这个敲钟、击磬的唱诵的声音非常美,所以我也加入他们一起唱诵。而《华严经》打开的第一篇,有一页都是拼音,那是因为佛经里面,有的我们是把它的文字的意思翻译了,但是还有很多是唱诵的偈赞,都是拼音,所以要学习唱诵的声音,这种伴随着佛经唱诵的曲子就是法曲。当然,佛教也是经丝路传进来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丝路的文化交流。因为唐玄宗是一个懂得音乐、爱好音乐的人,所以他就下了一个诏令,使“法曲”(宗教的乐曲)与“胡部”(丝路文化传进来的外族的乐曲)“合奏”,把很多新的资料都加进去了,而这在一般人看来虽然是“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但是“宴乐”亦自此盛行,所以,从周朝的“雅乐”到六朝的“清乐”,加上“法曲”,加上胡部传来的音乐就是“宴乐”。这是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词”,就是配合宴乐而歌唱的曲子,按照音乐的谱子填写上的歌词,所以我们说“填词”不说“作词”,是fit in,是你要按照乐曲填上歌词,也因此我们又把“词”叫做“长短句”,因为要配合音乐的节奏,所以歌词是不整齐的。我们说过,诗是“二三”或者“二二三”的节奏,是根据人体的生理之自然,我们说话声音大多是两个字两个字一停顿比较方便,可是你配合音乐,就不一定是两个字两个字这么整齐了。而按照乐谱填写的歌词,之所以流行得如此之广,就是因为它所配合的那个音乐真是美妙,根据中国音乐史的记载,自从这么美好的新兴的音乐传进来以后,那个高低抑扬、那个变化无端,不知道比中国古老的雅乐、清乐更有多少动人之处。所以那个时候,不但是一般人要学习按谱来填词,而且在佛教里面法曲唱诵的时候,有时候佛家年轻的弟子们一边抄这些佛经,一边也就把一些流行的曲调抄写进去了。
这个不是我空口在说,接下来我要举出例证来。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哈佛大学图书馆买进来一本非常厚重的大书,这本书就叫做《敦煌曲》。什么人编的这本书?就是饶宗颐先生。一切事情莫不有一个机缘。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记述来,是因为我看到了饶宗颐先生编的这本书。饶宗颐先生为什么能编出这本书?因为饶宗颐先生在1967年到1968年之间曾经受聘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差不多有将近一年之久。而英国、法国距离很近,英法海峡来往方便。所以饶宗颐先生就在他访问期间,走遍了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什么研究中国的文化要去外国的博物馆?就是因为我们晚清的时候国家真是积弱,一切都没有法度,一切都没有人管理。那个时候敦煌的洞窟有一处倒塌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没有人闻问,没有人管理,西方的考古学家、汉学家斯坦因与伯希和到中国来,他们发现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于是向看管这些资料的王道士用很便宜的价格买走了我们几千几万卷的敦煌残卷。这真是我们国家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而饶宗颐先生是有心人,并且他真是喜欢研究,学识非常广博,他也很幸运地有这样的机会来做成这件事。其实,有这个机会,你有没有这种能力,你有没有这种心意,你有没有缘来做成这件事,也是不一定的。而且你有没有缘还不在于你碰不碰得到,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储备的知识以及情意和理想来完成它。饶宗颐先生就利用这段时间,把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面斯坦因与伯希和两个人从中国取得的所有敦煌残卷都加以整理,编成了非常厚重的一本书,书名就是《敦煌曲》。
我也是因为对于词曲真的很有兴趣很有感情,才把饶先生这么厚重的一本书翻完了,把里面一些重要的材料记了下来。可是一般人没有兴趣,一般人不看。我前几天为了准备这个讲演,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我在里面看到的敦煌的旧曲子,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回到哈佛去,我就找我从前在哈佛的一个学生帮我找一些材料。我的学生都已经退休了,她说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不到这本《敦煌曲》,因为这本书太大,占了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人看,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这本书拿走了,放在外边的一个储藏室里面去了。我的学生费了很多手续把这本大书找出来了,并且也找到了其中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中,有一篇是《鹊踏枝》的曲子,这是在饶宗颐的书里边把敦煌的残卷影印下来的。我们来看一看敦煌残卷里的《鹊踏枝》是怎么样的:
独坐更深人寂寂,忆念家乡,路远隔关山。
寒雁飞来无息消,交儿牵断心肠忆。
……
这些文字都不大通。其中“息消”应该是“消息”,“交儿”应该是“娇儿”。为什么不大通呢?因为这些在丝路上来往做买卖的商人,并不是诗人,并不是文人雅士,他们是按照丝路流行的曲调比较通俗地写自己的感情。所以,对于敦煌的曲子,大家没有兴趣去读,因为那些写作的人文化不是很高,他常常写有错字、有别字,有文法不通的地方。但是虽然如此,《鹊踏枝》这个传进来的胡曲、这个外来的音乐却因此传下来了。我是个爱好诗词的人,所以我愿意讲这个题目,我觉得通过丝路上的文化交流能够传进来新的音乐,让我们知道为配合新的音乐而填写的新的歌词,那些照着胡乐的乐谱所填写的歌词,那些东西真是美妙。因此,如果我们当年没有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没有丝路上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把那些按音乐填写的曲子传进来,我们以后就不会有辛弃疾,不会有李清照,不会有南唐的中主、后主和冯延巳。有的人是词写得好,有的人是诗写得好,虽然辛稼轩既写诗也写词,但是他的诗没有词写得好。苏东坡是天才,不管是古文还是诗词都写得好,但是即使诗词都写得好的人,也是诗是一种风格,词是又一种风格。如果没有从丝路上传进来的这种胡曲的音乐,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美妙的歌词。
我现在要利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一首后来文人所写出来的《鹊踏枝》的歌词。我们刚才看见的是《敦煌曲》里面的歌词,不管它有多少缺点,但是这个音乐传进来了,这个歌词的调子传进来了,有了这个调子我们就有了文人写出来的非常美好的歌词。我们现在就来看冯延巳所写的一首《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关于冯正中的词,清朝很多人对之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有个叫冯煦的,自命为冯正中的本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只看饶宗颐先生对他的赞美。饶宗颐先生在《〈人间词话〉平议》中写道:“予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正中”是冯延巳的字,关于冯氏的名字有些争论,有人以为是“延己”,有人以为是“延巳”。我们中国很奇妙,用天干地支配合出来各种的年月日时并用作医学、占卜的依据,“巳”字下面即是“午”,“正中”即是午时,是正当中,所以冯氏的名字应该是延巳。我们说天之生才不易,天之生才,给你一个美好的机遇,你能碰到这个机遇,你能够掌握这个机遇,这是不容易的。伯希和与斯坦因掠夺了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敦煌的卷子到英国和法国,如果不是饶宗颐先生把它们整理出来,我就没有机会来述说来谈论我们后来的歌词这种文体的兴起与丝路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所以,做成一件事,不但在于你的一个机会,而且在于你的见识。一个人要有理想,愿意为你所研究的对象付出代价,愿意为你所研究的对象尽上一份心力。对于冯正中的词,你看就看过去了,可是饶宗颐看了,他说,我觉得冯正中的词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扑面而来,笼罩宇宙——那不是可以用只字片语来解释的,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一个字一个字雕章琢句的小巧的精美的文字,而是一大片铺天盖地而来的感情和气势——“《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当然冯延巳的词有很多,他写的这个《鹊踏枝》的调子就有好几首,他说这几首尤其沉郁顿挫,非常沉重非常深婉。为什么有这种顿挫?一念就知道了!这个词的节奏跟诗是不一样的,不是五个字七个字整整齐齐的样子。所以我说,丝路文化的交流把这个外族的歌曲传进来,跟宗教的法曲结合,产生这么美妙的音乐,后来影响了我们中国的作者、这么伟大的词人,被他填写出这么美妙的歌词。
而“词”跟“诗”有什么不同?我可以举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例来做一个说明,其诗曰: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是王之涣出使到塞外的凉州,怀念故乡时所作。玉门关外,那是一个很荒凉的沙滩,那是离你的故乡很远的地方,王维也有一句诗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小时候在家里读书,我伯父很喜欢我,常常跟我聊天,告诉我很多故事。有一天他告诉我,纪晓岚(也有人说是明朝解缙)有一次给人写王之涣的《凉州词》时,不小心把“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漏掉了。旁人提醒他,说先生你丢掉了一个字。纪晓岚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他说我没有丢字,你们误会了,我写的不是一首诗而是一首词,于是他就念了:“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你发现节奏一改变,情调就改变了。词之所以美妙,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参差错落、长短不齐的顿挫节奏,所以它能够表现我们内心之中最幽微隐曲、最难以言说的一份感情,而正是因为从西域传过来了胡曲的调子,才有了这种美妙的节奏。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冯正中的这首《鹊踏枝》的词,《鹊踏枝》的牌调又叫《蝶恋花》,这是词牌不是题目。大多数诗都有题目,可是词一般只有词牌没有题目,因为词是song words,是配合音乐的调子填写的歌词,所以他不写题目,就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样,可以给大家很丰富的想象。“谁道闲情抛掷久”,这个词的顿挫变化的节奏之所以妙,就在于这一句话之中,有多个遣词的转折。先说这个“闲情”,曹丕曹子桓写过一首《善哉行》,说是“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内心多愁善感的人,像林黛玉,你不知道她为什么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发愁了。你不知道你的愁从何而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你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悲愁,所以这是“闲愁”,这是“闲情”。他说,我要把这“闲情”抛掷。他没有说是什么情,只说是闲情,你无缘无故的那种心里的感受。他说,这没有什么道理,我不要每天这么多愁善感,所以我要把它抛掷。而且,我也曾经努力了很久,我以为我已经把它“抛掷久”。可是“谁道”两个字一打就打回来了,谁说我把这个“闲情”抛掷了很久?为什么我知道我没有抛掷掉呢?因为“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每次春天到来,我那种忧伤,我那种惆怅,我那种闲情,就仍然如故地回来了。你看他这一句话有多少转折。他是怎么样用语言表现的?春天,百花盛开,你可以游春赏花,所以他说,我努力要把这闲情抛掷,这是第一层意思;而我曾经努力了很久,我以为我已经把它“抛掷久”,这是又一层意思;可是,你看他的开头两个字“谁道”,是谁说我“抛掷久”?这是又一层的意思。“日日花前常病酒”,我每次看到花开,我就饮酒,饮到沉醉,饮到为它病酒,就是喝酒喝到不舒服的程度。“病酒”,喝酒已经喝得生病了,当然是不好。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一点不好,我自己也知道喝酒喝多了是伤害身体的,我对着镜子,我看到了我的“朱颜瘦”,但是我“不辞”,我不推辞,我不逃避,我宁愿为它消瘦,就算我在镜子里面反省自己,看见我的“朱颜瘦”,但是“我不辞镜里朱颜瘦”。所以就是这么短短的几个字、几句话,他的用情的那种缠绵往复那种固执那种坚持,都在语言之中表现出来了。而这种表现,被饶宗颐先生看到,饶宗颐先生说:“予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冯正中是写对花饮酒、“病酒”,而且是“不辞”病酒,看到“镜里朱颜瘦”,仍然要为它病酒。李后主有一首词,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为什么要饮酒?因为这花落了。什么时候再开?明年?今天落的花,明年就再不会飞回到枝头上去了,所以王国维说:“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杜甫也曾经说过:“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因为我不忍心看到花落,因为这个花今天落下来了,它永远不会再回到枝头上了,所以我“不辞镜里朱颜瘦”。
饶宗颐先生还有一句话:“语中无非寄托遥深,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为什么?为什么你冯正中有这样沉郁悲哀不能自解之情?你有一种感情,你可以解脱,你可以超越,你可以把你这样的感情放下。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感情你不能超越、不能放下?你努力地“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仍旧”,你宁愿“日日花前常病酒”,还“不辞镜里(的)朱颜瘦”。冯正中为什么写出这样的词来?饶宗颐先生看出来了,“语中无非寄托遥深,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冯正中有什么寄托?他是写伤春,他是写花落,他是写春归。可是,饶宗颐先生为什么看到一种“寄托”,而且说“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这是非常有见解的话。所以我说老师给学生讲诗,不能够只单纯地把诗念一念,把生字查一查。你要把诗人的身份、诗人的背景、诗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弄清楚,你才能够真的懂得他。冯公是什么身份?有一句话,我常常是非常不愿意说,但事实却是如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上天用各种的苦难成就了一个词人。“词”,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它写起来比“诗”更深入、更婉曲、更隐约、更含蓄,是你有不能够言说的、不能够直接说出来的感情,而只适合于用词来表达。天下从古到今,有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是悲剧的命运?命运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说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是悲剧的命运。那是谁?那就是冯正中。冯正中为什么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因为冯正中是冯令頵的儿子。冯令頵是谁?冯令頵是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开国元勋,所以冯正中的父亲冯令頵跟南唐的先主李昪是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好的朋友。冯正中小的时候就跟李昪的儿子后来的南唐中主李璟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填词。有一句有名的话:“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就是南唐中主李璟问冯正中的,两人喜欢谈论词。所以冯正中与南唐中主从小就在一起游戏,从小就在一起填词,等到先主李昪去世,李璟做了中主,冯延巳就做到了宰相。可是这个宰相不容易做,因为他做的是南唐国的宰相,而当时的南唐正处于五代十国的时候,其他小国都陆续灭亡了,所以他的国家处于危亡的、无可奈何的境地,后来到了李后主就臣服了赵宋,做了亡国之君。而冯正中真是不幸,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和一个即将亡国的国家的君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国势,进不可以攻,退不可以守,而在朝廷之中,作为一个宰相,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他,而且当时有很多党争,所以他无以言说,所以饶宗颐说:“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独立小桥’二句,岂当群飞刺天之时而能自保其贞固,其初罢相后之作乎?”“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河边的青草,每年都会发芽,白居易也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堤上的柳树年年发芽,年年长叶,我的愁就跟那“河畔青芜堤上柳”一样,“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而我的愁无可诉说,“独立小桥风满袖”,我一个人站在小桥上,桥不是家,桥不是房子,桥是过路的所在,你为什么站在桥上,而且你在桥上四无遮避,四面的寒风都灌入你的衣袖之中,“独立小桥风满袖”。而且人家都回家了,“平林新月人归后”,路边桥上所有的人都回家了,我一个人还站在这里,远远地看着月亮从一排排树林中慢慢升起,所有的人都回家去了,我为什么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桥上,任凭四面的寒风吹袭。这是冯正中,因为他身负国家的重任,而南唐又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他无可言说、无可告诉,只能接受满朝的指责。
如果没有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敦煌曲》中的《鹊踏枝》那些语言不通的词,冯正中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词来?所以我说,因为丝路上的文化交流,传进来的“法曲”跟“胡乐”合奏产生了这样一种新的乐调,因为要配合这种乐调,于是产生了这种跟二三节奏的诗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词的体式。因此,我作为一个诗词的爱好者,觉得丝路文化的交流是一件非常重要可贵的事情。如果没有丝路文化的交流,哪里有我们今天文学史上韵文史中这么美好的词的体式呢?谢谢大家。
后记:本文是根据2015年10月10日叶先生在横山书院“2015文化中国秋季讲坛”上的讲演整理而成,欲知叶先生详细之论述,请参看《灵谿词说》中叶先生所写的《论词的起源》一篇文稿。
按,本文由刘靓整理,经作者审订。
(叶嘉莹,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化研究:新媒介政治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两篇由作者授权、中文首发的新媒介与技术政治专题的论文。新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决策的各个方面。一个由技术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中国是否会在世界技术主义的潮流中发生重大的变革?诸多问题,以期后论。(周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