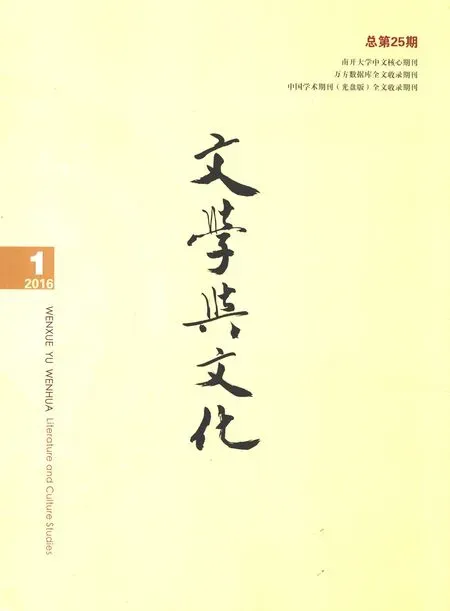“酸馅”与“酸馅气”考释
2016-11-25冯珊珊陶慕宁
冯珊珊陶慕宁
“酸馅”与“酸馅气”考释
冯珊珊陶慕宁
宋元笔记、话本、戏曲中常见的“酸馅”一词,指一种产生于北宋的面食。它在“人日”用作节令食品,称为“面茧”;明代又用作“佛诞日”的供品。“酸馅”以酸菜为馅,因此得名。形似馅馒头,而面皮较厚、褶儿较粗。荤素皆宜,由于寺院常用作斋供,元代以后多为素馅。宋代夜市还有烤制的焦酸馅售卖。所谓“酸馅气”,原指酸馅制作中发酵气体受热产生的胀气,苏轼最早用于诗歌批评,借以形容僧人缺乏新意、格调酸腐的诗风。明清时期,这个概念被扩展到书画艺术评论、人物气质评价等领域,适用者也不再限于僧人。
酸馅 酸馅气 文学批评范畴 艺术评论 苏轼
苏轼的诗作《赠诗僧道通》,在“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一句下面有则自注:“谓无酸馅气也。”①[宋]苏轼:《赠诗僧道通》,《苏轼全集》卷上,傅成,穆俦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0页。这里提到的“酸馅气”,此前从未出现在诗歌批评中,现代读者也很难理解。朱自清先生《论书生的酸气》把“酸馅气”解释成“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②朱自清:《论书生的酸气》,《朱自清全集》卷三,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换言之,在朱自清看来,“酸馅”就是“酸了的菜馒头的馅”。这种认识其实是个误解。
宋元以来笔记、小说、戏曲中数见“酸馅”一词。如宋郭彖《睽车志》卷四讲到,常州华严寺僧道良转世为牛,长老道素令寺僧“日以僧食啖之,酸豏至顿食五十枚”③[宋]郭彖:《睽车志》卷四,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05页。。《喻世明言·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说:“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揣在怀里……”④[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三十六,许政扬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23页。“宋四公怀中取出酸馅,着些个不按君臣作怪的药,入在里面,觑得近了,撇向狗子身边去。狗子闻得又香又软,做两口吃了,先摆番两个狗子。”⑤[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三十六,第525页。无名氏《度黄龙》杂剧末折【沽美酒】亦云:“道理分明心印传,枉了那蒲团上数年吃酸馅,枉劳倦。”⑥无名氏《度黄龙》,见《孤本元明杂剧》(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13页。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显然,“酸馅”是一种以“枚”、“只”等为计量单位的有馅的食品,而非变质的馒头馅。
“酸馅”的形、味究竟如何?是何种食材制成,又当怎样烹饪?上述文学作品皆未作说明。许政扬先生注酸馅为“菜馒头”⑦[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三十六,第523页。,《戏曲词语汇释》《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则释为“菜包子”⑧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岳国钧主编:《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19页。。二者意义相近,但现代的馒头、包子种类繁多、形状不一,要据以揣想古代酸馅的准确样貌,仍很困难。更重要的是,“酸馅”之“酸”由何而来,尚无方家予以落实。
北宋以来,“酸馅”一词常为诗学批评借用,“酸馅气”是相当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因此很有厘清的必要。兹考述如下。
一 何为酸馅
酸馅出现在北宋。宋代以前,文献中未见“酸馅”一词——该结论得到“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数典”等电子检索工具支持。究其原因,首先是制作酸馅的原材料要到宋朝才普及。其次,酸馅是蒸制食品,蒸在北宋取代烘烤,成为面食烹饪的主流。宋代史料里,有关酸馅的记载频频出现。它不仅是中原人民喜闻乐见的主食,也是颇有风味的夜市小吃,并且在节庆风俗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酸馅的名称
现存宋代文本中,有酸 、酸馅、酸饀、酸豏等数种不同写法。
从欧阳修的记载可以知道,“酸 ”是这种食品通行的正确写法,俗写为“餕馅”,又误读为“餕饀(俊叨)”。清代郝懿行《证俗文》的考证说明,“”等于“馅”,“酸”就是“酸馅”:“肉裹谓之。《释名》:‘,衔也。衔炙细密肉,和以姜、椒、盐、豉,已,乃以肉衔裹其表而炙之也。’案:音陷,或作馅。《字汇》:‘凡米面食物,坎其中,实以杂味曰馅,或作 。’”③[清]郝懿行:《证俗文》,《郝懿行集》(三),安作璋主编,齐鲁书社,2010年,第2591页。
一种事物出现之初,约定俗成的标准写法还未深入人心,所以可能有多个同音字同表其意。通行本《归田录》中用“”字,从“食”;另一种常见的写法,则是写作“酸豏”,从“豆”。
前文已引宋郭彖《睽车志》卷四,常州华严寺之牛每顿食用“酸豏”至五十枚。④[宋]郭彖:《睽车志》卷四,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05页。黄庭坚《山谷别集》卷七《智海禅院大殿功德疏》有“不可酸豏里咬不著”⑤[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郑永晓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6页。之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条则记载当时夜市有“酸豏”出售。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伊永文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313页。豏,《类篇》谓之“饼中豆”,即豆馅。之所以写作“酸豏”,盖因这种食品往往是掺杂豆馅的。详于下文。
(二)酸馅之酸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荤素从食店”条云:“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且如蒸作面行卖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卖米薄皮春茧、生馅馒头……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细馅儿夹儿、笋肉夹……甘露饼、肉油饼……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肉酸馅、千层儿、炊饼、鹅弹。更有专卖素点心从食店,如丰糖糕、乳糕……麸笋丝、假肉馒头、笋丝馒头……七宝酸馅、姜糖辣馅、糖馅馒头、活糖沙馅……包子……”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149页。文中提到了“肉酸馅”、“七宝酸馅”两种食物。显然,在南宋时期,酸馅是有荤有素的。素酸馅中还有杂馅,如七宝酸馅。
《梦粱录》在此列举了很多蒸制的面食。比较晚出的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条也列有“子母茧、春茧、大包子……大学馒头、羊肉馒头、细饀、糖饀、豆沙饀、蜜辣饀、生饀、饭饀、酸饀(饀即馅)……”②[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等名目。总结两种记载,可以找到宋代的面食中由面皮包裹馅心制成的四大品类:“茧”、“馒头”、“包儿(包子)”、“馅”。宋朝人之所以作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方法存在一定区别。今人将“酸馅”解释为“菜馒头”或“菜包子”,都忽略了当时人眼中“馅”和“馒头”、“包子”明确的区别,所以略欠允当。
“酸馅”类是“馅”类面食中的一种,今日北方方言中,该词语仍保留了一定遗存,比如一种介于包子、蒸饺之间的食品在河北等地被称为“大馅”。酸馅和糖馅、豆沙馅、蜜辣馅……之间的差别,只在其中包裹的馅心。恰如今日的包子,以豆沙为馅便称作“豆沙包”,以糖为馅便称作“糖包”,以肉为馅便称作“肉包”。“酸馅”面皮中包裹的,是某种“酸”。当酸馅的馅中含有肉时,便称为“肉酸馅”;含有七种不同食材时,便称为“七宝酸馅”。
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是“酸馅”之“酸”究竟何指?
元代成书的《农桑辑要》卷五“蓝菜”条引《务本新书》云:“(蓝菜)二月畦种,苗高,剥叶食之。剥而复生,刀割则不长。加火煮之,以水淘浸,或炒爁,或拌食,或包酸馅,或卷饼。”③[元]司农司编:《农桑辑要校注》卷五,西北农学院古农研究室整理,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170~171页。其中谈到,酸馅是用“以水淘浸”过的蓝菜叶包成。
这“以水淘浸”过的菜叶也叫做黄虀。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记载,赓集“食素”部“菜饀”条云:“黄虀碎切,红豆、粉皮、山药片,加栗黄尤佳。五味拌打拌搦饀包。”④[元]熊宗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赓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饀”即“馅”,其实也就是酸馅之类。
所谓“黄虀”,或作“黄齑”,就是现在的酸菜。宋代朱敦儒《朝中措》词云:“自种畦中白菜,腌成瓮里黄齑。”⑤[宋]朱敦儒:《朝中措》,《朱敦儒集》卷中,洪永铿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明白告诉我们当时人用瓮腌白菜制作黄虀,与今日腌制酸菜无异。《农桑辑要》所谓“加火煮之,以水淘浸”指的是酸菜的腌制过程。清人丁宜曾《农圃便览》“酸菜”条云:“用肥嫩白菜稭少煮,不可太熟。取岀冷透,入礶內,温小米饭清汤浸之,勿太热;不用盐。才酸便用。陆续添汤、菜,可竟冬食。”⑥[清]丁宜曾:《农圃便览》,王毓瑚校点,中华书局,1957年,第77页。其要领与宋元时代的制作工艺无根本改变,而于火煮火候、淘浸方法记述差详。
“虀”同“齑”,《周礼·天官·醢人》“以五齐”,郑玄注:“齐当为齑……凡醢酱所和,细切为齑。”⑦《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六,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简单说来,可指酸菜、咸菜、酱菜等腌制食品。酸菜腌制中,绿色素被破坏,呈现黄色,故名“黄虀”,今人缘其色、味,俗称黄菜、酸菜。黄虀又称“淡虀”,一来因为酸菜制作过程中“不用盐”,与其他腌制食品迥异;二来酸菜适宜与脂肪丰富的肉类一同烹饪,以改善口感,而贫民仅取其廉价,无油水调和,则味道难免寡淡——此“淡虀”之“淡”,近乎梁山黑旋风李逵之“口里淡出鸟来”。黄虀味酸,古人常说“酸黄虀”。元杂剧《玉清庵错送鸳鸯被》第四折中有【沽美酒】云:“则他这酸黄虀怎的吃,粗米饭但充饥。”⑧[元]无名氏:《玉清庵错送鸳鸯被》,《全元戏曲》卷六,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王实甫《北西厢记》第五出【叨叨令】云:“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糁。酸黄虀、烂豆腐,休调淡。”①[元]王实甫:《西厢记》,见《六十种曲》(四),毛晋编,中华书局,1978年,第28页。明代郭勋《雍熙乐府》卷三第二十九首【端正好】中也有“酸黄虀、烂豆腐”②[明]郭勋:《雍熙乐府》卷三,明嘉靖刊本,《四部丛刊续编·集部》(78),上海书店,1985年。的俗语。酸黄虀、烂豆腐、粗米饭并提,显然三者都是廉价的素食,尤其前二者,更都因发酵带有异味。
酸馅用黄虀包成,所以文献常把酸馅与黄虀、淡虀并提。元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牧羊关】云:“‘虽然是食酸馅,捱淡虀,淡只淡,淡中有味。’”③[元]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全元戏曲》卷三,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明代王衡《郁轮袍》杂剧第六折【驻马听】云:“那壁厢百种针槌,道我斋头酸馅瓮中虀。这壁厢齐声赞美,又道我眼能说话手能飞。”④[元]王衡:《郁轮袍》,《盛明杂剧》卷二十,沈泰辑,民国七年至十四年武进董氏诵芬室刻本,第22页。这“酸馅”和“淡虀”、“瓮中虀”都是一套东西。
宋代人开始制作酸菜。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检索“酸菜”、“淡虀”、“黄虀”、“黄齑”,得到的结果与检索“酸馅”相似,全是宋代以来资料。有了关键食材酸菜,酸馅这种面点食品便在宋代应运而生。
(三)酸馅的制作与食用
《武林旧事》早说过,酸馅属于“蒸作从食”,是蒸出来的。明代无名氏《度黄龙》杂剧第三折,正末“袖中倒出蒸食四个科”,云:“您众人看,这个是扬州琼花,这四个酸馅是琼花观斋食也。”⑤[明]无名氏:《度黄龙》,见《孤本元明杂剧》(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10页。这条材料,可以证实明代的酸馅也是蒸食。
但是酸馅也可以烤着吃。酸馅有一种形态,名曰“焦酸馅”,或曰“燋酸豏”。
《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中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伊永文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312~313页。
”燋",古同“焦”,从火焦声。《周礼·春官》曰:“以明火爇燋。”⑦《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8页。“燋酸豏”即“焦酸馅”,当是以火炙烤过的酸馅。《东京梦华录》说此物在夜市出售。《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亦云:“又有夜市物件……木檐市西坊卖焦酸馅、千层儿。”⑧[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0页。有关“焦酸馅”的记载不多,而都与夜市相关,很可能这种食品和今天的地摊烧烤一样,基本只在夜市上出售。至今开封尚有“马道街”,地处繁华,长年累月,夜市无间,所卖食品亦多有烧烤类,其情形与《东京梦华录》中“马行街铺席”的状况仍极相似。
话本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夜里三更时分外出买“焦酸馅”,正可以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相印证。烧烤可以提升面食的香味,使之外焦里嫩,增加口感,故而小说中说宋四公买到的“焦”酸馅“又香又软”。
做酸馅,无非面皮和馅心。
宋代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面茧,以肉或素馅,其实厚皮馒头、酸馅也。”⑨[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13页。“厚皮馒头”和酸馅并举,可见宋代酸馅面皮比一般馒头更加厚实。
元代熊宗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云:“(酸饀)馒头皮同,褶儿较粗,饀子任意,豆饀或脱或光者。”⑩[元]熊宗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赓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这说明,元代酸馅也类似馒头,只是面皮上的褶儿比馒头上的粗。
元刻本《新刊的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寨儿令】:“是谁家些贤妇女,孝儿郎?准备的正齐拖拽着谎,糖饼儿香,酸饀儿光,村酒透瓶香。”⑪[元]武汉臣:《新刊的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全元戏曲》卷二,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55~656页。所谓“光”,与馒头、包子等白面细粮制作的面食蒸熟后的表皮特征相符。
《梦粱录》有“肉酸馅”,然而酸馅的主流渐渐趋于素食。酸馅自产生以来,便常被僧人用作素斋食用。见于宋代载籍的有:
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云:“方其(僧道楷)死时,招聚大众曰:‘汝等偕来,尝吾大酸馅。’食竟,独入深山,久不出。众往视之,坐石上,已跏趺坐化矣。”①[宋]蔡絛撰:《铁围山丛谈》卷五,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91页。
2.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天仓洞”条云:“医人张世宁,先为僧,名法晕。”法晕曾到天仓洞,洞内“石床茶竈相连。就之略憩。或觉馁,思酸馅食,面前寻有一双酸馅。”②[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8页。
3.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解制日”条云:“七月十五日,一应大小僧尼寺院设斋解制,谓之法岁周图之日。”自解制后,“禅教僧尼,从便给假起单,或行脚,或归受业,皆所不拘。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诸宫观设普度醮,与士庶祭拔。宗亲贵家有力者,于家设醮饭僧荐悼,或拔孤魂。僧寺亦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家市卖冥衣,亦有卖转明菜花、油饼、酸馅、沙馅、乳糕、丰糕之类。卖麻谷窠儿者以此祭祖宗,寓预报秋成之意……”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页。
4.郭彖《睽车志》卷四,常州华严寺僧道良转世为牛,长老道素令寺僧“日以僧食啖之,酸豏至顿食五十枚。”④[宋]郭彖:《睽车志》卷四,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05页。
可见北宋时酸馅已成为斋食的主要品种。酸馅和僧人异常密切的联系,使它渐渐由一种食品转变为与僧人有关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一般人家斋僧,也常以酸馅为供。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的一则趣味为例:宰相章惇宴请一位“行解通脱,人以为散圣”的僧人净端,章惇吃荤食馒头,净端吃素食酸馅。仆人“误以馒头为酸馅,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而章惇则吃到了酸馅,“知其误,斥执事者,而顾端曰:公何为食馒头?”结果,“端徐取视曰:乃馒头耶?怪酸馅乃许甜”。⑤[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
同为面食,馒头多是肉馅,而明清两代所见的关于酸馅的记录,几乎均为素馅。时间长了,人们忘记酸馅的本意,便以为酸馅只能是素食,甚至将它等同于菜馅馒头。清代刘墉在《以自制饽饽奉馈金圃并小诗请和并引》中说:“抟面蒸食,古以裹肉者为馒头,包菜者为酸饀。今则加以蔗糖,拌以果实,秦晋总谓之馍馍,燕齐则谓之饽饽,南方无专名也。”⑥[清]刘墉:《以自制饽饽奉馈金圃并小诗请和并引》,《刘文清公遗集》卷十二,道光六年刘氏味经书屋刻本,第8页。此即一例。
虽然《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说酸馅“饀子任意”,可是两件东西却不能少。这两件就是酸菜和豆馅。前文已引,“豆饀或脱或光”,但是最好用红豆。上等的酸馅用的是多种食材的混合馅料:“黄虀碎切,红豆、粉皮、山药片,加栗黄尤佳。五味拌打拌搦饀包。”⑦[元]熊宗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赓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馅料如此丰富复杂,可见酸馅是一道很有讲究的美食。
讲究的选料让酸馅不只是一种市井小吃。它还是一种节日食品。
宋朝在人日食用的“面茧”,实际上就是一种酸馅。北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面茧,以肉或素馅,其实厚皮馒头、酸饀也。馅中置纸签,或削作木书。官品人自探取以卜异时官之高下。贵家或选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途,然亦但举其吉祥之词耳。故欧公有诗云‘来时壁茧正探官’之句。”⑧[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13页。人日即农历新年的第七天,是唐宋时代重要的节日。宋时,在这一天会有相当热闹有趣的节庆活动,而活动的中心,就是这种面食。该习俗经过变形后,在明清以至现代有所保留,即在新年食用的饺子中置物以卜吉。
明代焦周《焦氏说楛》记载了各个节日应景的活动及食品,其中有“四月八,指天,酸馅”①[明]焦周:《焦氏说楛》卷五,明万历刻本。的说法。酸馅是明代佛诞日(四月初八)的应景食品。
二 从酸馅到“酸馅气”
苏轼《赠诗僧道通诗》自注“谓无酸馅气也”②[宋]苏轼:《赠诗僧道通诗》,《苏轼全集》卷上,傅成、穆俦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0页。,把食品酸馅带进了文学批评领域。“酸馅气”是个新奇的字眼,一经坡公拈出,遂而流行开来,其涵义不断扩展。
(一)“酸馅气”之本义由来
元刻本大都新刊关目的本《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尧民歌】云:“(带云)百姓每恰似酸馅一般,(唱)都一肚皮填包着气。”③[元]孔文卿:《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全元戏曲》卷三,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这则材料说明,酸馅这种面食制成之后,面皮内包裹着一团气体。究其原因,是酸菜馅含有因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在熟制过程中,气体受热膨胀,却又被面皮包裹,无法排出。僧人多食酸馅,酸馅外表饱满、内质酸陈空虚的特点,恰又与僧诗往往内容陈腐空洞的现象十分相似,因此被苏轼拉来作一雅谑。
此后,“酸馅气”一语固定下来,摇身变作一个重要诗学范畴,在文艺批评领域活跃了近千年。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④[宋]叶梦得:《石林诗话选释》卷中,樊运宽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5页。并举前引苏轼《赠诗僧道通诗》及注为例,给这一范畴做了界定。此后,“酸馅气”以及“酸馅”,都被用来形容由僧人创作,格调酸腐、意境凡近、内容及技巧缺乏创新的诗风。
“自作一种僧体”一语,是个具有很高价值的理论突破。宋人开始使用“体”的概念评价诗歌,叶梦得生活在南北宋之间,他使用这个概念,比主要活动在南宋理宗朝的严羽创作《沧浪诗话》早了百年左右。文学批评史在论定功绩时,观点应当改写。
“僧体”概念刚一诞生,便因富含“酸馅气”而带有浓郁的贬义色彩。清代张玉书编《佩文韵府》时,收录“僧体”,并引用《石林诗话》中的这段文字作解释。叶梦得的见解被后来的诗歌批评者广泛接受。后人评点僧诗,往往以有无酸馅气作为衡量标准。譬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称:“秀才作诗不脱俗,谓之头巾气。和尚作诗不脱俗,谓之酸馅气。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能脱此三气,则不俗矣。”⑤[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李东阳集》卷二,周寅宾校点,岳麓书社,1984年,第545页。此“三气”及不俗之说,在批评史上影响很大。又如明代杨慎评价元天目山释明本(号中峰)《九字梅花诗》曰“后四句有斋饭酸馅气”⑥[明]杨慎撰:《升庵诗话新笺证》,王大厚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816页。;清代沈涛《匏庐诗话》下卷评如皋诗僧默然《雪夜归山》、《初秋》两诗“皆无酸馅气息”⑦[清]沈涛:《匏庐诗话》下卷,《清诗话访佚初编》(三),杜松柏主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65年,第372页。;清戚学标《三台诗话》评价元代天台僧人子贤《题绿筠楼》、《寄敏仲谦于洞庭翠峰寺》等诗“皆极闳整,无些子酸馅气”⑧[清]戚学标:《三台诗话》,《全浙诗话》卷二十六,陶元藻编,俞志慧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707~708页。;清代祝德麟《赠长沙僧寄尘》诗云:“僧家学酸馅,习气良可鄙。”⑨[清]祝德麟:《悦亲楼诗集》卷二十九,清嘉庆二年姑苏张遇清局刊本,第8页。例子尚多,不必赘引。
(二)“酸馅气”适用范围的扩展
“酸馅气”本来专指僧诗。但是,在广泛的使用中,“酸馅气”的概念逐渐扩展,主要表现于三个层次。
首先,由评价僧人诗作扩展到评价僧人创作的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如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文部《赵吴兴真草千文后》云:“其结法遒紧圆润,工力悉敌,而波磔之际,往往锋铩中发异趣,酸馅之气为之一洗……”①[明]王世贞:《赵吴兴真草千文后》,《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六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将赵孟頫、智永两家真草千字文作比较,“酸馅之气”被移于评价僧人智永的书法作品。与之相类,清代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九则以“酸馅气”贬斥僧人怀素的草书:“怀素满纸恶习,始终是酸馅气,非士人本领。”②[清]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九,嘉庆二十二年陆贞一刻本,第36页。
在此类批评中,“酸馅气”和“士人本领”是两大对立范畴。“酸馅气”作为指代僧人的符号,对僧人、世俗作者二者加以区分,并作出贬义性的价值判断。
第二,由评价僧侣诗人平移到评价世俗诗人。如杨慎《丹铅总录》谓《水经注》所载古歌谣如《三峡歌》等“皆可以入诗材,胜俗子看《韵府群玉》,搜出酸馅恶料令人呕哕也。”③[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酸馅指代诗歌素材的熟常。清代魏裔介《朱公艾越游草序》云:“大约别才别趣之说固为知言,然非多读书则其识不高,而怀不旷。识不高、怀不旷,纵呕尽满腔血,终是酸馅气耳。”④[清]魏裔介:《朱公艾越游草序》,《兼济堂文集》卷六,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136页。酸馅气指诗歌格调不高、见解不精、风格常俗。
值得注意的是,当“酸馅”被移于评价世俗诗人,其含义即由僧人之口头禅习气转化为经生儒师的迂阔酸腐作风。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见于清代沈起凤《谐铎》卷三《穷士扶乩》:吴中穷士马颠为盐贾与诸名士扶乩,大受赞赏,待他将自己的诗稿呈给众人时,“诸名士才一批阅,曰:‘此穷儒酸馅耳,何足言诗!’连阅数首,俱言不佳”。⑤[清]沈起凤:《穷士扶乩》,《谐铎》卷三,乔雨舟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7页。酸馅和僧人的文化联系被抛却,使用者仅着眼于“酸”,并衍生出酸腐、穷酸等意义。
继而酸馅与儒生形象的联系固定下来,用以指代沉溺经学、迂腐拘执的冬烘。由此衍生出涵义扩展的第三个层次——
第三,由僧诗平移并扩展到世俗作者的其他文艺创作,即前两个层次的综合。最普遍的用法是文体间的平移借用,特别是常用于评价儒师经生酸腐迂阔的散文。清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五《评品》中说《孙明复墓志》“作经师文字,无酸馅气,立意高,用笔超也。胡翼之墓表精于史汉,故无庸腐铺贴诸病。”⑥[清]张谦宜:《评品》,《絸斋论文》卷五,清康熙六十年刻本,第11页。“酸馅气”的表现即“庸腐铺贴”,它和“立意高,用笔超”相对立,用于评价“经师文字”。这一涵义泛化之后,也可以指代“庸腐铺贴”的空话、废话,如清代彭士望《树庐文钞》卷十《论战国秦》篇云:“胜、广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死,又能择死,何事不成?其令徒属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侯王将相宁有种乎?’要言不烦,英英勃勃,觉后人吿檄俱酸馅气。”⑦[清]彭士望:《论战国秦》,《树庐文钞》卷十,清道光四年刻本,第18页。
在指代冬烘先生方面,“酸馅气”的近义语为“头巾气”。例如《明文海》卷二百四十,薛应旂《遵岩文粹序》云:“迨至弘德间,习尚旋流,识趣日溺。于是李献吉、何仲默各以文自负一时。人士尠有定见,亦遂翕然归之。何之言犹或近于理道,李则动曰‘史汉,史汉’,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⑧[明]薛应旂:《遵岩文粹序》,《明文海》(三),黄宗羲编,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481~2482页。将头巾与酸馅并提。头巾是明代秀才的服饰,在明人俗语中,“头巾气”通常指代经师,特别是宋代以来理学家令人生厌的板重面目。经师、理学家以为作文害道,其说经文字有一套固定化的话语体系,风格俗而琐,不符合“古文”的规范。故而郝敬《心丧记》论志墓文,即曰:“文人死,须文人作传;公卿大夫死,须公卿大夫题铭。乃为同调知己,轻车熟路,岂经生训诂酸馅语可充数也?”①[明]郝敬:《心丧记》,《明文海》(五),黄宗羲编,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642页。
在古文理论领域,“酸馅气”的概念曾被若干重要理论家运用,因此它受到比较广泛的接受。如明代唐顺之的理论名作《答茅鹿门知县》曰:“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②[明]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唐荆川文集》卷七,明万历刊本,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上海书店,1989年。像这样不经意的运用,说明“酸馅气”已是文学批评中的常用话语。
除散文批评外,“酸馅气”也适用于其他文体,或书法等艺术门类。例如在词学批评中,明代杨慎《词品》在评论冯伟寿《春风袅娜》词时指出:“殊有前宋秦晁风艳,比之晚宋酸馅味、教督气不侔矣。”③[明]杨慎:《词品》卷四,岳淑珍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页。即以“酸馅味”指代理学先生迂腐的说教气。又如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以之评价书法:“唐文皇以天下之力摹书法,以取天下之才习书学,而不能脱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脱僧气,欧阳率更不能脱酸饀气,旭、素、颜、柳、赵吴兴不能脱俗气。”④[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6992~6993页。僧人智永被归纳为僧气,而“酸饀气”则用于世俗官员欧阳询,可见在一部分明代人手中,“酸馅气”已断去了初始的基本涵义,而转化为酸腐板滞的代称。
Acid Stuffing and Acid Stuffing Gas Textual Research
Feng Shanshan and Tao Muning
“Acid stuffing”, commonly found in notes, story -tellers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refers to a kind of flour food and produced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It was used as festive food on Man’Day and called flour cocoon.In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used as offering on Vesak Day.It used acid sauerkraut as stuffing, so, people called it acid stuffing.It looks like a steamed bun, but the wrapper was more thick and the crease was bolder.Its stuffing could be meaty or vegetarian items.Many temples used acid stuffing as offering, so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ere was used to be vegetarian stuffing in it.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burned it to be hard and sold it in night market."Acid Stuffing Gas" at first means the gas produced in fermentation when the acid sauerkraut was heated.Su Shi is the first to use it as a poetry criticism category.It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monks’vulgar style lacking of innovation, vulgar, sour and old.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s range of application was expand to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critic, people’s temperament and so on, not only apply to monks.
Acid stuffing; Acid Stuffing Gas; Literary Criticism Category; Art Review; Su Shi
(冯珊珊,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陶慕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