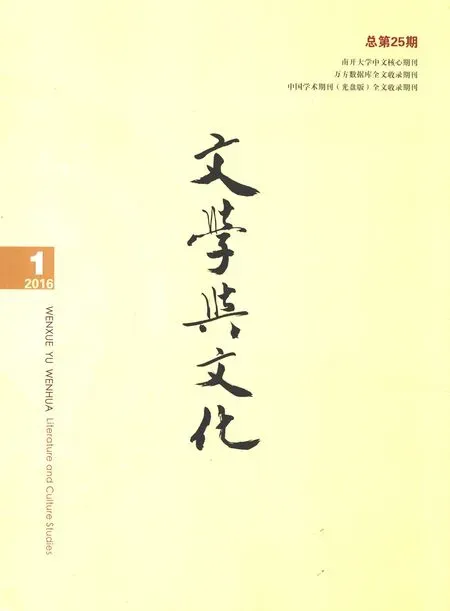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2016-11-25张斌
张斌
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张斌
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成绩:一是刘云若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二是刘云若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三是刘云若小说报载方式的得失。四是刘云若与张恨水创作之比较。总的来说,有关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
刘云若 小说创作 社会言情小说
刘云若(1903—1950)是民国时期社会言情小说写作的大家,在北方通俗文坛享誉盛名,时人称为“天津张恨水”。他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作品,生动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生活,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0年刘云若猝死后,这位曾在报界和文坛颇有名气的作家逐渐被遗忘。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亲人家属、并世友朋对其生平追忆文章,涉及小说创作特色、艺术价值的只言片语时或穿插其间。①此期相关文章包括:《张恨水与刘云若》(徐铸成)、《旧体章回小说家剪影——忆刘云若》(刘叶秋)、《我所知的刘云若》(吴云心)、《刘云若挥泪写章回》(李默生)、《先父刘云若》(刘美珠、刘美文)等。90年代,有关刘云若创作的研究依然少见,但其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开始受到肯定。1991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将刘云若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同年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将刘云若纳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视域。在这前后,还有《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范伯群,1989)、《鸳鸯蝴蝶派》(袁进,1994)、《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刘扬体,1997)从流派史的角度观照刘氏小说的风格、特色。世纪之交,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问世。该著为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设立专章,论及作品类型、情节技巧、人物塑造、主题思想、创作心态等不同方面,所占篇幅和分析的深度前所未有。此后,包括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在内的近十种文学史程度不同地提及刘云若②进入新世纪,论及刘云若的各类文学史还包括:《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张华)、《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谢庆立)、《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佘小杰)、《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中国现当代文学·第1卷 (五四—1960年代)》(黄万华)、《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范伯群)等。,其文学史价值得到确认,理论分析也有所深化。2014年,张元卿以钩沉刘氏生平、简介佚文佚作、短评作品内涵等为主要内容的读书札记和学术随笔性质的文集《望云谈屑》出版,该书为第一部刘云若研究专著。同期,有9篇硕士学位论文以刘云若作为研究对象。2015年,张元卿择其4篇辑为《云云编:刘云若研究论丛》。此外,有关刘云若生平的研究也为探讨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③刘云若的生平研究中,张元卿的《刘云若传略》(《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刘云若年谱简编》(《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等文章考证较为翔实深入。
迄今为止,有关刘云若小说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兹分述之。
一 刘云若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
首先是对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关系的考察。董秀婷《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①董秀婷:《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从天津地域文化对刘氏平民意识的培育、对其重传统与重情义的价值观和“逗哏儿”的审美趣味的影响以及刘氏展示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等三方面入手,揭橥天津地域文化与刘云若小说创作的密切关系。该文总结了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关系,对目前刘云若小说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基本共识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侯福志《〈小扬州志〉与津门演艺习俗》、倪斯霆《刘云若笔下的天津大杂院》、箫箫《刘云若笔下的“罗园”》②侯福志:《〈小扬州志〉与津门演艺习俗》,《天津记忆》第30期(《刘云若逝世甲子纪念集·天津通俗文学研究专号之七》);倪斯霆:《刘云若笔下的天津大杂院》,《旧文旧史旧版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箫箫:《刘云若笔下的“罗园”》,见张元卿、顾臻编《品报学丛·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等类似文化散文,不拘泥理论方法,更注重从刘氏作品的具体内容出发展示其地域文化细节,显示了论者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热衷、谙熟和以民俗学作为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出发点的治学旨趣。
相比之下,以下几篇论文探究刘云若小说地域文化特色时更注重文化阐释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孙玉芳《刘云若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③孙玉芳:《刘云若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见张元卿编《云云编:刘云若研究论丛》,2015年,第221页。在对天津城市空间、城市人物、城市情状进行较为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刘云若在理想天津与现实天津间不能自足的“城与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初步展示了作家与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陈艳《〈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④陈艳:《〈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将刘云若小说的“归哏”特色解读为“天津式幽默”,认为刘云若作为同时接受了中西文化影响的现代通俗作家,其小说的“天津式幽默”不仅源于天津本土的相声文化,而且与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现代幽默思潮及林译小说的“滑稽”成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肯定地域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思潮的整体观照下,考察刘氏小说“归哏”特色的“现代性”多元因素,作出了打破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理论隔阂的尝试。张元卿《地域特征与文学品格——北派通俗作家对天津的读解行为研究》⑤张元卿:《地域特征与文学品格——北派通俗作家对天津的读解行为研究》,《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页。从津门通俗小说家对天津城市的传统与现实的读解、市民话语和边缘写作的形成与确立等角度,认识天津地域文化对于津派作家群创作的作用和影响。在作者看来,刘云若面对天津这座城市的传统与现实持一种“厚古薄今的读解心理”,“这种基本的读解姿态支撑了他小说的整个思想框架和表达方式”。文章还指出,对市民话语的运用和边缘写作的策略凸显出刘氏在书写地域文化方面的贡献。这一研究超越通常对地域文化文学呈现的平面化梳理,深化了文学现象和城市特质间关系的探讨。此外,《刘云若论》⑥张元卿:《刘云若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107页。指出,天津的地域文化氛围造成了刘云若小说题材、人物、场景多有雷同、创新乏力等局限。闫立飞《“方志”书写与文学天津》⑦闫立飞:《“方志”书写与文学天津》,《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通过对刘云若小说《小扬州志》中天津民俗风貌与空间构型的考察,探讨《小扬州志》建立的“方志”形态的文学书写,认为该作品是建构文学天津这一城市文化文本的开端。该文通过文本现象把握刘云若以小说形式为城市治史立传的“史家意识”与“史志情结”,为探究刘氏小说与天津城市的关系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其次,对刘云若小说中天津城市人物进行梳理分析,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方面。近代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水运码头和工商业基地,不同地域、行业、遭遇的人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五方杂处的“杂八地”。刘云若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城市人物、尤其是底层市井人物十分关注,通过文学书写生动描绘了天津的城市人物谱系以及他们的生活、命运,勾画出天津人的精神轮廓和情感模式。
刘云若笔下的天津城市人物从位居上流的名士、报界从业者、资本家到底层挣扎的车夫、小贩、妓女、艺人、女招待、混混,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天津市民的面貌。有论者对此做过粗略分类①如《天津卫中的九流——试论天津地域文化与刘云若人物形象塑造》、《三津故地安乐,燕赵子弟风流——试论天津地域文化与刘云若人物形象塑造》两篇人物专论文章对刘氏笔下城市人物分类描述后,没能做进一步的内涵挖掘。,张赣生则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以“草莽气”②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概括刘氏小说中天津的底层社会生态和市井人物气质,认为这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刘氏文学天津和现实天津的精神肌理的重要方面。宾恩海《略论刘云若〈春风回梦记〈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理想》③宾恩海:《略论刘云若〈春风回梦记〉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理想》,《广西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则通过对《春风回梦记》中人物的文化形象的分析(如国四纯所代表的名士文化心态、底层市井人物“无极善极恶”的复杂性格与如莲所象征的善良、纯真、勇敢、坚毅的文化理想等),探讨刘云若的文化理想和其作品的文化品格,认为刘云若建立了诗气与悲意并存的文化品格。该文无意对刘云若小说城市人物做分类梳理,且文化释义也不囿于地域范畴,而是从更大格局的文化理想角度读解小说人物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这一比较开放的认知无形中反驳了以往认为通俗文学文化格调不高的成见,在重新定位通俗文学方面说服力较强。
混混是极富天津码头文化特色的特殊人群,对理解天津历史和地域心理意义别具。李国平《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④李国平:《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见张元卿、王振良主编《津门论剑录》,2011年,第395~407页。对刘氏小说中混混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天津特有的文化性格展开讨论。文章通过对护法掌班、吃软饭的混混以及女混混等各类混混的分类梳理,总结了刘氏笔下混混身上的无赖、不要命、讲义气等复杂的性格特征,由此指出刘氏小说除了具有言情的“脂粉气”之外,还兼具“江湖气”。
妓女形象是刘云若笔下各色人物中引人瞩目的一类。迄今尚无专文论述,但不乏相关讨论。长期以来,刘氏因涉笔青楼声誉不高,如左笑鸿的评论:“(刘云若)生活相当散漫,因而对娼妓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小说中有不少写到妓女的,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的拿手。”⑤左笑鸿:《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六十五)刘云若》,见魏绍昌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96页。较早对刘氏小说涉笔娼门给予一定程度肯定的是吴云心,他在《刘云若办〈大报〉写小说》一文中指出:“刘云若对天津中下层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平日谈论社会问题,也有他自己的见地,所写小说,每多涉及到妓女生活。但也有同情穷困妇女……实际上他也不是一个以专门写下流淫秽的小说为业者。”⑥吴云心:《刘云若办〈大报〉写小说》,《吴云心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92~593页。张元卿的思考视野更为开阔,他认为“‘妓女生活’作为底层生活的阴暗角落最易反映社会的兴衰,时风的变迁以及人性的善恶”,因此“妓女生活”对于包括刘云若在内的津门通俗作家来说是“对这个城市的读解的写作策略”。他还指出,刘云若与时人描写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刘氏“更注重通过对妓女身心两方面的入微描绘,反映其完整的人性”。⑦张元卿:《地域特征与文学品格——北派通俗作家对天津的读解行为研究》,《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10页。张元卿对妓业所承载的地域史、风俗史价值和刘氏探微妓女人性的理解,着眼于现代通俗文学有别于革命文学为主导的“翻身”、“解放”式女性叙事传统,强调了源自平民视角而非精英、政治视角的文学叙述与历史存真的另外一种逻辑和标准。
二 刘云若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
刘云若的写作成就和作品局限与其对通俗小说的技巧、形式的承继和创新密切相关,这也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刘氏文本实践中所具有的某些现代质素得到开掘。
其一,承继传统文学,制造情节波澜的艺术魅力。刘叶秋指出,“他在小说中所安排的情节,无不波澜叠起,意趣横生……”①刘叶秋:《忆刘云若》,《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范伯群则认为,刘云若《红杏出墙记》“情节之曲折离奇,令人手不释卷”,其“魅力的奥秘”“首先来自结构情节的技巧”。②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以上二者看到了刘氏小说情节波澜的魅力,但尚未深入探究其情节曲折的奥妙所在。钦鸿《略论〈春风回梦记〉的情节描写》③钦鸿:《略论〈春风回梦记〉的情节描写》,《绥化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在这方面有所弥补。该文具体探讨了刘云若小说的情节设置,不过基本止于对情节曲折、冲突错落的现象描述。张元卿《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④张元卿:《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23页。论及《小扬州志》综合运用了“背面敷粉法”、“横山断云法”等传统章回小说技巧,并着重分析了刘氏成功运用“草蛇灰线法”制造奇绝情节引起读者兴趣的作用。张赣生从刘氏小说形式特点深入到方法技巧,并且为这种方法溯源,认为:“刘云若小说的艺术魅力,还与他善于巧妙运用程式化技巧有很大关系。”⑤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具体说来,就是刘云若在设置人物、安排情节上借鉴了传统戏曲程式化的分行当的方法,其小说的基本格局建立在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基础上,并加以灵活处理。这样作者既能在起笔前通盘考虑情节安排,又使得每个角色形象都很鲜明。这种为现代通俗小说情节模式寻找原型的尝试,刘云若的好友景孤血早已为之。他指出刘云若小说结构“差不多都是两个旦角,一个小生,一个花脸”⑥景孤血:《〈粉墨筝琶〉序》,转引自张元卿《并世友朋的相知——简评几篇序文对刘云若的评价》,《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128页。,不过作为戏曲理论家的张赣生沿着这一思路论述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其二,在情节编排与情感烘托、故事叙事与心理刻画的关系处理上的匠心,亦即发挥小说人物情感的情节推动功能。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图示说明了《红杏出墙记》中由“循环纠结的情爱网络”构造的“人物—情节”模式,简略论及该著减少回目对小说情节结构与心理刻画关系的影响:“它把每回拉长到四万字(相当一般章回小说的四倍),以减少回目过多、而每回对子式题目又要求有两个情节高潮的限制,从而使颠倒错综、悲欢离合的情节得到充分的心理阐释。”⑦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51页。刘扬体在《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指出刘氏小说情节与情感、叙事与心理的关系处理对于通俗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认为:“刘云若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能把笔墨放在人物感性形象构成上,让通俗文学的叙事形态,在人物个性的心理深度上发生并不单纯依赖情节、乃至超越情节的变化。”⑧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90页。在情节冲突中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感情世界,人物往往走向“至性心态”,其“唤情意识”火辣强烈,故事的情节则往往跟着人物情感跌宕起伏。谢庆立《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一书对刘氏小说人物内心情感的叙事功能表述得更为明晰。该著指出:“在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中,‘人性’、‘情感’常常是驱使小说情节发生复杂变化的主要力量。”这种情感的情节驱动力,也就是刘扬体所说的人物心理对情节变化依赖的“超越”。但超越不是脱节,谢庆立还强调,刘云若把社会内容与“人性”、“感情”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将“人性”、“情感”引入到小说文本的情节建构中去,避免为展示社会内容而虚设情节,于是刘氏小说具有“万变不离其心”的情节结构特征。论者从叙事学角度看待刘氏小说的心理书写功能,并由此看到了刘云若在现代通俗小说流变中的革新意义:“一改过去社会言情小说的路径……在通俗社会言情小说的演变中,刘云若的大胆尝试,使社会言情小说能直逼新文学常常触及的人性、人情的深层处。”①谢庆立:《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页。对刘氏小说人物心理所具有的情节推动功能的明确认知,是突破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的理论壁垒的关键之一,也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以往只是与新文学作家相关联的先锋品格和现代性质素才能为通俗作家所“共荣”。例如吴福辉认为,刘氏小说呈现一种“探索性”,“而探索性正是先锋文学应有的一种品格”。②吴福辉:《刘云若言情小说自成经典》,《游走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这样的观点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的拓宽和评价尺度的多元。此外,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指出,刘云若小说用“出走”的情节模式拓展故事,将人物引入新境界。③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1页。虽然只是简单提及,却直击刘氏小说中普遍存在但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种情节模式。
其三,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如前文所述,杨义对刘氏小说的情节构造、人物心理与“减回”变革的关系做整体观照,是对刘氏小说的改良章回较早、较深入的认识。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简略论及刘氏依据情节需求,扩大回目内容,突破章回体制的限制。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2004年,第344页。对此理解和分析比较透彻的是张元卿的两篇文章。《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一文阐述了刘云若改良章回体的复杂状况,指出刘氏处女作《春风回梦记》第一回开篇全无旧章回体小说“且说”、“话说”的套话引子,“这表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但刘氏之所以在结尾又拿出了“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旧套路,说明他只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尝试创作,并且这种模式成为日后刘氏小说利用和改良章回的基本路子。⑤张元卿:《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57~59页。该文深入到刘氏“心路历程”看待其形式选择和文本实践,认为其小说“减回现象”的由来经历了一个文化市场检验的过程,在初试写作得到良好的市场反馈后,消除了谨慎和不宁,自如地利用章回小说的体式和技法而又不拘泥于章回小说的严格要求。文章还强调了刘氏改良章回中的不足,认为其作品呈现出“极驳杂的面目:似章回又不严格地分回叙事,似新小说又常有些旧章回体的陈词滥调”,说明此时刘云若的写作已不太用心,以致其小说整体质量大打折扣。《在章回体中“起舞”的现代性——刘云若论》从作家的思想认识层面探究造成其小说止步于改造章回而没能在文本实践中彻底脱掉章回外衣的原因,认为“除卖文为生,以一般读者为上帝,视市场文化需求为指针及长期写通俗小说的写作惯性外,最主要的是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局限和对社会人生的必然性的认识”。⑥张元卿:《在章回体中“起舞”的现代性——刘云若论》,见王之望主编《天津作家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有论者认为刘云若小说“说书人口吻贯穿于叙事中”⑦谢庆立:《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叙述者以采用古代说书人凌驾一切的权威口吻叙述”⑧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399页。,并对这种“说话人”角色持批评态度。与此相反,张元卿认为刘云若改造小说“说话人”具有创新价值。他以《小扬州志》和《冰弦弹月记》为例,深入分析了刘氏小说“说话人”向现代小说叙述人转型的努力,认为刘氏小说“说话人”“消解晚清以来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夸大,同时否定了‘说话人’作为史官、‘道德化身’的权威形象,把‘说话人’界定为现世中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完全恢复其世俗的一面”,由此“拉近了‘说话人’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同时“刘云若小说中的说话人却因刘氏的改造而具有故事亲历者或者不参与实践的无处不在的同谋的意味,这无疑强化了‘说话人’的叙事功能”。①张元卿:《在章回体中“起舞”的现代性——刘云若论》,见王之望主编《天津作家论》,第68~69页。在其看来,刘氏小说“说话人”与新文学作家的个性叙事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张元卿揭橥了刘氏小说“说话人”已具备了现代文学的三点要素——凡俗的人性、平视的心态、受限制的叙述视角。这样一来传统“说话人”摇身变为有血有肉、能憎能爱、活生生的现代社会的个体。当然,刘氏的创作文本未必全然符合这一判断,其著作等身良莠不齐,并非所有作品都能达到《小扬州志》的水准。
三 刘云若小说的报载方式
刘云若与同时代通俗小说家一样,“向来作品,皆先刊报端,而后归书局出版,从未直接为写作刊行”。②刘云若:《酒眼灯唇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页。报纸连载机制和文学市场化、商品化深刻影响了其小说创作,这也是引起较多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当前研究通常注意的是报纸连载小说机制对刘氏小说创作的限制和对其小说艺术价值的损害。有学者指出,报刊连载“这种写作条件也给刘氏的许多作品带来缺陷”③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例如鉴于读者的喜爱和报社的发行量与经济利益,《粉墨筝琶》续写的后半部分,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又如在编辑追稿太急、作者写作草率的情况下,《红杏出墙记》中一些人物的姓名、性格都出现了错误和偏差。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也认为作者“为着小说的商品利益而敷衍命笔”造成艺术伤害“实在令人扼腕”④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第199页。。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同样强调读者和编辑对作者小说创作的参与和指挥是通俗小说家刘云若身上的教训。⑤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461页。也就是说,通俗小说家对文学市场的迎合,对经济利益的迁就,往往会产生敷衍急就的心态,从而对作品的艺术标准有所放松,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则受到了损害。这些批评是符合实际的。正如刘云若在《酒眼灯唇录》自序中坦承:“此书数刊于报端,仅八月有奇,以期限迫近,乃匆匆结束,表面虽若完篇,实有头重脚轻之病,读者多为惋怅。”⑥刘云若:《酒眼灯唇录》,第2页。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市场病”,张元卿注意到文化市场、报载方式对于刘氏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认为包括刘云若在内的北派通俗作家对新文学所不关心的社会边角题材兴趣盎然并落实为文本的“边缘写作”风格,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群体游离于文学时代主潮之外,不必顾及宏大的文学思潮,“而可以从容地按照文学市场的规律自我调节自己的写作”,发挥文学表现日常生活和地域风情的功能。他在《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一文指出,刘云若比较完满地将商业写作和地域性有机结合,刘氏的成功表明“津派”通俗作家这一共同的艺术追求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特色写作虽然在50年代初就结束了,但其影响却很久远”。⑦张元卿:《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20、40页。应该说,张元卿看待刘云若小说创作与文学市场的关系是比较客观的。
此外,与小说报刊连载方式类似,刘云若的报业从业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同样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在现代社会渐趋发展的表征。陈艳《〈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⑧陈艳:《〈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除了对刘云若小说的“归哏”特色进行解读之外,还从报刊编辑经历的角度对其作出考察,认为编辑《北洋画报》的人脉积累和题材资源直接促成其由编辑向小说家转型,并且掌舵《北洋画报》的编辑思想与风格贯穿其后期小说创作始终。该研究凸显了现代媒体对刘氏通俗小说创作的意义。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小说家身份与现代媒体关系,也包括编辑经历对作家心态与成长的影响。
四 刘云若与张恨水创作比较
最先对刘云若与张恨水的创作进行比较的是郑振铎。据徐铸成回忆,郑振铎曾高度肯定刘云若的小说创作,认为“他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①徐铸成:《张恨水与刘云若》,《旧闻杂忆》(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0页。郑氏的评语被谈及刘云若的后来人反复征引。不过,迄今为止,局限于从孰高孰低的角度比较刘、张的议论较多,深入细致地辨析和对照二人创作模式、艺术风格的研究较少。
《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新论》一书在论述张恨水时提及刘云若的创作,这一角度本身就显现出对后者价值有所肯定,然而作者赵孝萱仅以《红杏出墙记》作为材料支撑,在几百字的有限篇幅内就判定了刘氏小说情节煽情夸张、人物情绪举止做作、有猎奇搜秘之嫌、多陈词套语、人物刻画平板、叙述者口吻张狂、极少写景笔墨,并讥讽“若说刘云若是‘天津张恨水’,未免让张恨水太过委屈”。②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第399页。其材料不足,结论也显草率。事实上,《红杏出墙记》虽因曾受到新文学大家肯定以及被改编为电视剧而名声大噪,但以其作为刘云若创作水平的代表未见得恰当。张元卿指出:“刘与张孰高孰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刘云若的文学史地位在于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模式外,另创了以‘诡异奇美’为特征的通俗小说新模式。”③张元卿:《在章回体中“起舞”的现代性——刘云若论》,见王之望主编《天津作家论》,第66~67页。也就是说,刘张比较应该建立在对二人创作模式与艺术风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他的《从“〈啼笑因缘〉现象”看刘云若小说的传播》④张元卿:《从“〈啼笑因缘〉现象”看刘云若小说的传播》,《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114页。一文从作品传播的角度比较张恨水与刘云若的影响与地位,指出除了作者的思想认识、文本的时代情绪等因素,媒体助力的悬殊也是刘云若不及张恨水的知名度和认可度的重要原因。张赣生从创作风格比较张恨水和刘云若的区别,认为前者偏重社会、比较客观、追求变化、更为写实,而后者偏重言情、比较主观、坚持风格、更为写意,这样就超越了“孰高孰低”的空泛议论。⑤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23页。范伯群在《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对比刘、张的艺术特点,指出刘云若不同于张恨水靠拢新文学,而是巩固自己风格,坚持“拿来主义”立场,保持了纯正“通俗味”,并且认为刘氏小说情节密度大于张氏,得益于细节描写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认为刘、张也存在一致性,即二人在艺术探索方面有着相似的困扰,比如自我复制,写急就章,作品参差不齐、虎头蛇尾、张冠李戴等等。⑥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2006年,第189~190页。
总的来说,经过多年实践,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有了一定的收获。与此同时,也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一是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发掘、整理还有较大欠缺。在几十年历史变迁和通俗文学被忽视的历史遭际中,刊载刘氏各类作品的报刊及其小说的民国版本很多都已散失,大部分研究通常只是围绕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版的包括《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十余部作品展开,缺少对刘氏创作整体面貌的观照。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其创作的全面把握,影响了视域的扩展和研究的创新。二是将刘氏小说作为文学文化现象进行平面化梳理比较普遍,研究深度不足。譬如,对刘云若小说中城市人物的分析多是按身份进行人群分类,但对各类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成因的深入分析不够,对群体内外人物的比较意识欠缺,对“人与城”的互动关系认知还比较模糊。三是研究视角比较单调。除前文提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通俗小说创作成就两方面之外,其他角度尚待开掘,比如对刘云若以文学书写呈现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动态转型的探究,又如对刘氏塑造的大量女性形象进行探讨并由此揭橥时代及刘氏个人的性别观念等等。总之,刘云若小说创作研究整体上仍处于初探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Survey on Liu Yunruo’s Novel Writings
Zhang Bin
From 20th to 80th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Liu Yunruo’s novel writing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in Liu Yunruo’s novels, artistic merits of Liu Yunruo’s popular novels, gains and losses of newspaper serialization for Liu Yunruo’s novels, and comparison of creative writings between Liu Yunruo and Zhang Henshui.On the whole, the study i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Liu Yunruo’s Novel Writing; Romance Novel
(张斌,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市文联干部)
文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