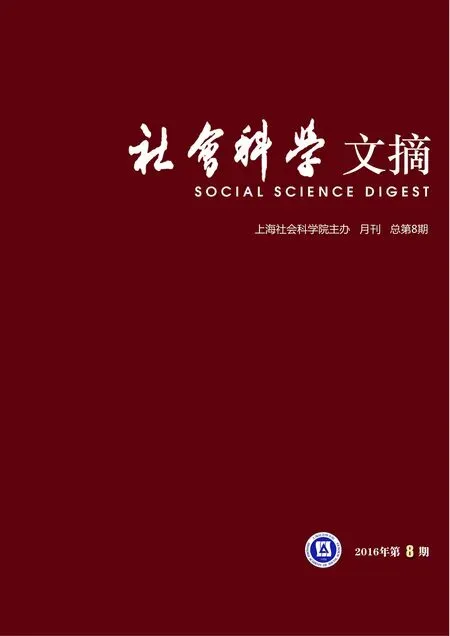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2016-11-25杨焄
文/杨焄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文/杨焄
锺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之中,激起后世不少非议。清人王士祯便直截了当地指出,陶潜“宜在上品”。这表明随着时代风气的递嬗,人们对于陶诗的评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在现代学术史上,“陶诗品第”的话题,再度引发海内外一大批学者展开讨论,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场争论促使学者从各个角度研讨《诗品》及陶诗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重新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也不难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重要特征。
从“宜在上品”到“本在上品”
这场争论最初起源于古直在1926年出版的《陶靖节诗笺》,书中提道:“考《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锺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是则今传《诗品》乃后人错乱之本,以此蔽罪锺嵘,嵘不任受矣。”古直对自己的新发现极为得意,在两年后刊行的《锺记室诗品笺》中,再次重申,就此正式揭开这场“陶诗品第”之争的序幕。
古氏之说甫出,立即得到很多人的赞誉和肯定。胡小石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中认为:“锺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随后叶长青在1933年出版《诗品集释》,在《导言》中说道,“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太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在中品“宋征士陶潜”条下也径引古直的意见。又隔了3年,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道:“《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锺嵘《诗评》(《隋书·经籍志》亦作诗评),原将陶潜放在上品。安知我们现在的传本,不是后人的窜乱呢?”这段评述也显然源于古说。庞俊在其《享帚录》中也述及古直《诗品笺》,“据《御览》卷五百八十六证明陶潜本在上品,今本《诗品》在下品者,乃后人所窜乱。此条尤精。大抵校注旧籍,要必有如此者数事,乃可谓有功古人耳”,不但称赏古氏发潜阐幽,甚至还将其著作奉为了典范。
古直依据宋人所编《太平御览》,有力地“证明”在《诗品》原书之中“陶公本在上品”。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这一“新发现”就迅速得到诸多同行学者的认可和接纳。可是,问题真的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吗?
是“后人窜乱”还是“明人妄改”?
既然“新发现”的主要依据来自《太平御览》,就有批评者对此进行追究复核。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在论及《诗品》中陶潜的排名时发现“通行本《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列上品,但宋本仍列中品”,可惜只提到《太平御览》的通行本与宋本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孰是孰非并未给予明确评判。汪辟疆在《读常见书斋小记·明人妄改〈诗品〉》中,通过比较《太平御览》传世诸本的引录情况,判定古直所依据的并非宋本,而是明清以来的刻本;并进而推断将陶潜列入上品诗人的名单之中,只是明人在刊书时妄改古籍所造成的结果。
依据宋本和通行本《太平御览》之间的差异,似乎很轻易就能将古直驳倒。不过古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疏漏,实属情有可原。罗根泽、汪辟疆提到的宋本《太平御览》,要迟至1935年底才由商务印书馆根据日本所藏宋本予以影印出版。此前在中国本土流传最广的是嘉庆年间的鲍崇城刻本,并没有完全呈现宋本原貌。由此看来,即便古直在立论时所凭借的《太平御览》只是明清时期的刻本,在当时也是迫不得已,对此应具了解之同情。况且,古直做出那样的误判,也属事出有因:一方面,极有可能误以为鲍刻本体现的就是宋本的原貌;另一方面,无论是鲍刻本还是宋本,在开列《诗品》上品诗人的名单之后,紧接着都征引了其中5位诗人的评语,在曹植、刘桢、张协、阮籍等4位上品诗人之后,就是陶潜条的评语。这样的征引方式本身就容易滋生出误解,令人产生了不应有的联想。
汪辟疆与古直意见相左,但就研究方法而言,双方其实并无差异,都是借助宋人所编类书来进行考察。这种方法先天就存有缺陷,因为就算是宋刻善本,《太平御览》的编纂距离锺嵘撰写《诗品》之际也已相隔近500年,站在古直等人的立场,完全可以反唇相讥:即使陶潜的姓名未见于宋本《太平御览》所开列的上品诗人名单,“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
晋宋诗风与《诗品》义法
仅据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陶公本在上品”,显然未必行之有效,因而另有学者尝试从晋宋之际的创作、评论风气入手进行研讨。例如汪辟疆又曾结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述晋宋时期的创作风尚,以及颜延之、萧统等人表彰陶潜的重心所在,分析陶诗风貌迥异于时风;而《诗品》对于陶潜的评价也明显带有节制,“其有意抑扬,语有分寸,亦未可与上品曹植、谢灵运诸家平品之语等量齐观也”,联系整个时代的风气嬗变来考察锺嵘对陶诗的认识。逯钦立在1947年发表的《锺嵘〈诗品〉藂考》中也同样认为,“锺嵘为评,实难列之上等,何者,世俗嗜好之所限也”,强调陶诗虽受后世尊崇,但在当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而锺嵘绝无可能将其置于上品。
汪辟疆、逯钦立等从大处着眼,避免以偏概全的一隅之见;但其前提是锺嵘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必须服从顺应晋宋时期的诗坛风尚。这也容易遭到对手的质问:难道锺嵘就不能挑战当时普遍的审美观念?因此,由最初的文献复核转向对时代风气的考察,依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从《诗品》自身寻找内证,来验证“陶公本在上品”之说是否可信。许文雨于1938年出版《锺嵘诗品讲疏》,针对古直有过直接的批驳,其中一点尤其值得重视:“案本品所次,历受人议,实则记室绝无源下流上之例,故应、陶终同卷也。”他强调锺嵘既然认为陶诗“源出于应璩”,而应璩被置于中品,因此陶潜绝无可能躐等而跃居上品。同样注意到锺嵘在推溯源流时应该遵循某种规律的还有王叔岷,他在1948年发表的《锺嵘评陶渊明诗》中说:“锺嵘既谓陶诗源出应璩,应诗列在中品,则陶诗仅当在中品。列某人之诗于上品,而谓其源出于中品某人之诗,《诗品》无此例。故《御览》引陶诗在上品,疑经后人改窜,非《诗品》之旧也。”论述虽然稍显具体,不过因为尚未着眼于全书,所以还很难取信于人。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就直接对锺嵘推溯源流之举的可信度表示怀疑。而陶诗源出应璩本身又聚讼纷纭,一旦牵扯到这个话题,势必会引发其他的争议。
受到前述诸家批评意见的启发,钱锺书对“陶诗品第”的问题做出最为深入周详的考述。在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中,钱氏从文献校勘、时代风尚以及撰述体例三个角度,对“陶潜本在上品”的说法力予辩驳。在文献校勘方面,他指出“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在时代风尚方面,他认为锺嵘评诗“囿于时习而已”,都点到即止。其研讨重点主要放在探究《诗品》的撰述体例之上,他极为细致地归纳出《诗品》在推溯源流时所遵循的几条基本规则:“有身居此品,而源出于同品之人者”,“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上一品之人者”,“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若夫身居高品,而源出下等,《诗品》中绝无此例”。最后再根据这些撰述体例,重新考虑“陶公本列上品”的问题:“使如笺者所说,渊明原列上品,则渊明诗源出于应璩,璩在中品,璩诗源出于魏文,魏文亦只中品。譬之子孙,俨据祖父之上。……恐记室未必肯自坏其例耳。”他首先统观全局,条分缕析地总结出《诗品》的体例义法;然后以此为参照,细致梳理由魏文帝曹丕至应璩再至陶潜这一系诗人的承传关系;又辅以文献校勘、时代风尚等相关证据,最终彻底批驳了“陶公本居上品”的谬说。
余波不断的论争
在钱锺书论定“陶诗品第”之后,“陶公本在上品”的谬说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不少人信从。尤其是陈延杰的《诗品注》,进一步扩散“陶公本在上品”的错误。陈著早在1927年就已出版,虽然认同陶潜“宜居上品”的看法,却并未怀疑《诗品》曾遭篡改。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氏着手修订旧著时,却增补了一段内容,指出《太平御览》所引《诗品》上品诗人名单中有陶渊明。这个意见无疑承袭自古直,只是未能明辨是非,导致后来众多研究者受到误导。汪中在60年代末出版的《诗品注》也存在类似问题,他虽然参考过许文雨《诗品讲疏》等论著,但在陶潜条中依然征引古直《诗品笺》的说法,隐约可见他对争论双方的取舍态度。陈延杰、汪中等显然都没有留意到钱锺书的意见,这或许是因为钱锺书在当年学术界的声望,还远远不如后来那样足以形成马太效应,以致《谈艺录》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此外,《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6月,虽然次年7月又曾再版,但直至1984年才得以补订重印,其间近40年的空白也使得其他学者鲜能参酌其论说。
当然,自5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在继续批驳“陶公本在上品”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一些海外汉学家。日本学者中沢希男在《〈诗品〉考》中认为《太平御览》的“‘陶潜’二字恐为后人窜入”。他对《太平御览》中所说“十二人”是否包括“古诗”也颇有疑问,大胆推测“十二人”或为“十一人”之误。韩国学者车柱环在《锺嵘诗品校证》中据影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古直,同时提出所谓“十二人”应当包括创作《古诗》的无名氏在内,使得具体名单和人员数字能够对应,无形之中也回应了中沢希男的疑惑。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锺嵘诗品集校》中也对古直持批评态度,在利用影宋本《太平御览》并联系时代风气进行研讨之余,同样注意到如果把陶潜置于上品,则名单中的人数将达到13人,而非12人。综观上述各家论说,虽然关注到名单人数的问题,但终究无关宏旨,主要证据并未超出前人范围,而且也都没有注意到钱锺书《谈艺录》中的论述。
另有一些学者则集中研讨“陶诗源出应璩”的问题,如王叔岷在《论锺嵘评陶渊明诗》中提出:“锺氏所谓‘源出’,乃就体裁相似而言。……陶诗非仅体裁与应诗相似;即词句、命题,有时亦受应诗影响。”王运熙在《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中认为,“《诗品》谓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是说陶诗的体貌源于应璩”,并进一步分析两家诗歌的共同特色。虽然并没有直接涉及“陶诗品第”,但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诗品》体例义法的领会。
整场论争的真正终结则要等到80年代中期,随着《谈艺录》补订重印,特别是钱锺书的学术地位日渐提升,他在40年前针对“陶诗品第”问题的论述才重新为人关注,在学界中才逐渐形成共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此落下帷幕。
从“陶诗品第”之争看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型
重新回顾这桩公案的因果始末,对于审视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迁变,带来不少耐人寻味的启示。参与这场辩论的学者前后有20余人,而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这场论争的深入展开颇有影响。例如钱基博与叶长青同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先后发表议论而又观点相左。叶长青早年从学于陈衍,陈衍所撰《锺嵘诗品平议》在当时极有影响,叶长青在无锡国专时讲授过《诗品》,与其师承渊源当不无关联。而陈衍对钱基博之子钱锺书又格外赏识,在与钱锺书闲谈时曾提及叶长青“新撰《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见《石语》)。由此可见,钱锺书后来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立论时又能别具卓识,除自身天资过人、博闻强识之外,既得益于家学熏染,又受惠于交游闻见。
以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学术机构则为这场争论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极佳的平台,使得诸多参与者既能各守专攻,又能切磋交流。除了钱基博与叶长青同时在无锡国专任职之外,古直与方孝岳均在中山大学任教,胡小石、汪辟疆、陈延杰和罗根泽都在中央大学共事,逯钦立与王叔岷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学、共事;伍叔傥则相继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任教,和古直、胡小石、汪辟疆、王叔岷等学者都有过学术交流。绝大部分学者还承担着教学任务,陈延杰《诗品注》、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叶长青《诗品集释》等原先都是授课的讲义。个别受教的学生之后也陆续参与到争论之中,例如韩国学者车柱环曾受知于王叔岷等人,其《锺嵘诗品校证》深得王氏赞赏。跟随车柱环研习过《诗品》的另一位韩国学者李徽教,在60年代末又至台湾大学攻读硕士,在其学位论文《诗品汇注》中也曾依据许文雨、王叔岷、车柱环的论述,继续批驳过古直。这些学者在无形中构成了一张异常复杂的关系网,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的学术共同体。彼此援引发明,相互质疑问难,使得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具备良好的互动机制,极大促进了研究的深入细化。
通过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论争,还可以发现在从传统诗文评转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也在逐步发生相应的转变。相较而言,传统诗文评注重赏鉴体悟,更偏于感性;现代学术研究则强调评析裁断,更趋于理性。虽然近现代以来学术风气丕变,但传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式还是凭借强大的惯性,延续到以大学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机构之中,对于身处其间的学者带来很大影响。作为最重要的现代学术机构,大学固然能为学者们提供良好的专业研究场所,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就这场围绕“陶诗品第”展开的纷争而言,大部分学者最初之所以更习惯于从文献考订入手,而相对忽视对《诗品》体例义理的阐发分析,与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应该也不无关系。
亲身经历过这场“陶诗品第”之争的学者,对此自然更有发言权。钱锺书在一篇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虽然充分肯定整理、考订文献资料的必要性,但又指出考据仅仅只是手段和途径,最终还必须把文学放在首要位置,将焦点集中于理论的剖析研讨之上。尽管这番议论针对的并不是《诗品》中“陶诗品第”的问题,但对于理解这桩公案背后所呈现的研究范式转型而言,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通过考察这桩公案的始末原委,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现代学术研究在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该已经远远超出了“陶诗品第”这个问题本身。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